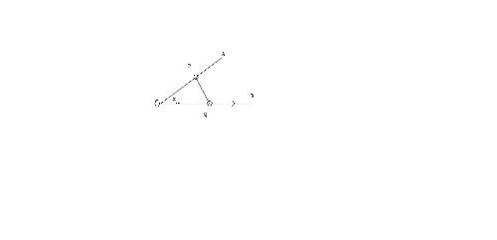30年代前半期,余叔岩隐退,言菊朋下坡,北方老生中顶梁的恐怕要算高庆奎和马连良了。像高庆奎这样的创派人物,材料很少,至今没有一本哪怕是薄薄的传记,这篇写起来也就有点难度。
云横九派浮黄鹤
高庆奎、言菊朋、余叔岩三人同庚,都是1890年出生。高庆奎的父亲是名丑高四保,也算梨园世家。高庆奎很小就学戏,幼功很好,12岁就开始上台演出了,在戏班里曾给谭鑫培配演过一些娃娃生的角色。
他16岁开始倒仓,没嗓儿了,只能给人跑龙套,当底包(群众演员)。他成名后也不忌讳这一段,常对人说:“我是从拎着靴包到处赶场走过来的,身上这点能耐,也是从跑龙套那儿攒起来的。”磨难和挫折没折了他成大角儿的雄心。那时,艺人出科(毕业)后,如果想再提高,就要拜名师,叫下挂。他选择下挂到贾丽川、贾洪林叔侄名下。
二贾是何许人也?贾丽川和谭鑫培是同辈人,世皆称贾二先生,他是王九龄一派的传人,戏路渊博,能教汪、谭、孙三派,门徒甚众。他侄子贾洪林外号狗子,当年红的时候,直逼老谭,败嗓后最擅做工戏,念白也精纯。老谭对他很佩服,晚年倚为左右手,在当时的二路老生里他是坐头把交椅的。高庆奎嗓子没倒过来,学贾洪林的东西正对路。当时马连良也下挂在这。可以说,贾洪林的东西是后来高、马两大流派的前源支流。
贾洪林(右一)演《桑园寄子》
高庆奎在贾氏叔侄的栽培下,除了老谭的,汪派、孙派还有贾家门自己的东西他都学,眼界渐渐开阔了。据说长江到了湖北江西交界的九江一带,加入九条支流,江面阔大,这一带的长江也称九派,老人家有“云横九派浮黄鹤”的丽句。高庆奎早期在众多流派的滋养下,开始一点点成熟,到后来自成一派,还要吸收更多其他派别的给养。
就这样到24岁,他开始正式搭班唱戏了,不过这时候他的嗓子还没有倒过来。这时候正是民国初年,北京名角如林,老谭等名宿还健在,资深一点儿的像王风卿、贯大元、王又宸等已稍有地位,余叔岩、言菊朋也露了头角。高庆奎觉得,要想在这强手如林的地方打出一方天地,非得从“观摩先进,培养观众”这两方面入手不可,那就只有多搭班,多上台。于是他定了一个“三不争”的原则:不争主角配角,不争戏码先后,不争份儿钱多少。这个风声一放出去,各班的管事人都觉得他谦退随和,纷纷约他搭班。于是别人在家闲着等邀角儿的时候,他却忙得不可开交,一天要赶几个场子。这样,他在台上有机会观摩名宿的剧艺,又能在台下培养观众缘儿,一步一步的,按照他的计划实践起来。现在看来,这个“三不争”既是低调的为人之道,也是高明的经营策略,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薄利多销”,靠更多的露脸和实践,获得更多的机会和经验值。
在他搭过的众多班社里,俞振庭、梅兰芳、杨小楼三人对他的提携之功最大。比如在俞振庭的双庆社,那时候梅兰芳正在窜红,是头牌。俞振庭着意让高给梅垫戏、配戏,在梅的新戏里,高几乎无役不兴,俨然成了梅党人物。梅兰芳那时候比谭鑫培还能叫座,观众最多,而在梅兰芳的观众心中,自然就有了高庆奎的地位了。
1918年,梅兰芳赴日演出,老生带的是高庆奎、贯大元。梅在日演出16场,每场都有高。《汾河湾》中扮薛仁贵,《天女散花》中扮罗汉,《霸王别姬》中扮老兵,《宇宙锋》中扮小太监等等。梅说:这次到日本演出,从北京请了个“百搭”来了,说的就是高。(所谓“百搭”就是麻将牌里的“混儿”)。
而就在去日本之前,他的嗓子也一下好起来了,比倒仓前更高更宽更亮,这真是一百个唱戏的里面也出不来一个的。他的艺术人生转向一片大好前途。到1920年就摆脱配角生涯,开始挂头牌了。又经过半年的挂头牌的日子,高庆奎认为自己声势已壮,基础已稳,从1921年起,就自己挑班了。
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十年,由搭班、演二路,到能唱正戏,再到挂头牌,直至自己组班,他凭着一颗雄心、耐心和虚心,循序渐进,扶摇直上。以后又跑外码头,大红大紫,一直到1934年倒嗓为止,轰轰烈烈地唱了15年戏。
晴空一鹤排云上
说高庆奎就不能不提刘鸿声,刘也是创派宗师。如果说贾洪林东西是高派的前源支流,那刘鸿声的东西则是高派的干流主脉。
刘鸿声是梨园界的异类。他比老谭稍晚一点,原来是个小刀铺的伙计,是票友,最初唱花脸,还给老谭配过戏,后来改唱老生,博采众长,汪孙谭都学,有人说他基本轮廓还是谭的(刘曾复),也有人说他的戏路接近张二奎一派(吴小如)。不管像谁吧,他的特点极其鲜明,就是能唱。他的天赋太好了,嗓子好得出奇,调门高得罕见,想怎么使就怎么有,爱怎么唱就怎么唱。从刘改演老生直到死前演的最后一场戏,他始终吃乙字调(上、尺、工、凡、六、正、乙,这七个调门是以前戏曲记录曲调的尺谱,相当于音符的从1到7。六字调是一般老生的常用调门,乙字调比它高两个调门,有些演员没倒仓前能唱这个调门,而刘则是终其一生不降)。因为本钱太足了,只要唱功多的戏他都敢唱,低腔也高唱,高腔更高,逢高必送到顶峰,而且音质清脆透明,人称“玻璃翠”。这就和谭派的东西不一样了,又杂上奎派、汪派、孙派的东西,渐渐的自成一派。观众听他唱的感到过瘾、解渴。他红得发紫的时候,谭鑫培也得揖让三分。
刘鸿声的《辕门斩子》戏词: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杨延昭下位去迎接娘来。见老娘施一礼躬身下拜,问老娘驾到此所为何来?
但刘鸿声的缺点也很明显,早年因病落下一点跛足,武戏和动作繁难的戏就动不了了。(不过据看过他戏的刘曾复说,在台上正常表演看不出来)而且,因为是票友出身,念白和身段也缺功力。即使是唱,也不能一高遮百丑。他的调门太高,走低腔反而成了弱项,还有个毛病就是唱快板时,节奏欠分明,旋律太单调,没有抑扬起伏,字音也囫囵不清,内行叫一道汤。
还是上面这出戏戏词:讲几个年幼人娘且听来: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太宰,石敬瑭十三岁拜将登台;三国中周公瑾名扬四海,十岁上学道法人称将才。十二岁掌东吴水军元帅,他看那曹孟德如同婴孩。在赤壁用火攻神鬼难解,烧曹兵八十万无处葬埋。这也是父母生非神下界,难道说小奴才是禽兽投胎?
字都被吞了,确实有点“连汤狗不涝”的,不写出戏词,谁能听懂啊。
1921年,刘鸿声在上海大舞台演完《完璧归赵》下场后,死在了后台。老天爷带走了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会再降下一个。高庆奎就是接班人。就是在1921年,他自张一军,独立挑班。那条当世无双的好嗓子,万众倾倒。
高庆奎亲眼看到刘鸿声当年,连老谭也要退避三舍。现在自己有了这个条件,自然跟踪而上。当时有人说他的嗓音,虽不及刘的清脆水灵,但刚劲挺拔有过之。刘当年的代表作“三斩一探”(斩黄袍、辕门斩子、斩马谡、四郎探母),高学得很像。刘鸿声唱腔的一个特点是气口少,拖腔长,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高也喜欢用长腔,不加休止,一气呵成。其实一个人的肺活量本没有那么大,但到底他在哪偷气换气,观众又听不出来,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本事。《逍遥津》所唱的导板“父子们在宫苑伤心落泪”和回龙“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只有两句唱,就将近三分钟,占了唱片的半面。特别是前面的导板,无论孙菊仙、刘鸿声,都没有高庆奎拖腔那么长。
“父子们”三个字一张口就让人觉得委屈得抑制不住了,之后连续用哭音,“在”音调往下拉,用的是哭音;“宫”慢慢往上揉,还是哭音;“院”用颤音,也透着哭腔,把内心的悲愤表现出来。开头这一句,就为后面的大段铺垫好了气氛。
高庆奎宗刘又有发展变化,把刘的缺陷扬弃了。他的快板比刘的节奏鲜明,铿锵有力,不像刘那么含混不清。另外,高还有两个特点是刘没有的。一是高派独有的“疙瘩腔”,后期经常使用。它和谭派的疙瘩腔不同。老谭的软,是像擞一样的颤音,而高庆奎的音符之间转换清晰,起伏明显,一个个的音符棱角分明。比如《斩子》中“见老娘施一礼躬身下拜”的“下拜”二字,用疙瘩腔,曲折委婉,煞是好听,反映剧中人复杂为难的心情。二是高在走低腔时比刘有讲究。还拿上一段举例子,下拜后唱“老娘亲架到此所为何来”,刘鸿声唱“为”字时用两个重复翻起的高腔,而高庆奎唱“为”字只使平腔,后面的“何来”也走低音,全是谭派劲头,反比刘唱得委婉有情致。(刘的这句可听前面的音频)
京剧里有一种翻高再翻高的唱法,叫“楼上楼”。在别人得攒足了劲,偶尔努一把,而对高庆奎来说只是家常便饭。开头“听说是”就是个高腔,表现了听说老娘来了心中一惊,到“老娘亲”委婉一些,见了娘不能再咬牙切齿的了,但“亲”字并不低,到“帐外”的“外”再翻高,就是楼上楼,老娘快进来了,怎么交待呢,心情自然激动。翻高也要符合人物感情逻辑的,不能乱卖嗓子。
1921年挂了头牌后,高庆奎眼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戏该怎么演。这时和民国初年相比,观众群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女性可以进戏园子了,大批年轻学生也挤进来了。当时老生里的余、言、马、麒等都在求变,就是谭小培也不是一成不变地按他老子的唱。高庆奎很自然地走创新的路子,虽然在京朝派的环境里长大,但他脑后的反骨大,对外江派的东西敢于、也乐于吸收。他对海派的艺术颇有好感,多次赴沪演出,和周信芳交流合作,砥砺身手。他还拜王鸿寿(三麻子)为师,学南派的关公戏。
高庆奎从1921年起挑班,班名庆兴社,后改名庆盛社,一直到他1936年辍演为止,演出的地点,以北平前门外鲜鱼口的华乐园(今天的大众剧场)为大本营。高庆奎的扮相,飘逸不足,敦厚有余,加之鹤唳九霄的嗓子,特别适合演悲苦激情的戏。刘派的“三斩一探”,是他常唱的。他不独有一条好嗓,由于得了贾洪林的东西,再加上多次去上海演出,和周信芳等南方艺人合作,做戏深刻、细腻,脸上、身上都有戏。
高庆奎的观众很广泛,士农工商都有,谁不知道高老板的戏听着过瘾、解恨呢?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和花脸郝寿臣合作阶段是黄金时期。那时在华乐园,每周有夜戏数场,还加演星期日白天,大都是满堂。当时挨着华乐园的小果局子(干果店)和小蜂糕铺,每逢高庆奎演出,都要门前排队。那时堂会又多,高庆奎能在一个昼夜唱三出《探母回令》(白天在戏院演,晚上赶两处堂会),精神饱满,气力充沛,同行也叹为奇迹。(倒想起纳达尔最红的时候,压过费天王,当时费身边的人就说,照纳豆这么不要命地打,伤病期就不远了。)这样的红火局面,持续数年,那扶摇而起的气势,真像晴空一鹤直上云霄。随着火候已足,高庆奎开始自立门庭了。
高派的特色,除了上面说过的那些,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杂糅百家,自成一家。当时京城的梨园界送给他一个绰号:“高杂拌儿”。杂拌儿是北京的一种小吃,其实就是干果拼盘,蚕豆、花生、桃仁、柿饼、糖球……怎么拼都行。这当然不是好听的话了,意思是东西大杂烩,不精纯。在北平,有些自命为正宗的听戏行家是不听高庆奎的。
高本人对这个“杂拌儿”的恶名,也有个态度:“我是唱二三路班底出身的,过去什么好角、什么派我都见过,我也陪着唱过。我演戏没那么多死规矩,谁演得好,我就学谁,谁的玩意儿适合我的路子,我就拿过来试试,好了我就用,不好我就扔。这样我的戏路能不杂吗?能够成个杂拌儿的流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叫由人家去叫,我好自为之。”据说高庆奎和余叔岩关系很好(我想两人风格和观众群不太重合,不在一锅里抢饭,倒是能处好),有一回去饭馆,上了一个菜是烩杂拌儿,同桌的陪客先动了筷子,还念叨,我就爱吃杂拌儿。余用筷子捅了他两下,暗示禁言。高看到后哈哈大笑,对陪客说:不碍事,我也最爱吃烩杂拌儿了,里面什么都有,哪样对胃口就拣哪样吃。
高的杂,反映了他善于融汇、革新,也是他能自成一派的原因。他的杂,第一体现在新编剧目多。民国初年梅兰芳刚开始走红时,就孕育了编排新戏的思想,1912年第一出新戏《孽海波澜》就是梅、高两人合作的。之后每年编些新戏,大红大紫。有样学样,慢慢的大家都竞排新戏,一新耳日。高庆奎也不例外,像《浔阳楼》、《哭秦庭》、《史可法》、《煤山恨》、《赠绨袍》等都是他的首创,也成了高派的代表作。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能在国难当头的大时局下,编演了《史可法》、《战睢阳》、《煤山恨》这些反应王朝末路的新戏,《杨椒山》一剧因台下反响极大,甚至遭到当局干扰。这就不只是创新精神,更有一层爱国情怀在里面了。
《煤山恨》高庆奎饰崇祯,他的儿子高盛麟演小皇儿
高的杂,第二体现在宗法的流派不一,即使他演某一派专擅的剧目时,虽以这一派为基础,但同时也兼采别派的唱腔和|唱法。前面说过,高庆奎主要作为做为刘派传人,但他会的多、见的广,汪、孙、谭、贾、三麻子的东西都有。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学的扎实、钻的深刻,化用各派的东西,仍然是有规矩可寻的,不是无中生有,生编硬造,观众看着也能顺眼,听着也能顺耳,没有牵强生硬、离奇怪诞的感觉。也就是说,杂糅了百家,最终还是化成一家了。
《煤山恨》的这段“三眼”就有南派唱法,有麒派《追韩信》唱腔的韵味,表现了一种失望无奈的情绪。比较一下两段:
煤山恨戏词:并非是我朝中无有能贤。最可叹周遇吉身带乱箭,最可叹栋梁臣与共大难。到如今孤有泪皇天明鉴,哭也枉然,箭刺心穿。
追韩信戏词:天降下擎天柱保定乾坤。全凭着韬和略将我点醒,我也曾连三本保荐于韩君。他说你;出身低贱不肯重用,那时节;怒恼了将军,跨下了战马身背宝剑就出了东门。高的杂,第三体现在他爱反串。他反串,不是玩票,完全按正规的戏路子演唱,内行看了也能认可。有个小故事。1930年,他的庆盛社贴演《连环套》,高庆奎反串黄天霸,马富禄反串朱光祖。梨园旧规,演员要有师承,才能吃这碗戏饭,没拜过师父不成。这个行规一方面表示尊师重道,更主要的是约束各行当的人安守本行,别捞过界了,得让别人也有口饭吃。高庆奎喜欢反串,如果在年终封箱戏偶一为之,倒也不算违规。但是高庆奎甭管什么时候,一高兴就反串,老旦、花脸、武生什么都唱,班中那些本行演员,早已不耐了。但碍于他是班主,是老板,又不好直接发难,所以就冲着本来是文丑,这回却反串武丑的马富禄了。班里的诸多人暗中筹划,单等马富禄一进后台,当家的武丑傅小山立刻从他头上把朱光祖的鬃帽抓下来,质问他为什么文丑擅动开口跳的戏,违反行规,欺师灭祖。所有后台同仁都异口同声。马富禄哪见过这阵势,吓傻眼了。高庆奎明知一半是对着他的,毕竟理亏,也不敢出来说话,默默地躲开卸装去了。结果是有人出面缓颊,安排马富禄第二天拜傅小山为师,大摆酒席,破财消灾。当时成了北平梨园界的大新闻。
其实,高庆奎的反串,不单是过戏瘾,还有博彩众长的一面。他把一些老旦方面的造诣就化用到老生戏中来。还说《逍遥津》那个著名的导板“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一句,既不是孙菊仙也不是刘鸿声的唱法,而是把老旦龚云甫《游六殿》中的导板“刘清提站都城兢兢战抖”一句的长腔搬过来的。
华亭鹤唳讵可闻
1934年底,高庆奎的嗓子突然发病,暗哑得一字不出。关于病因,有多种猜测,有的说是早年的病积至壮年复发,毒火延及喉咙;有的干脆说是喉癌;还有的说是被人下药暗害。他不得不辍演在家,徐图休养。那穿云裂帛的鹤唳,毕竟不是祥音。天道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虽然高庆奎
本人谦退和善,但那样高亢的声音终究不能长久。从自然之道,开掘使用太过,就容易出毛病;从人世之道,那样一条好嗓子,难免遭人嫉恨。总之,老天给了你一样超乎寻常的禀赋,也会在这
上面再给你找些麻烦,不会让好者恒好,坏者常坏的。
经过德国医院的医治和调养,到1936年,高庆奎的嗓音略有恢复,而且再不唱生计也成问题了,就在这年端午节前夕,他和筱翠花、袁世海贴演《浔阳楼》。这当然成为轰动一时的消息,大概比这段日子王菲复出还要引人注意。据袁世海回忆:高先生出场刚在幕内念出一句“列位,少陪了”,我的心就咯噔地沉下来,险些“哎唷”一声喊出口,怎么嗓音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高亢、嘹亮,变得干涩、沙哑啦?后台的人们也都惊讶地竖耳静听。老先生上场后,“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等几句四平调,几乎堕入无声地演唱。到我刘唐上场,和宋江酒楼会面,老先生完全失音了,全凭眼睛、手式、动作与我对话,不惜力地凭借动作、神情将戏演下去。我望着老先生脸上滚落的黄豆粒一般的汗珠,能理解此刻他该多么焦虑。而我只能竭尽全力地放开喉咙,让观众听清我的唱念,以协助他们理解宋江的无声表演。观众的情绪、态度更令我感动。面对舞台上的半哑剧表演,他们竟能长时间地屏气而看,不叫倒好。逢老先生表演到精彩之处,仍报以掌声。
这之后,高庆奎知道祖师爷不再赏饭吃了,在台旁贴条儿,次日《史可法》回戏,退回预售票款,从此刚强地谢绝了舞台。从1938年起,就在北平戏曲学校以教戏为生。
1940年冬,他的女婿李盛藻受聘演出于上海黄金戏院,请他随行把场。上海是他当年成名的地方,旧地重游,忆谈往事,长夜不疲。演期将满时,有一场义务戏,戏院经理看他生计困顿,请他在大轴的《扒蜡庙》里演一场“握刀过场”的褚彪,露露一代名伶的眼目,可以得酬千元。他却婉言谢绝:“我当年以好嗓子驰名海上,今天一字不出地蒙哄观众,知我者悯,不知我者谇。丈夫不受人怜。我虽如涸辙之鲋,也只能望洋兴叹了。”(这最后一句真叫人感慨不已啊!)
“我高某人平生也没有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偏偏老天爷把我嗓子毁啦。”这是他和同行说的。伶人毁嗓,如同音乐家失聪、学问家失明、政治家失势一样难熬时日。高庆奎最后的几年,可以想见的积闷怅惘。已成“涸辙之鲋”,离最后的日子就不远了。1941年,病情恶化,咽喉红肿不能进食而卧床不起。1942年2月4日,高庆奎故于北京烂熳胡同七十八号寓所。
高庆奎
高派要求有一条好嗓子,不易传习,很难成为大宗。高庆奎的弟子只有白家麟、李和曾。白以唱红生为主,偶尔唱老生。李和曾得到的真传不少,高派戏大部分都会。毛泽东很喜欢李和曾的戏,“文革”后期,李被管制期间,还被抽调给老人家录制影片。看来以老人家革命家的气质,喜欢高派这种高亢激昂的风格。妄猜一句,估计在越剧里,他应该会喜欢徐派,不知在强手如林的越剧小生界,最后徐玉兰出演贾宝玉,是否与此有关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