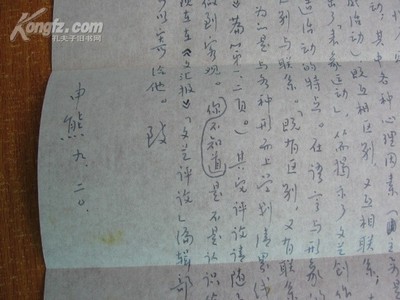《小姨多鹤》的故事梗概:十六岁的日本遗孤多鹤,抗战胜利后,被卖到了东北某火车站站长家,成为张俭(二孩)传宗接代的“工具”,因为二孩的妻子小环被日本人惊吓导致不育。新中国成立后,张家既要掩饰多鹤的日本人身份,又要对外界和孩子们掩饰她是孩子母亲,张俭的“妾”的身份……
是个好故事,曾经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在导演看来,这是一个很富戏剧性的题材。但是,我历来对故事不感兴趣,对只热衷情节曲折的题材,我总是有偏见,认为在知晓情节后,缺乏回味的深度。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电视拍得会有严歌苓写得好。严歌苓的文笔,永远是在情节之外,有更浓酽的诗意,更深远的人性。除夕的下午,我酣畅淋漓地读了这本小说,直到日暮,直到开灯,流了很多眼泪,这是一次阅读的盛宴,眼泪不是悲伤和绝望,是用来软化心灵的,洗刷灵魂的。
开拓团是日本的农民,被骗到中国东北垦荒的,逃离中国时,遗弃了很多人,很多女人在战后嫁给了当地的农民,这样的故事,在东北,并不稀罕,当年好友的姐姐结婚后,就曾告诉我们她的妯娌,沈阳新民县人,就是这样的中日混血儿。但是,这些遗孤的命运,在战争结束后的艰难悲惨,我还从来没有看过。
科学没有国界,文学没有国界,在对人的悲悯面前,没有国度,没有意识形态,这是真正艺术家该有的视角。这段逃生的描写,惊心动魄,凡是人类,都该心生悲悯,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同胞曾经对我们做过罪孽,那是两回事。这段描写也奠定了我们对多鹤的同情。
村民在村长的命令下,集体自杀后,余下的三千人,一路遭遇各种游击力量,死伤无数,母亲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伤员们自愿自尽。也有不愿被处死的,阿纹就是一个,“她枕着一块土疙瘩,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婴儿也躺在血中,已经走完了他几分钟长的一生,“别杀我,我一会就赶上你们!我还没有找到我儿子和丈夫呢!”多鹤的父亲死于菲律宾战场,母亲,弟弟妹妹死于这次撤退中的一次爆炸中,多鹤成了孤儿。多鹤的生命意识在失去中也得到了新生,千惠子杀死了自己不足一岁的小儿子后,又朝多鹤背上的自己女儿扑过来,多鹤求她:明天再杀她,让她再活一天。
这是一个新的角度,我们知道但不清楚的角度。面对过去的这一切,其实不该有多少恨,该是深深的悲悯,对人和生命的悲悯。杀过人的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前两天看蒙古族作家原野写当年他父亲作为蒙古骑兵参加四平保卫战的一个细节,碉堡前黑压压的,都是八路军的尸体,血流成河,战马都害怕得不敢前行。后来写他父亲在文革期间被连着吊打十五天,我忽然想,如果一个政权是用鲜血夺来的,他对他的子民几乎不会手软,杀过人的手,对生命没有怜悯。(三年内战,抗美援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如果主子但得对百姓有点怜悯)。
在网上看了严歌苓的一些创作心得,《小姨多鹤》的故事原型她在国内听说,但是,真正动笔是在她去过日本,真正地和在中国生活过的这些日本女人交谈之后。是的,没有对多鹤命运的深深的悲悯和体察,是写不出这部书的。
其实,这本书的三个人物,多鹤,张俭,小环,都不是特别丰满,小环的形象是我们比较喜欢的那种“嘴糙,心善”,生存能力极强,泼辣的好女人,这种女人如果按照想象,塑造起来不是特别的困难,也能讨得读者的喜欢,我们历来喜欢强悍,泼辣,心善的好女人,而张俭的塑造,我认为也是非常困难的,对一个文化不高的北方男人,作家要想塑造得成功,真是很不容易,说得过去就行了。对一个女作家来说,描写这种类型的男人,是最困难的。
最打动我仍然是多鹤的命运。最打动我的细节是多鹤写过的一张纸条。那是多鹤被人用麻袋装着卖到了张家,和张俭同房后的几个月,她穿着刚来张家时的日本衣服逃走了——没有人不思念自己的祖国,愿意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家庭里,成为一个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但是,她逃走后又回来,就在全家百思不得其解时,她写了张字条:“竹内多鹤,十六,父母,哥弟,妹亡。多鹤怀孕。”这张纸条让张家人心里不平静。也让我心里不平静,已经失去所有亲人的多鹤,在得到自由,有可能回到祖国的情况下,发现自己怀孕后,还是舍不得腹中的骨肉而回来,孤儿多鹤对亲缘血脉是多么珍惜,又是多么可怜。
张俭和多鹤的关系的描写我觉得也很成功。他们的感情是逐渐发展的,最初他们是没有什么感情的,是很陌生的,大概因为压抑了几千年的原因,近年来国人的作品,过于重视动物本能,其实,人之所以为人,和动物还是有着亿万年的进化差距的。感情在男女关系中还是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张俭这样一个文化不高,正当年的男人。写张俭去多鹤房里过夜,“多鹤现在好些了,不再把衣服穿得跟入殓一样。”“它们(多鹤的手)总是会胆小地,试探地摸摸他的肩,背,腰,又一次,摸了摸他的额。她多么可怜巴巴地想认识他。”多鹤尝试着对张俭说中国话:“二河(二孩,张俭小名),压豆(丫头)。”她在尝试着和她有着肌肤之亲的男人(还称不上丈夫)交流,她在适应着环境,尽可能地亲近着周围的一切,因为要活下来,活下去。在他们真正成为爱人之后,张俭提起了他们的第一次,也就是所谓的圆房。她的手一下子就捂上了他的嘴,那一夜她所有的回忆都是黑暗的。对他们来说,那是可怜可悲的夜晚。作家的描写是真实,可信的,是站在人的角度,没有凭空想象的。
小说从第六章到多鹤回日本前的几章,不太好,原因是插入的小彭和小石这两个人物的不成功,故事必须有起伏,尤其是经历文革,但是,小石和小彭两个对多鹤有好感的男人写得比较苍白,估计还是和作家对这一阶层,文化不高的男性的了解储备不够有关,当然,在很多长篇小说,进行到中后部分时,往往出现一些低谷,但是,由于初期的精彩,是读者往往能原谅这些缺憾。
小说最后,张俭和多鹤去了日本,在病危但不知道自己病情时给小环写了一封憧憬未来的信,关于信的描写,也打动了我,“他一定把这封没写完的信压在了褥子下,怕多鹤看见。他还得在两个女人之间继续玩小心眼儿,就像多年前一样,孩子们和多鹤瞒他瞒得真好,他一直都相信,他还有很多好日子要过,还有不少麻烦要处理,比如他的两个女人,还有在他们之间玩小心眼的必要……所以他才在给小环铺排出那样长远的未来。”是啊,在两个女人之间玩着小心眼,处理各种麻烦,吵吵闹闹,可是,也是生之欢乐,也是热闹的现世,让人历尽千辛,也不忍割舍的红尘。
严歌苓小说里,最动人之处,超越一切的,还是那个永恒的话题:人道和人性。对读者来说,是没有穷尽的陶冶。人要永远学着体会他人的心境,体恤他人的处境,超越种族,民族,意识形态,战争双方的立场,永远同情悲悯个体生命,有赋予每个个体生命尊严和欢乐的美好夙愿。
在这篇小说里,还有一种无声的看不见的力量,那就是人对生命的热爱,坚韧欢乐的活下去的力量。多鹤的逃生,三个人的“凑合活着”,小环泼辣的生存之道,多鹤的清洁和能干,使这个悲苦开始,死亡孤老结束的小说,通篇洋溢着生之欢乐,毫无意义地,这也是伟大的作家使命:让我们无条件地热爱生活,活下来,活下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