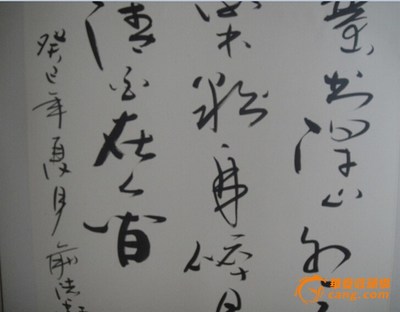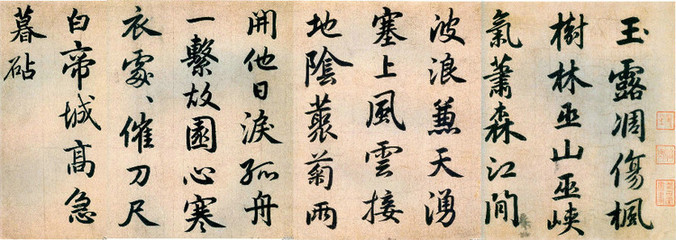方广锠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摘要:前此已有学者指出,大藏经中署名为鸠摩罗什译的《大明咒经》是依据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及其它资料抄集的抄经,而所谓玄奘翻译的《般若心经》是中国人编撰的伪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玄奘在赴印度前得到的《般若心经》可能就是署为鸠摩罗什译的《大明咒经》的早期形态。玄奘将该经带到印度,翻为梵文,即其后流传的《梵语心经》的最初流传本。玄奘回国后又把《梵语心经》译为汉文,即现在大家习知的《般若心经》。现存《梵语心经》写本中,尚有经不空润色者。此外,印度僧人又在玄奘本《梵语心经》的基础上编辑成的三分具足的《般若心经》,该经回流中国,先后为法月(先后两译)、般若共利言、法成、施护等人译为汉文。《般若心经》是“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又一例证。
关键词: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 般若心经 疑伪经
一、序言
“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是笔者归纳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如下: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恒河中下游一带,然后遍传南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等古代东方世界。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宗教的传播本质上属于文化传播,而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不可能是单行道。所以,起源于南亚的佛教在遍传亚洲各地的过程中,也受到各地文化的滋养,呈现出种种形态,在影响各地文化的同时改变着自己。亦即佛教在影响所在地文化、为所在地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文化资源、滋养出新的文化形态的同时,适应所在地文化的需要、与所在地文化相融合、融摄所在地的文化,营养自己、发展自己、衍生出新的形态。所以,佛教的产生虽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而佛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亚洲其它地区文化的汇流。
上述命题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从佛教发展的全局看,从古到今,佛教随着传播区域的扩大而不断变幻其形态。因此,研究佛教,必须把所研究的对象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用发展的眼光审察它与其它文化系统的关系,分析引导、推动它发展的内外动力,探讨发展的结果,研究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研究这种发展对其它文化体系、对后代佛教的影响,才能把握其历史轨迹与真实面貌。
第二,就传入某一地区的佛教而言,与所在地文化互融共存以实现“本地化”,是佛教能够在所在地生存、发展的必然策略选择。当然,任何宗教都会有基要主义的内在冲动。如果我们把这种基要主义的内在冲动称为“本色化”,则“本地化”与“本色化”成为一对相互纠缠,共同促进佛教发展的内在动力。早年有人反对“佛教中国化”这一提法,现在学术界主流已经接受佛教中国化这一事实。目前,在汉传佛教研究范围内,研究佛教日本化的成果越来越多,研究佛教朝鲜半岛化、越南化的成果相对较少。笔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的成果也会不断涌现。
第三,如前所述,文化的传播从来是双向的。当某地文化向外传播时,它同时也受到外地文化的影响。任何一个地区的佛教除了受到传播源头佛教形态、受到本地文化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①]。同样,作为佛教源头的印度文化,在向周围地区传播印度佛教的同时,也受到周围地区诸种文化的影响,从而对印度佛教本身的发展产生这样、那样的作用。
上述第一点,讲的是“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方法。上述第二点,现在已基本得到佛教研究界的认同。至于第三点,目前关注的人还比较少。比如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研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如何适应中国文化,逐步改造为中国佛教的论著比较多;而研究朝鲜半岛佛教,日本佛教乃至越南佛教对中国佛教、中国文化影响的则几乎未见。即使有些论著对此有所涉及,亦属客观事实的记载或个别事例的叙述,缺乏从“文化汇流”角度去进行研究的问题意识。比如在印度佛教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把印度佛教视为印度文化自我逻辑的演化,而忽视周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的影响。中国与印度是两大文明古国,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固然对中国影响深远,以儒教、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印度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无视这一影响,显然是非历史主义的。实际上,如果用文化汇流的观点考察印度佛教,特别是考察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的影响,则以往的一些扞格不通之处,诸如“真常唯心系”是否存在、《大乘起信论》是否伪经之类的问题,可以豁然贯通。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具有强烈的文明自觉,主张以史为鉴,故产生了无可计量的各类典籍。虽经天灾人祸,各类典籍损失惨重,但保存下来的古籍依然汗牛充栋。有人说印度没有历史,这固然有点夸张。但印度的历史大量隐没在宗教传说中,印度的风土条件亦使它的典籍难以保存,却是事实。这一情况对研究者研究古代印度造成极大的障碍。凡此种种,与研究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比,研究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的影响,困难极大。且不说语言素养,仅就资料来源而言,除了发掘梵文原典、实地调查印度古迹之外,必须另辟蹊径。笔者的办法是寻找、考订曾有哪些经典或文化元素原产于中国,其后流传到印度,在印度被翻译为梵文或被组织进印度典籍,然后又回传中国,重新被翻译为汉文。如果历史上的确曾经存在过这样一批“出口转内销”的典籍或文化元素,则可以证明:
第一,中国文化曾以典籍的形式传到印度,中国文化元素曾经进入印度典籍。
第二,中国文化的确影响了印度佛教——因为这些梵文典籍自然是印度佛教僧人或其它印度人学习的对象。
中国文化曾经影响印度佛教这一结论如能成立,则解决《大乘起信论》等问题便有了新的方向。再通过资料的收集、文本的比对、思想的梳理、历史的研究,则诸如“真常唯心系”等问题便可以得到最终的解决。
从这一思路出发,笔者先后发表了《试论佛教的发展中的文化汇流》[1]、《试论佛教的发展中的文化汇流附赘语》[2]、《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3]等文章。本文依然循着这一思路,论证《般若心经》的原本产生于中国,其后传到印度,又以梵文的形式回传到中国。
二、关于《般若心经》的两个问题
《般若心经》,简称《心经》。因该经用最简约的语言论述了印度大乘佛教般若性空的理论而闻名于世,属于在中国,也是在世界流通最为广泛的佛教经典之一。林光明编纂的《心经集成》收入各种《心经》版本184种,包括汉语50种,梵语39种,英语29种,日语39种,藏语6种,韩语7种,印度尼西亚语1种,越南语2种,法语4种,德语4种,俄语3种,另附满语和蒙古语各一种。[4]纪赟指出:“林先生没提及的尚有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语等语种的译本。”[5](P115)历代对《心经》多次翻译,至今流传略本、广本[②]等多种译本。历代对它的注疏也层出不穷。虽然自古以来对这部典籍的来源已有各种传说,但从来没有人怀疑它属于印度佛教经典这一身份。上世纪以来,先后有陈寅恪、长田彻澄、孔泽、霍维茨、派依、魏曼、贝雷、兰卡斯特、福井文雅、沈九成、马克瑞、小唐纳德·洛佩兹、那体慧、方广锠、葛维钧、林光明、万金川、廖湘美、纪赟等人的对它进行整理与研究。上述诸位的研究各有侧重,观点也各不相同。限于篇幅,本文难以对《般若心经》的研究史做详细的叙述。好在纪赟的《<心经>疑伪问题再研究》[5]、万金川的《敦煌石室<心经>音写抄本校释序说》[6]中已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可以参看。本文仅就如下两个问题做一些总结与探讨。擒贼要擒王,笔者以为如果这两个问题可以论定,则《般若心经》“出口转内销”的身份便能确定。
(一)关于鸠摩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呪经》
现各种版本大藏经均收有署名为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呪经》(以下简称“大明咒经”),属于略本《般若心经》。如果这一记载可靠,则该罗什本《大明咒经》是《般若心经》的最早译本,由于罗什本与其后的玄奘本虽然文字有差异,但内容基本相同。所以,只要该罗什本确为罗什所译,则玄奘本的真伪自然毫无悬念。
1987年,福井文雅在《<般若心经>之史学研究》中,对比罗什本与玄奘本,主张罗什本确为鸠摩罗什本人所译。[7](P178)
1988年,沈九成[③]撰文指出:《大明咒经》有无梵文原典,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他考察了《大明咒经》与鸠摩罗什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有关经文,比较了《大正藏》本六百卷《大般若经》卷末所附咒语与《般若心经》中的咒语,主张《大明咒经》的文字实际是鸠摩罗什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经文集录、简约而成,本身并无梵文原典。[8](No.195,P3-13)
1992年,那体慧发表《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9]那体慧对罗什本与玄奘本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在指出两者存在若干不同的同时,指出《大明咒经》与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的相关经文有着对应关系。那体慧不同意福井文雅主张的《大明咒经》为鸠摩罗什所译的观点,认为该《大明咒经》到底是谁的作品现在难以断定。她提出,出现该《大明咒经》的时间上限,不会早于《大智度论》翻译年代——公元406年[9];至于下限,她介绍了马克瑞在《禅宗的<心经>注:汉传佛教蜕变的初步推理》[10]中表述的观点,亦即《大明咒经》实际产生在玄奘本之后。[④]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大明咒经》到底是翻译,还是集录?
在这一问题上,沈九成,特别是那体慧已经做了非常绵密细致的工作,证明该经是集录,而非翻译,且无梵文原本。我赞同这一观点。该经到底是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还是从《大智度论》中集录,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因为无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是《大智度论》,都是鸠摩罗什所译,且《大智度论》全文照抄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因此,要区别《大明咒经》究竟辑录哪一部典籍,还需要更精细地爬梳文本。此外,同为鸠摩罗什译的《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中亦有与《大明度经》对应的文句,所以不排除《大明咒经》的构成,来源于多部典籍的可能。如下文所述,《大明咒经》文末咒语,鸠摩罗什所译诸经论均无,另有出处。
第二,该《大明咒经》大约出现在什么时候?
如前所述,沈九成主张《大明咒经》的集录工作由鸠摩罗什本人完成,则该经应出现在姚秦时期。那体慧虽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但介绍了马克瑞的观点。而马克瑞主张该经可能出现于玄奘本之后。
纪赟从另一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受沈九成文章启发,追索《大明咒经》末尾咒语[⑤]的出处。发现该咒语与唐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三之“般若大心陀罗尼第十六”可以对应。故纪赟主张:罗什版《心经》“主体部分乃是抄自什译《大经》(或《大智度论》中所引的《大经》),再加上阿地瞿多译经中的咒语。罗什本最后定型的时间自然是在此时间之后,并且也晚于玄奘本。”[5](P175)纪赟将《大明咒经》目前的形态视为分阶段形成的结果,这一思路具有启发性。
第三,玄奘赴印前已经得到《心经》
根据现有资料,在玄奘本以前确有一部《般若心经》在流通,玄奘赴印度求法前已经得到该本。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称,玄奘西行求法,行走在沙漠戈壁,“顾影唯一,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11](T50,P224b)并交待了玄奘一路念诵的这部《般若心经》的来历:
“初,法师在蜀。见一病人,身疮臭秽,衣服破污。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病者惭愧,乃授法师此经。因常诵习。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能全去。及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11](T50,P224b)[⑥]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慧立,永徽元年(650)敕任大慈恩寺翻经大德,参与玄奘译场。因敬佩玄奘事迹,遂为之修传,撰《大慈恩寺三藏传》五卷。据说慧立担心该书有所不足,一直秘藏地窖,不以示人。直到命终前,才令门徒掘出。此后该书流离分散。彦悰,贞观(627~649)末年曾就学于玄奘之门,乃搜购慧立旧稿,排列、补校、笺述,续成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由于慧立、彦悰均曾亲炙玄奘,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的上述记述。且上述记载比较平实,没有像本文附录一《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序》那样,出现把授经“病人”改为“病僧”,并称之为观音化身[⑦],这增加了它的可信度[⑧]。
第四,《大明度经》应为玄奘本的祖本
既然玄奘赴印之前,已经得到一部《般若心经》,且就现有文本看,玄奘本与《大明咒经》均属略本,内容、文字亦为近亲,两者有明显的递承关系。又,敦煌遗书伯4577号首题作“大明咒藏摩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内容为两行悉昙体梵文及一行汉文音译,内容与玄奘本《般若心经》相符,首题的形态也说明玄奘本与《大明咒经》确有亲缘关系。故从现有资料看,把《大明咒经》视为玄奘本的祖本,当无大差。
查《出三藏记集》卷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著录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呪》一卷。《般若波罗蜜神呪》一卷(异本)。”[11](T55,P31b)后代经录虽有参差,但大体沿袭了这一著录。那体慧主张这一著录与《大明咒经》无关。但笔者以为目前没有资料可以证明这一著录与《大明咒经》无关。这里又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对“神咒”亦即“陀罗尼”的理解,对《大明咒经》这一名称的理解。第二,对《大明咒经》卷末真言来源的理解。
限于篇幅,本文难以展开详尽论述。对上述两个问题,笔者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咒”,亦即“陀罗尼”,原意为“总持”。《大明咒经》的内容正是“总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称之为“咒”,当之无愧。
第二,纪赟提出《大明咒经》末尾的咒语可能来自《陀罗尼集经》,对《般若心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进路。依据《开元释教录》卷八记载,玄奘《般若心经》译出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四日。阿地瞿多的《陀罗尼集经》译出于永徽四年(653)三月十四日至五年(654)四月十五日。由于两段咒语基本相同,故更大的可能是《陀罗尼集经》采用了先出的玄奘《般若心经》中的咒语而加以改造。进而考虑到《大般若经》第六百卷所附的两道咒语,则古代显然存在着平行流传的同类咒语。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大明咒经》末尾的咒语或许另有出处。而《大明咒经》现在的咒语形态,则显然是受玄奘本影响的结果,这可以视为《大明咒经》乃分阶段形成的证明。
总之,玄奘在赴印之前得到一部《般若心经》,他一路持诵这部经典前往印度。这部经典应该就是目前收录在大藏经中,挂在鸠摩罗什名下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呪经》。可能就是《出三藏记集》卷四著录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神呪》或《般若波罗蜜神呪》。现已明了,该经并非鸠摩罗什所译,而是依据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及其它资料抄集的一部抄经。其目前形态,存在一个分阶段形成的过程。
第五,玄奘所得本与《大明度经》的关系
玄奘在四川所接受的《般若心经》的形态与大藏所收的《大明咒经》是否完全相同?我以为颇可怀疑。在写本时代,抄经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嬗衍是十分正常的。这解释了为什么其后玄奘本《般若心经》与《大明度经》的文字会有异同;也解释了为什么道宣在其《大唐内典录》中既著录玄奘译本,[11](T55,P305a)又著录了一部失译的《般若心经》。[11](T55,P294a)
第六,玄奘所得本的语种
玄奘得到的这个本子是汉文还是梵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正因为没有明确记载,笔者认为它应该是汉文。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如为梵文本,会有明确记载。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例外,则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如果该经是梵文本,那么有如下两种可能:
1、这个梵本从印度传入,还没有来得及翻译为汉文。
2、这个梵本是从上述集录而成的《大明度经》回译为梵文的。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则沈九成、那体慧等关于上述《大明度经》乃集录而成的观点就要重新考虑,乃至完全不能成立。这与目前的研究成果矛盾。也与上文已经串成的从《出三藏记集》以下的证据链相矛盾。此外,如果那个病人[⑨]向玄奘传授的是梵本《心经》,那自然要同时解释这个梵本的汉文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兼通梵汉语文,有翻译经典的能力。在当时条件下,他应该是一个入华的胡人、梵志。一个入华的外国人,将一部梵文典籍翻译为汉文,哪怕只是口授,站在中国佛教的立场上看待此事,这就是译经。如此重大的事情,理应记入经录。但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没有任何一点线索暗示这个病人是外国人,这一“病人授经”事件并没有视为“译经”,仅仅处理成玄奘施恩得报而已。则显而易见,玄奘所得本应为汉文。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玄奘所得到的是从《大明度经》回译为梵文的经本。那么,沈九成、那体慧的研究成果固然可以成立,但依然不能回避是谁回译了这个梵本?是那个病人?他兼通梵汉?其不合理处上文已经分析,此处不赘。
综上所述,玄奘在四川所得,应为汉文本。
(二)关于《般若心经》梵本的译者
玄奘曾在四川得授汉文《般若心经》,其后出现梵文本《般若心经》。经我调查,敦煌遗书中存汉文音译梵文6号,悉昙梵文附汉文音译1号,《般若心经》咒语梵文习字1号。中国民间传本汉文音译梵文2号。此外,《房山石经》、日本古写经中均有保存,且均为略本[⑩]。万金川对敦煌《般若心经》之汉文音译梵文本的语音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可以参看。[11](P95-119)
那体慧在《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中,对《般若心经》的汉文本与梵文本做了详尽的对照与研究,指出该梵本乃从汉语回译,行文与梵文行文习惯有异,比较生硬。其观点可以信从。现在的问题是回译者是谁?
现在我们掌握的资料是:《般若心经》的前身是《大明咒经》,为汉文。玄奘得到这个汉文本,一路念诵前往印度。玄奘留学印度十余年,兼通华梵。该《般若心经》其后出现梵文本,出现的时代在玄奘留学印度以后。该梵文本乃从汉文回译。上述种种资料汇集在一起,则从常理推测,回译者除了玄奘,似乎不会有任何其它人。但从那体慧以下,诸多研究者对此均持谨慎态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不予表态。因为我们的确找不到玄奘回译《般若心经》的直接证据。相反,《开元释教录》卷八明确记载: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见《内典录》,第二出。与《摩诃般若大明呪经》等同本。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四日于终南山翠微宫译。沙门知仁笔受。”[11](T55,P555c)
笔者认为,这条记载与至今为止我们掌握的关于《心经》的资料是矛盾的,与学术界对《心经》的研究成果是矛盾的。亦即如果承认这一记载,那玄奘在四川所得应为梵本《心经》,所谓《大明咒经》无梵本等结论都要重新考虑,乃至不能成立。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一记载。亦即玄奘在粗通梵文时将《心经》翻译为梵文。回国以后,又把这个梵本译为汉文。这一次的翻译,自然会对四川所得那个文本作文字的再整理。这既可解释玄奘本《心经》与《大明咒经》差异的原因,也解释了其后流传的《梵语心经》的来历。
我们从敦煌遗书中的《梵语心经》来探讨这一问题。
如前所述,敦煌遗书中存汉文音译梵文《般若心经》6号,为斯2464号、斯3178号、斯5627号、斯5648号、伯2322号、北大118号。在此将各号抄写内容、首题、著译者表列如下。首题、著译者照录原文,不做修订。文中敬空照样保留;“/”表示换行。此外,日本京都大谷大学存有一个古写本[11],为悉昙梵文,附汉文音译、意译。为了便于对照,亦罗列于后。
编号
慈恩序
不空莲花部
玄奘梵语心经
斯2464号
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序/西京大兴善寺石璧上录出慈恩和尚奉 昭述序/
特进鸿胪卿开府议同三司封肃国公赠司空官食邑三千户/勅谥大辨正广不空奉 诏译/莲花部普赞叹三宝/
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不润色/
斯3178号
无
莲花部普赞叹三宝/
梵语般若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不闰色/
斯5627号
无
无
梵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不润色/
斯5648号
无
梵本般若多心经 莲花部/……/勅谥大辨正广不空奉诏译/
梵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 不空闰色/
伯2322号
无
无
(有经文,无首题及署名)
北大118号
无
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莲花部等普赞叹□…□
大唐三藏传梵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亲教授梵本不闰色/
大谷大学本
唐梵对翻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记/
无
唐梵对翻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 诏译/
上述7号,显示出4种抄写形态:
1、同时抄写慈恩序、不空莲花部、玄奘《梵语心经》者,1号。
2、只抄写不空莲花部、玄奘《梵语心经》者,3号。
3、只抄写玄奘《梵语心经》者,2号。
4、只抄写慈恩序、玄奘《梵语心经》者,1号。
在只抄写玄奘《梵语心经》的2号中,因斯5627号首脱,前面抄写什么内容难以判定。因此,真正只抄写玄奘《梵语心经》的是1号——伯2322号,接续抄写在其它文献的后面。
上述4种形态的《梵语心经》提供给我们的研究信息非常多。例如,长田彻澄提出:玄奘认为“观音”、“观世音”等名词翻译错误,提出应该使用“观自在”一词。而上述慈恩序中却出现“观音菩萨”,由此它不可能是玄奘的嫡传弟子慈恩窥基所写。[12]其实,现在固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该序言为窥基所撰。但以是否使用“观音”一词,作为判断某作品是否为窥基所作的基准,却没有说服力。因为窥基的多部著作,比如《妙法莲华经玄赞》,大量使用“观音”、“观世音”等词汇。何况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玄奘当年的观点并不准确。限于篇幅,本文难以一一罗列上述资料可供进一步开拓的各种课题,在此仅讨论一个问题:上述《梵语心经》的译者是谁?
7号文献中,除掉无首题1号、日本写本1号,5号存有首题及著译者。
就首题而言,除了“梵本”、“梵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多心经”等表述的差别外,5号首题之最大差别在于北大118号的首题上明确有“大唐三藏传”5字,强调这一《梵语心经》乃由玄奘传授。
就著译者而言,上述5号的共同特点是均强调“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这一神圣性来源。並主张该《梵语心经》曾由不空予以润色[12]。
如前所述,敦煌遗书中另存伯4577號,为悉昙梵文附汉文音译《般若心经》,首题作“大明咒藏摩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书写形态看,该文献约为7世纪末期、8世纪早期写本。这说明在玄奘时代或玄奘逝世以后不久,各种形态的《梵语心经》开始在中国流传,早期流传形态还带有从《大明咒经》衍出的痕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之类的神话开始出现。但无论传播形态如何变化,在人们观念中,该《梵语心经》乃玄奘所传,并无异议。
上文提到,从常识推论,既然《心经》是抄集,没有梵本。其汉文本是玄奘带到印度。则依然由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梵语心经》的译者,只能是玄奘。上面对敦煌本首题著译者的讨论,那体慧所述梵本《心经》实际为汉文回译、行文比较生硬的研究结论,均支持“《梵语心经》的译者应为玄奘”这一从常识推出的结论。
再讨论不空润色问题。
根据敦煌遗书的上述资料,不空曾经对玄奘所传《梵语心经》进行润色。由于资料有限,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其它直接证据对所谓“不空润色”进行证真或证伪。但我们可以依据间接证据来探讨这一问题。所谓间接证据,就是不空曾经得到过玄奘遗留的梵夹。正因为不空曾经得到过玄奘遗留的梵夹,所以他完全有可能对玄奘的作品有所润色。当然,如果不空没有得到过玄奘遗留的梵夹,照样不能排除不空润色玄奘作品的可能,但毕竟有点勉强。
我曾在《般若心经译注集成》的前言中提到不空曾经得到过玄奘遗留的梵夹,[13](P12)现在依然坚持这一结论。理由如下:
《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保存了两道文书的原文:不空的“奏表”与肃宗的“制许”,记录了如下一段史实: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三月十二日,不空上表,要求“天恩允许,请宣付所司”,将“中京慈恩、荐福等寺及东京圣善、长寿、福先等寺并诸州县舍寺村坊,有旧大遍觉、义净、善无畏、流支、宝胜等三藏所将梵夹”统统搜寻、拨交给自己,“其中有破坏缺漏,随事补葺。有堪弘阐,助国扬化者,续译奏闻。福资圣躬,最为殊胜。”[11](T52,P828a-b)5天以后,乾元元年(758)三月十七日,肃宗制许之。
“奏表”与“制许”均提到慈恩寺与“大遍觉”。慈恩寺是唐玄宗为玄奘修建的寺院,在其中別造翻经院让其译经,又建大雁塔以储存梵夹。至于“大遍觉”,则为唐王朝对玄奘的谥号。由此可以证明,不空的确得到玄奘遗留的梵夹。所以,如果没有有力反证,对敦煌遗书中“不空润色”的记载不宜否定。
廖湘美从音韵入手对敦煌遗书《梵语心经》进行研究,认为它们的音韵系统与玄奘的音韵系统不合,主张:“此一敦煌石室心经音写抄本的年代应不早于不空时代,以为‘出自奘师之手’说,显然难以成立。”[14](P208)笔者赞同上述结论的前部分。这几个敦煌遗书的确抄写于不空之后,无论从写经形态还是从文献内容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对廖湘美结论的後部分不以为然。因为该《梵语心经》明确载录它已经是一个经过不空润色的本子。既然经过不空润色,自然不可能照旧保持玄奘本的原貌,也就失去用以探讨玄奘音韵系统的价值。以此否定该本出自玄奘,逻辑上似乎值得斟酌。
相反,笔者认为敦煌遗书不空润色本的出现,补强了梵文原本为玄奘所传的结论。因为不空与玄奘仅相距百余年,均为佛教大师、梵文大家,不空在得到玄奘遗留梵夹之后,不但有能力,也具备了对《梵语心经》是否玄奘所传做出评判的条件。敦煌遗书《梵语心经》的译著者名称告诉我们:不空自承,或时人都认为不空对这个“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进行了“润色”,亦即不空或时人都认可“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这一观点。所以,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现在没有理由推翻这个观点。站在那体慧成果的基础上,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测,不空的润色,是否就是为了消弭玄奘译本中“回译”的生硬呢?[13]但这个问题已经超出笔者的能力。好在诸种梵文本现均有留存,此一工作敬待能者。
总之,综合各方面资料及现有研究成果,《梵语心经》的译者均指向玄奘。现在的《梵语心经》有多种写本,其中有的写本应该曾经不空润色。
唐代,玄奘与《般若心经》的故事深入人心。敦煌遗书有《赞<梵本多心经>》存世。今作为附录二,以供欣赏。《赞<梵本多心经>》发展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能全去。及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11](T50,P224b)[14]的说法,渲染玄奘一路上凭籍此经“降邪魔,伏妖魅”,看来这一类流传在民间的赞颂就是后来《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乃至《西游记》的源头。
三、结论
玄奘以后,大本《般若心经》源源不断从印度传入。所谓“大本”,是指在玄奘本《般若心经》的基础上,加上传统佛经必备的“序分”、“流通分”,并将原玄奘本作为“正宗分”,从而使《般若心经》三分具足,外观成为标准的佛经。唐代先后翻译大本《般若心经》的有法月(先后两译)、般若共利言、法成、敦煌失译、智慧轮。宋代则有施护。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须赘述。
可以想象,玄奘传入印度的《般若心经》因其三分不具足,不符合印度佛经的一般形态,于是印度僧人对其进行改造,使之三分具足。这种三分具足的形态再次回流中国,使得中国佛教典籍又多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品种,也使我们研究“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增加了一个新的例证。
《般若心经》就其思想理论而言,无疑属于印度文化系统。但该经在中国形成,流传到印度,又回流中国的复杂过程对我们研究中印文化交流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2013年4月30日于通州古运河北端
附录一:《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序》
说明:敦煌遗书中保存《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或《梵本般若心经》多号,但保存序言者仅斯02464号1一号。此外,日本大谷大学存有日本明德三年(1392)抄本,所抄亦为本文献。今以斯02464号1为底本,以大谷大学本为甲本,录文如下:
唐梵翻对[15]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序[16]
西京大兴善寺石璧上录出,慈恩和尚奉诏[17]述序[18]
梵本《般若多[19]心经》者,大唐三藏之所译也。
三藏志游天竺,路次益州,宿空惠[20]寺道场。内[21]遇一僧有疾。询问行止,因话所之。乃叹法师曰:“为法亡[22]骸,甚为希有。然则五天迢递[23],十万余程[24]。道涉流沙,波深弱水。胡风起处,动塞草以愁人;山鬼啼时,对荒坵[25]之落叶。朝行雪巘,暮宿冰崖。树挂猿猱,境[26]多魑魅。层峦迭于葱岭,萦似带雪之白云;群木蔟于鹫峰,耸[27]参天之碧峤。程[28]途多难,去也如何?我有三世诸佛心要法门,师若受持,可保来往。”遂乃[29]口授[30]与法师讫。至晓[31],失其僧焉。
三藏结束囊装,渐离唐境。或途经厄难,或时阙斋馐[32],忆而念之,四十九遍,失路即化[33]人指引,思食则輙现珍蔬。但有诚祈,皆获戬佑。
至中[34]天竺磨竭陀国[35]那烂陀寺,旋绕经藏次[36],忽见前僧而相谓曰:“逮涉艰崄,喜达此方。赖我昔在支那国[37]所传三世诸佛心要法门。由[38]斯经力[39],保尔[40]行途。取经早还,满尔[41]心愿。我是观音菩萨。”言讫冲[42]空。
既显奇祥,为斯经之至验。信为般若,实为圣枢。如说而行,必超觉际。究如来旨,屡[43]历[44]三祇;讽如来经,能销[45]三障。若人虔诚受持者,体理斯而勤焉。
(录文完)
附录二:《赞<梵本多心经>》
说明:据笔者目前掌握,敦煌遗书中的《赞<梵本多心经>》仅1号,为伯2704号背,今据以录文,无校本。
《赞<梵本多心经>》
此经实谓文深莫测,义广难明。贯六百卷之幽言,显万千重之奥理。故疏云:若历[46]事备陈,言过二十万颂;撮其枢要,理尽一十四行。此是大唐三藏当离东土,欲往西天,沿路忽忽[47]。朝遇豺狼,夜逢龙鬼。或即口中焰出,或乃头上烟生。有时笑似前头,或即吟俄后面。跳掷自在,变化多般。一行行发似朱砂[48],一队队身如雷[49]电。三藏睹之而莫测,一心忆念此经。闻题目而罗剎皈降,诵真言而鬼神自退。遂得声传此[50]土,喻遍支那。使千山无限碍之[51]程,得万水没难达之路。皆因缘力,尽自圣言。闻之则罪灭河沙,听之者福臻云雾。
般若题名观自在,圣力威神无比对。危难之心讽念时,龙鬼妖精寻自退。
往西天,别东土,不倦驱驱与辛苦。朝看虎狼罕逢人,夜听猿啼此伴侣。
绕经盘山,寻溪涧水。路僻[52]人稀[53],凭何所止。
降邪魔,伏妖魅,忆想如来情不异。为重多心一卷经,讽念幽深清净理。
佛赞此经世所稀[54],于中枢要甚珍奇。听闻必使添新福,讽念终教[55]离苦危。
恶兽夜叉皆敬仰,毒龙蚖蝮尽收威。当时三藏凭经力,取得如来圣教归。
行深般若状云雷,五蕴皆空义似排。色即是空空莫喻,空即是色色难裁。
心无罣碍长安乐,意乃无明定没灾。真实不虚经里说,能除罪障怯[56]三灾。
(录文完)
参考文献:
[1]方广锠.试论佛教的发展中的文化汇流[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2]方广锠.试论佛教的发展中的文化汇流附赘语[J].东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2007,(11).
[3]方广锠.再谈佛教发展中的文化汇流[J].敦煌研究,2011,(3).
[4]林光明.心经集成[M].台北:嘉丰出版社,2000.
[5]纪赟.心经疑伪问题再研究[J].台北:福严佛学研究,1912,(7).
[6] 万金川.敦煌石室心经音写抄本校释序说[J].台北:中华佛学学报,2004,(7).
[7] 福井文雅.般若心経の歴史的研究[M].东京:春秋社,1987.
[8]沈九成.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义[J].香港:内明,No.195 ,1988;No.196,1988.
[9] JanNattier.The Heart Sūtra: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 Journal of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Volume15(2),1992,pp153-223.
[10] JohnMcRae.Ch’an Commentaries on the Heart Sūtra:Preliminary Inferenceson the Permut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th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ume11(2),1988,pp87-115.
[11]中华电子佛典集成[Z].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2011.
[12]长田彻澄.敦煌出土,东寺所藏两梵本玄奘三藏音译般若心经の研究[J].密教研究,1935,(56).
[13]方广锠.般若心经译注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4]廖湘美.敦煌石室心经音写抄本所反映之声母现象——兼论译者归属问题[J].台北:中国学术年刊(秋季号),2008,(9).
[①]在上述研究中,应注意如下情况:虽然文化传播受“势差规律”的影响,发展层次较高的文化、强势的文化对发展层次较低的文化、弱势的文化的影响会大一点;但不能否认发展层次较低一点的文化、弱势的文化对前者同样有着程度不等的影响。
[②]传统将《般若心经》译本中仅有正宗分者称为略本,将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等三分俱足者称为广本。
[③] 沈九成(1915—1989),香港《内明》杂志主编。1988年出家,法名熙如。
[④]本文所用那体慧:《心经:一部中国的伪经?》为纪赟中文译本,待刊。特向纪赟先生允许本文采用其未刊稿表示感谢。
[⑤]沈九成考察了六百卷《大般若经》所附的《般若佛姆心呪》、《般若佛姆亲心呪》等两条咒语,指出虽然形态、译音略有区别,但其中的《般若佛姆心呪》正是罗什本乃至玄奘本《般若心经》文末的咒语。沈九成由此推测《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文末也应有相同的咒语,只是鸠摩罗什没有译出。但这一推断目前看来不能成立。因为在历代大藏经中,现知仅《高丽藏》本(《大正藏》底本)、《碛砂藏》本《大般若经》第六百卷的末尾有这两条咒语,其它诸种藏经均无。敦煌遗书中现存卷尾完整的《大般若经》第六百卷仅BD06390号、杏雨204号等两号,末尾也没有这两条咒语。故玄奘所译的《大般若经》末尾原无咒语,《高丽藏》本、《碛砂藏》本《大般若经》所附咒语乃后人所加。沈九成仅依据个别藏经的《大般若经》附有这两条咒语,以为玄奘译《大般若经》一定附有这两条咒语,进而推断《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之后也有这两条咒语,显然证据不足。其实,沈九成本人对这一推论也并不自信。因为《大般若经》就是玄奘翻译的,沈九成指出,既然玄奘“明知有二咒,而《心经》未加补录,殊难索解。”
[⑥] 文字据校记有修订。
[⑦]如《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序》所示,从此《般若心经》与观音菩萨联系起来,并被纳入观音信仰的范畴。敦煌遗书中颇多《般若心经》、《观世音经》合抄的写卷,就是这一信仰的反映。但这一点与本文主题无关,此不赘述。
[⑧]与玄奘同时代的道宣在其《大唐内典录》中著录了玄奘的《般若心经》,但在他的《续高僧传·玄奘传》中,没有提到观音传授《般若心经》说。这说明当时还没有将此事神化。否则,特别注重三宝感应的道宣应会记录此事。
[⑨]在敦煌遗书《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并序》中,这个“病人”被改变为病僧。但按照《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叙,该人身份显然是一个俗人,所以玄奘才可怜他,“愍将向寺,施与衣服、饮食之直”。
[⑩]约20年前,笔者曾将当时收集到的若干经本录文收入《般若心经译注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现在看来,该书观点、校勘、标点均有可议之处。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拟重印此书,起先曾提出修订再版,但因出版社固请,且笔者一时无暇修订,故因循重印。参见重印后记。
[11] 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所梶浦晋先生代为复制,特致谢意。
[12]著译者行文中有“不润色”与“不空润色”等两种表述。很显然,“不润色”在此文意滞碍;而联系前文之不空译《莲花部普赞叹三宝》,则以“不空润色”文意为长。今取后者。
[13]纪赟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提出疑问:“我对是否是玄奘法师回译了《心经》,还是有一点旧的疑惑。即我们都知道他一生中花了很大的力气不辞劳苦地译了大部头的《大般若经》,而且梵语经典有个众所周知的怪毛病(从我们中国人好尚简约的角度来看),即名相重复极多,很多用法都是颠三倒四地用。我们以前读梵语般若经中的部份就有此感,但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查了一两遍字典之后,那些常用的术语和名相就滚瓜烂熟了。而现在梵本《心经》中的一大问题就是其中的术语不是梵本《大般若经》中的常用术语,那体慧也作过比较。再加上回译的某些地方,有硬译的痕迹,比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一块,完全是照汉语硬搬过去,而梵语的语法(主要是语序)其实是与汉语有别的,所以我当时就有个印象,觉得这个回译者一是语法不是特别熟练(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坐实,因为古代确实缺乏现代人这样标准化的语法知识);但第二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个回译人,对《大般若经》梵本中的常用语(《般若心经》中讨论的用语确实都是些最常见的问题,好多词应该出现了数以千遍)感觉不是特别熟悉。还有就是般若经也是重复非常多的,而梵语《心经》则有很多华人尚简的特点,玄奘对般若经典很熟悉,如果是他回译,可能会译得更有印度味道。所以我‘直觉’觉得不是玄奘,而是成千上万中国去印度朝圣的人中的一位,而且梵语不算特别好,对《般若经》也不是特别熟悉。”“难道是因为这部《心经》是出自玄奘译大本般若之前?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解释得通。因为那时一则玄奘梵语没那么好;二则也没有译般若经(如果我没有记错,玄奘是在临死前才译完这部,也就是最晚的译作之一)。”
事实的确如此。根据《开元释教录》卷八,玄奘本《心经》译于贞观二十三年(649)。而《大般若经》开译于十多年以后的显庆五年(660)正月一日,至龙朔三年(663)十月二十日完成。
[14] 文字据校记有修订。
[15] “翻对”,甲本作“对翻”。
[16] “并序”,甲本作“记”。
[17] “诏”,底本作“昭”,甲本无,据文意改。
[18] “西……序”19字,甲本无。
[19] “多”,甲本无。
[20] “惠”,甲本作“慧”。
[21] “内”,甲本无。

[22] “亡”,底本作“忘”,据甲本改。
[23] “递”,甲本作“遍”。
[24] “程”,底本作“逞”,甲本作“裎”,据文意改。
[25] “坵”,底本作“兵”,据甲本改。
[26] “境”,甲本作“景”。
[27] “耸”,底、甲本同,下似脱一字,或为“如”。待考。
[28] “程”,底本作“逞”,甲本作“裎”,据文意改。
[29] “乃”,甲本无。
[30] “授”,底本作“受”,据甲本改。
[31] “晓”,甲本作“晚”。
[32] “馐”,甲本作“羞”。
[33] “化”,甲本作“他”。
[34] “中”,甲本无。
[35] “磨竭陀国”,甲本无。
[36] “次”,甲本无。
[37] “国”,甲本无。
[38] “由”,甲本作“犹”。
[39] “力”,底本作“历”,据甲本改。
[40] “尔”,甲本作“汝”。
[41] “尔”,甲本作“汝”。
[42] “冲”,甲本作“沉”。
[43] “屡”,底本作“巨”,甲本作“[侣-亻]”,疑或为“屡”字音误。待考。
[44] “历”,底本作“历”,据甲本改。
[45] “销”,甲本作“消”。
[46] “云:若历”,底本作“云若历云若历”,据文意删改。
[47] “忽忽”,疑或为“怱怱”之误。
[48] “砂”,底本作“沙”,据文意改。
[49] “雷”,底本作“蓝”,据《维摩诘经讲经文》改。
[50] “此”,底本似为“化”,据文意改。
[51] “之”,底本作“之之”,据文意删。
[52] “僻”,底本作“擗”,据文意改。
[53] “稀”,底本作“希”,据文意改。
[54] “稀”,底本作“希”,据文意改。
[55] “教”,底本作“交”,据文意改。
[56] “怯”,底本作“佉”,据文意改。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