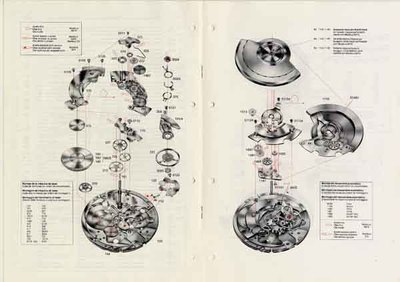五六十年代的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科技发达,有众多智力玩具和电脑游戏可供娱乐玩耍,却有许多集体游戏,像斗鸡、斗蛐蛐、官兵捉强盗、打游击、弹玻璃球比赛等等,始终陪伴着我们。然而,最让我钟爱的还是其中最有趣也是最自然的玩法——斗蛐蛐。
蛐蛐,亦称“促织”、“趋织”、“吟蛩”、学名蟋蟀。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同科有油葫芦、棺材头,白米饭蟋蟀等等,种类很多。最普通的为中华蟋蟀,雄性好斗,年生一代。
那时候,我玩蛐蛐简直入了迷。每当夏天,为了捉到好蛐蛐,不管阴晴圆月,还是烈日当头,总要同小伙伴们一起去捉蛐蛐。拉拉藤下,砖石堆里,小河沿上,甚至茅厕旁边,都是我们“狩猎”的目的地。为了这些,我没少受伤,也没少挨母亲的打骂,像拧耳朵、踢脚骨拐子(脚踝骨)是常有之事。纵使这样,我亦秉性难改,照玩不误。
好的蛐蛐,如 “青虫”“黄虫”、“大翅”等等,不仅个儿大,后腿粗壮有力,全身上下无不透出那样一种精气神儿和霸王气息,是不可多得之上品。谁拥有这些上品,如同获得了最高荣誉证书,在小伙伴中便有崇高的位置。为获到这样的地位,我们不畏艰险,绞尽脑汁,用一切办法予以得之。传说“蜈蚣把门”、“蛇把门”蛐蛐最好,我们便特意留心寻找,哪怕危险在即。好蛐蛐在野外声音低沉,并不总是喳喳呼呼地叫个不停,而是好半天才叫两声的那种沉稳者。为了得之,我们总是耐着性子,仔细倾听、辨别,小心翼翼地翻着每一块石头,生怕惊跑了它们;为了得到它们,我们甚至敢拆卸人家的房基。

再好的蛐蛐捉到手,也要保证它身体不能受到任何伤害,这便是我们常说的做到“全须全尾”。为达此目标,我们特意制作专门捕捉工具:用细铁丝制作的罩子。一旦发现蛐蛐,须小心翼翼地用罩子罩住,再用蛐蛐草将其引至罩上,然后将蛐蛐装进纸筒或竹筒,方才完事大吉。
捉到好蛐蛐,还需细心呵护。别的小朋友只有瓦罐、搪瓷缸,我家却有上好的专养蛐蛐的细陶缸,那是父亲儿时玩的,留给了我们,总共有十几盆。这种细陶缸,通体青砖色,浅圆桶形,有盖,盖上刻有花纹,缸里摆设有带盖的小房子,是专为喜穴居的蛐蛐待的,房外尚有个青花瓷饮水浅盆。捉到蛐蛐后,需放在这清凉黑暗环境下静养数日。这几天,既不能饿着,也不能让它吃得过饱;不能给它吃米饭之类涨肚子的东西,要给它吃辣椒或肉类激发斗志之食物。待蛐蛐养精蓄锐并忘却捕捉它时的诚惶诚恐后,便可派上角斗场了。
斗蛐蛐要用到蛐蛐草。蛐蛐草是路边生长的一种分开有3至5个针状叶子的矮小植物,学名牛筋草,禾本科,穇属。人们将蛐蛐草从上部中间撕开一段,弯折后去芯留皮须,就做成一只不错的斗蛐蛐“指挥棒”。可别小看这不起眼的柔软蛐蛐草,用处可大了。有了它,捕捉时可方便地驱赶蛐蛐进入罩子,而不必“掀砖倒瓦”般折腾;有了它,决斗中能轻易地指挥“战神”征战,而不会使其受到伤害。
待斗蛐蛐那天,小朋友们,甚至还有大人们,围成一圈观战。决斗前,首先要对两只参战的蛐蛐“验身”,看有否“背子”——身上背有卵的蛐蛐不符合决斗规则,因为它“护子”心切,更能战斗。拿去蛐蛐缸里的房子、水盆,将合格蛐蛐轻轻放进缸里,用蛐蛐草挑逗、引导,两只蛐蛐便开始大战起来。一般战力相差较大的两只蛐蛐,不消几个回合,便能分出胜负。胜利者展翅高鸣,失败者落荒而逃,有时,甚至会被咬掉大腿。而战力不相上下之两强相争,总要决战十几回合,甚至几十回合,方能分出高低。你看,只要它们一旦进缸,立刻晃动触须“扫描”,警惕观察四周。两相遭遇,也不打招呼,双方便使劲儿蹬着后腿,张着利齿,相互撕咬起来。只杀得天昏地暗,肚皮朝天,仍不罢休,大有古罗马角斗士“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之气势。再看那尚没格斗便叫声不迭的蛐蛐,正如“怯”狗遇人便狂吠一样,那是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之表现,绝不是好虫子;只有胜利后才高鸣庆祝者,方为深藏不露之“英雄豪杰”。而主人与角斗场上的蛐蛐同样,斗赢了,兴高采烈;斗输了,则灰溜溜地“抱缸”而去。当然,亦有不服气者,信誓旦旦,扬言来日再战。
据说有人能让蛐蛐过冬,以好来年再战,我也想尝试。便找来黄泥放在蛐蛐缸里,让蛐蛐做窝。再在上面放些棉花、碎草之类,还有吃的,将缸搁在暖和之地,指望梦想成真。然而,不待冬天来临,那些宝贝疙瘩早就一命呜呼了,害得我失望了好一阵子。这,就是我,少儿时代曾做的一次“杰出”而天真荒唐的实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