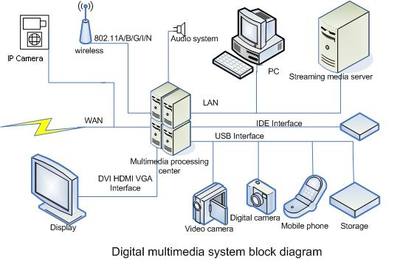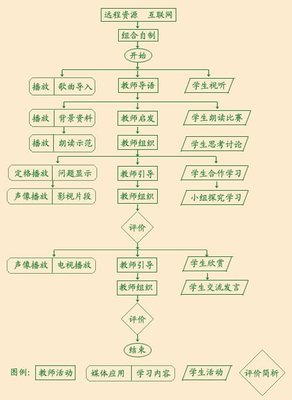第二次大致在革命文学大行其道之时。在走向大众化与以大众语言创作的背景之下,新诗创作形成了与后期新月派、象征诗风与现代派诗歌并行的另外一翼。此翼新诗对大众口语的运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方面,“说的是流动的,写的就成为固定的”[12] 90,口语作为一种活的语言,在刻绘的生动性上为书面语言所不能及,更易彰显出诙谐幽默的风格,巴赫金(M.M.Bakhtin)曾谓:“诙谐是专制的天敌。”故而,口语诗歌可以通过诙谐达到讽刺政治的效果。鲁迅就曾用上海方言创作出了《公民科歌》,诗作立意讽刺,有如此之言:“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大家切莫耶耶呼。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猡力如牛。第二着,先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第三着,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第四着,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做。”瞿秋白用北平话与上海话写就的《东洋人出兵》,以及模仿无锡景致小调所作的《上海打仗景致》,亦是着力于对时局的嘲讽。另一方面,口语贴近民众、取材民间的语言特质可以使左翼革命思想迅速向民间传播。左翼革命诗歌的渊薮中国诗歌会以集体性的创作去践行这一创作,他们的目标便是“要使诗歌成为‘群体的听觉艺术’,以便普及到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工农大众中去”[1] 274,为了使“诗歌应当与音乐结合一起,而成为民众歌唱的东西”[13],他们对歌谣、时调、弹词、小曲、鼓词等民间艺术形式进行利用与改造,从而创作出语言浅显俚俗,风格逼向歌谣化与大众化的诗歌。
第三次大规模的大众化口语诗歌写作出现在抗战时期,依然承继了上一次群众鼓动与时局讽刺的政治色彩。当时整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救亡主题成为压倒其它一切的思潮。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普通民众开始休戚相关,他们之间开始由文化上的隔阂而走向一体。“要使得诗重新成为‘听觉艺术’,至少是可以不全靠眼睛的艺术,而出现在群众之前,才能使诗更普遍地,更有效地发挥其武器性,而服务于抗战”[14] 102。为了对群众进行抗战的宣传鼓动,无论在诗歌的形式抑或是内容上,诗人们都不得不降格以求。继加工改造歌谣、鼓词、时调等民间说唱文艺后,又出现了街头诗、朗诵诗、口号诗、明信片诗、传单诗等新型而又便捷的诗歌形式。在解放区,由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主流文艺思想,大众口语诗歌的创作更是繁茂壮观,而解放区所处的地域文化亦为诗人提供了艺术上的源泉和灵感,如陕北民谣“信天游”作为一种抒情的民歌体,经过诗人们的转化,遂焕发出时代的生机,担负起革命宣传与启蒙教育的重任。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堪称此类诗歌的经典,除此之外,较著名的还有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以及阮章竞的《漳河水》。这一时期讽喻时局的口语诗歌大多集中在国统区,最为著名的是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诗集中的诗作多用方言创作而出,前期多为重庆的四川方言,而在后期诗人至上海后,又采用上海方言。方言中的俚俗特点很好地成为了诗人针砭时弊、嘲讽揶揄的语言工具,而同时更能为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从而带来口耳相传的核裂变式的传播。以马凡陀作为笔名的袁水拍也确实让“马凡陀”这个笔名深入到下层市民中间,以波及之深广实现了新诗大众化的目标。
第四次是解放之后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更是将新诗的大众化推向了盛况空前的图景。对此,徐迟在他的《诗与生活》中有着饱满而热情的记录:“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几乎没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这场“新民歌运动”由“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样的创作主体构成,普及面之广,几乎达到了“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新民歌运动”的特点有二:“一方面,通过行政命令限时限量、高指标高速度完成创作,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运动受到‘运用质朴生动的民间语言、捕捉新时代气息’的良好愿望的支配,民歌创作成为表达人民向新的时代、社会感恩的方式和手段”[8] 59。这是以政治力量为动力,将政治、宣传口号进行歌谣化的一场运动,显然也是借助了大众化语言便于传播的优势——“在语言、格式和表达上,它的明朗、口语化,大体整齐,易诵易记的特点,与大多数以书面语作为媒介,和某种程度上曲折、晦涩的新诗构成对比,在大众接受和承担政治动员上,将发生更有效的功用”[15] 82。毛泽东认为:“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6] 124“新民歌运动”可以看成是“五四”以来新诗走向“大众化”、民间化乃至民族化的一次努力。但是,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次努力最终的结局是失败的——由于政治的过度干涉,使得这种“古典”+“民歌”的模式仅仅成为政治教条的载体,其承担过多的政治宣传任务,也就远离了真正民间的声音。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那么,这种立足载道的文体很难说具备了多少诗歌的元素。这种与政治过分媾和的大众化的“新民歌”进入“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曾经辉煌的光景便消失怠尽。八十年代前期涌现的朦胧诗开始重新彰显对“个体”精神价值的强调,充满着“启蒙主义”的激情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以诗歌的形式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行解构,那么反映在诗歌的语言上,那么便是一种“异质性”,以朦胧、晦涩、含蓄、含混见长,在特定意识形态下表现出“语言的反叛”,即“拒绝所谓的透明度,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合作”[17]XVI。
第五次大规模的口语化写作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日益巩固,社会生活也日益世俗化,一般公众和知识分子曾经高涨的政治热情和启蒙精神都开始萎缩;而随着影视等现代媒介的普及,国家对诗歌也不再需要作过多的宣传任务,民众的精神生活也开始远离“纯文学”,此时的诗人面临着四顾皆茫然的尴尬历史境遇,于是他们笔下的诗歌只得开始关注琐屑、平庸的个人生活,这一时期掀起的平民诗风使得新诗在语言上又呈现出口语化的倾向。对于其积极意义,姜耕玉先生认为此时的口语诗歌以“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和情绪,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18] 23。
口语作为因素之一,和“欧化”白话、古典语言一起共同成为作用于中国新诗语言的重要因素。可以发现,诗歌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语言的问题,诗歌和语言是共同发展,双向互动的,正如F.W.贝特森在《英诗和英语》中所说的那样:“一首诗中的时代特征不应去诗人那儿寻找,而应去诗的语言中寻找。我相信,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话语”、八十年代的“语言意识的觉醒”和语言论转向,这一次次语言上的变革都导致了新诗所产生的相应变化,同时,新诗创作上的成绩也巩固了语言变革的基础。中国百年来新诗的流变和语言存在着一种休戚与共、如影随形的关系,那就是——言文互动。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A].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4]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5]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钱锺书.七缀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7]寒生.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A].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8]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石灵.新月诗歌[J].《文学》8卷1号.
[10]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1卷[M].花城出版社与三联书店分店1984.
[11]沈奇.口语、禅味与本土意识[J].创世纪诗刊·春季号,1999.
[12]朱光潜.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13] 穆木天.关于歌谣之制作[J].新诗歌·2卷1期,1934-6-1.
[14]任钧.新诗话·略论诗歌工作者当前的工作和任务[M].两间书屋,1948.
[15]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7]刘禾.持灯的使者[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18]姜耕玉.汉语智慧——新诗形式批评[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The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linguistic evolvement of new poetry during hundreds ofyears in China
Abstract:From the birth ofthe new poetry in the May 4th period, its languageproblems came into the field of vision of many creators andresearchers. Without the complete overturn of language, the May4th new-poetry movement could hardly have avoided themisfortune of failure like the poetry revolution in the late QingDynasty. What’s more, it would never have had the prosperous stageof the new poetry in the next hundreds of years.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poetry, its development was interactivewith the evolvement of langu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oetryis meanwhile the evolvement of language, that is, the interactionbetwe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riefly, the linguisticdevelopment of new poetry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ree factors,namely, the Europeanized language,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thecolloquial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se three factors, thisessay is trying to clear out the linguistic evolvement of newpoetry during hundreds of years in China.
Key words:the interactionbetwe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ewpoetry;Europeanizedlanguage;classicallanguage ;colloquialism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