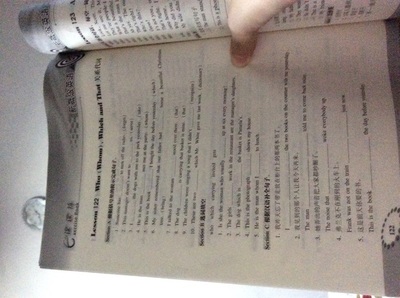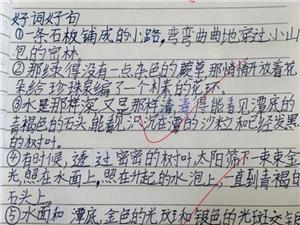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社会活动家。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丁玲文集》6卷。
1904年,生于湖南省安福县西乡黑胡子冲村(今临澧县佘市镇高丰村);父亲蒋保黔为清末秀才,在丁玲4岁时去世,母亲余曼贞带她去了外祖父家,后任教师供她上学。
1918年,丁玲考入桃源县的湖南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与王剑虹同学;
1919年,转入长沙周南女中;
1922年,夏,好友王剑虹从上海回乡,带丁玲前往上海,入上海平民女校,改名丁玲;
1923年,与王剑虹共入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
1924年,王剑虹与老师瞿秋白相爱并同居,丁于夏季只身赴北京,欲进北京大学学习,无果;认识《京报》副刊编辑胡也频;
1925年,与胡也频在北京同居;
1927年,12月,在北平写成并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
1928年,2月,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轰动文坛;年底丁玲追情人冯雪峰至上海,胡也频随后也追去,之后三人到杭州谈判,冯雪峰退出;
1929年,胡也频因欠债到去济南教书,不久丁玲也到济南;
1930年,5月,因胡受到通缉,双双逃回上海;
1931年,2月胡也频被枪毙;担任“左联”刊物《北斗》主编,11月与翻译冯达同居;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与冯达一起遭国民党当局绑架;
1936年,逃离南京,抵达陕北,先后担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等职;
1942年,38岁的丁玲在延安与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
1948年,发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949年后,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
1951年,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金;
1955年,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主要成员;
1957年,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被划入右派后,受到各种迫害,包括下放北大荒,投入监狱等;
1979年,被平反,并重返文坛;
1986年3月4日,逝世。
——-据维基百科
《过年》(1929年,短篇小说)、《母亲》(中长篇小说)、《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1979年,散文)、《我的自白》(1931年,演讲)、《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1946年,散文)、《小火轮上》(1929年,短篇小说)
丁玲的母亲于曼贞是辛亥革命之前妇女解放与自立的先觉先行者。这个三十多岁、有两个小孩子的寡妇,面对日益衰败的家庭和社会,毅然卖田卖屋,和五六岁的丁玲一起上学读书。在丁玲母亲的那些同学里,便有中共早期的革命家向警予(向大约即是《母亲》里夏真仁的原型)。丁玲有这样一位开明的母亲,无疑受到其影响是非常之巨的。丁玲在《魍魉世界》里还回忆,每到她处境艰困之时,这个了不起的母亲便默默地承担了照顾丁玲子女的重担,并给与了她精神上的支持。
《母亲》写到小城武陵发生辛亥革命止,是一部似还可以写下去的小说,其艺术特色虽然并不突出,不过它的描写相当写实,保持了丁玲早期作品扎实的细描功夫。《母亲》的社会意义应该是更大的,中国妇女千年来受裹脚之害,以中上层女性尤烈,下层的劳动妇女因为要劳动的缘故,裹脚的倒少,“一些乡下女人,山上也去得,水里也去得,”为害尚小,可是一些大户人家的女性,有的竟把脚裹小到只有“两寸多”,弄到连行走、站立都很困难,束缚到只能当迈不出家门的家庭妇女,丁玲母亲那一辈中上层妇女,不仅要经历裹脚一苦,还要经受放脚一苦,她们凭借觉醒而生的毅力,艰难地向社会迈出了她们勇敢的一步。
丁玲在另外一篇小说《小火轮上》里,写了知识女性在内地闭塞的环境里难以容身,被迫向外流落的境遇。
《暑假中》、《岁暮》(短篇小说)
《暑假中》里的一群新式女教师、女学生,她们在时代遽然而给予她们的一份小小的自由天地里,心魂不定,伴随着初时觉醒而生的那份女性意识、性爱意识、生活情趣、审美意识是有些浅薄,甚至是有几分可笑的,不过她们的青春的苦闷与焦渴依然是真实的,她们在无法获得如意的异性的友谊和温情的时候,她们甚至想紧紧拥抱着她们的同伴取暖,甚至有几分近似同性恋的心理,只不过她们焦躁的心性让她们又彷佛变成了一只只相互难以挨近的刺猬,她们挨近,刺疼,分开,再挨近,再分开,再挨近,如是而已。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980年,散文,回忆录)
丁玲的第一个好友是瞿秋白的第一个爱人王剑虹,这个“美人如玉剑如虹”的王剑虹是桃源那所师范闹学潮的学生,算是把丁玲带到广阔天地里去的第一人。丁一生虽然跌跌撞撞,可是她大约总是她其时的那个社会的主角之一,其经历甚富,遇人甚多,与中共两个领袖人物瞿秋白、毛泽东皆颇亲密接近。瞿毛在做政治家之余,皆是文学家,尤其是瞿秋白,其文学才华在中共的政治家中当属第一,即使在现代的文学家中也算称一流。我曾在一家书屋里看到过一册旧的厚厚的瞿的文集,那是瞿探讨语言大众化的专门文字,前不久又在武汉的一家旧书屋里,也偶遇到那本著名的鲁迅在瞿逝世后编的瞿的译文集《海上述林》,摩挲两书甚久,最后我都是轻轻叹口气放下了,因为我即使有心,也可能无力无暇来读一读瞿的这些文字了。
如今还会有谁关注瞿?我所见有限,只记得当代的红色作家梁衡写过一篇《觅渡,觅渡,渡何处》的文,算是瞿作为一个政治家在百年后遇到的一篇知音吧。现在读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觉得丁在数十年之后,是完全理解了作为一个革命家的瞿的,她甚至能完全理解了瞿之灵魂,可是对作为丁之密友、瞿之恋人的王剑虹之死,丁对瞿的怨仍耿耿在心,一直难以完全消除。丁玲经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真是老了也没能变得世故起来,还是那个直率脾气。
要不是读丁文,我对瞿王之恋尚无所知,不过我颇熟悉瞿秋白与杨之华的恋情。我最初在郑逸梅的《艺林散叶》里见到一条大意“瞿秋白为杨之华治‘秋之白华’印,具巧思”的记叙,后明白这印还可读为“华之秋白”、“白华之秋”,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意,觉真巧!又听说杨之华原是有丈夫的,只是那是个让杨失望的不成器的世家公子而已,杨离家跑去上海大学求学,其时瞿即杨之师。王剑虹病故后,瞿杨相恋,他们结合的障碍当然为杨之夫婿,瞿与杨之夫谈,杨夫倒明理,深为瞿之魅力折服,后在同一天同一张报纸上他们刊登了杨与夫离婚启事、瞿与杨结婚启事及三人成为好友的启事,瞿杨婚礼且这前夫出席,如此的风流佳话,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却有,在今天这社会倒似乎绝迹了。
《梦珂》(1927年,短篇小说)
初以为《梦珂》是以王剑虹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因为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里,丁玲说:“秋白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读后才知我的想当然是完全错误了。
那时的妇女解放潮流,多以女子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到一个更加开放的地方去求学、工作或者做社会运动为时髦,可是她们寻路难,行路难,一旦走出去,再回首即便觉得故园虽好,也再回不去;可是面对都市的凡庸、虚伪、压抑,她们即使不甘心,可是却也往往不自觉地坠入到庸俗的环境中,尽管这环境正是时代精神所要她们去反抗的。大约因为人都是有重量的,所以似乎有天然下坠的重力,当一个人不能上升时,他她往往要么便停滞在平凡里,要么便会往下堕落、沉沦。梦珂的苦闷正是时代的苦闷。
《韦护》(1929年,中长篇小说)、《我的自白》(1931年,演讲)
在《我的自白》里,丁玲说:“《韦护》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又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里,丁玲这样谈《韦护》:“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因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做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
就像《梦珂》一样,《韦护》由于缺乏剪裁,因为素材运用的过密而显得有些芜杂,似不是可以令人十分满意的成熟之作,比较起来,我更喜欢《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更觉到真实本身的力量和动人,也许瞿秋白作为人的,作为文人的及作为政治家的一面,他的丰富的真实的存在是很难描摹的,而丁玲即使用小说去描摹,也是不大成功的。我对照《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瞿秋白与《韦护》里的瞿秋白,一时便很难把这两者联系到一起,我也不能从韦护爱着的丽嘉身上看到王剑虹的影子,不能从丽嘉的好友姗姗身上看到丁玲的影子,不过倒觉得丽嘉的个性是更像丁玲而不一定很像王剑虹的,这个臆想是有些有趣的,因为从这个臆想出发,我觉得也许丁玲似乎透过这篇小说,投射了她自己心里也对瞿秋白存过一份隐秘的爱情,这因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可以让所有女人产生向往梦想心的男人。有一点是相同的: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里,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同居生活是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密不透风的;在《韦护》里,韦护与丽嘉的同居生活是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密不透风的;在沈从文的《记丁玲》里,胡也频与丁玲的同居生活也是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密不透风的。
《自杀日记》(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短篇小说)、《日》(1929年,短篇小说)
在丁玲早期作品所塑造的女性中,还真的难以看到像《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莎菲这样个性独特到令人难忘的人物了,一般的女人,也许只有一种心思,或者三五种心思,可是莎菲却似乎有一千种心思,一般的女人,也许只要有了一样便可满足,或者三五样便可满足,可莎菲却似乎要一千样也难满足,她的纷繁、她的矛盾、她的大胆的青春的欲念、她的要全,甚至比丁玲自己塑造的梦珂、丽嘉、姗姗、美琳这样一些女性的全部个性加起来都还要来得更丰富、更鲜明,可是这个女人又如此单纯,她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完全真实、完全忠于自己的女性意识的自我而已,当她找不到一个匹配她的完全理想的男人时,她最终宁肯选择孤独也不肯要那缺乏动人光泽,或者那缺乏灵魂的不完美的所谓爱,这样一个具有全新的现代意识的女性,被丁玲永远定格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册上。
《自杀日记》及《日》大约系《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雏形作品。《日》里百无聊赖度日的女子,和莎菲比显得很是单薄,但此篇小说开头的场景描写倒是非常宏大。
《阿毛姑娘》(1928年,短篇小说)
我之前根本不知道丁玲写有《阿毛姑娘》这样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恐怕只有丁玲才能写得出来,《阿毛姑娘》又何尝不是?这些都是非此人难以为之的独特的作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单单《莎菲女士》独享大名,而《阿毛姑娘》却如此籍籍无名?我读完《阿毛姑娘》,想找一找它的缺点出来,一时却难找出。表面上看,是现代文明的花花绿绿诱惑害死了一个淳朴的姑娘,可是如果丁玲想表达的是此,她大约只是个很一般的作家了。丁玲与沈从文同时出道,可是出道之初,丁玲似乎远比沈从文的思想来得复杂而成熟。在沈从文多年以后致力构建他的世外桃源“湘西世界”,沉湎于他的三三、萧萧、翠翠的纯洁淳朴时,丁玲已经早在《阿毛姑娘》里,塑造了一个像三三、萧萧、翠翠们同样“纯洁淳朴”的姑娘,是怎样因为向往外面的生活、向往那文明一点的生活而致癫致疯致死的。当一个人一旦觉醒,除了向前,向前,继续向前,达到更清晰更深刻的觉悟,他她是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原点了的,阿毛远比三三、萧萧、翠翠有深度的是,在她一步一步看似浅薄的感悟里,她最终明白了她过的生活并不值得一活,而读者也明白,这姑娘所向往的、无法得到的一切,都是多么正常又正当!
《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短篇小说)
写都市下层妓女悲惨的生活,写得好的,无一不有一份作者的同情悲悯心在里面,可是,如果像《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里的妓女,虽然她们也有一点儿平常女人的小小的希望,可是随后也便过去了,她们似乎乐得把那神女生涯当一份很正当的职业去做,未见得有什么委屈不委屈、苦不苦的,作者既如此写,读者当然便要尊重作者如此写,其实,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也都没有必须板起面孔、大发道德心去谴责她们什么的义务,因为,这是文学。
《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1930年)、《一天》(1931年)、《消息》(1932年)、《夜会》(1932年)(短篇小说)、《杨妈的日记》(1931年,短篇小说)
《给我爱的》(诗,1931年)
当普罗文学成为当时的一股思潮后,丁玲参与左翼文艺的工作,胡也频和她的转变都是颇为彻底的,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事业,不过很多当初很时髦的作家赶不上这趟,变得“落伍”了,如早期的普罗作家蒋光慈就是一个例子,记得郁达夫在《光慈的晚年》里记:“据吴女士(蒋光慈之妻)谈,光慈的为人,却和他的思想相反,是很守旧的。他的理想中的女性,是一个具有良妻贤母的资格,能料理家务,终日不出,日日夜夜可以在闺房里伴他著书的女性。‘这,’吴女士说‘这,我却办不到。因此,在他的晚年,每有和我意见相左的地方。’……又听一位当光慈病殁时,陪侍在侧的青年之说说,则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精神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光慈晚年每引以为最大恨事的,就是一般从事于文艺工作的同时代者,都不能对他有相当的尊敬。对于他的许多著作,大家非但不表示尊敬,并且时常还有鄙薄的情势,所以在他病倒了的一年之中,衷心郁郁,老没有一日开畅的日子。此外则党和他的分裂,也是一件使他遗恨无穷的大事,到了病笃的时候,偶一谈及,他还在短叹长吁,诉说大家的不了解他。”为什么读《一九三0年春上海(一)》让我想起蒋光慈来?因为这小说里的那个脆弱的、落伍了的作家子彬,连同社会对子彬的一般的态度,实在是像极了蒋光慈的,子彬的同居者美琳,也是离开了他而走向了社会运动,留下了愤懑的、孤独的作家在那里独自自恋自怜。
其实知识分子深入(城市底层)民众、动员民众是非常之难的,《一天》里既写了他们真诚认真的态度,也写了他们不为民众理解和接受的难堪与狼狈,不过《消息》里,他们终于获得了朴素的理解、盼望和拥戴,《夜会》里,群众已经被组织了起来,到《杨妈的日记》,他们已经从精神上、文化上做起了群众启蒙工作。《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二)》与《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并不是连续的小说,它写一个小资产阶级女人和已变成革命者的旧恋人之间重聚、同居又分手的事,无疑,这又是一个“革命加恋爱”的故事,那个望微的形象有几分胡也频的影子,但与丁玲能和胡也频共同参加左联活动不同,小说里的女主角玛丽根本无法融入望微的社会革命活动。大约以蒋光慈始,初期的普罗文学便形成了一个“革命加恋爱”的范式,早期的丁玲也未能免俗,以致在她写了《水》后,茅盾评论说:“《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无论在丁玲个人,或文坛全体,这都表示了过去‘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已经被清算。”
《水》(1931年,短篇小说)、《法网》(1932年,短篇小说)、《五月》(1932年,散文)、《团聚》(短篇小说)、《奔》(1932年,短篇小说)、《松子》(1936年,短篇小说)、《一月二十三日》(1936年,短篇小说)
《鲁迅先生于我》(1981年,回忆录)
鲁迅说:“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丁玲当然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鲁迅的这话,一方面是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后他对她的声援,同时大约也是指很多的所谓无产阶级作家写的作品太坏,而丁玲比较起来又写得很好的缘故。《水》这一篇以1931年中国十六省水灾为背景写成的小说,我想不仅可以看作是1931年水灾,大约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历朝历代灾难史的一个缩影的,那种中国农民面对巨大灾难苦难所表现出来的温良、不屈、觉醒与抗争,是惊心动魄的,穷人穷到不能活命了,他们便是有绝大的力量的,这样的一篇场景视角宏阔,描写紧张有力,比报告文学来得更真实、也更富有文学力量的小说,恐怕是连很多男性作家也很难写得出的,可是却在丁玲这样一个女性作家手中写成了,并且整篇丝毫看不出半点女性笔墨通常的纤弱痕迹;《五月》也是雄浑的充满了力的社会素描,展现了作者对社会事件惊人的抓取能力和概括能力,这不能不令人惊奇湖南的男男女女,他们彷佛都是些天然视野开阔、洞悉社会及群众心理、拥有极大气魄的人,他们敢想、敢闯、敢做,做事情往往就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自然,他们写文学往往写出的也不是那样些风花雪月的小摆件。
鲁迅说“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这样的话,其实也非无因的空话,丁玲除了写过《一九三0春上海》这样一些赶潮的作品外,还扎扎实实地写过一些无产阶级的生活的作品。与鲁迅等早期的乡土小说时代相比,短短十几年二十几年间,中国农村受到的冲击是更大的,人民从农村到城市都急速地破产了,丁玲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饥饿写得最有力的作家之一,《奔》、《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里遍地饥饿,那些无以聊生、走投无路的饥民,简直生活在人间地狱里一般,《法网》里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城市贫民的悲哀和苦难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社会的贫穷把一群善良的、可怜兮兮的人逼疯、逼到杀人了的地步。也不仅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无法生存了,《团聚》里旧官僚一家,老老少少也无以为存,那是到一个社会将要崩溃的前夜了。
《诗人亚洛夫》(1932年,短篇小说)、《多事之秋》(未完稿,1931年,短篇小说)
现代中国是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的社会,在那时外国殖民者所谓“东方乐园”的中国里,不仅有外国的各色高等有产者们,还有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中国的一些破落的流亡者及“(印度)红头阿三”们,诗人亚洛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俄国的流浪者,他们虽已如残枝败叶,可是却可笑地留念过去时代的好日子,根深蒂固地保持着高人一等的可鄙心态,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张牙舞爪,助纣为虐,丁玲为这些丑陋的人画了一幅辛辣的漫画像。
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丁玲就写了反映沪上民众抵抗情绪的《多事之秋》,这篇小说手笔虽大,惜表现空疏,艺术性并不强。被国民党幽禁后的中前期,她的创作差不多便中断了。
《田家冲》(1931年,短篇小说)
其实丁玲成功清算了“革命与恋爱”的,并不仅仅只靠一篇《水》,还有《田家冲》等。《田家冲》里的三小姐,是城镇士绅阶级家庭的反叛者,因宣传革命思想,被父母送到了乡下佃户家去幽禁,可是她偷偷发动周围群众,并慢慢使这佃户一家觉醒,加入到反抗压迫剥削者的队伍中来。这是一篇毫无范式化的小说,一切在静美的田园和一群极端善良与辛劳的人群里自自然然地展开,自然的美和人情的美让人深深沉醉,更由于湖南湖北的普通乡村生活与人民的方言十分接近,读《田家冲》,让我一下子有了回到了童年时候一样的亲近感觉。
《仍然是烦恼着》(散文)、《不算情书》(1933年,书信)、《一个真实人的一生》(1950年,散文,回忆录)、《从夜晚到天亮》(1931年,短篇小说)
在《不算情书》这封致冯雪峰的信里,丁玲说到她和胡也频的关系,她说:“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作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外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到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可同时,丁玲遇到了冯雪峰,她告诉他,“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但这个让她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男人,终无缘和她走到一起,直到1957年,在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后,他们在政治上才终于拥抱了共同的厄运。1972年,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里,回忆冯雪峰在湖北咸宁向阳湖边下放劳动的情形,十分感人:“冯雪峰主持一片菜园,终日徐行畦町间,好几次见到拄锄于颐下,注目新长菜苗,如有深忧,满头如雪,而面目古朴严肃如西汉壁画,令人起严肃感,不易忘也。”
丁玲一生都是个敢爱的女人,她在文字里,几乎从来没有讳言她生命中出现过的四个男人: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不算情书》是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一封滚烫的信,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写这样热烈的情书,大约只有石评梅、卢隐写过,在延安压抑的时期,她在《风雨中忆萧红》想到的首先就是冯雪峰;在胡也频死去20年后,丁玲为胡也频文集作序,写成《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的回忆录,既抒发了对胡的感情,同时也表达了她对他的性格与精神的深切的理解,像为瞿秋白一样,在纸上,丁玲为胡也频建立了一座庄严的纪念碑;在《魍魉世界》里,丁玲记录下了与冯达的同居生活;在《“牛棚”小品》和《初到密山》里,她记下了陈明与她不弃不舍的深情。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在沈从文的护送下把孩子送回湘西交其母亲抚养,自己又回到了上海,她在《从夜晚到天亮》里记录下了在上海时的那段生活与心境。
《魍魉世界》(1981年,长篇回忆录)
1933年至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绑架事件,最终促使她逃离国统区,奔赴延安,从而从一个异见反对者一变为一个更加坚定的革命者,这一部《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很详细地回忆了整个事件的经过。由于那是一段曾经有争议的历史,在丁玲“文革”之后写成的这部回忆录里,她甚至不得不为自己的历史辩之凿凿,确定自己如何之坚定不移,尽管她的辩解也确实是站得住脚的。当社会与政治太严酷时,清白者也都必须竭力自证、自辩其清白与正确无误和完美无瑕,几乎不能、不敢袒露一点意志的软弱和心性的徘徊。
沈从文《记胡也频》、《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传记)、《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报道)、《某夜》(短篇小说,1931年)、《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1931年,短篇小说)
左联时期,胡也频等被杀,丁玲被绑架,是整个文坛为之牵动的事,茅盾为之写过《丁玲传》,鲁迅写下了《悼丁君》的诗:“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等还与国际上的一些知名人士联名写过呼吁书。
胡也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客,他的作品现在再版很少,也没有多少人读,我手头只有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北风里》,是一篇类似沈从文早期作品的纪实性小说,讲年青的作家在艰难困苦里是如何坚守文学的。沈从文的回忆文字《记胡也频》,颇长的篇幅,大约因为篇幅过长,《记胡也频》和《记丁玲》都不见于沈从文一般的散文集子。我是从沈虎雏编的沈从文的一册文集《友情集》中偶读到这记胡也频的文字的,初读时看着沈、胡、丁这一群不畏艰苦,性格坚定,乐观的,有理想的,奋斗着的,有为的,优良的文学青年,得到的印象极好,沈的一些士兵朋友被杀了,他的一些文学朋友也被杀了,这些文字的意义,是引起人们问,是这么些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好好地活在这个世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沈是他们的朋友,这是沈一点一滴的真真实实的见证,这比其他别的人更有说服力,沈是要人们记住这些人,不要忘记了他们,他们在沈的笔下是那么鲜活,从此永远地活在了纸上,的的确确让我们深深地把他们记住了。
以前中国的作家,似乎很不习惯写像外国作家那样长篇幅的人物印象记,中国作家写的,多是两三千字的传统散文,仅及一个人突出来的一点或几点,不如读了外国作家那样枝枝节节的文字可以多方面地感受一个人。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其实不过是高尔基回忆托尔斯泰一类文字的仿作,文体稍一变,就让不少人大声地叫好。但现在晚近读到的好的人物印象记倒是有好些了,如巴金写的萧珊,杨绛笔下的钱钟书,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里写的诸人,都是十分好的文字。不过应该说,沈从文的《记胡也频》和《记丁玲》,似乎为这类文字之滥觞。
沈的《记丁玲》写的是作为一个青年女人的丁玲,而《记丁玲续集》则写的是作为地下革命者的丁玲。丁玲晚年读到沈写的这本书,因为其格调低而怒,两个朋友就此便成了敌人仇人一般。丁对沈进行了攻击,丁是怎么攻击沈的,我不知道,不过沈背后议论丁的一些句话,却也让我足够地吃了一惊。那是沈晚年和助手王亚蓉在火车上聊天,王说:“她跟胡也频时,不也跟冯雪峰吗?”沈答:“是的,她可以说乱得很,长得又不好。跟萧乾也有来往,萧乾不理。”王说:“齐光说,那时她在延安使劲追彭德怀。”沈答:“彭说我不愿意看她。没办法,老太婆啦!”(见《沈从文晚年口述》)说实话,沈给我的印象差不多都好,就是这些话让我感到不好,因为这些话听起来实在并不好听。
我读《记胡也频》、《记丁玲》,感到这三个人的友谊原真是极好的。沈笔下的丁玲,虽然不是太绝色的美女,可是“圆脸长眉大眼睛,”也是很可爱的。有人说他们似乎有过三角恋爱,我觉得这个不好说,我估计沈丁两人大致没有多少男女的爱情,但友谊一定是很深的,沈对丁可以说也十分的仗义。胡被捕,只有沈那么尽力地为之奔走;胡被杀后,是沈陪丁送孩子回湖南;丁被捕,也是沈大声凛然为之疾呼。而一部《记丁玲》为什么让晚年的丁玲那么生气?这书一九三三年就写了,我不清楚为什么丁玲到一九七八年前后才读到。其实一本《记丁玲》,记丁玲个性之自由,意志之坚韧,人格之素朴,情感之丰饶,皆让人感到丁是一个很是有迷人魅力的女人,丁应该没有太大的生气的理由的。不过一九七几年,那可是一个很政治的时代,我记得一九八几年,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都还被称为“黄色歌曲”,歌带都要遭收缴查封的,所以一九七几年刚被“解放”的丁玲会是多么恐惧《记丁玲》里提到的她与叛徒冯达同居这样的一些历史呵,这是出于政治的恐惧;再沈下笔也太真实,不少地方把青春的丁写得很饥渴的样子,写她那个年龄臂膀要拥抱嘴唇要亲吻,且还有一段写丁胡婚后吵架,胡跑去找沈,沈似乎觉察胡不怎么懂床上哄女人的事情,就授给了胡一些机密,果然事后丁胡两人如胶似漆的。这样的描写让人几乎忍俊不住。当丁玲看到《记丁玲》里的自己这样情色狂的样子,作为女人的她又如何不又羞又恼呢?
1931年7月,丁玲写《某夜》,截取了一批革命者义无反顾走向刑场被屠杀的一景,是丁对胡也频们的纪念。在《莎菲日记第二部》(未完稿)里,莎菲已经不是《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那个虚构人物而还原成丁玲本人了,她在里面草草地记下了她失去胡也频后的恓惶心境。
徐志摩、邵洵美《珰女士》(中长篇小说)
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丁玲记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最终,徐志摩、邵洵美、沈从文的努力都是有限的,没能挽回胡也频的生命。可是沈从文、徐志摩、邵洵美都用文字对胡、丁进行了声援,表达了他们对这两个殉道者般的人的敬意。徐、邵《珰女士》里所谓珰女士,喻丁玲,也许取的“玲珰”之意,“黑”喻沈从文,当是因为沈、胡、丁三人合办过《红与黑》刊物的缘故,“蘩”喻胡也频,但不知其用意。《珰女士》写蘩被捕,珰、黑以及廉枫(喻徐志摩)、云(喻邵洵美)为之徒劳无望地奔走,其主干情节几与沈在《记胡也频》、《记丁玲》里的记叙相同。
当时的丁玲,在作家们眼中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可同时,那些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男人们,对她瞩目也侧目,看丁玲的眼光时是桃色的,在他们的心目中,丁玲差不多就是一个莎菲,多认其多情甚至滥情,如这部邵洵美续徐志摩《珰女士》之作,想当然地映射沈、胡、丁之三人恋情,甚至更进一步,写珰对蘩、黑、廉枫、云均怀有男女恋情,邵洵美的这臆想实是有点儿自作多情了,如果说邵如此是出于创作的臆造,可是这又近乎于造谣,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种对人对事较为严谨的态度。
《我怎样来陕北的》(1939年,散文)、《七月的延安》(诗歌,1937年)、《到前线去》(1936年,散文)、《彭德怀速写》(1936年,散文)、《河西途中》(1937年,散文)、《冀村之夜》(1937年,散文)、《一颗未出膛的枪弹》(1937年,短篇小说)、《马辉》(1938年,散文)、《秋收的一天》(1939年,散文)、《战斗是享受》(1941年,散文)、《十八个》(1942年,散文)、《二十把板斧》(1943年,散文)、《三日杂记》(1944年,散文)、《田宝霖》(1944年,散文)、《老婆疙瘩》(1944年,散文)、《“海燕行”》(1946年,散文)、《说鬼说梦的世界》(杂文)
丁玲投奔延安,受到高度礼遇,毛泽东亲笔作《临江仙》一词赠与她:“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看其时的丁玲,把自己改造得几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她穿着红军或八路军军装,下前线宣传,上荒山劳动,一变得肥胖,臃肿,粗豪,把自己女性的意识和风采泯灭到几乎尽失,其文学也更左一步,从左联的文艺跨进到革命的文艺,很忠实地实践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但这些在战争倥偬中写下的文字,除了《我怎样来陕北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彭德怀速写》等少数几篇尚可一读外,其余粗糙到几乎没有多少阅读的价值。
《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年,短篇小说)
当我们没有仔细去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当然地臆想他她!如我曾臆想,丁玲到延安之后的岁月,她写出过好作品吗?这样自问后,我的脑子里不知怎么会那么武断地自答:“她肯定没有,到延安之后她的所有作品都不值得一读。”所以在我的意识里,无端地以为《我在霞村的时候》根本就不值得去读。
但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后,我要说它确实是一篇值得一读的作品。丁玲说到陕北后,她的感情“变得很粗”了,可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她是不会那么容易就把她的敏锐的感觉完全丧失掉的,丁玲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得到了延伸,一个被很多日本人糟蹋过,染上了难医的病症的“破鞋”女人,她会嫁给“有良心的”、“短小精悍、很不坏”的革命战士、自卫队排长夏大宝吗?记得毛姆有一个叫《伯莎与克雷笃克》的小说,里面的丈夫克雷笃克是一个身体健壮、道德毫无瑕疵的所谓好男人,可是却偏偏又是个缺少趣味与灵魂的男人,这样的一个男人当然是留不住一个精神健全的女人的了。在《阿毛姑娘》里,当阿毛的心灵与精神慢慢觉醒时,她那心灵和头脑同样粗浅的丈夫根本无法觉察与回应她,只能莫名其妙傻愣愣地看着她毫无留念地死去。同样的,整个霞村里的人,包括“有良心的”自卫队长,都无法了解那个失贞的、名字叫贞贞的姑娘的心灵和精神世界,这个坚定、决绝的女人,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村子,走上了她认定的路。在这样一篇小说里,丁玲带着理解、赞赏态度写的这个女人,是完全没有什么革命需要的革命感情、阶级感情的,这个女人甚至无情地嘲笑和践踏了那革命战士的感情。
《夜》(1941年,短篇小说)
《夜》似乎是某个未完成的中篇或者长篇小说的一个片段,丁玲到底是很优秀的作家,在延安时期,她也没有完全沦为一个粉饰、讴歌时代的歌者,当她按现实来写作时,《夜》等的现实感便凸显出来了。《夜》里的农会干部何华明文化程度不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严肃、认真,有热情,有由衷的自豪感,在他眼里,很多人、很多事已经是“落后”的了;他是一个没有脱离土地的干部,对土地、对耕牛充满了很朴素的感情;他厌恶他的老婆,想和这个又老又丑的老婆离婚,除了不再对这女人有身体上的兴趣外,她不能给他生孩子也是他想离婚的莫大理由之一;何的妻子除了可嫌之外,却也又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女人,在何的朴素的意识里,即使他和她离婚,他也会把房子、土地、家具、耕牛等都给她;村里年青的妇联会委员侯桂英也想和丈夫离婚,并且诱惑式地喜欢着何华明,可是何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欲望,他的唯一的理由却是“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这短短的一篇小说里,没有一个人是脸谱化的,他们都是没有超出他们的生活与经历的有血有肉的丰满的个体,又如地主的女儿清子,这个妖娆诱人的姑娘,她“倚在门边,无言的眺望着辽远的地方。”这个姑娘又是在向往着什么呢?丁玲寥寥几笔写下的这个姑娘,也令人十分难忘。
题材是没有好坏的,只有表现的好坏。丁玲到延安后的这一些作品尚保持了她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真正的的水准。
《“三八节”有感》(1942年,散文)、《风雨中忆萧红》(1942年,散文)、《在医院中》(1941年,短篇小说)
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文人中不合时宜的王实味、丁玲,还有吾乡的吴奚如等成为一时批判的对象,王实味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吴奚如从此名不见经传,丁玲载浮载沉。其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成为大受争论的作品,据说毛泽东亲自发话要保丁玲,这样她才算过了一关,毛当然是要保丁玲的,因为丁毕竟是第一个进入解放区的知名文人,受到过他、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树大树,毛不保她,恐怕是自打耳光的事。那时的延安,当然有令人向往的朝气,可是它毕竟首先是一个政治之地,在一切强调政治、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环境下,天性自由的敏感的文化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自然首先感到了切肤的不适应,恰其时,受大鸣大放的号召一鼓动,他们便稀里哗啦把感到的、看到的不合理的现象全给倒出来了,不想随后便受当头棒喝。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提出的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等问题是相当尖锐的,尽管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善意的,即使今天读来,它们也是浑身是刺、可以伤人、可以让人不能舒服的作品。文革时,李建彤被指用小说《刘志丹》反党,其实按文革那个逻辑,丁玲才当是用《在医院中》等小说反党的第一人。大约因为受到了批判,那时丁玲的心情显得相当的抑郁,甚至有些的愤懑与悲凉,这心境在《风雨中忆萧红》里表露无遗,在这篇著名的散文里,她感到环境的压抑与孤独,怀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无私无怨的冯雪峰,怀想着在政治生活中不改初心的瞿秋白,怀想着“少于世故”、与之交“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的朋友萧红,可是此时的丁玲、以后的丁玲,依然是个坚定的、没有丧失掉信心的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篇小说)、《给曹裕明同志的信》(1953年,书信)
现代中国的土地革命,始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那一时真是暴风骤雨,曾见过一份《中共海陆丰起义之革命纲领》,其上规定:“1、籍国民党者杀,2、反土地革命者杀;3、曾任文武官员者杀;4、曾充民团警兵者杀;5、曾充反动政府机关差役者杀;6、一切土豪地主劣绅者杀;7、讨债讨租者杀;8、还租还债者杀;9、藏匿契据者杀;10、立妾蓄婢者杀;11、不服征兵役者杀;12、当堪舆命卜者杀;13、当巫婆媒婆者杀;14、吸鸦片者杀;15、惯作盗窃者杀;16、盲目者杀;17、麻疯者杀;18、残废者杀;19、老朽不能操作者杀;20、信仰一切宗教者杀。”这实在是离谱得有些可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反思这段历史,说“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存在着严重的‘左’的错误,如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是没收一切土地,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主张把一切反革命杀得干干净净;规定‘不革命不得田’,等等。”后来在1947年共产党即将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再次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山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使农村各阶级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贫、雇农基本获得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但是,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倾向,主要表现为:有的因划分阶级成分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政策界限,把部分劳动阶级(主要是中农)错误地定为地主或富农;在一些老区、半老区早已完成土改,且中农占多数的地方,仍然重新平分土地,侵犯了中农和靠自身劳动新上升的富农的利益;有的地区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分,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斗争,不给生活出路,甚至一度发生‘扫地出门’和乱打乱杀的现象。”(以上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如忆苦之作《高玉宝》里被唤作“周扒皮”的地主,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其原型人物周春富生前其实十分简朴,对伙计并不苛刻,可是土改时周春富被批斗的群众每人一棍子地打,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而周春富只是其所在地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1948年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到195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度,把农村人口划分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如此一直到大约1970年代末,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规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我出生在1960年代末期的农村,模糊中还记得一点斗地主的事情,那时那些地主、富农极其子女的日子真是难过极了,我做小孩的时候,也和别的同伴打过他们家的小孩,往地主家的屋顶扔过石头。记得一个地主临死前提出的一个最奢侈的愿望是喝一瓶汽水,等他家人到镇上买了一瓶汽水回家,那地主已经咽了气。恢复高考后,地主们的子女考上的格外多,当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似乎格外的聪明,现在看来,是他们学习格外刻苦,急于改变家庭及自己的命运的缘故吧。
在《田家冲》里,丁玲便在她的作品里触及土地问题,写1947年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算得上丁玲写的一部土地改革运动的史诗,这并不是一部图解式的枯燥的书,丁玲为写这部书,也曾亲自参加过几个月的土改,她几乎没让这个题材有什么沉淀,便迫不及待地写作,所以她笔下的农村农民一切都很鲜活,它的结构环环相扣地紧凑,又因为建立在真实的心理基础之上,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大变革时农村阶层所有角落里人们的期望与恐慌,这让这部书可能比一般所谓的革命书籍要真切、朴实、有趣。我看土地改革运动,其时的农民真的是普通的太穷了,赤贫者在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下几乎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地步,土地制度是到了非改不可,让农民获得他们该得的土地的时候了;地主里当然也有罪该万死的,可是这样的人毕竟并不是很多,地主也是有他们的社会道德的,并且很多地主富农的所谓富裕,往往不过是低层次的富裕,所谓“(地主)李子俊的甜馒头不错啊!”农民羡慕地主富农的也不过是能吃一口饱饭而已,农民在土改时斗地主的心理,往往是自己翻身了,担心地主将来报复,所以一不做,二不休,要么不斗地主,要斗就往死里斗,让那些地主富农永远不得再翻身。
《中国的春天》(1952年,散文)、《谈“老老实实”》(1950年,杂文)、《粮秣主任》(1953年,散文)、《记游桃花坪》(1954年,散文)、《重庆——曾家岩》(1957年,散文)、《诗人应该歌颂您》(1981年,散文)
《“牛棚”小品》(1979年,散文)、《初到密山》(自传一节,散文)、《远方来信》(1985年,散文)
《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口述自传)
建国后,那些文学家们很少没有不变主题,不走上“歌德一派”的,应该说,这些人大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可是那些文字,即使是有才华的作家勉力为之,它们离真正的文学也甚远,只能算是一些相对高明的宣传品。可是像丁玲这样尽心尽意讴歌党、讴歌新时代、讴歌新社会、讴歌新的人和新的事的人,却一下子被荒谬地打倒了,失去了二十多年的自由,身经无数的屈辱和折磨,却没有被真正地击垮,这个女人的身心实在是很结实、很顽强的。在《“牛棚”小品》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男人始终支撑着丁玲,这个男人就是她的第三任丈夫、一个叫陈明的衷心呵护陪伴她走过了五十年的男人。
陈明80多岁的时候,前后花了数年时间口述,由查振科、李向东整理出自传《我与丁玲五十年》,在这本朴素而深情的书里,已垂垂老矣的陈明讲叙了1937年后他与丁玲的全部生活,这对革命夫妻,相伴而行,患难与共,他们的爱情和际遇让人为之动容。
《歌德之歌》(1981年,诗歌)、《访美散记》(1983年,长篇连续散文)、《似无情,却有情》(1982年,散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1980年,回忆录)、《鲁迅先生于我》(1983年,回忆录)、《魍魉世界》(长篇回忆录)、《怀念仿吾同志》、《我是一颗小草》(1983年,讲话))、《杜晚香》(散文或短篇小说)
丁玲再次解放后,得到了很大的尊敬和荣誉,她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写了,一旦得到写作的自由,她以回忆录为主题,井喷似的写下了不少东西,其中尤以《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鲁迅先生于我》、《魍魉世界》的史料性和文学性最强。《杜晚香》作为丁玲复出的首发之作,塑造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新中国的朴素的劳动妇女形象,他们就是我们的母辈、父辈。步入老年的丁玲,精神尚未僵化、老去,她的那些来自人生深处的记忆,彷佛岁月燃烧后留下的结晶,散发出又辛又辣的馨香。这个女人的一生,以一个激情的勇敢者的奋姿开始,而以雕塑般沉静地眺望凝眸一段醉人的晚霞而作别,她遗留给世人的面影,终是迷人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