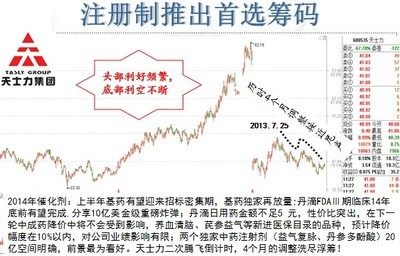当代二胡音乐创作透视
关铭
二胡音乐是雅俗共赏的音乐,二胡音乐文化是雅俗共育的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的文学艺术在“二为”方针的指导下,音乐的教化功能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而音乐的审美和娱乐功能已被人们日益淡化。二胡音乐是给人们听的,人们对一个作品的认知首先是从旋律开始的。我认为:二胡是一件以展示旋律为特长的线性思维乐器,从《病中吟》到《长城随想》记录着一部二胡音乐创作史,载入这部史册中的二胡作品,无一不是以旋律美而著称,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旋律美呢?我想借用孙维权先生在《中外名曲旋律辞典》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凡是人们所公认的优美旋律,大都是具有以下三种素质:
不同凡响就是运用独特的音乐语言向人们提供新鲜、别致、独特的音乐信息给人们特定的深切的艺术感受。
入情入理就是符合人们感情发展逻辑与音乐思维逻辑,好的旋律总是给人们既新鲜又熟悉的感觉。“新鲜”是指语汇独特,“熟悉”则体现了与文化传统及社会欣赏习惯的联系。一些作曲家的成功经验是:音乐语汇(单词)力求新鲜,而组成语汇的文法则注意符合传统。
一气呵成是指艺术上的整体性,包括语言要流畅自然,结构要前呼后应,风格要浑然一体。
这就是关于旋律美具体而生动的诠释。优美动听的旋律是作曲家的心声,是作曲家卓越的艺术创造,也是二胡音乐的灵魂所在。
上世纪70年末代到80年代初是二胡音乐创作大丰收的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唤醒了科学的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开了思想大解放的闸门,在“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哲学思考中,揭开了二胡音乐文化的新篇章。文化寻根热潮的兴起,社会环境的大改变,专业作曲家的强势介入,将二胡音乐创作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专业作品提升了二胡音乐的品位,丰富了演奏技法,拓宽了二胡的表现力。天时地利、政通人和,一大批风格浓郁、技巧新颖、旋律优美、形式多样的二胡新作应运而生,如陈耀星的《战马奔腾》、刘长福的《草原新牧民》、张晓峰的《新婚别》、吴厚元的《红梅随想》、张式业的《一枝花》、朱昌耀的《江南春色》、周维的《葡萄熟了》、闵惠芬的《洪湖人民的心愿》、关铭的《蓝花花叙事曲》、刘文金的《长城随想》等等。这些大型的叙事曲、随想曲、协奏曲的集中涌现,标志着二胡音乐创作步入了新阶段。
80年代末至今二胡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新时期必然碰到新问题,产生新理念,使用新技法。二胡音乐创作无论从形式、内容、技法、理念,均进入多元时代,协奏曲、狂想曲、叙事曲、套曲、组曲的不断问世,标志着二胡音乐创作步入成熟期。二胡音乐艺术在创作、教学、表演领域已进入竞技时代。其间,一些带有探索性的新潮民乐作品相继问世,虽有一定数量,但属上乘者不多,但在这一时期内,仍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得到了业内外的公认,并快速传播开来,他们是:刘文金的《秋韵》《如来梦》、王建民的一、二、三狂想曲、邓建栋的《草原情韵》、关铭的《西口情韵》、高韶青的《随想曲》、朱晓谷的《倒板与流水》、刘光宇的《蚂蚁》、关廼忠的《追梦京华》等。在这一时期中,由于二胡演奏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众多作品中将高技术含量作为创作中的重点。笔者在《琴思弦韵》一书中读到王安潮先生的《中国二胡音乐交响化发展的史学研究》一文,文中列举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的二胡新作品共有90多首(大型居多),移植小提琴作品20余首,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出现这么多新作,可谓是二胡音乐创作的大丰收。产量之大,前所末有,但质量是否之高呢?值得商榷,近百首作品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品在象牙塔里流传,而广大二胡社会音乐市场却还是吃不饱,或者是吃不好,因为雅俗共赏的精品太少,让人‘三月不知肉味’的作品不多。如何将二胡作品的可听性与技巧性完美的结合,这是摆在作曲家面前的重要课题。在现实生活里某些作品中常常出现顾此而失彼的现象:注意了技巧性,忽视了可听性,注意了创意性,忽视了风格性,注意了作曲技术上与国际接轨,忽视了欣赏传统上与民同乐的现象。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胡是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想为二胡写作品,在语汇选用上,还是选用中国母语为好,中国人大多可以听得懂,这一点对于本土作曲家尤为重要,对于多年旅居海外的华人作曲家,由于掌握语种较多,语言较杂,中国话讲的不怎么流利,如果想为二胡写点东西,还是讲汉语为好,不要一会法语,一会德语,由于音乐语言不统一,弄得大家一头雾水,找不到北。在这一点上刘天华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十大名曲已为我们做了诠释,1927年,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中阐明自己处理中西音乐的指导思想是:“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刘先生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语言同民众对话,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曲式、旋律、旋法、调式、音阶都是民族的。总之他在用汉语讲话,用民族的音乐语言在陈述,符合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欣赏习惯,因为他知道他的服务对象是中国人民大众。这就是刘天华先生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平民音乐思想”的集中展现。
用二胡表达作曲家的心声,就要掌握二胡独特的语言规律、表达方式,用二胡自身擅长的语汇进行表述,就更能动人心弦。二胡音乐艺术要寻求可持续发展,创作应为龙头,二胡音乐创作一定不能离开中华传统音乐这片沃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接地气。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成功经验在于创作时找到了“根”,这个根深深地扎进了民族传统音乐的沃土之中,刘文金先生的优秀作品“都是民族音乐土壤中开出的鲜花”以及有着“民族器乐创作明确的,深重的使命感”。
近年来一些音乐艺术院校作曲系的学子们接受现代音乐教育多年,想在二胡上一试身手,写了些作品,但除试奏者之外,大多无人问津,应该总结经验,找一下不成功的原因。听这样的作品要修身养性,不要指望听一、二遍就可以听出名堂,如果有CD,听上十遍八遍的,最后还是听不懂,干脆别听,因为那不是给你写的。
自从我国申奥成功以来,奥运精神就在神州大地上传播:“更快、更高、更强”已经是家喻户晓的竞技目标。近年来,我们的二胡音乐创作,我们的艺术实践颇受这种精神的影响,好像不快,不高、不强就缺乏时代精神,不能与时俱进。其实这是一种片面认识,二胡音乐艺术有着自身的规律,属艺术生产范畴,不是竞技体育。这种现象在一些二胡作品中的表现是:高难度技术部分占的篇幅过多,太满、太挤、太吵,整体音乐缺乏对比,音量、音色,快慢、强弱等等缺乏统一布局,听这样的作品,容易产生听觉疲劳,感到很累,这就是作品中没有“留白”。“留白”是中国书法艺术中重要的手法,也是庄子“有无相生”哲理的妙用,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留白恰能尽显墨色”,一条线、一个点加上大片空白,却能给赏者留下无尽遐想。如果作曲家能将“留白”融汇贯通,出神入化地运用到作品中,他的作品就能天人合一而得其道、通其韵、晓其格,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相反,由于作品思维、理念、技法、离现实较远,没有民族根基,可听性差,很难得到业内公认,业外同仁更不敢问津,用傅庚辰先生讲的话来形容:“如果一个作曲家创作一部作品,指挥不愿指,演奏家不愿奏,听众不爱听,那就是作曲家的悲哀了”。
2006年刘文金先生在杭州讲学时讲到民族器乐曲创作时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民乐创作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出现了一批较有实力与前景的作曲家和作品,但是也出现一些怪异现象,如毫无人文意识,为所欲为的作品也不少,这些作品无章无序,言之无物,甚至有些是无理取闹。严格地说这些不是作品,而只是作业而已。一个日本作曲家说过一句有见地的话:中国当前某些作曲家的作品是正在走50年前日本一些作曲家走过的弯路。
刘先生还强调要探索符合中国百姓欣赏习惯和口味的创作理念。他说民族民间音乐是民乐创作者的母语。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作品既无人民性、又无民族性和可听性,并将炫技当“出新”的曲作者,还是回到中国现实生活中来才能大展宏图,因为你的服务对象是中国人民大众,这才是音乐艺术的根本所在。二胡音乐艺术要发展,二胡音乐创作要繁荣就“必须于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当代人保持亲近的关系,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表现他们的精神境界。哪一天疏远了、淡忘了,这门艺术也就萎缩凋敝了”②。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在中国音乐的发展过程中,以洋为重的所谓中西结合,我们得到的只不过是并不时髦的包装,而失去的则是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尊严”③。
在二胡音乐创作中,我坚守的是背靠传统·面向现代的理念,在具体实施中我坚守的是中国二胡·中国料理的操作流程。我的认识是:
一.风格·旋律·技巧三位一体完美结合是二胡音乐创作一种可取的创作模式。风格泛指中国风或地域风,无风则不成格,无格则不生韵。旋律泛指作品的律动、旋法,在这里可释为作品的可听性。技巧泛指作品的技术部分,无论是慢是快,都要恰到好处,要与作品内容联系起来,技巧的运用要溶入旋律之中,脱离内容的技巧是身外之物,是炫技,建议写成练习曲。
二.线点结合相辅相成。二胡是线性思维乐器,以展示旋律线条为其特长,以线为主,线点结合,方能相辅相成。如果点多线少,作品的歌唱性就会减弱,我把线比成唱,把点比成说,先说后唱,或先唱后说,或有说有唱都行,但决不可以只说不唱。
三.母语文化不可缺失。二胡是中国民族乐器,为二胡写作品还是选用中国母语为好,我的观点是:中国二胡·中国料理。说普通话、各地方言都可以,但不能说日语、英语,更不能说鸟语或太空语。母语是根,是源,二胡音乐创作一定不能离开传统音乐这片沃土,这就是接地气。母语在何处?在典籍之中,在传统之中,在人民大众之中……。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句。如果我们的作曲家能效
仿杜甫进入‘曲不动人死不休’的境界,那么我们的作品就可以传承开来。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一定要有恒心,有决心,有功力,有实力,且要耐得着寂寞。
四.两支队伍,三个面向。在二胡音乐创作中大致可以分成两支队伍,一是学院派(作曲系师生),二是院团派(表演艺术团体及非职业演奏者)。学院派的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主要面向音乐艺术院校教师、学子,作品大多在这个层面传承。院团派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大多和市场接轨,因为他们要生存,必须要面向大众、面向市场,满足观众的需求,同时他们还谱写一批短小精干、可听性强、雅俗共赏的二胡作品,面向非职业演奏者,满足他们的音乐文化需求,这是一支数目可观的队伍,是二胡音乐文化的基础力量,不可小视。
在学院派作品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技法新,理念新。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成熟作品,在圈内得到公认,列为比赛及音乐会常用曲目;另一种是作品尚不成熟,还在试验阶段,停留在作业层面。未到收获季节就拿来上市,为时过早。这些作品大多注重了创新性,忽视了可听性;注重了作曲技术与国际接轨而忽视了欣赏传统与民同乐的现象多有发生。
我常听一些业内人士说听不懂,这就是大问题。音乐是听觉艺术,一部作品拉起来不顺手,听起来不好听,言之无物,不知所云,费解难懂,是不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未解决?
我想,作为中国的作曲家有责任有义务扛起音乐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大旗,像曹雪芹那样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像杜甫那样进入‘语(曲)不动人死不休’境界。如能卧薪尝胆,耐得寂寞,方能谱写出反映人民大众心声,具有中华神韵、民族精神的新作品。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当今音乐界缺少的是音乐评论和音乐批评,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愿意讲真话、实话,这并不利于创作繁荣,今天我大胆的表述一下个人观点,不是批评,只求能引起重视。
在二胡音乐活动中我常听一些老专家说二胡界有三无作品(无调性、无旋律、无风格)和三累作品(写的累、拉的累、听的累),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界内的重视,为什么人的问题和如何为的问题仍然是我们文艺界的指导思想,不能忽视,更不能忘记。一位音乐艺术院校作曲系的学生告诉我:他老师说了,别人吃过的东西你不要吃,别人用过的技法你不要用,我怎么办?我说:老师是让你出新,另辟蹊径,你在学习阶段,不吃就会饿死,不用就会困死,还是现实点!更有意思的是近日在西安院听一位二胡毕业生音乐会。其中有一首现代作品,这首作品在某某比赛中获二等奖,听完后,坐在我身旁的一位70后某团二胡首席问我:这首作品为什么是二等奖?我说不知道。他十分风趣地告诉我,因为它没有一等奖那么难听。我笑了。我想没有生活、没有服务对象、没有相对的音乐文化积累,仅靠作曲技法和兴趣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我们的作曲家应该立足传统,面向大众,建立文化自觉精神,更应该推陈出新,面向现代,建立文化自强精神。我们的二胡作品应该以中国古典文化和东方心态,在实现生活中与当代听众进行一种深层接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现象,约稿时说好要写红脸关公,结果整出来一个白脸曹操,让人哭笑不得。有些作品‘技巧高了’,‘韵味淡了’。为给江河水整个故事,结果江河水的动人旋律整不见了;为整个我的祖国,结果原来的美妙、动听的音调整没了,这种带有改编性的创作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我认为:原创作品的改编一定要升华,要拔高,要有新意,不然就失去创作的意义。
现将我听到的、见到的和感悟到的在二胡音乐创作中顾此失彼,舍其长而取其短的现象归纳为三种:
一.听不清旋律。从《病中吟》到《长城随想》记录着一部二胡创作史,载入这部史册之中的二胡作品无一不是以旋律优美而著称。这里说的旋律美不只是指曲调优美动人,旋法新颖别致,风格清新浓郁,线条清晰舒展,更重要的是指旋律本身蕴含的民族音乐神韵以及旋律线条所展示的曲线美。民族审美理念和审美意识孕育了民族欣赏传统,我国人民对音乐的曲线感,对旋律的流动感与生俱来。然而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作品在创作时并没有认真考虑立足中国现实,没有顾及二胡的特质,没有考虑雅俗共赏,没有将技巧性与旋律性真正的结合起来,路子越走越窄,越走越远。在这些作品中,旋律被淡化,曲调被稀释。一个动机,一个主题犹如婷婷玉女,千呼万唤始出来,刚一露脸,没唱上几句就隐伏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主题的割裂、异变。这种技法并不强调旋律陈述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音乐展开的过程中,时而伴有重重的音团和怪异的音块,使人望而却步。这种音乐听起来费力,记起来费劲,即使您是一位音乐记忆十分超群的人,不花一番功夫,绝对让您找不到北。
二.读不懂调式。西洋大小调系统、中国民族调式音阶为二十世纪音乐创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步入二十一世纪,这种音阶调式能否再立新功,则要看作曲家的脸色了。民族音阶调式是构建民族音乐文化的基础。在这种音阶调式上,承载着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积淀。正是这种调式音阶将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粹传承到了今天,正是建立在这种调式音阶上面的民族音乐和民族器乐曲打开了奥地利的国门,直通金色大厅,让高鼻深目的洋人一睹民族音乐的风韵。然而这些成功的经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某些二胡作品中,调式功能被模糊,调式音阶被淡化,读不懂调式,搞不清音阶,这种技法是对传统单一调式的反叛,消减了同一调式上音乐的谐和性。这是作曲家用西方作曲技法在中国二胡园地里播种的一块试验田,成功与否,尚无定论,这可能是对‘洋为中用’一词里的中用还不理解,听这样作品,要修身养性,不要期望一两遍就可以听出名堂,如有CD,听上十遍八遍,自然可以悟出一些道理来。
三.找不到风格。刘安《淮南子·主术训》中云:“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这是说:风格决定音律,音律产生音调,音调组成音乐,此声之宗也。风,指风格。风格就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语言、风俗、民情、民趣活的载体。风格是建立在特定的音阶调式上的。不能离开调式、音阶谈风格,否则就是纸上谈兵,“律生于风”就不灵验了。如在同一部作品中一会儿是江南春色,一会儿是北国风光,一会儿是大漠孤烟,一会儿是东海渔歌,那就有模糊之嫌了。前面的调式音阶已被淡化,后面的风格自然是不翼而飞了(此处的风格指作品的音乐风格,不指作曲家个人的创作风格)。
今天,我将这些现象摆在桌面上,只是想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如果能展开讨论,求同存异,取得共识,对于胡琴音乐创作和胡琴艺术的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仔细研究一下中国二胡音乐中的精品,其实它们在作曲技法上并不那么新奇,在创作理念上或许还有一点保守,但是这些作品和民族文化传统、民族审美情趣是那么贴近,结合的是那么完美,内容和形式是那么统一,旋律和技巧是那么和谐,风格和调式是那么融洽。这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这些成功作品中,作曲家的实力与功力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线性思维是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二胡音乐创作不能丢弃线性思维这一根本,二胡音乐的旋律美感就蕴藏在线性思维之中。音色化主题,多变性音型,以及点状音块和怪异的音团是替代不了绵绵不断的主题旋律的。在二胡音乐创作中不管选用什么创作理念,使用什么作曲技法,我认为立足传统,博采众长,重视旋律写作,加强作品的可听性,充分发挥乐器性能,注意作品的音乐风格,探析调式色彩的多样化以及体裁结构的多元化是二胡音乐创作获得成功的经验之一。
二胡学会是中国音协专业性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社团定位,学术性的宗旨确立,理应引领中国二胡音乐艺术健康发展,这是首要任务。学会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但要主次分明,抓大事、正事,我认为今后很长一个时期要做以下几件大事:
一.建立中国二胡档案库,收集曲谱、照片、剧照、节目单、论文、评论、音像资料、书刊,为编撰“二胡史论”提供素材。
二.狠抓二胡音乐创作,多出作品,出好作品,如果每年有20-30首新作品供选择,我们事业的发展就有了动力。如能定期举办新作品比赛或音乐会,就会促进创作繁荣。
三.重视二胡音乐艺术的理论建设,支撑这一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完成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这一良性循环。(理论又分为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两部分)。
四.恢复中国二胡杂志,这是学会联系作曲家、理论家、教育家、演奏家及二胡爱好者的重要纽带和平台,若干年后,也是后人研究中国二胡有据可查的历史资料。
五.梳理二胡界传承关系。追根朔源,将流与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风格特点、演奏技巧区分开来,为后人提供一部详实的史料。
六.为二胡音乐艺术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作曲家、教育家、演奏家、理论家和乐器制作家树碑立传,并在中国二胡刊物上分期刊登,以体现二胡学会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学术性,不要忘记他们大多是70后、80后、90后,这是一件带有抢救性的工作。
七.学会的视野应放高放宽放远一点,不仅要考虑九大音乐艺术院校的问题,也应考虑到全国一百多万拉二胡、学二胡、教二胡的二胡人的问题,他们是学会的社会基础,是金字塔的塔基,这就是普及与提高并重,专业与业余并举的大问题。因为你是全国性的专业学会。
以上是几点不成熟的建议,供学会新班子参考。
今天我的发言不免会碰撞一些人和事,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一家之言,难免偏颇,百家争鸣嘛!
注:
①梁茂春评《长城随想》。
②乔建中《二胡艺术的现代精神》。
③吴赣伯《二十世纪香港中乐史稿》。
2012年6月6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