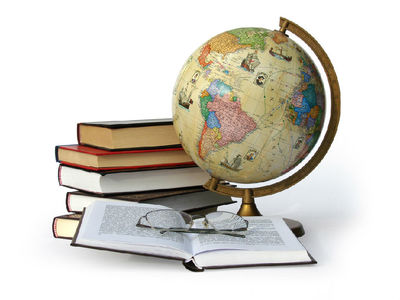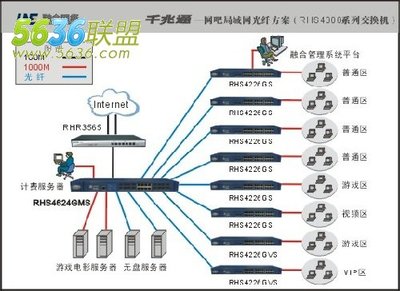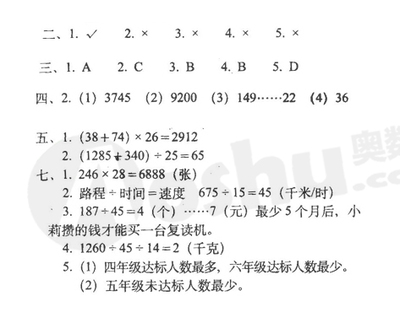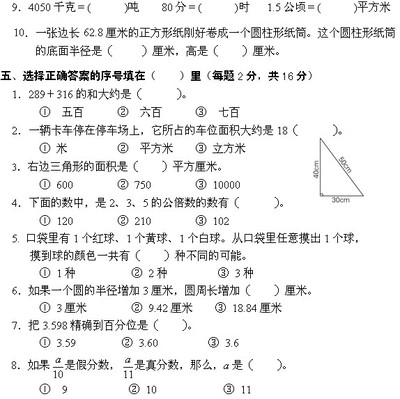一.远行岂可不备书
要出行了。短期的。
其实是同学中的热心人大力鼓动的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庆祝活动。如今好像联谊活动成风。同学间飞来飞去的电子邮件已经渲染了数学系、化学系...的哥们儿如何如何,其他院校的活动怎样怎样,然后每届同学中总会出几个大腕级人物,“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张罗组织,我们这伙随大流的吃货那也就只能打蛇随棍上了,尽管夏天飞机票是格外地同咱们的钱包不见外。
以往外出,为了打发飞行中的无聊,总要带一两本书。如今条件好了,有电子书,一个U盘64G,里面装的书几乎可以摆满一个小图书馆,那就只要确认看什么书了。这次很明确,准备读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为什么选它?首先是总得选一本,要不然路上干什么呢。另外在我蜻蜓点水式地在我那一大堆电子书中翻阅时,这本书真的让我眼睛一亮。什么是亮点呢?对我来说,就是它的文字。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在这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一个人总得喜爱点什么。可我,先天是个欲望很低的人,什么美食时尚之类,对我毫无吸引力。别人可以通宵打的扑克、麻将之类,我也没有这么大劲头。要往那高端的精神享受上移动,音乐、艺术我的鉴赏能力也很有限(但我又非常喜爱两首交响曲:贝多芬的《命运》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不怎么爱运动。只有一点,有时读点诗文,觉得好了,就衷心喜爱。比方说,我的思想右倾明显甚至反动,但我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却很是珍爱,时常在记忆中欣赏,觉得谁的文章写到这个地步了,那他就真的会写文章了。
冯先生的书打动了我。说来见笑,专业的精湛和论述的行云流水、举重若轻当然是没得说,但最初打动我的却是它的语言。我当然知道冯先生是晚清到民国期间出生、成长和成为大家的老一代学人,他们这些人是从文言文开始学习写作的,“五四”后白话文逐渐成为主流,他们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时代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其文字中留下痕迹。但我读到的这本书,却是极为纯熟的现代白话文,读来没有丝毫的凝滞感,这就令我大为赞叹也略有疑惑。我知道书是冯先生四十年代赴美讲学时所写的英文讲稿,但我误以为还是冯先生本人用中文把它重写回来的。直到这次真的要把它通读一遍了,才在电子书的开头发现这本书这本书是由赵复三先生在二零零四年翻译的。
对此书的流传过程有了兴趣,难免到网上去搜寻一番,这一下子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此书早在一九八五年就由冯先生的弟子、北大哲学系的涂又光教授由原著翻译为中文,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一再印刷,发行量远远超过十万本,可谓影响巨大。新世纪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赵复三先生又重新翻译此书,并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配以大量图片出版,影响也很巨大。我得到的就是这第二个版本。
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由两位高层次的学者先后翻译出两个版本,对于有兴趣的读者来说,自然想一窥瑜亮之比。网上有的是好事之徒,对这两个译本对比评论的也大有人在。从数量上来看,扬涂抑赵者为多数,论点多为涂译简练,赵译罗嗦云云,甚至有人说涂先生的本子他读了不下十遍,爱不释手。另还有不少人证实涂教授是在冯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翻译的,得到了真传。
拥赵派居于少数,但举例较为详细。另外我们不得不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涂教授的译本先问世近三十年了,此期间已经有了大量的读者群,人对于自己熟悉并真心喜爱的作品从感情上一定是维护的;另一个是赵先生身为一个高级的社会科学专家,必定早已读过冯先生的英文原作和涂先生的译作,是什么原因推动他以近八十的高龄来重新翻译一遍呢?
好在我手头两个译本都有。涂教授的译本,收在冯先生作品全集的《三松堂全集》第六卷,我也把它的开头部分认真读了,得到一点体会。这里摘录两个片段。
涂又光版
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
《论语》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
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国人以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海洋国家的人,如希腊人,也许不能理解这几个词语竟然是同义的。但是这种事就发生在汉语里,而且是不无道理的。
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如果我们用现代标准看距离,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可是《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话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仲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闻名。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只是他的过分热心并没有博得孔子喜欢,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孟子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只仅仅想到“浮于海”。生活在海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该是多么不同!
赵复三版
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
在《论语》里,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23节)读孔子的这段话,使我想到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思想不同的由来。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古代中国人心目里,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在中文里,有两个词语常常被用来表达“世界”,一个是“普天之下”,一个是“四海之内”。住在海洋国家的人民,如希腊人,会不明白,居住在“四海之内”(比如说,住在克里特岛上),怎么就是住在“普天之下”。而在中文里,它就是如此,而且是有理由的。
从孔子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没从来没有到海上冒险的经历。在现代人看来,孔子和孟子住的地方都离海不远,但是在《论语》里,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7节) 仲由即子路,在孔子的学生中,以勇敢著名。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非常高兴。孔子却并没有因仲由的过分热心而高兴,他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意思说,仲由虽然勇敢,可惜不能裁度事理。)
孟子提到海的话也同样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 孔子只想泛舟浮于海,孟子也只是望海兴叹,并不比孔子好多少。对比之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出生在海洋国家,漫游列岛,又是多么不同啊!
有了具体的文字,这个比较就容易做了。两位学者翻过来的文字,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可见他们都十分忠实于冯先生的原文。不同之处在于,涂先生的工作重点是尽可能真实地表达冯先生的原文,文字精炼而富于条理,而赵先生却着重于尽可能让读者理解冯先生的原文,文字翔实而时有华彩。换句话说,涂先生是一句一句翻的,赵先生却是一段一段翻的。哪种翻法更好,不同的人见仁见智了。不过对于我这样天资较为愚钝的人来说,后一种似乎更合口味。
这段“考证”工作有点意思,它使得我不但确定了要读一本书,还让冯友兰先生和赵复三先生的经历都走进了我的视野。
二.激流百折叹书生
冯友兰先生名气很大。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当还在儿童或少年时期,寡言的四舅有一次忽然说了句“北大有个冯友兰”,那次大人闲谈的内容似乎又是与“哲学”有关的,这就记住了。不过那时“北大”,“哲学”,“冯友兰”等等离我实在太遥远了。
等到多少年后真的到北大念书了,有时就会想起这个名字。一般人都知道北大的北面有个未名湖,但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实在未名湖更北面的居住区尚有大片的水面,水边有一幢幢中西合璧的小楼,再加上石径树丛,真是春风杨柳摆,秋月荷花香,说不出的雅致。这楼里一般都住着有成就的学术前辈,冯先生的“三松堂”也应该在这一带。但我入校的那个时候是不可能见到冯老的,因为他当时正因为文革时与“梁效”写作班子的关系被审查,没有自由。现在想来,一个一辈子纯粹从事学术研究的哲学家,却在八十岁高龄时因为涉及“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被批判审查,就觉得这个历史的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我喜欢读故事,也爱讲故事。要读冯先生的书,就先读他的故事,于是《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冯先生的自述就兴致盎然地读下去了。当年读梁漱溟先生的自述也是一样,当然梁老的晚年对话录《这个世界会更好吗》也至少读了一两遍。冯先生讲故事果然同长髯飘飘道骨仙风的照片一样,平实、从容、超脱,一派祥和,是那种在历史激流中折冲沉浮后的淡定感。读他的故事,无疑是在与历史同行,是一种新的体验。
看看这些民国名人的出生日期:冯友兰先生,一八九五年;傅斯年,一八九六年;毛泽东、梁漱溟,一八九三年,胡适,一八九一年,周恩来,一八九八年...这是个新旧交替、风云激荡的年代,这些历史人物无不先浸透了旧中国的文化教育,才去投入新的时代开始新的追求。多少年过去了,当“五四”的历史大变革已成为可供研究的过去,我们才蓦然发现,其实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双方,都是由旧中国、旧文化早已准备好的优秀人才。
冯友兰先生就是典型的一个旧式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冯氏在河南省唐河县是一个有一千五百亩地的乡绅人家,父亲在乡间读书,考中过进士,曾参与过张之洞在湖北推行的洋务运动,担任过崇阳县令,为官清正,积劳成疾殁于任上。母亲冯太夫人深明大义,知书达理,坚韧克己,丧夫后勉力料理家政,抚养子女。冯氏后代皆成大才:冯友兰是中国大哲学家自不待说,乃弟景兰也赴美学习地质,后成为中国第一代地质学部委员,最小的小妹冯沅君也随兄赴京读书,后成为中国著名文艺史专家,尤善中国戏曲史,后为五十年代山东大学第一批一等教授之一。冯氏是货真价实的一门三杰。
冯先生的求学经历很有代表性:幼承庭训,从习诵儒家经典开始旧式教育,再逐渐接受已进入中国的西方知识,后进入北大哲学门读书,毕业后先回河南谋职,再考入官费留学,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完了哲学博士学位,回国进入学界。以后季羡林先生也是如此,考入清华大学学习西洋文学,毕业后先回乡谋职,再考入官费留学,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印度学,完成了博士学位,后回国开创北大东方语言系。在同一时期的学人中却有路数不同的人:陈寅恪先生留学十多年,只学课读资料,却不拿任何学位,其实以他的学力拿好几个博士也都绰绰有余了;傅斯年先生天资卓绝,十几岁就已饱读经史,有“黄河圣人”之称,但出国后也是只读书不拿学位;吴宓先生在哈佛大学如鱼得水,博士学位唾手可得,但国内刊物请他回去,说走就走,决不留恋。这是为什么呢?关于其中缘由,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讲得很清楚。旧中国,即使是五四以后的社会,还是难免要讲门第出身的。家族显赫的子弟,如陈先生、傅先生,只要自己确实有才,士林是买他们帐的,即使没有洋文凭,那旧家族的声望依然是巨大的社会资源。但像冯先生、季先生这样的出身偏于中下层的子弟,那就得靠自身的努力更上一层楼了。不过,我们还是得承认,当时的社会还是提供了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向上流动的机制,这同中国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是有某种内在延续性的。
学成归国后的冯友兰先生意气风发,在河南、广东的大学短期任教后,最终选定清华大学这个中国的学术重镇作为治学之所,授业之余潜心写作,终于在三十年代初写出划时代的两卷巨著《中国哲学史》。此前十余年前,他的老师胡适先生就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成为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和规范开展中国学术研究的开山人物,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但胡先生人忙事杂,未能终卷。而冯先生的研究却是宏大、完整而翔实,得到了学界巨搫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赞许,成为中国哲学界三十年代学术研究的代表成果,他本人也因此确立中国哲学界领军人物的地位。
三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是与国际充分接轨的。冯友兰先生成为中国著名的学者,自然就有了许多的国际交流,受到邀请,远赴欧美考察及参加国际会议,还于一九三四年访问了苏联。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访问给他带来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牢狱之灾。
原来冯先生到苏之后,受到热情接待,到处访问,当时经济快速发展、同欧美国家经济危机下的一片黯淡形成鲜明对照的苏联社会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也难怪,我们现在熟知的共产党国家的一整套对外宣传手段,当时迷惑了不少人,甚至世界著名的哲学大师罗素也都着了道儿,兴奋不已,冯友兰先生也难免着迷。一个书生,不谙政治,回国后演讲发文,想什么说什么,对当时的苏联多有赞扬之意,这就触怒了正在忙于“剿共”的国民党当局,认为他宣传赤化,有危害民国之嫌,于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国府的“保定行营”竟出动军警将冯先生带上手铐从清华园捕走。此举引起全国学界的震惊,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声援和营救行动,加上审讯也实在问不出什么名堂,不久冯先生就获释了,算是有惊无险。
关于这番遭遇,我们当然要谴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但是,历史是可以比较的。就在二十年后,一个叫胡风的知识分子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写了一封有关文艺方针的建言书信,引起了先皇的不快,于是雷厉风行,以搜集一批知识分子的私人书信为线索,制造了一个导致几百知识分子入狱、判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那个时候中国的学界可有鸣冤和营救的行动吗?丝毫没有。知识分子中,有良知的也是噤若寒蝉、不敢作声,那无良的文人,像是郭沫若之类,就落井下石、对同类痛下杀手以邀宠了。以后的历次运动莫不如此。所以,即就冯先生这次的牢狱之灾的经过而言,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当局对知识分子还是相当宽松的。
冯先生出狱后愈加声名大噪,来慰问的人士络绎不绝,此时的他,夸过苏联,蹲过大狱,命运似乎给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左倾”教授的位置。但出人意料的是,冯先生不仅没有对抗,反而选择了与当局合作的方式,加入了国民党,还出席过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过,以后的人们看他这段经历,并不会因此认为冯先生已成为国民党阵营中的政治活跃分子,还是把他定位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这是因为,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意识控制远较同它对垒的共产党来得松散,没有什么“组织上入党,思想上也要入党”那些教条和改造。冯的选择,无非是给自己涂上保护色,安心做他的学问而已。不过,即就如此,我还是觉得此举反映了冯友兰先生性格中的某些软弱之处,这个弱点应当也是造成他文革中身陷“梁效”悲剧的因素之一。
但是,冯友兰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卷入国内的党派政治之争,并不代表他们对于国家大事的无动于衷。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加快了侵华的步伐,整个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敌人对我们的进犯,不仅是要吞并我们的国土,奴役我们的人民,还要灭绝我们的文化。在这种形势下,冯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的文化,并非两耳不闻天下事的纯学术研究,恰恰相反,他们带着深深的爱国情怀和沉重的历史使命感,是在进行一场在亡国威胁下捍卫祖国民族文化的战斗。这一点,我们从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序二中一段话感受得特别强烈:
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
这一种为民族文化而战的使命感,在七七事变后的中国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始终贯穿于冯友兰先生的学术活动中。华北沦陷,各校南迁,长距离的搬迁,可谓颠沛流离,在大后方昆明北大、清华、南开等院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冯先生抱着中华民族一定复兴的信念,埋头著述,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构成了以中国传统儒学为基础,而又包含新的见解的完整哲学体系,被称为“贞元六书”,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冯先生的工作,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风貌。中国人民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殊死搏斗的年代,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以赤诚的奉献精神努力在教育和学术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年代。那是条件最为恶劣的岁月,却又是中国学术和教育空前兴旺的岁月。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条件简陋,衣食难继的西南一隅,办成了中国最好的大学,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级的科技人才,奠定了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傅斯年先生带领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们在甲骨文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昭示了我中华民族光辉的文化史,战后受到民国政府的特别嘉奖。陈寅恪、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侯外庐...等一大批学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可谓一时之盛...如今回顾这段令人激动的历史,我等后辈怎能不心头涌上无限的崇敬。
我们手里这本《中国哲学简史》,就是冯友兰先生在二战后应邀赴美讲学的讲稿。抗战已经胜利,学业又有巨大成就,冯先生此时的心情应该是轻松的,准备教材无疑也是胸有成竹,取舍自如。然而,这样的一本“简史”,却浓缩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精华,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对于初学者尤为适宜,因此被西方的多个院校多年来列为教材,影响深远。八十年代后转译回中国,又在国内的学习者们中引起巨大的影响,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我今天选读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以易懂的形式,再现了民国学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采,因为事实的阐述,观点之抒发,都是从心而发,毫无桎梏,那思想的自由是令人神往的。联想到冯先生以后回国将会面临的巨大变局,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虽然不是他学术生涯的结束,但这本书凸显的鲜活生动的写作风格,对于冯友兰先生来说却可能成为绝响。
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胜负已定,国府撤往台湾。人们经常说蒋介石在撤离前运往台湾多少黄金,其实蒋先生的心中有比黄金更宝贵的财富。他动用宝贵的轮船资源,将抗战时千辛万苦运到后方的故宫文物又转运到台湾,他更是不惜动用更加珍贵的飞机资源,尽量劝说国内一流的学术人才迁往宝岛。冯友兰先生当也是劝说的对象之一。可惜,人不是可以搬来搬去的箱子,大多数的学人毕竟故土难离,再加上当时中共地下党出色的工作,真正去了台湾的人很少,如傅斯年、钱穆、毛子水等。不过,当以后赴台的学者在学术上再创辉煌,而留在国内的人们遭遇到的却是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无情的摧残时,不知他们心中作何感想?
冯友兰先生的感觉肯定是最快的。刚刚进入五十年代,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冯先生想向当局表达合作之意,给毛泽东主席上书,表示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毛的回信来得很快却是毫不客气:“像你这样的人,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好”。冯先生无疑是吃了闷棍,立即辞去了系主任的职务。其实这也是个多此一举。很快新当局就推行院系调整,实施苏联式教育,原有的民国英美式教育体系被彻底推倒了,冯先生也因此不得不离开他治学多年的清华园,迁往未名湖畔的北京大学任教。至于他的“新理学”,一九五零年就已是批判的对象。
以后的岁月,大家都很清楚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大都是靶子,人格尚且难保,斯文扫地,所谓的学术研究一而在再而三地沦为党八股的工具,冯先生五十年代开始的主要工作,竟然是用“马克思主义”把他的名著《中国哲学史》改写为《中国哲学史新编》。即就如此小心,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总有知识分子落马,入狱、劳改的事情并不罕见,老一代学人被公开要求的就是“夹紧尾巴”。说来可悲,在政治运动中下场最惨的往往是那些历史上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人,像胡风、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他们自以为协助共产党打天下有功,有资格做个铮友,结果就太出意外了。倒是冯先生这样同国民党有过瓜葛、自己又极为谨慎的人,好歹能多多少少熬过几场运动。
但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真所谓“避脚台高三百尺,高三百尺脚仍来”,终于有一天,“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大学发源,风暴席卷了燕园的每一个角落。冯友兰先生无可逃避地被“揪”出来了,那“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对他几乎就是量身定做。批斗,炒家,隔离审查,这些程序他是一个也跑不了。我所看到的最令人发指的一幕,是一个“工宣队员”把冯先生这样一批年逾七十的老知识分子带到外文楼,令每人抱上一捆稻草,指着水泥地下令“你们就睡在这里!”冯先生的回忆使用很平淡的口气叙述的,但我看了真是难抑愤怒。古往今来,多少民族,有几个会让它最渊博的学者有家不能回,刻意让他们睡稻草,当牛做马呢?以后毛要搞写作班子,需要懂得历史知识的专家,一句话冯先生又出了牛棚,生活待遇突然改善,但条件是必须在政治上配合“梁效”写作班子,这时的老人也身不由己了,何况冯先生本来就是个性格较弱的人。这样又造成了他文革后被审查,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有人不能谅解他。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风暴中的丧失人格,饱受凌辱和戏弄,在冯友兰先生的身上也算是淋漓尽致了。
文革结束了,冯先生的“问题”也总算是结束了,这时年逾八十的冯友兰先生已是心如止水。一个学人,在他不再被政治风云强行驾驭,身心再度自由后,最放不下的还是他的学问。冯先生的最后几年仍然拼尽了老迈的气力,全力写作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最终完成了这部七卷的巨著。据说,这部著作的水平很高。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部巨著的序言时,看到的尽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我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等等,就令人少了敬重,多了心酸。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已经深深地渗入了这样一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哲学家的灵魂,他还是丧失了自我。带着锁链的舞蹈,就算水平再高,它能美吗?因此我们如果想读冯先生的著作,最好只读他一九四九年前的书,譬如像《中国哲学简史》这样的书,在那里我们才能发现一个真实、自信、充满灵气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
三. 冲破罗网风入怀
赵复三先生多少有点神秘。他很长时间不是专职的学者,却分明具备贯穿中西的学者素养。其实他早年的经历似乎就有些神秘。
我们来看看他的简介:
赵复三(1926年-),上海人,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随后任职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1950年7月,时任北京青年会副总干事的赵复三,成为《三自宣言》的40名发起人之一。此后,赵复三出任中华圣公会牧师、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总干事、燕京协和神学院教务长、北京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
1964年夏,赵复三突然作为革命干部奉命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负责批判神学的任务,从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到1980年代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3]和党委副书记),并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中国大陆宗教学界的“三赵”之一。
1980年代,赵复三出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赵复三又在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委员。又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0年6月被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此后赵复三在美国南方一所大学任教。
如此看来,赵先生曾是上海有名的教会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北上到北京教会工作,出任牧师。他曾是官方策划的《三自宣言》,即主张中国教会与西方宗教界脱钩,成为独立的教会,其实也就是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教会组织那个宣言的发起人之一。这个时候他似乎成了一名“进步”牧师。但是他如何在六十年代以党员干部的身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并逐渐成为一名中共高干呢?这种身份的切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我对于这个转变有了些猜想。关键是他的出生年龄。
赵先生是一九二六年出生的,同我父亲是同一代人。这个时候出生的人,特别是出生在上海这个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城市的一代人,已经不再接受旧式教育,而是从西方式的小学读起。赵先生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父亲是孔祥熙的同学,由清华学校培养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在金融界工作,自然为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创造了条件。但他又是个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曾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因此也影响到四个儿子,在大学里都参加了学生运动。这一点上,我从父亲的经历中是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氛的:四十年代末大学中的左倾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的精心策动下几乎是压倒性地影响了学生的大多数,在大的城市里尤其如此。
但是,赵先生上的毕竟是教会大学,所学的内容还是不可避免地对他发生重大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被赵先生反复称为“恩师”的徐怀启先生。如此称呼,可见这对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徐先生是哈佛大学神学博士,中国有名的基督史专家。他学识渊博,是中国为数不多的能用希腊文和拉丁文直接阅读西方学术文献的专家,因此从一九四零年起在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授多年后,又在一九五零年代上海筹办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时被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延揽到该系当教授,而冯契先生恰巧又是西南联合大学金岳霖、冯友兰两位大哲学家的高足。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赵复三在五十年代后通过徐怀启和冯契两位学者,又得以与金岳霖、冯友兰两位教授有所来往。学术的延续和发展是要有传承关系的。赵先生无疑从这些第一流的学者身上吸取了丰富的知识营养,使自身也具备了充沛的学养。他的朋友回忆说,即使五十年代赵先生已作为“宗教界进步人士”出现在人面前时,他对西方文化渊博的知识,特别是对基督教的经典、教义和礼仪极为谂熟,如数家珍,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赵先生以后敢于动手翻译《中国哲学简史》,又显示了他深厚的国学根底,这方面的知识他是怎么得来的呢?这对于我还是一个谜。
那么如何解释赵先生是从一个牧师变成了学术机关中的党员干部乃至高干呢?首先他在四十年末参加学生运动是应当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的身份,则是世上极为少见的中国特色所致。
我们知道,一个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党,胜利前在敌方控制区一定得以地下的形式存在和开展活动。但中国有一大怪事,就是共产党在取得全国胜利,成为无可争议的执政党后,还保留了一大批秘密党员,让他们以党外人士的身份活动。在他们中间,比较有名的有胡愈之,到死都是“民主人士”身份;茅盾(沈雁冰),著名文学家,一辈子都以党外人士身份活动,八十年代逝世后,报纸上却十分罕见地登载了一条短短的新闻:“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党龄从一九二二年算起。”原来这位“统战对象”早就是大内成员,从一九二二年起就不以真面孔示人了!这次的“正名”,恐怕还是家属力争的结果,他们不愿意沈老戴着假面具入土啊。
由此看来,赵复三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担任的那一串串的基督教会职务,包括那个要去讲经布道的牧师职务,统统不过是幌子。他的党员身份才是他的使命所在,他所作的一切都是要完成党所赋予的控制和监督宗教界的使命。我们不知道在五十年代初期他所作的这些会不会在他内心同他所学的知识,以及他的老师们对于他的影响发生冲突,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后,他内心有了越来越深的怀疑和矛盾是一定的了,因为所谓的革命正在越来越疯狂,它必然要在赵复三从所学所研究的人类文化精华知识所带来的正义和良知,优雅和高贵等等内心深处的沉淀激起不可避免的反感和冲突。
赵先生在一九六四年突然结束了这种假牧师的身份,以党员干部的身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原因也许是他的年龄毕竟还较轻,不必像茅盾这样的名人死撑到底。另外,当时的社会科学院聘请了他的老师徐怀启先生为特约研究员,准备撰写《古代基督教史》,这也许是他改变工作职位的又一个因素。不过很快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呼啸而至,所有的学术活动被冲击得无影无踪,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赵先生也不例外。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以我亲身经历过的见证,这场浩劫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丝毫没有可取之处。但不可思议的是,目前在中国社会竟然有相当大的声浪要为文革翻案。我想不外乎两个来源:一部分是文革中那些整人为乐,手上至今还有受害人鲜血的左派分子。这些人是永远不可能忏悔的,恰如季羡林先生说过的那样:“坏人,就像自然界有毒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另一部分则是天性偏激、又未曾经历过文革的较为年轻的一代。当年毛就是利用类似的人群来掀起狂热,而邓小平先生在否定文革时投鼠忌器,不能彻底清算文革和毛的罪行,就为今天极左思潮的重新泛起种下了祸根。但对于赵复三先生来说,文革是他实实在在的噩梦。他的家庭背景,与基督教会的渊源,以致工作和社会圈子造成的不可避免的与外国人的交往,都使得这个家族在这场巨大的历史风暴中在劫难逃。
大哥赵忠一,在北京协和医院做妇产科主任,文革中受迫害自杀。
二哥赵中玉,在开滦煤矿当工程师,因井下救人而牺牲,葬入烈士陵园。但不幸的是他生前娶的是一位南开大学加入中国籍的美国教授的女儿,此时岳父和妻子都被当成特务,这个已死的人自然也是特务,无资格呆在烈士陵园里了,就被刨坟掘骨。妻子和两个女儿不准进陵园,只能哭着在墙外一根根地捡收扔出来的骨头。
赵本人又因本人在基督教会的复杂经历,及后来因精神错乱而死的二嫂曾在威逼下承认三弟是潜伏特务,在运动中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但这一段经历我没有找到,只能从略。
十年文革,给中国人留下了累累伤痕。在七十年代末开始思想解放的时候,劫后余生的中国思想界开始了文化上的反思。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在中国统治了许多年的党文化,都成为有独立见解学人的反思对象。这个时候的赵复三先生正是五十来岁,“五十而知天命”,他定是对于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命运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都有了深刻的再认识。这一期间他的深厚的学力、渊博的知识,特别是对于西方文化深刻的了解,使得他在学术界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后来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和常务副院长及宗教界的各种职务,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发表文章,在十余年中成为学术界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与刘再复等学术新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历史给了赵复三先生一个特殊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他内心的文化冲突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一九九零年前一年中国首都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惨案发生时,赵复三正率领中国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代表团在巴黎开会。事发以后,六月九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发生的这个事件理所当然地成为会议议论的中心话题。赵在场,若按他代表“党和政府”的常规,当装聋作哑,保持缄默。但是,他开口了。他用最柔和的语言,表达了最坚定的观点:对事件感到震惊、为死难者表示哀悼、中国历史从此开始重写。
我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赵复三先生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完全知道自己简简单单的三点声明对他个人的命运意味着什么。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在政府方面已经有了副部级的待遇,只要全身而退,自然晚年无忧。而只要话一出口,命运就不可预料,这一点在党文化的阴影里挣扎多年的他心知肚明。
从七十年前开始,从那个著名的“讲话”开始,党文化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物,随着执政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夺取政权,就逐渐在中国结成了铺天盖地的罗网。任何的个人,任何的个性,都要随时随地被限制在这张罗网之内,“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早已都是负面的名词,人们被要求做驯服工具和螺丝钉。八九年那场事件,归根结底,就是觉醒者对这张大网的反抗,也因此在这张网前付出了血的代价。
但是,赵复三先生已决意要冲破这张罗网。多年积累的人类高尚文化及其必然形成的良知和正义感,此时再也不能容忍那把人变成奴隶的党文化的束缚。于是,他毅然出走。后接到邀请,去了美国南部的俄克拉荷马市大学任教。他的深厚的学术素养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任教后,赵先生开始了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
自由是有代价的。一九九九年,七十三岁的赵复三又回到了比利时。这时他已经退休,孑然一身,在两个女儿家来回住住还是感到不便,孤独中的他想到了在比利时找一家修道院养老。我想欧洲的宗教社会有这样一些对退休神职人员的服务。不过此时他却突然又有了生命中的一段奇遇。他在早年认识的一位小妹妹陈晓蔷女士,已从耶鲁大学图书馆主任职务退休,知道了他的消息和想法,立即赶到比利时劝说他回到美国,并很快同赵先生结为夫妇,从此赵复三又有了一个安定和幸福的家庭。
以后的年月,他埋头著述,先后翻译了《欧洲文化史》、《欧洲思想史》、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等等。这些学术著作翻译起来都有相当的难度,而赵先生已是八旬老人,却能不辞劳苦,把一本本的新作奉献出来,不为别的,只为一个流亡老人对祖国的一片情意。
一个父辈学人,当他挣脱了罗网飞向自由的天地,他却仍然心系故国,不改深情。在一段私人通信里,他写道:
“……中夜醒来,胡思乱想,问自己:行年八十,已经进入一生最后的一个阶段,现在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什么?我想,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看到中国十三亿人,其中有许多好人,竟然不会思索自己的人生;这就使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建设成就、以至现在物质生活的进步,都失去了光彩。问自己,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想,最希望的是看到中国人都学会思索自己所经历的人生,这是中国未来无限希望的保证。这是我最大的向往,也是我现在生活的目的。”
我们可以理解他吗?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理解吗?但愿如此。一个真正成熟和理性的民族,无论如何,应当善待和理解它最有良知和博学的学者,那样才能让祖国的天际永远闪耀着智慧之光。
有意思。想看一本书,却引出了两位学人,引出了他们的故事,引出了这样洋洋洒洒的一大篇文章。但愿没有离题万里吧,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书,爱读书的人难免在生活中读来读去,寻找他心中的那片天地。所以我们还得说那句老话:“开卷有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