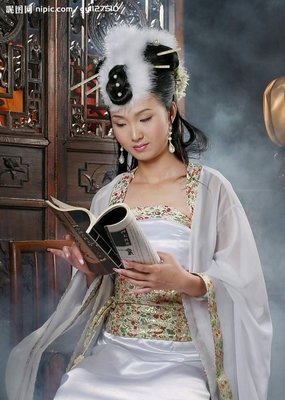文/王侯
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燕王哙继位。
在历史学界这个燕王哙(?─前314年)可是个大大的名人,搞先秦史的人,往往对他聚讼不已争议不决。
燕王哙作为召公的后裔,姬姓,名哙,燕易王之子,战国时期燕国第三十八任国君。他最出名的事就是他搞了一次春秋战国乃至先秦时代绝无仅有的“禅让”。
王德恒出于形象思维,是从分析这个人开始的。
侯坤是成功的企业家,评价这个人是从结局开始的。
于是,争议产生了。
燕王哙即位的时候,燕国的状况很不好,靠近齐国的边境十个城市被齐夺去了。而且,他也看出秦国势力越来越大,有称王甚至独霸天下的野心。
到了前319年,也就是燕王哙上台三年的时候,他信从公孙衍合纵的建议,与齐、楚、赵、韩支持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将任魏相的张仪驱逐回秦国。次年,与魏、赵、韩、楚合纵攻秦。这次行动中他就玩了一个小小的心眼,令本国的军队跟在后面,不真正去阵前冲杀。其它国家也是各揣心腹事,也不太积极进攻。这次伐秦无疑是散伙的结局。
他知道,尽管没有在合纵中吃亏,但是,其它各国由于人稠地广,先行改革,国力都逐渐强大,而燕国偏于一隅,又墨守成规,别说在在七雄中争霸,就是想平稳立足也很困难。他要改变这种状况。但在他继位的时候,距秦国的商鞅变法已有近五十年,苏张之辈周游列国,推行合纵连横的主张。燕国的贫弱和环境的险恶,促使燕王哙苦身忧民,殷殷望治。地处偏僻文化发展落后燕国,寻找一条什么样的改革之路才能迅速强大起来呢?燕王哙面对中原各国各种新的思潮和变法革新之风颇感茫然,他知道自己难以承担富国强兵的重任。
王德恒认为,此人很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的才气不够,必须借助于能人。其它变法成功的国家就是如此。经过一番寻觅,他找到了子之这个人。从其子姓来看,此人可能是殷商燕族的后裔。

他观察了一个阶段,觉得此人"贵重主断"。不久,他任用子之为相国。果然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朝政一片清明肃然。
对于子之,著名先秦史学家杨宽先生说他是“近于申不害一派的法家”。
侯坤认为,申不害是法家的末流,不代表社会的进步。《韩非子》中记载了他督责手下的小手腕,事情类似于韩昭侯所为。采用这一派的学术,不用进行困难的改革,不触及世家大族的利益,只试图加强对官员的监督,以此提高行政效率,简单易行,效果有限。不过这足以让燕王哙认为他是治世之臣,是自己所能遇见的最好的人才。
就在这一年,苏代作为齐国使臣出使燕国。
这个苏代是苏秦的哥哥,也是纵横捭阖之士。他和子之的个人关系很好,是可以密谋秘事的那种交情。这时,他来到燕王哙的面前,燕王哙问苏代:“你觉得齐王怎么样?”苏代回答说:“齐王必不能称霸。”燕王哙又问:“这是为什么?”
苏代回答:“因为齐王不信任和重用他的大臣。”
苏代想用这话激燕王哙重用子之。果然,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后更加重用子之了。为此,子之送给苏代百余金,并表示要听从苏代的吩咐。
这时又出来个叫鹿毛寿的,此人谁也查不到他的来历,他劝燕王哙:“不如把国家让给子之。当年,帝尧之所以被后世称为贤君,因为他曾经要把国家让给许由,许由没有接受,所以尧既得到了让贤的美名又没有失去天下。现在,大王如果将国家让给子之,那么子之必然不敢接受,这样一来大王便可以与当年的尧相媲美了。”
燕王哙听信了鹿毛寿的蛊惑,采取一些措施使子之的权位更加大了。还有大臣劝燕王哙说:“当年,禹把伯益定为自己的继承人,但他任用的官吏都是启的党羽。等到禹老了,觉得启的党羽不足以担当统治天下的大任,就传位给了了伯益。而启却和他的党羽攻打伯益,最终夺了伯益的国君之位。所以天下人都认为禹虽然名义上传位给了伯益,但不过是给了他一个虚位,而实际上是要让启取而代之。现在,大王您说要把国家让给子之,但所任用的官吏都是太子的人,这就和当年的禹一样,表面上要把国家让给子之,但大臣们都是太子的人,实际上还是太子说了算。”
于是燕王哙竟将三百石俸禄以上大官的玺全部收回,另由子之擢贤任用。这样,子之大权在握,成了实际上的君主。而燕王哙自己也不上朝听政,只想做一个臣子。
侯坤认为,这其实是一场丑恶的闹剧。在这件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高尚道德可言,充满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事件的核心是愚蠢的燕王哙想要得到禅让的虚名,贪婪的子之想要获得骗取政权的实利,想从子之那里获得好处的纵横家上下其口,推波助澜,促成了禅让事件的发生。至于造成燕国内乱,齐国出兵的原因,则是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计谋,假禅让以取高名,实际维持太子平实力,使他能够日后夺回王位,可以说是愚蠢“阳谋”,谈不上是富国强兵的改革。你们吉林大学的教授金景芳先生说燕王哙想要用禅让制代替早已确立的传子世袭制,是开历史的倒车,败不足惜。
王德恒当然不同意“阳谋说”。认为燕王哙改革之心是真诚的。用禅让的方式放权,让有能力的人充分发挥能量,即便想在改革成功后收回政权也无可厚非。问题产生在道德上准备不充分,传贤禅让固然可行性不高,但是大家都承认这代表了最高的道德水准,特别是儒家孔孟之徒也是认可的。所以,不能因此过苛的责备燕王哙,何况他只是传贤禅让,没有证据说他要确立禅让制。
两人都认为,一切都看结果如何。看看子之进行的改革如何,他的改革动作如何?(侯坤说:不能将他的所有行政行为都看成改革。)
对于燕王哙让国,到内乱爆发的三年里,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文献记载极少。所以只能推测和猜想。好在对于资料奇缺的先秦史,甚至更早的历史,可以采取“即使非常严肃的史学家也不时伸展一下想象的翅膀”。
先秦史专家杨宽先生说“子之在燕国进行了封建地主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燕王哙与子之的禅代是进步的。”
这是从积极意义上的对子之也是进一步对燕王哙的肯定。
例如,子之在燕国采用了申不害一派的统治之“术”改革。韩非子内储说上篇说:“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
千万不要误会这是“指鹿为马”的测试。也不是“白马非马”的逻辑学论辩。这是对官吏的一种考察,是对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真相后再回答问题的一种督责。否则,“左右皆言不见”的问题将更加严重。
有人指出这与韩昭侯用术的故事很相像,可见他很讲究督责臣下之术。虽然薄弱,这也可以算是证据。侯坤则认为,这只能证明子之自己掌握了督则之术,不代表进行了改革。
提高了行政效率、增强了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的风气,无疑,对慵懒只看表面的即处理事情的官吏作风是一种改变。促进“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的尊重实际的风气的提升。
子之改革和任何改革一样,都是从启用人才开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他启用了一个名为潘寿的隐者:
一曰:潘寿,隐者。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
原来,虽然燕王哙对子之禅位,但主要大臣的任免权没有交给子之,几乎都有太子的人把持着。这无疑将造成两派的对立,甚至会出现夏代“启”与“益”的对立,最后居于是“太子之位”的启杀掉了益。您燕王哙禅位而不交重要的人事任免权,朝中大臣没有子之的人,子之的下场就是“益”。
潘寿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说服了哙,使燕王哙将俸禄三百石以上官员的任免权都交给了子之。燕王哙在这里为了燕国的利益,牺牲了太子的利益,牺牲燕王室的利益,只为让燕国在群雄并立的情况下,通过改革,立于群雄之林。
什么叫人才,看到问题的本质,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够说服关键人物,就是人才。
王德恒的老师金景芳认为:“燕王哙让国一事,也应纳入战国时期变法范畴之内,但它不是主流,而是逆流。”
王德恒认为这个观点有些莫名其妙。在那个时代要想重新建立禅让制固然是不可能了,可是燕王哙只是要禅让给子之,如果子之本人能力和威信足够高,号召力够强,未必不能稳定局势,使燕国强盛,进一步传与子孙。这从“三家分晋”可以看出来。三家都不是姬姓世家,也都传了下去,并且变法成功。子之如果做到这一点,就是历史进步的主流。
可惜,子之虽然也算人才,但不是大人才。从他因为苏代替他说了一点好话,就给予酬金来看,身上是充溢了小家子气的。
侯坤认为,不能将燕王哙看得过高。他认可子之是一位可以托付全国,带领燕国走向富强的贤臣,这本身就有一个识人的错误。他是为了充分发挥子之的才能,以禅让的形式给予他全权,同时使自己获得像尧舜一样的名声。本质上他要授权至自己去世时为止,届时太子像启从益手里夺权那样,再把王位夺回来。
王德恒则认为,燕王哙禅让和让燕国强大起来绝对出于真心。《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对燕王哙给予了高度称赞:“燕君子哙,召公奭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橶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汙池台榭,外不罼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可以说,他能够为燕国做的他都做了,只剩下禅让这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他存了“届时太子像启从益手里夺权那样,再把王位夺回来。”的心,他不会不和太子说明,说明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太子之乱了。也不符合他一心一意期望燕国富足强大的本意。
前314年,子之行新政三年,将军市被(读音:fubei抚背)与太子平聚众作乱,围攻子之,数月,死者数万。社会上人心慌慌,百姓们都离心离德了。
史籍中关于燕国内乱的记载,主要是《战国策》中的两段:
“子之为国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市被太子平谋,将攻子之。储子谓齐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谓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降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寡人国小,不足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
“太子因数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燕人恫怨,百姓离意。”
“恫恐”“恫怨”这两个词,恫是恐惧,怨是怨恨。
子之严厉,百姓十分恐惧。不能暖民,根本就不是合适的改革者。这里的“百姓”应该是各大宗族所属的民众,包括平民阶层。
“燕人恫怨”就是全民的不满了。
对于燕国这种情况,齐国早就注意到了。储子说的“因而仆之”,是指利用燕国的内乱的时机来进攻燕国,因此要在已乱之后出兵。齐宣王不愧是有为的国君,他让人给太子平传话,制造国际支持的舆论,坚定其叛乱的决心,对齐国而言是惠而不费的。如果太子平听信了齐宣王的话,又证明燕国人的政治思维远远落后于时代。在齐桓公的称霸时代,齐国可能为了维持燕国公室的利益而出兵,并不谋求具体的私利,只为其霸权服务;可是在战国,齐宣王追求的不是称霸,而是兼并。
最有意思的是后一段,百姓开始和太子平一致,支持将军市被进攻子之。危机已经酝酿了这么久,而且两人的密谋连齐宣王都知道了,子之又焉能不知,所以市被攻子之而不克,因为子之早有准备。当然没有攻下来。结果呢,
“将军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
令人太难理解了,攻打子之不成,反过来就攻打太子平!
诡异!
在网络上搜索到,有一人解释:将军市被与太子平是两股势力。太子平与子之无论谁当政,对于将军市被而言都是无可无不可的,只是总也不能确定有点太折磨人。市被的目的是早日结束政出多门的局面,太子平根基正,所以首先帮助太子平攻打子之,后来发现子之的准备十分完善,不易攻克,就回过头来进攻太子。如此而已。
侯坤认为此种解释甚为恰中。
市被首鼠两端,结果是谁都想利用他,可是谁都不信任他,谁都不帮他,没准后来谁都想先消灭他,所以“将军市被死,以殉”。这是死亡的第一个大人物,本来不该他死的,这场权力斗争中本来没有他的事儿,可是他最先挑起内乱,然后就这样殉难了,这是一位闹剧中的悲剧人物。
笔者两人对一个问题颇有疑惑:看到一个材料,说太子平据说在与将军市被的作战中就被打死了。也有的说他就是后来有名的燕昭王。侯坤看《通鉴》得出的是这样的观点。
王德恒言之凿凿认为燕昭王是公子职。诸多文物证明有燕王职其人的的存在,证明和作为颇多。至余司马光为何要说太子平就是燕昭王,不得所解。
太子平是在内乱中被打死了。不过他代表的整个燕王室的利益,即使他死了,王族还是要坚持战斗。
其他贵族和官僚可能像市被一样首鼠两端,也可能只是作壁上观。
由于燕王哙的前期工作做得好,王室与子之两派的势力相当平衡,谁也打不败对方,预期的政变变成了持久的内战,以至“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1996年,遗址域内不远的高迈乡解村东发现十四座人头坑,从已清理的两个坑看,不少人头骨上留有箭头,显然他们是战死者。据估计,14座人头坑内总计约三万多颗人头,斑斑血痕、狰狰白骨,回放出残酷的争斗场景令人目不忍睹。这疑是燕王哙让国子之引发内乱留下来抹不去的历史印证。至于为什么只有人头,而没有身躯,可能是齐国占领的三年根本没有处理收拾尸身,自然腐烂,当后来燕昭王时,只能将头骨掩埋了。实际死亡的人数,应该还超过这个数字。
最后取胜的是有准备的子之,但是,燕国因此而残破凋零了。
著名的孟轲此时正在齐国,据说他在主持着稷下学宫。听说了燕国的事变后,他找到齐宣王说:“现在出兵燕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是建立周文王、武王一样的功业的时候。”
于是,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5 年),令匡章(陈璋)率"五都之兵"及"北地之众",向燕进攻。这个匡章是孟子的学生。由于燕国人民痛恨子之,对齐的进攻反而表示欢迎,所以齐军很快攻下燕国的国都,燕王哙身死,子之被擒后处以醢(剁成肉酱)刑而死。齐宣王本是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他缺少必要的准备,如何对付其他强国的干涉,如何制止燕国旧贵族的反抗,如何怀柔燕地的百姓?都没有见到齐国有何有效的对策。齐国以一种随意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件大事,从大义着想,使得齐军以胜利者的身份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十分残暴,连同宗庙祭器都当做战利品拉回齐国,“杀其父兄,系累(捆绑)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国之重宝)”。导致燕国人民于是又纷纷起来反对齐军。齐军占领燕国三年之后,内有燕民的反抗,外有赵、魏、韩、楚、秦等国的压力下,齐军不得不被迫退出燕国。
赵国派兵护送在韩国的燕国公子职归燕,是为燕昭王。
乘燕国内乱的时候,夷狄建的中山国也出兵夺得燕国的大片土地,据出土的中山王鼎铭文载,在燕王哙让国子之的时候,中山国的相邦司马赒"率三军之众,以征不宜(义)之邦",为中山国“辟启疆土,方数百里,列城数十,破敌大邦”。
燕国王哙死,子之被杀,国土被齐、中山攻破,几乎亡国。赵国想吞并中山,不愿燕国就此破灭,赵武灵王见燕国无王,于是把流亡在韩国的公子职请到赵,立为燕王,派将军乐池送回燕国,这就是燕昭王。
说燕昭王是燕文化继承人,没有任何异议,他丰富了燕文化的人才学,并将其发挥致极致的地步。
侯坤对燕昭王啧啧称叹。
王德恒说:实际上,燕昭王走的还是燕王哙的路线,只不过他才气横溢,性格坚强,颇有自信,张弛有度,所以成功了。
有人论述:如果说让国之乱和齐国破燕有何进步意义的话,可能就是经过这样一闹,把燕国的旧势力旧体制一扫而光,燕国真是一穷二白,正好绘画美好的图画。赵国进行干涉,送燕公子职回国继位,这就是有名的燕昭王。把燕王哙让国归于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范畴固然勉强,燕昭王重新建立燕国的政治体系,可能充分利用当时先进的政治理念。他的变革没有许多值得一提的新意,也没有遇到巨大的阻力——能够制造阻力的人都已经肉体消灭了,但确实给燕国带来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使燕国变得富强,以致三十年后,几乎在复仇之战中完成兼并齐国的盛举。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