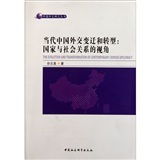书名:心路
作者:杨勋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年:2004-1
页数:337
ISBN:9787501166015
豆瓣评分:7.8分(10人评价)
博主评价:
未评价
来自豆瓣读书资源
全力支持发展组
1980年合肥编书会后,我就忙于编写我在会上承担的那几章书稿,指望尽快有一本综合大学能通用的教材,以满足教学急需并减轻我的教学负担。虽然我的农经课在北大经济系是一门小课,学时不多,但属于必修课,还是很重要的一门必修课。我有责任把这门课程教好,而且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让学生们了解并重视中国农业、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但是,这门课从1956年起就只有我一个教师,1963年有个叫李学智的农经毕业生来北大教农经,不到两年就调走了。北大不好呆,留不住人!我一个人要在很短时间编出一本象样的教材是很困难的。因此,我积极推动全国综合大学经济系的农经教师联合编书。
由于综合大学的农经教师大部分都是人大农经系毕业生,我是1956年首届毕业生,是他们的学姐,又在北京大学任教,我出来发起这件事比较容易。辽宁大学经济系有三位农经教师,他们主动承担了编书的具体工作,而且还联系了辽宁出版社一位副社长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每人只分了几章,只要按时交稿年底就有希望统稿、定稿送出版社,第二年就可能有自己编写的通用教材了。有了教材,讲课就方便多了。为了尽快出书,我们想方设法争取各自所在的学校系领导的支持,保证我们编书的时间和轮流在各校讨论书稿的旅差费用和小型讨论会的费用。
为了多有一点经费,我还找了高教部教材司和国家农委杜润生主任,最后从农委争取到了3000元资料费。我将这3000元全部交给辽大的同志们支配,也不无小补啊!最少可以用于打印若干份初稿,统稿时就不用手抄稿了。
为了出这本书,还得协调好这十几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如何确定统编组人选,还有主编和稿费分配等。由于当时大家都是讲师,只有复旦大学一位老先生是副教授,所以我提议不设主编,稿费由辽大的同志处理。我只坚持书中必须明确肯定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样,我们的编书组的工作就非常顺利,全国第一本《农业经济学概论》1981年秋就出版了。后来这本书还得了全国教材奖,参加编书的这帮人又编了几本书,大家不仅有了研究成果,先后提了职称,而且还乘着编书之便,在全国各大城市游玩,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厦门、沈阳、成都、昆明等等,当时想去的地方都去了。跟我们同时起步的一本农业企业管理统编教材,则因相互争主编争稿费半途夭折。
1980年暑假期间,正当我埋头专心撰写我们的教材初稿时,何维凌在北大校园的南北阁附近遇见我并介绍我认识了同他走在一起的陈一咨先生。何维凌原是北大技术物理系毕业生,是邓朴方的同班同学。何在文革中因与同班同学胡定国合写了“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送进半步桥关押。1968年底他们跟我同是“北苑监狱学习班”第二组的学员。文革后期,何维凌、胡定国因是反动学生分配不出去,留校在清河劳改。周培源担任校长后,重新处理他们的问题,把他们留校任教,成了化学系的教师。
从监狱学习班回校后,我和何、胡虽然从未联系,但因是同窗难友,相互是信任同情的。何维凌是上海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聪明能干,热情开朗,性格豪爽。同他走在一起的那位陈一咨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经所的研究人员,据说是刚从河南农村基层调来北京的。
陈一咨原来也是北大的学生,1959年因写了万言书向党中央进言,被康生点名思想反动,没有按时毕业,文革后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在河南确山地区当了人民公社书记和一个什么农校校长,历经艰难困苦从基层爬上来,通过邓力群——胡耀邦的关系调回北京。我对这种经历的人相当熟悉,并从内心敬佩,凭直觉断定这是一个有头脑、想干事、能吃苦、也能干事的人。我们一见如故,相互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过了若干天,何维凌带陈一咨到朗润园十公寓的我家拜访。陈说他到社科院农经所后被分在人民公社研究室,因为他当过公社书记,了解农村基层情况,当时的室主任王贵辰就让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问题。他想听听我的意见,问我:“这是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怎样研究?”我当时正在编写农村互助合作史这一章教材,评价人民公社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我深知人民公社是一种站不住脚的体制,于是,顺口就说:人民公社本身前途未卜,人民公社管理怎么研究?说不定,不等你作出研究成果,人民公社就不存在了,你研究它干什么?于是,大家一起议论农村的形势和人民公社中的问题,最后商定,不研究人民公社管理问题,而是要研究人民公社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发展前景问题,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存亡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农村正在兴起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问题。在那次谈话中,我还向他们介绍了在合肥同万里同志谈话的情况和安徽省委支持包产到户的情况。他们非常重视我提供的观点和信息,兴冲冲地走了。
暑假过后,陈一咨约我去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农经所副所长王耕今同志家。同陈一咨一起去王耕今家的还有他的研究室主任王贵辰同志。王贵辰是人大农经系59级学生。我们一起参加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早就认识。陈一咨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回来写研究报告文章报中央。我为陈的大胆设想叫好,表示将全力以赴,并建议利用学生暑假组织志愿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执行。王贵辰热情不高,犹豫不定。王耕今对这项农村调查计划表示热情支持,说利用大学生调查既省钱也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比用专职干部和专业研究人员好,因为我们并不是为了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而调查。大家还就如何组织和争取领导支持等出了不少主意。这天,我们在王耕今家吃了饭,各自散去。
王耕今是老资格农经研究者,早年曾在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调查减租减息,那时他是山东省委调研室的研究人员,薛暮桥同志的部下。1949年进城后,王耕今一直研究农村问题,1978年社科院农经所恢复后任副所长,1980年创办《中国农村经济》,任主编。1979年在密云的全国农经学会上,我把“批左”的那篇文章打印稿交给他请他指导,他给我很大鼓励,将文章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创刊号上。后来接触,王耕今是一位非常善良热情又思想深刻的学者,对青年同志无保留地支持。王耕今的前妻还曾是我们“抗属小学”的老师,文革后期死于“57干校”。王耕今的两个儿子王鲁、王冀也是我们“抗属小学”的学生。王耕今现在的妻子孙毓椿女士原来是北大中文系图书管理员,1957年被划右派后,调到五道口新华书店,五十多岁后,才同王耕今结婚。孙也是一位非常正派善良热情而且是非观点极为鲜明的人。我们在王耕今家吃饭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当时王耕今已经70岁了,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智慧而慈祥。他对青年人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一样。我们在王耕今家可以无拘束地随便谈话,不需要任何提防。正是那次谈话决定了不少青年人的前途和命运。因为正是在王耕今家的餐桌上画出了中国农村发展组的蓝图。
自那以后,陈一咨开始约我同他一起策划筹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当时,发展一词还是刚刚兴起,可能是何维凌他们翻译进来的,大家都觉得新鲜。陈一咨对农村基层很熟悉,他是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又转学历史系,考虑问题很周密,很实际。他的一些设想令我信服,所以我很愿支持他的计划,并把农村研究的希望寄于这个研究组。当然,在当时,我的支持对他们也是强有力的。
1980年,我在经济系是实权人物,在北大也相当有影响。由于我是“翻身户”,又是经济系的副书记,系里的日常事务我并不管,但重大问题是有决定权的,完全有条件以一个北大中层组织单位的名义为陈一咨的计划提供各种支持。
陈一咨是一位思想极其敏锐组织才能出众的人物。他虽然不懂经济学中的要素组合理论,但很快就把各种社会组织资源整合起来了。我利用自己当时在学校的影响找图书馆馆长谢道渊同志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并为他们办了三十个借书证。这样,发展组的兄弟们就可以自由出入北大图书馆和北大校门了。
陈有了北大的这块根据地,就可以在人民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师大、民院和外语学院等广招高年级学生。他把北大经济系杨勋的电话地址通知各校的学生头目,让他们将申请加入发展组的个人自荐资料寄给杨勋老师。这样,学生家长放心,不追问他们的校外活动,杨勋老师也认真对待。
这种课外研究活动对于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快就招来了三四十人。他们多是文革后翻身的中高级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他们比较关心国家大事,政治上敏感,也敢于冒风险。在发展组的骨干中有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人大78级(第一届人大学生)经济系的人最多,有杜鹰、白南丰、周其仁、白若冰等;农经系的陈锡文,工经系白南生、罗小朋等。当时人大经济系78级学生的班主任是吴树青。吴曾担心学生们老去北大会卷进持不同政见组织,后来听说是杨勋领头也就放心地让他们去了。有的学生家长怕学生在外面闹事惹事,陈一咨就约我去向学生家长做解释,解除他们的顾虑,如江百辰等。
江百辰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他父亲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他加入发展组带动了北京经济学院的不少人,如王文重、李庆曾、杨冠三等。民族学院的谢扬,外语学院一位王亚南的孙子都是自荐申请加入发展组的。这位外语学院的同学在申请时还附上了他对台湾土改的一份研究成果,那执着的热情和流畅的文笔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为了筹建发展组,那个冬天我陪陈一咨东奔西跑、上窜下跳、到处活动,几乎拜访了在北京的所有农业专家学者权威人士,还找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筹到了20000元人民币做为研究经费。那时的200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能相当于现在的20万吧!那是我和陈一咨在邓力群家里,邓当面打电话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同志叫到他家定下来的。几天后,社科院科研局李兰亭局长很快就派人把20000元打到了北大经济系账号上。我委托系办公室主任董文俊和会计常瑞华代管,支付凭我签字。
有了这笔钱,陈同我商量在未名湖后湖“梁效”住过的北大二招楼上租了一间办公室(每月租金200元),又从贵州调来了一个叫孙方明的外科医生在北招值班。就这样,发展组终于有了自己的固定联络据点。
北招在十三公寓旁边,距我住的十公寓很近。这对发展组活动很有利,有时讨论问题至深夜还可以从我家里煮一锅面汤端到北招楼上大家当夜餐吃,那热情真像当年闹革命了。
由于在北招建了联络点,同外面的联系方便了,也显得有来头有气势了,更多了一层保护。
此后几年,孙方明一直都在北招值班,协助陈一咨处理发展组的具体事务。陈的家在西单,有时只有孙方明一个人住北招。他为发展组立了大功劳。假如没有孙方明坚守,发展组的人都是在校学生,一群乌合之众,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孙方明能来北京,也是很偶然。孙是贵阳市一个麻袋厂的外科医生,文革期间因为认识罗小朋的爱人而认识罗小朋。罗小朋又在河南认识了邓英淘、陈一咨等。他们当时就约定有朝一日出了头,在北京聚集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罗后来考取了人大工业管理系研究生,孙等不安于麻袋厂的工作,就到北京入了发展组。在发展组,孙方明显得格外踏实苦干,1982年我从校内搬家至中关园,孙方明还主动来协助。孙方明在发展组期间,他的家属仍在贵阳。他长期同妻子分居,真是太亏他了。
后来,我大胆地用北大经济系的便笺去贵阳麻袋厂借调孙方明来京,居然调成了。麻袋厂可能一见是北京大学的信纸和印章就认为孙方明被调到北大,于是顺利放行了,反正孙每月的50元工资不要就是了,可以由我们那2万元经费中支付嘛!
孙方明能来北京,实在是应当感谢邓力群同志。假如没有那2万元,发展组可能无从发展!
邓力群对于农村发展组的支持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他不仅指示社科院拨给2万元科研经费,亲自促成把陈一咨调北京,并支持儿子和女婿加入发展组,后来还派书记处研究室吴象同志负责联络发展组,同意发展组以书记处研究室名义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最后使发展组成了一个具有权威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
由于有了北大北招这块地盘,各校投靠发展组的1977级和1978级学生热情极高。他们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在北大讨论学习,何维凌亲自为他们讲授“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当时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何根据外文讲授),这对发展组成员的知识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基础作用。何维凌还将他在20楼的一间单人宿舍提供给发展组使用,在木樨地22号楼,他的家也成了发展组的读书活动据点。何维凌为此得罪了卓琳的老乡——北京市一位政协委员。后来他的国外来信常被北京市公安局检查,并诬陷他里通外国,致使他不得不离开发展组,转到邓朴方的康华公司,创建了“中美中小企业国际联络处”。
1981年暑假前夕,发展组骨干们酝酿利用假期赴安徽滁县地区进行农村调查,所需经费由张木生的爱人杜英(社科院借调会计人员)负责提现金7000元。由于得到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的支持,又在农村所得到了副所长王耕今、所长詹武的支持(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矛盾,但对发展组都是支持的),又有了经费和重点大学的专业教师及应届毕业生参与,于是一个二十几人组成的民间调查队伍7月中旬冒着酷暑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安徽滁县地区,在那里受到了地委书记王郁昭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和配合。他们派了秘书长刘钊同志冒着高温陪我们下乡调查。
1981年滁县调查历时一个多月,那正是最炎热的八月间。据当地干部说,那种季节一般人都不下乡了,但是我们去了,而且来头那么大,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深知变动时期一切难以预测,他们热切的希望中央支持他们包产到户的试验,所以对这个“通天”的调查组非常重视,秘书长刘钊同志负责接待我们,工作生活照顾十分周到。
调查组兵分三路,一路为专题组,分别下队蹲点,如大塘、小塘等,主要有陈锡文、杨冠三、梁晓东等;一路是综合组,有邓英淘、王小强、周其仁与我和陈一咨等;另有一组称为流通组,专门调查供销社和产品销售系统的,主要有白若冰、王子平等。
调查工作的总部署由综合组负责。综合组共有两部专车,在20多天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凤阳和嘉山两县,重点是凤阳。主要调查方式是听汇报、看资料和找农民干部座谈,并到田间农舍实地参观考察。调查中,实行包产到户的小队干部和农民们兴奋地给我们介绍他们争取这一试验的经过和包产到户后的变化,热情地拿来他们种在包产地上的西瓜、甜瓜、煮花生和玉米,一定叫我们品尝并向我们诉说三年困难时期公社不准他们种地,大批社员外出逃荒饿死的情况。
我们用心地倾听着那些动人的农村改革故事,各人的小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录音机这类调查工具,一切收获都只能装在各人心中。
在小岗,我们见到了严队长,看见农民住的屋子里喂着猪和大牲口。在有一间破烂小屋门前,陪我们的干部给我们推开门,只见一个中年妇女赤身站在地上,那家里只有一些黑乎乎的破棉套和几件破锅破碗盆。我们不敢看,那干部却不以为然。他向我们介绍,当时有人全家只有一条裤子,大家出门替换着穿。看着这难以置信的贫困状况,心中像燃烧的火一样发抖,真不知用什么办法立即去改变它,真是恨不得立即把天地翻转过来。
在滁县,我们调查组还收集了许多反映包产到户的打油诗顺口溜,如:“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产到了户,不用村干部”等等。在田野里,我们看到农民们高兴地在地里一边跑一边喊叫:“我们解放了,我们解放了。”那种激动兴奋的模样是难以形容的。他引起我无尽的思考,给我无穷的力量:我坚信,一场深入的农村改革势不可挡了。
8月中旬回到滁县地委,我和孙方明、王小强一起听了计生办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汇报。由于内容太尖锐,最后,他俩不敢听了,由我一个人听到底。8月底回京后,杜润生同志通知我,中央要了解农村计划生育问题情况,我立即整理写成一篇“农村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送杜润生并转报中央胡耀邦、万里等。这时,光明日报正一连五天以大标题发表滁县地区“生产大上,人口大降”的专题报导,我的人口问题报告却通篇反映了农民们的怨气和愤怒,而且是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真不知后果是吉还是凶啊!后来的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1982年底,万里在中南海接见发展组人员时讲到了农村人口问题,并转告我:“你的调查报告中央用了。”他指的是1982年中央关于农村人口问题的11号文件。那份文件为中国农民可以生两个孩子开了一个小口子,说有困难的可以生第二胎。这里所说的“困难”,就是第一胎生女孩者。
1981年8月底,大家带着丰盛的调查成果回到了北京,为国庆节后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农村调查资料。
为了赶在国庆节前把所有调查报告打印出来,我利用国庆节的三天假期,请经济系打字员马尚云和她的好朋友加班加点为我们打印那批调查材料。那时还没有什么报酬给加班的打字员们。感谢她们的方式就是请她们去看几部外国电影,如《魂断蓝桥》、《翠湖春晓》、《音乐之声》等。这种电影票是我家的老赵从他们的工资理论组搞到的。他们理论组在于光远指导下研究按劳分配问题,那组里有后来的大经济学家董辅仁、孙尚清等,赵是人大派去的,组里的罗元铮先生有办法搞到一些外国电影票。在当时,那是一种特权,一般人是见不到的。
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中央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生产责任制,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安徽的责任田试验被中央承认了,邓小平专门讲话肯定了安徽凤阳的包产到户。当初被人攻击在安徽支持包产到户造成混乱的万里也随之当了国家农委主任。于是,包产到户的争论很快就停止了。四川省广汉县在省委书记赵紫阳支持下,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们胜利了。发展组这个非正规组织成了农村改革的急先锋,后来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1号文件的制定,终于被承认是一支有影响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1981年我和陈一咨被指定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除了我和陈外,其他理事都是各部部长,我认识的有崔乃夫、彭佩云等。
1981年11月,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正式在北大成立。成立大会是在北招的会议室召开的。到会讲话的有邓力群、杜润生。会议由王耕今同志主持。我还专门邀请了经济系主任胡代光同志到会。当时,北大校园里正在闹竞选,发展组能在北大召开成立大会,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1977级和1978级大学生、研究生。同是青年人,他们的目标心路和行为方式却是这样的不同,真是够耐人寻味的一种社会现象!
发展组的真正策划者是邓英淘和陈一咨。邓上北大前在河南是陈一咨所在公社的生产队长。他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交情很深。后来都回到了北京,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实现自己当年的愿望。我和何维凌也都不是安分的人,从文革到半步桥都是因为有自己的抱负。现在大家找到了一个一致认同的大题目,作起来齐心合力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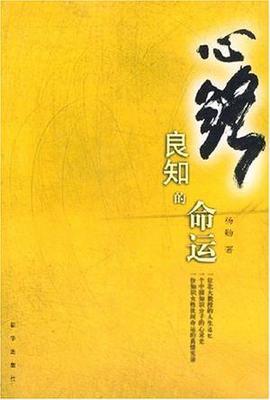
发展组宣布成立后,开始时暂寄中国社科院农村所。1981年77级的毕业生们通过国家计委宋平同志的帮助,争取到了几十个编制指标,就先后分配到了社科院农村所。发展组是农村所的一个研究室,所里有一间房子的牌子写着发展组,但发展组的活动并不在所里,也不在北大北招了。他们在西直门内租下了当年属于中联部的伍修权的公馆的一半作为发展的活动基地。就这样,发展组总算是一个正式被承认的组织了。陈一咨宣布王耕今是组长,他和杨勋是副组长,后来又说他是组长,杨勋、何维凌是副组长。再后来还说吴象、王耕今、杨勋是他们的顾问。现在,我记不清他的各种说法了,我和耕今从来就没有注意自己在这个组织中的称呼和地位。我们几乎是无条件地支持他们,只要他们能组织起来认真地研究农村问题就满意了。
发展组的一切成就当然是陈一咨他们这帮人费尽千辛万苦争取到的。我同他们不是一辈人,王耕今跟他们更不是一辈人,大家谁也不想在这个组织中争什么个人地位名声。这也就是发展组的力量所在。后来这批人真的发展了,影响越来越大,在一次会上被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发现了。他们请王小强牵头出来组建体改所,于是,发展组面临着重新分化,分成了三部分:体改所、国家农委发展所和社科院农发所。此时,发展组得了“农民党”的外号,成立体改所后以城市改革为主了,于是人们说“农民党进城了”。我还是死守农村,继续做顽固不化的老农,同进城后的农民党联系少了。后来,主要是从报纸上电视上见到当年发展组兄弟们的好消息了。
1983年以后,陈一咨因劳累过度病倒了。根据书记处研究室的安排,他不得不在上海、苏州疗养。1983年我在厂桥中直机关招待所见到他。他悲观地放声痛哭,对我说:“上海医生判他活不过一年了”。那天我们在中直机关招待所吃午饭,吃了甲鱼汤。也不知哪个省的农村干部给他送来了一池子小王八,他每天吃一只。我对他说:“不要悲观,不要相信医生的话,你会活的长的。每日一个王八是皇帝的生活,你要有信心才是。”在场的陈锡文、白若冰都耐心地照顾他,相信他是过度劳累致病,只要休息一些日子,就会恢复健康的。
陈一咨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在那种情绪下还把写给女儿的诗歌念给我们听,很是感人。陈为了发展组,不仅丧失了健康,还失去了可爱的小家庭。他的妻子吴彦同他分开了,他成了孤独的单身汉,一心扑在工作上,发展了还要发展。陈一咨后来去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他说还要办一所像样的学校为中心现代化培养高级人才。我把这消息电话告诉了90岁的王耕今,王耕今也托我祝贺他,认为他肯定能成功。在王耕今看来,我还算年轻,陈一咨还不到60岁,就更是年轻了。我们祝愿这位发展迷永远发展不断取得成功!
1983年陈一咨在南方疗养期间,王小强代表发展组兄弟们来我家,邀我离开北大调到发展组去,因为那时中央还没有干部年轻化的政策,陈病倒了,何维凌被北京市公安局盯住了,他们只好请我去挂名主持工作。我当时正在北戴河度假,我的赵先生代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他认为我在北大过的太累,既然支持农村发展组,还不如离开北大彻底同发展组的青年们一起干。我没有表示反对,就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从感情上陷于两难:既要支持发展组,又舍不得离开北大,最后还是同意离开北大去社科院专心农村研究。当时他们正在兵分三路,我表示:只要有一个名额,我也要留在社科院农村所,决不去国务院农发中心,也不去“体改所”。那时一再表示要跟我一起走的有杨冠三、宋国青等。我于1985年11月正式去社科院报到,是因为这期间发生了左腿骨折,又遇上评定职称、整党等干扰,调离的事一拖再拖,前后拖了两年。
我到社科院农村所时已经53岁了。这样的年纪社科院还要我,真不容易了。当时我下定决心要在社科院农村所好好地干几年,绝不能占着社科院研究人员这个名额!
我调社科院农村所,得到了王耕今同志的大力支持。记得当时的所长詹武同志曾找我谈话,向我到所后如何安排?我当时听不懂他的意思。他说发展组组长是陈一咨同志,你来了以后如何安排?我才恍然大悟,他说的安排是指行政职务。我对詹武所长说:“我在北大是一名普通教师,担任党的工作是社会兼职,是党员选举的,不是专职的党政干部。”在北大很少有过等级观念,除了工资是有级别的,职务很少有人注意。我告诉他,我来社科院是为研究农村,不存在什么工作安排问题。我也干不了什么行政职务,我是教师,不是党政干部。詹武听后表现出轻松,可能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一个向他伸手要官的人。过了若干年后,我才发现,社科院到底是一个国家部委级机关,在很多方面官气十足等级分明,这和北大有很大的差别。我已进入老年,思维和行为方式早定型了。我不可能重新适应官场,不管到那里,我还是我,我只能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如今,当年发展组的一些年轻人的确发展了。我为他们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总算没有白费力气支持他们。杜润生1981年11月在北大北招发展组成立会上的讲话一直响在我耳边:“我支持你们,你们走到底我支持,你们走不到底我也支持。”我想要加以注解的是:“我为中国农村发展支持你们,我的支持是无条件的,不求任何回报,支持学生是一名教师的崇高责任。”
我衷心感谢发展组的青年朋友们,他们曾激起我的信心和力量,鼓动我进入思考的新天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