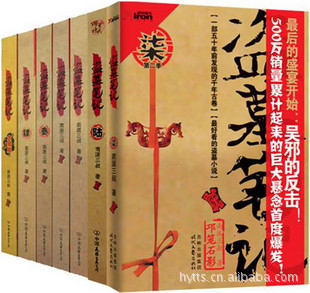克罗齐埃主张在面对社会阶层断裂时以投资模式替代摧毁模式,对人际关系进行投资,吸收精英。这让我想起了改革的路径。
改革之难,难就难在要以非暴力、曲意逢迎各方利益,并恰当地安排改革顺序。不这么做的休克疗法激进改革则主张人不可能分两次跨过悬崖,不过即便可行,也是需要一个条件的——崖间距不能太大,否则你一次也跳不过去。但符合这样社会条件的社会太少了,成功的变革总是在无意之中,就一个个完成了,以至于没有人感觉得到。当民众、执政集团意识到一个国家、社会需要改革时,这个社会早已撕裂了很大的距离。中间是惯性文化、利益集团.....转型的目标社会拥有一套内在匹配的多元主义、自然法习惯、宗教系统。转型中的社会则未必,改革不是即意味着与习惯不和谐,改革集团在官僚体系与社会民众中两头受气,而且绝无可能摆脱二者,他们需要向官僚体系借力,以保证改革,促使他们行动的动力是许之以新的利益;还需要向大众借势,保证改革合法性,保证政治现代化能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保证政治发展能够容纳政治参与。纯粹偏向一方,都会带来恶果。创造互相依存的、互补社会分层使他们唯一的办法,亦如改革者的曲意逢迎,否则分之则是社会地带的撕裂,社会分层将持续对立。改革者摧毁社会阶层关系,是下策;中和各方利益,是中策;投资各方利益,并使各方相互需要,则是上策。
能够创造互相依存的社会阶层结构并不容易,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资源越丰富,一旦越来越集中,则竞争程度越小,合作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就是社会的板结、固化,改革发力也将耗竭,改革的生命力将仅仅维持在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秩序供给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