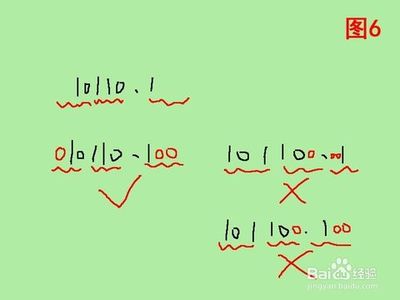《公开的情书》
在我记忆中,1980年似乎是以靳凡的《公开的情书》为开端的,其实这个中篇小说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的《十月》上,它上市已经是二月了。可见其当时对我影响之大。靳凡就是金观涛的太太刘青峰。
以书信体为小说并不少见,但这部“小说”却基本没有情节推进,开始的第一封信是老嘎向朋友老久推荐身在贫困贵州山区的真真,最后一封信是老嘎向真真的情感告别。如果说有故事框架,其框架是,老嘎向老久推荐真真后,才意识到自己深深爱着真真,于是两个好友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在情感道路上屡屡受过伤害。最终是追求艺术的老嘎选择了退出。在这个框架里,真正吸引当时我们的,是一封封长信中思辨的问题:爱情,情感。我不知道它是否刚走出校门,踏上社会的刘青峰与金观涛,以及与他们的朋友们精神交流的真实记录。当时刘青峰就分配在贵州山区教书。金观涛在杭州一家工厂当工人。在1980年,这些情书给我的启蒙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可以这么丰富的。
这些信写于1970年。现在人们控诉文革,在我看,其实往往只看到了文革之表面。比如文革表面是现代迷信导致的红色恐怖,是打砸抢之后的一片文化沙漠。但恰恰是在这片文化沙漠中,许多人在穷乡僻壤,守着一盏孤灯,获得了人生中很安静的一段很从容的读书时光。现在回顾,我们读书最多的时光,竟就在文革时期——因为那时书反而凸显其珍贵,于是它在一群群人的传阅中,更加如饥似渴。同样,现在回顾,我们写得最多、写得最长的信,当然也是在文革时期——书信大约是文革中最具体的一种精神寄托吧。那时我们与最亲近的朋友谈读书,谈理想,都通过一封封的长信。这些信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单纯而幼稚,而也就是在那个年代,才会有那样的单纯。我是把曾拥有过那样近似透明的单纯当作人生财富的。
正因我们当年的信不能与靳凡他们比,他们的精神世界才成为1980年我们仰望的方向。这些信中吸引我们的,在当时还不是爱情,而且,其实,其中除了“亲爱的”,“想念你”、“吻你”这样的表达情感方式,真几乎没有情欲的成分。它所吸引我们的,其实是那种豪迈而浪漫的激情——
我会把这春天的枝条高高举起,像湖边放风筝的快乐的孩子一样,那将是我们的旗帜。
一颗软弱的心是容纳不了世界上正在经历着的史诗般的剧变的,你应该是一把火,一柄剑!
这是典型那个时代的语言。我还记得下乡时,曾很敬仰同宿舍一位老高二知青,就因为看到他枕头下日记本的扉页上,用很有力的笔触抄写着——
我愿生如闪电般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般迅忽。
《公开的情书》中老久对爱情的这一段理解也有很鲜明的那个时代特色——
不会生孩子的爱情是不完善的。如果说婚姻是为了种的延续,那么新时代的爱情将是为了新思想、新道德的诞生!
情爱也是为了播火。
这些书信对于当时的我们,就像老久在给真真的信中所描写的,“我们好像是在那被闪电照射得忽明忽暗的哲学思想的密林深处狂跑”,它提供了多少吸引我们的信息啊。比如哥德尔,老久的信中告诉我们,“一个完备体系本身必然是自相矛盾的,要不就是不完备的”,这在当时真是太振聋发聩了。再比如赫尔岑,真真给老久的信中用了这段当时令我作为格言抄到日记本上的话——
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刚制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力求唤醒年轻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力求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是这段话引导我找到了巴金翻译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现在回头看八十年代,《公开的情书》可看作是一代新知识分子的亮相。他们,金观涛与刘青峰,代表着文革前培养的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有意思的是,五十年代培养的大学生很难有的那种在黑暗中追求的批判精神,在文革中却在这一批人身上孕育了起来。他们在1970年就超脱了当时我们还沉浸在“早请示晚汇报”中的环境,就有了守护自我、追求自由思想翱翔的意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真实地是由这样一批人最先推动的。这个有意思的结论是,自由思想其实是播种于文革的,这对简单思维的人而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八十年代诞生了前后两大拨思想者,第一拨就以包遵信、严家其、金观涛、刘青峰为代表,他们组成了后来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这个编委会成员很多是下乡回城的知青思想者,当时最活跃的王岐山、王小强、唐若昕、陈越光、翁永曦等都在其中。《走向未来丛书》是八十年代第一套开启我们心智的丛书,小32开,白色封面黑字,它在1983年出了第一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