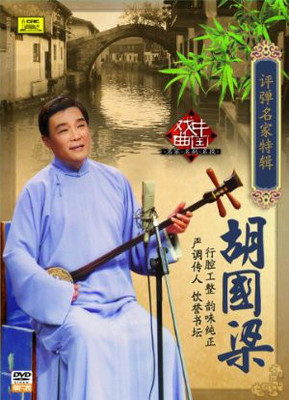老兵胡国忠是我的同行。这个有着十年志愿兵生涯的老兵,退役后与我在一所学校教书,同教初二语文平行班。
同行跟他论课研,他却决意要说打靶,他说当兵那会儿故意把半自动卡宾枪准星瞄向一位老乡面前二百米胸环靶。结果老乡得到嘉奖,做了他的上司,他却用宽大的绿袖子掩起嘴巴笑,而且,居然还在被子里笑。同室的战友以为他梦见了媳妇,他却嚷嚷:老乡老乡,靶上一枪。
语文课上有关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课目,他总喜欢讲几个亦真亦假的故事。他是战争的当事人,自然没人敢说他讲的是假的。他说,新兵时他的投弹是军区出了名的远。有一回军事演习,他却只投出了十米,最少的一次,甚至是五、六米。投这么近连黄毛丫头也会,但他却冲上去拣起吱吱冒烟的手榴弹,重新又远远地投出去的。他说,三天两头投弹,太没劲,想试试投近一些的滋味。领导训话他,抗不过,他说投远投近一样有意思,两样技能同样重要,你还说要是敌人就在五、六米那里打着埋伏呢!结果他得了一个警告处分。八十年代初,中学语文课有珍宝岛自卫还击战一课,轮到他上课,他会从樟木箱里掏出那套有些泛白的黄军装,毕恭毕敬地穿上,然后迈着军人的步子走上讲台,让学生郑重地把课本摊开,却从不教课,连一个生字也不教。他在课间只说一个故事,说完,课也就算上完了。说穿了也就是一个小故事,却让每一届的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听的时候心都吊到喉咙口,硬是一愣一愣的。
那是除夕的边境,瞎天黑地的,营部却不许点灯。天刚下过没膝的暴风雪,荷枪实弹的他,一个人在距营房百米远的边境哨卡值班。
那一刻,他将耳朵竖得比枪刺还高,突然,远处传来“嗷——嗷”的声音,像一个受了重伤的人痛苦的嚎叫。作为训练有素得过军区全能比武第一名的他,心里第一反应是“有情况”。他马上转身悄悄地给营部值班室拨了一个电话,电话其实是一个三位数的喑号,只有接电话的值班员知道这情况多重要。然后,他揣起卡宾枪,轻轻地趴伏在哨卡门口的雪地里。连长接到报告,汗毛都竖起来了,立马组织了一个加强排,猫起腰全副武装地从哨卡周周摸黑包抄过来。奇怪的是,当包围圈收缩到哨卡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敌情,根本没有什么“嗷——嗷”的声音,连长发狠话,骂了句“狗熊!”便率部全撤了。刚撤不久,偏偏“嗷——嗷”的声音在暗夜里再一次响起,这声音似有似无,似近似远,会不会……,这回啊,老兵胡国忠没有去哨卡打电话报告,而是等这声音逼近,再逼近。
终于,听得见对方十分粗重的喘息声了,真真切切的,这回,他的身子居然突然发起怵来,怎么办?向上级报告呗,一旦再一回发现前一次的情况,可能又会受到一顿怒斥,弄不好还会说我谎报军情,受到摘掉领章帽徽的军纪处理。不报告吧,这分明像是敌人来犯的举动啊,而且估摸着在大约十米至二十米远的地方。于是,他尽可能地把身子在雪地埋伏下去,只露出眼睛,把枪一次次瞄准发出声音的地方。他知道,要想提前撤销上次投弹引来的警告处分,只能将功补过。年关还未过去,他却觉得自己的好运提前来了。他把子弹推上膛,等待敌人撞上他的准星。可是,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要瞄准敌人,那怕瞄准敌人的一个影子,也是多么难易做到啊。
“嗷——嗷”的声音再次响起时,他终于不自觉地叭叭叭地射出了一梭子弹,他定了定神,仿佛发现敌人被他击中了,“嗷——嗷”的声音越发大声了,然后嘎然止住。听到枪声,连长带人火速突奔过来。发现哨卡空着,屏住呼吸在哨所四周仔细了望了一会,发现四周的山野除了寂静还是寂静。有人遂发起莫名的火来:“人呢,死了啊,人呢!”
“敌情?屁也没有一个!”连长突然拧亮挎在肩上的长长的手电,借着发白的灯光,发现不远处雪地里有一串串鲜红的血迹,像正月里的腊梅,开得无比耀眼,循着斑斑点点的血迹找去,居然发现一头栽倒在雪地里的正在喘着粗气的大野猪“嗷——嗷”地叫着。而这时,老兵胡国忠却揣着卡宾枪突地在雪地站了起来。
这一回,边境这个设了十九年的哨所第一次受到上级嘉奖,得了一面二等功的锦旗。老兵胡国忠得了个人三等功。大红的嘉奖令寄到胡国忠所在的乡里,乡长嘴里居然与部队首长说的是同一句话:“国忠同志敌情意识强,好样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