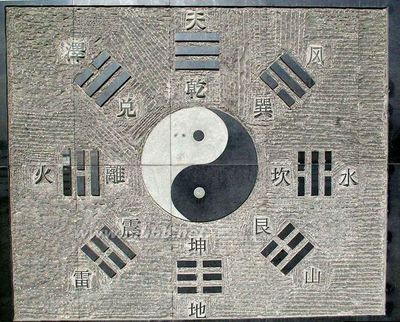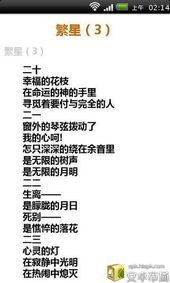按:
黄宗江、阮若珊伉俪是中国文艺领域中一对杰出的人物,他们为中国戏剧和电影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心血,他们相依“伴老”,历尽生活艰辛,也享受了无穷的家庭欢乐。二老合著的《老伴集》,各自用或平实亲切细腻、或幽默睿智豁达的文字描绘了那一段历经酸甜苦辣的人间真情。这里摘录的是书中阮若珊所叙述的和黄宗江的一份情缘,而且,黄老性格的各个侧面都得到了翔实、生动的反映。当然,阮团长对事业与爱情的坚韧、执着也在文字中时时不经意地表露出来。作为晚辈的我们在重读二位老人写在十多年前的这些文字时,不能不留下长久的感动与思索。祝愿二老在另一个世界里永恒地厮守在一起,如他们生前一样精彩……
(本文标题《阮若珊:我与宗江》为博主所拟)
前排左起:黄宗江、外孙叶涵、阮若珊、外孙吕男。
后排左起:三女儿阮丹青、大女阮丹妮、二女儿阮丹娣。
1956年春,住在南京鼓楼四条巷一所别致的、带小花园的小洋房楼下,据说这里过去是西班牙(或葡萄牙)使馆的房子。正是7月炽热的夏天。忽然有一天,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其实这时我们都已三十五六岁了)推开我的房门,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他说:"请你看看",我还没看清他是什么样子,他就关上门走了。我接过这封厚厚的信件,不知是稿件还是什么,放在书桌上就忙团里别的事情去了。
午后,孩子们和阿姨都午睡了,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封洋洋万言写给我的信,但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啊?最后署名是"您的,陌生的黄宗江"。黄宗江?好像听团里人提到过此人,也许在团部办公室匆匆见过一面?不太记得,反正从来没有和这个名字有过任何联系或联想。我把信看下去,他谈到对我的印象。他从l953年就在丁洪同志口中知道了我的名字,我的身世和不幸的婚姻;1955年吴白桦在越南牺牲他又联想到我;l956年话剧汇演,他说他远远地,也是近近地看到我,信中对我只获三等奖有所不平。这一切他都有意,我却完全不知。后来我们相识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正在太湖畔创作《海魂》和《柳堡的故事》两部电影,思想很活跃,他给我送信那天饭都没吃,只吃了两块冰砖。他充满了年轻人一样的激情给我送来这封信,一封热情、真挚、坦荡的情书。这里有他的自我介绍,也有苛刻的自我批判,有对不幸婚姻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他"蓦然回首"寻到了我,深感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阮若珊:我与宗江](http://img.413yy.cn/images/31101031/31093134t01b1c76cdee8e3ff4e.jpg)
信中说到他的留日电机工程师父亲,"无冲突"的和睦相爱的家庭。从小受到《寄小读者》、《爱的教育》、《小妇人》、《黑奴恨》的熏陶,形成了温情的、"斗争性不强"的性格……他和我是多么相像啊!我也有一个留日在庆应大学法学系毕业的父亲,也有一个和睦相爱的家庭,也读过同样的书籍……他有七个兄弟姐妹,我也有七个姐妹兄弟,他小时候住在北平西单大木仓,我住在西四南大院胡同内三道栅栏,我们离的不远,可惜无缘见面。他离婚后,不少人为他提过年轻、漂亮的才女,但宗江不为所动,他告诉他妹妹宗英,他要找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离过婚的女人。可他怎么会找到我呢?而且是那么坚定。
经过青年时代不幸的婚姻,又经过一段痛苦的,经常自责而又不能摆脱的无望的爱情。现在吴白桦牺牲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已将感情的闸门紧紧关闭,决心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再也不愿在感情的围困中折磨自己了。我毕竟过了35岁,并且对戏剧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总向往着参加建设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创作实体,我热爱我的工作,这些就已经包融了我全部的情感。但宗江的信激起我内心的波澜,打破了我的平静,对这样一位真诚的、坦荡的、谨慎严肃而又热情的人,我不可随意对待。从他的信中我感到他很有才气,品格不俗,很有些相见恨晚之感。但我又很顾虑,毕竟我们很陌生,距离较远,而我才貌乎平,不像他幻想的那么好,这位才子怎么会对我有好感呢?我一下子不敢接受,说容我考.虑,但我隐瞒不了对他已有的好感,难负他一片痴情……这时,宗江的好友王啸平、胡石言也常来看我,并向我介绍宗江是个好人……宗江急于得到我的答复,在南京的一个暑假,他几乎每个清晨都来看我,彼此的感情逐渐升温。他很喜欢我的两个女儿,这也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很快的互相了解,感情迅速增长。我们像两个大孩子一般去游玄武湖,乘着木船,船娘摇着橹,在暮色苍茫中度过那美好的夜晚。两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过了一段谈情说爱的日子,在美丽的玄武湖定下终身。
好事还须多磨
宗江说我们都老大不小的了,用不着花前月下培养感情,也不需长期考验,我们彼此已经很了解,很相投,而且一个在南京,一个在北京,相聚时间难得,何必拖呢?天赐良机,暑假后我带着孩子回北京上学,宗江去了总政创作室,我们又可以经常见面了。于是我们在1957年元旦,就在我家故居隔壁"三道栅栏40号"一间小平房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买了些水果、糖、茶之类。来的客人都是我同班同学,他们来自祖国各地,都是新朋友。而我的老战友,老同事,有些人却没有来,这也是他们的态度。我知道在我的老战友中,对我和宗江的结合是有异议的,他们不能认同宗江。我的老上级、知心老战友王地子也只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么!"我的另一位同事,还和我到中山公园诚恳地劝我"慎重从事",意思是此人不可靠……对这些议论我心毫不动摇,我喜欢像宗江这样温文的文人学者,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是个真而又真的人,不会骗我。当时我家庭的态度,也是很犹豫的。虽说没有杀出个老夫人,但老爷子来信说:"我家无白丁"。我们全家,父母、兄弟姐妹无一不是共产党员,现在怎能接收一个"白丁"呢?老父母觉得遗憾,但他们并未阻止我,我也相信宗江一定会成为"红丁"的。我的弟妹们给予了我同情、理解和支持,特别是我的四妹若瑛,忙里忙外帮我照顾两个孩子,帮我张罗婚事。就这样,宗江这位前半生有家无实的流浪公子,带着仅有的半条军毯、半柳条包揉成一团团的旧衣服,和我一起建立了一个清贫但温馨的家。
开始大女儿想不通,不能接受这个"黄叔叔",她心里只存在一个"白叔叔"。二女儿却很开心,管他叫"黄爸爸"。我们带着两个女儿出去玩,宗江肩上扛着贝贝(丹娣),宝宝(丹妮)噘着嘴生着气跟在后面,她比贝贝大两岁,情绪有些混乱……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两个女儿都很自然的改叫爸爸了。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表妹婿,是某省一首长,见面时对我家大官热络,对宗江却很冷淡,让他很生气,还是四妹劝慰了他。总之,我们家不是党员,就是官员,宗江承受着压力,但他毫不自卑。按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我们是不般配的,一个是老党员,准师级干部,一个是非党员,排连级干部,一个来自红区,一个来自白区,好像很难协调。但我们俩人却从未想过这些,也毫不在乎这些。我坚信爱情不能受地位、等级、物质等条件的限制,爱情是由高尚的情操和真诚的情感结成的。我虽受过不幸的婚姻和痛苦感情的折磨,但我仍持之不变。人家批评我感情至上,我也认了,对客观的责难不予理会。当时也有不少人是赞成我们的结合的,如我们的老首长陈沂部长、江岚部长、陈亚丁部长等等。婚后我们到呼和浩特省亲,两位老人家见了宗江很满意。妈妈说他斯斯文文,很有礼貌,是有学问的人,对这位自找上门来的大女婿也认可了。l958年春节,我们全家都在南京。这时我已怀孕,我们游了梅花山,宗江肩上扛着丹娣,手里牵着丹妮,连同我肚子里的丹青,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5月3日,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在布谷鸟声声催唱中,我无痛分娩生下女儿丹青。宗江无比高兴地第一次作了父亲。同年夏,我调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从此我们全家定居北京,开始全新的生活。
结婚并没有使我们安乐、懈怠,而是更加努力工作,努力学习,逐渐赢得众人的理解。有人曾认为我结婚后就会不断生孩子,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事实上我和宗江婚后很小心地只生了一个小女儿丹青,我们的精力全放在工作和事业上。正如宗江给我的信中所说"我们也许是两支文艺大军合流后两个小卒携手向前的范例吧。"我的二姨很喜欢宗江,他们又是燕京大学的老少同学,二姨年轻时在北平幼稚师范演出过话剧《卓文君》,她很欣赏卓文君的作为。二姨是我们婚姻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可能与此有关吧?
宗江的爱与痴
我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宗江由于他父亲早逝,很小即走上社会,以后婚姻生活不顺利,几乎长年没有个真正的"家"。单身汉的生活习惯是有的,他没有积蓄,有钱就请朋友吃饭。其实他是很爱"家"的,我们成家后他努力想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很顾家,不乱花钱,尊重妻子,疼爱女儿,包括她们长大成婚后的夫婿、孙儿。他很笨,家务活儿一窍不通。"文革"中劳动改造,朋友们笑谈他的"手笨的和脚一样",实在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即使让他干某个家务活,也总出反效果,还得别人收拾残局。但他心是好的,抢着倒垃圾,有空时负责采购,家里的饼干、糖果以及那些盒子,都是由他负责装配。他对我的两个女儿视同己出,后来我们生了4个女儿,三个女儿就是亲姐妹,因为爸爸待她们一视同仁,无任何差别。小女儿长很大才知道两个姐姐是同母异父姐妹,但她们早已没有这个界限了。我们婚后几十年,宗江从未对我说过一句严厉的话,从不和我生气,而且总是顺着我。我当然也很尊重他,他以满足我的一切为最大快乐。他如此挚诚,我倒很不愿意提出什么要求,怕给他增加麻烦。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外出"深入生,活",从西藏的拉萨,新疆的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他一个人进行着边疆的苦旅之行。1964年秋,他随一当时秘密的新闻代表团,赴越南南方丛林一年有半。接到他封封来信,有时是诗,信中饱含着对我们母女的一片痴情。在越南南方游击区艰苦环境中,他写了不少诗体日记,还有在吊床上打摆子写的、他最珍爱的话剧《南方啊南方》。我以他的刻苦、勇敢、奋进而自豪。
宗江极爱朋友,对朋友的热诚是无可比拟的,特别是对那些遭难的朋友,宗江从不嫌弃他们,总是给他们力所能及的援助,这一点我实在不如宗江。对一些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和一些所谓"右派"朋友,我是有些怕联系。一方面我有"左"的情绪,对这些同志有不正确的看法,另外也怕惹出事来。现在看来宗江是对的,他对真正的朋友是信任的,不改变自己的看法。我记得大约是"四人帮"被粉碎前夕,他的好朋友白桦、徐光耀赶巧一伺来到北京,那时他们的问题尚未解决,宗江热诚的留他们在家吃饭,晚上并把他们留宿在我们那间小破屋里,相谈极为愉快。我在宗江的影响下,对朋友的看法,特别是对他的老朋友有了信任和崇敬的感情。其实一个人品质的优劣,不在于他参加革命时间的早晚,也不在于他地位的高低,而在于人品、人性、人情、人格。以后宗江的朋友,我的朋友,都成为我俩共同的朋友。
宗江待人和善,人缘好,只要政治观点一致(这一点他很重视),都能成为朋友。他对长辈尊敬,称为恩师。对同辈朋友,对有才华的朋友十分钦佩。对年轻的,力求进取的人,他很乐意给予帮助。有一位自学写作的青年金岛,本来素昧平生。他曾看到作家梁晓声同志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他刚调来北京时的遭遇。是黄宗英给他写了个条子,让他有困难去找黄宗江。见面后宗江热情地接待了他,可他又因为腼腆,而未提任何要求……金岛这次从甘肃来京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住在火车站,受梁晓声同志文章的启发,也来找宗江。宗江热情地招待他吃过饭,只是没地方招待他住,只好塞给他几十块钱,还有宗江那块作为"陪嫁"的半条毯子,鼓励他好好准备……后考试未中,但他保留了那半条毯子,和宗江成为忘年交。不幸他于前两年路见不平失手打死了人,犯罪入狱,屡次来信说他在狱中还不断磨练写作。我们希望他经过这次炼狱,能造就成一个有用的人。
说到宗江对文化艺术,特别是对戏剧艺术的迷恋,可说是痴迷了。他从小因父母亲喜欢听京戏,受到熏陶,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校园戏剧的积极分子。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他应邀在重庆南开中学对同学们讲演,校长就曾用这话介绍说:"周恩来同志,曹禺同志,黄宗江同志,是我们南开三大女演员。"在燕京大学时,他更是热衷于剧社的活动,编、导、演样样都尝试了,以至未读完大学即弃学到上海孤岛,参加了佐临师领导的职业剧团,与石挥、韩非等齐名。后因逃避日伪演艺界对他的邀请,弃高薪往战时重庆投奔夏衍、于伶等前辈。在重庆因演《戏剧春秋》一赶三颇具名气,但不久又出人意料地参加了赴美参战海军,飘洋过海近两年。宗江为什么不安于现状,总是变换环境孜孜以求?除了一些感情生活的失意,主要的他有一种追求,他要当一名作家,心目中曹禺大师是他向往的目标之一。受过西洋文学熏陶之后,美国剧作家奥尼尔又成为他年轻时的偶像,他于是投笔做一名海员,"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体验海上生活。巧的是,他不但像奥尼尔一样当了一名海员,后来也像奥尼尔似的得了肺病,躺在床上写剧本。这样几番折腾,他前后上了9年大学而未毕业。然而这位无文凭学历的人,1986---1987年被美国国务院的富尔布莱特基金会聘请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了客座教授。
宗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受到我国传统教育的抚育,又受到欧美文化的熏陶,崇尚人道、人性、人情的高尚道德观念。他最终找到最高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世界大同,或说解放全人类,或说英特纳雄奈尔都是一致的,他甚至说和释迦牟尼的极乐世界、耶稣基督的天国都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应是最高的人道主义。说起来好像他的思想有些繁杂,实际他很单纯,他一生的信条就是要做个好人。
由于宗江接受中西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他对艺术的追求主张也多样性。他自己不但欣赏各种艺术本身的多样性,他也喜爱各种各样的艺术,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民间艺术等等,尤爱戏剧。各种剧种,昆曲、越剧、豫剧、沪剧、黄梅戏、曲艺、评弹……他都欣赏。对京剧最熟悉,特别喜爱优秀的演员。至今他的床头必备一收录机,每晚听着戏曲录音带,听着谭鑫培、余叔岩……方能入睡,真是痴迷之极。他已经听坏了好几个收录机,我在他枕边也慢慢适应了这种西皮二簧的催毛。
他的多样性也表现在生活中。他自称美食家,不但喜吃淮扬体系的南菜、上海小吃,也喜欢北京的北菜、小吃,时不时的要吃窝窝头,水疙瘩咸菜。西餐、中餐都喜欢,不论南北。讲究质量,要够味儿。他喝少量各色的酒,品各种茶,绝不拘泥于一种。他又十分怀旧,最有趣的是他有一种儿童一理,往往吃到一种东西,觉得很对味儿,就非常高兴地说:"和我小时候吃的一样",为了做得"和小时候的一样",我可费了老劲了。
宗江是在建国前夕参加的部队文工团,在他面前是一个他不熟悉的全新的革命文艺工作,这使他总觉得自己甚差。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是虔诚的,并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他投身于抗美援朝前线到西藏深入生活,写出《农奴》,到新疆,到中印边境,到越南南方密林中,到硬骨头六连……,他相信"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他相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必须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所以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到各地深入生活,很少在家。小女儿是怎么长大的,他很少有记忆。好像经常念念不忘的,是有一次在东安市场给小女儿买了一份她最爱吃的奶油栗子粉,女儿失手掉在地上,脸一下子紧张了,他怕她伤心,马上又送上一份……仅此而已,虽然他对三个女儿是那么疼爱。
建国后的l7年,他虽然努力深入生活,但更多的时问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学习锻炼"。宗江的思想被束缚了,工农兵对他仍是陌生的对象,自身的改造又使他莫衷一是。建国初期与人合作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独立创作了《农奴》等,还算有成绩。大跃进中与现已故去的王云同志努力创作了《江山多娇》,之后写的《县委书记》、《硬骨头六连》就力不从心,不知所从了。l964年在越南南方他以真正的生活体验写出话剧《南方啊南方》,他认为是自己的代表作,而迎接他的是江青操纵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引发了对这株"大毒草"的批判。当时,我正在陕西三原参加"社教四清"运动,看了他的本子,以我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立即预感到这个本子有问题,为他捏了一把汗。这时我对宗江的艺术追求、艺术观点并不完全理解。
宗江在越南南方一年半的生活是很值得记忆的。在河内,他和新闻代表团受到胡志明主席的亲切接见,亲眼看到胡伯伯穿草鞋,住简陋的平房,十分简朴的生活,很受感动。行军穿越胡志明小路,到了越南南方。天气闷热潮湿,他和好几位同志得了疟疾。更奇特的是有一种蚂蟥,寄生到宗江的鼻子里,后因鼻子出血,才被发现。南方的军医,突然袭击地将它钳了出来,那蚂蟥已经长得像蚕那么大了,若再蹿下去,生命也难保了,这些都是他回国后才告诉我们的。在美国飞机疯狂轰炸中,宗江病卧吊床,坚持写作剧本。他见到了阮文追的妻子,密林中受到越南游击队对中国"同志加朋友"的热烈欢迎……本来应该是载誉归来,但迎接他们的却是"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刀枪,对人身的侵害和凌辱。
磨难中见真情
台风席卷,首当其冲的是文艺界。1966年6月,我被斥为"走资派",关到学院牛棚挨批斗。宗江在那个"座谈会"之后被开除了党籍、军籍,并被逐出北京,送往甘肃天水"劳动改造"。大女儿丹妮去了北大荒修地球,二女儿丹娣去西双版纳割橡胶,空荡荡的家只剩下八九岁的小女儿丹青。照顾她的保姆许阿姨作为"被剥削"对象,也被逼回家了。小女儿一人独立门户,接受厄运的考验,一个温暖、温馨的家,拆成5个地方。宗江和我有两三年音讯全无,我只痴痴地相信他能经受住考验挺过去,默默地为他祝福。直到有一年他们一群挨整对象"造反"回京。那时宗江犯了肺病,住进黑山扈的309医院,我几次请假去看他,我们才又得相见。不久,宗江再次被打成"反革命"送往山西"劳改"。这期间,我们的运动转入抓"五一六",对"走资派"放松一些,我就在部队小卖部买了两斤黑粗毛线,为宗江织毛衣。一个学生说"老阮是在织心呢!"确实,我默祷希望他将来能穿上这件毛衣。
一场浩劫冲垮一切等级、地位、荣誉、尊卑,以至国统区、解放区的文化人统统被打成30年代、17年文艺黑线人物,几乎无一漏网,除非那些丧尽天良爬上去的"新贵"。宗江说:"江青做了件好事,打碎了文艺界一切新老宗派,通通的'反革命',倒也团结了。"我和宗江之间,一切人为的、客观的差距,都被冲垮了,而我们的思想,达到完美的融合与一致,我们的理想和信仰,经过这一严峻的考验,逐渐从对偶像的崇拜中醒来。
1969年春,宗江和我都还分别在各自的"牛棚"。我的一位在南开大学的表妹说漏了嘴,造反派就来追查我们攻击江青的言论。我实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宗江可是竹筒倒豆子,把我们的枕边话,不分巨细地给她来了个22条,并涉及其他当时的各位首长、首脑。幸亏造反派怕自己背上"扩散"之罪,没敢交上去,否则我们两条小命早没了。我到现在还说不清我们都说了,骂了什么,宗江发表了一篇《坦白书》可考。我知道他这个人一向求真,但没想到能真到这种程度,生死不顾。他生性温和、调和,可到了节骨眼上,就什么都不论了。
世事难以预料,1970年林彪葬身于蒙古温都尔汗,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宗江他们得以解放回京。这时我仍在部队接受"审查"、"锻炼",宗江到玉田县4623部队来看我,当时的政委还通情达理,给我们一间房,还请宗江吃饭,把他灌醉。这是5年来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欢愉之情难尽。
金色晚年
"文化革命"的10年如一场噩梦般过去了,"四人帮"被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内开始了改革开放。在这一背景下,我于1979年秋平反落实政策,摘掉了l3年来强加于我的"走资派"、"反革命"的帽子,并从北京电影学院又调回中央戏剧学院,协助金山同志担任负责教学业务的副院长。宗江早已恢复了工作和党籍。80年代初,他5次出访美国,并日本、德国、法国……"文革"耗去了我们的壮年,此时我们年已花甲,身体尚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力拼搏。
1982年,金山同志逝世。我们以金山为首的领导班子,成为一个过渡的班子,牧虹同志暂为代院长。在这一时期,学院盖起了比较现代化的一座剧场,还有教师宿舍,演出了几部经典剧目,培养了若干位较有成就的演员,然而我个人工作并无大创意和进展。1986年初,我65岁正式离休,我的生活进入又一个新的阶段。工作了一辈子,一下子闲下来,我没有感到寂寞、失落,而是欣喜地开始了从童年、少年时代就向往的学习生活。我多么羡慕那些上过大学的同学,于是便开始自学,而且兴趣浓厚,越学越觉得学无止境,不觉老之已至。这一梦想的实现,还应归功于我的好丈夫宗江,在学识上他可说是我的老师,一开始他就为我安排了广播与电视的英语学习,从初级英语讲座、"维克多电视英语"、"走遍美国"电视英语,从陈琳、许国璋到申葆青,现在的蔡文美星期日英语讲座等等,他引导、鼓励、督促我自学。198卜1987年我随宗江赴美讲学,在那里又得到美国英语教师的辅导,回国后我居然翻译了一篇关于莎莉·邓波儿的生活报导,及美国黑人明星考斯比的小传,虽然翻译的磕磕巴巴,总是译出来了,前一篇还在电影报刊上发表了。直到现在,宗江还一直耐心的指导我自学英语,买了好多课本,订了《中国时报》、《英语电视报》,为我录制星期日英语,甚至他在广州拍片时,仍帮助我坚持电视英语学习。我一直坚持着,虽然学习进展很慢,特别是口语,听力差,记忆力也减退,只能阅读简单的书信、报纸,只是学习的意志不减。另外,宗江是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我补读了我青少年时代未能读到的或读而未解的西洋文学名著,如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些书籍有的在少年时代读过,但没有读懂,后来参加革命部队,就再也摸不到这些书了。现在重新阅读这些书籍,使我开阔了视野,对l9世纪文学作品中反映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得到认识、理解,这使我和宗江在哲学思想、世界观及文艺观方面,更得到深深的融合和一致。何况我们童年时,都是受过《寄小读者》、《爱的教育》、《苦儿流浪记》的熏陶,也从戏曲艺术中受到我国古典文学的熏染,如对高则诚、汤显祖、关汉卿等等。因此,当我们双双离休进入晚年,我们不仅在感情上,思想上,生活上融为一体。而且常常不用说就都想到一起了,我们的敏感和认识不用交流,而是默契。在美国圣地亚哥一年,回国后在广州、深圳、杭州,还有他的家乡温州,外出工作或旅游,无处不留下我们金色晚年的足迹及美好的记忆。宗江最不喜欢逛街、购物,可是愿意和我一起外出,在雨中漫步,过斑马线他总是拉着我的手怕撞了车。不论在家或外出,似乎我们每天都在度蜜月、蜜日。我们仍像年轻时的情侣,无比温馨,无比幸福……我们的感情是圣洁的,我不允许有任何玷污。宗江有许多女朋友,有的关系较近,我也有一般女同志的醋意,有时不太愉快。宗江倒是很规矩的,他从不越轨。只有一次遇到少时的旧情人他动了心,但很快我们都谅解了,再不提此事。我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圣洁的。宗江是一个很重情的人,他追求专一,白头偕老。
说宗江笨手笨脚,其实他对妻子,对女儿、女婿,对孙子无比细心,体贴。他操心太多了,对每个人的生日、假日,他都用心安排,甚至写出提纲。他不会做饭,但他抢着做别人顾不到的杂事。自己的衣物从不让我操心,不论出门还是在家,完全自己整理,可能这是过单身汉生活留下的习惯吧。每次他出门,关于饼干、糖果、茶叶、报纸、书刊、钱,一一交待都放在哪里,因为在家时,这些琐事都由他管,也费去他不少时间。他虽不会做饭,但他吃过,会当顾问。我是半路出家,70岁才掌勺,许多菜我还得请教他,他乐此不疲。对于钱,我俩都很糊涂,常常数不清多少,反正合在一起每个月都够用有余。宗江自己却很节俭,总是穿旧衣服,还拣女婿的衣服穿,不舍得买新衣,他说新的不舒服。尤其到了晚年,更不喜欢花钱,只对我,对两个孙子舍得花。大孙子男男还常笑姥爷"葛朗台",他不舍得扔东西,坐汽车买票,少一站可省5分,还要计算。但该用大钱的时候,他却毫不吝啬。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爷爷。
离休之后,宗江确实离而不休,他仍忙于写作,也替年轻人看剧本、看戏、参加座谈会。宗江的文章看来很随意,人家都以为他很不费力,所谓"大笔一挥"就写一篇。其实我知道他写一篇常常酝酿很久,很费思索,必须想透了。无论写剧本,写文章,他总是清晨三四点钟起来,如同作战一般冲刺。是吃早饭时就冲出来了,若冲不出来就等下一次灵感爆发。只要冲出来,他就会蛮得意的拿给我看,我是他的第一读者,而且负责描他的"天书"。宗江写的很苦,又很在乎灵感,这灵感是多年的积累和无时无地缜密的思考。
宗江从青年一直到老年都很用功,对时间爱惜如命,他不打牌,不跳舞,没有任何嗜好,闲时和孙儿们玩玩。他全部时间用来读书读报,为别人看稿,看电视,还要为我在电视报上划记号,如书法、绘画、可看的电视剧……等等,最主要的他还要为写作动脑筋。所以他很忙,老着急时间不够用,常说"来日无多"。大孙子说"夏伯阳要动脑筋了",就谁也不理了,小孙子接上说"老熊猫谢绝参观了"。的确,他无时无刻不在"动脑筋",惟"谢绝参观"难。
我的晚年已离开戏剧学院的专业,并从学院的旧居搬到八一电影厂宗江的宿舍。平时除自学英语外,经常写些回忆之类的文章。凤霞嫂说我应该出个《青衣集》,宗江努力为我收集我的文稿。但我没有用心写,也不会写,连初稿都找不到了,很辜负他们的好意。只这篇《我的良人》还是用了心写的。我作为一个老年主妇,相夫教孙,学学书法、绘画,很多事都靠宗江。我对录音、录像、开电视、听音响,所有电器的东西都不会开关,更别说电脑了。宗江常戏说"我死了你怎么办?"
我心地坦荡,三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了,无所牵挂。对当前社会虽有失望之处,但对未来仍充满了希望。惟一的心思是我们俩现在谁都离不开谁,谁先离开这个世界,谁先走了,另一个都受不了,怎么办呢?如果他先走了,我失去了老师、顾问,半个生活秘书,我将怎么生活?如果我先去了,他又怎么生活?我们相约活到下一个世纪,我们能一块进入另一个世界吗?……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