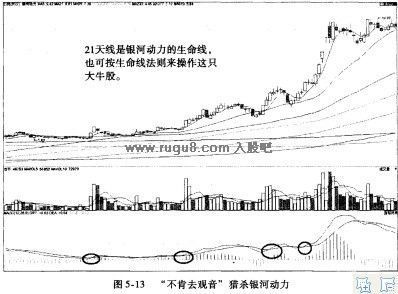然而,对于孤悬海中的昌国(今定海)梅岑山来说,咸通四年却极为不凡。在这一年,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慧锷,第三次选择从明州(今宁波)出发,回返故国。许是前两次返程都太过于平顺的缘故,本次行程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大异从前,波澜不断:先是慧锷从五台山请来的观音像,原本就他一个人背着的,临登船时却变得“重不可举”!好不容易由同行者帮助,装船成功,大家顺利起航,可船只刚驶至梅岑山附近,风云突变,平静的洋面遽然间“涛怒风飞”,暴雨骤至,而且,势头之大,连船主张友信特为此行打造的这艘坚舟,都颠簸冲击得如同空中飞扬的果壳!“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想来后世的这一名句,除了形容此时的暴风骤雨外,或许更能表达此刻人们的紧张心情。慧锷一行慌忙靠向梅岑山觅地避风,可由于风暴实在太大,梅岑山咫尺天涯,总不能靠近,而且,几次泊停,船只竟不免触礁有损,此情此景,“舟人惧甚”!费尽九牛二虎,历经七上八下,总算总算,一行人最终狼狈上岸,暂时得以安顿。是夜,慧锷于似梦非梦中,忽见一胡僧,告诉他说:“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惊醒之际,慧锷大哭,以梦告众,大家方才明白:原来是观音到此不肯去啊!于是,“敬置其像而去”。
这便是著名的“不肯去观音”的传说了,其最早始见于南宋宝庆二年(公元1226)的《宝庆四明志》——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的关系,该志书将此事发生的时间弄错成唐大中年间,提前了几年。这倒无关紧要,南宋志磐和尚于咸淳五年(公元1269)编写著名的佛教史学巨著《佛祖统纪》时,比此志书不过晚了43年,竟也将此事记录得与志书差上一年呢。关乎紧要的是,慧锷的“不肯去观音”传说,拉开了梅岑山由一个仙道胜地(此山秦有安期生、汉有梅子真、魏晋有葛洪均曾来此炼丹修仙,且,梅岑山之得名,即源自梅子真,意为“梅子真居住的小山”)向观音道场海天佛国普陀山的转变,是所谓“佛选名山”的肇始发端。故而,近代大家康有为曾登山赋诗曰:“观音过此不肯去,海上神山涌普陀。”这句名诗,极其到位,一笔点出:倘没有日僧慧锷的“不肯去观音”,孤悬海外的梅岑山,能否成为如今赫赫有名万众归心的普陀山,真的还很难说呢!
可是,如此意义非凡的“不肯去观音”,究竟是什么样貌?何种材质?许多人纷纷前来征询,惜乎材料匮乏,目前只能作一揣测而已。
根据孙昌武先生的研究,中国的观音信仰有一个长期复杂的演化过程:佛教初传到六朝,流行的是以《普门品》为代表的化身无数的救苦观音,故而关于观音的多种灵验记便于此时不断涌出;六朝后期到唐初,中国净土信仰盛行,所以负责接引往生西方的净土观音就广受瞩目,造像极多;而从盛唐到北宋,密宗佛教在皇室与高僧的推动提倡下,于中国大行其道,则此时的观音像,就以多手多面的密教风格于世称雄;至于南宋以后的观音信仰,自然是伴随着妙善观音传说和各种民间宝卷的不断渲染,一路直下,迅速道教化、俗神化,而他们所塑造的圣母娘娘南海观世音,当然就是信众们万口称念的标准形像了。
慧锷三次入唐,时间均是晚唐之际,理论上他所请的“不肯去观音”应该是密教形像。然从唐之前杂密时期著名的十一面观音——梁武帝的国师宝志据传便是其化身,到入唐后纯密时期的不空羂索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马头观音、千手观音……密教观音是千奇百怪层出不穷,到底哪一种观音形像最有可能为慧锷所请呢?这里就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了。
首先是慧锷请像的地点,是在五台山。慧锷三次入唐,三上五台山,这绝非偶然。作为佛教名山,五台山早在北魏时就已经非常有名了——相形之下的普陀山,却是在宋代定名,明代才出名,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即使南宋的皇帝们对普陀山恩渥有加,时常封赠,但彼时的观音信仰中心,却是固定在杭州的上天竺!五台山则不然。入唐以后,由于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有天下的,故而太原府辖下的五台山,自始至终都被李唐一朝看作是自家的“龙兴之地”、“祖宗植德之所”,历代皇帝建寺度僧,供养无算。原本其在北魏出名,那还不过是传说文殊菩萨在此,而到唐景龙四年(公元710)菩提流志翻译《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以及武则天的老师法藏大师撰写《华严经探玄记》,则是干干脆脆地直接点明,文殊菩萨住持的清凉山就“是代州五台山也”,(代州即现在的忻州)把五台山的文殊道场之名坐实了!发展到中唐,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灌顶国师”、官封肃国公的不空大师,更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上书代宗皇帝,奏请天下寺院都建文殊阁、各地寺院食堂都供文殊,借助行政的力量,把五台山的文殊信仰迅速推广到全国了……咳咳,说这些与“不肯去观音”有关系么?
当然有,而且关系大极了!因为也就是这位不空国师,作为唐代密宗佛教的实际创立者,他与其师善无畏、金刚智三人,共同把中土密教观音的信仰崇拜,着实推向了一个新时代!据国内观音研究大家李利安教授的统计,唐宋时期从印度传入我国的密教观音经典共有108种,其中译自唐代的74部,而74部当中,仅不空一人就译有32部,倘再加上两位老师翻译的13部,那么,只此三人,就译出密教观音经典达45部之多!而且,尤为应当注意的是,45部密教观音经典中,此三位大师不约而同地都译有关于千手观音的经文,均推重千手观音的信仰。这是何故?想来应该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前有先导。武周时来中国传法的菩提流志法师,早就注重了千手观音类经典的翻译与弘传,且因为其在所译的《宝雨经》当中,巧妙增加了为武氏易唐为周摇旗呐喊的内容,深受赏识,武则天甚至还激动地给他改名了——菩提流志本来叫达摩流支!而正是这位后来的女皇,曾令宫女绣成千手观音像,“或使匠人画出,流布天下,不坠灵姿。”二是像有总结。日本学者中村元,在他的名作《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曾指出:唐代密教东传给观音信仰带来重大变化,突出表现是观音信仰的复杂化,而复杂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各种不同名称的观音相互混合!由此可见,唐代的观音信奉者,实际上是分不清楚密教观音像的各种名头的。所以,千手观音的出现,实为所有密教观音的集大成者——密教观音的特点就是多手多面!故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观音研究专家于君方认为,在传入中国的密教观音像中,千手观音虽然出现相对较晚,但在前后几位密教大师的合力提倡下,加上朝廷的护持,最终后来居上,集其他密教观音像的盛名于一身。因此,从唐王朝与五台山的密切关系,以及千手观音的流行盛况来推论,慧锷的“不肯去观音”应该是千手观音像。
再一个需要考虑的,是慧锷入唐的时间。慧锷三次入唐,均是在武宗会昌元年到懿宗咸通四年的22年内。虽然唐武宗会昌五年灭佛,使佛教大伤,唐密消亡——其实是被不空的徒弟惠果传给空海,带到日本去了,是为“东密”,至于现在的藏密,是直承印度晚期密教而来,与唐密并无直接关系。但五台山作为李唐的“龙兴之地”,在会昌六年武宗暴亡后,经由出过家的宣宗大力扶植,迅速又得以复兴。过去五台山供奉千手观音,是因为他与文殊一样,被密教大师们强调了护国佑民的政治色彩,现在复兴,应该情形也差不许多。况且,宣宗朝的宰相,是著名的佛教居士裴休——也就是送子出家成为法海和尚的那位——他还有一姑娘,据说曾被鬼缠身,后为当时的神智大师通过诵持大悲咒所救,引发极大轰动。此事为《宋高僧传》所载,时间在公元847到859之间,正是慧锷第三次入唐的前几年。而与宣宗、懿宗交好,并被后面的僖宗封为“悟达国师”的知玄,早年入帝京,也有因诵念大悲咒而改乡音为国语的神奇经历……此类事件很多,这说明晚唐的千手观音信仰还是很盛行的——大悲咒就是千手观音的根本咒,故千手观音又名大悲观音。查验下学术界的材料,果然,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有篇专门研究唐代大悲信仰的论文,内中表明,唐末五代正是大悲信仰的“黄金时代”!所以,从时间节点及时代背景来看,“不肯去观音”恐怕还真的就是千手观音。
那么,这尊“不肯去观音”又应该是什么材质的呢?
早期的资料都没说,晚期的如元代之《佛祖历代通载》和《释氏稽古略》,倒是明确说是“画像”,不知何据,徒令方家所笑。个人以为,确定“不肯去观音”的材质,还是要从最早记载此事的宋代材料入手,宋代的记载,虽蛛丝马迹,却亦有章可寻。如《宝庆四明志》,内中说,观音像是慧锷一人于五台山背到宁波的,并且,是在放置一段时间后,临登船时才被发现变得“重不可举”,倘不考虑个中神异,那么,此点,唯有吸湿性较强的木质,方能如此。而《佛祖统纪》引用北宋道因法师的《草庵录》说,其实真正的“不肯去观音”,早被宁波人请到市内的开元寺供奉去了,普陀山所供的“不肯去观音”,是有人以“嘉木”“仿其制刻之”,后迎上山的。如此,若以古人保持圣像的完整性、一贯性来逆推论,“不肯去观音”是木质的可能性,更是极大。
然而,电影《不肯去观音》中,却把此像材质定为秘色瓷——也就是秘密配方的青瓷,不知是何种考虑。历史来看,秘色瓷作为越窑出产的皇家专用瓷,在晚唐五代确实十分流行,而且,其现存的代表作,便是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瓶碗盘碟——出土资料表明,这些秘色瓷,就是当时的皇帝唐懿宗敬供,且,时间恰好在咸通年间——咸通十五年(公元874),法门寺地宫完全封闭再未开启——这与慧锷第三次入唐时间极为吻合,或许,正是因为这个时间上的重叠,才给了电影创作者灵感的激发吧。
但,硬伤显而易见,秘色瓷名气虽大,却只有小件器皿,没有大型塑像。“不肯去观音”其实不可能是瓷质的。元代出使日本的普济寺方丈一山禅师,到日本后做了天皇的国师,并开创了著名的“五山文学”中的“一山派”。他培养了一个日本好徒弟叫虎关师练,写下了该国第一本佛教史著作《元享释书》,地位特别显赫。此书记“不肯去观音”的传说,有个细节不同以往所载,说慧锷他们触礁搁浅后,船不能行,“舟人思载物重,屡上诸物,船著如元,及像出舶能泛……”船搁浅了要丢弃重物,这是习见之理,观音像搬出舱了,船才能开,如此可见,这像,竟是连小型的瓷像也不太可能了,恐怕只能是木像!
说这个虎关师练呢,其实他还有些个不同也颇为耐人寻味。前人记叙“不肯去观音”,均大谈宝像显灵、祷告有应的灵异,独虎关师练统统删除,毫不保留。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倘是观音有感,不肯去日本,这岂不是让日本蒙羞,极为不美?更何况,在慧锷之前,东渡的鉴真大师已经带去观音像了,今天又何需你“不肯去”!再说,既然中国人以慧锷为普陀山的开山始祖,那么,我这《元享释书》就再加点料儿吧——书中直接让慧锷留在普陀山,“结庐海峤以奉像,渐成宝坊,号补陀洛山寺”,就没回日本。怎么样?这一招,够绝!
可是,如此一来,日本人开心了,韩国人却不美了。有韩国学者曾撰文说:记载普陀山“不肯去观音”的最早史料,其实是比《宝庆四明志》还要早上102年的北宋徐兢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本书是实地见闻录,应该比他书可信,然而,此书中却说——留“不肯去观音”的是“新罗贾人”,而且,山上早有僧人,所谓普陀山开山始祖云云,根本就没慧锷的事儿!呵呵,这个比虎关师练更绝!
我们中国人不参与日韩争端,只谈自家的事吧。回头说咸通四年,交州陷落,在当时影响虽小,可后来引发的结果却极大,因为直到公元875,即法门寺地宫关闭的第二年,大唐才驱逐南诏,收回交州,而此时,正是懿宗死后的第三年、黄巢起义的第二年……正像公元880年,唐宰相卢携总结南诏战事所表明的,其实自咸通始,唐王朝就已经开始风雨飘摇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