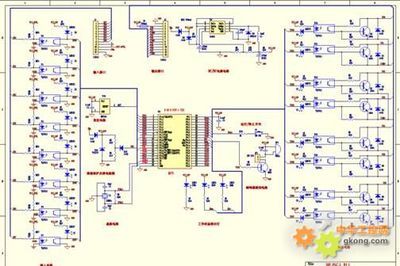我说的不是洗澡。
我说的还是入台初感觉。
乍到一地,总要忐忑一阵,彷徨一阵,凄凉一阵。面对无边的陌生,人像可怜巴巴的外地小孩,躲在一隅,孤独地测度着、观望着这个世界的热闹。总要一、两天,人才能渐渐进入、慢慢融入。可是,人到台湾,这些感觉却没有,或者这些感觉还没来得及开始,就被接连遇到的温暖代替和消融了。
巴士票口的温暖。
下了飞机,想搭计程车去我所住的西门町桔子酒店。一问,要一千五百块台币。我还没弄明白台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比率,一听到“千”了,便作了罢。心想,这台湾的出租车也高得太吓人了吧。虽然百般不愿去坐转来转去的地铁巴士公车之类,但还是找去了巴士窗口。
“我要去西门町,请问我坐哪班车?”
那女售票员就像早在等着我似地,给我出了票,又如此这般地详细告诉了一番。看我认真听讲却满脸懵懂,便笑笑,拿起笔在票是写道:请第一饭店下车,转搭计程车(大约100块台币)到西门町您所预订酒店。我接过票,说,谢谢您!她竟回说“谢谢我”!
看惯了咱家服务窗口的冷脸、木脸和没脸,对于这种温如春风、暖如细雨的周到,除了感动感叹,还有点小小的不习惯。就是说,人一旦被煅炼成钢铁了,再享受柔软竟也会不习惯。
计程车的温暖。
下了巴士,见一辆计程车在一边,还没等我拖着行李走过去,司机就下来了,过来帮我提箱子,也像是在专门等我的。上了车,我说了酒店的名字。司机说台北的酒店有一千多家,连锁店也很多,最好有个具体的地址。可我说不出具体,也没有电话。我正想电话问嘉华。司机却说你别管,我来问。他不知问的是谁,反正,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们很快就到了桔子酒店。到了后,并没见酒店的招牌。他说你先别下车,我下去问问,就跑下车了。跑出门时,小孩一样欢欣地指着酒店那个小小不起眼、中间镶有一只桔子的英文标牌:FORTE0RANGEHOTEL,说,哈哈,这不是吗?福泰桔子酒店,我们都没看见。我也笑起来。我是被他孩子气的高兴逗高兴的。
台客先生的温暖。
酒店有点小贵,但很舒适很干净。放下行李,洗了个澡。正擦着头发呢,忽听房间的电话响了,以为是服务员呢,却是台客先生,也不顾礼不礼貌,即惊问:您怎么知道我住在桔子?
他呵呵一笑,说天涯把你的行程发给了我啊,一查就能查到的,呵呵呵——

这个爱操心、爱管闲事的天涯!
台客先生接着说,正好你们西南大学的R教授也在这儿,我明天要陪他去《文讯》杂志社查些资料,就一起吧。你先好好休息,明天八点半我去酒店接你。
台客先生是天涯多年的诗友,《葡萄园》诗刊杂志主编,正宗台湾人。平日与天涯并无多少来往,与我这个朋友的朋友更是素昧平生,隔了厚厚一层,不好一来就麻烦人的。但台客先生的语气之理所当然,让我说不出一句推辞的话来,只好称是称谢。
第二天八半点,台客和一位有点驼背的老先生如约敲响了我的房门。
驼背先生也是诗人,笔名:傅予。
两位诗人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先生了。
闲话了几句,台客先生拿出一本自已的诗集《续行的脚印》,签了名,送了我。又拿出一包凤梨酥,说是他家乡莺歌的特产,还有一只小塑料袋,内有红、黄、绿三只水果,红的是苹果,绿的是桔柑,黄的是平柿——里边还有一只红色的简易削皮器。
台客先生说,没有来得及去买,出门时从家里带了现有的几只。女孩子出门,都喜欢吃水果。
正是“从家里带的”,正是一只小小的削皮器,正是这种经意经心又自然而然的人情味,让年过半百的“女孩子”心头一阵热浪滚过:谢谢——这一声谢,与客套无关。
送上拙作《带你回家》,我自己却有了回家的感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