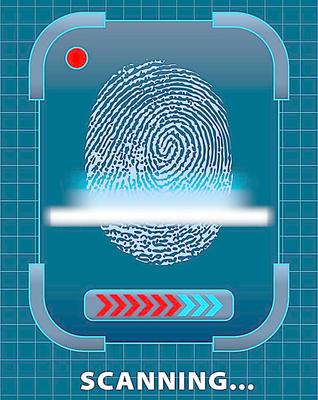今天跟诸位相见,我非常荣幸。也不知从哪里讲起,就从我那部小说(「上海往事」说起)吧。
我是祖祖辈辈的上海人,要查祖宗十八代可能也可以查到一直是上海人。怎么会写上海三部曲的呢?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王安忆写过一部小说叫「长恨歌」。「长恨歌」后来被海外东亚系从台湾来的一些教授捧得很高,在大陆又拍了电影电视剧。所有的舆论,各方面都认为,这就是上海了,过去的上海就是这样的,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就是上海。我跟王安忆也算是比较熟的,以前在上海的时候,经常一起开会,彼此关系也蛮好,可以说是蛮客气的。但我看了「长恨歌」以后,很不认同。因为,王安忆严格来讲不是上海人,尽管她祖籍是浙江的,好像是杭州,她母亲是那里的人,但严格来讲他们跟上海没什么关系的,他们是新四军一系,她父母是跟着新四军一起进城的。她母亲茹志娟当时是上海作协主席,现在王安忆又连任了--上海作协主席也是家传的,呵呵--她所写的上海跟我听到的我所经历的上海,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当时就觉得我也应该写写上海,并且有了个模糊的想法。有一次台湾出我的书,我去开新闻发布会,开完之后出版社的主编带我去九汾玩,坐在九汾半山腰上的一个饭店里吃饭。我看着大海,突然冒出一句:看来我要写一部小说,关于上海的,我想把我的经历,我的家族史和上海的故事整合在一起。那个总编听了特别高兴,说太好了,有人写过东京人,有人写过什么什么人,就没人写过上海人,你来写太好了,你来写我来帮你做,是这么讲起来的。
后来我满脑子的不能对他食言,记着那个承诺,在这样的动力下开始动笔,一写就写了三部。
第一部「上海往事」讲的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一直讲到四九年。第二部,是我自己的经历,8*8和美国的流亡,叫"星河流转"。我本来要写的第三部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那些故事实在太惨痛,而我觉得悲剧写多了以后觉得很累,最后就没有写。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突然想起了农场的事情,第三部就改作了在农场当知青的故事,本来叫"被遗忘的岁月"。但是在台湾出版的时候,主编说台湾对这些故事没什么感觉的,你索性换个名字,他硬给我换成了"毛时代"--台湾人就知道什么"毛时代","蒋时代",这样,出了第三部「毛时代」。
上海往事出版的时候是非常隆重的。当时的中国时报副刊,周末破天荒地两版整版连载我那篇关于「上海往事」的文章。这里面提到民国的一些人物--像章太炎啊,杜月笙啊,对有民国记忆的读者来说,是很有阅读兴趣的。
我今天想着重讲的不是后面两部--因为关于8*8流亡和上山下乡的事情是另外的话题--我想着重讲的是第一部,就是三、四十年代的上海。
我这部小说的核心人物确实是我家族的祖辈,还有一个核心人物是杜月笙,在这部小说里我当然换了一个名字,叫申常德,申先生。
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对我的家族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我是写完以后才知道。我们家是从来不谈以前的事情的。我们家在四九年之前遭了一次抢劫,一抢就抢成了穷人。这情形和「活着」很像,但「活着」是赌博赌成了穷人,我们家里是遭抢。家道中落以后,我的父辈到上海的工厂里面开始做学徒,那时候他们叫做学生意,这一来就改成工人阶级了。改成工人阶级以后,工人阶级的时代,他们从来不愿意谈以前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我是从我祖父那里略知一些的,我祖父也从来不讲。我祖父是四九年国民党失守上海时跑掉的。跟杜月笙一样,他跑到香港,在香港一直待到我出生那一年,五五年的时候回来。回来的时候重新登记,这时候风头过了,回来变成了爱国行为,所以一直没事,文革的时候才被揪出来。
我小时候有一个什么记忆呢?就是他经常领着我到复兴路老西门那一带去串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到处串门。有时候找不到他要找的人,有时候找到了以后呢,那些人说话都是小声得一塌糊涂,就好像老鼠一样,当时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些人活在一种非常巨大的恐惧里面。我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实祖父也从来没有给我讲过是怎么回事。我后来才明白过来,就是,他要找的人,全都消灭了。就是说,他要是当年不走的话,那也已经没有了,肯定没有了。后来我才听说,上海刚刚打下来以后,那个时候镇反嘛,一卡车一卡车地拉出去枪毙。没有任何审判,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所以那些人全部杀光的,就是说肉体消灭的。那些景象在我的小说里有所描述,在小说后面部分。我的小说讲说了过去的上海是怎么消失的--以肉体消灭的方式消失的。像我祖父这样的人呵,即便活在毛时代,他的脑筋也根本洗不过来的,他讲的那些话永远是民国年代的话,他不会讲新时代的话。我当时很担惊受怕,因为生怕他讲那些话很反动,但好在生活在工人新村这样的环境里,大家的神经不是很敏感,所以他总是没事,当然文革的时候他逃不过。这是我祖父的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杜月笙。我以前关于杜月笙的印象就是上海三大流氓之一: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后来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接触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文字。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杜月笙的传记啊,旧上海的介绍啊等等这些,我一接触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然这是一个longstory,这里不多讲。我对杜月笙的评价,写在「上海往事」的那篇跋里面,就是在中国时报副刊上连载的那篇。
杜月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简单讲来就是,中国进入了所谓现代化,我用最最俗的这个词,就是从1840年以后,西方的文化,通过文明的战争的方式,物质碰撞的方式,迫使中国开始进化的时候,迫使中国政治开始慢慢向西方文明靠拢的时候(当然还没有融合为一),产生过一些--我称之为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的人物--这可能得列一张名单出来。其中我觉得最突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曾国藩。曾国藩我专门有过论述,在我的大陆出版的五卷本文集里,专门有一章论述他。还有一个是杜月笙。说起来这两个人好像完全不相干。
曾国藩是典型的一个儒家重臣,怀有修齐治平之志,他是近代洋务运动的一个核心人物。可以说中国假如有过现代政治家,可能他可以排上第一号。曾国藩做的事情是非常具有现代意识的,但是他的文字毫无这个意识,无论是他写的一些奏折家书,还是什么其他的,你根本看不到有什么现代意识,其文字和行为反差很大,非常滑稽。曾国藩讲出来的话全部是儒家那套话。所以蒋介石后来学曾国藩是无从学起的,因为蒋介石不懂里面的奥妙。曾国藩的精彩不是精彩在他的文字里,是精彩在他的事功上。
有一次李鸿章请教他如何跟洋人打交道,曾国藩问他你是怎么打交道的。李鸿章说我跟他们打痞子腔,曾国藩说,错了,你不能这样,我们跟洋人打交道要以诚待人,然后就跟他讲了一番道理。曾国藩很有现代政治意识,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意识。曾国藩知道的是,凡事要给对手留余地,不搞你死我活,这是他的政治方式的核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政治一直是你死我活的政治。而且他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走这种传统的政治道路。在打下天京后,他拒绝北上称帝。因为当时剿平太平天国以后,他如日中天,而且具有最强的军事实力,手下又网罗那么多的一批人,有这样一些人才。不管他的人才是什么人才,比清廷那肯定要精彩多了。而且当时清朝是满族人的异族王朝,曾国藩只要打出驱逐鞑虏的旗号,肯定是一呼百应的,总之,他拥有各种北上称王、称帝的条件,但他拒绝那么做。他说了两句话,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山高心自知。当时理解他这种行为的人是很少的,尤其是他弟弟曾国荃是绝对不理解的,因为曾国荃是直接领兵打到南京的人,然后就想着要打到北京去。这种政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我觉得是没有过的。但是关于他这种意识,这种政治行为,没有人用文字来阐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意识,是怎么样的政治方式,没有人阐述过,他自己呢也讲不清楚。曾国藩他的这种政治方式,假如后来,清末民初以后那些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能够学到一半,中国的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的这套东西,没有让那些政治人物所承继,相反,在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身上体现了出来,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的行事做人,是自发的,全然出自天性。他是没有读过任何书,是标准的草根出身的人,过去是卖水果的。他的看家本领就是削梨,削梨的本事非常高明。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行事做人居然跟曾国藩一模一样,也是从来都是留有余地的方式。他在黑道上出道的时候,行事作人就是这么做的。他出道比黄金荣晚,当时是投在黄金荣门下,但是他后来远远超过黄金荣。
他当时在中国的声望,蒋介石都受不了。因为当时二战结束以后,他应该是名正言顺的上海市长,他的朋友戴笠还为此私下跟他讲过,上海市长是非你莫属的,但蒋介石在这方面心胸非常狭窄,死活就不让他做。因为他隐隐地感觉到,杜月笙是比他强多了。当时民国那些风云人物,没有一个人不对他表示佩服。而且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草莽人物,非常风雅的人物,都非常佩服他。那么,为什么很佩服他?不是说他是教父这样的角色扮演得好,而是他的政治方式,是一种非常让人心服口服的方式。
其实从蒋介石来说,他理应让杜月笙做大,但是这个人的心胸实在是太狭窄了。杜月笙帮过他很大忙的,第一个大忙就是二七年,杜月笙帮他搞定了上海的共产党,这个是立大功的,然后抗日杜月笙又帮他立了大功(听众:帮共产党立了大功)...那是后来,这就是杜月笙和蒋的另一方面的不一样,他不搞黑白分明的,不是好像我跟你蒋是哥们,就跟另外一方面一定是敌人,他没有这个观念,这是杜月笙了不起的地方。抗日一开始他就不分国共了。杜月笙是在日本人进来以后他开始支持共产党,他在这方面,不懂共产党的黑,新四军没有和日本人好好打过仗,新四军打得全部是同胞,他们叫做顽军,其实就是国军--当然这个故事在「沙家浜」里是反过来写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杜月笙的政治方式,共产党是不会接受的,蒋介石也不接受。蒋介石假如说有杜月笙的头脑,那么中国早就可以开始两党制。日本人打跑以后,中国是最有机会做两党制的时候。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实力强到敢跟蒋介石决一死战的程度,毛当时假如能够到联合政府混一个总理当当,他会很高兴。就好像赌徒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全赢,能够赢一半他们已经很满足了。蒋呢因为抗战胜利,所有的功劳全都记在他的头上,他又是红得发紫如日中天的时候,威望很高的时候。他假如走这个道路的话,不说别的,英美肯定支持他的。所以从各个原因来讲,中国错失的最好的一次两党制机会,就是在蒋手里。蒋根本没有这个sense,根本没有这个头脑。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怀念蒋介石,吹捧蒋介石,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所以,我的「枭雄与士林」(台湾出版叫「百年风雨」)里面,有关于对蒋、对汪、对毛的论述,是不带偏见的。蒋是一个没有现代文明这种sense的人,而这种sense杜月笙是有的。蒋在抗战胜利以后他不仅不让杜月笙当上海市长,而且想方设法地排挤他打击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假如我的思考到此为止,还不能构成「上海往事」这部小说给我的这种文化感。更深的东西是另外一个问题:杜月笙有这个sense,而当时很多饱读诗书的人,很多在政治上叱咤风云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这种sense?这种sense自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更有意思。因为,杜月笙没有留过学,西方文明根本不知道,什么托克维尔,什么孟德斯鸠,他哪里知道这些名字啊,为什么他本能地有这样一种现代政治和现代文明意识?这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我今天很想谈的是这个问题,而不是什么"海派""京派"这些问题。用"海派""京派"来谈杜月笙,太不着边际了。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有地域特征的。比如非功利的审美文化,比较集中在江南,诸如王国维,徐志摩,还有与杜月笙齐名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邵洵美。这些人物身上有审美能力,或者说有非功利的纯粹文化的能力。相对来说,北方跟这个情况就有点不一样。尤其是经常做王朝首都的地方,这种sense是阙如的。这种sense比较浓的是在南方。上海开埠比较早,跟西方文化接触也比较早,有着殖民地文化的根基。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文化的承传。假如用西方文明对上海的影响来解释杜月笙的现代政治意识,似乎还有逻辑可循。但倘若要从中国文化的承传上去寻找,就不太容易了。但是我觉得杜月笙身上的很多东西,恰恰是跟中国文化的承传,非常有关系。因为他当时跟邵洵美两个人,都各有一个外号。邵洵美被称作海上孟尝君,杜月笙被称作海上春申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当时民国年代的人会把春秋战国这两个人物跟邵和杜联系到一起?跟邵洵美联系到一起,还有承传可言,因为邵洵美出自望族。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夫人,都有望族背景,说起来是一脉的贵族承传。但是讲到杜月笙身上,似乎就讲不通了,因为杜月笙没有望族背景,极其草根,很难说得通为什么这样一个草根出身的杜月笙会具有春申君的气度。
杜月笙对章太炎特别崇拜。虽然他不知道章太炎的学问是怎么回事。崇拜到什么程度呢?崇拜到把章太炎感动的程度,因此章太炎为杜家祠堂专门写了一篇文字。章太炎是多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他晚年在苏州讲学的时候,蒋介石将五万大洋送到他府上,他理都不理,因为蒋介石跟陶成章的死有关系,而陶成章是章太炎的朋友。那么心高气傲的章太炎,会给杜月笙写杜家祠堂记,而且把杜月笙的家世一直考证到上古,好像是西周时代,这简直是破天荒的。这不是夸张。好像杨度也对杜月笙也有过相类的评价,还有民国最有名的写赋大家饶汉祥,写过一个对子,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把他比作古代的贵族。这些人都绝对不是随便讲的。这些人本身都非常有根底的文化人。这个承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后来就想到一个缘故,可能可以做为一个猜想来说,但是没法像西学那样做量化的求证。
文化的承传和文明的承传,有一个区别,文明的承传是递进的,线索非常清楚,比如从青铜器到铁器到蒸汽机...,一步步的承传,有物的根据,有物证的。文化的承传是找不到物证的,或者说物证是次要的,它是一种在生命里发生的事情,通过生命的密码来承传。把杜月笙比作春申君是一点不夸张的,而且我觉得杜月笙在政治智慧上还超过了春申君。因为春申君的贵族气是有的,但是后来是被一个小人李园给暗算了,这个在杜月笙那里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杜月笙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比春申君要高多了,但是彼此的气度是一模一样的。杜月笙虽然手里经过的钱像流水一样,但临死的时候只有一两万美元,没有多少钱的。而且无独有偶,章太炎的好友陶成章也是这样一个人。当年陶成章他们闹革命的时候,收到的捐款极多。陶成章去章太炎家里做客,穿着露口的鞋子,章太炎的孩子不知就里,就嘲笑他,穿的鞋子怎么这么破,章太炎马上板起脸训斥他们,责怪他们根本不懂陶成章是何等人物:几百万大洋过手,分文不动。所以那时候那些人的这种气度,可能现在人是没有了。这种品质,从古代的春申君到杜月笙一路承传下来,无案可稽,没有文字可以追寻的,只能用生命密码这样一个说法来解释。
上海本地人也有这样的秉性。有一次很偶然读蒋勋的一本书,手帖,他在考证中国书法的时候,讲到陆逊家族。当时上海这个地方原来叫做华亭,陆逊家族就是华亭的望族,属于当时的江东士族。我发现由于三国演义的坏影响和误导,对江东士族非常贬抑。蒋勋无意之间触及到这个话题,他就讲到陆家承传,从陆逊到陆机,包括他们还出过一个书法家,好像叫陆云,蒋勋还特别把他的字拿出来,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蒋勋还讲到这些人的脾性,这好像世说新语里也没有提到过,三国志里也没有看到过。陆家的人作为南方士族,碰到一些北方的豪门人物,见对方很摆谱,陆氏很不买账,然后有一番对话。我看了就不由大笑,因为那番话好像我讲的一样,彼此在脾性上非常相像。后来我看到有关上海史的介绍,里面特别提到,上海的大姓就是陆姓,陆家的后裔就是上海本地人。当然我不想从家族的渊源上来寻找线索,因为我认为这种承传是无迹可寻的,是通过生命密码延续的。就好比一种幽灵,不知什么时候就在哪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了。以前有一部英国电影,叫鬼魂西行,就是说有一个英国城堡搬到美国来,结果这个鬼魂也跟着城堡一起过来了。生命密码的承传与鬼魂西行的故事很相像,文化以密码的方式像鬼魂一样承传下来了。在我的上一辈长辈里面,他们都没有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但是天生有这种气度。我曾经感到非常奇怪,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官宦世家,我父母也不是什么很了不得的大人物,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就觉得很奇怪,你这个人怎么会有这种贵族气,你这种贵族气是从哪里来的。我后来才明白过来,文化的承传里面,是有生命密码在起作用的,这样的密码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文品质。
我为什么对王安忆的小说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其实我对她这个人一点不反感。王安忆不是一个很夸张的人,行事做人中规中矩,你不会很喜欢,也不会很讨厌。但是我对她的「长恨歌」很反感。因为她这部小说跟上海人,太不相干了。你们去读我的「上海往事」就会知道,上海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上海本地人,好像天然就有这样一种贵族气,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祖母过世的时候,做丧事是摆流水席的,所谓流水席是什么?在场地上摆开一张张桌子,什么人都可以坐上去,坐满一桌就开宴。我在看史料的时候,杜月笙过生日的时候,那个排场之大,出手之阔绰,全然是战国四公子的派头。我后来到宁波人家做客吃饭就很难受。宁波人喜欢用很小的碟子,放一点点小菜,还使劲叫别人吃啊吃,没有人敢吃,筷子一动就没有了。但是本地人摆宴席就怕被人家说小气,都是大碗大盘的上菜,叫做摆流水席,一摆就摆三天。本地人当中特别看重什么呢?过去人家误读叫面子,其实是尊严,本地人特别看重尊严。本地人的性格特征是,你伤我钱财骗我钱财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是伤我尊严,那是绝对不会放你过门的。
杜月笙身上就体现了这种本地人性格,不怕破财,抗日的时候,他毁家纾难,但你要伤他尊严他绝不客气。这种性格绝对不是什么民国性格,而就是先秦性格。先秦的时候,华夏人就有这个性格。比如伍子胥逃难的时候,碰到一个村夫,一个船夫,就因为一句话,我是被通缉的,你不要告诉别人,就这么一句话,村妇当场就把菜刀横过来抹脖子,船夫就把船摇到江心自沉,把自己翻到船底。这是先秦时代的人文品质。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承传。这不是什么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区别,根本不相干。我在上海往事里面,写到后来,不仅仅是一个家族史,也不仅仅是一个上海史,就像我的一个朋友高尔泰讲的,家族史上海史和整个的民族历史,全部混在一起了。
刚才有人问我,怎样理解人文精神?「上海往事」所讲的故事里,就有人文精神的兴衰在其中。但假如用人文精神来概括,那肯定是不到位的,更不用说用「精神文明」这样的词来讲说,简直荒唐了。「上海往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悼亡,悼念那些被消灭的上海人,那些人的音容笑貌,那些人的行为方式。因为我从我的父辈从我的祖父那里是可以感受到这些东西的。而且非常有意思,我在崇明农场上山下乡的时候,发现来自上海市区不同区域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从南市区来的知青,带有民国年代的上海气息。虽然他们这些人都是些混混,我跟他们互相瞧不起。我瞧不起他们不读书,整天瞎混,他们瞧不起我读马列。那个时候在中国流行学马列,知青的有文化通常以谈马列来表现。但从南市区来的那些知青,从来不谈马列,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马列,他们整天讲的是民国年代的故事,尤其是沪剧,申曲,筱文滨之类,总之都是上海滩上的一些老戏,老派的明星,他们对民国时代的许多轶事滚瓜烂熟,这样的人在上海并不少见。
文革当中上海枪毙过一个人,叫人民大道一只鼎,那个人姓姚,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怎样一个人,后来我在美国碰到当年上海的造反司令潘国平,告诉了我那个死刑案的真相:那个被枪毙的人叫姚守忠,这个案子根本就是个冤案,姚守忠被抓的原因是喜欢聊天。他呢经常拿一把椅子坐在人民广场,天南地北,讲民国往事。周围围着一大帮年轻的听众。简单讲他们就是民国脑子,洗脑洗不过来的,姚的言论没有什么攻击共产党的,被抓后判了五年,因为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后来是姚文元说,这种人怎能不杀?然后就枪毙了。你们不要看姚文元被审判时那副可怜相,手上也是沾过血的。要说姚守忠真的犯过什么罪呢?也许是文化罪。因为他还活在民国年代。我们民国时的上海,是怎样被抹去的?除了在文字上被抹去,还有就是,肉体消灭。但从另一方面说,文化承传其实又是消灭不了的。这就是我在「上海往事」里面想写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寻找上海最本真的文化真相,也就是文化密码是如何承传的。老上海人被消灭了,文化的密码照样会被承传。
有关北京文人的那篇文章,是我文学备忘录里面的第九章,文学备忘录的缘起我在答凤凰网的采访时讲过了,跟海外跟大陆一些学府混混的嚣张有关,那些人编当代文论的时候把八十年代一些敏感人物全部删掉,导致了一些人的反弹,要我站出来说话,我就写了那部文学备忘录,并且着重写了北京和上海的作家。有关上海的这一篇被很多人在网上转载过。北京和上海的对比是非常鲜明的,我讲的诸如杜月笙邵洵美这样的人物,在北京是不可能有的。邵洵美是上海滩上最大的出版家,不要说当年上海滩的各种文人,就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都是他最早出版的,但是邵洵美后来完全被大陆官方的文学史抹掉了,好像从没有存在过一样。那还算是个比较有名望的人物,不太有名的大概都被肉体消灭了。北京文人的特色是皇权意识很浓重,哪怕做皇帝身边的奴才也很荣耀,这种心态在北京的文化人当中很普遍,包括「今天」里面的朦胧诗人。因为都写在那篇文章里,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二0一四年七月十九日演讲于芝加哥近郊友人客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