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把脉络轻轻改写,试管里萃取出的青葱色泽,在漫长的消耗里退成苍白与灰蒙。
旭日暖阳是你凝望的眼。
与荒芜对峙,与时间对峙,与锋利对峙,与和煦对峙,与酸痛发胀的年少岁月对峙。
停留在过去的单薄少年抬起手擦去尘埃。
被承载于玻璃片上上的青春标本,在时间时许不停的风化里,终于流徙成为了宇宙里漂浮的尘埃。
它们汇聚成漫长的光河。
楔子
你曾经有梦见这样无边无际的月光下的水域么?
无声起伏的黑色的巨浪,在地平线上爆发出沉默的力量。
就这样,从仅仅打湿脚底,到盖住脚背,漫过小腿,一步一步地,走向寒冷寂静的深渊。
你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么?
在很遥远,有很贴近的地方想起来。
像是有细小的虫子飞进了耳孔,在耳腔里嗡嗡地振翅。
突突地跳动在太阳穴上的声音。
视界里拉动出长线的模糊的白色光点。
又是什么。
漫长的时光像是一条黑暗潮湿的闷热洞穴。
青春如同悬在头顶上面的点滴瓶,一滴一滴地流逝干净。
而窗外依然是阳光灿烂的晴朗世界。
就是这样了吧。
第一回
苍白寂寥的冬天 冗长的弄堂 逼仄而潮湿的弄堂
眼睛里蒙着的断层是只能看到咫尺的未来。
弄堂里弥漫起来的晨雾,被渐渐亮起来的灯光照射出一团一团黄晕来。
还没有亮透的清晨,在冷蓝色的天空上面,依然可以看见一些残留的星光。
头顶是深冬里飘荡着的白寥寥的天光。
深冬的清晨。整个弄堂都还是一片安静。像是被浓雾浸泡着,没有一丁点儿声响。
头顶是交错而过的天线,分割着不明不暗的天空。云很低很低地浮动在狭长的天空上。铅灰色的断云,沿弄堂投下深浅交替的光影。
就是这样的世界,每天每天,像抽丝般的,缠绕成一个透明的茧。虚荣与嫉妒所铸就的心脏容器里,被日益地灌注进粘稠的墨汁。
发臭了。
就像是横亘在血管里的棉絮棉絮,阻碍者血液的流动。“都快凝结成血块了。”心里是这样满满当当的压抑感。总觉得有一天会从血管里探出一根刺来,扎出皮肤,暴露在空气里。
易遥十三岁的脸,平静地曝晒在夏日的阳光下,皮肤透明的质感,几乎要看见红色的毛细血管。
临近门,回头的罅隙里。
密密麻麻的。填满在心里。
就像填满一整张演算纸。没有一丝的空隙。
想要喘不过气来。
生命被书写成潦草和工整两个版本。再被时间刷的褪去颜色。难以辨认。
每一个生命都像是一颗饱满而甜美的果实。只是有些生命被太早地耗损,露出里面皱而坚硬的果核。
窗外是冬天凛冽的寒气。
胸腔中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像是突然滚进了一颗石头,滚向了某一个不知名的角落。然后黑暗里传来一声微弱的声响。
水龙头哗哗的声音。
像是突然被打开的闸门,只要没人去关,就会无休止地往外泄水。知道泄空里面所盛放的一切。
兀自 带着年轻气盛的血液,回游在胸腔里 暮色四合
头顶飞过的一只飞鸟,留下一声尖锐的鸟叫声,在空气里硬生生扯出一道透明的口子来。
风几乎要将天上的云全部吹散了。
冬季的天空,总是这样锋利的高远。风几乎吹了整整一个冬天。吹的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白寥寥的天光,从天空里僵硬的打下来。
他都会感觉到有人突然朝自己身体里插进一根巨大的针筒,然后一点一点地抽空内部的存在。
空虚永远填不满。
弄堂里各家的窗户中都透出黄色的暖光来,减弱着深冬的锐利寒冷。
眼泪一颗接一颗掉下来,像是被人忘记拧紧的水龙头。眼泪掉进锅里烧热的油,四处飞溅。
突然变强烈的心跳,压不平的慌乱感让齐铭朝楼上走去。
路灯将黑暗戳出口子。照亮一个很小的范围。
走几米,就重新进入黑暗,直到遇见下一个路灯。偶尔有一两片树叶从灯光里飞过,然后被风又吹进无尽的的黑暗里。
大风从黑暗里突然吹过来,一瞬间像是卷走了所有的温度。
冰川世纪般的寒冷。
以及瞬间消失的光线。
揶揄。嘲讽。尖酸刻薄。
可是,却在身体里某一个地方,形成真切的痛。
黑暗中人会变的脆弱。变得容易愤怒,也会变得容易发抖。
她从沙发上起来,把刚刚披散下来的稍微有些灰白的头发拂上去。然后沉默地走回房间。伸手拧开房间门,眼泪滴在手背上。
比记忆里哪一次都滚烫。
心里像插着把刀。
黑暗里有人握着刀柄,在心脏里深深浅浅地捅着。
像要停止呼吸般地心痛。
黑暗中,谁都看不见谁的眼泪。
门外,母亲像一个被撤掉拉线的木偶,一动不动地站在黑暗里。
消失了所有的动作和声音。只剩下滚烫的眼泪,在脸上无法停止地流。
空无一人的学校。在初冬白色的天光下,像是一座废弃的医院。又干净,又死寂。
蜚短流长按照光的速度传播着,而且流言在传播的时候,都像是被核爆炸辐射过一样,变化出各种丑陋的面貌。
依然是冬天最最干燥的空气,脸上的皮肤变得像是劣质的石灰墙一样,仿佛蹭一蹭就可以掉下一层厚厚的白灰来。
一连划破了好几层,墨水洇开一大片。
那一瞬间在心里的疼痛,就像划破好几层纸。
听到流言的不会只有齐铭一个人,易遥也会听到。
但是她不在乎。
就算是齐铭听到了,她也不会在乎。
但她一定会在乎的是,齐铭也听到了,并且相信。
在你的心里有这样一个女生。
你情愿把自己早上的牛奶给她喝。
你情愿为了她骑车一个小时去买验孕试纸。
你情愿为了她每天帮她抄笔记然后送到她家。
而同样的,你也情愿相信一个陌生人,也不愿意相信她。
而你相信的内容,是她是一个婊子。
易遥推着自行车朝家走。
沿路的繁华和市井气息缠绕在一起,像是电影布景般朝身后卷去。
就像是站在机场的平行电梯上,被地面卷动着向前。
这一点,在易遥心里的压抑,就像是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重重地压在心脏上,几乎都动不了了。
血液无法流回心脏。
身体像缺氧般浮在半空。落不下来。落不到地面上脚踏实地。所有的关节都被人拴上了银亮的丝线,像个木偶一样地被人拉扯着关节,僵尸般地开阖,在街上朝前行走。
她捂着心口那里,那里像是被揉进了一把碎冰,冻得发痛。
第二回
我也忘记了曾经的世界,是否安静得一片弦音。
有一些隔绝在人与人之间的东西,可以轻易地就在彼此间划开深深的沟壑,下过雨,再变成河,就再也没有办法渡过去。
心里像覆盖着的一层灰色的膜,像极了傍晚弄堂里的暮色,带着热烘烘的油烟味,熏得心里难受。
屋外的白光突然涌进来,几乎要晃瞎齐铭的眼睛。
前一分钟操场还空得像是可以停的下一架飞机。而后一分钟,像是被香味引来的蚂蚁,密密麻麻的学生从各个教室里拥出来,黑压压地堵在操场上。
广播里的音乐荡在冬天白寥寥的空气里,被风吹得摇摇晃晃,音乐被电流影响着,发出哔啵的声音,广播里喊着口令的那个女生明显听上去就没有精神,病恹恹的,像要死了。
易遥回过头,眼睛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一片后脑勺。她定定地望着前面,说:“齐铭你对我太好了,好的有时候我觉得你做什么都理所当然。很可能有一天你把心掏出来放我面前,我都觉得没什么,也许还会朝上面踩几脚。齐铭你还是别对我这么好,女人都是这样的,你对她好了,你的感情就廉价了。真的。女人就是贱。”
齐铭回过头去,易遥望着前方没有动,音乐响在她的头顶上方,她就像听不见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像是被撤掉了插头的电动玩具。她的眼睛湿润得想要滴下水来,她张了张口,却没有发出声音,但齐铭却看懂了她在说什么。
她说,一个比一个贱。
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讲了一个自以为得意的笑话。眼睛笑得眯起来,闪着湿漉漉的亮光。
却像是在齐铭心里揉进了一把碎玻璃。
千沟万壑的心脏表面。穿针走线般地缝合进悲伤。
地心神厨的那些悲怆的情绪,沿着脚底,像被接通了回路流进四肢。伸展运动,伸手朝向锋利的天空。那些情绪,被拉扯着朝上涌动,积蓄在眼眶周围,快要流出来了。
心脏像冬天的落日一样,随着齐铭突然下拉的嘴角,惶惶然下坠。
暮色像是墨水般倾倒在空气里,扩散得比什么都快。
被过往的车灯照出的悲伤的轮廓。毛茸茸地拓印在视线里。
齐铭抬起脚,用力一踩,齿轮突然生涩地卡住,然后链条迅速地脱出来,像条死蛇般掉在地上。
暗黑色的云大朵大朵地走向天空
沉重得像是黑色的悼词。
生命里突兀的一小块白。以缺失掉的两个字为具体形状。
易遥口里那一声“爸”,被硬生生地吞了回去。像是吞下一枚刀片,划痛了整个胸腔。
冰冷的风硬硬地砸到脸上。眼泪在风里迅速地消失掉温度。
心里像被重新注入热水。
一点一点地解冻着刚刚几乎已经死去的四肢百骸。
像是路灯跳闸一样,一瞬间,周围的一切被漆黑吞没干净。
那些久远到昏黄的时光,像是海浪般朝着海里倒卷而回,终于露出尸骨残骸的沙滩。
这次,连眼泪也流不出来了。眼眶像是干涸的洞。恨不得朝里面揉进一团雪,化成水,流出来伪装成悲伤。
易遥站在原地,愤怒在脚下生出根来。那些积蓄在内心里对父亲的温柔的幻想,此刻被摔碎成成千上万片零碎的破烂。像是打碎了一面玻璃,所有的碎片残渣堵在下水道口,派遣不掉,就一起带着剧烈的腥臭翻涌上来。
发臭了。
腐烂了。
内心的那些情感。
变成了恨。变成了痛。变成了委屈。变成密密麻麻的带刺的藤蔓,穿刺着心脏的每一个细胞,像冬虫夏草般将躯体吞噬干净。
那种心痛。绵延在太阳穴上。
刚刚被撞过的地方发出钝重的痛来。
其实无论夜晚是如何的漫长与寒冷。那些光线,那些日出,那些晨雾,一样都会准时而来。
这样的世界,头顶交错的天线不会变化。逼仄的弄堂不会变化。
那些油烟和豆浆的味道,都会生生地嵌进年轮里,长成生命的印记。
面前的易遥突然像是一座在夏天雨水中塌方的小山,整个人失去支撑般轰然向旁边倒去。
第三回
领队的那只蚂蚁,爬到了心脏的最上面,然后把旗帜插到了脚下柔软跳动的地方,用力地一插——哈,占领咯。
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钟声。来回地想着。
却并没有诗词中的那种悠远和悲怆。只剩下枯燥和烦闷,固定地来回着。撞在耳膜上,把钝重的痛感传向头皮。
与时间相反的是眼皮上的重力,像被一床棉絮压着,睁不开来,闭上又觉得涩涩的痛。光线像一把粗糙的毛刷子在眼睛上来回扫着,眨几下就流出泪来。
目光像窗外寂寥的冬天。呼啸着的白光。在寒冷里先出微微的温柔感来。一层一层地覆盖在身上。
淡定的表情像水墨画一样,浅浅地浮在光线黯淡的走廊里。
日光把他的背影照得几乎要吞噬干净。逆光里黑色的剪影,沉淀出悲伤的轮廓来。
周围几个女生的目光像是深海中无数长吻鱼的鱼嘴,在黑暗里朝着易遥戳过来,恨不得找到一点松懈处,然后扎进好奇而八卦的尖刺,吸取着用以幸灾乐祸和兴风作浪的原料。
周围一圈女生的目光骤然放大,像是深深海底中那些蛰伏的水母突然张开巨大的触须,伸展着,密密麻麻地朝易遥包围过来。
眼睛迅速蒙上的雾气,被冬天的寒冷撩拨出细小的刺痛感来。
目光绷紧,像弦一样纠缠拉扯,从一团乱麻到绷成直线。
无限漫长时光里的温柔。
无限温柔里的漫长时光。
一直都在。
头顶是冬日里早早黑下的天空。
大朵大朵的云。黑红色的轮廓缓慢地浮动在黑色的天空上。
学校离江面很近。所以那些运输船发出的汽笛声,可以远远地从江面上飘过来,被风吹动着,从千万种嘈杂的声音里分辨出来。那种悲伤的汽笛声。
远处高楼顶端,一架飞机的导航闪灯以固定频率,一下一下地亮着,在夜空里穿行过去。看上去特别孤独。
黑夜里连呼吸都变得沉重。
空中小姐一盏一盏地关掉头顶的黄色阅读灯。夜航的人都沉睡在一片苍茫的世界里。内心装点这各种精巧的迷局。无所谓孤单,也无所谓寂寞。
只是单纯地在夜里,怀着不同的心事,飞向同一个远方。
其实我多想也这样,孤独地闪动着亮光,一个人寂寞地飞过那片漆黑的夜空。
飞向没人可以寻到得到我的地方,被荒草淹没也好,被潮声覆盖也好,被风沙吹走年轻的外貌也好。
可不可以就这样。让我在没人知道的世界里,被时间抛向虚无。
可以……吗?
其实无论什么东西,都会像这块血迹一样,在时光无情的消耗里,从鲜红,变得漆黑,最终瓦解成粉末,被风吹得没有痕迹吧。
黑暗里的目光。晶莹闪亮。像是蓄满水的湖面。
那些话传进耳朵里,然后迅速像是温热而刺痛的液体流向心脏。
天空里永远都是这样白寥寥的光线,云朵冻僵一般,贴向遥远的苍穹。
是这样的时光。镶嵌在这几丈最美好的年华锦缎上。
这样的话题,以前就像是漂浮在亿万光年之外的尘埃一样没有真实感,而现在,却像是门上的蛛丝一般蒙到脸上。
镜子里自己年轻而光滑的脸。像是一个瓷器。
窗外的日光像是不那么苍白了。稍微有了一些暖色调。把天空晕染开来。
冲出楼道的时候,剧烈的日光突然从头笼罩下来。
几乎要失明一样的刺痛感。拉扯着视网膜,投下纷繁复杂的各种白色的影子。
站立在喧嚣里。渐渐渐渐恢复了心跳。
眼泪长长地挂在脸上。被风一吹就变得冰凉。
渐渐看清楚了周围的格局。三层的老旧阁楼。面前是一条人潮汹涌的大马路。头顶上是纷繁错乱的梧桐树的枝桠,零星一两片秋天没有掉下的叶子,在枝桠间停留着,被冬天的冷气流风干成标本。弄堂口一个卖煮玉米的老太太抬起眼半眯着看向自己。凹陷的眼眶里看不出神色,一点光也没有,像是黑洞般咝咝地吸纳着自己的生命力。
第四回
我也曾经走过那一段雷禁般的区域。
像是随时都会被脚下突如其来的爆炸,撕裂成光线里浮游的尘屑。
每一条马路都像是一条瘫死的蛇一样,缓慢地蠕动着。
夕阳模糊的光线像水一样在每一寸地面与墙壁上抹来抹去。涂抹出毛茸茸的厚实感,削弱了大半冬天里的寒冷和锋利。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只感觉得到瞬间漫过耳朵鼻子的水流,以及那种刺鼻的恶臭瞬间就把自己吞没了。甚至来不及感觉到寒冷。
——其实那个时候,我听到身后顾森西的喊声,我以为是你。
——其实那个时候,我有一瞬间那么像过,如果就这样死了,其实也挺好。
在冬天夕阳剩下最后光芒的夜晚,四周灰蒙蒙的尘埃聚拢来。
少年和少女,站在暮色中的灰色校门口,他们四个人,彼此交错着各种各样的目光。
悲伤的。心疼的。怜悯的。同情的。爱慕的。
像是各种颜色的燃料被倒进空气里,搅拌着,最终变成了漆黑混沌的一片。在叫不出名字的空间里,煎滚翻煮,蒸腾出强烈的水汽,把青春的每一扇窗,都蒙上磨砂般的朦胧感。
却被沉重的冬天,或者冬天里的某种情绪吞噬了色彩。只剩下黑,或者白,或者黑白叠加后的各种灰色,被拓印在纸面上。
第五回
就这样安静地躺在地面上。
安静地躺在满地闪闪发光的玻璃残渣上。
我并没有感觉到痛。
也没有感觉到失望。
只是身体里开始生长出了一个旋涡。
一天一天地发育滋生起来。
天边拥挤滚动着黑里透红的乌云。落日的光渐渐地消失了。
十分钟之前,各种情绪在身体里游走冲撞,像是找不到出口而焦躁的怪物,每一个毛孔都被透明胶带封得死死的,整个身体被无限地充胀着,几乎要爆炸开来。
而一瞬间,所有的情绪都消失干净,连一点残余的痕迹都没有留下。而在下一个时刻汹涌而来的,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寒冷。
湿淋淋的衣服像一层冰一样,紧紧裹在身上。
乌云翻滚着吞噬了最后一丝光线。
被风不小心送过来的种子。
掉在心房上。
一直沉睡着。沉睡着。
但是,一定会在某一个恰如其分的时刻,瞬间就苏醒过来。在不足千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迅速地顶破外壳,扎下盘根错节的庞大根系,然后再抖一抖,就刷的一声挺立出遮天蔽日的茂密枝丫与肥厚的枝叶。
接着,慢镜头一般缓慢地张开了血淋淋的巨大花盘。
这样的种子。一直沉睡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等待着有一天,被某种无法用语言定义的东西,解开封印的咒语。
第六回
我在梦见你。
我在一次又一次不能停止地梦见你。
梦中的我们躺在河水上面,平静得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木偶。
或者亡去的故人。
也不太记得他们说过人的梦是没有颜色还是没有声音。
如果是没有颜色的话——
自己的梦里明明就经常出现深夜所有电视节目结束时出现的那个七彩条的球形符号。也就是说,经常会梦见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看到深夜,一直看到全世界都休眠了,连电视机也打出这样的符号来,告诉你,我要休息了。
而如果是没有声音的话——
自己的梦里又经常出现教室里课本被无数双手翻动时的哗啦哗啦的声响,窗外的蝉鸣被头顶的电扇转破敲碎,稀疏地砸到眼皮上,断断续续,无休无止。空气里是夏天不断蒸发出的暑气,闷得人发慌。连黑板也像是在这样潮湿闷热的天气里长出了一层灰白色的斑点来。下课后的值日生总是抱怨。然后更用力地挥舞黑板擦。那种刷、刷、刷的声音。
还有那些来路不明的声音。有的时候是哽咽。有的时候是呜咽。有的时候是啜泣。有的时候是饮泣。然后一天一天地,慢慢变成了呐喊。
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梦里什么都有吗?
刚上到楼梯,走进走廊,窗户外面就刷刷地飘过一大堆白色的塑料袋。
没有坠下去,却被风吹到了更高的天上。
其实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飞得那么高。没有翅膀。也没有羽毛。
仅仅就是因为轻么?仅仅就是因为没有重量么?
于是就可以一直这样随风漂泊么?
春天的风里卷裹着无数微笑的草籽。
它们像那些轻飘飘的白色塑料袋一样,被吹向无数未知的地域。
在冷漠的城市里死亡,在潮湿的荒野里繁盛。
然后再把时间和空间,染成成千上万的无法分辨的颜色。
梦里曾经有过这样的画面,用手拨开茂盛的柔软蒿草,下面是一片漆黑的尸骸。
冬天难得的阳光,照进高大的窗户,在地面上投出巨大的光斑。
尘埃浮动在空气里,慢镜头一样地移动成无数渺小的星河。
像是在地理课上看过的幻灯片里的那些微小的宇宙。
像是有虫子爬进了血管,一寸一寸令人恶心地朝心脏蠕动着。
每一句话都像是黑暗里闪着绿光的匕首,刷刷地朝着某一个目标精准地刺过去。
黑暗中弥漫的血腥味道,甜腻得可以让人窒息了。
终于爬进心脏了。那条肥硕的恶心的虫子。
被撕咬啃噬的刺痛感。顺着血液传递到头皮,在太阳穴上突突地跳动着。
一整条安静的走廊。
消失了声音。消失了温度。消失了光线。消失了那些围观者的面容和动作。时间在这里变成缓慢流动的河流。粘稠得几乎无法流动的河水。还有弥漫在河流上的如同硫磺一样的味道与蒸汽。
走廊慢慢变成一个巨大的隧道般的洞穴。
不知道连接往哪里的洞穴。
越靠近傍晚,太阳的光线就越渐稀薄。
易遥抬起头望向窗外,地平线上残留着半个赤红的落日。无线绚丽的云彩从天边滚滚而起,拥挤着顶上苍穹。
世界被照耀成一片迷幻般的红色。
在某些瞬间,你会感受到那种突如其来的黑暗。
比如瞬间的失明。
比如明亮的房间里被人突然拉灭了灯。
比如电影开始时周围突然安静下来的空间。
比如飞快的火车突然开进了幽长的隧道。
或者比如这样的一个天空拥挤着绚丽云彩的傍晚。那些突然扑向自己的黑暗,像是一双力量巨大的手,将自己抓起来,用力地抛向了另一个世界。
第七回
你是不是很想快点离开我的世界?
用力地认真地,想要逃离这个我存在着的空间?
厚重的云朵把天空压得很低。像擦着弄堂的屋顶一般移动着。
楼顶上的尖锐的天线和避雷针,就那样哗哗的划破黑色云层,像撕开黑色的布匹一样发出清晰的声响。
黑色的云朵里移动着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模糊光团。隐隐约约的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光晕。
在云与云缝隙里间歇出没着。
右手死死地抓紧着书包一边的肩带,用尽力气指甲发白。像溺水的人抓紧手中的淤泥与水草。
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飞速地离开自己的世界。所以想要抓紧一些,更紧一些。紧的透不过气也没有关系。
只要不要离开自己的世界。呛人的油烟从两旁的窗户里被排风扇抽出来直直地喷向对面同样转动的油腻腻的排风扇。凝固成黑色粘稠液体的油烟在风扇停止转动的时候,会一滴一滴从叶片上缓慢地滴向窗台。易遥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用洗洁精擦一次。那种手指上无论洗多少次多少次也无法清除的油腻感,刻在头皮的最浅层,比任何感觉都更容易回忆起来。
冰冷的黑暗,以及住在不远处的悲伤的温暖。
它们曾经并列在一起。
它们曾经生长在一起。
它们还在一起。
它们会不会永远在一起。
像是宇宙某一处不知道的空间里,存在着这样一种巨大的旋涡,呼呼地吸纳着所有人的青春时光,年轻的脸和饱满的岁月,刷刷地被拉扯着卷向看不见尽头的谷底,被寄居在其中的怪兽吞噬。
从腹部传来的痛觉像山谷里被反复激发的回声渐渐变得震耳欲聋。有一把掉落在腹腔中的巨大锋利剪刀,咔嚓咔嚓地迅速开合着剪动起来。
恐惧像巨浪的一样,将易遥瞬间没顶而过。
世界上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叫做相信的东西的。
有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地相信一个并不熟悉的人。你会告诉他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这些事情你连你身边最好的死党也没有告诉过。
有时候你也会莫名其妙地不相信一个和你朝夕相处的人,哪怕你们曾经一起分享并且守护了无数个秘密,但是在那样的时候,你看着他的脸,你不相信他。
我们活在这样复杂的世界里,被其中如同圆周率一样从不重复也毫无规则的事情拉扯着朝世界尽头盲目地跋涉而去。
曾经你相信我是那样的肮脏与不堪。
就像曾经的他相信我是一个廉价的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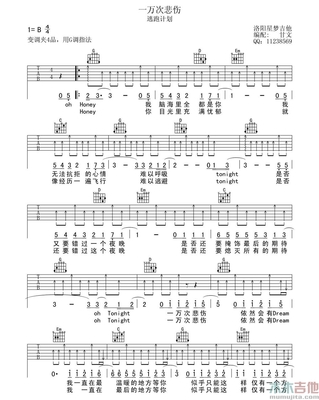
我就是这样生活在如圆周率般复杂而变幻莫测的世界里。
慢慢地度过了自己的人生。
其实很多时候,我连自己都从来没有相信过。
窗外明亮的阳光烫在眼皮上。
很多游动的光点在红色的视网膜上交错移动着。
渐渐睡了过去。
于是也就没有听见来自某种地方呼喊的声音。
你没有听见吧?
可是我真的曾经呐喊过。
第八回
有时候会觉得,所有的声响,都是一种很随机的感觉。
有时候你在熟睡中,也听得见窗外细小的雨声。而有时候,你只是浅浅地浮在梦的表层,但是窗外台风登录时滚滚而过的响雷,也没有把你拉出梦的层面。
其实这样的感觉我都懂。
因为我也曾经在离你很近很近的地方呐喊过。
然后你在我的呐喊声里,朝着前面的方向,慢慢离我远去。
也是因为没有介质吧。
直到现在,易遥都觉得所谓的焦点,都是有两种意思的。
一种是被大家关注着的,在实现聚焦的最中心的地方,是所谓的焦点。
就像那一天黑暗中彼此拥抱着的顾森湘和齐铭,在灯光四下亮起的瞬间,他们是人群里的焦点。
而一种,就是一直被灼烧着,最后化成焦炭的地方,也是所谓的焦点。
就像是现在的自己。
被一种无法形容的明亮光斑笼罩着,各种各样的光线聚拢在一起,定定地照射着心脏上某一处被标记的地方,一动不动的光线,像是细细长长的针,扎在某一个地方。
天空里的那面巨大的凸透镜。
阳光被迅速聚拢变形,成为一个锥形一样的漏斗。
圆形光斑照耀着平静的湖面。那个叫做焦点的地方,慢慢地起了波澜。
终于翻涌沸腾的湖水,化作了缕缕涌散开来的白汽,消失在炽热的空气里。
连同那种微妙的介质,也一起消失了。
那种连接着你我的介质。那种曾经一直牢牢地把你拉拢在我身边的介质。
化成了翻涌的白汽。
汩汩的气泡翻涌的声音。( )不知来处的声音。P209
连最深最深的海底,都有着翻涌的气泡不断冲向水面。不断翻涌上升的白汽。连续而永恒地消失着。
连躲进暗无天日的海底,也逃脱不了。
还挣扎什么呢。
第九回
黑暗中慢慢流淌着悲伤的河流。淹没了所有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青春和时间。
你们本来可以逃的很远的。
但你们一直都停留在这里,任河水翻涌高涨,直到从头顶倾覆下来。
连同声音和光线,都没有来得及逃脱这条悲伤的巨大长河。
浩淼无垠的黑色水面反射出森冷的白光,慢慢地膨胀起来。月亮牵动着巨大潮汐。
全世界都会因为来不及反抗,而被这样慢慢地吞没么?
第十回
那些被唤醒的记忆,沿着照片上发黄的每一张脸。
重新附上灵魂。
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是一定可以伤害到你的事情。
只要你足够冷酷,足够漠然,足够对一切事情都变得不再在乎。
只要你慢慢地把自己的心,打磨成一粒光滑坚硬的石子。
只要你把自己当做已经死了。
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东西可以伤害到你了。
不想再从别人那里感受到那么多的痛。那么就不要再去对别人付出那么多的爱。
这样的句子如果是曾经的自己,在电视里或者小说上看到的时候,一定会被恶心地冒出胃酸来。可是当这一切都化成可以触摸到的实体,慢慢地像一团浓雾般笼罩你的全身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都变成了至理名言,闪烁着残酷而冷静的光。
易遥每次看着林华凤的时候,心里都是翻涌着这样黑暗而恶毒的想法。无法控制地席卷着大脑里的每一个空间,膨胀德没有一丝罅隙来存放曾经稍纵即逝的温暖。
还没有到夏天,所以空气里也没有响亮的蝉鸣。只是阳光一天比一天变得刺眼。正午的影子渐渐缩短为脚下的一团。不再是拉长的指向远处的长影。
记忆力的夏天已经遥远到有些模糊了。就像是每一天在脑海里插进了一张磨砂玻璃,一层一层地隔绝着记忆。
一声一声沉闷的打桩的声音,像是某种神秘的计时,持续不断地从远方迎面而来。
齐铭眼睛渐渐红起来,像是被火炙烤着一样,血丝像要把眼眶撑裂了。
那一瞬间,她什么都明白了。分布在身体里的复杂的电路,被迅速接通了电流,刷刷地流过身体,哔啵作响。
那一刻,唐小米觉得伸向自己的那本词典,就像是一把闪着绿光的匕首。而面前易遥那张凝固着真诚笑容的脸,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了所有的光线和声音。
他望向自己的目光,就像是在漏风的房间里燃烧的蜡烛,来回晃动着,在最后的一瞬间熄灭下去,化成一缕白眼消失在气流里。
而现在,他也像是若无其事地把手伸出水面一样,在无数词语组合而成的汪洋里,选择了这样一枚叫做“恶毒”的石头,捞起来用力地砸向自己。
易遥没有让开的意思,她还是站在齐铭的面前,定定地望着面前的齐铭,抓着书包的手微微颤抖着,没有血色的苍白。在那一刻,易遥前所未有地害怕,像是熟悉的世界突然间180度地水平翻转过去,面目全非。
曾经被人们假想出来的棋盘一样错误的世界。
江河湖海大漠山川如同棋子一样分布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而你只是轻轻地伸出了手,在世界遥远的那一头握了一握。于是整个棋盘就朝着那一边翻转倾斜过去。曾经的汪洋变成了深深的峡谷,曾经的沙漠高山被覆盖起无垠的水域。
而现在,就是这样被重新选择重新定义后的世界吧。
既然你作出了选择。
既然你把手放在了世界上另一个遥远的地方。
——该怎样去定义的关系?爱情吗?友谊吗?
——只是当你生命里,离你很近很近的地方,存在着一个人。她永远没有人珍惜,永远没有人疼爱,永远活在痛苦的世界里,永远活在被排挤被嘲笑的空气中。她也会在看见别的女孩子被父母呵护被男朋友照顾时心痛得转过脸去。她也会在被母亲咒骂着“你怎么不去死”的时候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她也会想要穿着漂亮的衣服,有很多的朋友关心,有美好的男生去暗恋。她也会想要在深夜的时候母亲可以为自己端进一碗热汤而不是每天放学就一头扎进厨房里做饭。她也会想要做被捧在手心里的花,而不是被当作可以肆意践踏的尘。
——当这样的人就一直生活在离你很近很近的地方的时候,当这样的人以你的幸福生活作为镜像,过着完全相逆的生活来成为对比的时候,她越是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你就越是没办法抽身事外。
——你一定会忍不住想要去帮她擦掉眼泪,一定会想要买好多好多的礼物塞进她的怀里,你一定会在她被殴打哭泣的时候感受到同样的心痛,你也一定会在她像你求救的时候义无反顾,因为你想要看到她开心地微笑起来,哪怕一次开心地微笑起来。又或者不用奢求微笑,只要可以抬起手擦掉眼泪,停止哭泣也好。
——你陪着她慢慢长大,你看着她一路在夹缝里艰难的生存下来。
——你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全部去给她,塞给她,丢给她,哪怕她不想要也要给他。
——这样的她就像是身处在流沙的黑色旋涡里,周围的一切都哗哗地被吸进洞穴。她就陷在这样的旋涡里。伸出手去拉她,也只能随着一起陷下去而已。而如果放开手的话,自己就会站得很稳。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站在漩涡边上,眼看着她一天一天被吸纳进去的感觉。
——甚至当有一天,她已经完全被黑色的旋涡吞噬了,连同着她自己本身,也已经变成了那个巨大的黑色旋涡时。
——好像要远远地逃开。逃离这篇卷动着流沙的无情的荒漠。
心脏像是被人用力的抓皱了。
却像是黑暗中有一只手指,突然按下了错误的开关,一切重新倒回向最开始的那个起点。
就像那些切割在皮肤上的微小疼痛,顺着每一条神经,迅速地重新走回心脏,突突地跳动着。
就像那些被唤醒的记忆,沿着照片上发黄的每一张脸,重新附上魂魄。
就像那些倒转的母带,将无数个昨日,以跳帧的形式把心房当作幕布,重新上演。
就像那些沉重的悲伤,沿着彼此用强大的爱和强大的恨在生命年轮里刻下的凹槽回路,逆流成河。
第十一回
曾经散落一地的滚动的玻璃珠,突然被一根线穿起来,排成了一条直线,笔直地指向以前从来看不出来的事实。
好像很多年一瞬间过去了的感觉。所有的日日夜夜,排成了看不见尾的长队。而自己站在队伍的最后面,追不上了。于是那些日日夜夜,就消失在前方。剩下孤单的自己,留在了岁月的最后。
生活中到处都是这样悲伤的隐喻。
如同曾经我和你在每一个清晨,一起走向那个光线来源的出口。
也如同现在他载着我,慢慢离开那个被我抛弃在黑暗里的你。其实在自行车轮一圈一圈滚动着慢慢带我逐渐远离你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了,被熟悉的世界一点一点放弃的感觉。
在那个世界放弃我的时候,我也慢慢地松开了手。
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清晨了。
第十二回
下起毛毛雨的微微有些凉意的清晨。把池塘里的水蒸发成逼人暑气的下午。
有鸽子丛窗外呼啦医生飞向蓝天的傍晚,夕阳把温暖而熟悉的光芒涂满窗台。
虽然在时光的溶液里被浸泡的失去了应该完整无缺的细节,可是却依然留下根深蒂固的某个部分,顽强的存活在心脏里。
易遥看着眼前微笑着的齐铭,心里像是流淌过河流一样,所有曾经的情绪和波动,都被河底细细的沉沙埋葬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地壳的运动重新暴露在日光之下,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是已经变成了化石,还是被消磨得什么都没有剩下。这些都是曾经青春里最美好的事情,闪动着眼泪一样的光,慢慢地沉到河底去。
就是这样一片一片装载载玻片和覆玻片之间的标本,纹路清晰地对青春进行注解与说明。
顾森西靠在墙壁上,张着口像是身体里每一个关节都跳了闸,太过剧烈的电流流过全身,于是就在也没办法动弹。
易遥没有说话,风把她的头发突然就吹散了。
从每一个心脏里蒸发出来的仇恨,源源不绝的蒸发出来的仇恨,那么多的痛恨我的人蒸发出来的仇恨。
无数个持续蒸发的日子,汇聚在我的头顶变成黑色的沉甸甸的云。
为什么永远没有止境呢?
为什么停不下来呢?
你们的那些持续不停地浇在我身上的,湿淋淋的仇恨。
乌云从天空滚滚而过。
凌晨三点。月光被遮得一片严实。
这个世界上每一分钟都有无数扇门被打开,也有无数扇门被关上。光线汹涌进来,然后又在几秒后被随手掩实。
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甚至是粉红色的世界。
为什么唯独你生活在黑色的世界里。
黑暗中浮现出来的永远是你最后留在电视屏幕上的脸,呆呆的想要望穿屏幕的眼睛,不肯合上的口。欲言又止的你,是想对我说“原谅我”,还是想说“救救我”?
是想要对这个冷冰冰的,从来没有珍惜过你的世界,说一声“对不起”,还是一声“我恨你”?
顾森西站在弄堂的门口,望着里面那件再也不会有灯光亮起来的兀自,黑暗中通红的眼睛,湿漉漉的像是下起了雨。
最终回
齐铭醒来的时候已经傍晚了,窗外万家灯火。坐在床上朝窗户外看出去,江面上有亮着灯的船在缓慢地移动着。
——黑暗中你沉重的呼吸是清晨弄堂里熟悉的雾。
——你温热的胸口。
——缓慢流动着悲伤与寂静的巨大河流。
番外
可是真的好多事情,就那样渐渐地消失在了我的脑海深处。只剩下一层白蒙蒙的膜,浅浅地包裹着我日渐僵硬的大脑。
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在顽强地保护着自己吧。
但那又是为什么,你们统统都选择了去死呢?
在最应该保护自己的时候,你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不仅仅只是放弃了你们自己,而是连带着这个均匀呼吸着的世界,一起放弃了。
森西妈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目光呆呆地定在电视与沙发之间的某一处。也不知道在看什么。隔一段时间会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剧烈但是非常沉闷的叹气声。
其实听上去更像是拉长了声音在哭。
风卷动着灰色的云从窗外海浪一样地翻滚而过。可能窗户关太紧的关系,整个翻滚沸腾着气流的蓝天,听上去格外的寂静。
像把耳朵浸泡在水里。
有一朵细小的蘑菇云在心脏的旷野上爆炸开来。
遥远的地平线上生起的寂静的蘑菇云,在夕阳的暖黄色下被映照得绚烂。无声无息地爆炸在遥远的地方。
似曾相识的感觉像是河流堤坝被蚂蚁驻出了一个洞,四下扩张的裂纹,像是闪电一样噼啪蔓延。
一定在什么地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定在什么时候出现过同样的表情。
火烧云从天边翻腾起来。顺着操场外围的一圈新绿色的树冠,慢慢地爬上头顶的天空。也不知道那片稀薄的天空被烧光之后会露出什么来。夏天里感觉日渐高远稀薄的蓝天。
挂了整整一天的风终于停了下来。
那种孤单的感觉,会在每一个嘈杂的瞬间从胸腔里破土而出。
然后在接下来的安静的时刻,摇晃成一颗巨大的灌木。
像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世界。
每个人都像是存活在子宫中的胎儿一样与这个世界保持着同步胎动的联系。
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有一天切断脐带,抽空羊水,剥离一切与子宫维系的介质,那么,我们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安静而庞大的,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世界。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时态里,一定都会愿意活在过去。
现在的种种痛苦,和未来不知道会经历什么样的痛苦,都触动着我们的本能。启动生物趋利避害的系统,让我们不愿意活在当下,也不愿意去期待未来。
而过去的种种,也在生物趋利避害的系统下,被日益美化了。忘记了所有的痛苦,只留下美好的记忆让人们瞻仰。
所以,所有的过去都带着一张美好得近乎虚假的面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像是被茧包裹的幼虫一样,心甘情愿地活在过去虚构的容器里。
却想起来那么遥远。遥远倒像是从此时到彼时的路途里,每天与每天之间,都插进了一张磨砂玻璃,两百张磨砂玻璃背后的事情,看上去就是一整天冬天也无法散尽的大雾。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黑暗。
浓郁的树荫。月球的背面。大厦与大厦之间的罅隙。还没两头的清晨弄堂。突然暗下去的手机屏幕。深夜里被按掉开关的电视。突然拉灭的电灯。
以及人心的深处。
无数的蕴藏黑暗的场所。
无数喷涌着黑暗的源泉。
他们滋养着无穷无尽的不可名状的情绪,像是暴风一样席卷着每一个小小的世界。
而又一些痛觉,来源于你无法分辨和知晓的地方。只是浅浅地在心脏深处试探着,隐约地传递进大脑。你无法知晓这些痛的来源,无法知晓这些痛的表现方式,甚至感觉它是一种非生理的存在。
像有一个永动机被安放在了身体里面,持续不断的痛苦。没有根源。
你内心一定觉得特别痛苦吧?尽管你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旅行过来的人,完全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崭新的世界。
喷涌而出的黑暗源泉,冰冷的泉水把整个沸腾的嘈杂的世界洗涤得一片寂静。没有温度的世界,没有光线的世界。
全宇宙悬停在那样一个冷漠的坐标上面,孤单的影子寂寂地扫过每一个人的脸。
燥热的喧哗。
或者阴暗的冰冷。
世界朝着两级奔走而去。
在这烟火的纲常世间,生命的河流深处是静默,却静默的悲欢俱在。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