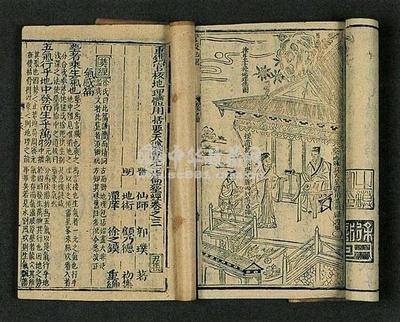今年真是个多灾的年份,西南大旱、玉树地震、南方大水,正当我暗自庆幸我的家乡就像它的名字“永吉”一样一直风调雨顺、永远吉祥时,灾难来了。
永吉县的汛情是从7月20日开始的。那几天永吉及上游县市连降大到暴雨,上游磐石境内的黄河水库泄洪,严重威胁着西部饮马河流域黄榆、金家、万昌等乡镇的安全,27日,饮马河大堤告急,我开着私家车,带领两名记者赶赴一线采访。由于现场情况紧急,下游人员已全部转移,警察封锁了所有进出道路,我们是唯一获准进入该区的媒体。在现场抢修大堤的十几个小时中,我完成了五次出镜,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吉林市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交通台和永吉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十一次连线。28日凌晨三点四十分,大堤险情暂时得到控制,我采访完吉林省副省长王守臣、向中央台传完录音,驾车返回。谁知,迎接我的是更大的洪水……
遭遇大水
车子在黑暗中向前行驶,由于连日的大雨,乡路很难走,再加上困意不断袭来,觉得路是那么的漫长。
天渐渐亮了,车也驶上了202国道,这时我发现,道路象水洗过一样,路面上有许多小树枝,我意识到下大雨了。到西阳镇大叉村时,路面上的水有二十厘米深,我快速冲过积水,招呼两名同事下车采访。这个二百余户的村子,大部分农家进水。
车继续前行,水情越来越严重,人造新农村——马鞍山村被山洪冲得七零八落,当快进入县城时,我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永吉县城口前镇地处吉林市西南22公里,202国道和沈吉铁路穿城而过。西面的五里河、南面的四间河在县城铁北街交汇,一直是城市防洪重点县城。此时的城西大桥已被上游涌下的玉米秸塞满,洪水几乎接近堤顶。我马上拨通单位李局长的电话,提出要涨大水了,广播电视节目要做适当调整。李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并授权我全权负责,并告诉我更大的洪峰马上就要来了,单位附近水已上岸,车进不来,马上把车送到高处再回单位。
我把两位同事送到离单位最近的水边,周县打来电话,告知县城有洪水,政府已在公安局成立了以潘县为首的临时指挥部,我开车来到公安局时,两位县长以乘公安局的越野车出去查看险情了,此时收音机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出“新闻和报纸摘要”,我昨晚上传的录音新闻排在第二条。这是周唯研来电话,省电视台的“守望都市”要连线报道饮马河大堤的新闻,可过了七点电话仍未进来,我弃车顺202国道向单位奔去。此时四间河已经漫堤,路上水越来越深,行至中心转盘时,水已经没过了膝盖,流速在加快,水中混着杂物,此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大洪水来了。
我生在县城下游的一个小村庄,两条河汇集后从小村旁流过,46年来经历了两场大水,可哪次都没有这么大。经验告诉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和十几位不同年龄的群众退到街边嘉鹏鞋业的台阶上,转眼间水就漫过了台阶、进入了一楼。我们一边帮助店家往楼上搬商品,一边向上撤退。当登上四楼经理室顺着窗户往外看时,我惊呆了。
视野中都是浑浊的洪水,泛着巨浪,撞开了对面商城的卷闸门,商品随着洪水奔涌而出;不断有柴火垛、牲畜、机动车、甚至简易房屋在大浪中翻滚;街路上已没有行驶的机动车,高档车封闭好象船一样顺流而下,低档车就地沉没,在水中翻滚;东边四间河桥墩上一个五十左右的男子,紧紧抱着路灯杆,转眼间没了踪影……街路成了奔涌的黄河,所有的建筑物都在洪水中呻吟,随着一个个大浪打来,身边不断传来尖叫声。我身边是74岁的王老先生,他在喃喃自语,“太大了,太大了……”
第一个发出现场报道
罕见的天灾令我震撼,记者的本能告诉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出报道,向外求援,而此时广播成为首选媒体。我不断地拨打中央台、省台、市台的热线电话,最先打通的是省台外联部记者赵梦秋的电话,她帮我联系了中央台,九点多,我第一次传出了电话连线报道。同时,吉林市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交通台,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都市110台等同行的电话也纷纷打入,一次次连线成功。当时的信号已很微弱,每次连线要无数次反复拨打才能通话。我作为身在孤岛的唯一媒体,第一个向外报道了水漫县城口前的消息,第一个紧急呼吁派遣舟桥部队驰援永吉。
报道发出后,第一个打进慰问电话的是远在北京的三哥,他和朋友听到了我的报道。之后收到问候都是的短信,我知道这时电话已很难打通了。我不敢用手机拍照,因为不知要被困多久,这是我唯一的武器。
后来网络通了之后,我搜索了网上最早关于永吉洪水的新闻,大多都是根据我的电话报道整理而成的。这里要感谢中央台的樊主任、姜主任、省台的赵梦秋、市台的李台、武台、经广台的沈台等。
目睹灾情
时间过了了中午十二点,洪水在接近一二楼缓台后开始缓慢下降。这时有人喊,看见解放军了,看见冲锋舟了。我淌着齐腰深、浑浊的洪水慢慢走向商场门口,只见两艘冲锋舟上载满了部队的官兵和记者,沿着202国道向中心转盘行进,远处还有消防官兵的也在船边集结。我的心踏实了许多。1981年我在辽宁当兵时,曾参加过辽南抗洪抢险,我知道,在这种时候,部队的集结是最快的。果然,当洪水开始慢慢消退时,不断有部队官兵赶来,紧张的救援开始了,不断有群众被救出。
下午四点多,我坐上了环卫处查看灾情的大胶轮铲车,顺吉桦路西行,一路上的情景触目惊心。横卧在公铁交叉路口的是一列装满煤炭的火车,难以想象洪水是怎样的力量把它从站台冲出几百米,冲出铁轨,倾覆在路基上,挡住了通往重灾区老街、站前街、河北滨江路的通道,给救援带来了极大地困难。口前火车站区一片汪洋,只有候车室上“口前站”三个字依稀可见,平时车来车往的站区,如今行驶的是救人的冲锋舟。我知道,火车站在这个地区地势还算高的,平地与西边和北面的平房区的屋脊在一个水平面上,那里的情况可想而知。还有西面的解困楼、站前街的五七楼等,远远望去,大水都漫过了二楼。
28日夜晚,我是在设在公安局的抗洪救灾指挥部度过的,各地的消息不断汇总,我的心不断地下沉,看来这次洪水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第二天一早,街路上的水基本退了,我翻过公铁交叉路口横着的火车,沿着永吉大街走向单位。这是当时水流的方向,尽管我目睹了涨水的全过程,可眼前的街路仍让人触目惊心,我给中央台的连线报道中用了“满目疮痍”四个字。所有街路两侧商铺的卷闸门都被撕裂了,有的门窗没了踪影;路两边的树连根拔起,软硬覆盖冲成了深沟,地下管线和有的楼房的地基都裸露在外,而每条街路的交叉路口,都漩出了深坑,达三四米深,站前路上一辆查险的大铲车掉进水坑,没过了整个车体;各种机动车横七竖八卧在路边、楼边、河堤、河道,千姿百态,有人在五里河和四间河交汇处不足一百米的河道里细数,竟有37台之多;单位办公楼旁作为景观修建的河堤大部分被冲毁;永吉大桥上的路灯、栏杆没了踪影,桥墩移位,桥面大部分坍塌;我们广播电视机房通向北山发射机房的光缆、电力线路全部中断,道路也全部损毁;整个县城停水、停电、停信号,手机偶尔有一两次可以打通;街上到处是受灾群众,眼神中满是惊恐、焦躁、哀伤、愤怒……
雪上加霜的“原料桶”
29日晚,我在指挥部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永吉开发区新亚强化工厂等两户化工企业的五千余吨、七千余个化工原料桶被洪水冲进了松花江,环保部来了一位副部长,中央台“焦点访谈”也来了。
永吉开发区地处县城东面偏北,近几年招商引资引来了一些现代城市不容、发达地区不要的中小化工企业,虽然建有污水处理厂,可台里的同事从未拍摄到里面运行的画面。我出生地廼子街村孤榆树屯就在那里,每次回乡时看到水田里枯死的秧苗,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论对财政的贡献和创造的价值,这些秧苗“牺牲”值得,可长远呢?
吉林市的朋友告诉我,吉林市江面上一度飘满了蓝色的化学原料桶,有的还在水中不断爆炸,爆出白色的烟雾。吉林市紧急停水,尽管不断有宣传说停水与化学原料桶无关,而且即使化学原料桶破裂也是无毒的,那话只有三岁以下孩子能信。
一定把化学原料桶拦截在吉林境内,这是省里的死命令。不能再像前几年吉化大火之后那样授人以柄,让哈尔滨炒作,让俄罗斯讹诈。一道道拦截,一次次失败,沈阳军区某部工兵团参谋长关喜志在松原架设浮桥拦截时不幸牺牲,黑龙江境内也设立了拦截点。虽然最终没有化工原料桶进入黑龙江,但一时间公众、媒体对打捞化学原料桶的关注度远超过了灾区,尽管灾区还在废墟中呻吟。
迟来的通稿
灾害发生后,准确、及时、透明公布相关信息和最新汇总咨询,是消除谣言最好的手段,也是政府的责任。大水退后,我们一边自救,迅速恢复播出,一边安排采访、准备稿件。感谢我的同事孝义、一歌、刘娇等在大水来临时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大量珍贵的视频资料,小马利用这些资料制作的特别节目片头也很震撼。电来了,线路通了,可我却拿不到一个权威资料,一个可以公开播出的通稿。宣传部一遍遍写,领导一遍遍审,三天多快四天时,我才见到一份四不像的东西。播音员不断拿稿件问我咋念,我说:“按发音念!别管成不成句,别管是否重复,别管数字是否可信,写啥念啥。”
然后就是挨批评,领导找不到记者我和李局就挨批评,可我手里可用的记者远没有领导多。后来索性把记者都派到指挥部宣传组上班,听宣传组调遣,省得挨骂。那以后我再也没看过“通稿”,我在不断寻找典型,挖掘深度报道,与省台、中央台联手,采访播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节目。
感动我的人和事
在工作中,我结识了许多普通的百姓,可就是这些普通的百姓,在洪水到来时有了那么多不普通的故事。
王志敏、王超是一对父子,洪水袭来时他们被巨浪卷走,先是抱住装满空矿泉水瓶子的编织袋,后来抓住了一棵大树,父亲王志敏把儿子托上树,自己泡在水中,九个小时中,对面检察院家属楼上众多的居民在喊话鼓励他们,给他们抛掷矿泉水、方便面。当解放军把他们解救上快艇时,父亲对儿子说:“咱爷俩就算玩一次漂流了。”这个过程被政法委的杨树槐用TV拍摄下来,成为关于口前洪水最热的视频。
43岁的于洪江是口前镇官马山村农民,洪水袭来时,他本来已撤到了安全地带,可听说别的社还有人没撤出来,他开着自家的拖拉机一次次往返,救出120多人,当他第9次载满13人返回时,拖拉机被洪水掀翻,10人遇难,其中就有于洪江。他是家中的独子,我们采访他67岁的老父亲时,老人家说:“我儿子是好样的,他一个人换来120人的命,值得!”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时,这句话打动了无数人。
谣言与疑问
洪水发生以来,谣传很多,有些纯属无稽之谈。
流传最广的是:防汛期间,县领导和某富商出国旅游去了。恰巧,他们说的富商是我的好朋友一平。而实际的情况是,一平利用子女放暑假,和几家朋友去马尔代夫度假。原计划我家三口也一起去,因儿子暑假晚而放弃,都是自费去的。而防汛这些天,县领导都在抗洪一线,我一直在前线采访,没见缺谁。县委书记李长山四天三夜都没合眼,而且都在最危险处,整个人瘦了一圈,很令人感动。
有谣言说某某政府官员被抓起来了,更是没影的事。试想,这样的消息是最好的新闻素材,我能放过吗?
有谣言说某某地一次抬出多少具尸体,我问过公安局和殡仪馆的熟人,没影的事儿。
有谣言说没通知撤离。我老家的村子大部分房子淹没在水中,可没人伤亡,在洪水到来前,政府通知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还有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俊红去镇西村组织转移时,被困在一个水塔上,十几个小时后被救。这说明是通知了,其他我不清楚。
谣言止于智者,可有些疑问如鲠在喉。
“东北的水文甚至东北的历史记载有1600年吗?”媒体和材料不断出现“1600年一遇洪水”的说法,根据何在?
“究竟死了多少人?”我知道没有传说那么多,也没公布的那么少。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为何就不能实事求是呢?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水?大水为何来的快退得快?小水利何以变成大水害?”这次洪水中,20座小型水库、386座塘坝损毁。这些小水库、小塘坝由谁来监管,防洪由谁来负责?
…… ……
洪水已经过去,关于洪水的话题还会继续。关于7.28特大洪水,截止目前官方的最新统计是:“7月26日晚,全县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局部最高降雨量12小时达290多毫米,多处山洪暴发,二十座中、小型水库受损严重。9个乡镇、一个开发区、136个村、682个自然屯受灾,受灾人口28470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6万公顷,绝收13820公顷。倒塌房屋16775间,水毁道路316.81公里、桥涵1006座,已确认39人遇难,31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6.7亿元。”
2010年7月30日---8月10日于三惜草堂
◆此文刊登于《北方传媒研究》2010年抗洪特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