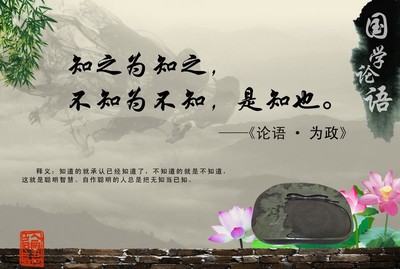若干年前,龙应台女士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讲演后回答问题,有中国留学生问她是否视中国为其“祖国”,龙应台用英语答以“中国文化是我的祖国(motherland)”。这话激起国内杨姓学者严厉反驳:龙应台“没权力把中国与中国文化割裂开来”。杨先生写了篇文章,《龙应台,“中国文化”怎能是您的“祖国”?》,一时在网上流传甚广。
杨先生似乎以为这类说法是龙应台首创,其实,这种认语言或文化为“祖国”的态度,在欧洲久已存在。例如,2008年10月16的《南方周末》曾登过当年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一句有趣的话。获奖之前,他在接受《今日法国》(LabelFrance)杂志的访谈时说:“〔另一面是我热爱法语,〕法语可能是我唯一真正的国度。”
追根溯源,让这一态度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开始流行的,当是一位德国人——二十世纪有数几位最伟大作家之一、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干杯吧,托马斯·曼!》。内中说:“托马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回答:‘Woich bin, ist Deutschland。’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曼确实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德国文化就在我身上”。
曾有评家曰:如果说乔伊斯就是爱尔兰和英语,如果说普鲁斯特就是法国和法语,那么托马斯·曼还在德国和德语之外。历史上,欧洲德语区的范围远在今日德国政治疆界之外。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发端于德语区。经过百年内战,德语区北部以新教为主,南部则仍然是天主教的地盘。北部经济发展较快,按马克斯·韦伯的观察,就是新教精神有助于资本主义。但南部维也纳等城市却保留着更为精致的文化氛围。曼出生于德国北部中产阶级家庭,但他在南部慕尼黑读的大学,他喜欢德国传统的文化。托马斯·曼的得了诺贝尔奖的名著《魔山》(DerZauberberg),开篇就是男主角汉斯·卡斯托尔普坐火车从北部家乡南奔瑞士(德语区)的“魔山”——从象征意义上讲,就是自新教地区赴天主教地区文化“朝圣”。曼的作品,涵盖了整个德语区。
希特勒可以用暴力加宣传吞并奥地利,用武力吞并法国和捷克斯的德语区,但他也没能吞下瑞士。托马斯·曼的小说,却在德国本土之外,征服了这些地区的人心。
托马斯·曼这一“文化重于国家”的思路,大概基于“文化德国”远大于“政治德国”的现实;成形的契机,则在德国一战失败的乱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曼还是很讲爱国主义的,坚定地站在德国政府一边。战争失败,王朝倒塌,德国成了共和国。曼担心民主、自由这些西方概念(来自德国之西的英国和法国)会污染德国文化,以歌德、叔本华、瓦格纳和弗利德里希大帝等为代表的德国文化传统,将被淹没在民主制的庸人政治中。1918年,在德国正式投降前一个月,托马斯·曼出版了《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Betrachtungeneines Unpolitischen)一书,试图在政治德国之外,划出一个诗歌、哲学和音乐的文化德国,一个他仍然可以寄托心灵的德国。
魏玛共和国早期的良性实践,使曼逐渐改变了看法。他从高呼“我要君主制”,转向接受民主。按后来的政治正确标准,《反思》是一本反民主的“反动”书籍,但是,曼本人从来没有否定过这本书。《反思》清理出来的文化、政治两分法,在二战中成了托马斯·曼对抗纳粹们在德国大搞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思想武器。
其实思想的嬗变可以更为错综迷乱。曼的“反思”,或许正来自民族主义的文化基因。托马斯·曼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德国文学集大成者。当时德国文学有两大流派,一是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尼采/瓦格纳民族神话崇拜;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托马斯·曼的作品,贯通着现实主义,却也融汇了神话故事。如果从神话角度来看,先民对幻想和现实、梦境和现实、文字描写和现实的分割,并没有我们现今这般“科学”。能运用神话性思维的人,说出“我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并不那么奇怪。我国志怪故事中,比如《聊斋》,秀才也会读书读进书中之境,与仙女一夕销魂——蒲松龄可是当真事来记录的。
龙应台是留美文学博士,学成后曾在瑞士和德国居住、教书。她知道托马斯·曼的观点,实在很正常。杨姓学者说:有些人声称“只有中国实行西式民主之日,他才能‘爱国’。我认为,这是可耻的言论”。其实,托马斯·曼所秉文化之重,超越了政治分野。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只要不尊重文化甚至摧毁文化,他就坚决反对。
龙应台反对陈水扁政权“去中国化”;同时她也尖锐指出,“其实中国大陆‘去中国化’更甚:“社会运动频仍,把中国的传统伦理也割裂了。‘紊革’对原来讲究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影响?它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化里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里,庶民所信仰的‘头上三尺有神明’——儒家的说法就是“修身慎独”——民间宗教是行为道德的基础,也在各种社会运动中受到极大冲击。宗教长期被简化为‘迷信’。所有这些,才是全面性的、渗透性的‘去中国化’,远比台湾的‘正名’运动要彻底多的多。”
龙应台讲到中国文化时,她说的是不要在婴儿奶粉里掺假放毒、不要用地沟油煎油条、不要在大学自主招生中收“条子生”、“头上三尺有神明”这样的道德警诫。此般文化-道德要求,能用“爱国”或民主来驳斥吗?
经过长期的内战和分裂,北面的大陆有政治优势,南面的台湾却保留着更为精致的传统文化氛围。画家陈丹青访问台湾后,曾在《台湾的文艺家》一文中感叹:“一来二去,总觉得这些同文同种的同行和我们有点异样。”这就是两岸文化人在文化上的点点不同了。
海外华人学者其实早有“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提法。余英时先生写于1997年的《陈寅恪研究因缘记》中说:“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见的区别。”余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批评大陆某些学者在所谓的“陈寅恪热”中,将文化与国家混为一谈。
不过,龙应台和克莱齐奥的出国家入文化,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两个各有特色的群体。一是流亡者,特别是被俄国和德国当时的专制政权赶出国的,单是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有德国的托马斯·曼,俄国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约瑟夫·布罗茨基,波兰的切斯拉米·米沃什(后两位是在美国获奖)等。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更有大批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学者来到西方。政治上,他们不认同母国的专制压迫,同时对西方政府也多有批评。但在文化上,保留母国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放开襟抱接纳西方文化。很自然的,对他们而言,文化就比政治更有份量。
这批学者里,国人比较熟悉的代表人物,当数已经去世十年的爱德华·萨伊德教授。他于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单看标题,以萨伊德的巴勒斯坦背景,似乎该是批判西方文化如何为帝国主义保驾护航。其实萨伊德在书中猛烈抨击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痛斥伊拉克的萨达姆那流领导人,他们在“爱国”的旗号下肆意践踏法制和人权。母国的政治令人失望,萨伊德只能倡导文化“移民”。他说:虽然帝国的扩张给弱势民族带来过种种灾难,但是,时至今日,不管是曾经站在帝国一边的人,还是曾经站在抵抗一边的人,都应该把这段历史作为共同的历史。不管是历史上的帝国文化还是抵抗文化,今日已汇合为我们的共同文化。
第二个群体是“混血”者,这里的“混血可以是生理上的,也可以是文化上的。“混血”者往往也是流亡者。克莱齐奥曾说:他在法国经常感到自己是外人,大概因为他的出生于毛里求斯的背景。而且,虽然克莱齐奥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却是英国人。托马斯·曼也有外国血统,母亲是巴西人。萨伊德是阿拉伯人,却是基督徒,自幼就读于英国学校。
专制制度的辩护士可以声嘶力竭吼叫: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但当代的社会现实却表明,没有了祖国,你可以活得好好的;有才具者甚至长成为大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