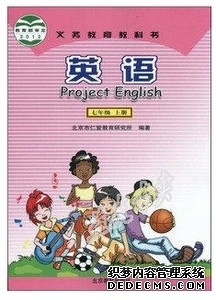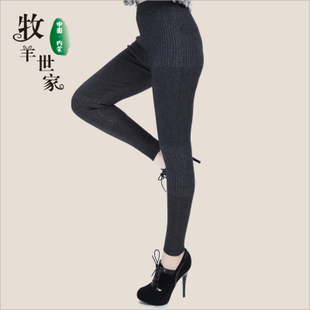同义词条:元朝宗教
目录[隐藏]
1佛教1.1元代佛教的发展
1.2曹洞宗和临济宗
1.3白云宗和白莲教
1.4佛教典籍
2道教2.1对道教势力的打击
2.2朝廷管理道教
2.3著名道教人物
2.4道教的传播
3伊斯兰教3.1伊斯兰教的起源
3.2元代伊斯兰教的发展
3.3清真寺
4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4.1聂思脱里教
4.2天主教与东正教
4.3犹太教
4.4摩尼教
4.5湿婆教
5萨满教5.1萨满教的信仰
5.2萨满教的崇敬对象
5.3火在萨满教的地位
元代宗教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都采取开放的政策,加以优待和提倡,唯独禁止白莲教和弥勒教,因为这两种宗教在民间秘密流传,已成为农民进行反抗斗争的工具。在这种政策之下,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部得到很大的发展。
编辑本段
佛教
元代佛教的发展
蒙古统治者最先接受的佛教,似为中原汉地的禅宗。1214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禅僧海云当时只有13岁,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1242年,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蒙哥汗时期,中原佛教势力迅速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大致在此前后,吐蕃佛教(通常称为喇嘛教)亦开始渗入蒙古宫廷。元代佛教各派当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白莲教等教团,在南方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徒众。
至元初,元政府设总制院以掌浮图氏之教,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
在江南地区,初置诸路释教总统所领佛教事。至元二十八年立江南行宣政院,治杭州,不久遂立总统所。此后,江南行宣政院迭经废置。至顺年间废行院,立广教总管府于各地,凡16所,隶于宣政院。府设总管,以僧人为之,又设达鲁花赤一职,僧俗并用。元统二年(1334),又废广教总管府,复置行宣政院于江南。地方上的僧官有僧录、正副都纲、僧正等,一般由政府任命僧人担任。度牒出家须由官府批准,实际上私度僧尼也很普遍。据宣政院统计,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有寺院24000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凡21万余人。
元代设有帝师一职,领宣政院事,既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也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帝师的法旨行于全国各地僧寺。帝师而外,元廷还封若干“西蕃僧”为国师。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到吐蕃延请僧人为“王师”。出身于唐兀族的吐蕃僧人杨琏真迦,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见于记载的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节思朵、积律速南巴等人,都是吐蕃人。吐蕃佛教僧人凭借其政治势力,在内地据有不少规模很大的寺院。一些吐蕃僧人以传授“房中运气”的“大喜乐”、“秘密法”之类,向蒙古宫廷取媚固宠;同时在中原、江南等地也化度了少数信奉者。
总的来说,在内地流行的佛教,基本上还是从宋、金流传下来的各派。
宋代寺院已经分为禅、教(指天台、法相或称唯识、贾首或称华严等宗。
元人把各派特点扼要归纳为:“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入元以后,禅僧德辉于1265年重编《百丈清规》(此清规最初由初创禅院的唐代后期僧人百丈怀海制定);律僧省司等编成《律苑事规》(成于1325年);教僧自庆编成《增修教苑清规》(成于1347年)。三类寺院的内部规定,都进一步制度化,“固各守其业”(《元史·释老传》)。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廷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即大都)问法”。据《佛祖统纪》,这次廷辩的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但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社会,此后最为流行的仍然是禅宗中的曹洞和临济两家。
曹洞宗和临济宗
曹洞宗在元初北方势力较大。著名的万松行秀(1166-1246)在金元之际成为出入于儒释之间的北方文士领袖,他著述甚富,《从容庵录》6卷为其举扬曹洞宗风的重要代表作。万松弟子福裕(1203-1275),后来在西京主持少林寺。福裕一系,乃是元代曹洞宗的主要继承者之一。
临济宗的传播最广。北方的临济宗以海云印简(1202-1257)一系最为有名,因而后来被元廷封为“临济正宗”。南方的临济宗,宋元之际亦大盛。雪岩祖钦(?-1287)、高峰原妙(1238-1295)、中峰明本(1263-1323)师徒相继,阐扬宗风。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有元一代禅僧的代表人物。元朝统一云南以前,在大理白人及汉人中流行的佛教,“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在云南,密教僧人称阿叱力(或阿阇梨,梵语Acarya的音译),或称轨度僧,有妻子。至元中叶,禅僧雄辩(善阐李氏)、大休相继归滇或入滇,当为云南传入禅宗之始。其后,有云南僧人玄鉴东来,问法于中峰明本,“一闻师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图归以介道,而殁于中。吴鉴之徒画师像归国南诏”。“至中庆城,四众迎像入城,..由是兴立禅宗,奉师为南诏第一祖”。据陈垣先生考证,玄鉴初访中峰后曾经返滇。后又重访中峰,以至于死。玄鉴原是教僧,访明本后改教为禅,遂成为云南禅宗第一祖。此后,阿叱力教虽在云南继续长期存在,但禅宗势力也开始在云南发展起来。
元代的教、律各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僧人。如天台宗的玉冈蒙润(1275-1342),华严宗的真觉文才(1241-1302),法相宗的普觉英辩(1247-1314)、云岩志德(1235-1322),律宗的光教法闻(1260-1317)等。临坛大德律师惠汶(1260-1232)传戒法于河北等地,“两河之间、三监旧邑,从化者盖以万数。锱素相率而求戒法,幢幢接迹于途”。
白云宗和白莲教
由佛教派生出来的两个道门,即白云宗和白莲教,在元代也拥有不小的势力。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1043-1121)在杭州白云庵发起的一个教团,提倡素食念佛,所以又称白云宗。它援引天台教义,攻击禅宗,在宋代一直被当作异端而受到禁止。入元以后,白云宗为政府承认,得以公开活动,势力发展很快。其中心在杭州普宁寺。延祐七年(1320),复被官方作为异端邪说取缔,此后逐渐绝迹。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其创始人为南宋初年的吴郡昆山僧人茅子元。他所创立的白莲教并不要求门徒出家,可以娶妻生子,在家出家,所以在下层社会中得到迅速的传播。至十三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处处有习之者”,并在宋亡之前已经传到了北方。
元代白莲教的发展比较曲折。元朝统一后,一部分白莲教徒在杜万一的领导下,于宋亡后次年曾举兵起义。起义失败后,白莲教仍然取得合法地位。庐山东林寺在元成宗时一再受到政府的封赏,从而推动了该教在全国的空前规模的发展。但元政府内部对白莲教一直存在两种意见。因一些地方白莲教徒的骚乱活动,武宗在继位之初(1308)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元史·武宗纪》)。后因镇江妙果白莲寺和尚普度赴大都,通过国师感木鲁(即哈迷立)人必兰纳识里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活动,并为此上书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下旨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地位。这时其信徒不但有下层百姓,还有社会上层人士。寓居大都的高丽国王也皈依白莲教,并在其国内创建寿光寺白莲堂。但英宗即位后,又于至治二年(1322)下令限制白莲教的活动。在民间,白莲教徒的数目一直不断增加。到元末,白莲教为红巾军起义所利用。
佛教典籍
元代佛教典籍的流传,颇具时代的特点。吐蕃藏经在这时传入内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汉译佛典重译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直接译自梵文。由是出现了对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进行比较研究的目录学著作,即吉庆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0卷。同时有部分藏文佛典在这个时期译为汉文,被吸收到汉文藏经中。武宗时期,继八思巴字创制、改进之后,由大德29人译藏文经藏为蒙文,可惜其刊本今已不传。在汉文藏经的刊印方面,至元时期,元政府对金代传下来的大藏经板(系以北宋版大藏经为底本雕造)加以校补雕,刊印36藏,颁行各方。白云宗僧人、杭州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发起刊刻的藏经称为普宁寺本,6010卷。自宋季开始雕造的碛砂版藏经也在元代完成,共6300余卷。据新近发表的资料,元代后期还曾刊印过官藏。 编辑本段
道教
宋室南迁后,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蒙哥时期改名为太真)、全真等诸派及浑元教等。其中正一为宋以前旧教派,而全真等则为宋室南渡后北方新创教派。
全真道由道士王喆于金朝中期所创,追随他为发展全真道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其七大弟子。全真教宣扬道、儒、释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金末元初,全真道及时投效蒙古统治集团,因而后来居上,获得了比太一、大道诸教以及佛教、儒学等远为优越的地位,以至能在三四十年内在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的局面。蒙哥在位时期发生了两次佛道辩论,全真道士两次遭到失败。其结果不但使道教的地位降至释教之下,而且也稍稍改变了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的状况。全国统一以后,活动于南宋故土的旧道教符箓各派继续流行于江南各地;在北方传播的仍然是全真、真大等教,而以全真道的势力最大。
对道教势力的打击
道教势力在世祖至元年间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蒙哥时曾勒令道教归还被他们霸占的佛寺二百余所。到至元十七年,“僧人复为征理”。据释教声言,全真教徒殴击僧徒,诬僧人纵火,声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这场官司仍以道教失败告终,全真道士被诛杀、剿刖、流窜者达十余人。释教乘势要求朝廷追究曾经蒙哥禁断、但尚流行于世的道教伪经。元廷遂于次年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偕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人,会集长春宫,考证道藏诸经真伪。释道辩论达数十日之久,结果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经典悉被判为伪经。释教敦促朝廷再次下令焚经,忽必烈说:“道家经文,传论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他命令道教诸派各推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张宗演等人惊慌失措,承认“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忽必烈于是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诸经一概焚毁,并禁止醮祠,遣使晓谕诸路遵行。这次打击,祸及南方道流,其影响超过蒙哥时局限于北方的焚毁道藏之举。不过,《道德经》外,“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的诏令,并未完全执行。由于正一道人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恳请,道经中之“不当焚者”或“醮、祈、禁、祝”等仪注皆得保存。忽必烈末年,又撤销对醮祠的禁令,“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当时由于桑哥等权臣沮遏,这道诏旨只在京师公布,“而外未白也”。成宗即位以后,又将它重新颁行天下。道教这才从焚经厄运中喘过一口气来。 朝廷管理道教
自蒙哥时候起,全真、真大、太一等教门宗教领袖的掌教地位均由朝廷任命或加以承认。入元以后,更由此发展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国朝之制,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单,得行文书,视官府。”各宗掌教的人选,由本宗上层推定后经皇帝批准赐印,有时也直接由皇帝委派本宗中深孚众望者担任。在南方,世代居住在龙虎山的第三十五代正一天师张可大,南宋季年已受敕提举三山(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箓。忽必烈攻鄂时,他曾对来访的蒙古秘使预言“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忽必烈灭南宋后,对可大之子,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倍加宠渥,命其主江南道教。此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也都经过元廷的认可,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事。成宗时,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又受封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江南道教符箓各派遂正式并于正一道门之下。正一天师就是正一掌教。惟元廷仍许其住在龙虎山,不像北方三派掌教“必得在禁近”。
元政府除了对各派掌教竭力加以控制外,还设置专门机构,对“教法”
以外的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与道教之间关系的各种有关事务加以干预和管理。在中央,以道教隶集贤院;地方上各教门,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元代道官主要有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道官虽多由道士充任,但一般由政府任命。地方上的道官衙门和宫观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著名道教人物
元代道教人物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长春真人邱处机。邱处机是全真道创始人王喆七弟子之一。他曾奉成吉思汗召请,远赴中亚。他死后,全真掌教尹志平(1169-1251年)、李志常(1193-1256)在促成本宗的全盛方面显示了经营大家的才干,在他们的主持下,全真道进行了几项大规模的活动。其中包括为邱处机举行显耀的葬礼;大兴土木、广建宫观,乃至筑道院于和林;在终南祖庭会葬祖师王喆,并扩建重阳万寿宫;刊行道藏;在广度门徒的同时,竭力争取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另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是真大道第九传掌教张清志。在八传掌教岳德文死后,张清志归丧大都天宝宫,“丧毕潜遁”。数年后为徒众推举,曾任掌教。因不堪谒请逢迎而隐去。后因找不到合格的继任者,朝廷遣使寻访,给驿致之。张清志度不可辞,只得入京,但他舍所赐驿乘,徒步赴京。到达大都以后深居寡出。贵人达官来见,常告病不出,但对于社会贤良却宁愿徒步去见。随着元廷对道流的利用和笼络,其上层率多趋炎附势,肆行威福,早已忘记了刻苦自励、淡泊寡营的标榜②。张清志的行止,与他的同道相比,应该说还是高出一筹的。
由相传为张道陵后裔世代相袭的正一道天师的居处龙虎山,宋代已成为官定的正一道祖山。元代正一道另外还有两个著名人物,即张留孙(1249-1322年)、吴全节(1266-1346年)师徒。张留孙,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学道。正一天师张宗演奉忽必烈之命北觐时,选留孙等从行。与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派别不同,正一诸派都持符箓念咒作法,大概更容易得到蒙古贵族的信从。元廷选正一道士留住大都,诸人以“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中”。最后留下了奏对称旨的张留孙。张留孙以法术为皇室驱邪禳灾,渐受眷隆。至元二十五年,元廷以其预议掌管道教的集贤院事,实际上把他推上了南北道教诸派钦定盟长的席位。此后他主盟道坛三十余年,受玄教大宗师印,视二品,领集贤院事,位大学士之上,进入元代品秩最高的道官之列。张留孙死后,至元年间由他推荐入京师的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吴全节深通儒术,在“学问典故”方面一直是张留孙的顾问。张留孙、吴全节与朝中许多较有地位的儒臣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除主盟道教外,他们亦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议国政,“国家之政令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这个阶段,正一道对元廷的政治影响,似乎超过了全真等教派。吴全节死后继任玄教大宗师的是其弟子夏文泳(1277-1349)。
道教的传播
由于蒙古帝国版图辽阔,道教随着被蒙古人征发的汉人传播到遥远的边疆。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阿力麻里的道教徒曾设立三坛。和林城的一所道观“三灵侯庙”一直存在到元末。和林遗址额尔德尼召至今存有至正九年(1339)所立的“三灵侯庙之碑”,参与建设这所道观的有各民族的人。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宝藏》,是由全真道在其全盛时代主持完成的,“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已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即王喆)至李真常(即李志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为了争取道流正宗的地位,扩大传道手段,全真掌教尹志平决定命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藏。前后设经局27处,以管州(治今山西静乐)所存《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搜求遗佚,加上全真道人的著述,一并刊刻入藏。是役起于1239年,告竣于1244年,陆续印造了一百数十部。元刊道藏共计七千八百余卷,约比《大金玄都宝藏》多一千四百卷。可惜道藏刊成后不久,便遭到蒙哥时代和至元十八年焚经之祸。经板和相当一部分经书被毁。明正统道藏《缺经目录》所著录者,绝大多数系因元代焚经而致亡阙。元代南方一些较大的道观,也保存了部分道藏。其来源大都是从两宋幸存下来的《政和万寿道藏》刊本。 编辑本段
伊斯兰教
从唐代开始,伊斯兰教即在留居中国沿海地区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泉州的“圣友之寺”、扬州的礼拜寺(明代重建,今存)及其创建者补好丁(今译普哈丁)之墓(地在今扬州东关对河),都是两宋时期伊斯兰文化的见证。但迄于两宋,其传播规模一直很有限。蒙元时代,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个时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
伊斯兰教的起源
伊斯兰一词最早见于汉籍,似为金代,当时译称为移习览。但该词尚未见于元代汉文史籍。伊斯兰教徒,元代一般音译为木速鲁蛮或木速蛮,汉文史籍经常称他们为回回人。
关于回回的名称,元初王恽曾记录“宋克温说”云:“..回鹘,今外五(按即畏兀儿);回纥,今回回;..今人以名不佳,改之”。其实回纥、回鹘在唐代原本是一个概念,只不过使用先后有别。到了宋辽金时代,“回纥”及其另译“回回”被用来专指中亚
人。而回鹘则继续指西迁的那一部分回鹘人,即后来的畏兀儿人。
“回纥”(回回)从指回鹘人转为指中亚人,主要是因为宋朝疆土局限于内地,宋人对西域的了解远逊于唐代。而西迁后的回鹘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所以宋人把途经回鹘入汉地贸易、操与回鹘人类似语言的西域人都视为回鹘人,统称之为“回纥”,即回回。这应是用回回指中亚人的原因。元代中国的版图包括中亚,元人对回鹘人与中亚其他民族的区别甚为清楚,所以“回回”、回纥成为专指西域人的名词,而回鹘、畏兀儿则指唐代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的后裔。
在元代,回回主要指伊斯兰教徒,其所遵行的伊斯兰教法律称为回回法;但回回所指也包括其他西域人,如聂思脱里教徒等。犹太人有时被称为“术忽回回”,信奉东正教的阿速人被称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为“罗里回回”等。到后来,甚至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被称为“回回”。但在大多数场合下,回回人还是指伊斯兰教徒。元代徙居中国各地的回回人,是今回族先民的主体。
元代伊斯兰教的发展
元朝境内的回回人主要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任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人,也包括前代即已寓居中士的波斯、大食人后裔。回回构成了色目人中的绝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统治者信用,不少人在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担任要职。他们在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中统四年户口登记时,中都(即后来的大都)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当然,更有大量的回回下层即工匠、平民等被括入官府或诸王贵族的匠局,从事纺织、建筑、兵械、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例如专造纳失失的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南洗马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时期以回回人匠三千户建置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干人。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于是造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回回人都固守伊斯兰教教规,“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
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元政府的宗教兼容政策,促成了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按照“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原则,元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阿拉伯语Qadi意为法官)领之,依回回法掌本教门的宗教活动、回回人的户婚钱粮等词讼以及部分刑名之事。仁宗即位以后,“罢回回合的(按即哈的)司属”(《元史·仁宗纪一》),下令“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根据上引史料,回回哈的司在“外头”有“设立来的衙门”,也就是说,它曾在各地设有相应的地方机构。它们应当是由各地的回回大师或掌教哈的主持的。皇庆以后,回回哈的司所属各地方机构当在革罢之列,元廷企图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哈的大师的职掌被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到文宗时候,又有“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元史·文宗纪一》)。伊斯兰教在元代虽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间流行。此外,出嫁或者被卖给回回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男女,当亦有一部分信奉了伊斯兰教。元朝移居西北的蒙古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先后改宗伊斯兰教,而居于汉地的蒙古诸王贵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则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忽必烈之孙阿难答。阿难答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是回回人的聚居地。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剌,以使他向封领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至元十七年他嗣位为安西王后,使所部15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
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明史·西域传》)。伊斯兰教很早就分裂为若干派别。现存元代描述内地穆斯林的史料多出自汉人之手,对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似乎注意不多。但如果我们仔细搜寻,仍然能发现一些资料,可反映元朝境内伊斯兰教各派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泉州“圣友之寺”中回历710年(1310-1311)的阿拉伯文题铭提到,愿安拉“宽恕阿里派者,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这说明泉州有什叶派活动,很可能“圣友之寺”就是一所什叶派清真寺。此外泉州的穆斯林有崇拜灵山圣墓的风俗,与苏菲派教义吻合。根据伊本·拔图塔的叙述,神秘主义和苏菲派在元代业已传入中国。元代穆斯林中常见的术语“迭里威失”(darvish)也是苏菲派所特有的。
从公元十世纪起,波斯语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时代中亚已经普遍使用波斯语了。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在哈刺和托回回寺遗址发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年圣旨碑后有一行异域文字,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蒙古国故都和林也有一块立于1339年的波斯文碑。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辞,如答失蛮(danishmand,指回回文人)、迭里威失(darvish,指苏菲派托钵僧,与之相应的阿拉伯语为faqir,未见于元代汉籍)、纳麻思(波斯语namaz译言礼拜,相应的阿拉伯语为salat,亦未见于汉文史籍)等。
清真寺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反映。入华的回回人很早便开始建寺。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入元以后,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最古的清真寺是广州的怀圣寺。大食人苏莱曼公元九世纪中叶到广州时,已看到那里有清真寺。南宋岳珂10岁居广州时(十二世纪末),怀圣寺已立于珠江边。元至正十年(1350)所立之《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也提到此寺建于唐代。泉州也是清真古寺较多的地方,据那里的“圣友之寺”大门甬道北面石墙上的阿拉伯文题记记载,此寺建于回历400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1010);据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载,清净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
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上述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之寺”、清净寺在元代都得到维修。元末吴鉴的《重立清净寺碑》提到,“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现今发现的泉州清真古寺遗迹除了上述“圣友之寺”和“清净寺”以外,还有涂门外津头埔的所谓“宋也门寺”、南门的所谓“元穆罕默德寺”、东门外东头乡的“元纳希德重修寺”和所谓“元无名大寺”等。此外大都(北京)、杭州、扬州、定州、开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所建的寺院。俄国人柯兹洛夫等人还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发现十四世纪的礼拜寺址及波斯文残碑,蒙古国都城和林遗址的1339年的波斯文碑,提到了当地的经学院。这些都证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元代从陆路和海路入华的回回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入元以来,回回人继续从海路入华,并定居于沿海港市。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合马,即为耶路撒冷人。与从陆路入华的回回人不同,他们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阿拉伯色彩。近数十年来在泉州发现了许多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①。在其他地方也发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广州怀圣寺的元末的阿拉伯文碑铭、扬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惟此类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至正年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提到了清净寺内的四种教职:“..摄思廉(shaikhal-Islam),犹华言主教也;..益绵(Amin?Imam?),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Mutawalli),犹言都寺也;谟阿津(Mu’azzin),犹言唱拜也。”
为阿拉伯语的音译,与沿陆路入华的回回人习用波斯语明显有异。泉州的“圣友之寺”在建筑上表现出明显的大马士革风格,与中国境内众多的汉式清真寺截然不同。
编辑本段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
聂思脱里教
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0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发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首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chdeacon)拜泥(Bayniel)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动。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员专门管理。元代聂思脱里教虽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来与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发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
天主教与东正教
元代罗马天主教与中国已有接触。蒙古西征远达东欧,使罗马教廷为之震动。法国国王和教廷曾遣使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的政府。此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着。蒙古西征中所掳回的战俘、军队、工匠等人口中有一些西亚、东欧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汉地,他们信仰的宗教也随之东来。不过,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聂思脱里教派。
1294年,孟特·戈维诺等人受教廷派遣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努力活动,使罗马天主教赢得了一批信徒。经孟特·戈维诺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6000人。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几个天主教堂。随蒙古军东来定居于大都的阿兰人原来信奉希腊正教,这时也皈依孟特·戈维诺,其人数在三万以上。汪古部部长阔里吉思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在孟特·戈维诺影响之下,率很大一部分部众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当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但他的行为遭到其兄弟的反对。在阔里吉思被西北叛王都哇俘杀后,那些改从天主教的汪古部众又重新被聂思脱里教派所争取。1307年7月,罗马教廷继委任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暨全东方总主教之后,又派遣了一批教士来中国,其中热拉德(Gerard)、彼列格林和安德鲁(Andrew)三人抵达中国。
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大主教阙任。一部分在大都的阿兰显宦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来。这件事发生在元顺帝在位时。实际上,罗马教廷后来任命的大都大主教,始终未曾抵达大都。
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住有若干天主教士。
现代在扬州发现了1342年拉丁文墓碑,证明当时该地确有天主教士在活动。鄂多立克所言不诬。泉州是天主教在江南的活动据点。自十四世纪初开始,即由孟特·戈维诺向该地派遣主教。自此至元末,担任泉州天主教主教之职者,先后为热拉德、彼烈格林和安德鲁。他们受到当地富裕的天主教徒慷慨赠予和友好接待。安德鲁死于1326年,葬泉州。他的墓也已在泉州发现。
孟特·戈维诺曾经翻译了部分天主教经文,但恐怕不会是译成汉文。聂思脱里教的文献,据十三世纪末叶阿儿马尼及Nisibis京城大德著录,共存三百余种。但迄今为止,除了敦煌发现的唐代景教文献的汉文译文以外,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有哪一种曾在元代被译成汉文。这个事实也有助于伯希和的下述论断,即元代的基督教,大致可以说不是汉人的基督教,而是阿兰人、突厥人以及少数蒙古人信仰的宗教。
犹太教
犹太教从宋代起,就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定居在今开封。他们把自己的教士称为“满剌”,把希伯来文老师称为“五思达”,这两个词分别是波斯语mulla和ustad的音译。由此可见,他们应来自波斯或中亚,可能是落籍不归的西域商旅的后裔。这部分犹太人在开封有自己的社区,保存了自己的宗教“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金代大定三年(1163)开封的犹太人在俺都喇(’Abdal-Allah)的组织下开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犹太教教堂。清代发现的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碑文中提到,开封犹太人曾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重建古刹清真寺”,即上述始建于金代的祝虎院。元代这座重建的犹太教堂“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丈”。开封的这所“祝虎院”中供奉着数部手抄《摩西五经》的古羊皮卷本。开封的犹太人在元代似未产生什么重要的人物,大约他们并没有与混在随蒙古军东来的回回人中的犹太人发生很密切的关系。
犹太人在元代被称为术忽,或主吾,与“祝虎”同为波斯语Juhud(意为犹太人、犹太教徒)的音译,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术忽回回。蒙古人并不注意区别回回人中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把他们视为一类人。在一般情况下,蒙古人对回回人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干涉。但这种宽容的政策以不损害蒙古统治的尊严为限度。
回回人和犹太人以抹喉法宰羊,而蒙古人则采用开膛法屠羊。从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观点看来,以蒙古开膛法宰杀的羊不洁,故他们不肯吃蒙古人做的饭。这种态度引起蒙古朝廷的震怒,成吉思汗曾下旨斥责他们,声称西域诸地均为蒙古征服,绝不允许西域人不食蒙古“茶饭”,并禁止以回回法抹杀羊只。在元朝政府任职的回回人、犹太人和斡脱商人为数很多,势力颇大。成吉思汗的法令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他们乘驿旅行时,往往还是不肯吃站户按规定为他们宰杀的羊,“非自杀不食”,沿途骚扰,百姓叫苦不迭。至元十六年,一些西域人从八里灰、吉里吉思地区来到内地向元廷进贡海青。因途中不食蒙古站户预备的饭食,要自行宰羊,引起站户不满,事态扩大。忽必烈下旨严斥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这种行为。在杭州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他们中有许多在砂糖局中供职。大约是蒙古西征时带来的一批掌握制糖技术的犹太人。这部分犹太人的后裔在明代仍然在杭州生活,并在那里也建了一所“祝虎院”,即犹太教会堂。
摩尼教
摩尼教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安史之乱”以后传入漠北回鹘汗国。回鹘因协助平乱有功,成为内地摩尼教的保护者。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以后,回鹘人把摩尼教带入今吐鲁番一带地区。内地的摩尼教虽遭唐政府禁断,但并未绝灭,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流传。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称为“明教”。元代泉州华表山建有摩尼草庵,庵中塑有“摩尼光佛”像,明末何乔远在其《闽书》中曾有著录,此寺至今犹存。明教在元代得到政府的承认,但元廷对波斯传来的明教和聂思脱里教并不详加区分,曾命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温州也是一处摩尼教徒集中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潜光院”,是一所明教寺院。元末陈高曾经提到它,并指出“瓯闽人多奉”明教,教徒们“斋戒持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持诵膜拜”。有一些知识分子学习明教经典,隐居于此。明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旨禁“左道”时,明教与白莲教、白云宗同被禁止。洪武七年公布的明律重申了此项禁令。但摩尼教并未因之绝迹,泉州的草庵仍受到官府的庇护;而建宁的明教寺院也直到弘治二年(1489)才为当地知府拆毁。 湿婆教
元代文献中未发现有关湿婆教(印度教)的记载。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泉州曾多次发现元代湿婆教雕刻遗物共200余方,特别是近年来屡有新发现。1984年底,学者们在泉州通淮门城墙附近发现一方湿婆教石刻。该石呈长方形,体积为47×57×22厘米,石质为辉绿岩。其主体部分刻成屋形方龛,龛顶正中为一钟形纹饰,屋脊顶层饰有狮子头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层相迭的莲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状磨盘,承托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塔状磨盘左右各有一神像,头戴宝冠、颈项上饰念珠,腕上套有镯环,以同样姿式坐在莲座上。这里的神像应为印度教破坏之神湿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状磨盘则应为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湿婆教认为破坏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虽然是破坏之神,但也有创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此石刻属于湿婆教建筑外观饰物,常嵌在内殿的层楼顶上。五十年代初期吴文良曾收集到类似的龛状石。湿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带发现得不少。
1985年以后,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湿婆教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头两方。一方为25×98×98厘米,前后两面各雕有莲瓣及十字形花朵,两侧花朵对称向下垂。另一方为26×86×86厘米,形制与前一块一致。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头很多,都为南天竺式样,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1985年在泉州南门附近发现了希腊式柱头石;1989年在鹿园灵山附近发现了葫芦状柱顶石。另外还在筑路施工中发现过石横枋,两端雕有花纹,左侧有眼镜蛇相交的变形图案,右侧长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边缘雕有科形莲瓣。此石当为廊柱柱头檐之间的横向梁枋。这类横枋1988年还发现过一件。
1956年吴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发现过域外文字的碑铭。后经印度学者和日本学者辨认为泰米尔文。泉州的这些印度教石刻证明元代这里曾经存在着湿婆教寺院。
在泉州活动的湿婆教徒主要应是从南印度的马八儿泛海而来的商旅。马八儿又称南毗国,宋元明时代与泉州的海上联系十分密切。据赵汝适记载,宋末有南毗国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湿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尔文碑文的出土地点。可以设想,时罗巴智力干父子,是当时居于泉州的湿婆教徒社团中。
编辑本段
萨满教
萨满教(Shamanism)是原始巫教的通称。此名最早的汉译见于南宋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据载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变通如神”,其国人称之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清代通译为“萨满”。《新唐书·黠戛斯传》载黠戛斯人“呼巫为甘”(甘,唐音Kam),此即麻合木·可失合里《突厥语辞典》著录之qam(意为萨满)。《元朝秘史》所记蒙古巫师之号为“孛额”(bo’e),译为“师公”、“师巫”,即男性萨。他们被认为具有能通神灵的超自然力,经过一番装神弄鬼的宗教仪式,显示神灵附身,宣布神灵对所求问之事的回答。卢勃鲁克根据其在和林的亲身见闻记述了蒙古巫师的请神情况:“他们在夜间把想求问魔鬼(神灵)的人集合在他们的帐幕里,并把煮熟的肉摆在帐幕当中。做[请神]祈祷的那个巫师(cham-kam)开始反复念咒,并用手里拿着的鼓猛烈地敲打地面(即跳神动作)。终于他进入发狂状态,并把自己绑起来(显示神灵附身),于是魔鬼(神灵)就在黑暗中降临了;给他供上肉食,他就给予各种回答(传神言)。”
萨满教的信仰
萨满教的基本信仰观念是万物有灵。据载,古代蒙古人对日月、水火、山川土地等一律崇敬,在进食以前(特别是早晨),把食物和饮料首先供献给它们。正是出于萨满教的这种自然崇拜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是头顶上的“长生天”(MongkeTenggeri)。“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知着。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人们知道天意,一是由能与天神通言的萨满(孛额)传示,一是通过占卜。志费尼记载说,他“从可靠的蒙古人那里听到”,当铁木真收服诸部、事业鼎盛时,出了一个人,此人常在严寒中赤身露体走进荒野和深山,回来宣称: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名他为成吉思汗。”蒙古人把此人叫做“帖卜·腾吉里”。
《史集》记载,此人就是晃豁坛部族长蒙力克(铁木真的继父)之子阔阔出,人称帖卜·腾格理,据说他习惯于在隆冬时节到最寒冷的地方(在斡难--怯绿连之地),裸坐冰上,凝冰被他的体温融化,升起一些蒸气,蒙古人就说他骑着白马上天去。他曾屡次对铁木真说:“最高的主(即‘长生天’)让你统治大地”;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大会诸王群臣时,他又宣示天意说:“最高的主命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据多数学者解释,帖卜·腾格理(Teb-Tenggeri)有“真正天上的”、“极神圣的”之意,以Teb(突厥语Tev)加于“天”字之上,表示“尤其”、“特别”的强调意义,大概相当于汉籍中的“天人”、“神人”。《元史·宪宗本纪》载,宪宗初生时(1209年初),“有黄忽答部(按即晃豁坛部)知天象者,言帝后必大贵,故以蒙哥为名。蒙哥,华言长生也”。此人应即阔阔出,“知天象者”疑即Teb-Tenggeri的汉译。阔阔出无疑是当时蒙古萨满的首领。卢勃鲁克《东行记》中就记载有蒙古巫师能知天象,预言日蚀、月蚀的时间,宣布行事吉、凶的日子,为新生儿预言将来的命运等等。

从《元朝秘史》(第244-246节)的记载看来,成吉思汗建国之初,阔阔出权势甚大,他竟纠集其七个兄弟吊打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又向成吉思汗进谗说:“长生天的圣旨有关于汗位的神告:一次铁木真掌国,一次合撒儿掌国。如果不掩袭合撒儿(把他预先除掉),事未可知。”挑起了成吉思汗兄弟的激烈冲突。后来,“九种言语的百姓”都聚到阔阔出处,连成吉思汗御马所人员和斡赤斤的百姓也有许多投向阔阔出,斡赤斤派人索讨,反遭殴打,斡赤斤本人也被迫向他下跪认错。这样,成吉思汗才决心除掉他,暗示别里古台在角力时把他弄死了。这个事件说明,萨满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萨满首领竟敢与皇室相抗衡。经过这次打击,他们的势力显然被削弱了,但在蒙古人中他们仍居于受敬畏的地位,并且继续以其宗教方式在军政事务中发挥作用,从大汗到一般民众,对由萨满之口所宣示的天意都不敢不遵。汉文、蒙文、波斯文史料都记载,1232年窝阔台从中原北还途中患病甚重,命萨满们(bo’es)占卜,他们声称这是金国的山川之神因蒙古军掳掠人民、毁坏城池而作祟,一定要用亲人做替身才能免祸,结果拖雷代兄承难,喝下萨满念过咒的水而死。拖雷之死事颇蹊跷,很可能是窝阔台利用萨满编造山川之神作祟的鬼话,逼他服了毒水,除掉这个掌握着大多数蒙古军队、威望极高因而危及他的汗位的亲弟。在蒙古历史上,用这种手法害死政敌的事例并不少见。
十三世纪的东西方史料对蒙古人的占卜都有详细记载。《黑鞑事略》载:“其占筮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琵琶。事无纤粟不占,占不再四不止。”据《蒙鞑备录》,其方法是用铁椎烧红钻羊骨扇,视其裂纹以定吉凶,和汉人龟卜相似。《元朝秘史》(第272节)“占卜”作abitlaqu(动词),伯希和谓此字来自于“肋扇”(《秘史》第12,57节:qabirha[r],《至元译语》:合不合儿),即烧钻肋骨为卜;“烧琵琶”即烧钻琵琶骨为卜(肩胛骨,《至元译语》作“答娄”,即蒙语dalu,故占卜者称daluchi);《秘史》(第201、272节)中“占卜”又称为tolge(名词,动词作tolgelegu),是指卜卦用的签子,如小树枝、小棍子之类,故占卜者称tolgechin。耶律楚材所以受到成吉思汗的器重,主要是因为他知天文、善占卜。有一次他准确地测算了月蚀的时间,成吉思汗大为惊异,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间事乎。”于是每次出征,必令他预卜吉凶,自己也烧羊骨以符之。可见蒙古人对占卜的重视。
古代阿尔泰各族都把地和天并奉为最崇拜的神祇。《蒙鞑备录》说蒙古人“最敬天地”,《元朝秘史》中就常见到天地并提。早年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协助下攻打蔑里乞人获胜,感谢他们道:“因罕父和札木合安答的协力伴同,因天(Tenggeri)地(Qajar)添气力,有威势的天神指示着,母亲地神(Ekeetugen)导引着”,才灭绝了仇敌蔑里乞人(《秘史》第113节。又,第255节作otogeneke)。卡尔平尼记载说,蒙古人称其神为Itoga。马可波罗说,蒙古人有神名为Natigay(Nacigay),是保佑其子女牲畜的地神,甚受崇敬;他们各供奉一神于家中,用毡布制作神像及神妻神子之像,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子之口。卡尔平尼的Itoqa和马可波罗的Natigay,当即上引《秘史》之EkeEtugen(一作Itugen,1362年之《忻都公碑》蒙文作utugen)的讹读或讹写。此字和Tenggeri(天、天神)似乎同为古阿尔泰语,相应含有“地神”的意义,古突厥人的圣地于都斤山(突厥文碑作otuken或utugen)亦即此意。蒙古人加上eke(母,这里是加于神祇的尊称),称为“地母神”。蒙古语的udaghan(女萨满)可能就是由此演变来的。
萨满教的崇敬对象
天上的日、月,地上的山、川诸物,都是萨满教崇敬的对象。《秘史》中有Ekenaran一词,即“太阳母亲”(日神);当人们向天祈祷时,要面朝着太阳。卡尔平尼记载说:“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新事,因此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按:其实是神的意义,卡尔平尼此处有误解),并向它下跪祈祷。”这和《蒙鞑备录》所载“其择日行事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月出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见新月必拜”,是完全吻合的。这种信仰在古代阿尔泰诸族中似很普遍,如匈奴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突厥人“候月将满,辄为寇抄”;回鹘可汗徽号之“爱登里”(AiTengri),即“月神”之意②。如同突厥人以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为圣地一样,蒙古人也尊崇其祖先始兴之地三河(鄂嫩河、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Burqanqaldun)。《元朝秘史》(第103节)记载,铁木真早年遭到三姓蔑里乞人袭击,躲进不儿罕山得以脱难。下山后他捶胸告天,感念不儿罕山救了他的性命,许愿要每早祭祀、每日祷告,让子子孙孙都要遵行,说着将腰带挂在项上,帽子挂在手上,捶着胸,向着太阳,下跪九遍,洒奠祷祝了。他和他的子孙无疑都遵守着这个誓言。
据《元史》记载,宪宗二年(1252),始用中原礼乐祀天于日月山,由学士魏祥卿、徐世隆和燕京行尚书省郎中姚枢等率领东平路征召、训练的礼乐人五十多名赴漠北行宫,祭毕遣还;四年,宪宗又“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七年秋“驻跸于军脑儿,洒马乳祭天”。所举行的祭天仪式,当是“合祭昊天后土”,并以祖宗配享(见《元史·祭礼志·郊祀》)。“日月山”应是漠北时代大汗“郊祀”的地方,忽必烈迁都漠南后,就改在桓州西北望祭了。“日月山”显然是汉人给起的名称,今地何在颇难索考。从上引资料看,似应在颗颗脑儿之西或军脑儿附近。颗颗脑儿疑即《秘史》第89节“不儿罕山前的古连勒古山内的桑沽儿小河的合剌只鲁之阔阔纳兀儿”。桑沽儿河即克鲁伦河上游支流僧格尔河;古连勒古山(《亲征录》作曲邻居山)即蒙元诸帝葬地起辇谷,也就是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之源不儿罕山(肯特山)之南派;军脑儿(Gunnaur,深湖)为克鲁伦河上游西著名的“撒里川”(Sa’ariKe’er)中一湖,明人金幼孜《后北征录》载撒里川之地有元宫殿及祭坛遗址。据此则所谓“日月山”似即不儿罕山或其一部分(郊祀处)。无疑,不儿罕山是蒙古人萨满教信仰中极尊崇的神祇(地神?)。
火在萨满教的地位
火,在萨满教信仰中占有很重要地位。据卡尔平尼记述,蒙古人禁忌用刀子接触火,或在火旁用斧子砍东西,认为这样会使火遭到杀害;他们相信火能净化万事万物,因此使者或王公们到他们那里时,都被强迫携着带来的礼物从两堆火之间通过,以便加以净化(卢勃鲁克也有类似记载,并谓所有死者之物也都要用火来净化)。凡“遭雷与火者,尽弃其资畜而逃,必期年而后返”,以为神灵示儆。火还有表示家灶、家产的意义。成吉思汗给家族成员分封民户时,因其叔答里台斡赤斤曾追随王罕反对过自己,准备不给他分份子,博尔术、木华黎和失吉忽秃忽谏道:“这就像熄灭掉自家的炉火(O’er-unqaliyan),坏了自己的帐房一般。”当时蒙古习俗由幼子守家产(诸兄长大后都分出去自立门户),在家庭中拥有特殊地位,故幼子称为“火王”(灶王),意思是掌管家灶(家产)之主,不过此词当时不用蒙古语的qal,而借用突厥语的ot-tegin,音变为ot-chigin(斡赤斤)。蒙古人把ot(女神火)认为是幸福和财富的赐予者,各家各户的保护者,把火炉也看作神圣的地方,因为没有火,家也就失去存在价值了。此外,阿尔泰民族中还有其他一些习俗和萨满教信仰有关,如婚姻、生育、疾病、丧葬、服色等。元朝统治者采用了中原的仪礼制度,但还保留了许多“国俗旧礼”,祭告用蒙古巫觋(萨满)。虽然一部分蒙古人(主要是社会上层)接受了佛教或景教,多数人民仍保持着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和习俗。东北边远各族(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也都信奉萨满教。
分享
词条分类[我来完善]
按学科分类:宗教(综合)原始宗教、古代宗教其他宗教
按行业分类:
按地域分类:
开放式分类:宗教.
注释信息[我来完善]
扩展阅读[我来完善]
1.国学网:http://economy.guoxue.com/
2.白寿彝《中国通史》:http://www.xiexingcun.com/
3.21CN教育:http://edu.21cn.com/
相关词条[我来完善]
元代文化发展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