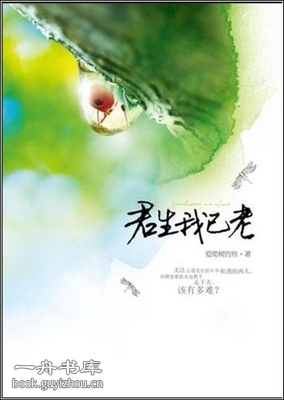我的老班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转业在江西边陲——定南县的老班长联系上了。
老班长原先在北京军区27军军部当兵服役。27军曾是解放军战斗序列中的王牌军之一,南征北战,打过不少硬仗、恶仗,战功显赫。
老班长入伍不久,就被选到军部理发室学理发。理发室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军部机关人员的理发。部队讲究蓄发不得露于帽子外沿,这既是军纪,也是传统。从军首长到机关参谋、干事及工勤人员,基本上每隔半个月都要到理发室理一次发。所以理发室的任务相当繁重而且重要。
表面上看当理发员,整天默默无闻地呆在不足二十平米的斗室与剪刀、电推及头发打交道,在部队不会有没很大的出息,退伍后的就业路子也窄,顶多就是开个理发店,当个理发师。不像在战斗连队,军事训练练好了,能立功受奖,甚至有机会提干带兵,解决“农转非”的问题。所以许多战士不愿干这个。但老班长不这么看。他想,理发室进进出出的都是部队首长,最大的到军长政委,最小的也是参谋干事。别小看参谋干事,翻开军、师、团甚至大军区首长的简历,绝大多数都有在机关干过参谋干事的履历。“宰相府里七品官”,只要理发工作干好了,与首长们熟了,关键时候就不愁没人帮您说句话、办件事。所以老班长也就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学好理发这门手艺。
当上理发员后,老班长因服务技术好,工作细致、吃苦耐劳,深得上下好评,27军的不少首长都点名要他理发。不久,老班长被保送到军直司训营学开车。学成后到基层锻炼了一段时间,不久又调到军部司令部机关小车排,专门给首长开车。别小看给首长开车的司机,他们的能量极大,发展也不同常人。在笔者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看到不少首长的司机,呼风唤雨,人生之路走得十分顺畅,立功、入党、转志愿兵,甚至提干都首当其冲,有的还借助首长的光环走上了师、团领导岗位,即使最不济的也通过首长的关系安排到地方公检法等有关部门工作。
在人生之路走得有些顺畅、得意之时,老班长参加一次同乡聚会时高兴得多喝了一点酒,之后开车不慎出事了,同时也把驾驶岗位也给出没了。老班长感到辜负了首长的关心,没脸在老部队呆下去了,于是通过首长出面,跨军区调到离家乡比较近的广州军区。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曾任过27军军长,因而广州军区司令部军务部的领导就对27军来的同志格外关心。他们征求老班长对工作去向的意见。老班长提出最好能到驻潮汕地区的部队去锻炼锻炼。当年潮汕地区走私现象比较严重,媒体的曝光率较高,名气大,给老班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军务部领导尊重他的选择便开出了介绍信。
潮汕地区原是陆军第55军、1985年以后是第42集团军所辖防区。老班长先后在潮汕地区的凤山部队招待所任过炊事员、饮事班长。一九九0年,成立凤山部队教导大队时,又到教导队二中队当炊事班长。
出身在江西贫困山区、家庭又没什么背景且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班长,是个勤奋之人,也是耿直之人。不同于一般从乡村入伍的老实巴交的战士,他聪明藏于拙愚,机灵隐于木讷之中,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办事老到,不论在哪个岗位,都勤勤恳恳地工作,老老实实地做人,从不给领导出难题,也不给事同添麻烦。因而,领导对他放心,战友喜欢与他交往。
老班长与家属(军人的妻子在部队统称为“家属”)据说是堂兄堂妹关系,可能属于近亲。但在信息闭塞、贫困落后的农村,对这个是不太讲究的。参军入伍后,老班长经过教育的洗礼,才知近亲是不能结婚的,于是提出分手。家属得知后便一纸述状告到部队,说他环境变了,身份变了,想当“陈士美”。部队在婚姻问题上历来保守,特别反感“陈士美”,在这个问题上处理起来也从不讲情面,没有商量的余地。当时因没把控好个人前程与爱情婚姻的关系,在这方面摔了大跟头,断送了原本美好前程的例子不少。老班长惧怕“陈士美”这个恶名葬送了他在部队的发展前程,只好以生存大局为重,与家属结婚了。
老班长的家属在家务农,家境不好,生活负担重,身体又不好。为减轻生活负担和照顾好家人,家属便常常带孩子来部队长住。
按部队规定,士兵实行供给制,家属来队,吃住是不用花钱的。许多家在农村的士兵家属,为减轻生活负担,经常拖儿带女地在部队长住。但家属来多了,住久了,对部队建设不利:一是士兵的心思不能一心扑在工作训练上,一有空就往家跑,带孩子、做家务、陪老婆。二是士兵家属在连队吃饭的开支,是从众多战士的口粮和伙食费中均分出来的。经济上的分子不变,负担的分母不断变大,负担就会加重,整体的伙食就会下降。于是部队规定,士兵家属在部队居住的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三个月,一到三个月就要做工作立马遣走。
老班长所在的招待所主要负责接待师团首长和来这儿办事的工作人员,开支实报实销,增加一两个人的吃住那是小菜一碟。对老班长的家属在招待所长住,单位领导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不太管,只要老班长把本职工作干好就行。
部队特别是野战部队讲究乡党关系。可以这么说,乡党的多少,乡党的官有多大,一定程度上决定你个人前程和发展潜力。如果你很能干,但没乡党帮忙,你将干得十分辛苦,甚至会白干。按征兵惯例,各大军区的兵源来自各管辖的战区。江西属于南京军区,江西的兵极少到广州军区,更别说老乡了。所以老班长在凤山部队的发展注定受到制约。
老班长在凤山招待所工作时,时任凤山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后在组织科)干事的我,节假日或平时没事或缺少营养想打打牙祭的时候,便会去他那儿坐坐。其实在老班长没来招待所之前,我在陆军55军军部担任文化教员时曾在那儿住过大半年,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并在那儿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美好时光。
我与老班长出生同年(他比我大两个多月)、入伍同年、又是同乡,共同语言比较多。当时正是我落魄之际,心境比较郁闷,正需要有个倾述的场所和对象。再说,老班长是个心境豁达之人,也十分尊敬像我这样所谓的文化人。于是,我去他那的次数特多。时间久了,两家走得也十分亲密。我的妻子带孩子来部队的第一顿饭基本上是在他那儿吃的。
每次到老班长那儿,他便会炒些首长用于招待客人的荤菜和端上首长招待客人没喝完的高档白酒,在他那杂乱的房内或房前那棵粗大的凤凰树下招待我。我喝茶或饮料,他喝白酒,俩人边吃边聊。他谈得最多的是首长在饭桌上与客人的谈话秘闻,然后再掺杂他个人的看法。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揣磨和掌握首长的爱好和动向,为我今后的写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老班长的烹饪技术好,不仅我们喜欢吃,就连首长每次招待客人时,都点名要老班长亲自掌厨。我曾私下问他,从开车到弄饭做菜,而且这么快就上路,其中有什么奥秘?老班长说,也没什么,开车与弄饭做菜其实是一个道理,留心琢磨服务对象,认真细致做好本职。部队的首长湖南人居多,其次就是广西、湖北的。他们的口味与我炒的家乡菜差不了多少。每次招待,来的是什么人,要下什么料,做什么样的口味,我都会事先琢磨一下。
当年的招待所有许多的猫腻,在那儿工作的战士一般不会干得很久,基本上是二、三年换一批。老班长在招待所时间长了,可能知道了许多不该知道的秘密,他又不属于单位领导的乡党,怕走露风声,一九九0年组建凤山部队教导大队时,单位领导便找了一个借口把他调到那儿。
教导大队驻扎在普宁县,距凤山六十多公里。由于相隔远了,与老班长的来往便少了,偶有几次,陪领导去驻扎在普宁县英歌山的部队蹲点,俩人会过几次。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大事。当时改革开放起步不久,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国家财力有限,邓小平同志便要求军队以发展大局为重,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精神,要“忍耐”。于是,中央军委在军队建设上就提出了“军队要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指导方针,鼓励全军经商、官兵经商,以弥补军费不足的问题。
老班长的经商意识浓厚。到教导队工作后,发现当地(普宁)出售的卷烟(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比家乡的便宜不少,每条的差价在10至30元不等。于是他不时叫家属或自己从驻地买些香烟带回家乡转卖。烟属专控商品,路上查得很严。为降低风险,他只带些低档烟,每次在50条以内。带回家后转售给烟摊,来回一趟可以赚个四、五百元。当时部队营、连职干部的薪金也就是二、三百元一个月。一次,他回家探亲,胆子大了一些,带了三箱烟(150条,约三千多元),途经丰顺县检查站时被烟草稽查队查到,并要全部没收。一副憨厚老实模样的老班长掏出士兵证说自己是军人,烟是带回家结婚用的。稽查队队长也是刚从部队转业的,看到老班长当兵多年还穿着打补丁的士兵军服,可能也想起自己当年当兵的穷酸样,测隐之心顿起,挥挥手,网开一面,放行了。
通过来来回回蚂蚁搬家式的小量贩运,老班长先后赚了一万多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万元是笔不小的财富,特别是对月收入不足300元的部队干部、志愿兵来说。当时,我倾家所有不足千元。
一九九四年,当兵十三年的老班长按志愿兵的服役年限该转业了。他从数十公里外的教导队风尘仆仆地来凤山部队司令部军务科办理转业手续,并在我那儿住了一个多星期。之所以住这么久,我猜他是想瞅机会找部队首长说说,看能不能留下来再干几年。他说,家乡和家里现在都比较穷,部队的收入低但稳定。当兵离开家乡十多年了,回去能不能适应、生存下去,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有点惧怕回去,在部队能拖一年是一年。
我心里清楚,现任的部队首长有不少都吃过老班长当年在凤山招待所饮事班时做过的饭菜,趁现在对他还有点印象,找首长说说,私下再做点工作,留下来再干几年应当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我对他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迟早都要走,晚走不如早走。志愿兵又不象军官,慢慢熬终有出头之日。再干几年,也改变不了身份,再说年纪大了再回去,更难适用,心理负担更重。
老班长临走的那晚,外面风雨交织,我俩坐在昏暗、摇曳的灯光下,煮茶闲谈,借以打发这无聊的时光。夜深人静之时,我准备休息了,谁知老班长又燃上了一棵烟,突然说起了早些年发生在老军部一位年轻女性身上的故事。故事梗概为:当年部队首长的一位千金不知为啥,与一位小战士好上了,虽然首长夫妇反对,但俩人还是藕断丝连,偷偷来往。后来这名战士不知咋的就不见了。有人说,首长知道女孩和战士的事后,非常生气,责成军务部门把他从部队开除并押送回家了;也有人说,他是正常退伍回乡的,现在下海经商发了大财;还有人说,他考上了军事院校,上学深造去了。
老班长说,当时关于她与那名战士的传说有许多版本,但谁也没有一个准。一九八五年裁军百万时,首长一家离开部队回原籍工作生活了,在外读大学的她不知为啥,毕业后又回到这并坚守了很长时间,先是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企业垮了,又到部队子弟学校当老师,部队撤了,就失业守在这儿,生活得十分艰难。
望着漆黑的窗外和屋檐淌下的水帘,我默默地聆听着老班长的述说。
最后,老班长掐灭了手中的烟蒂,起身说,她这样死守,我猜,八成就是为了等他吧?当年许诺时,以为那只是一段感情,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她的一生。
听完老班长的述说,我内心怦然一动,然后又若无其事地说,今晚反正无事,何不去看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孩还在不在?
挟着凉爽的雨风,老班长打着手电,撑着雨伞在弯曲伸展在黑夜的泥泞土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引导着我,向数公里之外的女孩居住地走去。临近女孩住所时,雨越下越大,我们躲避在一棵硕大的芭蕉树下。借助天空闪电的亮光和老班长的手势,我远远望去,女孩居住的房屋已墙体斑驳,四周灌木丛生,荒草也有一人多高。猛然,从密实、摇曳的灌木树丛中,我隐隐约约看到在漆黑一片的房屋里透射出一缕橙色的灯光。这昏暗、橙色的灯光在夜深人静、风雨交加的夜晚显得分外温馨。我撇下老班长,独自前往。挨近才看清,女孩居住的房间的门是敞开的,室内的灯光静静地泻了门外一地。我抹了抹脸上的雨水,仔细地聆听着屋内的动静。屋内是死一般的寂静。当我鼓起勇气走到门口时,一只硕大的老鼠从屋里窜了出来,吓得我几乎三魂出窍。我喘着气,捂着狂跳的心,定了定神才看清眼前的一切:屋内是空荡荡的,只有窗前悬挂的一幅粉红色的窗帘,还有几片枯叶在屋内随风轻轻地飘动着。这就是曾经寄托了一个年轻女性多年梦幻的闺房?我仔细地浏览着房间的每一处,想从中寻找出这位女主人当年生活过的蛛丝马迹。除了那幅粉红色的窗帘,一切寻索都是枉然的。
老班长也许没料到我会与这个故事有关,并是这个故事前半段的当事人。但老班长说的,演义的成分较浓。有些可能是他道听途说的,有些可能是别人捕风捉影的。当年的事既没有他说的那么精彩,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娱乐。其实说白了,当年的我只是给她的学习辅导了一把,其它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陆军第55军机关在裁军百万中撤消了,我从清闲的军部文化学校调到训练任务十分繁重的战备机动部队,俩人从此再没什么联系了。这段往事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是老班长到招待所之前。老班长来时,招待所的领导和战士都换了一茬,没几个人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至于老班长说的女孩后半段的故事,我不清楚,也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猜,之所以会衍生出这些八卦故事,许是当年的我们才二十出头,都很年轻,女孩又是首长的千金,长得漂亮,引人注目。再加上军营官兵的生活单调,需要一些八卦的故事来滋润枯燥的精神生活。于是传来传去就走了形、变了样。尽管如此,回到住处,我的内心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老班长离队时,我没什么好送的,翻箱倒柜收拾了一些旧军装送给他,老班长收下后迭谢不已。半年之后,得知老班长分在江西边陲小县一个地处山区的偏僻单位,从此就杳无音讯了。
二00一年,我从部队转业,并通过多种途经与老班长联系上了。我决定利用在家待分配的空隙去老班长那儿看望一下。当时乘坐的是吉安至定南的列车,票价低廉,区间运行,车厢破旧,乘客特多。列车到站时,由于人多、开门又不及时,许多乘客都从窗口爬进爬出。
不足二百公里的路程,火车三小时就到了。老班长与他的同事早早就到火车站迎接,并在县城较好的餐馆设宴款待。多年过去了,老班长的性格和为人还是一点都没有变,只是年龄长了几岁,相貌老练了许多。
老班长说,当年转业回家乡时,他挑着部队买菜的两只破旧箩筐(一只装着部队发放、用了多年的衣服被褥,另一只装着连队饮事班用旧了、淘汰下来的锅碗瓢盆),后面跟着家属并牵着几岁大的孩子,走进了他离开十多年已经陌生的县城,面对未来的生活,他和家人一脸的茫然: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全家该怎么才能活下去?
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老班长就是在县城花三千元买了一间农民废弃多年的土坏房,稍微整修了一下,把家属、孩子安顿好后,自己再去十几公里外一个偏远的、半死不活的单位报到、上班。家属则在县城摆摊补鞋、修表讨生计。
老班长凭借个人的能力和忠诚,凭借个人的机灵和胆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乡下调回县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班长一家的日子渐渐地滋润起来。一九九八年,他在县城中心地段买了一块地,起了一栋五层楼的房子,下面四层对外出租。老班长说,如果早几年从部队回来,情况也许会更好些。
老班长虽说是个志愿兵转业。但他没有像多数志愿兵那样回到地方就无声无息了。应当说他混得比一般的人还要好。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没多少文化,人又勤奋、耿直,谁都喜欢这样的部下。人太过精明,领导往往不放心;二是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只要放得开,善于变通,个人的环境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三是他所在的地方与广东交界,给他改善经济状态带了机遇。
晚宴之后,老班长请我去县城最好的舞厅娱乐。多年没进舞厅的我,不知有什么规矩。老班长说,只要有钱就行,舞伴由舞厅负责提供,也不要小费,基本上是本地人,陪一个晚上,她可以从舞厅得到十元人民币的报酬。
进入舞厅,看到男士们都坐在舞池两旁的酒吧椅上喝着啤酒、闲聊,当舞曲响起时,一大群花枝招展的舞女便从休息间里涌出,走到客人面前邀请跳舞。不会跳舞的我只是在里面尴尬地坐着。舞伴看我是外地人,非常热情周到。看到涉世不深的年轻女性为人这样纯朴、厚道,而且收入又这样低廉,感到有点不值,在我的建议下,我们早早退场。
第二天离开县城,搭车返程。
附:2012年后注:

生活还是要悠着点
老班长近日来电说,身体感觉越来越差了,高血压、糖尿病二期、脂肪肝。最近老感到心闷,估计心脏有问题,想来赣州做心脏搭桥手术。我劝他还是去广州做个全面检查吧。
记得2001年第一次去看望老班长时,他的饭局非常频繁,烟瘾很大。据说,每餐至少喝半斤以上的白酒,每天抽三包以上的烟。我感到,他这样下去有损健康,于是劝他:酒是喝不干的,烟是烧不完的,身体是自己的,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家人着想。要学会克制,要注意哦。
当时年富力强的老班长一笑了之,说没事,没事。
这不,没出几年,老班长的身体果然出问题了。
在部队工作时,实行封闭式管理,军人与外界的联系少,更不用说应酬式的饭局了。当时,大家都渴望有与外界交流的饭局。转业后这样的机会就扑面而来了。如不学会控制,就会带来许多的负作用。
我刚从部队回地方工作时,因负责接待和联系新闻媒体,饭局也特别地多。妻女给我记过一笔帐:有一个月曾有21天不在家吃饭。为此,妻女俩正儿入经地找我“约谈”过。
我是个家庭观念十分重的人。深知,这样下去,既不利于家庭生活,也有损于自己的健康。于是,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对可去可不去的饭局坚决不去;即使在外吃饭,油多的菜,坚持用矿泉水洗涮一下才吃;饭局时间长就多喝水。在部队时我就不喝酒,到地方工作后仍坚持不懈。
到外地出差,特别是有同学、战友和朋友的地方,一般不与他们联系,因为一旦联系上了,就是一顿酒池肉林。实在想与他们见面,一般是在餐后联系。但夜霄坚决不吃。因为,看到因饭局吃垮身体的例子太多了。
许多人把饭局多当作是有本事、在地方混得开的象征。其实,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想得到什么就必然会失去什么。上帝对任何事的设置都是公平的。
朋友,岁月很长。生活还是悠着点好。师里的老政委张阳(现任广州军区政委)说的得好:想活得时间长一些,就慢慢喝,想活得时间短一些,就频繁喝。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