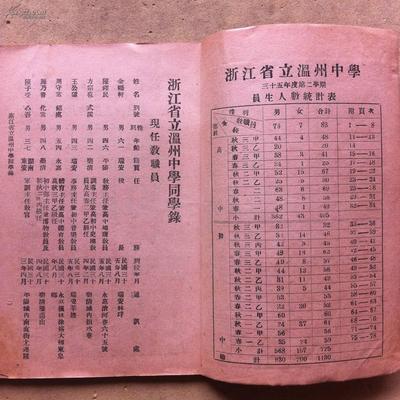消逝的长春旧书市
来源:新文化报 - 新文化网
当年旧书市上的卖书人如今在各古玩市场坚持 本报记者 刘阳 摄
旧书市一度栖身在西解放立交桥下
人们在旧书市场淘书 资料图片
B05版
■开栏语
这里是“这是你的长春”新城市文化联盟穿越长春第三季。
2012年,第一季,我们穿越了牡丹街、桂林路。
2013年,第二季,我们穿越了一三三厂、机车厂等长春老厂。
如果说,第一季带您领略了长春的时尚样貌,第二季触摸了长春的坚硬骨骼,那么,今年的第三季,我们将感知长春的文化血脉———穿越长春的书世界。这里有消失的旧书市,依然辛苦经营的旧书老板,城市的人文地标书店,公共阅读的图书馆,也有那些痴书的私人藏书家……
枯黄纸墨,穿越历史沧桑,志书史料,觅得前世今生。百万读者、千家书店、众多大小图书馆构架起的长春书世界,住着一个个追求完善精神自我的长春人。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本报带您穿越这城市书海,感受字里乾坤,墨中人生的阅读快意。
让我们共同在穿越中,认识长春、读懂长春、建设长春,让我们的长春不但拥有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更拥有一个优雅的灵魂。
今天,我们的穿越第三季开始了。
一碗 查米 条,一份土豆泥,一份辣椒泥,一碟辣白菜……吕大龙一股脑儿倒进碗里,拌好,端进书房,对着满屋子书画,大口吃起来。他“吸溜吸溜”地吃得很响,速度很快,但“ 查米 条还是那碗
查米 条,味儿却不是那个味儿”。再没有旧书市的路口,一群人吃 查米 条的快意,也找不到老友旧识,“有些东西跟着那旧书市一起消失了……”
酷爱文史的吕大龙,当年一头扎进旧书市,一晃近二十年。如今,这段岁月已成追忆。
春日暖阳正好,站在长春市同志街街口,向西望向义和路,一个个路口念叨,直到牡丹街,这一段路上,温热犹在。
当年,街这头三块钱一碗的面条端着,一家家逛旧书摊,迎面遇到旧友,“买啥了?”“都见到谁了?”几句寒暄,面条吃罢,继续逛。
街那头,新疆街市场路口,开着豪车吃 查米 条的人,停稳车,端碗 查米 条,路边蹲或站。吞了这暖暖的一碗,打个饱嗝,旧书市来嗨淘开。老书、旧书、名画、信札……能遇见的便是缘分,教授、工人、医生、学者……能聊到一处的便是雅士,只这一街,再无它处。
书市勃兴
淘书要趁早,大伙儿管这段交易时间叫鬼市,黑灯瞎火,买的凑过去,“有啥好的?”卖的一件件掏,拿手电照着看,相中了交钱
吕大龙,39岁,篆刻已有20年,藏书、藏画,旧书市里淘宝的奇人一枚。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家住在三道街,平房扒迁,大伙儿把破烂拿出来摆地摊,桃源路上热热闹闹地摆满街,以往当废纸卖的旧书也摆到街边,没多久,地摊越来越多,挪到东安屯,长春最大的旧货市场,就此开始。
那边地摊兴隆,同志街四分局这边,集邮大热。邮局南边的小胡同口有家书报亭,集邮类书籍卖得火,同志街边儿,几个此类书摊前儿总是围了一群人。街对面是外文书店,再走几步清华路口长春市图书馆。吉林大学在北面的解放大路,家属区、学生宿舍就在前后左右,“这差不多是读书人必来之地。”
王爱亮,人称老王,当年周末来溜达时发现,这是商机。他把家里的旧书划拉一丝袋子,用自行车驮着,到四分局跟前的永昌副食地摊边,就着集邮热支了个旧书摊。跟他一样躲在卖菜摊里的书摊儿,还有三四家。最初生意不好不坏。卖旧书的人都爱书,纷纷告诉亲友,不少人赶来卖旧书,慢慢地,旧书摊越来越多,沿着主街、胡同一直蔓延,连桃源路、东安屯的旧书摊儿也都过来了。
三两年,旧书摊儿一路支上义和路,向西漫过长庆街、牡丹街,“最繁盛时有两三里长,近百家大小摊位!”老王说到这,眼睛锃亮,一口河南口音,描述极富现场感。
王爱亮平时上班,周六周日摆摊,早晨三四点钟,骑自行车驮书到旧书市,地面收拾干净。摆书有讲究,必须分类清楚,摆得整齐,翻得容易,找得迅速,还不能丢。自己忙不过来,他就把大女儿叫上帮忙。

买书的一样得早起,漆黑天,吕大龙支一把手电,骑自行车,从三道街往义和路赶。
大伙儿管这段交易时间叫鬼市,黑灯瞎火,买的凑过去,“有啥好的?”卖的一件件掏,拿手电照着看,相中了交钱。“等天亮了,好东西就等不到你淘了。”鬼市很短,天亮了,卖面条的摊子也支起来了,3块钱一碗面条,边走边吃,不耽误逛。
就这么着,旧书市的一天热热闹闹地开始了。学生买参考书,读自考等继续教育的,参考书奇缺,这儿必来。懂行的买线装本古书,遇到喜欢的就拿下。
王爱亮家里的旧书卖差不多了,把妹妹当年上学的作文书、课外书也拿来卖,后来去联合书城批发清仓书,“成本高,总不见回头钱儿。”这时有人告诉他,“去扒废品收购站!”他去了,“满院子都是宝啊!”钻进书堆开挑,老板说,“不管你买啥书,全都两块钱一斤。”
第一回,他买了四五十斤。绿园区的大大小小废品收购站,他扒个遍。走街串巷的收废品的,都跟他有联络,卖旧书时间长了,很多买书人都记住了满口河南音的老王,家里有书卖,叫他上门收书。
当然,当年还有很多积压的书送达长春造纸厂,从厂里材料库批发出来的书,品相特别好。
长春旧书市忧伤小史
上世纪90年代初
同志街四分局附近义和路上,一些人借集邮热支起旧书摊,两三年内发展到近百家摊位
1997年后
哈尔滨、沈阳的爱书人也来义和路淘书,外地人只要来长春出差,必逛旧书市
1999年左右
旧书市达到鼎盛期,摊主们说这里“全国最大”
2002年前后
治理马路市场,义和路旧书市被取缔
后来
大家争取到吉林省图书馆后院的一块空地,继续经营
2007年起
空地被收回,旧书市搬到长春宾馆附近,没两年又搬到西解放立交桥下,再后来,这里也被取消,有些卖书人还在各古玩市场坚持
书中淘宝
最开始,他也不知道什么书能卖上价儿……后来弄明白了,不到10年,身家几百万
渐渐地,字画、小古董,甚至古墨都被书贩们翻捡出来。有懂行的,就此发家,旧书市里,淘出来的百万富翁很多。
摊主小国(化名)就是一个,2004年前,他还在黑龙江鹤岗扛大包,后来到了长春,买了一辆自行车,揣了几百块钱开始收书。去收破烂的家里翻书,早晨5点出家门,晚上10点进家门,一天蹬几十公里,全长春都跑遍了。灰里土里,一本本扒拉,日复一日。
最开始,他也不知道什么书能卖上价儿。“绝对有上万的,十几块卖出去的时候。”吃一堑,长一智,小伙儿学会了,但凡看上去有点不一样的,都先压着不出手,自己学,找明白人问,跟买书的打听,“我们手里的很多东西都是网上没有的,那都是一点点淘到的。”就这样,弄明白了,出手一件,不到10年,身家几百万。
这样的故事不少,普通人的故事更多。老王的大闺女上班了,二女儿又来帮他看摊。自行车一次也驮不了百十本。下了岗,他彻底投身旧书市,跟几个相熟的摊主在义和路附近租地方摆书,那时候,路边还有小棚子,雪糕店、大阳台,全被摊主们租了寄存。卖两天书,收五天书,日子辛苦。
摊主们的辛苦成全了旧书市的繁荣,1997年后,除了长春人在逛旧书市,哈尔滨、沈阳两地的爱书人,赶上周末也来淘,慢慢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甭管在哪儿,只要来长春出差,必逛旧书市。1999年左右,旧书市达到了鼎盛期,“全国最大!”这是摊主们的一致说法。
摊主陈向东说,当时在长的日籍师生也来旧书市摆摊。那时候,他关于老长春历史的书籍最多。日本摊主说着蹩脚的汉语,买走他的日文旧书。他也去逛他们的书摊儿,有很多伪满时期的中文资料,几乎没有在书市见过。原来,他们回国后,把中国淘来的书卖了,又把日本人手中的中文书籍买来,运到中国卖,“这是最典型的图书回流。”老陈说。
每个周末,旧书市的人推不开搡不开,摊主们回忆,一天总有个几千买书人,早来、晚走,买完了送回家,再来,再买,一趟趟转悠,“真有宝贝啊!”更多的“教书匠”、“书虫”就蹲在地摊边翻书看,从早看到晚。
都有啥宝贝?大伙儿说,全是“国宝级”的!吕大龙曾在博客里记录:“毛装书,古籍线装书,新文学版本书,每每总能让人感到有些惊喜……还有,林散之的山水题字画,沈鹏、张伯驹、于省吾、启功、朱东润、谢稚柳、成仿吾、罗继祖、孙常叙、冰心等一大批当代新中国文化名流的信札或书画作品等!”哪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
书结雅缘
一些藏书大家,吴振武、吕文郁、上官缨等,都是旧书市的常客。吕大龙就和上官缨老人成了忘年交
常逛旧书市的人,别看多,绝大多数人都混个脸熟,很多人成了至交。见了面,第一句:“买啥了?”第二句:“都见到谁了?”然后,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先聊一阵儿行情,也让大伙帮着鉴定一下自己的宝贝。
书友里,上了年岁的多,要是几天没见哪一位,大伙儿忍不住问:“是不是病了?”隔周再见,“格外亲”。
他们不仅聊书,还送书,自己写的,签了名送给旧书市的朋友。书市淘的,要是有人喜欢,也送。“买书的、卖书的,全在这,书为媒,每周两天雅集!”吕大龙说。
一些藏书大家,吴振武、吕文郁、上官缨等,都是旧书市的常客。吕大龙就和上官缨老人成了忘年交。
上官缨是吉林省十大藏书家之一,一生爱书,家中藏书几万册,苦于借书的人太多,只好将藏书挨本用白纸包上书皮,并嘱咐借书的人珍爱书籍。旧书市繁盛时,老先生总是一身布衣,在人潮中淘宝。经人介绍,俩人认识了,吕大龙特意将收藏了十一封田琳(旦娣)晚年的信札的事,说与老先生。上官先生不但跟他聊了些有关田琳的旧事,还很郑重地跟他说:“‘东西’不错,很珍贵。”两周后再见面,老先生特意送了吕大龙一本《艺文碎片》,2006年,又送了他一本《东北沦陷区文学史话》,他则送老先生藏书章。再后来,老先生将所藏书籍及名家字画,捐赠给长春市图书馆,成为藏书史一段佳话。
可是,这样的繁盛没有维持太久,2002年前后,治理马路市场,义和路旧书市被取缔了。
老王把书全摞进了仓库,开始闹心。后来,大家争取到了吉林省图书馆后院的一块空地,继续经营,但是,“元气大伤”,很多摊主改行了,原来一百多家,变成了几十家。好在,不少逛了多年旧书市的买书人,加了进来,吕大龙开始摆摊,卖印章,换了钱,继续买他的旧书、旧照片。而刚退休没两年的孙希财则每周坐火车从九台来长春淘书。“跟通勤上班的人一起来,再跟着他们一起回九台。”
老人以前是高中老师,酷爱藏书,文史社科类最多,尤其跟九台有关的书籍、字画,全都搜集。逛书市,就是为了充实他的大藏书柜。
虽然旧书市规模大不如前,可新疆街市场的 查米 条很火,一个老太太带着残疾儿子,早早出摊,卖 查米 条给这些买书、卖书的。“一碗一块钱。”
一碗 查米 条,一份土豆泥,一份辣椒泥,一份辣白菜,往一块一拌,那叫一个香,吃完了,身上暖和的,进去淘书,那感觉有多美?“语言没法形容”。
可书市的生意远没老太太的生意顺利,2007年前后,空地被收回,旧书市继续搬家,搬到长春宾馆对面的雅居二楼,后来又回到了楼下马路上,“那段各种档案资料、画家草稿、信札出了不少。”陈学奎老人说。买书的卖书的又少了不少,过了没两年,老王他们继续搬家,到了西解放立交桥下,再后来,这里也被取消了。长江路上的花鸟市场还有十几家旧书店,辛苦坚持。
曾经享誉全国的旧书市场,就这样,从浩浩荡荡一二里,到无处可寻,虽然当年那些卖书人,有些还在各个古玩市场坚持,但是,“文化认同的消失足够让人伤心”。
一些专门研究古籍的老学者都说,“旧书市的消失,是长春人的一大损失。”
而今,老王他们搬进古玩城,旧书摊名号不变,依旧有买熟人追过来翻淘,倚着门,他笑着说,“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可总觉得缺点啥。”
吕大龙全心做自己的篆刻工作室,闲时,自己在家做 查米 条,试图让味蕾唤醒记忆,在回忆中,和那些老友旧识相遇……但是,书斋不是义和路,举架藏书没有地摊温度,大男人忍不住一声叹息,满眼温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