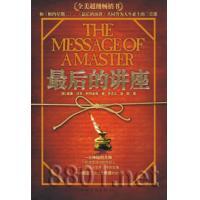不了解北大中文系情况的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那里是文学新人成长的沃土,是最适合做作家梦的地方,然而,在北大中文系做作家梦,是很需要些定力的——北大中文系固然出了一些作家,甚至还出了一些名作家,但恐怕更多人的作家梦是在那里幻灭的,因为,北大中文系不是“做梦”的地方,或者说,如果那里是“做梦”的地方的话,也鼓励你做学术梦,而非作家梦——这也是老系主任杨晦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几乎成了其后每位系主任在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必讲的“口头禅”的原因。
在我们读研究生的新千年前后,在北大中文系做作家梦变得更加艰难了,因为除了我上面所说的原因外,随着文学的日渐边缘化,知识界对文学的体认越来越少,对文学的态度也越来越不令人乐观——如果不是悲观的话。大体上说,当时知识界对文学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由于外部环境的挤压和内在精神的丧失,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处于“崩盘”的边缘;另一种则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仍兴旺发达,但他们眼中的文学往往到1990年代中期的先锋文学等就戛然而止,即使谈到当下的文学创作,也往往只是聚焦于“八零后”等所谓的文学现象上。表面上看来,这两种文学判断似乎南辕北辙,冰炭不能同炉,但究其本质,却有一定的相关性,那就是看不到或不相信文学的未来。我想,这样的判断,对正做着作家梦的同学少年的压力是无形而又巨大的吧?
李云雷属于那种有定力的人,在那样的文学环境下,他依然执着地做着自己的作家梦,那么淡定,甚至有些忘我。那时候,我们两个都租住在北大西门附近的城中村挂甲屯局促的平房内,除了读书与上课,我们两个经常凑在一位安徽阿姨开的一家饭菜实惠的小饭馆内(那里留下了多少温暖的回忆啊),一边喝着酒,一遍谈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他的《花儿与少年》、《少年行》、《朝圣之旅》等小说,这都是他的旧作。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就很是为他小说中洋溢着的纯粹诗意和纯熟技巧而感叹,但我也常常批评他的小说缺乏现实感,缺乏思辨的力量——那时,我正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往往拿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事儿,说他的作品缺乏火与冰般互相颉颃而又彼此交融的艺术感觉和能量。现在重读他的小说,特别是他的《花儿与少年》等关于童年记忆的小说,我有些怀疑起自己当初的判断来。在乡土社会瓦裂、乡土文化衰败、乡土心灵孤寂的今天,对我们这些一条路越走越远,远得既不能真正回归故乡又无法真正融入都市(特别是其现代逻辑)的“双面人”来说,这样的小说不正是我们关于“故乡”的最后记忆?小说里边那虽则艰苦但却父母慈爱子女孝敬的“家”的图景,不正是我们关于“家”的最后一抹温暖记忆?那正是我们最后的乡愁啊!在时间延展中,这种安静的书写与颓败的现实之间构成了激烈的对话关系。
我想,凭着云雷的定力,他的小说一定会越写越好——实际上,他也的确越写越好。然而,大概在2004年前后,他却突然暂时中断了小说创作,或者说,中断了所谓的“纯文学”创作,做起文学批评来,并且成为“底层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和研究者,以至于有朋友认为他背弃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变成了“新左派”。但在我看来,云雷是始终走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的,只是在这条道路上,他越走越艰难,越走越纠结,也越走越遥远。在漫长的跋涉中,青春的明快和稚气渐次离去,生活的沉重和沧桑却次第袭来。于是,他观察社会的眼睛深沉了,他对生活的呈现复杂了。
细读云雷早期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他是在用纯粹明快而又散发着淡淡的忧伤气息的文字营造一个心灵诗意栖息的家园,在这个家园里,生活着他勤劳憨厚的父亲,慈祥温厚的母亲,美丽善良的姐姐,淘气纯真的童年伙伴,在城里生活的舅舅,星期天可以不用干农活的县城里的同学……在这个洋溢着人间烟火的家里,他就像鱼儿游弋在水中一样,无忧无虑,自然自在。细读云雷现在的小说,我们又发现他是在寻找一条路,寻找一条回家的路,寻找一条回到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亲人朋友身边的路。他寻找得那么孤独,那么无助,又那么坚决,那么执拗。因为,就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他发现支撑这个家园的大地日益碎裂,家园也日益衰败,他那可爱可敬的亲人也渐行渐远渐无书……从这个层面上看,在云雷小说中一再出现的“家园”的意义就格外丰富厚重了,因为,他寻找的已不是个人的家园,而是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游子的家园,是几代无家可归的“底层”的家园。
促使他从在想象中建构家园转变到在现实中寻找家园,既有个人遭际的原因,更有社会巨变的原因,或者说,是充满痛感的个人遭际充当了他思想和情感的催化剂,使其情感和思想得以升华,从而睁大眼睛,看到了更加残酷的现实,更为艰难的生活。
不用对云雷的生活有很深的了解,仅读他的小说,就知道他一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段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是这幸福的家园,为他的顺利成长、成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但这动力支持,大概到了2003年前后的时候,就难以为继了,或者,不如反过来说,这个时候,需要他为家庭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因为他那一直扛着这个家艰难但却稳健前行的父亲患上了癌症,对他那都在家乡务农,收入几乎入不敷出的兄弟姐妹们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承受的重压,因而需要他把这个家扛起来。对一位正在读博士的穷学生来说,这也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但他默默地承担了下来。我记得那段时间,他几乎谢绝了一切活动,整天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沉默地“做书”,以挣取稿酬,把父亲接到北京治病。那时,我偶尔去看看他,跟他聊聊天。原本话就不多的云雷更加沉默了,几乎一整天说不了一句话,只是时不时地发出沉沉的叹息。记得老人到北京的时候,我去探望。我知道这种病的后果,但我仍然不得不假装轻松,“违心”地说着安慰的话。老人默默地听着,礼貌地笑着,几乎不说什么话。但当我说到云雷的学业,说云雷很优秀,是他的骄傲时,老人突然高兴起来,眼里发出晶莹的光……因此,当我在《花儿与少年》中再次读到“我又一次说起自己得了小红花的事,爹很高兴,多喝了二两酒,对我说:‘行,好小子,你就好好学吧,考上一个大学,也让咱祖坟上冒冒烟’。”这一段时,竟百感交集,泪花闪烁。我想,正是对儿子的爱和期望,使老人勇敢面对疾病,坦然面对生死。后来,云雷不止一次对我讲过,当疾病发展到晚期后,虽然痛彻骨髓,可父亲从来没有在儿女面前哼叫过。这是怎样的爱啊!
鲁迅在回忆自己的人生轨迹时曾说过,在从小康堕入困顿的途路上,最能看出人情的冷暖来。我想,父亲的疾病,倒不是让云雷看出了人情的冷暖来,而是让他想到了知识的责任之所在,文学的责任之所在。从个人的角度看,就是我们——这些据说获得了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如何才能不亏欠“父亲”那沉甸甸的爱?如何才能让那日渐衰退的家园再度焕发生机?往大里说,就是我们怎样才能不亏待那千千万万操劳的“父母”?怎样才能让那一个个陷落的家园重新挺立起来,安宁起来,幸福起来?到现在,我还时时“看到”老人那微笑的眼睛,亮光闪烁的眼睛。它让我一刻也不敢放松对自己心灵的拷问。我想,这双眼睛对于云雷的意义,恐怕比我要重千倍万倍吧!大概就是在这时,我们看到了云雷《假面告白》中近乎“精神分裂”的自我辩驳声。后来,我们又听到了他发出的“我们为什么读书”的叩问声。

我想,深深地刺激了云雷的,还有“上访事件”。那大概是2005年前后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已硕士毕业,在一家单位不死不活地上着班。一是由于疲惫,二是由于迷茫,我很少找朋友聊天,跟正处于读博关键时段的云雷的交流,也少了许多。一个晚上,云雷突然给我电话,让我去他宿舍聊天,我就赶了过去。在那里,我见到了几张跟我的兄长们一样的农民的面孔。原来,这是云雷的同乡,耕地被当地政府粗暴占用了,屡次上告、上访无果,就想到了他们在北京最高学府读书的“小兄弟”了,想他读了那么多书,那么有知识,或许能给自己出个好主意。在云雷请他们吃饭的时候,那几个粗朴的山东大汉,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热泪。他们横流的热泪,再次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柔弱和不甘。我们多么渴望这些强壮的汉子们不是在这里热泪横流,不是在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的路上漂泊,不是到处上访,而是在家园里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是在田野里汗滴禾下土啊。可是,跟疯狂的资本相比,跟非理性的GDP追求相比,跟不科学的发展观相比,这些兄长的热泪和我们所谓的知识是多么的无力啊,因而,面对着他们泪痕斑斑的诉说,我们除了无力的安慰和沉默,又能干些什么呢?我记得事后云雷多次跟我说起这些兄长们的热泪,说他在这热泪前的无力感和愧疚感……
我想,正是这种种现实的刺激,催化了云雷的知识观,拓宽并深化了他的文学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短暂地告别了小说写作,为“底层文学”鼓与呼起来,为“十七年文学”仗义执言起来。他也常常打电话给我,邀我一起去参加一些讨论会,让我多写一些评论文章,尤其是我到《小说选刊》杂志社工作以后……由于我有自己的执着,也有自己的无奈,因而他的呼唤,我响应得很少,但几年的时间内,他一个人,拳打脚踢,上下求索,竟开创了一片文学的新天地,使“底层文学”成为当下最为有力的文学力量。他的文学实践,特别是文学批评,有力地回应了知识界的文学判断:文学不是一个可以被终结的概念,它的根系在历史中,它的芬芳在未来;文学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不仅牵连着作家们的心灵世界,更牵连着宽广的现实世界……
我想,大概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体味和认知,重新写小说后,云雷的笔触深沉了许多,凝重了许多,艺术上也严谨了许多,严肃了许多。是啊,对一位想通过文学为自己、为千千万万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找一条“回家”的路、找一个温暖的“家”的人来说,非如此不可以。因此,在其新作《舅舅的花园》中,我们才能从“我家”小院里的一棵花椒树出发,看到县城里舅舅家那葳蕤的花园,看到那葳蕤的花园伴随着舅舅的衰老而枯萎、消失,看到一座小花园中所包容的时代的沧桑巨变和其中心灵的颠沛流离。在《父亲与果园》中,我们才能看到在暮色苍茫中,成年的“我”穿越时光,穿越果园,在村头与虎头虎脑的、穿着笨重的棉衣的、在寒风中交替地跺着脚等着“我”的“童年的我”迎面相遇,才能听到从“我”心灵深处发出的那声呐喊:“我终于回来了。”
去年,由于家中发生的一些变故,由于我那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却依然东游西荡不愿回家的弟弟,由于我那为生活所压一度几乎精神失常,白天黑夜都奔走在田野中的满头白发的母亲,由于我那更加沉默寡言的父亲——这样的画面,在农村中几乎司空见惯——也由于我今年做了孩子的父亲,我更加明白了“家”的真意,更加明白了云雷的寻找意义之所在,我更愿意与他一起寻找一条回家的路,与他一起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因为,这不仅是他的路,也不仅是我的路,而是“我们的路”——千千万万底层人民的路,千千万万关注底层人民的人想要寻找的路!只有找到了这样的路,我们的父母那苍苍的白发才不会在飘摇在寒冷的风中,像悲伤的旗帜;只有找到了这样的路,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才不会奔波在各样的歧路上,像无家的幽魂;只有找到这样的路,我们的孩子们才能有明亮的笑脸,不像离群的小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