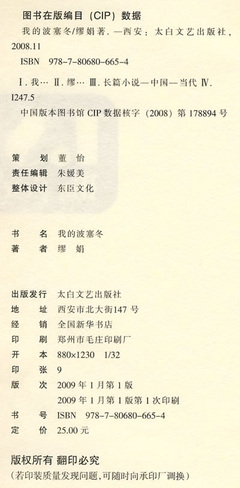身体之外的诗歌生活
——谈沈浩波及其诗歌
刘波
沈浩波这位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的诗人,与当年伊沙一样通常被人称作“恶人”,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他的骂名胜过了他的诗名。与诗人韩东的好斗一样,沈浩波给人的印象是同样好斗,在此,我并不想谈论沈浩波性格上的问题,那与诗歌无涉。如果说要谈论70后诗人,沈浩波当仁不让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虽然很多的人对这样的选择定有微词,但是我们无法略过沈浩波去谈论那些在诗歌与诗学理论上毫无建树的平庸诗人。
沈浩波在他22岁时以一篇《谁在拿九十年代开涮》引起了诗坛对他的关注,尤其是他在该篇与此后的一些文章中与当时的学院派诗人激烈过招和交锋,说出了很多虽然偏激但不无道理的事实,以此来支持当时处于诗坛上不明状态的民间派。在后来与一些诗人的交谈和自己的阅读中,我发现大多数人对沈浩波以及他的诗歌都嗤之以鼻,认为他只不过是诗坛上的一个混子而已。要说混,中国的大多数诗人几乎都是混出来的,依靠诗歌为生的人寥寥无几,难道我们能说一个诗人成天不埋头写诗就不算专业,就没有敬业精神吗?事情好像不是这样的。不管混与否,作品是最主要的,所以从诗歌本身入手,是衡量一个诗人最理性也是最根本的方式。
沈浩波当年的《自画像》这首诗就以自嘲甚至玩世不恭的话语方式彻底地与虚假的诗歌写作断裂,此诗一方面以口语化的语言表面上暴露了自己的生理面貌,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他需要对口语诗歌进行充分实践的力量与野心。在对待诗歌上,他似乎从来没有绝望与沉默的时候,在每一次风口浪尖,他总是勇敢地站在巨浪的前头,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你,他就是这样自信,他相信,口语化的诗歌同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诗人施展语言才华。这样的诗歌与他在大学时写就、并在后来被许多人叫好的《福莱轩咖啡馆·点燃火焰的姑娘》那种优雅的抒情诗相比,沈浩波更觉出了诗歌需要一种极端的、无情的、歇斯底里的语感,畏缩、牵强与虚妄,对于需要良好语感的诗歌来说,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正像沈浩波在回答《南方都市报》记者对他的提问时一样,“强健,宽阔,应当是诗歌最好的境界。”后来,他一直在朝这方面的努力,并逐渐地进入了境界,并做得更加到位了。此时,他找到了一种具体可感、生机勃勃的特殊的话语形式。
又圆又秃
是我大好的头颅
泛着青光
中间是锥状的隆起
仿佛不毛的荒原上
拱起一块穷山恶岭
外界所传闻的
我那狰狞的面目
多半是缘于此处
绕过大片的额头
(我老婆说我
额头占地太多
用排版的专业术语
这叫留白太大)
你将会看到
伊沙所说的
斗鸡似的两道眉毛
它使我的脸部
呈现斗鸡的形状
是不是也使我
拥有了一只斗鸡般的命运
十年之前
人们说我“尖嘴猴腮”
而现在
却已经是“肥头大耳”了
一只肥硕而多油的鼻头
彻底摧毁了我少年时
拥有一副俊朗容颜的梦想
——《自画像》
其实,沈浩波从进入诗歌写作开始就一直是以一个民间派的口语诗人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他更多的关注诗歌与口语、日常生活与当下经验的关系,而不是悲剧性的宏大命题。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不受国外某个大师与国内朦胧诗人影响的情况下写诗,这样的年轻诗人在当时的诗坛上是并不多见的。当大部分学院派诗人还抱着弗洛斯特、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斯等人的诗歌吸取营养时,沈浩波觉得自己应该丢掉那些西方过去时的东西而直接吸收中国本土优秀诗人的新鲜营养,如于坚、韩东、伊沙等人都曾对沈浩波的诗歌写作有过或直接或潜在的影响,他对于诗歌口语语感上的传承更多的是来自他们。
自从后来沈浩波提出了“下半身”的诗歌宣言以来,他的诗歌就日益呈现为一种更加硬朗的风格:没有什么不可以入诗。这种看似游戏而并非游戏的诗歌在嫁接了摇滚乐形式后,与极富快感的语言节奏相融合,创造出了幽默、生活化与清新洗练的诗歌精神。有了“语言自觉”与“身体性”的理解后,沈浩波的诗歌已经彻底地摆脱了掩饰的成分,而充满激情地摊开了一切,卸下沉重的语言包袱,顿释胸中块垒,极富煽动性地覆盖了所有关于身体与个人经验的场景。不管其他人怎样不遗余力对他的那些被称为“下三路”的诗歌进行不屑的嘲讽与讥笑,他仍然一如继往地写下去,即使有人站出来为他的这种行为叫出了“诗歌之死”的哀鸣,沈浩波无法再回头了,因为他找到了一种长久地适合自己写作与成长的方式,但他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他将自己的另一面彻底地逼到了死胡同。在他看来,自己需要的就是从“地下”走到地上,从默默无闻走向声名大震,这样一种狂热的诗歌理想让他远离了抽象的词语与叫嚣诗歌技术含量的无聊理论,远离了无话可说而苦恼不已的状态,终于寻找到了明朗诗歌的入口,寻找到了口语诗歌的速度与加速度,从而告别了过去那些短暂的虚幻梦境与混乱的诗歌计划。沈浩波不会继续在诗歌写作上作摇摆不定的左右为难状了,他开始面对成熟有一种从容的诗歌心态。《成都行》即是佐证,这是沈浩波在诗歌写作上又一次开阔的、大气的尝试,他自信地摆脱了那种拐弯抹角地制造病态叙述的习惯,将自己的语言功能再次激活,写出精力充沛的句子,而将那些疲惫的形式抛弃在了传统的垃圾堆里任其自生自灭。
依靠鲜活的口语,明晰的结构形式,从日常经验入手,抒写诗歌与艺术的当下状态,自觉远离隐喻与象征的所谓技巧,而以一种尖锐的锋芒毕露的姿态来完成诗歌进入大众视野的努力,这是沈浩波目前基本的诗学准则。在表现硬朗的同时,他也需要在诗歌中克服迷惑性的障碍,从而抒写自己最为真实的感受,最终不会让这种感受在示人的时候还隔着一层难以抹开的面纱。即使是那些温情的诗作,沈浩波同样也能写出一种人类本能的对弱势者的怜悯与博爱,这不是极端的话语实践,也不是毫无理由的妥协,而是让诗歌尴尬的地位能有一次温和的回归。
一只蜥蜴
从一棵被烧焦的大树上爬下
仅有的一只蜥蜴
爬行在
一棵被烧焦的大树上
在澳洲东部的
这一片被大火焚尽的林子里
这只蜥蜴
几乎是仅有的活物
在一棵巨大的
被烧焦的树干上
爬行着
它是那么微小
缓慢地爬行着
还有比这更悲伤的
在北极洲
冰天雪地之中
两只年迈的白熊
搂抱在一起
度过它们的
风烛残年
——《你是否懂得一只蜥蜴的悲伤》
其实,这种形式似乎并没有让沈浩波看到诗歌已经有了令人可喜的转机,那些暧昧的话语方式已经满足不了众多诗人对于诗歌的理解了,你只能把它当作沈浩波温情一面的表现来看待。毕竟,他不能做出被流放的虚假的悲剧姿态,也不需要什么使命与承担,所以沈浩波后来变成了一个热闹的人。
在自己进行诗歌实践和与民间诗人接触的过程中,沈浩波发现了身体的好处,身体之于诗歌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了切实的身体的不在场,诗歌徒有精神的外表,那只不过是词语的凌空蹈虚而已。为此,沈浩波与他的众多的诗歌朋友们一起办刊物,几个回合下来,沈浩波出其不意地推出了他骇人听闻的“下半身”策略。在许多诗人乃至作家们都羞于启齿的东西,却被沈浩波作为宣言纳入进自己的诗歌理论范畴,语惊四座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甚至引起了诗歌界外部人士的关注。他所倡导的“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这一时段沈浩波写下了大量关于身体的诗歌,其在诗歌中突出了身体的惟一可感性,对于人的私密处的亮相揭开了一切伪诗歌与假抒情的面罩,这再一次造就了沈浩波诗歌鲜活的品质。他甚至提出了“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我们更将提出: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1)他为此实践的诗歌《我们那儿的男女关系》《淋病将至》等等都是如此。正像评论家谢有顺所说的那样:“‘下半身’作为类似‘跨掉的一代’那样的文学行为艺术,在中国并非毫无存在的理由。草率的否定是无济于事的。你只要认真读他们的宣言,便会发现,这里面有着强烈的反抗意义,也包含着很多有价值的文学主张,它既是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反身体的文学的矫枉过正,又是对前一段时间盛行的‘身体写作’中某种虚假品质的照亮。他们所深入的,是文学的底部,是文学的最底线,是身体最基本的部分——肉体主义。”虽然谢有顺并不是完全赞成沈浩波倡导的“下半身”写作,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其他的文学“绕不过去的一个参照物”。(2)现在看来,“下半身”也可能只是一个噱头和口号,虽然在提出之初,沈浩波及其同仁们也写过很多富有刺激性的“下半身”诗歌,但是这在他那些“自觉”的口语诗歌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部分,后来更多的人对此习惯并熟悉了“下半身”诗歌之后,只不过是“感觉正常”而已,因为人的观念是在不断改变的,包括对待诗歌的观念也是如此。
以上也只是由“下半身”观念延伸出的一些意外想法,但是在当初,沈浩波并没有被宽容,而是被称为不折不扣的“流氓诗人”,一如当年的朱文在小说《我爱美元》发表时被一些评论家称为“流氓小说家”那样,沈浩波在体制内只会是意识形态叫嚷着被打倒的产物,他的诗歌还没有真正地浮出水面。
在众多的人都骂沈浩波的诗除了下半身就是肉体,并没有半点精神的内含时,这些误解与非议对于沈浩波来说,或许就是需要这样的效果。他既不是另类,又不缺乏丰富的想像力,他只是让自己的诗歌读起来新鲜,有力,别人有别人的眼光与看法,他有着自己发出不同声音的自由权利。
赤裸裸地暴露那些感性的身体因子,与日常语境充分结合,这种状态看似远离了诗歌的灵魂缺席,而实际上却没有因此而疏离诗歌的真实意图。对于学院派诗人华丽词语的不信任姿态,导致了沈浩波无法不相信身体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诸多潜在表达功能。短句子、节奏感、开阔性在那些简单甚至粗糙、生猛和极富野性的分行文字里被他处理得游刃有余。而有时,他也需要抛弃那些假惺惺的伪抒情,而成就诗歌的纯粹性。
沈浩波敢于暴露自己,这总比那些隐藏极深的阴郁者们半遮半掩的诗歌要来得真切,诗歌在一些人看来是那种避重就轻的带着拆解生活的态度去做义愤填膺的聒噪,而在更多的人看来就是低吟浅唱、深沉含蓄的感伤主义,沈浩波却恰恰偏离了这些温文尔雅、四平八稳的小情小调,而是以偏执的信念成就了诗歌应该具有现场感的形式。他叫出了诗歌不再是清高优雅的贵族行为,而是与普通人有密切关系的事物。好的诗歌是理性与感性最为有效的结合,沈浩波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需要打破一切虚伪情感对诗歌的束缚,只有完成了这一过程,才能还原口语诗歌一个本真的面目。
正当词语的狂欢化组合与诗歌的不知所云让读者甚至诗人们都极度难堪时,沈浩波和他的一些前辈诗人一起质疑了知识分子诗人对于诗歌处于困境的闪烁其词的理由,他们迅速地找出了诗歌越来越不被当代人所认可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虚假与脱离个人真实的生活经验。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人都写诗的盛大场景一去不复返的时候,诗歌应该从形而上的隐喻和象征中回到人的本真与自我,回到当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回到对日常经验最为有效的抒写。
沈浩波在2003年的时候写出了他诗歌创作生涯中比较重要的作品,那就是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这对于沈浩波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诗歌转型,他在这首长诗中运用了马雅可夫斯基惯用的梯形结构,结合2003年年初所发生的一切时事,融合了诗人自己的诸多感受,在一种古典的意境里制造了诗歌的荒诞与高潮。由此,沈浩波可能开始走上了另一条承续着“下半身”的某些观念,但又略不同于以前的诗歌道路。
注释:
(1)沈浩波:《心藏大恶》,第318页至323页,大连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2)《话语的德性》第183至184页,谢有顺著,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