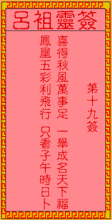一生低首小山词——评沈祖棻诗词

(年轻时的沈祖棻)
沈祖棻无疑是近百年词坛一颗耀眼的星。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以吕碧城、左又宜、沈祖棻为一代女流词人之选。今人或以吕、沈、丁宁为三大女词人。而沈的影响,似有过于吕、丁而无不及,被人称为“当代李清照”。这话要看怎么讲。如果就家学、身世、姻缘而论[1],沈祖棻简直就是李清照第二。但就词风而言,又当别论。
沈祖棻有一首题为“题乐府《补亡》[2]”的小词,调寄《望江南》:“情不尽,愁绪茧抽丝。别有伤心人未会,一生低首小山词。惆怅不同时。”程千帆笺曰:“祖棻尝戏云:情愿给晏叔原当丫头。即此词意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对别的词人,沈祖棻没有说过类似这样的极为倾慕的话。与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祯语)、郑燮署“青藤(徐文长号)门下走狗”[3]一样,这代表着她的一种美学景仰。
关于《小山词》,晏几道自序说:“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演唱)。”陈振孙说:“叔原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直斋书录解题》)冯煦说:“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总之是一种纯歌词的写法。北宋令词,更是“倚声”而写,而不是“填”,更重视口语与文言并用,而不是一派雅言,与南宋格律词派不同。此外,晏几道有“最为人们传诵的篇章”[4],那就是《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彩袖殷勤捧玉锺),绝对是压轴之作。
沈祖棻的创作实践,有一半与她的这个美学理想拧着。她在慢词(婉约派)、格律词上下了很大工夫,更是“填”,而不是写。她在婉约词创作领域,走的又是周邦彦、南宋格律词派及清代常州词派的路线,而非柳永、李清照及辛弃疾的路线。只要看一看《曲游春·燕》、《曲玉管·寒蝉》、《霜花腴·雪》,以及若干标明“和清真”的慢词,就可以知道。这与师承有很大的关系。她就读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国文学系时,师从词学家汪东,接受过科班的训练。这一段专业的训练对她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她一学就学得非常像,一学就学得非常好,一学就学到青出于蓝:
归路江南远,对杏花庭院,多少思忆。盼到重来,却香泥零落,旧巢难觅。一桁疏帘隔,倩谁问、红楼消息?想画梁、未许双栖,空记去年相识。 此日。斜阳巷陌。念王谢风流,已非畴昔。转眼芳菲。况莺猜蝶妒,可怜春色。柳外烟凝碧。经行处、新愁如织。更古台、飞尽红英,晚风正急。(《曲游春·燕》)
汪先生评:“碧山(王沂孙字)无此轻灵,玉田(张炎号)无此重厚。”另一首慢词《绿意·次石斋韵》,汪评:“足以上继玉田。”另一首咏物词《天香·藕》,汪评:“有此本领,乃能咏物。便觉碧山、玉田,去人不远。”还有《探芳信》,汪评:“清于梅溪(史达祖号),厚于玉田。”一次也没提到李清照,这决不是疏忽。似曾相识的题材,似曾相识的手法,加上似曾相识的藻绘——如“杏花庭院”、“香泥零落”、“旧巢难觅”、“红楼消息”、“王谢风流”、“莺猜蝶妒”、“新愁如织”、“飞尽红英”等等,读者频频脱帽,不免乎审美疲劳。所幸她的令词并不如此,关于这一点,下文再说。
未了伤心语。回廊转、绿云深隔朱户。罗裀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凭教翦断柔肠,翦不断相思一缕。甚更仗、寸寸情丝,殷勤为系魂住。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烟横锦榭,霞飞画栋,劫灰红舞。长街月沉风急,翠袖薄、难禁夜露。喜晓窗,泪眼相看,搴帷乍遇。(《宴清都》)
词前有序:“庚辰(1940)四月,余以腹中生瘤,自雅州移成都割治。未痊而医院午夜忽告失慎。奔命濒危,仅乃获免。千帆方由旅馆驰赴火场,四觅不获,迨晓始知余尚在。相见持泣,经过似梦,不可无词。”“长街”以下,汪先生的评语是:“清真(周邦彦号)家数”。小序是决不可无的,相当于变相的注释。没有这样的注释,读者就想不到“罗裀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几句,原来是描写手术后病房的情景。同样,“凭教剪断柔肠”句的自注:“割瘤时并去盲肠”,也是决不可无,不然,就会被当作一句套话,了无新意。这叫做以前人所有的手法(清真家数),写前人所无的遭际(时代生活),即梁启超所谓“以旧形式含新意境”。
清代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派,推尊词体,强调词的比兴作用和社会意义,如张惠言说词要“意内而言外”,要“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发扬诗骚的比兴传统;周济则说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强调“诗有史,词亦有史”。这一派理论,对沈祖棻创作的影响更大。
汪东说沈祖棻词有三变: “方其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情妍妙,故其辞窈然以舒”,此其一。“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则触忌讳,茹之则有未甘,憔悴呻吟,唯取自喻,故其辞沉咽而多风”,此其二。“寇难旋夷,杼轴益匮。政治日坏,民生日艰。向所冀望于恢复之后者,悉为泡幻。加以弱质善病,意气不扬,灵襟绮思,都成灰槁,故其辞澹而弥哀”,此其三。[5]
而第一阶段的词作,是被作者付之一炬了。事见《水龙吟》词,小序云:“与千帆共检行箧,得旧日往返书简数百通。离乱经年,欢悰都尽,因将绮语,悉付摧烧。纪之以词云尔。”这次焚稿,是作者的一次自我否定,这标志着她的创作,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在研究者看来未免可惜的事,对作者本人未必不是好事。唐代白居易存诗独多(约三千首),付出的代价是使得明人王世懋称“平生闭目摇手,不道《长庆集》。”[6]这就得不偿失。
沈祖棻诗词有一个主题词——“涉江”(词称《涉江词稿》,诗称《涉江诗稿》)。“涉江”本楚辞篇名,为屈原自叙放逐的经历和心情。其转语即“渡江”,自然令人联想到宋室南渡的痛史。用来概括词人身逢国难,乱离播迁的生涯与感受,既是高度概括,又有深厚的文化含量。不少的作品是“将身世家国之恨打成一片”(汪东),堪称词史。例如,写敌机轰炸:
晚云收雨。关心事,愁听霜角凄楚。望中灯火暗千家,一例扃朱户。任翠袖、凉沾夜露。相扶还向荒江去。算唳鹤惊乌,顾影正、仓皇咫尺,又催笳鼓。 重到古洞桃源,轻雷乍起,隐隐天外何许?乱飞过鹢拂寒星,陨石如红雨。看劫火、残灰自舞,琼楼珠馆成尘土。况有客、生离恨,泪眼凄迷,断肠归路。(《霜叶飞》)
序云:“岁次己卯(1939)。余卧疾巴县界石场,由春历秋。时千帆方于役西陲,间关来视,因共西上,过渝州止宿。寇机肆虐,一夕数惊。久病之躯不任步履,艰苦备尝,幸免于难,词以纪之。”敌机轰炸的场面,“写之以雅言”(施蛰存),便是:“古洞桃源,轻雷乍起,隐隐天外何许?乱飞过鹢拂寒星,陨石如红雨”,这样写很唯美,但会不会害意呢?还好,“看劫火、残灰自舞,琼楼珠馆成尘土”几句,终于扳回现实。不像黄遵宪写美国总统选举——“怒挥同室戈,愤争传国玺”(《纪事》)那样,在把陌生的现象运用修辞变得熟悉的同时,不免扭曲事物的本质。
李子对当代诗词有一针见血的批判,他说:“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梳理诗词语言的审美。登楼——如今楼顶不容易上去,看看风景也就罢了,和思乡怀人已经扯不到一块;携手——要是两个大男人,这种动作可不美。貂裘——太贵了点,我想没几个诗人花得起这钱,况且动物保护组织还老说三道四。击唾壶——有点不讲卫生,唾壶也早已更新换代了,如此等等。应该扬弃这类道具化、符号化的旧审美因子,代之以新的审美因子。”[7]
如起沈祖棻于泉下,她对这段话一定会激赏。因为她自己也感到过有此必要,而且进行过“寻求新的审美因子”的尝试:
碧褴琼廊月影中,一杯香雪冻柠檬。新歌争播电流空。 风扇凉翻鬟浪绿,霓灯光闪酒波红。当时真悔太悤悤。(《浣溪沙》)
这是一首刺时的令词。“电流”、“风扇”、“霓灯”都是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与传统语汇是匹配的,嫁接得一点也不生硬,故汪先生也加以肯定道:“如此用新名词,何碍?”同调之作还有:“电扇风回兰麝腻,冰盘凝雪橘橙香”、“流线轻车逐晚风……播音新曲彻云中”等,《虞美人·成都秋词》中有“银幕新歌”、“(地板)涂蜡”、“歌匣”、“新声爵士”等等,汪评:“善以新名入词,自然熨贴。”虽然还是小心翼翼的尝试,但已指出一个方向。
唐末孟棨论杜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沈祖棻“身历世变,辛苦流离”(程千帆语),亦毕陈于词,而且有意识运用比兴寄托,“推见至隐”,堪称词史。例如《浣溪沙·客有以渝州近事见告者,感成小词》三首,台静农先生曾书一首,并跋云:“此沈祖棻抗战时所作,李易安身值南渡,却未见有此感怀(指以时事入词)也。”
乱笳鸣。叹衡阳去雁,惊认晚烽明。伊洛愁新,潇湘泪满,孤戍还失严城。忍凝想、残旗折戟,践巷陌、胡骑自纵横。浴血雄心,断肠芳字,相见来生。 谁信锦官欢事,遍灯街酒市,翠盖朱缨。银幕清歌,红氍艳舞,浑似当年承平。几曾念,平芜尽处,夕阳外、犹有楚山青。欲待悲吟国殇,古调难赓。(《一萼红》)
作者自序:“甲申(1944)八月,倭寇陷衡阳。守土将士誓以身殉,有来生相见之语。南服英灵,锦城丝管,怆怏相对,不可为怀,因赋此阕,亦长歌当哭之意也。”唐高适《燕歌行》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名句,痛心战士忠勇而将帅不得其人,一面是轻生赴死,一面是醉生梦死,对举之、令人怵目惊心。此词之沉痛,大体近之。
沈祖棻还擅长以成组的作品纪录当下的历史。这种做法,可以远肇杜诗(如“三吏”“三别”,当然还可以追溯更远),或称连章体。连章体既能适应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之需要,又具有如下特点:单篇具有相对独立性;组合在一起又彼此关联,有序地表达同一主题。简言之,即可化整为零,又可聚零为整。成组的有序性虽强,却并不妨对单篇作品,独立地加以欣赏。集中组词甚多,如《临江仙》八首,《浣溪沙》六首,《鹧鸪天》八首等等,堪称力作。
碧槛瑶梯楼十二,骄骢嘶过铜铺。天涯相望日相疏。汉皋遗玉佩,南海失明珠。 衔石精禽空有恨,惊波还满江湖。飞琼颜色近何如?不辞宽带眼,重读寄来书。(《临江仙》八首之七)
《临江仙》组词作于1938年秋,第七首写战局失利,汪精卫投敌。程千帆笺注:“碧槛”三句,喻沿海沿江名城沦陷,敌军长驱直入,流亡至后方之人民与故乡相距愈远也。“骄骢”,寇骑也。是年10月,广州失守,武汉沦陷,故曰“南海失明珠”,“汉皋遗玉佩”。12月,汪精卫叛变,由重庆逃往河内,发表投敌宣言。汪少时从事民族民主革命,尝自比神话中衔木石以填沧海之精卫鸟,而晚节不终,堕落为汉奸,故曰“空有恨”。“飞琼”句,虑蒋介石难以承受此挫折,并望其不变抗战到底之初衷也。“飞琼”指蒋,“颜色”喻心情。“寄来书”指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所发表之自卫宣言。
这类有特殊历史背景,专事比兴的词,也就更加接近郭璞游仙、义山无题,而不是小山词了。或曰“取径二晏,归于清真”(吴世昌《诗词论丛·致荒芜函》),其实应该说是归于飞卿、或归于常州词派。诚如程千帆先生所说:“大抵作者东归后所为美人香草之词皆寄托其对国族人民命运之关注,尝谓张皋文(张惠言)求之于温飞卿者,温或未然,我则庶几。”这是一种优长,也是一种弊端,钟嵘《诗品序》说:“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汪先生有一段总评性质话:“《涉江词》令慢皆工,清婉之中,兼饶沉郁,伤时感事之作,或托诸屈原香草、郭璞游仙。其间微意,有非时人所能领会者,易世以后,谁复解音?此所以有(知音)愈来愈少之叹也。”(《寄庵随笔》)如果同时代的读者,没有程先生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笺注都难以索解,怎么能够寄望于后代的知音呢。因此,作者自纠其偏,或酌用赋法,“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钟嵘),斯为不隔,似更为可贵:
辛苦征人百战还,渝州非复旧临安。繁华疑是梦中看。 彻夜笙歌新贵宅,连江灯火估人船。可怜万灶渐无烟。(《浣溪沙》三首录一)
何处秋坟哭鬼雄?尽收关洛付新烽。凯歌凄咽鼓鼙中。谁料枉经千劫后,翻怜及见九州同。夕阳还似靖康红。(《浣溪沙》六首之一)
谋国唯闻诛窃钩,嵯峨第宅尽王侯。新声玉树几时休。何止百年宗社感,真成万世子孙忧。渐渐麦秀望神州。(《浣溪沙》六首之三)
前一首写抗战中“渝州近事”。后两首写抗战结束,内战又起,国事堪忧。“翻怜及见九州同”,反陆游《示儿》诗意而用之,悲苦更甚。“夕阳”句典出《宋史·五行志》:“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庚申,日赤如火,无光,盖亡徵也。”读之真觉惊心动魄,几乎一字千金矣。
由此可知,沈祖棻的令词更近温、韦、南唐,而不是小山,有时序的原因。“夫声音之道,与政相通;情感之生,与物相应。彼处成周之盛世者,必不得怀《黍离》之思;睹褒妲之淫乱者,又岂能咏《关睢》之什?彼其忧欢欣戚,有不期然而期者,非作者所能自主也。”(汪东《涉江词序》)因而,反是作者的闲适之作,更近于小山:
羞借清尊理旧狂,红楼珠箔但相望。十年空忍将枯泪,一夜重回未断肠。 欢意少,别怀长。凭栏争惜更思量。西风不管黄花瘦,自向闲庭做晚凉。(《鹧鸪天》四首录一)
何止琴尊减旧情,炊粱剪韭事全更。泼茶永昼书难赌,数漏寒宵梦易惊。 绫作褓,乳盈瓶。熏笼残烛到天明。无端低咏闲吟趣,换得儿啼四五声。(《鹧鸪天》)
可见,沈祖棻令词与其慢词路线不同。令词从选调到写作,都是北宋一路,“标格甚高,小令不作欧晏以后语”(施蛰存《涉江词钞》后记)。本来,《浣溪沙》、《临江仙》、《鹧鸪天》、《蝶恋花》一类北宋人钟爱的词调,多五、七言句,与近体诗近。作者更能做到自由地写,而非刻意地“填”,有含英咀华之妙,而无裁红量碧之虞,故能流畅浑成,耐人寻味。
诗词大家必为第一流作者,如沈祖棻者是;第一流作者不必为大家,如晏几道者是。而沈于晏,却有“一生低首”、“情愿当丫头”的话,这不全是贵远贱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晏有当家的词。任何人一提晏几道、言必称《临江仙》、《鹧鸪天》,就像一提到苏轼、言必称大江东去、丙辰中秋,一提到李清照、言必称《声声慢》、《一剪梅》一样,仿佛有了这几首当家词,余词不传无伤也。对小晏、大苏、李清照可,对沈祖棻则不可。她最负盛名的词作,是那首《浣溪沙》: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颦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浣溪沙》)
“此篇1932年春作,末句喻日寇进迫,国难日深。世人服其工妙,或遂戏称为沈斜阳,盖前世王桐花、崔黄叶之比也。祖棻由是受知汪先生,始专力倚声,故编集时列之卷首,以明渊源所自。”(程千帆)但你不能用它来作沈祖棻的标志。汪东评沈的另一首《浣溪沙》说:“在他人集中仍是佳词,于作者则常语也。”《涉江词》篇篇可读,求其一以当十之作,反不可得。前人说“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王世贞),一样的道理。所以在任何选本中,她总会吃亏的,如果没有数量保证的话。
这是“沈祖棻现象”——反而是在诗和新诗、即不被称为大家的领域,沈祖棻能以少胜多,占得风流。一首题为“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的七言律诗,轻轻松松就达到了这种体裁的最高水平。
合卺苍黄值乱离,经筵转徙际明时。
廿年分受流人谤,八口曾为巧妇炊。
历尽新婚垂老别,未成白首碧山期。
文章知已虽堪许,患难夫妻自可悲。
完全是杜甫的做派:沉郁顿挫,流畅清新,不经意间,通篇皆对。篇中巧妙地将杜甫《新婚别》《垂老别》篇名铸成一句,而饶有别趣,真是写杜甫所未见之奇穷,以杜甫所未有之奇句了。还有一首五言的《早早诗》,以元、白式的浅语,写左思、李商隐的题材[8],获得同辈名流(包括朱光潜)一致的叫好,甚至认为是她最高的成就,甚至说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空前未有的佳作”(舒芜)。平心而论,此诗的价值在诗内、更在诗外。它一方面“用童心的灯火照亮了苦难和屈辱的灵魂的暗隅”(同前),另一方面记录了一代知识分子灵魂之难。诗末有一段絮絮叨叨,却不可少:“爷爷放牛去,家家是老师。因取眼镜戴,一册两手持。为摹看书状,迂腐诚可嗤。儿勿学家家,无能性复痴。词赋工何益,老大徒伤悲。汝母生九月,识字追白傅。少小弄文墨,勤学历朝暮。一旦哭途穷,回车遂改路。儿生逢盛世,岂复学章句。书足记姓名,理必辩是非。……”有人说是反讽,也有人说是一本正经。“诗可以观”,在啼笑皆非之中,读者认识了一个时代。至于她那一首署名沈紫曼,以《别》为题的、短小的新诗,直令人惊艳:
我是轻轻悄悄地到来
象水面飘过一叶浮萍
我又轻轻悄悄地离开
象林中吹过一阵清风
你爱想起我就想起我
象想起一颗夏夜的星
你爱忘了我就忘了我
象忘了一个春天的梦
这首诗表现爱的矜持,无论就内在韵律,还是语言关系而言,完成度都很高,脍炙人口不逊色于小山词。沈祖棻的审美理想,似乎在这里得到了实现。诗经有一首《郑风·褰裳》也表现爱的矜持——“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彼此的文野、精粗之分,一目了然。真的,那怕只读到这样一首小诗,你就不好说“新诗迄无成功”。
(2013年6月应《中华诗词》之约而作)
[1]祖棻生于书香世家,其曾祖沈炳垣是清咸丰内阁大学士,祖父沈守谦长于书法、通诗词,与吴昌硕、朱孝臧一流人物为友。遭遇国难当头,饱经颠沛流离之苦。以及与程千帆婚姻的般配。都与李清照相似。故沈尹默题诗道:“昔日赵李今程沈,总与吴兴结胜缘。”
[2]晏几道《小山词自序》:“《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窃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
[3]这是《随园诗话》的说法。郑板桥原来的印文是“青藤门下牛马走”。
[4]沈祖棻《宋词赏析》关于晏几道《临江仙》一文。
[5]见汪东《涉江词稿序》。
[6]见王世懋《艺圃撷余》。
[7]见李子《远离青史与良辰》。
[8]左思有《娇女诗》,李商隐有《骄儿诗》,均其所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