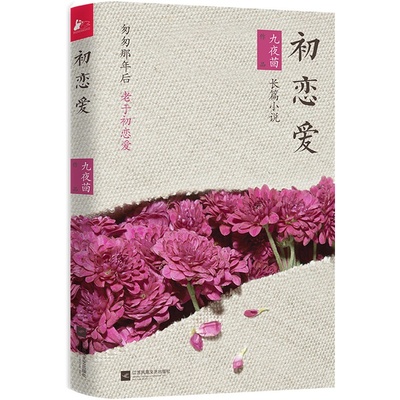发自:云南个旧2013-04-18 10:44:25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中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已累计达69座。和大多数城市人去城空的命运不同,个旧是一个更加特殊的样本。数以万计的矿业工人留守故土,他们所挣扎求存的“工人村”,从昔日的“光荣家园”沦为暴力和毒品泛滥的“法外之地”。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几代产业工人将个旧建设成为“中国锡都”,工人村由此诞生。如今个旧正在转型,“工人村”却成为这个新型工业化城市被遗忘和最疼痛的部分。
云南个旧,蹲在山坡上的锡矿工人,远处是露天的洗矿池。选矿厂逐一关闭,留下满山矿坑和上万失去生计的工人。 (南方周末特约摄影 程新皓/图)
“地鼠”掏空了城市的底部,房屋倒塌,地陷路裂。盗矿者用长刀、猎枪甚至炸药火并,护矿队员参与偷矿,警察被公然威胁。
1.2万产业工人下岗。工人村毒品和性交易泛滥,个旧已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与当地人口数相比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名单。
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存在“严重的群体性贫困、社会环境恶化问题。刑事犯罪率和总数也均在高位运行”。
云南个旧,锡矿工人村里,曾经的盗矿者、如今的艾滋病人程武终日躺在床上,等待死亡降临。
这里曾是“中国锡都”。和所有因矿而生的资源型城市一样,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几代产业工人在这个边陲小城建起“共产主义天堂”;在大工业飞跃时期,资源型城市普遍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耗尽蕴藏,陷入困境,大多人去城空。
程武所在的个旧是更加特殊的存在。在这个有着两千年开采史的“锡都”,人们安土重迁,以锡为生。随着1990年代矿藏逐渐耗尽,上万名工人下岗,但和其他空降式的资源城市不同,他们大多留在故土,艰难度日。
2008年,个旧进入中国首批宣布的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之列。数百家选矿厂逐一关闭,取而代之的是盗矿与抢矿团伙——其中不乏昔日的产业工人和工人子弟;曾经的火车站成为红灯区,廉价的下岗女工充斥其间;由于地处边境,毒品交易与艾滋病泛滥。
矿藏耗尽之后,工人村——锡矿工人昔日的荣光——成为这个城市中最先坍塌的部分。贫困、暴力和毒品正在侵蚀工人村濒临衰竭的生命,以特殊的方式演变成“法外之地”。
大哥
程武最常用的谈判方式,就是身上绑满炸药,留下一指长的引信,冲进对方房间,点燃打火机:“不想死的就把矿让出来!”
从昆明出发,出石林,过开远,沿着如刀般刻入云贵高原的326国道一路向南,一座环湖而建的城市迎面而来。这就是位于红河北岸的“锡都”——个旧。
新中国成立以来,锡始终是这个城市的基石,矿石从山间挖出,北至昆明、东出广西、南下越南,为人们提供生存资本。一度,这座边陲小城人口密度堪比上海——12平方公里的城区里,聚集了十余万的产业工人和近四十万常住人口。
而今繁华散去,作为资源意义上的个旧却处处可见衰败景象:群山满目疮痍,裸露着被铁铲、炸药与挖掘机刨开的斑驳伤口;数百家选矿厂被勒令关闭,闲置的机器锈迹斑斑;小镇上为矿工而建的电影院也早已关闭,红砖墙上爬满白碱斑。
程武就在这样的小城里等待死亡。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的他,体重由140斤下降至80斤。他曾是纵横一时的抢矿者,因矿而走上黑道、享尽荣华;也因矿而吸毒染病,最终走入绝路。
他常想自己这一生沉浮,与这座因矿而生的城市何其相似:“骤起骤退,就为了几块石头?”
1986年,18岁的程武不愿像父母那样做个寒酸工人,选择了当时最流行的路:上山抢矿。
那时正是私挖滥采最严重的日子,山上的锡矿多,直接裸露在地表。程武总是带着三辆东风大卡车的弟兄,四处游荡。一旦看中了矿,便跳下车:“这块矿我们要了!”
也有对方不服的情况,车上的兄弟们就会抄起长刀、猎枪,跳下车直接火并。最严重的一次,程武的右手差点被砍了下来,仅靠一些皮肉耷拉连着。
采到的矿极易出手,每天能赚两万。两年时间,20岁的程武便成了个旧最著名的大哥。程武很享受锡矿所带来的荣耀:卖完矿,上百个小弟总会跟在身后,“四哥”“四哥”地叫着。
好时光并未持续太久。1992年,程武用刀将人砍伤,被判入狱。1997年,出狱的他想要干回老本行,却惊讶地发现:多年乱采滥挖,从前随处可见的地表矿已难觅踪迹。
程武却没有停手:地表矿没有,地底下还有。但纵使如此艰辛,竞争也非常激烈。程武曾带人往下挖一处好矿源,眼看就要挖到了,却有人挖了一条捷径,抢到了前面;谈判也更加充满火药味,程武最常用的谈判方式,就是身上绑满炸药,留下一指长的引信,冲进对方房间,点燃打火机:“不想死的就把矿让出来!”
2001年,云锡集团矿区被偷挖的原矿就达二十多万吨,损失数亿元。
那时的个旧黑恶势力一度猖獗,有时连护矿队员也身兼偷矿者的身份。无奈的矿方,把退休老人也组织起来,成立了“老年治安联防队”,队员平均年龄66岁。
多年来,个旧屡屡对矿区治理整顿,情况却未好转。资源的日趋枯竭,催生了人们的不满心态与求富欲望,这让抢矿更加组织化,也更趋向暴力。2007年,一个犯罪团伙雇用了近百人的背工队伍,装备着猎枪、长刀及自制爆炸物“天雷”,浩浩荡荡开进了个旧市内一个矿区,抢走了大批矿石。
甚至连村庄也卷入了抢夺。个旧贾沙乡陡岩村的村民,不满祖辈的山被掏空却无法得利,就曾多次拿着枪械冲进当地矿山,疯抢锡矿与数百斤的炸药。
然而,这样血腥的抢矿盗矿,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这首先缘于矿的枯竭。2008年,个旧矿区的锡保有储量已不足探明储量的10%,仅可维持3至5年。

个旧地处边境,靠近金三角。毒品和艾滋由此泛滥。 (何籽/图)
主人
工人们在城市里都是趾高气扬的,“因为大家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整个红河也流传着“嫁人就嫁云锡人”的说法。
不仅是盗矿者。人们发觉,矿石的枯竭,也如章鱼一般控制着他们的生活。
63岁的宋爱华,如今是一家色情KTV的老板娘,每日都要站在街上,替一群打扮妖艳的性工作者招揽生意。头发花白的她,总会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
她想起工人村——位于城南老阳山上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建筑群。1956年,宋爱华随父亲坐着窄轨小火车来到个旧,趴在车窗上,望着远处红砖楼自山脚蜿蜒而至山顶,惊叹极了:“真像空中花园。”
1949年之后,位于个旧的云南锡业公司(下称云锡)被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工人村由此诞生。宋爱华回忆,由云南抽调八州人力物力修建的工人村,洋溢着那时特有的“共产主义是天堂”的理想主义气息。
上百栋“苏联专家楼”,均仿照前苏联三层起脊闷顶式住宅建造,对称、方正;内部设计也秉承“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没有厕所,一律上公厕;厨房也是两三家共用。
年幼的宋爱华,常会听到小楼里有人唱《三套车》、《阿廖沙》。歌声悠扬,一如这个西南边陲小城里日渐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那时工厂的姑娘们都会用报纸包上一双舞鞋,下班后奔向个旧工人文化宫跳舞。
人们也沉浸在集体主义的自豪中。宋爱华记得,每到周末,工人村都会掀起一场“卫生红标签大赛”。她站在山上俯瞰,几乎每家都在打扫卫生。
1975年,宋爱华如愿进入云锡选矿厂。那时她觉得工人们在城市里都是趾高气扬的,“因为大家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工人村初建时,杨树清家还是老阳山下种田的农民。小时候,他们称呼工人村的子弟为“上面的孩子”。
他羡慕工人村的安逸生活,为了能吃到“8个菜,还随便添”的工人饭,杨树清还偷偷用家里的菜去交换饭票。
一切荣光都因矿而生。
占世界十分之一、中国三分之一的锡储量,让个旧在1951年建市后迅速膨胀。1958年,个旧甚至取代蒙自,成了红河州首府。整个红河也流传着“嫁人就嫁云锡人”的说法。
与118座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资源型城市一样,新中国成立伊始,个旧就在赶英超美、实现工业化重责的驱使下狂飙突进;而工人们,也怀揣着革命激情投身其中,燃烧一生。
枯城
宋爱华从迭矿的冰水里爬出来,套上棉裤和外裤,在公示栏的提前下岗名单中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双腿颤抖个不停。
宋爱华从未想到,衰败伴随着疯狂猝然而至。
1980年代中期,在中央“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号召下,全国矿场掀开了大规模的群采。个旧也一样陷入热潮,每个乡镇都分到了相应的矿区,一些矿区没人要,政府还到各个乡镇动员。
一时间,十余万采矿大军涌入了一百来平方公里的矿区。矿区秩序也随之混乱,盗矿与抢矿频发,云锡集团老厂锡矿书记周志坚回忆:“很多人都在这里随意采矿,整座矿山被挖得千疮百孔。”
恶果接踵而至。据云锡集团宣传部长黄梓嘉介绍,进入1990年代,个旧地表砂矿的锡矿资源过早消失了。1993年起,云锡连续几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
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城赴个旧等地调查后称:“越是有资源的地方,越是容易出现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被经济学家称为“资源诅咒”——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会让城市步入歧途,进而在资源枯竭后将城市推入死境。
1997年后,不堪重负的云锡开始了被称为“拆船造舰”的下岗分流,三年间裁减了1.2万从业人员。一年后,宋爱华所在的新冠采选厂也停产了,上千名职工下岗。
宋爱华记得,那天她刚从迭矿的冰水里爬出来,套上棉裤和外裤,和工友们一起挤在宣传栏前看提前下岗名单。宋爱华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双腿颤抖个不停。
45岁的宋爱华不得不艰难求生:来到个旧火车站,开了家只有两个小房间的小歌厅。
此时的火车站业已废弃,成为全市著名的红灯区。曾经的铁轨、候车室变成数十间歌厅、酒吧、按摩院,主要收入来源是向客人介绍小姐。
刚到火车站时,宋爱华坚守着“工人阶级的骄傲”,不肯做色情生意。她甚至提醒客人哪些小姐吸毒染病,还劝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要来这儿,“我和她们不一样”。
城市的下滑,还是不由分说地将宋爱华拖下泥潭。2003年,红河州政府决定,将首府由个旧迁往蒙自;同年,个旧陆续关闭7座大中型矿山,失业和贫困人口大量地涌现。
生意惨淡的宋爱华,不得不放下尊严,站在街上拉客。“办事”的地点就在沙发上,一次的价格是70元,她这个“老鸨”则可以抽10元至20元。
宋爱华总想起几十年前,工人村的家里,木地板总是打磨得锃亮。如今,每个喧嚣的晚上,宋爱华来到店里,看着满是污渍的沙发,忽明忽暗的红色灯泡,感觉屈辱。她甚至不愿坐在沙发上。
老人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有一点却明白了:矿是一点点挖完,人也是一步步低头的。
拯救个旧病人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邵世伟 记者 范承刚 2013-04-18 11:13:31来源:南方周末
李曼,个旧的一个组织“苦草”的负责人,由于缺乏经费,一些救助当地艾滋病性工作者的活动已经停止。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个旧是全国艾滋感染者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
除了政府在行动,个旧艾滋病人群体也起来自救。除了治病和生存,他们更渴望的是尊严的回归。
1980年代,靠近云南南部边境的个旧市便开始受到毒品的侵扰,艾滋病也在1990年代中期紧跟而至。至2010年,个旧已成为全国HIV感染者人数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
而个旧的资源枯竭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由此产生的大量失去生计的产业工人成为毒品和疾病的主要受虐者。一项媒体报道的数字是,在人口40万的个旧,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5400多人,其中至少70%以上感染艾滋病毒。
2004年,当地政府进行大规模筛查,干预控制艾滋病。同年,云南省第一个国家海洛因成瘾者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在这里启动。“出乎预料的高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家如此评价。
民间也没有坐等。2005年起,个旧陆续成立了十余家艾滋病预防、关怀民间组织,其中有些是艾滋病感染者自发组织的。
美沙酮与清洁针具
在当地卫生系统,曾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有100个被感染的,其中80%是吸毒人员。”救助吸毒人员,成为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
2004年4月,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启动。仅第一个月,治疗点便接纳超过80名病人且无一人脱离治疗。美沙酮是一种毒品替代物,也是国家严格控制的鸦片类麻醉药品,流到黑市上便成了毒品。
治疗中心主任闵向东2005年对来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我们一直都在呼吁要为吸毒者公开提供一种替代药物,以阻断他们共用注射器吸毒的行为。”
到2010年,个旧市已有2家美沙酮门诊以及4个拓展治疗点,服用美沙酮人员累计已达1000余人,管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59人,其中接受抗病毒治疗144人。
大多数吸毒者感染艾滋病都是由于共用针具,交换针具,就成了个旧卫生部门的另一项举措。从2004年开始,云南个旧的吸毒人员便可以在当地的艾滋病咨询中心免费领取到清洁的针具,用于静脉注射吸毒。
开展交换针具的初期,也曾发生过卫生部门与公安部门工作方针的矛盾。有的吸毒者刚交换完针具出去就被公安人员抓走,针具交换处一度门可罗雀。
在多方协调下,公安部门改变了方法,尝试去配合卫生部门的新举措。“我们要看看这种做法的效果到底如何。”一位警察学院负责人说。
直到现在,无论是美沙酮治疗还是针具交换都仍旧存在着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议。前者被认为是主动提供毒品,后者则被称作是在默许吸毒。而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方法遭到很多国家的禁止。
但对于个旧来讲,也许别无选择。闵向东介绍,开展这两项工作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戒毒,而是为了预防和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个旧这个出于现实考虑、在争议中前行的做法最终获得回报。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在29个实施注射针具交换的城市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发生率下降了5.8%,而在没有实施注射针具交换的52个城市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发生率却上升了5.9%。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顾问夏国美女士对此评价称,“中国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工作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自救的“苦草”
在个旧官方采取种种举措对抗艾滋病的蔓延时,民间也组织起来开始自救,其中还包括不少艾滋病感染者。
2005年,艾滋病感染者李曼成立了“苦草”工作室,服务人群与工作人员均为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与“苦草”同一时间成立的还有十余家防艾民间组织,如关注吸毒者的“胡杨树”,重视社区预防与关怀的“葵花园”等。他们更多地关注政府照顾不到的领域,如对性工作者的预防培训以及生产自救。
成立之初,“苦草”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向性工作者们普及防护知识避免交叉感染,“要让大家活下来”。此前由于缺乏艾滋病相关知识,许多性工作者在感染后便放弃了预防措施。李曼便曾见到一位苦草成员因为一直进行无保护性交易,导致了严重的交叉感染,并最终死亡。
几乎每个月“苦草”都会举办阳性预防的相关培训活动。因为频繁地有陌生人员出入,还曾有邻居打110举报“苦草”工作室说看到有一群“小姐”在聚众吸毒。
2009年,“苦草”工作室进行了一次针对性工作者常客的调查。结果发现,80名常客中,只有6名是艾滋病感染者。“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起作用了。”
“漂漂亮亮地走”
活下去之后面临的便是生存问题。
2008年,“苦草”工作室贷款开办了一家洗车场,起名为“芳草”,意思是苦尽甘来。
洗一次车要1个小时,收入仅有10块钱。但让李曼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成员都抢着想到洗车场工作,“来不了的还一直在抱怨”。最终洗车场让8名“苦草”成员告别了性工作。
“从来没挣过那么干净的钱。”杨慧在回忆洗车场生活时说。
随着工作的开展,“苦草”工作室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断有“姐妹”慕名加入。到2012年,“苦草”工作室已有注册成员276人,全部为感染艾滋病的性工作者。
出于吸毒者对自身身份的顾虑,许多人不敢去卫生部门交换针具,他们更愿意相信“胡杨树”这样的民间组织。“可能是因为同为吸毒者的关系吧。”胡杨树负责人辛德明说。
在民间组织活跃时期,有时候到了周末甚至会出现几家同时举办活动争抢成员的场景。“我们一下成了宝贝。”艾滋病感染者张琴说。
但与政府部门一样,民间组织也面临着种种难题。进入2010年后,由于国际基金组织的撤离,大多数民间组织陷入了资金紧张的困境。“苦草”工作室的阳性预防工作便不得不停止,“胡杨树”的吸毒人员走访也已暂停了很长时间。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才能救更多的人。”辛德明说。
经费紧张的同时,大批个旧的艾滋病感染者开始进入发病期,临终关怀成了各家民间组织的主要工作。
从2006年到2013年,“苦草”共送走48名成员。为让成员们能“漂漂亮亮”地走,李曼学会了遗体美容,还坚持每次都让尽可能多的成员参加送别。
这多少让其他人感到了一丝宽慰。“自己死后要是也有这么多人送别,那就不怕了。”张琴在回忆为成员送别的场景时说。
如今死亡不断降临,但对于李曼和更多的个旧病人来说,恢复生而为人的尊严才是他们更大的渴望。
“即使病了,我们也是一样的生与死,一样的人。”
“跟下地种田一样”:“十元店”性工作者生存现状调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发自:广西玉林最后更新:2012-04-27 17:48:51来源:南方周末
在十元店,“流氓燕”为四个人提供了免费的性服务。其中一个老人五十多岁,听说不要钱,他问为什么?“流氓燕”说:我是北京派来的。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不平等……性,居然也不平等。 (受访者/图)
在中国许多隐蔽而又随处可见的角落里,性交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在规模运作。严厉的刑罚和运动式打击,并没有让“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问题,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没有窗户,更像个潮湿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床头的电灯泡,拖着长长的电线吊在头顶。
吴献芳用一个揉皱的红色塑料袋裹住灯泡,粗糙的光线于是变成一片红色柔光。据说这种光线下的女人皮肤最好,看上去没有皱纹。
吴献芳48岁了,体型发胖,背面看直发乌黑,没人看得出是白头发染的。单人席梦思床占去了房间一半面积。她整天在床上躺着或坐着,等客人来。
这栋旧时骑楼改造的小旅社里,住着三四十个吴献芳的“姐妹”,年龄最大的有62岁了。年过四旬的农村母亲,构成了这群性工作者的主体。
当地人把这样的地方称作“十元店”。客人往往是本地老头子,或者中年的外地农民工。
每次的交易价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这些贫困性工作者同样面临被处罚、疾病、暴力、歧视的风险。
“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
吴献芳所在的县城,人口逾百万,涉及性服务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闲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业界人士把性工作者归为四档:最贵的如夜总会“天上人间”;宾馆和洗浴中心的“叮当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闲店和发廊,收费过百;第四如站街女,约六十元。而十元店,几乎是低到尘埃里,属于性产业中的“大排档”。
吴献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条细长的巷子里,背朝繁华的商业街。一进门就见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熏过的气味。楼共三层,每层9个单间,每间房比乒乓台稍微大些,木板隔开,透风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报遮挡。
毋须身份证,也毋须押金,只用15元,女人开一个房间即可营业。有姿色的,再赶上好运气,一天能流水线似的接十几个客人,每月挣两千来块不是问题。也有一整天开不了张的。总体看来这里生意不错,老板把地下室也利用起来,楼顶也搭了简易的房子。
姐妹们达成的共识是:来的客都是一群长期压抑的人,外出务工的,没老婆的,憋久了才来,平均5分钟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个白背心的老头子摸着阁楼的扶手上楼了,背后还破了两个小洞,头顶是“地中海”,背过手慢慢踱着步子,看到门开着的,就一间一间屋子来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个躺在床上吹风扇的大妈,开始讨价还价,“多少钱?”“没病吧?”
忽然老板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着大号塑料桶集体“出洞”了,楼道里吵吵嚷嚷。这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这里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热水也是限时供应。每天两次:上午八九点,下午两点。
开放完毕后,老板把水龙头锁上。
四处都黏糊黏糊的,墙,地下,床上。
吴献芳打好水回到房间,用一层硬塑料纸封在桶口,这样可以温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么收拾,头发乱糟糟的,吴献芳算爱干净的了,屋子里有条有理,她舍不得花钱买洗液,清洁工作也就指望这桶水兑点盐巴——盐装在一个可口可乐冰露的空瓶子里,放在房间里潮湿的墙角,旁边还有一个装药酒的娃哈哈饮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来喝两口。一个黑坛子装米,说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里自己煮饭,烧的是老板从隔壁垃圾场捡来的木头块,空气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为了保证客源,这里的女人大多数不使用安全套——何况这玩意还可能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吴献芳有时用,有时不用,用她的话说,“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她这套朴素的检测标准是:外表干净的应该没病,衣服破的旧的一定要防范。
吴献芳从来没有做过妇科检查。妇检的价格三十块,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风险,接三个客人才能挣到的。身体异样的时候,她坐车到乡下打一种叫“消炎针”的吊瓶,二十多块钱,说是青霉素,消肿以后立即开工。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五六年过去,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很勤快,“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疲沓了,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
做这行之前,苦活累活吴献芳没少干。她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坳里,方圆只有9户人家。女娃子没书读,她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后来她结婚生子,老公又赌又嫖还打人,她被男人伤透了,拖着两个儿子走了——没离婚,反正结婚证也没领过。
在异地他乡,她喂过猪,进过编织袋厂,还上工地,把石灰浆从一楼扛到四楼,每个月挣百来块,怎么都喂不饱两个儿子的口。难捱的时候她想过:实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带儿子一起死。
就这么扛到了三十来岁。有一天,一个女性老乡来找吴献芳,神神秘秘地对她说:“跟我走,保你挣大钱。”于是,吴献芳被带到广西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县城里。直到被扔进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这个来了。
开始吴献芳说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说话,闷房间里呆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费和车费。这时来了一个乡镇干部,肯为她出60块的“高价”,天天来,单守着她。第三天,吴献芳从了。
认为自己“走投无路”,几乎是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圆”不怎么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说话。有人说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说她老公又赌又嫖。女儿跟着她住县城,念小学四年级,从小就自己做家务。女儿越乖,桂圆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个小孩,她老公是游医,医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监狱里叮嘱:“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袁丽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总是哭丧着脸。她老公跟别人好上了,不离婚,还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着疤,有家不敢回。
这是一群来自农村的传统而贫困的女人,对她们,命运如一杆闷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小孩子上学要钱,农村盖房子要钱,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钱。
没有学历、技术、年龄限制,这个几乎零门槛的“工种”接纳了她们。
吴献芳不识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攒的钱都托老乡存到卡上,寄回家里。儿子是她最大的盼头。这些年,大儿子当了司机,倒插门嫁到了天津农村。二儿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阵天天要钱,后来才知道他“滚传销头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电话里对着二儿子哭,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总有个烂盆子在脑袋里敲,时间一长就拼命掉头发,直到秃头。为了不吓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块钱买药吃。不曾想,吃了药长出来的全是白头发,从那之后,她开始把头发染得乌黑。
“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姐妹们里流行“找个有钱人”,所谓有钱,就是那些每个月肯为自己花上几百块的老头子。事实上,除去吃饭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几百块。房租也涨了,每间13块、15块。
即便一天24小时都用上,也总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让她们转眼间一无所有——扫黄。
常规检查时还好,听说老板在公安局里有人,有事就会通个气。山雨欲来时,老板总能及时叫姐妹们躲起来,关灯闭门暂停营业,等警察撤退后再开张。
“最怕有坏人‘点水’。”吴献芳说。所谓点水,就是别人设套搜集了证据,赶紧打电话点对点举报,警察一来,人赃并获,跑也跑不掉。得罪客人、生意太好,这些都可能惹来麻烦。
带进局子里,第一次拘留15天,第二次劳教一年并通报家人,要么就罚款3000元。3000元,这对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意味着——她必须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兔年年底的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妹”就出事了。本来她买了当天下午六点回家的火车票,下午洗完头准备回家,突然来了个客人,她想着顺便接一个,结果中招了。三天后她出来了,据说罚了3000元,她收拾东西回老家,没再露过面。
几乎每个人都出过事。对这些不富裕的性工作者们来说,罚款远比拘留要可怕。
有人咬破手指往内裤上抹,有人索性把命都豁出去了,撞墙要寻死。有时能奏效——一次,王菊花被捉拿在场,瞅准空一脚踩在三楼栏杆上,警察放了她一马。她特别害怕读大学的儿子知道这些事。她总是对他说:妈妈在糖果厂打工,好多糖果,吃啊吃啊就长肥了。
吴献芳也被抓过两回,她性子讷胆子小,赶紧交钱赎身,头一回600块,第二次3000元,“怕儿子打不通电话,要担心”,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她曾想不干了,灰头土脸回家了。
谁也说不准,在某个缺钱的时刻,轮回又开始了。2011年,吴献芳又有了新的焦虑:大儿子家没钱盖房子,总归怕亲家瞧不起;二儿子脱离传销,当了司机,但眼瞅着21岁了,没钱找不上媳妇可咋办?她想着想着,又决定回来开工。
这时竞争愈发激烈了,要会勾肩搭背,嘴巴甜点也是本事。吴献芳说自己太本分,年纪大了,也不会说话,就搬到矿井一样的地下室去了。
时运更不济的是,她跟一位老乡起了口角,别人心一横,捡块砖砸断了她右手中指。医药费花了3000块。老板再三沟通,老乡一分钱也不肯赔。吴献芳陷入又一个纠结:算了吧,又是两个月白干了;报复吧,打官司还得花钱,如果警察反倒把自己抓了怎么办?
2012年4月,这些天农忙插秧,来的人也少了。袁丽蓉在为她即将结婚的儿子绣十字绣,王菊花找到新的靠山,《爱情买卖》的手机铃声总响起来,催她晚上出去喝茶,一些姐妹在天井里晒太阳。
吴献芳在地下室里干巴巴地等着生意。虽然搬了砖头把下水道堵住,恶臭还是涌上来。门口时不时有老头子经过,探头来看看货色。
尽管右手永远地残废了,尽管说不清哪天就会被抓走,这时候,吴献芳脸上挂满了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份媳妇家的母猪要下崽,她就要回去喂猪,再不回来了。
(为保护当事人,隐去事发地点,文中姓名为化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