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华先生与作者
赵光华先生与夫人和二女在静心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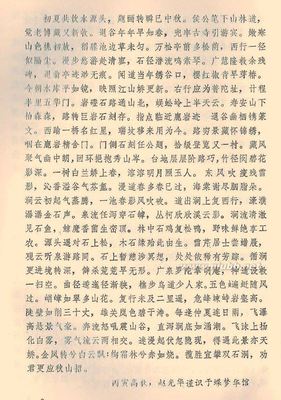
赵光华先生在赠与作者照片背后的题记
赵光华先生赠与作者的黄腊石
1974年,赵光华先生为“退谷出霁图”写的竹枝词
赵光华先生在作者出国前的来信
何日双骑与师还
— 追忆恩师赵光华先生及其他
我的桌上放着一块黄腊石,那是恩师赵光华先生赠送的,已陪伴我近二十年,每当写作前我都要把玩一番,仿佛先生就在面前。可是今日,那黄石却让我悲伤,让我落泪。刚刚得到迟来的信息,赵先生已于8月14日别世。我不敢相信,反复核实,直到看到他女婿的悼文,才知确实。睹物思人,时光又回到了二十八年前……
引路入门
我与先生初识是在1984年,那时北京市政府要编写一部北京建设史,
先生是其中园林篇的编委。开始时以市政府牵头召集各区文化部门开会,要求支持这项工作,然后是专家约稿。我当时在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工作,被单位派去开会,从而有幸结识了赵先生。那时我正忙于“卧佛寺与樱桃沟”一书的修改定稿,虽然已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在北京史学界还没有一点名声。但是先生慧眼识珠,交谈中得知我的写作情况后,马上表示向我约稿。不久,我就收到了北京建设史书编委会的撰写聘请。当时年纪轻轻,真的很激动。
说起来好笑,自己写作《卧佛寺与樱桃沟》一书的初衷与名利思想有关。
我是学中文的,本应搞文学创作,可那时文学繁荣,各种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深感文学之路竞争激烈。一番冥思苦想,决定另辟蹊径,研究北京历史风物本是我的爱好,便想在这上面下下功夫。选择卧佛寺与樱桃沟做切入点,只是觉得离家较近,周末可以骑车考察,根本没有想到后来竟真的走上北京史研究之路,带我走上这条研究之路的正是赵光华先生。赵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北京市研究方面的专家,待人极其和蔼,没有一点架子,
那次会后,赵先生邀请我方便时去他那里深谈。他当时帮助北海公园做
规划,在团城馀清斋办公。我当时在核实卧佛寺周边寺庙史实上遇到困难,不知道还有什么史料可以查找。先生对我说:你很刻苦,但好像对地方史料掌握得还不全面,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请他开个书目给你,应该有所帮助。之后他带我去见了赵其昌先生。记得很清楚,赵其昌先生住在西四,住家是一间大屋,为不影响家人,他在大屋对面搭了个了一个小棚屋,在里面工作,可能是当年的地震棚。赵先生当时正在从浩如烟海的《明实录》里摘选北京史料,就在小棚屋里接待了我们。赵其昌先生是定陵考古发掘的实际负责人,熟悉明史和明代文物,没想到这样一位有名的专家工作环境这样简陋。我明显的感到,这位赵先生是很严厉的人,如果不是赵光华先生带我去,恐怕说不上三言两语就会把我打发走。他听了赵光华先生对我的介绍,顺手开列了一个明清地方史书目。我特意请教元代的书目,他说流传下来的只有一本《南村辍耕录》这本书是我当时不知道的。我们大概只待了三四十分钟时间,就告辞了。之后,赵先生又带我见了周汝昌、罗哲文、徐平芳、万依、于杰、王爱兰等人。1985年,我在《紫禁城》杂志上发表了《妙高蜂醇贤亲王园寝》《健锐营演武厅和教场》两文,经先生向北京史研究会推荐,北京史研究会当年就吸收我为会员。
记得第一次参加北京史研究会学术讨论会时,先生向我介绍阎崇年,我因为紧张本想说“阎老师好”,却只点了一头,显得极不尊敬。当时北京史研究会的会员就我年轻,阎先生可能以为我年轻得意,孤傲清高,哪里知道我紧张得很呢。事后我和赵先生说起此事,深为没有给他老人家做脸而不安,请赵先生再见到阎崇年先生解释一下,赵先生只笑了笑。以后每次参加北京史研究会学术讨论会,赵先生都会为我介绍一些专家,如史树清、张开济、张驭寰、朱家溍、宿白、汪菊渊、侯仁之、李嘉乐、杨乃济、周维权、吴良镛等人都是这时认识的。有一次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会,会议已开始,赵其昌先生正在作石景山古城在哪里的研究报告,突然门外闯进一个鼻子很大的人,进门就连不迭声说“对不起、迟到了”。我看到赵先生和大伙都笑了,连声说“王爷来了、王爷来了”,我问先生这是谁呀?先生告诉我,这是溥杰呀。我惊得目瞪口呆,怎么也想象不到末代皇帝的亲弟弟竞是这个样子!后来在卧佛寺与溥杰又有过一次偶遇,他正在为卧佛寺题联,我对溥老说:“王爷的瘦金体可比原来乾隆爷的御笔要漂亮多了。”“哪里哪里”,溥杰谦虚道。
参加北京史研究会,聆听高人高论,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1986-1988年,我先后在《紫禁城》《法音》《燕都》《曹雪论丛》《文物天地》《古建园林技术》《文物》和《旅游时代》上发表了十几篇关于北京史地风物的文章,其中关于智化寺的研究和《弘法藏》的考证文章,都得到了较好的声誉。
1988年《卧佛寺与樱桃沟》一书问世,此书的出版同样凝结了赵先生的心血。书稿实际在1984年就已完成,那时出书有水平还要有关系,自己不认识出版社的人,每天看着一摞书稿发愁,心想这书要是过十年再出还有什么意义。先生理解我的心情,为了能够顺利出版,亲自骑车带着我去见卧佛寺与樱桃沟管理单位北京植物园的领导杨松龄主任,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终于联系上旅游出版社,还亲自为我作序。先生更像是我的经纪人,那本书得了两千元稿费。先生说,一定要答谢编辑,以后还要联系。亲自选址,在便宜坊请出版社的编辑们吃了一顿饭。
1988年以后,我的文章发表日多,1990年又出版了《古刹瑰宝智化寺》一书,先生很是为我高兴。
成果卓著
赵先生194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系,长期在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所工作,擅长园林规划,熟悉北京园林史。园林规划方面,早期的成果我不清楚,只知道北海公园静心斋的复原整理、紫竹院公园的扩建规划、恭王府的修复整理和圆明园遗址公园的规划都有他的功劳。至于著述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北京园林史上。
北京史学界都知道赵先生是北京园林史的研究专家,无论哪位专家在这方面有疑问都去找他。文革后百废待兴,北京园林史研究一片空白。1980-1981年,先生出版了《北海景物各论》《北海静心斋》的小册子,《北海静心斋》一书也是先生送给我的第一本著作。一般谈到北京园林,都说明清,因为明清园林建筑规模大史料多,而先生立志要编一部系统的北京园林史,对明清之前的辽金时期也下了很大功夫。北京文物研究所所长于杰先生是金史和金代文物专家,先生带我认识于杰时,两人交谈的内容都是金代苑囿。1984年先生发表了“金代北京地区园林史略”一文,受到关注。其后又在1985年发表了 “北京地区园林史略"长文,系统地讲述了北京地区园林发展史,填补了北京史研究中的空白。文中对很多失传已久的宅园和寺庙园林都有提及,使后人了解到北京园林发展的概况。海淀区文物管理所所长焦雄擅长工笔画,他根据史料和自己考察画出一些西郊的小园林图,我曾陪先生访问焦雄。我自己因为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走遍了东起高梁桥西至八大处,南自玉渊潭北达北安河的所有村庄庙底,也向先生提供了很多材料,并与先生实地考察过海淀的乐家花园和西山松堂及玉皇顶的园林建筑。
先生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研究更是成果卓著,先后发表了“圆明园之一景坐石临流考( 1981)”、“长春园建设及园林花木之一些数据(1984)”、“圆明园及其属园的后期破坏倒举(1986)”、“圆明园‘遗迹园林’的悲剧美学原则和整修的过渡形式(1992)”、“圆明园遗址刍议(1994)”、“圆明园遗址园林新议(1994)”、“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利用(1996)”、“整顿圆明园劫余山水宫苑遗址分两步走的观点与设想(1999)”等文。其中关于将圆明园遭劫分为“火劫,金劫,木劫,石劫和土劫”几个时期的划分观点,已被行内普遍接受。
园林离不开叠山造石,先生于园林史研究之余,对假山奇石亦很有兴趣,喜石、爱石、观石、赏石。“青莲朶”原是圆明园内的一座太湖石,1915年移至中山公园。先生很喜欢这座山石,为它写了“绮石 ‘青莲朶’考略(1980)”和“‘青莲朶’赞(1983)”两篇文章,后一篇遣词娇柔,构句华美,令人赞叹,是我阅读的第一篇先生文章。
先生涉猎广泛,著述当然不仅仅这些,“军都陉景物鑑赏综论”就是近几年发现的的一篇先生逸文,没写年代,应是先生的早期作品。
当时的文化人都有自己的书房名字,虽然大多数住宅拥挤并无真正的书房。蝶梦华馆是先生给自己书房起的名字,初时虚拟,分到园林局北太平庄宿舍后,将卧房与客厅合一,才腾出一间小屋做书房。先生的古诗词功底很好,写有很多赞咏园林山水的诗词,可惜未结集出版。记得先生一直津津乐道的是有一年中秋节,先生与周汝昌等文化人,乘船在颐和园赏月,兴致所至做诗唱和,大家公推先生与周汝昌的最佳,当时好不得意。他给我讲过好多人的书房名字,后来我也给自己命名了一间书房“三境斋”。
待若子侄
“你和我儿子年岭差不多,我们把你看做子侄辈,到我家这里千万不客气”,这是赵伯母经常对我说的话,赵先生何尝不是如此。带我出去拜会别人时,只要赶上饭点,就请我吃饭。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是在王府井北的翠华楼。那天去拜会北京建设史书编委的陶宗震先生,谈的已过了晚饭时间,主人的家属已在隔壁吃饭。我父母那时还住在农村,乡村纯朴,如果串门赶上饭点,主人都会客气地邀请客人一起吃点。赶上饭不请一下是不礼貌的,可是城里的风气却不是这样,我还有些不适应。就和赵先生说起这些。正好骑车到翠华楼前,先生说我们进去吃饭。我以为是我的话刺激了赵先生,很是不安,其实大错特错,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赵先生待我如子侄,只要一起出去赶上饭点,必掏腰包请我吃饭,我想拿钱都不行。当然不是每次都去大餐馆,赶上什么就是什么,不过我只记得在大餐馆吃的,记得先生还带我去过什刹海的烤肉季、北海的仿膳和东来顺,更多时还是在先生家里吃饭。我与先生和伯母在一起到不拘束,可是儿子儿媳有时女儿也在,就感到拘谨。逢到这时,先生和伯母都会一劲的劝我不要拘束,吃饭时,有好吃的就会夹到我碗里,也不让我帮厨,后来我和大家都熟了,也就随便了。
因为患癣疾,先生不能饮酒。可是每次我一去,就兴奋的像饮了酒,聊起很多故事。很多名人轶事都是在饭桌上听先生说的,如张伯驹为潘素购承泽园,启功的字是文革时帮抄大字报练出来的,万里副市长在十三陵果园热的脱光了膀子与他闲聊等等。先生最好的朋友是罗哲文与周汝昌,讲得最多的也是他们的故事。先生说,罗哲文实际是梁思成在西南联大时的书童,每日在书房随侍当助手,他没有上过真正的大学,古建学问都是跟梁先生学来的。梁先生很喜欢罗哲文,罗哲文也很聪明。周汝昌学习刻苦,家境并不富裕,回老家时曾一边在灶台边烧火,一边看书。没有钢笔,就把蘸水笔尖绑在细玉米杆上用,胡适先生特别赏识他。
我调到市文物局后,工作较忙,有一段时间与先生联系少了,先生就打电话过来,让我上他家去坐坐。先生知道我单身,名曰聊聊天,实际是请我吃饭。老在先生家吃饭,我也过意不去,有时就买点礼物送去,可是每次都遭到埋怨,不让我花钱。因为当时父母还在农村,能买到一些农村的特产,我就给先生买一些当年的好大米送去,本来是想送给先生和伯姆的,可是每次他们都给钱给粮票,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好像是在做生意。记得除大米外,还送过胡萝卜。
随着相识日久,先生对我越来越疼爱有加。经常对我说,我要是有三个女儿就好了,可惜我只有两个都已嫁人。我理解先生的意思,无论家里还是个人的事情都和先生诉说。先生人缘好,朋友多,经常得到赠书和杂志,凡是我有用的,他都送我。有些书只有一本,他也毫不吝惜。像周汝昌先生的《恭王府考》,开始是内部印刷,数量不多,周先生送给他一本。赵先生见我喜欢,就叫我拿去了,书上还有周先生的题字。
家庭逸事
与先生接触日久,感觉先生已把我当成朋友,很多家事私事都和我说。他给我写信都在名字后加上“同志”两字,只有私下里才叫我“惠利”。
先生大伯母几岁,他们两人是在迎接北平解放时认识的。先生之父曾是冯玉祥手下的军需官,后入股内联升。伯母出身名门,毕业于辅仁大学,父母早逝,一直跟大哥生活,幼时曾在淄博十笏园住过很长时间,她大嫂和李鸿章还有亲戚关系。我的汉语修辞老师吴家珍与伯母有同学之谊,她们每年都聚会,因了这层关系伯母与我很谈得来。她知道很多北洋政客的故事,我的《卧佛寺与樱桃沟》一书里有北洋长江三督之一陈光远墓的介绍,陈光远死时在天津出殡,排场宏大,伯母曾很详细向我讲述目睹过程。有一次把她年轻时的照片给我看,我一看太美了。伯母说那时追她的人很多,其实看不上老赵,可还是让他追上了。赵先生听了不服气,找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让我看,你看看我年轻时帅不帅,弄得我不知说什么好。老两口关系本来很好,可有一段时间却突然紧张,源于赵先生有位年轻的女友,两人在国内本是一种仰慕关系。可那女子去澳大利亚后,来信时竟似恋人口气。伯母知道后很生气,伤心的跟我诉说,要跟赵先生离婚,眼泪都要下来。赵先生怕我误会,忙把信拿来给我看,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那女子的情况。那信写得很长,很缠绵,,信中不称赵老师,而直呼先生的字“君实”。我知道先生生活严谨,劝伯母不要在意,那女子已经在布里斯班嫁给了老外,从信上看应是寂寞无聊,把赵先生当成幻想中的情人安慰自己。伯母力逼先生写信断绝和那女子的关系,方才罢休。我一个做晚辈的,感情经历不多,能说什么。后来事态平息,赵先生应是写了让伯母放心的信,那女子后来也不再写信了。这可算先生家中晚年最大的一次风波。
先生育有二女一子,各有特点。长女早嫁,夫妇和睦,我没见过几面。儿子最小,生性憨厚,儿媳是会计,两人生的孩子是赵先生的小孙子,虎头虎脑,招人喜欢。二女赵淳是个才女,个性强,是赵先生几个子女中最喜欢文史的,婚姻不顺,最让二老费心。先生常常后悔地对我说,当年顾颉刚先生喜欢赵淳,曾向我为他儿子求婚,我考虑顾先生名望太高,怕赵淳过去后不适应,没有答应,现在真是后悔呀!可能是因为大姐夫家是回民,生活习惯不同,赵淳与她弟弟与大姐走动较少。先生与伯母对大女婿看法到很好,说最让他们放心。
最后一面
1991年初,我因为单位职称评的不公,萌生出国之意。因忙于办理各种手续,没当面告知,只给先生写了一封信。先生大惊,知事已不可挽回,急忙回信嘱咐出门注意事项。1993年,我携妻儿回国去看赵先生,那时伯母尚健在,二老高兴极了,见我妻子是外国人,要在外面请我们,我说就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先生家中收藏了很多奇石,让我挑几样拿去。饭桌上,伯母问这问那,先生笑得合不拢嘴,一家人其乐融融,至今记忆犹新。说来遗憾,也许是太熟了,我和先生相识多年,竟没和他老人家单独照过像,只有一张中国曹雪芹研究会成立大会时的集体合影照。那天我向先生索要照片,伯母拿出相册叫我选,我选了一张他们二老和二女赵淳在静心斋的合影。先生沉吟片刻,在背面写了一首旧词题赠。接下来,又陪我们去琉璃厂,荣宝斋,与先生终于有了一张合影。
2005年冬,我再次回国,先生已经搬家,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他们的新住处。先生初住东单公园附近,后迁北太平庄双秀公园旁,这时随儿子迁到石景山区。一见面,我就惊讶得很,十几年不见,先生已患严重的帕金森症,行动迟缓,双手颤抖,伯母也已去世。我的眼眶当时就湿了,怕先生难受,忍了半天没有掉下来。许久不见了,家人问我要不要到外面吃饭,我说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哪儿也不去。先生身体不好,讲话不方便,那顿饭吃得是煮饺子,本是我爱吃的,可那天一点滋味也没有。吃饭间,先生忽然费力的抬起手指着二女和儿子说:惠利,我是不行了,把他们托付给你……”儿女愕然,我也一惊。先生的儿子与我年龄相仿,赵淳比我还大,他们的经济和个人事业都不错,照顾他们从何谈起,再说我何德何能,怎敢接此重托。我忙说,他们比我都强,有事找我肯定帮忙,托付给我哪里担当得起。现在想起,先生可能另有深意。我却因为这话,怕他子女多想,不敢再去。
后来家庭事业迭遭变故,回国时不好意思再去看望赵老。留了信箱给赵淳,希望有事联系,她也一直没跟我联系。没想到2005年一别竟是永别。我翻出了身边仅存的一本《卧佛寺与樱桃沟》,随手翻到赵先生的序文“燕山与太行交汇之阳,……”又想起与先生同去樱桃沟的情景。
雨洒西山红叶去,
风吹卧佛寒气来。
清溪一弯入退谷,
何日双骑与师还。
2012-10-23
Zagreb
三境斋
本文写完后,一直处于回忆之中,不断想起一些往事,所以续有补充修改,请读者见谅.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