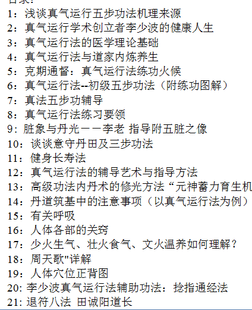49·2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解说】
1、这段话文字简明,意思清楚:古时民不争而自治,故赏罚不用;现在民相争,所以“倍赏累法”都不能让社会不乱,这原因则全在于那时“人民少而财有余”,而现在“人民众而货财寡”。我不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韩非子的这个思想,只想指出:他这看法是从他的老师荀子那里继承来的。《荀子·王制》篇中说:“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足见荀子早就把“民相争”归因于“物不能澹”(此“澹”字通“赡”),亦即“人民众而货财寡”。不过荀子主要是用这个理论来说明“礼”的起源与作用(礼制的绝对必要性)。所以在《礼论》篇中,他又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韩非子对这个理论的发展,在于他主要是用来申说奖赏和惩罚的必要性。
2、这段话中也有几个词语值得注意:①“丈夫”与“妇人”并言,可见是指成年男子。②“事力”的“事”是“从事”义,“力”是指谓很费力气的活动,所以“不事力”等于说不劳动。③“养足”是同“财有余”并举,故是主谓结构,“养”是指人民得以生养的物质资料。④“不行”、“不用”实际上是说“不存在”:“行”和“用”在这里是同义词,都是运用义,但不涉及谁是施事的问题。⑤“自治”是个偏正结构,即这个“自”是副词,相当于“自然地”;“治”和“乱”相对,指安定而有秩序的状态。⑥几个“人民”都相当于今天说的“人们”。
【辨析】
1、注家们对这一节的理解不会有大错,翻译则多有不准确之处,例如把“人民”照搬到译文中,把“乱”译作“混乱”、“纷乱”,让“子又有五子”的译文读来像是陈述实然情况而不是表示假设,将“不行”、“不用”直译为“不实(施)行”、“不使(采)用”,等等。——译文中出现这种“小毛病”,也可能是因为译者没有把原文“吃透”。
2、张觉先生在译注完这段话后写的“说明”中说:“韩非的这种说法仅是一种简单的推理,即使在石器时代、狩猎时代,也不是没有奖赏和惩罚。那时的人们正因为仅靠狩猎而深感食物不足,争夺不已,才发明了谷物种植。谷物种植普及后,粮食的增多才导致人口的增加”。我以为,这个批评,或者说评论,是不中肯的。且不说张先生的说法是否可以成立,重要的是:这里,韩非子不是要论定古代没有任何奖赏和惩罚,他是要说,那时候不存在作为“社会管理机制”的“奖赏和惩罚”,而且还是特指物质利益分配上的的奖赏和惩罚。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确认了这一点,张先生的评论就没有了“指向”,就落空了。可见张先生写这几句评论,乃是基于对原文的误解——我写这段“辨析”,仍然是着眼于对原文的准确理解问题,不是要做学术探讨。
3、冯友兰先生征引了此节中大段文字,评论说:在原始社会,“禽兽之皮和草木之实,也都是需要很多的劳动才能得到,并不是像他所说的‘不事力而养足’。不过,韩非在这里接触一个真理,那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随着历史社会情况的变动而变动的,它是历史的产物。”这个批评和褒扬性肯定,显然非常正确,但在作引用之前,他断言说:“韩非认为决定历史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的增长”(见739页),这作为对于韩非思想的“介绍”,就很不准确了:这里,韩非不是在一般地谈论历史变化的动因,正是把“人口的增加”当做“社会情况的变动”来陈述的,也即纳入到了“历史的产物”之中,怎么能得出他有这种“认为”呢?——这个小例子说明,大学者在介绍别人的观点时,也可能很不准确。
【译文】
古时候,男子并不耕种,因为野生草木的果实已经足够人吃的了;妇女也不纺织,因为禽兽的皮已经足够人穿的了;就是说,那时人们不要从事劳动,生活资料总是很充足的,即人口很少,财物有余。所以那时人们不会互相争夺。因此,那时候不存在奖励和惩罚,人们自自然然地过着安定平和的日子。现在呢?一人有五个子女不算多,每个子女又有五个子女的话,祖父还没有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辈了。因此,现在是人口多而财物少,人们从事着很辛苦的劳动,生活资料却很菲薄;所以人们就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予以奖赏,不断地实行惩罚,也不能避免社会的动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