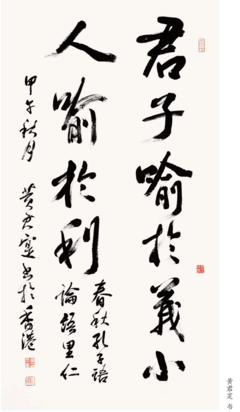王利器对《红楼梦新证》的评价
一、不知妄说
二、不知妄改
三、不伦不类
四、以讹传讹
五、张冠李戴
六、辗转稗贩
七、顾此失彼
八、道听途说
九、数典忘祖
十、“前知五百年”
周汝昌同志著《红楼梦新证》,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一九七六年四月又出版《增订本》。经过二十多年加工修改之后,他向读者宣称:“作者个人今天的见解与能力都已有所提高了。”我把这本有些参考资料的书翻了一遍之后,总觉得“其貌似新,其质实旧”,爰本责备求全之义,提出一些他山攻错的意见。
一、不知妄说
《红楼梦新证·人物考》51页写道:
同书卷二叶十一背面一条眉批云:“以自古来未闻之奇语(按指甄宝玉挨打喊“姊姊”“妹妹”的事),故写成自古未闻之奇文,此是一部书中大调侃寓意处。盖作者实因鹤钨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这段话极可注意:鹤钨、棠棣,皆喻兄弟;“棠棣之威”文义怪异,疑“威”是“戚”“感”之钞讹。如其不然,则“悲批威”二句应分属两人,一为棠村,早逝可伤;一为另弟,时见凌逼,如小说中所谓贾环之流者,为可慨叹。
《旧本》52页作:
同书卷二叶十一背面一条眉批云……这段话极可注意:鹡鸰便是棠棣,如果所指一人,“悲”和“威”便没法调和而讲不通了。我的解释是:鹡鸰之悲,悲的是这个棠村弟早逝,而棠棣之威,恐怕便指的是贾环对他有侵辱逼凌的事情。
在这里,周汝昌同志前后两次企图把“棠棣之威”说成是“贾环对他有侵辱逼凌的事情”,或者说“一为另弟,时见凌逼,如小说中所谓贾环之流者,为可慨叹”。我认为“鹡鸰之悲,棠棣之威”,二句一义,都是说兄弟死丧之事。“棠棣之威”,是用《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桦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常棣”即“棠棣”,《毛传》云:“威,畏;怀,思也。”《郑笺》云:“死丧,可怖之事。维兄弟之亲,甚相思念。”此《脂批》所本。《脂批》为了取与“鹡鸰之悲”相俪为文,故易“死丧”为“棠棣”。以“鹡鸰”喻兄弟,亦见此诗下章,“鹡鸰”作“脊令”,古通。《脂批》此处所用之典,乃一般童而习之的常典,并非僻典。
由此而联想起一个类似的情况,《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588页写道:
昭楗《啸亭杂录》卷一“理足国帑”条亦云:“康熙间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亨以驭国用,故库帑亏绌,日不暇给。”
《旧本》断句同。
案这里断句大误,当作:“康熙问,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亨’以驭国用,故库帑亏绌。”《易经·豫卦》:“豫之时义大矣哉,”又《丰卦》:“丰,亨,王假之,”王弼注:“大而亨者,王之所至。”《正义》:“丰者,多大之名,盈足之义,财多德大,故谓之为丰。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齐,无所拥碍,谓之为亨,故曰丰亨。王假之者,假,至也,丰亨之道,王之所尚,非有王者之德,不能至之,故曰王假之也。”此“豫大丰亨”说之所本。北宋末年,内外交困,权臣当国,出于固禄怙宠的企图,乃倡为“豫大丰亨”之说,以蛊惑君心。方勺《青溪寇轨》写道:“迨徽庙继统,蔡京父子,欲固其位,乃倡‘丰亨豫大’之说,以恣蛊惑;童贯遂开造作局子苏、杭,以制御器,又引吴人朱勔进花石媚上。上心既侈,岁加增焉。”周焯《清波别志》卷上写道:“尔后,有以‘丰亨豫大’之说蛊荡上意,及命巨珰五辈,分地展宫禁,土木华侈,糜费金宝,何可数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四《国用》二写道:“徽宗崇宁后,蔡京为相,增修财富之政,务以靡惑人主。……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以谀帝意。”瞿佑《归田诗话》卷中“周公礼乐”条写道:“蔡京当国,倡为‘丰亨豫大’之说,以肆蛊惑。”由此可见,则用“豫大丰亨”之说来为粉饰太平张目,为铺张浪费找藉口,实自蔡京作俑。周密(泗水潜夫)《武林旧事序》写道:“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者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兀祜’,‘丰亨豫本’,至宝佑、景定,则几于政,宣矣。”昭梿之文,盖即本之。周汝昌同志由于不知其义,从而不明其句读。
《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381页写道:
李煦四月有进端午龙袍请安摺。按摺后朱批云:“知道了。今春因玉泉超葵多事,打发回南。此人坚(案当作“颇”)不守分,尔当绝其往来方好。”此为何等人何等事,皆不可晓。或竟系李煦所进优人。
今案:张庚《国朝画征续录》卷下写道:“轮庵法名超揆,俗姓文氏,名果,中翰震亨子,文肃公侄。父殇,家落,走京师,佐总戎桑格幕,定滇逆,得官不仕,遂剃发。善诗文笔札,工画山水,多写平生游历之名山异境,故能独开生面,不落时蹊。圣祖南巡迎驾,召入京,恩赉优渥,年七十余示寂,赐塔玉泉山,予谥文觉禅师,异数也。”“超葵”即“超揆”,此满汉对音字异,如“曹玺”一作“曹熙”之比。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三十二收同揆《鼎湖篇赠尹紫芝内翰》七古一首,附小传云:“同揆,字轮庵,江南吴县人,著有《寒溪集》。轮庵,文中翰启美之子,文肃公犹子也。沧桑后,逃于禅。所为诗,皆人伦日用、盛衰兴废之感,墨名儒行,斯人有焉。”“同揆”与“超揆”歧异,疑出沈氏笔误。文震亨,字启美,天启中以恩贡为中书舍人。文肃公,即文震孟,字文起,天启中殿试第一,福王时追谥文肃。寻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和尚之孙应举”条写道:“文和尚名果,字园公,衡山裔也。圣祖南巡见之,命入京师,居玉泉精舍,宠眷殊厚。和尚一日携其孙入见,上曰:‘何事来此?,和尚奏曰:‘来此应举。’上曰:‘应举即不应来见。’盖防微杜渐,虑其希望非分之恩宠也。”康熙所谓“玉泉超葵多事”,盖即指其携孙入见事,则其人其事,非如周汝昌同志所谓“此为何等人何等事,皆不可晓”,甚而妄说为“或竟系李煦所进优人”也。
二、不知妄改
不知妄改,在《红楼梦新证》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745页写道:
甲戌本卷一正文之始有眉批云:“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付,即副字)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旧本》435页作: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红楼梦新证·文物杂考》798页写道:
如“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付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诸语。
又《脂砚斋批》855页写道: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付(即副字俗体,批中例甚多;原误钞作何)本,余二人亦大快于九泉矣!
又857页引作: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付——即副)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l
《旧本》550页作: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有误)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
又《红楼梦新证·脂砚斋批》867页作:
唯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
从上面所举诸文来看,在《旧本》中,周汝昌同志对“何本”二字,或注以“?”号,或注日“有误”;事隔二十余年,在出《增订本》时,他却一再地指出“何本”是“付本”错误,甚至迳改为“付本”。然而,按照他这样改法,我们试把这条《脂批》读一读:“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是书付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不仅蹩脚得很,而且不通之至。我认为“何本”二字是有错误,但错的不是“何”字而是“本”字。“本”当是“幸”字之误,“幸”字俗作“卒”,《龙龛手鉴》卷三《大部》:“李,又音幸。”“卒”与“本”形近,从而误成“本”字了。俞平伯先生《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四十一页注“幸”字于“本”字下,是也。《脂批》之意,是说:再出一芹一脂,则是书芹可以写完,脂可以批完,何幸如之!这本来是文从字顺的,然而周汝昌同志却改为“付本”,不仅此也,他又在《脂砚斋批》里引作“唯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删去了“何本”句,也未加省略号。
三、不伦不类
《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221页写道:
一六三四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甲戌金之汉官民诉差役繁,努尔哈赤晓谕之,词婉而实厉。
案:这条记载,实令人大惑不解。考《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卷之一:“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姓爱新觉罗氏,讳努尔哈赤。”同书卷四:“上二子贝勒莽古尔泰、贝勒皇太极请渡河击之。贝勒皇太极即太宗文皇帝也。”同书卷五:“天命元年(一六一六)丙辰春正月壬申朔,……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时上年五十有八。”同书卷十:“天命十一年(一六二六)丙寅八月丙午,上大渐,……庚戌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大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实录》卷之一:“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讳皇太极,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第八子也。……上即皇帝位,……时上年三十有五。诏以明年丁卯(一六二七)为天聪元年。”据此,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天聪为文皇帝皇太极年号,天聪八年,努尔哈赤死已八年,竟然又“晓谕”起人来了。这里,周汝昌同志把努尔哈赤当成皇太极,把父亲当成了儿子。再看,《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213页:“一五九二明万历二十年壬辰十月明东北地方长官建州左卫都督(后封龙虎将军)努尔哈赤之长子皇太极生。”皇太极本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现在竟摇身一变,又变成长子了。
四、以讹传讹
以讹传讹,主要由于知识贫乏之故,以致熟视无睹,甚而还产生歪曲原文的毛病,兹举二例以明之。属于前者:《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439页引张云章《朴村诗集》卷三《舞剑图歌》:“楚宫郑襄寡绝伎,名倡阳阿愧艳色。”《旧本》344页同。检《朴村诗集》原刻本亦同。器案:这里的“郑襄”当是“郑褏”之误,“郑褏”即“郑袖”,是楚怀王的宠姬,黄丕烈影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卷第十五“楚”二“楚怀王拘张仪”条作“郑͡”,凡四见俱如此作,“͡”当是“褏”之俗别字;又卷第十六“楚”三“张仪之楚贫”条作“郑褏”,凡四见俱如此作;又卷第十七“楚”四“魏王遗楚王美人”条作“郑褏”,凡五见俱如此作。元至正十五年刻吴师道注本《战国策》“楚”卷第五、明嘉靖二年河南重刻元黑口本吴师道校注《战国策》“楚”卷第五、嘉靖壬子吴郡杜诗梓鲍彪校注《战国策》“楚”卷第五,其“张仪之楚贫”条、“楚怀王拘张仪”条、“魏王遗楚王美人”条,俱作“郑褏”,鲍彪注:“郑褏,美人。”吴师道注:“袖、亵同。周紫芝《楚辞说》云:‘郑国之女多美而善舞。楚怀王幸姬郑袖,当是善舞,故名袖者,所以舞也。’”《史记.楚世家》、《张仪传》、《屈原传》都作“郑袖”。张诗之“郑襄”,即“郑褏”形近之误,其言“楚宫郑褏寡绝伎”,正就其善舞为言;若作“郑襄”,不独古代善舞者未闻其人,即就诗律而论,其平仄失调,真太蹩脚了。
属于后者,《红楼梦新证·人物考》92页引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刑部尚书富察公神道碑》:“公闻命不辨岩径,上马驰抵策凌部落。”《旧本》92页引文和断句同。查清乾嘉间刻本《小仓山房文集》卷二页十上《刑部尚书富察公神道》,原有圈点,今移录之,其文云:“公闻命,不办严,径上马驰,抵策凌部落。”周汝昌所据本,盖出后刻或坊间石印本、摆印本,没有圈点,又把“严”字错成“岩”字,遂弄出笑话了。“严”字在汉、魏、六朝诗文中经常使用,意谓“整装”,如《后汉书·清河孝王传》:“每朝谒陵庙,常夜分严装,衣冠待明。”又《陈纪传》:“不复辨严,即时之郡。”《风俗通义·正失篇》:“安帝始加元服,百官会贺,临严垂出,而孙适生。”这些“严”字,义都相同,而《陈纪传》一例,尤为袁文之所本。
五、张冠李戴
《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343页写道:
按陆漻,字其清,吴门医生。所居日听云室,鉴藏图籍甚富。著有《持静斋书目》、《佳趣堂书目》。
《旧本》260页同。
今按:《持静斋书目》是莫友芝据丁日昌藏书编辑的,同治问丰顺丁氏刻本,并非陆渗所著。
《红楼梦新证·文物杂考》825页写道:
唐代诗人王昌龄曾说:“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可为白居易诗作一佐证。
今案:这是李白诗,见《李太白文集》卷二十四《陌上赠美人》(-云《小放歌行》,一首在第三,此是第二篇):“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一作“青”)楼是妾家。”此所据为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缪曰芑重刊宋本。今所传《王昌龄集》,如《唐人集》、《唐人小集》、《唐诗二十六家》所收的二卷本《王昌龄集》,《唐百家诗·盛唐一十家》所收的三卷本《王昌龄诗集》,《全唐诗》第二函第十册所收的四卷本《王昌龄》卷,都无此诗,不知周汝昌同志的根据又是什么?
又《史事稽年》517页引施琛《病中杂赋》后写道:
按施诗中……“树倒猢狲散”-典,又出宋人《谈薮》所载曹咏作《树倒猢狲散赋》以刺秦桧戚党,寅之拈此,亦自用曹姓故事。
《旧本》393页引用此诗,于曹寅所拈佛语,未加按语;二十多年后:出版的《增订本》却加了这条按语。然而,宋庞元英《谈薮》的原文却大不相同:“曹咏侍郎妻硕人厉氏,余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与夫不相得,仳离而归;乃适咏,时尚武弁,不数年,以秦桧之姻党,易文阶,骤擢至徽猷阁。……方咏盛时,乡里奔走承迎惟恐后;独硕人之兄厉德新不然。咏衔怨,帅越时,德新为里正,咏风邑官胁治百端,冀其祈己,竟不屈。会之甫殂,乃遣介致书于咏,启封,乃《树倒猢狲散赋》一篇。”(据涵芬楼排印本《说郛》卷三十一)据此,则作《树倒猢狲散赋》的是厉德新,曹咏乃其讽刺的对象;曹寅拈此语,正以其为曹家本事故耳。
六、辗转稗贩
《红楼梦新证·重排后记》1125页自称:“一切文献,尽可能地根据原书原件,不敢蹈稗贩欺世的恶习。”还自诩他的大著“毕竟不同于转贩”。但他在《史事稽年》759页写道:
倪鸿《桐阴清话》卷七引《樗散轩丛谈》所称“苏大司寇”本。
同上760页写道:
八十回本《红楼梦》,存。有正书局据旧抄本石印本,八卷,八十回,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孙按语云:“邹瞍《三借庐笔谈》十一引《樗散轩丛谈》,谓《红楼梦》初刊本只八十回,临桂倪云癯大令鸿言曾亲见之。书林杜世勋为余言:十年前曾见八十回刊本。则八十回本《红楼梦》似曾刊行也。”
汝昌按,倪鸿《桐阴清话》卷七引《樗散轩丛谈》,则云:“《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巨家问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乾隆某年,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装订,坊中人借以抄出,刊板刷印渔利。”是乾隆间固似有刊行在先者。
同上761页写道:
倪鸿《桐阴清话》卷七引《樗散轩丛谈》:“其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续?”
又《脂砚斋批》928页写道:
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
(《石头记》)初仅钞本,八十回以后轶去。……原本与改本先后开雕(《桐阴清话》卷七引《樗散轩丛话》云:康熙问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乾隆某年苏大司寇家以书付厂肆装订,抄出刊行).……
从这些稗贩材料来看,则倪鸿、平步青、邹瞍都看见过《樗散轩丛谈》,并不是什么“珍秘材料”。有些人就是束书不观,不深入调查研究,人云亦云;即此《樗散轩丛谈》谈《红楼梦》一事,就提供一个很要紧的线索的何年从苏大司寇家传出来的问题,惜乎,谈《红楼梦》流传的,都从这些稗贩的材料知道在乾隆某年而已。现将这项材料公之于世。《樗散轩丛谈》十卷,吴江陈镛兰冈著,卷首有甲子夏五寿潜居士序,称其“数载京华,佣书三馆”。序末有木印“芝园”、“金瑶冈”二方,又有植庵徐乔林《调沁园春》词一阕。卷末有“苏州阊门外桐泾桥西首青霞斋吴刊刻”二行。卷二叶六“红楼梦”条写道:“《牡丹亭》杜丽娘死于梦,《疗妒羹》小青死于妒,二者不外乎情,然皆切己之事也。昨晤江宁桂惠泉,力劝勿看《红楼梦》,余询其故,因述常州臧镛堂言:‘邑有士人贪看《红楼梦》,每到入情处,必掩卷瞑想,或发声长叹,或挥泪悲啼,寝食并废,匝月间连看七遍,遂致神思恍忽,心血耗尽而死。’又言:‘某姓一女子亦看《红楼梦》,呕血而死。’余曰:此可云隔靴搔痒,替人耽忧者也。然《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钞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
七、顾此失彼
顾此失彼的情况,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表现为:-,同属一书,而发生顾前不顾后的事情;二,同为一人所著之书,而发生知有此而不知有彼的事情;三,同为曹寅要好的朋友,而发生知有甲而不知有乙的事情。
属于第一种情况的,如《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455页写道:
本年(康熙四十五年)曾修葺江宁府儒学;……《江南通志》卷八十七《学校志》“学宫”叶十一:江宁府儒学:四十五年织造曹寅修葺。按凡此皆捐修之谓也。
器案:《江南通志》卷八十八《学校志》“学宫”又载:康熙四十六年(一七○七),巡盐御史曹寅重修明伦堂,并附朱彝尊记,《史事稽年》于康熙四十六年失收此事。
属于第二种情况的,如《史事稽年》494页引陈鹏年《沧州近诗》中的《次韵答吴秋屏见寄》小注“札中述银台曹荔轩先生北行,相念甚切,故及之。”说:
按自注所云“相念甚切”,是曹念陈。“义觉云天重,春从黍谷回,二句当有本事,鹏年自去冬腊月以苏州知府署理江苏布政司事,或与此有关。
案:鹏年《秣陵集》卷二《楝亭诗二十五韵呈曹银台子清先生》:“种树知先德,过庭识素风,前徽冰署里,遗训楝亭中。鲁国门墙峻,平阳阀阅雄,逸才原哕凤,事业归从龙。尺五依宸极,魁三列上公,缁衣心倍笃,赤舄望弥隆。白下荣开府,秦淮宠锡弓,闲情余结构,清暇得和融。宇宙此间古,山川放眼空,楝花春雨细,亭屋紫烟笼。插架牙签满,披轩玉册充,谢池波荡漾,木石怪巃ᵝ。曙色娇巢鸟,秋光冷砌虫,苔侵双屐绿,月到一樽红。寂历回廊转,萦纡小径通,恍疑垂钓客,不亚住山翁。支许门前揖,求羊林下逢,鹤琴传介节,诗礼属宗工。先后箕裘映,辉光节钺崇,尚衣方赐蟒,簪笔更乘骢。静树思何极,重云望莫穷,肯堂思手泽,倾日想丹衷。干老蟠根大,枝蕃湛露中,栽培多玉笋,溉灌及兰丛,莫讶今犹昔,由来孝作忠。”《楝亭诗》是《红楼梦新证》津津乐道之事,陈鹏年与曹寅又是如周汝昌所承认的“知感交好之人”,乃从陈鹏年《次韵答吴秋屏见寄》诗注中见其交往之迹,而不录陈沧洲《楝亭诗》之作,这不是仪发而失嫱吗?
属于第三种情况的,那更未易覙缕,兹略举其荦荦大者。如梅文鼎《绩学堂诗钞》卷四《同昆山徐道济编修维扬卓鹿墟萧徵义纳凉于楝亭银台之真州寓楼》(戊子)七律一首,《真州奉陪荔轩银台竹村廷尉观江头打鱼同卓鹿墟胡来章杜吹万》(戊子)五古一首,《越三日立秋又奉陪江舟看雨》(同项景原程惟高卓鹿墟马质公)(戊子)五古一首,又如顾嗣立《秀野草堂诗集》卷三十一(己丑三月至庚寅十二月)《真州访曹鹾使荔轩留饮大椿轩即事》七律一首,诗中有注云:“先-夕,鹾使与鲍又昭唐序皇王植夫允文诸君江上打鱼,各有吟咏。”又卷三十八(辛卯)《曹银台荔轩座上喜晤洪去芜有诗见赠次韵奉酬》七律一首,又《和荔轩银台平山堂探梅各以姓名字号为韵之作三首》七绝三首,如此等等,都可以更好地反映当时以文会友的乐事,然而《红楼梦新证》于此都付之阙如。
八、道听途说
道听涂说,人云亦云,甚至于没来源,“不加称引,攘为已有”,这在《红楼梦新证》中屡见不鲜。兹各举一例以明之。
属于前者,《红楼梦新证·附录编》1121页写道:
第三项资料是胡大镛《七宝楼诗集》,其中颇有几处与《红楼梦》有关的题咏,并记下了友人余楠的某些谈《红》的情况。《诗集》为大册红格佳纸精写原本,残存十四册,编诗自道光十年始。……咸丰元年(一八五一)胡作《雨夜得古香北地书书诸柬尾》五言律三首,有小序及细注引余札中语,明白表示他们认为小说所写是北地而非南土。此一则,蒙张玄浩先生录示。
案这则材料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胡大镛《七宝楼诗集》,今残存原稿十四册,藏北京图书馆。卷二十七(辛亥)有《雨夜得古香北地书书尾》五律三首,而不是《雨夜得古香北地书书诸柬尾》,这首诗题有注写道:“来书云:‘访得《红楼梦》中大观园故址,晤老衲为赖大耳孙。’是真闻所未闻,夜雨无聊,拈句寄相思云。”这组诗写道:“尺书来日下,问讯到闲鸥。有分功名淡,奇情古迹搜。残僧感兴废,春梦误温柔。未必干卿事,词人惯买愁。”“闲愁消不尽,分赠素心人。入画楼台幻,无情草木春。三生悭好梦,一宿种前因。粉黛余黄土,葬花冢可真。”“仿佛湘裙蝶,清流有断桥。故宫悲瓦砾,野史话渔樵。(来札云:“馆舍埊仄如航。十里之远,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平桥远树,中间有僧寮与故宫王府一二处;数与老衲话于其间,即所谓赖大耳孙也。”)命共桃花薄,魂随柳絮消。天涯今夜雨,同梦忆迢迢。”这三首诗和两条注,都可供谈《红》者参考。周汝昌同志不是在大谈大观园吗?这组诗的题注,正好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材料;而“老衲为赖大耳孙”云云,拿来印证《史事稽年》689页所言:“此即贾府已许赖大之子开户,虽赖大仍为贾府管家,其子已不复以‘家生子’身份论矣”。——
属于后者,《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353页写道:
秋,李煦至粤传旨褒劳朱宏祚,并迎闵明我还自外洋。时煦为畅春苑总管。张贞《杞田集》卷十叶六:“上念公(按指朱宏祚)勤劳于外,壬申秋特遣内务营造司员外郎董君殿邦、畅春苑总管李君煦至粤传旨褒嘉,劳问甚渥。”迎闭事详《正教奉褒》
器案:这里所叙述褒嘉朱宏祚和迎闵明我二事,时间既前后颠倒,本末也交代不清。据黄伯禄编《正教奉褒》(光绪三十年甲辰孟秋月上海慈母堂第三次排印本)117页:“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六月初十日,奉上谕:‘前闵明我领兵部咨文,差往西洋,今该回到,兹差安多到广东澳门去接;若闵明我带有精通天历之西人,着取来京听用,其余随便居住,特谕。’十四日,上谕:‘差董殿邦、李煦同安多往澳。’十六日,上谕:‘安多前病,气力尚未全复,旱路难当,可以到济宁州上船,带殷铎泽往杭州本天主堂,照前居住安养,后到澳门,往回慢走,特谕。’十七日,殷铎泽、安多趋畅春园,谢恩辞行,蒙赐筵宴,并琼玉膏一瓶。上谕殷铎泽曰:‘你老人家,今有安多,并差官,作伴同回,朕可放心。’临行,上又念其走路艰辛,命载之御舟,由河而出。”又118页:“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闵明我回华复命,奏陈遵旨会商各情。上嘉之,赏赉甚厚,仍令治历供职。”按:闵明我,意大利国人,见《正教奉褒》69页原注。其差往西洋,据《正教奉褒》90页:“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上遣闵明我执兵部文泛海,由欧罗巴洲往俄罗斯京,会商交涉事宜。”从《正教奉褒》所载,我们看得很清楚,董、李奉命至粤有双重使命,接受任务在六月十四日,至粤传旨褒嘉朱宏祚在秋天;至于闵明我,此时尚未抵澳,故迟至康熙三十三年才“回华复命”。周汝昌同志叙述此二事,前后都失其据,盖亦未尝一检《正教奉褒》,而是从道听涂说得来,并把从何人得来的消息也干没了。如周汝昌同志曾读此书,他将会就在该书118页“差董殿邦、李煦同安多往澳’条之后,“闵明我回华复命”条之前,发现:“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五月,圣躬偶感疟疾,张诚、白进、洪若,进金鸡那(治疟疾西药)。一上派四大臣试验,给疟者服之,即愈。四大臣又自服,亦无恙。奏闻,上遂进用,不日即康豫。上欲旌张诚等忠爱,因于六月初九日,赐皇城西安门内广厦一所,并派内大臣饬工修整,以便修士居住。”这条材料,具体地说明了康熙是怎样得知金鸡那并服用而治好他的疟疾的。不仅此也,假如周汝昌同志读过《正教奉褒》,又会在100页发现:“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22月二十五日,圣驾幸江宁,进通济门,毕嘉、洪若迎至上方桥遇驾,时大雨,毕嘉、洪若即跪桥边恭迎。上一见,即勒马垂问,……又问赵侍卫:‘这是那个?’侍卫启奏:‘就是旧年万岁召进京的。’上云:‘是洪若么?’随谕:‘起来,起来,雨大,快些回去。’毕嘉、洪若即钦遵回堂。二十六日昧爽,毕嘉、洪若赴行宫,恭请圣安。
……二十七早,上差御前一等哈邬、侍卫赵赍捧黄袱,内包白金到堂,先叩拜天主,次传毕嘉、洪若出厅,随宣上谕,……毕嘉、洪若谢恩谨领。……卓午,毕嘉、洪若赴行宫谢恩。……回堂未几,赵侍卫又奉旨来堂,问‘南极老人星,江宁可能见否?出广东地平几度?江宁几度?’等语。毕嘉、洪若一一讲述。赵侍卫即飞马复旨。毕嘉、洪若,因匆遽回答,恐难详悉,至晚戌初时,细观天象,详验老人星出入地平度数,缮具黄册;二十八日早,趋诣行宫,进呈御览。三月初一日,黎明,上临行,颁赐珍馔三盘,差赵侍卫、邬哈,赍送到堂;毕嘉、洪若即设香案,出门迎接,叩问上安。……赵侍卫云:‘万岁今日出太平门,不在堂过矣,二位先生要送圣驾,可先登舟候送。’言讫,辞去。毕嘉.洪若随即出城,至仪凤门登船,开到燕子矶时,御舰已挂帆江心,乃由仪徵,先至扬州湾头恭候。初五日辰刻,御舰过湾头,侍卫一见毕嘉、洪若即启奏,随传旨命毕嘉船,附靠御舟。……奏对间,御舰已行十五里矣。上命赵侍卫送毕嘉、洪若过船,并蒙慰谕:‘来送已远,前途船多难行,不必再送,可速回堂。’毕嘉、洪若谢恩,叩辞圣驾而回。”这段文章写康熙第二次南巡,会见毕嘉、洪若的经过,有详尽而具体的描述,较之展转稗贩《方豪文录》,不更为“文献足徵”吗?
九、数典忘祖
数典忘祖,大都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遇事浅尝辄止,不求深入调查研究,是一种懒汉思想的反映。这种弊病,不仅不能深入地研究问题,有时,甚而大大地歪曲了历史真实。这种情况,在《红楼梦新证》中是相当普遍的,现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其问
《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364页写道: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叶四十五引吴之骤诗:“我闻楝亭下,嘉树影婆娑。书卷拥百城,尚友自吟哦。”按吴之騄骤,字鸣夏,号耳公,歙人,举人,镇江府学教授。有《桂留堂集》,未见。全诗是否咏楝亭,不详,俟者补
器案:吴之騄这首诗是题张见阳《楝亭夜话图》的,见陶梁编辑《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四“手卷类”《国朝张见阳楝亭夜话图》,共收了题跋十一首,吴诗是最末一首,现移录于此:卷头题署为:“楝亭夜话见阳”,有“子安”、“杏花书屋”、“见阳无声诗”、“见阳书画”四印章。第一首为曹寅诗,诗前有“楝亭”印章一,其诗颇与收入《楝亭诗钞》卷二者有异同,盖草创稿也,今附注于陶本之下,诗云:“紫雪冥漾楝花老,水曹(蛙鸣)厅事多青草,庐江太守访故人,浔江(建康)并驾能倾倒。两家门第皆列戟,中年领郡稍迟早,文气(采)风流政有余,相逢甚欲抒怀抱。于时亦有不速客,合座(坐)清严斗炎煸,岂无炙鲤与寒鹦,不乏蒸梨兼瀹枣,二簋用享古则然,宾酬主醉今诚少。忆昔宿卫明光宫,愣伽山人貌佼(姣)好,马曹狗监只嘲难,而今触绪复怀抱(痛伤枯槁)。交情独剩张公子,晚识施君通纻缟,多闻直谅复奚疑,此乐不殊鱼在藻,始觉诗书是坦途,未妨车毂当行潦。家家争唱《饮水词》,那兰小字几曾知?布袍(斑丝)廓落任安(谁同)在,说向(岑寂)名场此一(尔许)时。(按诗中重押“怀抱”二字。)”诗末有“曹寅”记名,及“真我”、“曹寅之印”二印章。诗末案语当出陶氏手,《楝亭诗钞》已改正,陶氏未及检校。第二首为施世纶诗,诗前有“真亭”印章一,诗末有“施世纶”记名,及“施印世纶”、“浔江”二印章。诗见《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382页。第三章为张纯惰诗,诗末有“张纯惰”记名,及“见阳书画”印章一。诗见《史事稽年》384页,惟“清暇”陶本作“情暇”,“逆迓”陶本作“迎迓”。第四首为顾贞观诗,见《史事稽年》384页,惟“草亭”陶本作“草堂”,“当丘壑”陶本“当’作“尚”,“藉”陶本作“借”,诗末印章为“梁汾顾贞观化峰图书”。第五首为王槩诗:“楝亭余每坐清昼,墙隅小草浓荫覆;楝乃水部手自栽,亭亦早岁摊书构。水部劳躅如文饶,青云顿觉生庭皋,四壁贞珉金错刀,雄文丽句凌奔涛。曲江才气排垂渎,楝亭夜集等空谷,唐渲宋椠任标举,陆海潘江半臣仆。坐列鼎足才颉颃,浔江齿则逊庐阳,水部从容当主席,尽超吏治雄词场。鸡声喔喔谈未倦,归复吮豪急洗砚,图中尚带灯烛光,光射当窗一株楝。次日流传遍艺林,新诗妙画双南金,楝枝直作梧桐视,清峙时闻鸾凤音。”诗末有“绣水王槩题”记名,及“王概之印”、“安节”二印章,《史事稽年》384页仅从《藏书纪事诗》转引六句,其数典忘祖一也。第六首为王蓍诗,诗前有“二翮山”印章一,诗云:“往闻顾仲瑛,幽居多楸梧,曾留张勾曲,且招杨廉夫,烧炬勒洗杓,顿忘清夜徂,于是王黄鹤,为作《夜话图》,其上各题句,次日传中吴。然皆枯槁士,话亦多痴迂,何若水部斋,坐两经世俪,庐江与浔江,俨然龚、黄俱,才气凌嵩、岱,彩笔抽珊瑚,所学奏奇效,比屋赓来苏。时当治理暇,文会惬瑾瑜,论经夺戴席,博古探顾厨,邻几与君谟,风雅同步趋。(蔡君谟、江邻几口同烧炬观宋中道书画。)庐江工纪事,遂起为操觚,点染虽水墨,亦复见眉须,叠席若字,谈笑闲喁煦。中庭树桦烛,烛影照氍毹,童子捧锦照,以待考证需,竹不弄清影,中有楝一株。楝亭此夜话,民物多含濡,用以较仲瑛,秦晋笑小邾。荷公命题句,弁陋惭巴歙,行见主与客,坦步联天衢,唐人《瀛洲图》,霞采生衣襦,公尤风雅宗,一世推盘盂。”(分书)诗末有“丁丑皋月既望绣水王蓍”记名,及“王印蓍”、“艸父”二印章。第七首为王方岐诗,诗前有“里华山樵”印章-,诗云:“石头城外水云碧,石头城里秋月白,露叶霜枝尚未凋,青荧灯火传阶席。水部风流自昔闻,浔江刺史称袖君,张星旧在天河上,一代才名动紫宸。此时正值风光好,壶尊小设相倾倒,拄颊齐谈夜气清,君卿扪舌淳于笑,漏鼓沈沈静不哗,一天凉露沾庭草。张公汲古神明异,间窗翰墨常游戏,竹石烟云腕下生,临摹更得前人意,共传佳句与人看,潇洒真如香案吏。三公兰锜旧家风,两郡为官政绩同,只今夜语空斋里,会见沙堤道上逢。”诗末有“广陵王方岐”记名,及“王印方岐,、“武徵”二印章。《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365页引王方岐《楝亭诗》一首,与此非一事也。第八首为姜兆熊诗,诗前有“芳树斋,印章一,诗云:“今日文官不爱钱,无如庐阳刺史贤。更有浔江廉太守,水部文章称三友,召、杜、龚、黄吏治同,才名子建传来久。
瑟瑟秋风下夕阳,主人爱客倾壶觞,楝花亭下谈心处,坐久那知更漏长。三家门第真煇赫,累叶貂蝉承世泽,生来性癖厌繁华,论交自合同金石。诗中有画画中诗,披图正复忆当时,人生胜事知多少,千古风流应在兹。”诗末有“会稽姜兆熊”记名,及“兆熊私印”、“芑贻”二印章。第九首为顾彩诗,诗前有“辟疆园”印章一,诗云:“翦烛谈心嗜好同,楝花亭敞月明中。硕交不愧莺求友,异政俱宜凤下空。茗碗味逾传酒炙,侍儿头任触屏风。曾披《三笑图》清绝,高论还应让数公。’诗末有“梁溪顾彩”记名,及“顾彩之印”、“天石”二印章。《史事稽年》311页引顾彩题《楝亭图》词一阕,与此亦非一事也。第十首为蒋耘渚诗,诗前有“鸴笑”印章一,诗云:“楝花覆院露零溥,水部邀宾夜欲阑。挥麈论文迟月上,拂笺吟句到灯残。何妨莲社成三笑,复见兰亭具二难。胜事未能常再得,披图直作写心看。”诗末有“醉里蒋耘渚”记名,及“蒋耘渚”、“隺汀“二印章。第十一首即吴之騄诗,诗前有“忍辱山人”印章一,诗云:“我闻楝亭下,嘉树影婆娑,书卷拥百城,尚友自吟哦。一朝德星聚,光焰耀庭柯,宝剑蛟龙合,精气腾泉阿。开尊聚三益,乐事此时多,彩笔干霄口(器案疑是“汉”字),才思若奔河。相逢共倾倒,笑语兼切磨,卜昼还卜夜,同心发浩歌。微云垂玉露,淡月笼金波,丹青图胜事,古谊孰能过。努力圣明代,鼎峙功不磨。”诗末有“歙浦吴之騄”记名,及“吴印之騄”、“达庵”二印章。据此,则吴之騄号达庵,别号忍辱山人,其诗重押“磨”字,当是草创稿。《史事稽年》364页仅从《藏书纪事诗》转引四句,不知其为《题楝亭夜话图》,而非《题楝亭图》也。
数典忘祖之弊,不仅如此而已,甚至还“捕风掠影,任意牵合”。《史事稽年》525—526页写道:
“李煦本年八月有因水灾捐赈筑堤之举,陆奎勋为作《筑堤行》。”并引录了《清诗铎》所载的陆诗。
今案:陆奎勋所咏者为李陈常而非李煦。《陆堂诗集》卷十《觉非小奠》(癸巳至甲申)《筑堤行为李鹾使作》,今举其与《清诗铎》有出入者,“命建新堤佥日诺”句下,《陆堂诗集》尚有“富商愿输银,贫商甘奋身,畚锸楗石纷如云,登登夯杵声相闻”。四句二十四字。“何羡芍药之陂龙骨渠”句下,《陆堂诗集》尚有“前吁后喁歌夹路,岂知肝胆在平素,权贵敛手避秋曹,一笔勾除广赡库。五马出郭炉然香,曩闻是举眉飞扬。书生束发饱经笥,谁无先忧后乐志,力苟弗赡时我违,颂酒赓花空老去。”十句七十字。“清风作颂属吉甫,书绩穹碑曜千古”二句作“清风何穆如,作诵非吉甫,更倩巨手韩、欧、苏,书功穹碑曜千古”。注作“明年鹾使病殁,惜乎其事中止。”“陆堂诗集》系编年体,此诗列在丙申(一七一六)仲春诗作之前,其前一首为《小除》作,则此当为乙未诗,当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据雍正《两淮盐法志》卷二《职官》、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三十四《职官》三、雍正《扬州府志》卷十t八《盐法》、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五《职官志·文职》七,并载两淮巡盐御史,李陈常,康熙五十三、五十四年连任。方志诗史,丝丝入扣。而且通过《陆堂诗集》,还知道李陈常于明年即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病殁;而李煦则是在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二月才病死于流放之地(李果《在亭丛稿》卷十一《前光禄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苏州织造李公行状》),时间相隔十三年。然而周汝昌同志竟然“错认颜标作鲁公”,把李陈常当成是李煦;而且“病疫”二字,《清诗铎》原作“病殁”,周汝昌同志既认为此诗是为李煦作,故列入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而李煦实死于雍正七年,因而改为“病疫”。
十、“前知五百年”
《红楼梦新证·人物考》67页写道:“大家都没有‘前知五百年’的本领,不独是谁一个。”本来是嘛,然而周汝昌同志却认为明初人就有知道清朝“旗下”风俗的本领。《红楼梦新证·引论》儿页写道:
在这里,历史知识和考证便成为必要了。邓文如(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原版)卷二叶二十三有一段话:“柴桑《京师偶记》引叶子奇《草木子》云:‘元朝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家童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贵家,必买臊达子小口,以多为胜,竞相夸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按所云‘黑厮’,或即昆仑奴之类;所云‘柳达子’,乃指蒙古。
旧本23—24页,标点全同,只是没有夹注“原版”二字。我看到这里,不禁大吃一惊,叶子奇这个明初的人真有“前知五百年”的本领,就知道满清王朝“旗下贵家”的生活,实在难以想像!我找出邓文如先生赠贻的那部《骨董琐记》,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十一月初版,和济印刷局排印本,没有标点,不知道这个本子是不是周汝昌同志所说的“原版”。他的《旧本》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初版的,那时,加以标点的《骨董琐记》尚未出版,那么,这里的标点无疑是出于周汝昌同志之手了。叶子奇《草木子》,有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自序,柴桑所引那段文章,见《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原文云:“元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草木子》原文仅止于此。下文“今旗下贵家”至“女口倍之”六句二十九字是柴桑的话。“按所云‘黑厮’”以下四句二十一字是邓之诚的话。这段文章,应该如此标点:
柴桑《京师偶记》引“叶子奇《草木子》云:‘元朝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家童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今旗下贵家,必买柳臊达子小口,以多为胜,竞相夸耀。男口至五十金,女口倍之。”按所云“黑厮”,或即昆仑奴之类;所云“柳达子”,乃指蒙古。
也就是在《引论》11页的下文,周汝昌同志写道:“读者起初几几乎真要相信了他。但一读邓先生的书,便觉哑然失笑了。”我现在一读邓先生的书,也不觉哑然失笑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