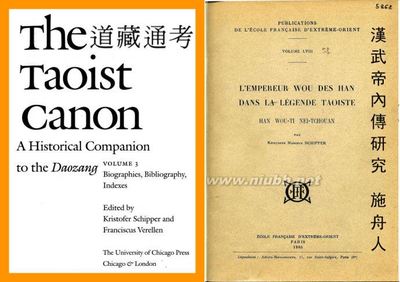施舟人《五经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PDF: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3987487.html(刊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1辑,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p.134-138)
《中华五经翻译》国际学术合作工程委员会名单:
主持人: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教授
名誉委员(10 位)
饶宗颐 (Jao Tsung-i)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及中国文化研究所伟伦荣誉艺术讲座教授
汪德迈 (Léon Vandermeersch) 教授,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
汤一介 (Tang Yijie)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儒藏》编撰中心主任
鲁惟一 (Michael Loewe) 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汉学系
李学勤 (Li Xueqin) 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康达维 (David Knechtges) 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系
杜维明 (Tu Weiming) 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
许嘉璐 (Xu Jialu)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
袁行霈 (Yuan Xingpei)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国学研究院院长
朱维铮 (Zhu Weizheng) 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
委员(36 位)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教授,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
伊维德 (Wilt Idema) 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
包弼德 (Peter Bol) 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艾兰 (Sarah Allan) 教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中文系主任
安乐哲 (Roger T. Ames) 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
白杰明 (Geremie Barmé) 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
卡多纳 (Alfredo Cadonna) 博士,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副教授
陈德鸿 (Leo Tak-Hung Chan) 教授, 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主任
齐思敏 (Mark Csikszentmihalyi) 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
丁荷生 (Kenneth Dean) 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东亚系
戴卡琳 (Carine Defoort) 教授,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中文系
杜润德 (Stephen Durrant) 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
伊若泊 (Robert Eno) 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
叶翰 (Hans van Ess) 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院院长
何志华 (Ho Che Wah)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祁泰履 (Terry Kleeman) 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
李炽昌 (Archie Chi-Chung Lee) 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
李零 (Li Ling) 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惠仪(Li Wai-yee)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
李集雅 (Tiziana Lippiello) 教授,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中文系
梅约翰 (John Makeham)教授,澳大利亚阿德来德大学
闵福德 (John Minford)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
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 教授,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尤锐 (Yuri Pines) 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主任
浦安迪 (Andrew Plaks) 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文系
普鸣 (Michael Puett) 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
桂思卓(Sarah Queen)教授,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中文系
李孟涛 (Matthias Richter) 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
袁冰凌 (Yuan Bingling) 教授, 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乐黛云 (Yue Daiyun) 教授, 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夏含夷 ( Edward Shaughnessy) 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系
苏芳淑 (Jenny Fong-Suk So)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斯泰格 (Brunhild Staiger) 博士,欧洲汉学学会会长
马克 (Marc Kalinowski) 教授,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研究主任
胡司德 (Roel Sterckx) 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汉学系主任
Wujing Project
关于《五经》翻译项目
中华文明是全世界最古老而未中断的人类文明之一,它的许多重要发明和辉煌的人本文化已被举世公认。近年来,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并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中国在科技、文化、教育、经济、通讯网络、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全世界都在注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
在这一新的时代潮流中,推广汉语教育、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应运而生,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到处都是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呼声。与西方文明、古印度文明不同的是,除了少数亚洲国家外,迄今为止,世界其它国家对中华文明所知甚少,对这一文明的起源和重要性认识十分有限。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包括《五经》在内的中国古代重要经典的译介不足,宣扬不力。
《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中国思想体系形成和帝国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很多世纪以来国家科举取仕的考试科目。由于它的重要性,秦汉以来,历代无数学者“皓首穷经”,为《五经》做了大量的传注疏义,形成一种被称为“经学”的显学。
所谓《五经》,是指除了汉以前失传的《乐》以外的《诗》、《书》、《礼》、《易》和《春秋》。虽然汉以来,有的经有今、古文之分,有的经多传并立,有的经只存残篇,以至于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之说,但总的来说,它们基本上都是从《五经》衍生出来的。这里我们所说的《五经》,即采用约定俗成的说法。
《五经》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可是迄今为止,一套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了解中国文化需要的多语种《五经》译本却不存在。虽然前人做过努力,《五经》中有的经曾有过英文、法文或德文译本,但大部分译本已经非常陈旧,有的甚至是在一百多年前翻译的!那些译本大多已经绝版,只有在非常专业的汉学图书馆才能找到。因此,我们必须出版一套全新的现代译本,不仅包含西方主要语言,而且要涵盖世界上所有重要的语种。只有这样,《五经》才能在世界伟大文明的经典之林确立它应有的地位,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才能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并真正接受。
与以色列古经《摩西五经》和印度古经《四吠陀》相比,中华《五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性毫不逊色,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传统上,以色列的经书被视为是上帝对摩西的圣谕,印度的《四吠陀》也被认为是天启圣典。《五经》却不同,中国文化不把《五经》当成神明之作。《五经》所表达的不是形而上的神学,而是与人类和自然界有关的知识。它所代表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可以说是中国对全人类最伟大、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我们从《诗经》听到的是人民的声音,《尚书》读到的是上古圣王的诰命,《三礼》记载的是古代圣贤协调社会、治理国家的经验,《易经》揭示的是宇宙与自然的运行法则,《春秋》告诫的是历史教训。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五经》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人本主义经典。
现在存世的《五经》译本大部分是一百年以前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作。1872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英译《尚书》、《诗经》和《春秋》(书名《春秋左传》,实际上只译了《春秋》本文),后来又出版了《礼记》和《易经》。这套译本在当时是开山之作,功不可没,但现在早已过时。另一套并不完全的早期《五经》译本是法国神父顾塞芬(Père
Séraphin Couvreur)的法译本,1889-1916年间陆续在河北出版。这个版本早已绝版,内容也已陈旧。
在单经译本中,德国人卫礼贤(RichardWilhelm)的德文本《易经》最出名。1924年出版时,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G.
Jung)为他撰写了前言。此书后来被转译成英文,195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然而,卫礼贤的译文有不少弊病,尤其是他在译文中随意加入自己的评论,与原来的经文不加区分。最流行的《诗经》译本是英国人魏理(Arthur
Waley)出版于1937年的英译本。他的译文优美,可读性强,问世半个多世纪依然广受欢迎。可是,魏理打乱了《诗经》风、雅、颂的原有次序,擅自将它另行分类。
在学术性译本中,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高本汉不仅对《五经》做了大量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也英译了《诗经》(1944,1950年)和《尚书》(1950年)。但他的译本是针对学者而做,很难普及。二战以后,出现过为数不多的新译本。由于某些原因,一些质量较高的译本却迟迟未能付梓面世。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翻译出版一套既有最新学术水准又有可读性的多语种《五经》,是一项事不宜迟的文化任务。《五经》翻译项目的实施旨在尽快结束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
实际上,重新翻译《五经》是不少中外学者的梦想。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饶宗颐教授就曾为中国经典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译介深感遗憾。从那时起,许多学者尝试过这项工作,均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2008年夏,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随后我们在北京召开了有关经文版本会议,并开始广泛接触海内外经学界、训诂学界、考古学界、翻译界等领域众多学者,筹备成立“《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汉学界相关领域聘请杰出学者担任委员会首批成员,在学术上确保这项大型国际汉学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将于2009年7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香山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位知名学者,将在三天会议期间商讨与项目有关的翻译体例、底本、出版等问题。
我们首先对《五经》进行英译。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但避免逐字对译,也尽量不受某一注疏或学术流派的影响。我们的宗旨是将原文翻译成符合时代语言特色的译本,既保证译文的精确性,也考虑译文的可读性。总之,新译本力争做到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并接受。
根据英译本并参照经文底本,我们将组织人员翻译以下八个语种: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之所以首先选择上述九个语种,是基于使用这些语种的人数众多或该语种在不同文化交融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正式出版的每一译本都将附有一篇导读性的前言,介绍该经的历史背景及重要性。译本不加注释,译文必须做到读者能够通过阅读经文而自明其义。特别重要的经文异字将在页边空白处标明。如果必要,校勘记将另行出版。
选定翻译的《五经》经文大约七十万字,译成英文约一百万个单词,两千五百页。其它语种的译本会有所不同。经过一年的启动筹备,预计实际的英译工作需要两年半时间,另加一年安排英译本的出版事宜,争取在三年半出齐《五经》英译本。其它语种的翻译工作,将在英译本定稿后尽快启动。
《五经》翻译项目主持人施舟人
2009年7月,北京
TOWARDS ANEW TRANSLATION OF WUJING
The Five Classics are the Odes 詩, the Documents 書, the Rites 禮,the Changes 易 and the Annals 春秋. They are China’s oldest, mostsacred book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y have been the canons ofChinese culture, the very heart of its thought and the foundationof its statecraft. Formerly, they were learned by heart by allstudents. A thorough and profound knowledge of the Wujing and theirexegesis was a prerequisite for all candidates at the imperial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ver the centuries, the study of the Wujing gave rise to a vastcorpus of erudite commentaries,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s andtext critical editions, just as this has been the case for thesacred canons of other cultures.
This great tradition came to a sudden stop when the imperialexaminations were abolished in 1905. Although the study of theWujing was not abandoned, Chinese scholarship during the 20thcentury mainly turned to other aspects of China’s culturalheritage. Research on vernacular literature, on Buddhism and Daoism– fields that had been hitherto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 greatlydeveloped. Simultaneously, enormous advances were made in China’sarchaeology. The knowledge of Early China, its history, its writingand its material culture, was completely renewed. On this basis,great strides were made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science history of later times. In consequence not only Chinaitself has today greatly changed, but also our knowledge andunderstanding of its unique civilization.
As a corollary to all these new developments, the erstwhile sohighly valued Classics have received far less attention. Only oneof these sacred books, the Changes 易 has become internationallyfamous, whereas the others have entered into a relative oblivion.Today, except for a small number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most people do not know very much about the Wujing.
This neglect has certainly gone too far. As many young scholarsin the field of classical studies have remarked, the fact so manyancient texts have been rediscovered these last decennia does notentitle us to forget the most ancient and revered Wujing. It istime that Five Classics finds their place among the sacred books ofthe great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Five Classics have been formerlytranslated and mainly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Most of thesetranslations are very old, some dating from more than a centuryago, whereas th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culture have made enormous progress. Therefore new, moderntranslations should now be made and not only into the major Westernlanguages, but in all important languages of the world. This is ourambition, our project and our great enterprise. Please help us tomake it a success!
THE VALUE OF THE FIVE CLASSIC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the Five Classics remain almost unknownoutside China is because their value is not sufficientlyunderstood. Although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civilization is certainly not inferior to the ancient books ofIsrael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also called the Pentateuch) or theFour Veda’s of Ancient India, the Wujing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The Sacred Books of Israel are traditionally accepted as the wordof God as told to Moses. As to the Four Vedas of Ancient India,they are seen as to be not of the authorship of man, but of divineorigin.
In the case of the Wujing, there is no such belief. They are notconsidered to be of supernatural origin. They rather deal with thehuman world and the natural universe. In the Songs are heard thevoices of the people; in the Documents, we read the words of theancient kings. The Changes reveal the structure of the naturaluniverse. As to three books that now represent the Rites, theycontain the words of the ancient sages for regulating the societyand the government. Seen in this way, the Five Classics are to beunderstood as the fundamental texts for preserving peace and orderin the world. As such, the Chinese Classics do not refer tometaphysics, but only to the human world. They thought is not seenas representing a religion, but rather as the basis of aphilosophy. This philosophy can be said to be China's one of the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mankind.
THE NATURE OF THE TRANSLATION
Until now, most translations of the Five Classics have followedthe academic tradition. That is: texts were translated as close aspossible to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out muchregard for the style and usage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Thereforethe syntax of the translation often followed the Chinese syntax.Also Chinese idiomatic terms were translated literally.
A literal transl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a good translation. Agood translation conveys more of the real meaning and also theliterary value of the original. For this new translation of thefive Classics, we aim at translating the texts in a way that themeaning is understandable for everyone and that the translated textis agreeable to read. Classical Chinese is very different fromcontemporary colloquial English.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understand the Chinese profoundly before adapting it in a flexibleway so as to translate the meaning in a significant and easilycomprehensible way that preserves the flavor of the original.
THE WUJING PROJECT
The idea of making a new translation ofthe five Chinese Classics into the major languages of the world wasfirst conceived in 1979 by Jao Tsung-I and KristoferSchipper. After having asked in vain for support fromseveral academic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t was tentatively putforward as a scholarly activity of the Library of the WesternBelvedere (Xiguan cangshu lou) in Fuzhou but equally withoutsuccess. . In the spring of 2008 the project was presented to theConfucius Institutes Headquarters in Beijing. After being evaluatedby an ad-hoc committee composed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itwas accept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institution with theundersigned as directing editors and with an internationalcommittee of scholars from China and abroad as advisors andsupervisors.
The Five Classics represent the very basis of Chinesecivilization, yet there are almost no modern translations. For themajor part, the existing translations have been made a a hundredyears ago. The best-known translation of the Five Classics is byJames Legge. Legge first published the Shangshu, theShijing and the Chunqiu with theZuozhuan in Hong Kong in 1872. Later Legge also didthe Liji and the Yijing. Although theywere remarkable for the time when they were made, thesetranslations are now completely out of date with regard to modernscholarship. The other old translation that is still used in theWest is the French one by Seraphin Couvreur that appeared between1889 and 1916. It is also more than outdated.
Among the Classics that have been translated individually, themost famous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Yijing byRichard Wilhelm,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G. Jung. Wilhelm’stransla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24. It waslat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Cary F. Baynes and published byPrinceton (Bollingen Series) in 1950. Wilhelm’s rendering remainsinadequate on many counts, not the least because he added his owncommentaries without distinguishing them from the original text.Another translation that remains popular today is theShijing of Arthur Waley (1937). Although the Englishis at times beautiful, there are many shortcomings.
Among the scholarly translations, the great Swedish scholarBernard Karlgren set the model. Along with learned glosses on manyof the Classics, Karlgren also published a translation of theShijing (1944 and 1950) and of the Shujing (1950).Both are only of interest to specialist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until recently, a limited numberof new renderings have been appeared, while many importanttranslations, complete or otherwise, have remained unpublished.
From all thi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Five Classics are todaynot available and that China therefore remains the only major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whose primal scriptural inheritanceremains largely unknown outside China itself. The present projectfor a new and accessible translation of the Five Classics into theworld’s major languages aims to remedy this situation.
Since two thousand year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lassics hasbeen the object of much discussion and changes. As known, inancient China there were not five but six Classics:Shi, Shu, Yi,Li, Yue and Chunqiu. Whenduring the Han the Classics were again assembled, it was found thatthe Yue was lost. Of the remaining five, theShi (Shijing), the Yi(Yijing) and the Chunqiu were more orless complete, whereas the Shu (Shangshu)and the Li (Yili) survived in fragmentarystate. Many changes took place during the Han. Instead of theShijing, the Yijing came to be consideredas the first among the Classics. The Shu was completedand reedited in a way that has since become one of the mostdisputed issues in classical studies. The Li wascompleted by adding to the Yili the Ritual Records(Liji) of the Younger Dai as well as theZhouli. The origins of this last text remainuncertain, but its influence has been very important.
We speak of the “Three [Books] of Rites” (sanli)when referring to the Lijing among the Five Classics,while often forgetting that most of the Classics are in factcomposites. The Shi contains odes from different dynastic periodsand intended for diverse ceremonials. The Shu, whatever the truedates of the fifty texts assembled therein may be is, even morediverse. The Liji is by all means a collection ofdifferent writings on a great variety of subjects. TheZhouyi is combines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gua) witha set of oracular pronouncements. These are clearly two differententities and the ex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remains amatter of discussion. And then there is the matter of thecommentarial traditions, the zhuan. Both the Zhouyi and theChunqiu obtained their status as Classics later thanthe others and both owe this status in the first place to theyuanyi that have been tagged on to them rather than totheir core texts. The traditional title of “Five Classics” musttherefore be understood in the sense that in China “five” maydenote a total figure rather than the true number of texts. Thisexact number of different texts assembled under the general titleof “Wujing” is for the moment hard to asses because, as notedabove, in many instances the yuanyi may be consideredas important as the core texts themselves. They should therefore beincluded in the tally and equally part of the translationprogram.
While keeping a traditional stance as to the definition of theWujing, the present program will also take into account modern textcritical researc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tudies in thephonology, etymology and syntax of the Wujing cannot be ignored.The data provided by archaeology are also extremely important. Theever increasing number of ancient manuscript versions for almostall the jing and zhuan is of paramountimportance. For the Yili and for theYijing we now have nearly complete early versions thatoffer important variant readings. The newly discovered“guwen” chapters of the Shangshu may wellcompletely reverse the accepted views on the textual history ofthis canon. If it can be ascertained that the same hoard of bambooslip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lso containsparts from the now lost Yue (Book of Music), then wecannot bypass it. Thus our new translation of the Wujing must bebased on up-to-date critical text editions and these have to beelabora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translation work itself.
The initial translation will be in English. It will attempt todo justice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yuanyi) of thetext, but without being literal. Neither should the translation beunduly influenced by a particular commentarial tradition. Thegeneral idea is to render the original text in a way that itconveys the sense of what is written in conformity to modern usage.Accuracy must be combined with readability.
For each of the Classics and their major subdivisions there willbe short introductory essays providing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histor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 in question. After this,the Wujing should be read for themselves. There will be nofootnotes. Truly important variant readings can be signaled in themargins. The remaining critical materials should be published, ifdeemed useful, in separate volumes.
On the ba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but with continuousr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texts, the Wujing will then be translatedinto the following languages: French, German, Spanish, Russian,Arabic, Hebrew, Hindi and Malay. These different languages havebeen chosen because of the number of speakers or for their culturalsignificance.
Fuzhou, November, 2008
Kristofer Schipper and Yuan Bingling
Annex: Biographical Notes of Kristofer Schipper and YuanBingling
Professor Kristofer Schipper (born 1934) is Member of the Royal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He obtained his PhD fromthe University of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in 1962,and his French State Doctorate in 1983. After having been a Fellowof the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he was appointed in 1972professor of Chinese Religions in Paris. In 1992 he was also giventhe chair of Chinese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AsDirector of the Daozang Project of 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he organized and edited the first complet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1500 works contained in the Daoist Canon of the Ming Dynasty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n 2004. He receivedthe Knighthood of the Legion of Honor of France, the Golden Medalof the Friendship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Lifelong ResidencePermi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tc. Professor Schipperis presently Specially Appointed Professor of FuzhouUniversity.
Professor Yuan Bingling (born 1962) studied Chinese ClassicalPhilology (Jingxue) at the University of Fudan, and Social Historyof China at Xiamen University. In 1992 she obtained a scholarshipfor advanced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where sheobtained her PhD in 1998,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Leonard Blussé. Her PhD thesis was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Leiden under the title “Chinese Democracies – A Study of the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0-1884).” This book has earned her wideacclaim in scholarly circles. Professor Yuan returned to herMotherland in 2001, and is now full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ofFuzhou University.
--------------------------------------------------------------
施舟人教授学术评传(英文、法文),全文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b465340100tp2y.html
19-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世界级学者云集于EPHE PARIS同台执教、会聚一堂,可谓不多见。LeviStrauss、Roland Barthes、Fernand Braudel、Lucien Febvre、Jacques LeGoff、Ferdinand de Saussure、Raymond Aron、Marcel Mauss、PierreBourdieu、Georges Dumezil、Jacques Lacan、Claude Hagege、GastonMaspero、Henri Maspero、Jean Yoyotte、Jean Bottero、LouisBazin、Jean-Pierre Vernant、Marcel Granet、Paul Demieville、JacquesGernet……年鉴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派、莫斯社会学、拉康心理学、杜梅齐尔神话学、索绪尔-海然热语言学、路易巴赞突厥学、韦尔南希腊学、埃及学、亚述学、汉学、闪学……群星璀璨。无声的轰轰烈烈。华人中有程抱一、饶宗颐毕业或执教于EPHE。施舟人接葛兰言马伯乐之法脉。
目录:
1. 《莱顿大学众弟子纪念施舟人教授——致敬RIK》
In honour of Kritofer Schipper (Rik)
by HARRIET T. ZURNDORFER (Ph.D. Leiden University)
2. 《施舟人——道体之复生》
Kristofer Schipper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Taoist Body
by Norman Girardot (Ph.D. University of Chicago)
3. 《华魂:三教合一,活的传统。施舟人教授学术回顾》
Rétrospectives et perspectives
de Kristofer Schipper (Ph.D. EPHE PARIS)
4.法国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EPHE PARIS众弟子致敬施舟人教授
功在千秋——施舟人主持《中华五经翻译》国际学术合作工程
由国家教育部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主办的“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务委员刘延东发来贺信,预祝会议圆满成功。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致开幕词。开幕式由国家汉办主任许琳主持。据许琳介绍,包括饶宗颐、汪德迈、施舟人、许嘉璐、汤一介、浦安迪、袁行霈、裴宜理、李学勤、朱维铮、普鸣等在内的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位知名学者,将在3天会议期间商讨与项目有关的翻译体例、底本、出版等问题。委员会将首先对“五经”进行英译,力争三年半出齐“五经”的英译本。选定翻译的“五经”经文大约70万字,译成英文约100万个单词。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8个语种版本,也将在英译本定稿后尽快开始翻译。
2008年夏,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并开始广泛接触海内外经学界、训诂学界、考古学界、翻译界等领域众多学者,筹备成立“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同时还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汉学界相关领域聘请杰出学者担任委员会首批成员,确保这项大型国际汉学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功在千秋——国际汉学盛举:施舟人主持多国学者用八种语言翻译《中华五经》。“五经”是指除了汉以前失传的《乐》以外的《诗》、《书》、《礼》、《易》和《春秋》。2000多年来,“五经”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五经”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虽然前人做过努力,“五经”中有的经曾有过英文、法文或德文译本,但大部分译本已经非常陈旧,有的甚至是在100多年前翻译的。迄今为止,一套适应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了解中国文化需要的多语种译本却不存在,翻译工作的实施旨在尽快结束“五经”缺少翻译译本、传播受限的的局面。
为系统翻译《五经》热烈鼓掌
据新华社电,国家汉办昨天在京宣布,将组织国际学术委员会,由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由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和以色列等国家的30多位知名学者组成,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已在北京召开,将用3天的时间具体商讨翻译的进程安排。
《五经》,即汉以前失传的《乐》以外的《诗》、《书》、《礼》、《易》和《春秋》,两千多年来,《五经》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古典思想体系的形成和中华帝国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历代也将《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经典文献。此次翻译《五经》,是一件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并进入国际文化舞台的大好事,我们为此事击掌欢呼。
首先,此次翻译《五经》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以政府部门的名义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这表明中国当前有力量也有号召力动员国际上的专家研究和传播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其次,此次翻译《五经》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五经》将有系统性的,符合现代语言习惯的全新的多种语言译本,这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为国际文化界所充分认识和正真接受,意义非常重大。以色列有古典的《摩西五经》,印度有古典的《四吠陀》,中国的《五经》与之相比,还不逊色,中国古人在《五经》中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以及天人和谐的理念,在当今世界,仍有重要的启示。
再次,此次翻译《五经》,将提供比较规范化的译本,据介绍,每一译本都将附有一篇导读性的前言,介绍该经书的历史背景、内容及意义。译文力求做到读者能够通过阅读经文而自明其义。而特别重要的经文异字将在页边空白处标明。必要时,还将出版专门的校勘记。这对于比较系统准确地了解中国《五经》典籍,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此次翻译《五经》,将有国际学术委员会组织翻译多种语言的译本,在词义上风格上将是比较统一的。委员会首先对《五经》进行英译,将原文翻译成符合时代语言特色的译本,力争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并接受,然后,根据英译本并参照经文底本,再组织人员翻译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等译本。显然,这是很系统的多语言译本,整体性地向世界推介中国古典文化,意义非凡。
长期以来,也陆续有对《五经》的翻译,但有的译本时间久,有的译本是节译;有的是中国人译的,有的是外国专家译的,并且多数是个人单干的,由一个多国专家组成的翻译研究团体来统一翻译,这是第一次,这可以使译本更准确,更符合时代风格和更具有所译语言的风格习惯,影响也将更大。
《五经》是中国文化典籍中之经典,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表现,这次系统整体多语言的国际性翻译活动,是中国古典文化进军国际文化舞台的战略性行动,它将对于世界文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悠久的文化思想史,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意义等,都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前,由美国的汉学家费正清,日本的铃木大左,英国的科学史家李约瑟,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等研究介绍中国古典文化,这对于中国文化传播世界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今,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由我们来组织国际性的学术委员会译介中国典籍,这表明我们对自己的古典文化更有自信心,也表明我们自己能向世界喊出评价中国文化的更响亮的声音。这,当然该给予热烈的掌声!
《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一次会议举行
以重新编译、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原典为宗旨,《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7月27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国务委员刘延东分别发来贺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等出席。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作大会致词。郝平指出,《五经》的系统翻译,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的开展,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献计献策,深入交流,密切合作。
郝平指出,《五经》不仅支配了20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且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许多朝代科举取士的考试科目,也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堪与以色列古经《摩西五经》和印度古经《吠陀经》相媲美。其思想对当今世界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由于历史原因,《五经》研究与翻译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仅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度还不高,而且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的适应世界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学习中国文化需要的多语种译本,个别经文只有英文或法文译本,有的译本甚至还是一二百年前传教士翻译的。这种现状非常令人遗憾。
郝平强调,各位学者在《五经》翻译上达成的共识非常重要:一是要重视继承前人的成果;二是要参考借鉴近30年来中国对经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三是要重视中国大陆的考古新发现和由此带来的经学研究新成果。
按照《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的计划,新《五经》将根据英译本并参照经文底本,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和马来语等8种语言。目前,选定翻译的《五经》经文约70万字,译成英文约100万个单词,2500页,其他语种的译本有所不同。编译将忠实于原文,尽量不受某一注疏或学术流派的影响,将原文翻译成符合时代语言特色的译本,既保证译文的精确性,也考虑译文的可读性,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理解并接受。英译本《五经》预计三年半后面世,其他语种版本《五经》的编译工作,将在英译本定稿后启动。
据了解,现存的《五经》译本大多是100多年前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1872年英国人理雅各在香港出版的英译《尚书》、《诗经》和《春秋》,后来又出版的《礼记》和《易经》。另一套并不完全的早期《五经》译本,是1889年至1916年法国神父顾塞芬在河北陆续出版的法译本,但该版本早已绝版,内容也已陈旧。二战后,虽然也出现过为数不多的新译本,但因某些原因,一些质量较高的译本迟迟没有面世。
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名知名汉学家会聚一堂,就《五经》的翻译体例、底本、出版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当用危机意识看待《五经》翻译
许石林
在多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的倡议下,《诗》、《书》、《礼》、《易》和《春秋》将由中国政府主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率先启动的英译本翻译将在三年半后完成,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我们必须出版一套全新的现代译本,只有这样,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才能被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并真正接受。”国家汉办主任许琳说。
我认为这应该被列为建国60年来重大的文化举措,这个巨大的翻译工程无疑将造福全人类,同时为中国政府奉行的和平发展理念铺设世界范围的文化思想基础。
这些宏观的大词儿就不说了,说说眼下具体的事儿——种种信息表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正越来越快速地被外国人接受和喜爱,远的如伏尔泰对孔子的崇拜就不说了,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法国宪法也不说了。日前中美两国举行的高端交流,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到国务卿希拉里,都有意地
引用了中国的传统俗话和孟子的话,甭管人家是不是就会这一两句,还是专为外交准备的特色辞令,这起码说明中国文化在人家那儿受到关注了,人家已经在主动亲近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了。
随着网络时代的沟通便捷,外国人已经越来越多地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成功开办就是一个例证。正在举行的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2009暑期特别节目“开心学国学”,虽然是初次举办,海外选手的
表现已经刺激了许多中国人。不仅是他们的知识掌握量,更重要的是外国选手身上表现出的诚敬之心,触动了许多中国观众和选手。
如今,由中国政府主持的《五经》的翻译工程正式启动,有的人会执拗地认为:中国传统的典籍是翻译不了的。我对此的理解是:即便是这种执拗的认识成为现实,也阻挡不了外国人通过学习翻译文字,而对《五经》原典产生兴趣,再进而追根溯源,最终掌握原典。那种简单地想像用语言的障碍阻挡文化的传播,是很不靠谱的。
中国人今天面对国学,还没有学习多少就争论来争论去,还停留在要不要学习等弱智问题上,还踟蹰在国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不给他搞清楚就不学——你还没学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有的还冷嘲热讽甚至胡嘴滥骂,将中国百年前贫弱落后的原因全推到传统文化身上……种种无意义的争论,像是烂泥塘里挣扎缠绕在一起的泥鳅,在那儿争论怎么入大海和要不要入大海。
想像一下,当这项翻译工程全部结束以后,外国人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会越来越热,那时候中国人还停留在这种烂泥塘的泥鳅阶段,那就不是受刺激的问题了。日韩有些对中华传统文化掌握得多的人,有时候对中国人表现出的傲慢和不屑,将会出现在更多的外国汉学者身上。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个养成的过程,不要以为读了几本书,会熟练背诵一些章句,就以为学到了传统文化。就是说,你拼命去学,也不一定学到文化的精髓。我接触的许多外国人,儒家倡导的温良恭俭让就体现在人家的行为上。
所以,我觉得应当用危机意识看待《五经》翻译工程,你不学、你不抓紧学,原本应该你先掌握的优秀传统文化就跑到人家那里去了。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有时候会重合,当两种认同不重合、有分歧的时候,我认为文化认同更优良、更高级。
原载《深圳商报》2009年7月30日
莱顿大学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
莱顿大学(LeidenUniversity)在世界享有盛誉。众多顶级国际学术刊物在此主编。始建于1575年2月8日,是荷兰最古老的大学,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均很发达,历史上曾诞生过许多著名的学者。莱顿大学有“欧洲汉学重镇”之称,早在1851年莱顿大学就设立了中文专业;1876年又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举办中国语言和文化讲座;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建立了中国学研究的专业学术机构———汉学研究院和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并与北京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等签订了合作协议,开展学者和学生的交流与合作。
(1)汉学研究院
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Sinological Institute)又名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ChineseLanguagesand Cultures Department)或汉学系(Department ofSinology),始建于1930年,主要从事中国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包括进行课题研究和研究生培训,出版定期学术刊物,举办学术讲座和专题研讨会等。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是戴闻达(Jan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其后是何四维(Anthony Frangois PaulusHulsewé)、许理和(Erik Zürcher)、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柯雷(MaghielvanCrevel)、赛奇(Tony Saich)和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等。汉学研究院的历任院长都是中国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对荷兰中国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在其发展过程中培养和造就了许多中国问题研究的专门人才。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荷兰中国问题研究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如何四维、许理和、弗美尔、柯雷等;也有一些人后来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从事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或教学,例如伊维德、赛奇、贺麦晓(MichelHockx)等。
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坚持研究与培训相结合的原则。培训的内容包括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中国宗教、中国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艺术等。
(2)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
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Documentation andResearch Centre forModernChina~DC)成立于1969年,隶属于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主要从事现代中国问题研究,包括学术研究和合同研究,同时也提供相关的教学和咨询服务。许理和任该中心的第一任主任。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参与莱顿大学及其亚洲、非洲和美洲印地安人研究院(CNWS)的现代中国研究计划。该中心每年举办1~2次有关中国特定领域最新发展或热点问题的国际会议或学术研讨会,并经常邀请来自中国的专家学者作专题演讲。目前,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有6名专职研究人员。他们不仅从事研究,也参与汉学研究院内外的教学和研究生培训活动,内容涉及现代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历史、法律和外交关系等领域。该中心还有一些特聘的研究人员,他们应邀参与合同研究,或通过多种方式向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接受荷兰教育、文化与科学部和莱顿大学的经费资助,并与中国和欧洲的政府组织、大学和企业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现代中国文献研究中心也是阿姆斯特丹-北京协会(AMPEK)、欧中学术网(ECAN)、欧洲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会议(ECARDC)的成员,并通过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院参与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伊拉斯谟斯交流网以及其他机构的交流计划。出版物:《中国信息》(ChinaInformation) ,专门刊登分析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文章。
袁冰凌教授简介
袁冰凌,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海外华人社会与福建历史。代表作为Chinese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in West Borneo, CNWSLeiden,2000.
荷兰人类学家高延及其对汉人社会的开拓性研究――以婆罗洲公司为例。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教授高延(J.J.M.deGroot,1854—1921),不仅以他对中国宗教的开拓性研究著称于世,而且也以他对汉人社会所做的最早的人类学研究而闻名于西方学术界。由于他在这一领域的著作都以荷兰文或法文出版,所以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此所知甚少。
在1877-1890年间,高延曾经在福建、印尼婆罗洲西部(加里曼丹)等汉人地区生活过十多年,对闽南人和客家人社会有深入的研究。他不仅学会了闽南话和客家话,还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文献研究。他认为那个时代欧洲汉学界虽然出版了一些中文字典和中国经典翻译作品,但对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十分有限。正因为如此,当时的英、荷政府对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中贡献最大的中国移民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他指出,对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汉学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他本人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为他赢得了莱顿(Leiden)大学中国人类学讲座教授的交椅。
本文拟以婆罗洲华人公司为例,谈谈高延对中国南方传统社会及其海外组织的开拓性研究,及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与局限。
欧美汉学界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领域的成就
陈东辉
中国古籍索引/通检①既是从事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必备工具书,编制工作本身又是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涉及版本学、训诂学、文献学,其难度、繁复艰苦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促进东西方汉学研究的交流,本文拟对欧美有关国家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情况作一概述。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地理原因,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古籍索引的重视程度不如日本。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约占世界各地学者所编制的全部中国古籍索引的80%,仅唐代文学古籍索引就达38种,其对中国古籍索引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
比起日本,欧美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少。但数量少并不等于没有价值,由于东西方学者在文化背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导致其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也各具特色,欧美学者在编制中国古籍索引方面有不少先进经验和技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况且,由于语言障碍和地域遥远等原因,中国内地学者对欧美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的了解,较之对台港地区和日本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的了解还要少。这就更有必要作些介绍。
法国堪称域外汉学研究之重镇,成果丰硕。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方面,法国和中国学术界合作组建的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于1942年在北平(今北京)成立。自1943年至1952年,该通检组陆续编制了《论衡通检》等15种中国古籍索引,总名《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1948年改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和中法汉学研究所(1948年改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通检组在1931年至1952年的20余年时间内,共计出版中国古籍索引79种,约占中国在1952年之前出版的古籍索引总数的70%。
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该丛刊以《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后改称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汉学通检提要文献丛刊》〖WTBX〗(Travaux d’ Index de Bibliographie et de Documentation Sinologiques)的新名称,刊出了法国学者施舟人(旧译施博尔KristoferSchipper)③主编的《抱朴子内篇通检》和《抱朴子外篇通检》、桀溺(旧译递尼J.P.Dieny)主编的《曹植文集通检》、加农(G.Gagnon)主编的《史通和史通削繁联合通检》等数种。
同时,施舟人还以个人之力编制了《道藏著作篇目通检》④、《黄庭经通检:内景和外景》和《云笈七签索引》。施舟人系法国著名汉学家,对中国道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曾在台湾研究道教多年,对中国文化、历史等情况十分了解,并在主编《抱朴子内篇通检》和《抱朴子外篇通检》时与台湾学者陈嘉然进行过合作。这就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所编制(或主编)的中国古籍索引的质量。
施舟人所编制(或主编)的上述5种索引都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有价值的中国古籍索引,所选用的古籍原文版本亦较为理想,如《抱朴子内篇通检》和《抱朴子外篇通检》所选用的是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校正本《抱朴子》。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当数施舟人对中国古籍索引编制事业的贡献最大。
桀溺也是中国通,主攻中国古代文学,对曹操、操植父子的诗文很感兴趣,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便有了《曹植文集通检》。笔者建议中国内地的出版社可以像重版《道藏著作篇目通检》那样,考虑重版另外几种索引,必将受到中国内地学者的欢迎。此外还有F.J.Chang编制的《宋代官职名称索引》、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制的《伯希和所获敦煌汉籍写本目录》等。
英国学者也编有少量中国古籍索引。如曾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一流汉学家翟理思(H.A.Giles)之子翟林奈(L.Giles)早在1911年就编制出版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该索引将条目
英译(附中文),按英文字母为序编排。E.D.Grinstead则编制了《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
本解题目录标题索引》。英国学者赖特(H.Wright)编制的《宋代地名索引》,1956年由巴黎
历史研究中心出版。此外,德国学者芬丝黛布氏(F.Kaete)编著了《汉代表演的内容和主题
索引》。除了美、法、英、德四国外,欧美其余国家所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极少。
由于近代经济原因,以美国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为最多。早在1930年9月,美国哈佛大
学和中国燕京大学合作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成立于北平(今北京)。从1931年2月
到1950年3月,引得编纂处编制了《说苑引得》等41种(50册)引得正刊,《毛诗引得》等23
种(31册)引得特刊(特刊一般附有原文),共计64种81册,总称《汉学引得丛刊》(Sinological Index Series),其中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即为美国
学者魏鲁男(J.R.Ware)②所编制。再有,佛若泽(D.H.Fraser)和洛克
赫特(H.S.Lockhart)编制的《左传索引》由英国牛津大学印书馆于1930年出版,巴克斯特(G
.W.Baxter)编制的《钦定词谱索引》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此外,S.J.Fidler和
J.I.Crump编制的《战国策索引》、汤姆斯编制的《韦应物诗注引得》、D.P.Jordan编制的
《法苑珠林志怪小说引得》、纳什(V.Nash)编制的《翟理思华英字典、康熙字典及佩文韵府
三字典引得》、麦克奈(B.E.Mcknight)编制的《丛书索引中文子目》、罗(K.Lo)编制的《四
部丛刊索引》、麦克马伦编制的《中国典籍索引》、拉克维尔茨(I.D.Rachewiltz)编制的
《蒙古秘史索引》和《金元文学作品传记资料索引》、米克尔(S.L.Mickel)编制的《甲骨重
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一:前编和后编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二
:续编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三:六种早期甲骨材料中重
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四:1925年到1933年出版的七种甲骨集
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五:1935年到1939年出版的七种甲
骨集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六:1938年到1945年出版的六
种甲骨集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七:1946年到1951年出版
的六种甲骨集中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八:殷墟文字甲编中
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九:殷墟文字乙编中重见片与成套卜
辞索引》、《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索引之十:1953年到1955年出版的五种甲骨集中重见片与
缀合片索引》等,均系用处较大、在欧美汉学界较有影响的中国古籍索引。其中由中国上古
语言和文学专家米克尔编制的“甲骨重见片与缀合片系列索引”实乃甲骨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书,早在1974年9月就开始在纽约《中国文化》杂志上连载,最后一部分登于该刊1983年第1
2期。但中国内地学者很难见到这一珍贵的资料,致使在相关论著中也很少提及。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利用在计算机领域的强大优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利用电脑
这一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编制中国古籍索引,如伊凡霍埃(P.J.Ivanhoe)等人早在1978年就利
用电脑编制了《朱熹大学章句索引》、《朱熹中庸章句索引》、《王阳明大学问索引》、《
王阳明传习录索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索引》、《戴震原善索引》等字词索引。此外,
当时在德国汉堡大学任职的吴用彤于1975年编制出版了《诗经索引》,这是首次用电脑编制的英译本《诗经》索引。
从总体而言,欧美学者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领域的成绩尚不能与中国本土相比,在欧美汉学界的学术成果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令人遗憾的是,上文提及的在现当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哈
佛燕京学社虽然继续存在,并且为促进国际汉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⑤,但其中的引得编纂处早已不复存在,整个机构再也没有编过任何中国古籍索引。《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汉学通检提要文献丛刊》虽未停刊,但差不多10年才出一种,几乎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与大名鼎鼎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实不相称。与日本以及台港地区的学术刊物经常登载中国古籍索引不同,法国虽然拥有《中国研究》、《中国研究丛刊》、《汉学书目杂志》、《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远东亚洲丛刊》、《
亚洲艺术》、《通报》等国际知名的与汉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刊物,却从未发表过法国或其他
国家学者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所以中国内地近来年刊布的有关法国及国外汉学的论著中很
少提及法国在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此外,上述中国古籍索引(尤其是编制年代
较早者)有的还有不少错误。如《左传索引》所采用的底本是19世纪出版的英译本《左传》
,《大公报》1937年5月20日《图书副刊》182期载中国学者聂崇岐文,指出了该索引的错误
之处。由于学风、师承等原因,欧美汉学家(包括华裔汉学家)一般更喜欢从事专门的学术
研究,而对编制古籍索引之类枯燥、繁琐的工作兴趣不大。加上他们觉得有大量中国、日本
学者编制的现成的古籍索引可以利用,就更不愿意、有时也觉得没有必要自己辛辛苦苦编
制古籍索引了。就算是编制索引,他们也更愿意编制汉学研究论著分类索引(这类索引相
对多一些),而不太愿意编制费时费力的中国古籍原文索引。这一现象目前在欧美汉学界并
无改变,并且他们所编制的中国古籍索引的数量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另一方面,欧美所编
的中国古籍索引一般或多或少夹杂着外文,这当然有利于西方学者使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中国、日本等习惯使用汉字的国家的古籍整理研究者利用这些索引。《巴黎大学北平汉学
研究所通检丛刊》中有许多法文、英文,令不少每天与古籍打交道的中国学者(还包括一些
日本学者)颇感头痛,这也许是这套通检丛刊在中国、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使用频率,
不如性质差不多、但几乎不含外文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制的《汉学引得丛刊》高的
一个重要原因吧。因此笔者建议中国内地有关出版社在重版这类索引时,应作一些改编。
笔者认为,西方汉学有重统计、重数据的传统,古籍索引在欧美汉学家从事研究时还是十分有
用的,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欧美汉学界可以利用他们电脑技术先进、经济实力雄厚等优
势,结合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在使用电脑编制中国古籍索引方面大显身手。
注
①“中国古籍索引”大体上可分为“中国古籍原文索引”和“中国古籍研究论
著分类索引”两大类,本文仅以前者为论述对象。此外,关于中国古籍索引,在一般情况下,
英美汉学界使用“Index”一词,法国汉学界使用“Concordance”一词,日本汉学界使用“索引”一词。
②本文提及的欧美学者的姓名,凡原书或有关文献中署有中译名者,则署中译名或中外文对照,否则署外文原名。
③笔者见到中国内地近年出版的一部工具书,在同一页码中将KristoferSchipper分别译为斯希佩、施博尔、施舟人,极易使人误以为这是3位不同的法国学者。
④该书经中国台湾学者李殿魁改编后,以《正统道藏目录索引》为书名,由台北艺文印
书馆于1977年出版;又经中国内地学者陈耀庭改编后,以《道藏索引:五种版本道藏通检》为书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⑤参见张凤《哈佛燕京学社七十五年星霜》,载《汉学研究通讯》(台北)第22卷第4期,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11月版。
汉学之源,博大精深;中西共建,源远流长
发布时间:2007年11月7日 浏览次数:867
汉学之源,博大精深
中西共建,源远流长
——记我院教授施舟人先生五经汉学讲座
11月5日晚七点,素质拓展中心学术报告厅里古乐阵阵,灯火辉煌,人文学院老教授施舟人先生所做的关于五经汉学的讲座将在这里如期举行。时间还未到,同学们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的来到会场等候。待施教授来到现场,全场立即掌声雷动,同学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施舟人老教授的到来。同行的还有本科评估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原教务处主任陈怡老师、福州大学副校长王健老师,以及施老先生的夫人——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袁冰凌女士。
施舟人教授,1934年生,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道教研究大家和宗教人类学家,精通八国语言,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潜心道教文化研究,于2004年完成并出版巨著《道藏通考》,并于2005年获法国政府骑士勋章和中国友谊奖。现任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在福州大学开设多门汉学课程,对中外汉学研究及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汉学学科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无偿捐赠藏书而建的西观藏书楼,更是福大引以为傲的一个宝藏。
施老先生一直致力于五经汉学的研究,这次讲座旨在为我们介绍五经在汉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发展状况。讲座开始,施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五经在世界文化中的涵义及其重要地位,分别列举了各国古文明的经典著作与之比较,在比较中为我们介绍了五经的历史。讲座的第二部分,施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西方对于五经的研究及五经汉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通过对利玛窦、汤若望、莱布尼茨等人的介绍,我们很好的明白了五经在世界史上的发展及影响。施先生在现场出其不意的小笑话常常逗得同学们开怀大笑,现场一片轻松祥和的气氛。在讲座的第三部分,施老先生呼吁我们:“不要忘记中华的本,研究古代也是一种现代化。”为我们阐释了重新翻译五经的重要性与必然性。据悉,施老先生得到我校吴敏生校长的大力支持,已与国内外多所著名高校联系,即将在福大建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汉学研究院。
讲座结束,同学们用热烈的掌声对施先生精彩的演讲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接下来,进入的是提问环节,施先生耐心的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关于何谓经典、如何克服翻译过程会丢失五经韵味的弊端等方面的问题,现场气氛一度达到高潮。短短的两个小时,让我们领略到了国际汉学家的风采,同学们纷纷为施老先生那儒雅的风范与睿智的幽默所折服,偌大的会场不断爆发出阵阵掌声。
之后,福大学生代表向施老先生赠送了一个极其特别的礼物——学生自创的模仿藏文的经文,意在把施先生致力于汉学研究的贡献比作当年玄奘取经的壮举,施老先生极为感动,表示会永远收藏。
施先生对于汉学的挚诚与热爱深深的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讲座在如此和谐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
汉学之源,博大精深;中西共建,源远流长。
施舟人先生讲座现场观众提问
(人文学院05级中文一班 赵娜娜 报道)
当前法国儒学研究现状
王论跃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08年10期
【原文出处】《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长沙)2008年4期第25~32页
【英文标题】The Present Status of French Research onConfucianism
(College of East Asia Study, Groupe des ENS,Paris, France)
【作者简介】王论跃(1964-),男,浙江岱山人,汉语言文化高级教师职衔、巴黎第八大学法国文学(符号学)博士、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汉学博士,获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博士生导师(HDR)文凭。现为知名学府人文高师(ENS
LSH,法国里昂)副教授,并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东亚学院(IAO)副院长。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符号学、法国当代文学与哲学。法文著作:《布朗修的符号学研究》、《理学的检验——王廷相的思想》(待版)、《中国今日的选择:传统与西方》(主编,待版)。合译《蒙田随笔全集》、《男女论》等。法国国家研究中心 东亚学院,巴黎
【内容提要】法国汉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内容上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数学等方面。近二三十年以来,法国在儒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于连、程艾蓝等知名汉学家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分别从思想、学术等层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对整个法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旨在讨论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工作,并尽量顾及他们的最新成果及其互相关系,从而揭示法国汉学界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Thehistory of French Sinology is of long standing, it containsliterary,
history, philosophy, sociology, mathematics and so on. Since recenttwenty
andthirty years, France made a great breakthrough on the researchof
Historyof Confucianism, sinologists such as Jullien, Ailan Cheng andso
on,they put forward a new research paradigm that from level ofthought
andlearning in the basic of previous scholar's study, and have madea
certaininfluence on ideological circle of France. In this paper inorder
todiscuss the research work of main reasearchers, consideringtheir
latestachievements and relationship, and reveal the latest developmentof
FrenchSinology in this research field.
【关键词】孔子/儒学/法国汉学/过程/相异性Confucius/Confucianism/French
Sinology/Process/Dissimilarity
【编 者 按】此文发表时,王论跃已受聘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8)04-0025-08
法国汉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自从17世纪以来,一代代的法国汉学家为推进法中文化交流,为法国乃至西欧对中国的了解做出了贡献。以汉学代表人物而言,17、18世纪时有来华传教的李明(Louie
Le Comte, 1655~1729)、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宋君荣(AntoineGaubil,
1689~1759)、钱德明(Jean-Joseph Amiot,
1718~1793)等;19世纪有法兰西学院前两任汉学教授(1814年设立此教席,标志着汉学研究从宗教界到世俗社会的转向)的雷慕莎(AbelRémusat,
1788~1832)、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再接下去有爱德华·沙畹(EdouardChavannes,
1865~1918)、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人。晚近的则有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及其尚健在的弟子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生)、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1928年生)等教授。鉴于国内对法国汉学历史、汉学研究机构以及老一辈汉学家的研究、介绍已经比较多,在这里我把文章论述的重点主要放在中青年法国汉学家上面。另外,法国汉学的涵盖面比较广,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数学等方面无所不包。为了避免面面俱到,我将以儒学思想史研究为中心,谈谈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工作,并尽量顾及他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我将以儒学思想史研究为中心,谈谈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工作,并尽量顾及他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而揭示法国汉学界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①
一 过程与创造
提到法国中青年研究儒学的汉学家,我们可以从于连(Franois
Jullien,生于1951年)的工作入手,原因是我们可以由他的研究所引起的争议引出其他学者及其他们的研究。于连曾经就学于著名学府巴黎高师(1972~1975),入学时的专业是古典文学,并以亚里士多德为题完成硕士论文。于连于1974年取得古典文学高级教师衔,于1975~1977年在北京、上海学习。1978年完成第三阶段博士论文,然后到香港负责法国远东学院分部。1981年任巴黎第八大学副教授,创立《远东、远西》(Extrme-Orient/Extrme-Occident)杂志。1983年获得国家博士学位。1985~1987年在东京的日佛会馆从事研究。然后到巴黎七大任东语系教授、主任。曾出任巴黎国际哲学院院长。现兼任巴黎七大当代思想研究所所长、法国大学研究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资深教授。于连的写作速度惊人,到目前已经出版二十余部汉学论著。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著作有《过程与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Procès
oucréation.Une introduction à la pensée des lettrés chinois,Paris: Le Seuil,
1989)、《势:中国的效率历史》(La Pron des choses. Pour une histoire del'efficacité en
Chine, Paris: Le Seuil, 1992)、《内在之象:〈易经〉的哲学解读》(Figures del'immanence. Pour une
lecture philosophique du Yi-king, le "Classique du changement",Paris: Grasset,
1993)。②
在其代表作《过程与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一书中,于连将过程视为“中国世界观的基本表征”,并将它与“在其他地方,尤其在西方所熟知的人类学、哲学模式”,即创造,对立起来。于连以王夫之哲学为例来说明中国哲学的过程性。他尤其参照了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以及《周易外传》、《周易内传》。于连在这一部书中不断地将过程等同于“道”。他这样说:“过程总是自成的。它以自身为模式,又是卓越的典范。既没有外来干涉又没有外加的规范:我们彻底远离如同所有‘创造’原型都必需的‘创造者’”(《过程与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袖珍版,1996年,页77)。那么是什么那样彻底地将过程思想与创造思想分开来的呢?于连的答复是:“如果我们在相异结构内再往上推的话,我觉得对立的原则应该如下:按照王夫之这样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基本直觉的系统化处理所设想的,在过程的源头,从来不只有一个机体(instance),而是两个。这两个机体一方面在互相确定时绝对地对立;同时,它们面对另一方均等地运作,而互相间从来没有先后、优劣之分。这样就产生了双向、连续互动逻辑。相对这一逻辑来说,根源的问题就失去了意义。没有什么超越;表征完好地反弹到本身;关涉的运作也不会招致与任一外在性的碰撞。说到底,这样既没有作为起始原因和第一动力的创世者的必然性——过程逻辑排斥这一点,也没有从更深层的角度讲的对他者——超越性的绝对的经验,我是说上帝——的参照”(袖珍版,页79)。于连通过道的阴阳两仪的二元关联性③说明中国哲学的内在性与非超越性。于是,他就把过程与创造的对立扩展到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对立。这一点基本体现了他的主要理论框架。
于连在《内在之象:〈易经〉的哲学解读》一书序言中说明为什么对此书的解释不可以停留在孔子时期。因为他认为:“在两千多年以来的不同时期,这一经典成为巨大的诠释对象。因为,中国人不断依据其特殊的关怀重新思考《易经》,同时将它视作主要的思考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说通过《易经》的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以这种阅读为起点,中国的思想得到了周期性的更新。三世纪的王弼以及十一世纪开始乃至后几个世纪反对佛教影响的理学家都是如此。因此试图独立于这一历史,或者因为全面考察这一历史太漫长却没有起码试图立足于这种沿革,这样来阅读这一经典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扎根于此,展现某一特定智性世界的文本的解释才有机会获取意义。”作者预设将《易经》与代表某一时代所有症结的决定性问题相对照,在最明确、最连贯的概念环境中考察这一经典,并在此基础上设问:“我们是否应该更有能力觉察这一文本究竟有什么用?有什么样的意义?”正是上述构想使得作者选取王夫之作为立脚点。不仅是因为《易经》使得处在动荡时代的王夫之找到对未来的信心,“《易经》的阅读位于他的思想的中心,他正是建筑于此来发现属于自然或者历史的过程的理性”。于连选择王夫之的第二个理由是通过他的论理的细腻、大胆、精确、严格来说明中国人并不总是依赖知觉,不重逻辑。于连接着卫德明(Helmut
Wilhelm)④将《易经》的卦的表征与神话模式作对照,两者的相同点在于都旨在显露超过抽象语言理解能力的某种东西,因而求助于一种形象图示;并且,两者都是以序列方式组织的。但是,两者的不同才是关键。神话如历史,将一出出戏搬上舞台,而《易经》的图式表征一种沿革(通过变化);前者需要表演者,后者则让一些组织因素(如阴阳)参与;前者是解释性的,对应某一原因,而后者则是某一倾向的指示;前者有创意,利用虚构,后者则起“侦探”式的作用(这跟它的第一功能,即占卜功能相吻合)。于连将这种区别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于是就有这样的结论:神话跟超越有关,而《易经》的卦的模式则是内在性的显露。于连还进一步探讨这两种不同思维模式的实质:“一种关注超越性的思想的特性试图探究他者的他性(即他者何以真正地为他者并得以组成外在性)。与这种对彼岸的开放相反,内在性思想的特性是试图凸现他者内的所有能关联起来的同一性的价值,让它们运作起来。”于连认为,统摄《易经》的思想是两极运作的组合逻辑,从这种逻辑自然可以引出连续的互动性。“因此《易经》这本书的唯一的目的是向我们显示内在于过程的连贯性。”于连《内在之象:〈易经〉的哲学解读》这一著作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试图步其后尘而构想何谓内在性逻辑”。
于连有关中西方思维二元对立的构思多少也是受到《易经》思想的启发。但是他比较关注两者的对立,而《易经》的二元互补逻辑主要还是导向一种和谐论。从总体而言,他的上述观点都是站得住脚的,也对我们理解中西方文化的实质有所帮助。但是当我们处理一些个案的时候,中西方的思想距离可能并没有这么大。葛瑞汉就曾经提醒我们关联式思维在古希腊并不陌生。如果说创造与超越的关系比较容易构想的话,过程与内在性却不是一种同位关系,因为过程强调联系、强调非封闭性,而内在性则注重结构与系统。这里我们应该把过程理解为一种宏观的宇宙体系的运作方式。
西方汉学家中谈过程的不止于连一人。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与郝大维(DavidL.
Hall)也非常喜欢谈论中国哲学的过程性。并从达尔文、怀特海、杜威等人的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他们基本上也是将“道”与过程等同起来。比如,安乐哲引用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庄子的“道,行之而成”(《齐物论》)指出“这个道不是已经创造好的东西,而是我们要参与的一个过程”。⑤但是,安乐哲也并不彻底排斥创造性,他接受他所谓的“协同创造性”(co-creativity),并在与郝大维合作英译《中庸》时大胆地将“诚”翻译成“creativity”。事实上,杜维明先生在研究《中庸》时已经作了这样的处理。安乐哲与郝大维的观点受到德国汉学家罗哲海(Heiner
Roetz)以及台湾学者李明辉教授的批评。⑥罗哲海强调儒家的“断裂超越性”及其“超俗道德”,李明辉则接着牟宗三的“内在超越性”批评安乐哲的儒学无超越性的主张。他们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适合于连的著作。于连用“évolution”一词表示过程的沿革、“进化”,并与历史(西方)相对照,也容易使人想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于连承继的是欧陆哲学传统(更多的是希腊的传统),并且他以中国与希腊的对话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而安乐哲与郝大维哲学上主要依据美国自身的实用主义传统。
承认过程的重要性还意味着对目的性的否认。而这一点在70年代就已经为汪德迈教授所注意到。他在1980年出版的《王道》(Wangdaoou la Voie
royale, tome II, Paris: EFEO,
1980)第二卷中提出“形态逻辑”与“目的逻辑”之辨,以区分以礼仪为主的中国式思想方式和以目的为主的非礼仪文化传统。不过,在我们看来,“形态”更加强调静态、系统的方面,而过程更加具有动态,属于变易哲学。顺便指出,在老一辈法国汉学家中,只有汪德迈对于连的工作给予肯定与支持。于连本人也多次表示对汪德迈的敬意。然而,于连的目的除了对中国哲学思想本身的思考以外,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这一外来思想重新思考西方,思考内在性,寻找西方思想的某种出路。因此王夫之乃至整个中国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迂回”,他的其中一本书的名称就叫《迂回与切入:中国、希腊的意义策略》(Le
détour et l'accès. Stratégie du sens en Chine, en Gréce, Paris:Grasset,
1995;中译本译名为《迂回与进入》)。
二 走出相异性?
于连的著作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法国哲学家如已故的利科、巴蒂厄(Alain
Badiou)等都对他的工作给予肯定。台湾辅仁大学、中国北京大学近年来还专门召开于连研讨会。他的著作被翻译到二十多个国家。很多局外人更是将于连与法国汉学划上等号。当然,大多数传统的法国汉学家对于连的治学方法一直有存疑,因而没有更多理会于连现象。就这样一直到毕来德(Jean-Franois
Billeter)的《反对法朗索瓦·于连》(Contre Franois Jullien, Paris:Allia,
2006)一书的出版。毕来德是瑞士知名汉学家,与法国主流汉学家有良好的学术关系。著有《被诅咒的哲学家李贽——晚明仕宦社会学考察》[LiZhi,
philosophe maudit(1527-1602). Contribution àune sociologie dumandarinat de la
fin des Ming, Paris/Genève:Droz, 1979]、《中国文字艺术》(L'art chinois del'écriture,
Genève: Skira, 1989)、《三次沉默的中国:论当代史与中国》(Chine trois fois muette:essai sur
l'histoire contemporaine et la Chine, Paris: Allia,2000)、《庄子讲座》(Le? ons sur
Tchouang-Tseu, Paris: Allia, 2002)、《庄子研究》(études surTchouang-Tseu, Paris:
Allia,2004)等著作。
毕来德在他的书的一开始就指出于连的整个著作“建立在关于中国相异性的神话之上”。接着他详细分析这一神话的历史渊源。他认为,这种相异性神话可以上溯到耶稣会士为了传教而对中国的某些美化,接着伏尔泰等多数法国启蒙哲学家继承了这些政敌对中国的看法,把中华帝国的专制性抽象掉,而展开对西方宗教、政治专制的批判。曾于1911年到1914年待在北京、天津的著名诗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在北京的时候这样写道:“实质上,我来中国并不是来寻找中国,而是对中国的看法”。知名汉学家葛兰言也在1911年到1913年在北京,他的汉学、社会学研究是追究中国社会的“体制基础”而回避比较。毕来德把比利时汉学家、长期在澳大利亚任教的李克曼(Pierre
Ryckmans, alias Simon
Leys,笔名:西蒙·李)也放入传播中国相异性观点的学者之列,因为他经常说中国是“人类经验的另一极”,“西方如果没有与中国这一根本的‘他者’的相遇,无法真正意识到其文化‘自我’的轮廓及其局限”。毕来德认为于连步这些学者的后尘,认为他把王夫之的思想等同成中国“文人思想”,说他没有将王夫之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比如蒙德斯鸠作历史性的比较,“似乎文人的思想从孔子到晚近都是一模一样”。“十八世纪以来谁也没有这样做过的。”毕来德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神学缺乏了解,于连笔下的西方思想也没有顾及教父哲学家以及其他神学家。在比较的问题上,毕来德以汉朝为例认为比较西塞罗与王充——法国知名汉学家马克(Marc
Kalinowski)正是这样做的——远比拿古希腊作比较更为恰当。毕来德还具体谈到于连的翻译问题,指出于连没有顾及汉语的多义性,他以“道”为例说明于连将这一中国思想的基本概念翻译为“过程”有不少问题。毕来德从自己翻译《庄子》的经验出发,说明“道”在不同的场合可以翻译为“方法”、“技巧”、“事物运作方式”、“路”等等。毕来德指出,于连借助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异托邦”的概念⑦,然而于连话语的“拓扑”的落脚点总是回到自身,回到自己的著作与系统上面。
应该说毕来德的很多话是切中要害的。他提出了比较学的共时性问题、提出了翻译的技巧等问题。事实上,翻译的问题不光是技巧的问题,也是认识论问题。毕来德不止一次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更重要的,他提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内在性思想归根究底是因为自汉朝以来的皇权的专制。这一观点在他的《三次沉默的中国:论当代史与中国》中已经有所论述。在我们看来,这一点可能也是毕来德论点的弱处。他一方面指责于连没有考虑到中国思想的断裂,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皇权专制的复杂性、多变性,也没有充分强调不同朝代以及同一朝代的不同阶段政权关系的复杂性。汉学家于连本人的回应也注意到毕来德这一破绽。他在《在路上:认识中国,推动哲学——反驳***》(Chemin
faisant, conna? tre la Chine, relancer la philosophie.Répliqueà***, Paris: Le
Seuil,2007)中说:“不可以像毕来德所做的那样,将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缩减为纯粹的政治行为,而完全不顾经济、社会因素,不考虑跟阶级有关系的生产方式:缩减为将通过利用文化而达到稳固长存,并由此将它的政权自然化、合法化的皇权专制。因为怎么可以令人信服这种内在性的思想可以在历史上这么多世纪里维持这样的社会状况?”(页120)于连在结束他的《反驳》时引用了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评他的一段话:“尤其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上正确’成了西方判断中国所依据的唯一参照,于连敢于站起来反对这点,他是有道理的。像于连那样要求的为了更好地回到自身而通过中国的迂回并没有来临。人们只是在别人的目光下再认识自己以及同类。人们终究只是在与他者的相遇中得到自我安慰,而不是怀疑自己甚至都不接受怀疑自己……‘政治上正确’的汉学家因此比某些还敢于谈中国的差异的汉学家更是‘欧洲中心论者’”(页141)。
毕来德的著作出来之后,几乎与于连的《反驳》同时出台的是程艾蓝(Anne Cheng)主编的《中国当代思想》(La Pensée enChine
aujourdhui, Paris: Gallimard,
2007)。作为此书的开篇,程艾蓝的引言便是《终结相异性神话》。作者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于连,但是其针对性还是十分明确的。程艾蓝生于1955年。与于连一样,她也是巴黎高师的高材生。入学时,读的是英文系,并获英文高级教师衔。曾经在复旦大学留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研究(1980-1982)。完成关于汉朝今古文之争的第三阶段博士论文后,进入国家科研中心任副研究员。1995年获博导文凭,1997年被任命为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2007年她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成为目前法兰西学院的第二位汉学家——另一位乃是1990年接替谢和耐教授的明清历史学家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教授。程艾蓝的主要著作有《论语》的法文翻译(1981年)、《汉代儒学研究:经典诠释传统的展开》(étude surle confucianisme
Han: l' elaboration d'une tradition exégétique sur lesclassiques,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et Institut des hautesétudes
chinoises,1985)以及巨著《中国思想史》(Histoire de la pensée chinoise,Paris: éditions du
Seuil,1997)。程艾蓝的《中国思想史》一书无疑是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英文版之后西文中最重要的中国思想通史著作,在法国甚至整个西方汉学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学家鲁林(Alain
Roux)在《中国在二十世纪》(La Chine au 20e siècle, Paris: ArmandColin,
2003)里称《中国思想史》与谢和耐的《中华世界》(Le monde chinois, Paris: ArmandColin,
1972年第一版)一样是当代法国汉学的集大成。《中国思想史》的作者从文献、历史的角度阐述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直接翻译了多数哲学大家的著名言论,无论对研究人员还是对普通学生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完成这一巨著之后,程艾蓝把很多精力放在中国当代哲学史的研究上,《中国当代思想》便是此类研究的成果之一。
参加这一集体性著作的还有语言学家艾乐桐(VivianneAlleton),政治学家白夏(Jean-Philippe
Béja),数学史学家林力娜(KarineChemla),语言学家褚孝泉(复旦大学法文系教授),谢和耐(Jacques
Gernet),宗教史学家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医学史学家伊丽莎白·许(ElisabethHsu),台湾学青年学者Damien
Morier-Genoud,人类学家杜瑞乐(JollThoraval)、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比较文学家张寅德以及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家左飞(Nocolas
Zufferey)教授。主编程艾蓝除了引言《终结相异性神话》之外,还撰写了其中的一篇论文:《“中国哲学”在中国的磨难》,其中对过分夸张相异性,对所谓的“内在性思想”论点都提出批评。另一些学者从他们自己的领域来批评相异性。林力娜的文章矛头直指一代汉学宗师葛兰言。后者通过《诗经》来验证中国语言的“诗性”、模糊性、缺乏逻辑、缺乏科学性。作者通过《九章算术》来证明葛兰言观点的幼稚。艾乐桐的文章讨论中国文字,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包括中国人本身,对中国文字的误解。上至莱布尼茨下至于连,很多人都将汉字当作表意文字。艾乐桐还批评有关汉字起源的宗教解释,她通过甲骨文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铭刻并不是卜筮的必然因素;我们可以将它们解释为有选择性的档案系统”。她的观点与汪德迈的观点正相反。后者在其论文《中国人的历史观》(页47-74)中说:“那没有它就没有档案记录的文字是为了记载卜筮而发明的”(页48)。在这本批评相异性,跟批评于连多少有关的集体著作中,汪德迈再次对于连的有关中国思想的内在性的观点表示肯定,并多次征引他的主要著作。谢和耐的文章名为《王夫之的现代性》。作者在晚年的力作《事理:王夫之哲学论》[La
raison des choses. Essai sur la philosophie de WangFuzhi(1619-1692),
Paris:Gallimard,
2005]中提出中西思想的两种不同范式:组合逻辑与话语逻辑。在《王夫之的现代性》一文中,谢和耐指出关于中国的两个常见的错误:“其一是认为存在没有时间性的‘中国思想’;其二也与之相关,是强加给中国一个与它所经历的深层变化所不能兼容的稳固不动性。”他还这样写道:“历史对他[王夫之]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是为了消遣读者而编的叙事:对普遍性变化显得最明显的领域,即历史的素材进行思考,那就是哲学思考的一种方式”(页38)。王夫之的历史观可能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谢和耐本人的历史观或者汉学观,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当代思想》中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的杜瑞乐教授所作。杜瑞乐教授兼治哲学、人类学,对中国与日本都非常了解。他的研究对象是新儒家,尤其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杜瑞乐在他的文章《当代中国的实用主义诱惑》中指出安乐哲与杜威以及新实用主义者罗蒂(Richard
Rorty)之间的关系,批评他们的非历史化倾向。杜瑞乐在文章中还着重介绍了李泽厚的工作,尤其是他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这在法国还是首次。对于李泽厚而言,第一哲学不是伦理学,而是美学。他的历史本体论“从根本上不赞同承继宋明理学的现代新儒学,不赞同以‘心性之学’来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李泽厚在提出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之时,已然提出原典儒学重视情感的特征,后见到战国出土竹简《性自命出》中“道生于情”的资料,更进一步提出原典儒学为“情本主义”。李泽厚的主张并非孤立的,自宋以后学者对于儒家哲学的认识有以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论”,刘宗周为代表的“意本论”,戴震为代表的“重情主义”等等。只是一般学者会将戴震思想看作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并不把它当作是向传统的回归。杜瑞乐注意到李泽厚的论点与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之间的不同以及他们两人对康德的不同解读。但是,他在文章的结论中也指出在李泽厚的思想中也有伦理的层面,在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中也给美的满足留有位置,如他的《原善论》的部分片断。在日佛会馆学报《日本研究》(Ebisu,
étudesjaponaises)第37期(2007年)上,杜瑞乐发表了一篇长文:《关于哲学的与非哲学的几点意见》(“Quelquesremarques
sur le philosophique et le
non-philosophique”,p.47-70)这样解释他所从事的“人类学的哲学进路可以使人觉察到在哲学话语与象征实践中存在一种关系。这关系不能简单地作为一个客观化或概念把握的过程处理。我们声称依据的象征实践,譬如宗教性的,不能只是简单的哲学话语对象。既具有某一哲学理念同时又加入一个特别传统的人,如一个犹太哲学家、一个新儒学家,必须在试图表述他们的思想之前先区分语言的活动及其多样实践”(页63)。他说的意思是本文化的语言、文化、象征等实践先于哲学活动。
三 其他儒学研究者
前面我谈论的内容相对集中,针对于连现象及其引发的问题以及程艾蓝主编的《中国当代思想》。可以说,于连与程艾蓝治学的方式以及采用的范式都有很大的差异。一个偏重思想,一个偏重学术。⑧至于毕来德,情况要复杂一些。他是一个兼治思想、学术的学者。他对于连的批评很中肯,但是有时候又回到同一个范式内,如前述的内在性问题。接下去我再讲几个汉学家,也是法国汉学界具有影响的学者。
我在前文中已经几次提到马克(Marc
Kalinowski)。他出生于1946年,1972年获得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汉语、西藏语学位文凭,1973年取得巴黎七大汉语学士学位。然后到巴黎天主教学院学习神学以及《圣经》的历史,同时在巴黎七大学习语言学。1978年获得巴黎七大第三阶段博士学位,1979年进入远东学院。1980年到复旦大学哲学系从事研究,1981到1984年到京都远东学院分部。1991年在巴黎七大获得博导文凭。1993年离开远东学院担任巴黎高等实验科学院(EPHE)教授。他的汉学研究主要涉及传统宇宙论、历法、占卜以及中国宗教、思想中的象征系统。他的研究具有扎实的文字学与语言学功底。他于1980-1982年间研究了汉代儒学的形成,以《吕氏春秋》为依据而反对那种认为秦帝国受法家思想支配的观点。1991年出版了《五行大义》的译注本[Cosmologie
et divination dans la Chine ancienne. Le Compendium des cinqagents(Wuxing dayi,
VIe siècle), Paris, EFEO,1991]。近年来对《周易》(上海图书馆藏简本)等都下过工夫。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早日问世。
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马蒂厄(Rémi
Mathieu)教授兴趣广泛,治学范围涉及中国古代的神话、哲学(儒家、道家)、文学、人类学多个方面。他早年翻译研究《穆天子传》、《山海经》等神话。近年来翻译出版了屈原的《离骚》、合作主编了《淮南子》的翻译。并首次在法国对《老子》三个版本(王弼本、马王堆本以及郭店本)进行比较翻译(Lao
tseu. Le Daode jing, Paris: Entrelacs,
2008)。法国治思想史的汉学家中关注近年来出土的楚简的并不多,马蒂厄对郭店《老子》的研究、翻译在这方面弥补了空白。在儒学方面,他重新注译了《荀子》等儒家经典,待出版。前两年出版了《孔子》(Confucius,
Paris: Entrelacs,
2006)。最后一本书的体例有些特别。全书分成两篇:《夫子的生平、著作、理论与继承者》、《文选》。夫子的理论分成仁、忠、礼、诚、修身五个方面来讲。夫子的继承者则主要谈孟子、荀子,也涉及子思。《文选》部分则分成“学”等二十个主题,并集中《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孝经》、《荀子》等经典文献对这些主体的阐述。第二部分由于翻译所牵涉的文本比较多,适宜作为资料查阅。
在马蒂厄教授的《孔子》出版之前,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知名法家、道家研究专家、小说家勒维(Jean
Levi)教授也于2002年在Pygmalion/GérardWatelet出版社出了同名书《孔子》(Confucius),此书袖珍本在2003年由Albin
Michel出版。勒维教授在《前言》中这样介绍他终于迟迟来到儒学空间的原因:
一个在我看来更教给人对社会的因循守旧而不是哲理的学派是不足以吸引我的。我所倾向的是福楼拜的那种思想:“荣誉使人毁誉,职衔让人堕落,职位令人愚蠢”,因此我对教育旨在培养人担任政府要职这样的儒家信条没有好感。相反,道家对我有吸引力。我喜欢庄子的自由、极端的夸张,否定所有社会机制的合理性,主张回归到野性的生活。《道德经》里句子的神秘、咒语般的特性让我入迷。韩非子的政治哲学把社会太平建立在对人的感情的有效控制之上,而儒家的乌托邦纲领则依赖从政者的仁义、善良来管理为利益所诱惑的百姓。我在前者中找到更多的清醒、现实主义与逻辑。如果说一个社会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一条狼,那么就像道家非常智性地说的那样,是否与其与城里的为伍,还不如与林中的来往,即使要冒着跟狼群嚎叫之嫌?因此我对边缘感兴趣,而留在中国传统的边际,周转于其周围而没有在其中心历险。[……]我在考察道家对以话语为手段传承礼仪的批评时,我发现庄子在偏离的同时处在孔子真实实践的直线之上。他把孔子的理论依据颠覆得如此之妙是因为他真正把握了它们。他正是以儒家的最基本的原则为名来指控它。这样,疑团就消失了;原来是一种误解。原来人们在孔予哲理不存在的地方寻找它,即在词语中而不是在动作中。
勒维就是要展示一个具体生动的孔子。另外可以顺便提一下的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的叶理绥夫人(Danielle Elisseeff)也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孔子:从词语到行动》(Confucius.
Des mots en action, Paris: Gallimard, coil. "Découvertes",2003)。
令人欣慰的是法国新一辈汉学家正在脱颖而出。专攻过张载、苏轼的11世纪儒学、文学专家费飏(Stéphane
Feuillas)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费飏出生于1963年,也曾是巴黎高师的学生,他的关于张载的博士论文导师是于连,之后一直在巴黎七大任教。费飏不仅大量阅读经典,还不断探寻“思想地”,包括文学。他还试图从西方传统以及现代哲人的解释中得到启发。譬口他在《从福柯到苏东坡:自我修养跨文化进路的几要素》(De
Foucault à Su Dongpo: éléments pour une approche transculturellede la culture
de
soi)⑨一文中,对福柯在《主体诠释学》⑩中所阐述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身体修养技巧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把对福柯的阅读与苏轼的《东坡易传》结合起来,探讨福柯自我修养论与苏轼的情性论之间的关系。在最近出版的关于“神”概念专辑的《远东、远西》第29期的一篇文章中,费飏讨论张载的“神”的概念,并结合他对狄德罗、斯宾诺萨、布鲁诺等西方哲学家、科学家的理解进行比较。可以相信,以费飏为代表的新一代法国汉学家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出色地完成他们这一代人的新使命。
四 结语
怎样研究儒学、研究中国思想史?相异性真的可怕吗?中国学应该采用哪一种或者哪一些范式?不管怎么说,中国对西方人、对西方汉学家来说是异域,所以相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汉学家能够回避这个问题的。如果从事中国研究的西方汉学家研究的视角、观点不能发挥其本文化的特点,而是跟中国自己的学者的研究方法大同小异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原创力将是很有限的。法国的人文思想常常以其形式的新颖而吸引世界,法国的汉学界也需要这种丰富的想象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面对相异性,我们能否像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提倡的“他人”哲学那样,让自我“放下其主权”,建立一种“无利益”关系,那就是对他者的责任或者“为他者的存在”(11)。这种对他者的负责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跟社会、文化、历史、种族等因素毫无关系。只有在这种伦理关怀下,相异性才能得到彰显。我所期待的西方儒学研究也正是这样一种无私的境界。
以上我选择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汉学家简单讲了法国儒学研究的现状,然而,研究儒学的学者远不止于我上面提到的学者,研究的课题也远非局限于此。法国汉学传统上对道教的研究比较深入。马伯乐、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施舟人(Kristopher Schipper)与罗比萘(IsabelleRobinet)、傅飞岚(Fransiscus
Verellen)等四代专家都为道教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施舟人对《道藏》统考所做的工作为世人瞩目。最近几年对庄子的研究也有很多新成果,于连、毕来德、勒维(Jean
Levi)、葛浩南(RomainGraziani)等都有专著出版。佛教方面的研究专家有兼治道教、禅宗、医学的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教授、远东学院的郭丽英教授等。法家方面研究有汪德迈于1965年出版的《法家思想的形成》一书。作者通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变迁,阐述商鞅、申不害、慎到和韩非子等人法家思想的形成过程。勒维翻译过《韩非子》、《商君书》等等。总之,法国的儒学以及一般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欧洲仍是一面旗帜,不容忽视,值得我们借鉴。
[收稿日期]2008-06-21
注释:
①知名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Vandermeersch)、程艾蓝(Anne
Cheng)曾在《世界汉学》第1期上发表过论文《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1998年,页94-99)。这里我尽可能谈新近的儒学研究。本文初稿曾经作为演讲稿,于2008年4月18日在岳麓书院明伦堂演讲。
②杜小真教授的《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附录中译有2003年以前的于连的主要著作介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77-99。
③英国知名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Graham)曾经在《阴阳与关联思想的性质》(Yin-Yang and the Natureof
Correlative Thinking, Singapour: The Institute of Esat AsainPhilosophies,
1986)一书中专门讨论中国思想的关联主义特性。他在该书《引言》中认为,葛兰言(MarcelGranet)著于1932年的《中国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仍然是关于中国关联思想的无法比拟的入门书。有关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史华慈(BenjaminI.
Schwartz)等人的看法以及黄俊杰先生本人对“联系性思维”的发挥,可以参见其《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中的〈传统中国的思维方式及其价值:历史回顾与现代启示〉篇,通北:喜玛拉雅基金会,2001年,页313-335。
④《〈易经〉里的天、地、人》(Heaven,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University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⑤安乐哲:《当代西方的过程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三辑,2004年10月,页5。
⑥详见何乏笔(Fabian
Heubel):《当代西方汉学家对“儒学”之哲学诠释初探》,李明辉、陈纬芬主编《当代儒学与西方文化·哲学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2004年,页43-84。
⑦福柯在1967年曾在法国建筑学会发表一个重要演讲,题为《另类空间,异托邦》(Les espacesautres.
Hétérotopie)提出建设“异质拓扑学”(hétérotopologie)的构想。此发言等到1984年福柯才让发表。
⑧姜广辉老师在主持演讲的时候将他们俩的治学方式跟李泽厚先生与李学勤先生的不同方法加以对照,很有参考价值。
⑨王论跃(FrédéricWang)主编《中国今日的选择:传统与西方》(Le choix de la Chined'aujourdhui:
entre la tradition et
lOccident),电子版参见www.ens-lsh.fr/colloques/chine2004,文字版将由LesIndes Savantes出版社出版。
⑩Michel Foucault,Lherméneutique du sujet, Paris: Gallimard/Seuil,coll.
"Hautes études", 2001.
(11)EmmanuelLevinas(列维纳斯):éthique et infini《伦理与无限》,Peris:Fayard,
1982,页42-43。NU28
北京大学对话丛刊卷首语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三分之一就这样在希望、失望、战争、仇恨、焦虑中过去。如何在强权与复仇中为我们共居的世界寻求一个较安定的未来,人们逐渐觉悟到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宽容与合作是一条必由之路,而理解、宽容与合作的前提是对话。
2003年岁末,在给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贺信中,联合国教科文所属文化政策与跨文化对话司司长卡特林娜·斯特努女士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多样性世界宣言",指出这一宣言已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接纳。它来源于2001年"911"事件后的觉醒,而文化交流正是新的全球化现象的轴心。她论证了“多样性”(diversity)、"对话"(dialogue)和"发展"(development)三者(即3个"D")的关系。认为文化的多样性绝非僵化不变的"遗产"的总和,而是鲜活的、可更新的人类财富,是确保人类生存延续的一种动态过程;她强调在本来即是多元化的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仅必须认识到各种形式的"他者性",而且也应认识到他或她的自我身份确认中所存在的"多元性"。她的见解极富启迪,我们在本期发表了贺信全文。
要实现这种新的对待"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就必须跳出百年来古今中外相互对立的各种争执,从新的高度来看待一切。汤一介教授的《走出"中西古今"之争,汇通"中西古今"之学》一文对此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金丝燕的《合 唱 与 隐 潜:一 种 世 界 文 学 观 念-- 论 中 国 当 代 文学 的 态度》则是超越"中西古今",站在世界文学高度来讨论现代性中国文学的一个实际范例。龚刚等三位博士关于"力"与"仁"的讨论也是从全球角度出发来讨论"全球治理"的。自从2000年《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出版以来,"全球治理"一直是一个十分热门的全球话题。三位年轻学者的讨论颇有深度地展示了中国青年一代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考。
本期重点讨论的还有另一个全球性问题,即如何消除"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相互隔绝的问题。斯诺?quot;两种文化"论点不但在当时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而且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莱维-勒布隆教授指出十九世纪以来,人类被划分为科学家与大众两类,前者被视为普遍与总体知识的拥有者,后者则被认为无知、缺乏分辩能力、需要灌输知识的对象。莱维-勒布隆教授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因为科学家除了在极狭窄的领域内拥有一些专业知识之外,对其他学科来说,与大众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提出科学必须重返文化中心。孙小礼教授的专著《文理交融--奔向21世纪的科学潮流》一书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反思,指出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正在被分裂成自我封闭?quot;两种文化",即以科学知识和技术操作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文化,以及围绕着人文研究所展开的人文文化。其结果是,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各自抱有偏见,使两种文化处于分离和对抗的状态。她认为必须承认科学与人文的不同,努力促进这两大知识领域的理解和交流,同时重视蔡元培先生多年前提出的"融通文理"的教育理想,才是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两种文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此外,读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札记和评《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两篇承接了上一期的"大学改革论坛",也承接了更上一期的"纪念白璧德逝世70周年",两篇都有与当前现实紧密相关的创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科学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教授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南音》,它扎扎实实地超越了中外古今,其资料掌握之丰富,见解之深邃,2003年在银川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首次报告时,就已是语惊四众,今天再看,仍然感到有很多收获!
联系人:
乐黛云
北京市北京大学中文系
邮政编码:100871
Tel:62752964
Fax:6275 2964
E-mail:tyjydy@pku.edu.cn
赵白生
北京市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
邮政编码:100871
Tel:62754160(O)
Mobile:13801364227
Fax: 62765009
E-mail:bszhao@pku.edu.cn
张 沛
北京市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邮政编码:100871
Tel:6276 2279
E-mail:zp30230@sina.com.cn
学者简介
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教授,1934年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施舟人通晓8种语言,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1979年施舟人来到中国专门从事文化研究,历时二十余年不辍。2003年,施舟人在福州大学建立了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
他是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中国首家西方人文典籍图书馆“西观藏书楼”创办人,被法国总统授予荣誉骑士勋位。主要代表作为《道体论》(The
DaoistBody)、《道藏通考》(Daoist
Canon)、《中国文化基因库》等数十种论著,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学者风采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
生平介绍
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施博尔)教授又1934年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妻子袁冰凌是福建德宁人,女儿施心韵。施舟人通晓8种语言,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目前,担任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暨西观藏书楼主任。
从“施舟人”这个中文名字,就能直观地感到施教授对中国文化的痴迷和精通。按他自己的解释,之所以取这样一个“道”味很浓的名字,是因为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老子是“周朝人”,庄子名叫庄周,都有个“周”字,故取其谐音“舟人”,同时包含有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渡人”的意思。
一种源自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始终牵引着施舟人的人生轨迹。施舟人年少时就被中国艺术所吸引。在阿姆斯特丹读完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主的中学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远东美术史和宗教人类学,后来受教于法国著名汉学家康德谟(MaxKaltenmark)教授门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1962年,施教授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就来到中国台湾做访问学者,1972年受聘于法国高等研究院,讲授中国宗教史。1976年,他在巴黎创办了欧洲汉学协会,会员规模500多人,在欧洲与各国汉学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之桥。
1979年中法两国恢复友好邦交后,他马上动身来到北京进行研究工作。发起并主持了由法国科技中心(CNRS)、荷兰莱顿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共同参加的大型国际汉学项目《圣城北京》。此后20余年,施舟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从西藏牧民到福建客家人,他都做了深入探访。2001年,在神州大地游历了22年的施舟人受聘于福州大学,并举家迁居中国福州,终于将脚步停留在福州,成为当地引进的最高层次人才之一。那里,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以收藏西方人文典籍为主的西文图书馆“西观藏书楼”。所收藏的一万余册西方各种语言的经典名著以及流失海外的部分中国古珍本,其文献价值不可估量。
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2003年施舟人在福州大学建立了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还有一个别致的名字——西观藏书楼。施舟人希望在10年时间里,将西观藏书楼建成10万册重要西方经典收藏量的西方典籍中心。施舟人与妻子向西观藏书楼捐赠了两万多册图书。这两万余册英、法、德、荷兰、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拉丁等西语文化典籍涵盖面异常广阔,多半是施舟人的个人珍藏,其中一些是16世纪以来的珍本图书,更是施舟人的心爱之物。
2004年,施舟人数十载潜心道教文化研究的成果集成皇皇巨著《道藏通考》出版,堪称世界道教研究的最新力作,并荣获在华外国专家最高荣誉——友谊奖。2005年,法国总统授予施舟人荣誉骑士勋位。
2005年11月23日,施舟人获得了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这对于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最高的认可。
目前,施舟人教授正在主持由国家汉办组织的大型国际汉学合作项目——《五经》的翻译工作。在对中国文化的不懈追求中,施舟人默默地品味着汉学研究的酸甜苦辣,他曾由衷地感叹:“研究汉学是十分艰苦的。做一个中国专家很难,做一个研究汉学的专家更难,做一个研究汉学的外国专家,其难度更是难以想象。而这也是我一生都不能停止的挑战,注定了我一辈子不能休息。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学者,他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要建立文化基因库。他先后被法国总统授予荣誉骑士勋位,被中国政府授予在华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友谊奖。
研究领域
中国道教
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
宗教人类学
出版论著
《论中国的进香活动》(Les pèlerinages enChine),载《朝觐》(Les
pélérinages),巴黎:Seuil出版社,1960年,第305-341页;
《汉武帝内传研究》(L’empereur Wou des Han dans lalégende
Tao?ste),巴黎法国远东学院第58期(1965年);
《抱朴子内篇通检》,巴黎:汉学研究所,1965年;
《台湾的道教文献》,载《台湾文献》第17卷,1966年第3期, 第173-192页;
《滑稽神》(TheDivine Jester: Some Remarks on the Gods
of theChinese Marionette
Theatre),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66年,第81-95页;
《五岳真形图的信仰》,Michel Soymié
译,日本东京:《道教研究》1967年第2期,第81-95页;
《道教科仪及其传承》(Taoism: The Liturgical
Tradition),1968年第一届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论文,意大利贝拉焦;
《抱朴子外篇通检》,巴黎:汉学研究所,1970年;
《中国的鬼神理论》(Démonologie
Chinoise),载《精神、天使与魔鬼》(Génies, anges etdémons),巴黎:
Seuil出版社,1971年,第405-426页;
《道教仪式中的文书》(The Written Memorial in Taoist
Ceremonies),载A.P.Wolf编《中国社会的宗教和仪式》(Religionand
Ritual inChinese Society),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74年,第309-324页;
《黄庭经通检》,巴黎:法国远东学院第102期,1975年
《道教的分灯科仪研究》(Le Feng-teng,Rituel
tao?ste),巴黎:法国远东学院第103期,1975年;
《道藏书名通检》,巴黎:法国远东学院第104期,1975年;重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老台湾的土地公会》(Neighborhood Cult Associations in
Traditional
Taiwan),载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末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
"都功の职能に关すち二、三の考察"(福井正雅译),载酒井忠夫编《道教的综合的研究》,东京:Kokushu
kankyokai,1977年,第252-290页;
《道体论》(TheTaoist Body),《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s),第17期(1978年),第355-386页;
《<老子中经>成书年代考》(Le Calendrier de Jade: note surle
Laozizhongjing),载《德国东亚自然与人类学会报告》(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lkerkunde
Ostasiens),第125期(1979年),第75-80页;
《中国古代的末劫救世思想》(Millénarismes et messianismesdans
laChine
ancienne),载《中国》(Cina)第2期副刊,罗马:IsMEO,1979年,第31-49页;
《云笈七签索引》第1卷,巴黎:法国远东学院第131期,1981年;
《道体论》(LeCorps tao?ste :-corps physique, corps
social),巴黎:Arthème Fayard出版社,1982年;英译本TheTaoist
Bod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荷兰文、意大利文等译本。
《云笈七签索引》第2卷,巴黎:法国远东学院第132期(1982年);
《道教的出家制度》(Le monachisme tao?ste),载Incontro di
Religioniin Asia tra il III et il X Secolo d.C.,
佛罗伦萨:Urbaldini,1984年,第199-215页;
《台湾的王爷和瘟神信仰》(Seigneurs royaux,dieux des
épidémies)载《宗教社会科学档案》(Archives des sciences
socialesdes religions), 第59卷,1985年第1期,第31-41页;
《道教仪式中的替身》(La représentation du substitut dansle
ritueltao?ste),见 《仪式的作用》(Fonction du
rituel),巴黎:SPASM,1985年,第33-54页;
《敦煌抄本中的道教职位》(Taoist Ordination Ranks in the
Tun-huangManuscripts),载G.Naundorf,卜松山和
H.-H.Schmidt主编《东亚宗教与哲学》(Religion undPhilosophie
inOstasien. Würzburg),1985年,第127-149页;
《唐代的许真人香火和道教科仪》(Taoist Ritual and Local Cultsof
the T’angDynasty),载M.
Strickmann主编《密宗和道教研究之三》(Tantric and TaoistStudies
III),布鲁塞尔:IBHEC,1986年,第812-834页;
《道教的白话法事与文言科仪》(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Ritualin
Taoism),载《亚洲研究》第45期(1986年)第21-57页;
《刍狗和纸老虎释义》(Chiens de paille et tigres en
papier:unepratique rituelle et ses
gloses),载《远东远西》(Extrême-Orient
Extréme-Occident)第6期,巴黎:巴黎八大,1986年,第83-95页;
《道教仪式中的时间循环》(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Time
Cycles inTaoist Ritual),见J.T.Fraser主编 The Study
ofTime第5卷: Time,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and
the West.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5-205页;
《从田野调查看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的理论》(Comment on créeun
lieu-saintlocal : à propos de Danses et Lègendes
de laChine ancienne de Marcel
Granet),载《汉学研究》(Etudes chinoises),
第4卷,1986年第2期,第41-61页;
《赵宜真的清微宗》(Master Chao I-chen and theCh’ing-wei
Schoolof
Taoism),载秋月观英主编《道教と宗教文化》,东京:平河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李渤及其真系传》,载饶宗颐编《韩愈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2-340页;
《道教的目连戏》(Mu-lien Plays in Taoist Liturgical
Context),载D.Johnson主编《仪式戏曲和戏曲仪式》(RitualOpera,
Operaticritual)伯克利:《中国大众文化丛书(一)》(Publications of
theChinese Popular Culture Project
1),1989年,第126-154;
《庄子的“礼”和“祭祀”概念》(Tchouang-tseu et lesrites),载A
Caquot和P.Canivet主编《礼教和精神生活》(Ritualisme et vie
intérieure),巴黎:Beauchesne,1989年,第110-120页;
《步虚考》(AStudy of Buxu:Taoist Liturgical Hymn and
Dance),见曹本冶和罗炳良主编《现代道教科仪和音乐研究》(Studies ofTaoist
Ritualsand Music of
Today),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10-120页;
《道教仪式中的净坛和建坛》(Purifier l’autel,tracer leslimites
à traversles rituels tao?stes),见Marcel
Détienne主编Tracés de fondation,
Louvain-Paris,Peeters,1990年,第31-47页;
《灵宝科仪の展开》,山田利明译,载酒井忠夫等编《日本中国の宗教文化の研究》,东京:平河出版社,1991年,第219-232页;
《旧北京的宗教行事结构》,《世界宗教研究》第51期,1993年;
《<痊鹤铭>及其作者》(L’épitaphe pour une grue' etson
auteur),载《饶宗颐教授75岁寿旦纪念文集》(A Festschrift inHonour
ofProfessor Jao Tsung-I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9-421页;
《道教》(Letao?sme),载Jean Delumeau主编《宗教》(Le fait
religieux),巴黎:Fayard出版社,1993年,第531-577页;
《道藏中的民间信仰资料》,载《汉学研究通讯》,1993年。
《中古道教概念中的纯净和外来污染》(Purity and Strangers:Shifting
Boundariesin Medieval Taoism),《通报》(Toung
Pao),1994年;
《北京东岳庙探源》(Note sur l’histoire du Dongyue miaode
Pékin),载桀溺主编Hommage à Kwong Hing foon:Etudes
d’histoireculturelle de la Chine,
巴黎:汉学研究所,1995年,第255-269页;
《欧洲道教研究史》(The History of Taoist Studies in
Europe),见Ming Wilson和John Cayley主编EuropeStudies
China,伦敦,1995年,第467-491页;
《<老子中经>初探》(The Inner World of the Lao-tzuchung
ching),见黄俊杰和E. Zurcher主编《中国文化的时间和空间》(Time and
space inChinese
Culture),莱顿:Brill出版社,1995年,第134-157页;
《道教科仪纲要》(An Outline of Taoist
Ritual),载《科仪论集》(Essais sur le rituel)第3卷,Louvain,
Peeters,1995年,第97-126页;
《庄子》(Zhuang Zi:de Innerlijke
Geschriften)荷兰文译本,阿姆斯特丹:Meulenhoff ,1997年;
《老北京的庙宇和香火》(Structures liturgiques et société
civile àPékin),载《三教文献》1997年第1期,莱顿:CNWS,第9-23页;
《东岳庙建立冥用什物圣会碑考》(Stéle de l’association pourles
diversobjets utilisés dans le monde des
ténèbres),载《三教文献》,1 997年第1期d: "莱顿:CNWS,第33-45页;
《道与吾》,《道家文化研究》,第15期,1998年; 。
《吴澄的大都东岳仁圣碑考》【Stéle du temple du Pic de
l’Est(Dongyue miao)de la Grande Capitale,parWu
Cheng(1249-1333)】,载《三教文献》1998年第2期,莱顿:
CNWS,第85-93页;
《明正统重建北京东岳庙考碑》【Inscription pour lareconstruction
du Templedu Pic de l’Est à Pékin par I’Empereur
Zhengtong(1447)】,刊载于《三教文献》1998年第2期,莱顿:CNWS,第95-102页;
《道教历史》(TheStory of the Way),见Stephen
Little主编《中国道教和艺术》(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56页;
《早期天道的环境保护思想2001年》(“Daoist Ecology: The Inner
Transformation. A Study of the Precepts ofthe
EarlyDaoist
Ecclesia),见N.Girardot等主编《到教育生态》(Daoism and
Ecology),哈佛大学出版社,第79-94页;
《第一洞天:闽东宁德霍童山初考》,载《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道教的清约》,《法国汉学》第八期,中华书局,2002年;
《道藏通考》(三卷本)(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to the
Daozang),与F.Verellen合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施舟人。1934年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施舟人通晓8种语言,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1979年施舟人来到中国专门从事文化研究,历时二十余年不辍。2003年,施舟人在福州大学建立了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他是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中国首家西方人文典籍图书馆“西观藏书楼”创办人。
中文名: 施舟人
外文名: KristoferSchipper
国籍: 瑞典
出生地: 荷兰
出生日期: 1934年
职业: 汉学家
主要成就: 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法国总统授予施舟人荣誉骑士勋位
代表作品: 《道藏通考》
贡献
1979年中法两国恢复友好邦交后,他马上动身来到北京进行研究工作。此后20余年,施舟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从西藏牧民到福建客家人,他都做了深入探访。2001年,在神州大地游历了22年的施舟人终于将脚步停留在福州,受聘于福州大学,成为当地引进的最高层次人才之一。
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2003年施舟人在福州大学建立了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还有一个别致的名字——西观藏书楼。施舟人希望在10年时间里,将西观藏书楼建成10万册重要西方经典收藏量的西方典籍中心。施舟人与妻子向西观藏书楼捐赠了两万多册图书。这两万余册英、法、德、荷兰、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拉丁等西语文化典籍涵盖面异常广阔,多半是施舟人的个人珍藏,其中一些是16世纪以来的珍本图书,更是施舟人的心爱之物。
2004年,施舟人数十载潜心道教文化研究的成果集成皇皇巨著《道藏通考》出版,堪称世界道教研究的最新力作,并荣获在华外国专家最高荣誉——友谊奖。2005年,法国总统授予施舟人荣誉骑士勋位。
名字由来
从施舟人这个中文名字,就能直观地感到施教授对中国文化的痴迷和精通。按他自己的解释,之所以取这样一个“道”味很浓的名字,是因为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老子是“周朝人”,庄子名叫庄周,都有个“周”字,故取其谐音“舟人”,同时包含有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渡人”的意思。
荣誉
名如其人,施舟人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汉学造诣高深,以研究中国道教而驰名于国际汉学界,同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和宗教人类学方面颇有建树,出版过《道体论》(TheDaoistBody)、《道藏通考》(DaoistCanon)、《中国文化基因库》等数十种论著,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施教授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汉学成果,也获得了许多学术荣誉,历任法兰西科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学术要职。
凭借如此雄厚的资历,施舟人本可以安逸地生活在欧洲,毕竟那里的研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优于中国。可是,对于这位已经醉心于汉学的人,中国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散发着无法比拟的魅力。
正是这种源自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始终牵引着施舟人的人生轨迹。施舟人年少时就被中国艺术所吸引。在阿姆斯特丹读完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主的中学后,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远东美术史和宗教人类学,后来受教于法国著名汉学家康德谟(MaxKaltenmark)教授门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1962年,施教授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就来到中国台湾做访问学者,1972年受聘于法国高等研究院,讲授中国宗教史。1976年,他在巴黎创办了欧洲汉学协会,会员规模500多人,在欧洲与各国汉学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之桥。1979年,他来到北京进行研究工作,发起并主持了由法国科技中心(CNRS)、荷兰莱顿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共同参加的大型国际汉学项目《圣城北京》。2001年,施舟人举家迁居中国福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以收藏西方人文典籍为主的西文图书馆“西观藏书楼”。所收藏的一万余册西方各种语言的经典名著以及流失海外的部分中国古珍本,其文献价值不可估量。
如今,施舟人正在主持由国家汉办组织的大型国际汉学合作项目-《五经》的翻译工作。在对中国文化的不懈追求中,施舟人默默地品味着汉学研究的酸甜苦辣,他曾由衷地感叹:“研究汉学是十分艰苦的。做一个中国专家很难,做一个研究汉学的专家更难,做一个研究汉学的外国专家,其难度更是难以想象。而这也是我一生都不能停止的挑战,注定了我一辈子不能休息。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学者,他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要建立文化基因库。
施舟人领衔主持 译《五经》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因为缺乏现代译本,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原典”的《五经》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国家汉办近日宣布,将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共同翻译《五经》,并计划在3年半内首先推出英译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是此次《五经》翻译项目的主持人。记者日前采访了施舟人。
是中国重要文化遗产
记:为什么会选择翻译《五经》?它似乎并不是中国特别通俗的读物。
施:所谓《五经》,是对《诗》、《书》、《礼》、《易》和《春秋》的约定俗成的叫法。《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它们的起源大多早于后来被称作“儒家”的学说。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是中国思想体系形成和帝国体制建立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很多世纪以来国家科举取仕的考试科目。
很多外国人读过中国文学的译本,但他们却不了解《五经》,甚至根本买不到《五经》的译本。
从年代、文化背景来看,《五经》和世界其它重要文明的经典有相似之处,但它最大的特色是与人有关。《圣经》、《古兰经》等都是关于神的作品,而《五经》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代表作,有很多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思想、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遗产之一。
多次呼吁翻译《五经》
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五经》的?
施:上世纪70年代,在国学界与季羡林先生一起被称为“北季南饶”的饶宗颐先生在我执教的法国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恰逢法国政府出资设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当饶宗颐先生看到项目中的中国典籍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时,年过六十的他流泪了:“我们完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源头是《五经》。”
饶宗颐先生的眼泪使我深受震动,看到这种情况,每一个相关的人,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会感到不安,我心中翻译《五经》的愿望也越发强烈。
在后来的30多年中,我多次在各种场合提到翻译《五经》的重要性。2008年,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接受了我的建议,经过多国学者参加的评审会,正式立项《五经》翻译项目。
需要各方面专家参与
记:《五经》翻译有怎样的重要性?
施:我对重新翻译《五经》的评价是:责任很重,难度不小。每一个学者的翻译都有其个人的色彩在内,因此要成立《五经》研究与翻译国际学术委员会,在国内学术界、国际汉学界相关领域聘请杰出学者担任委员会成员。关于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国内外的学者都会参与进来。
记:《五经》翻译对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帮助?
施:《五经》推广到国外一定会对想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有帮助。《五经》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就像洗手,两只手互相揉搓才会干净,但你可能不知道究竟是哪只手帮助另一只手洗干净的。
施舟人(K.M.Schipper),生于1934年,法国人,曾师从康德谟和石泰安先生研究中国道教史,以研究中国道教而驰名于国际汉学界,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基因库的人。现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中国福州大学特聘教授等。(朱静远)
施舟人 扎根中国的中西方文化信使
南方人物周刊
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人”,生于西方却对东方文化谙熟于心。他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并以反哺之情回馈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他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基因库的人,他以一种高远的眼光注视着中华五千年文化瑰宝
从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陈绍鹏手中接过标志着自己成为联想提名奥运火炬手的证书,那一刻施舟人教授的脸上洋溢着明媚的笑容。“我热爱中国!能成为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我感到非常荣幸!”为了跑好明年自己的那400米,年逾七旬的施舟人老先生打算从现在开始练习慢跑。
施舟人1934年出生在瑞典,祖籍荷兰。他有着非同一般的语言天赋,通晓8种语言,汉语造诣尤其高深,被誉为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在道教研究和宗教人类学方面均有建树。
施舟人28岁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法国高等研究院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又历任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施舟人本可以安逸地生活在欧洲,毕竟那里的研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要优于中国。可在施舟人看来,中国这片古老神秘的土地蕴藏着无限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后来成为一种长久的缘分,牵引着他的人生轨迹。
年纪很轻的时候,施舟人就被中国艺术所吸引。刚刚获得博士学位那一年,28岁的施舟人就来到台南做访问学者。首次中国之行,为施舟人提供了一种最直观的对于中国文化的体验。
1979年中法两国恢复友好邦交后,他马上动身来到北京进行研究工作。此后20余年,施舟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从西藏牧民到福建客家人,他都做了深入探访。2001年,在神州大地游历了22年的施舟人终于将脚步停留在福州,受聘于福州大学,成为当地引进的最高层次人才之一。
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文化,2003年施舟人在福州大学建立了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这个中心还有一个别致的名字——西观藏书楼。施舟人希望在10年时间里,将西观藏书楼建成10万册重要西方经典收藏量的西方典籍中心。施舟人与妻子向西观藏书楼捐赠了两万多册图书。这两万余册英、法、德、荷兰、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拉丁等西语文化典籍涵盖面异常广阔,多半是施舟人的个人珍藏,其中一些是16世纪以来的珍本图书,更是施舟人的心爱之物。
2004年,施舟人数十载潜心道教文化研究的成果集成皇皇巨著《道藏通考》出版,堪称世界道教研究的最新力作,并荣获在华外国专家最高荣誉——友谊奖。2005年,法国总统授予施舟人荣誉骑士勋位。
2005年11月23日,施舟人获得了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这对于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最高的认可。
跨越东西方文化 施舟人扎根榕城做中国事
新华网
一个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学者,一个为文化公平而来的国际友人,怀着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感恩之心,把大量西方典籍带到福建。“他向全世界播撒着中华文明的种子,一定会迅速蔓延。”这是著名学者杨健民研究员对施舟人的评价。施先生总是不停地忙碌着,经过几番预约,我们终于把采访时间定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几天前,他刚从国外为藏书楼又征集一批书籍回到福大。
穿过斑驳的阳光,在一座树木映衬的现代建筑物前,记者看到了古意盎然的“西观藏书楼”匾额。走进半掩的门,散发着原木清香的杉木书架、桌椅、柜子赫然呈现在记者眼前。
荷兰汉学家,标准福州通
“标准”的老外施舟人,却操一口原汁原味的普通话。老先生不喜欢人家叫他“老外”,更喜欢把他看作是福州人和福州大学的教授。事实上,在福州早已没人把他当老外。一见面,老先生就来了个“下马威”,提醒记者把“天气热”,念成“天乐”了。
施舟人今年70岁,看上去有点仙风道骨,或许这与他长期以来研究道教文化有关。在法国,施先生是研究道教文化的第四代传人,问及施先生日常生活时,他笑得有如夏阳般灿烂,“我什么都会做,洗衣、买菜、还会熨衣服,早上要给孩子煮麦片。我还会电工,略通木工。大多数时间,是和夫人一起找资料、备课、研究学术。”
在福大开“闽学”
施先生最近又在忙些什么呢?施舟人说:“昨天接待了荷兰来的代表,接下来要去芝加哥大学演讲,介绍中国道教史;马上还要给法、德两国准备一个论文集;下个月去哈佛大学演讲,介绍中国历史民间文学。”
采访中,施先生最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上学期他和夫人袁冰凌联手,在福大新开“闽学研究”课程,让学生们更为深入地了解福建。该课程以袁博士正在着手撰写的《福建历史》为蓝本,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心怀感恩,让汉学回归
半个世纪浸淫于中国文化,怀着对中国古文明的感恩之心,这是施先生建立中国第一个西文图书馆———西观藏书楼的所有原因。
先生与袁冰凌博士建在福大的藏书楼共上下两层,包括4间书库,一个阅览展厅,里面藏有近2万册英、法德、荷兰、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拉丁等西语语种的典籍,包括西方文明、海外汉学和善本3大块,涵盖了美术、社会学等,此外还有大量有关福建、台湾地区的历史文化文献。
西观藏书楼开放的对象不仅仅是福大的学子,更是面向所有兴趣和有志于西方文明和汉学研究的人。施先生用“我们十分欢迎”,表达了他的热忱。
老先生对记者说,他收藏的初衷是认为在西方国家,几乎每个大博物馆都藏有大量的中国古文物以及文学珍品,而中国却没有较完整的外国收藏,没有从西方拿到过等价的东西,“这样很不公平”。
为了这种公平,老先生不仅把自己的收藏都带到了福州,每年他还花上三四个月时间到欧洲各地寻购书籍,并取得荷兰政府的大力支持。施舟人的目标是,争取10年内,西观藏书楼的藏书能达到10万册。老先生的藏书中有很多珍本、孤本和善本,他严肃地说:“这些书是用来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用的,不是将书本束之高阁,更不是用以炫耀书的珍贵。”
藏书楼落户福州,面向世界
在国际汉学界,施舟人不仅是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还是国际上第一个提出建立文化基因库的人。这样一位大名人,他为何惟独钟情福建?
施先生告诉记者,是中国的美术引领他走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当年,由于在荷兰无法系统学习中国美术史,施先生便来到法国学习。1962年,28岁的施舟人获得博士学位,被派驻到台南做访问学者。1979年,中法友好邦交后,他马上来到了北京进行研究工作。四年前,施舟人受聘于福州大学,成为落户福建的最高层次的引进人才之一。藏书地点选择福州不是没有理由的,“福建与欧洲有着数百年的经济文化关系,荷兰人通过华侨认识了福建,对这里的人民有很深的友谊和好感。”施先生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荷兰女王访华,福建一定是她的必经之路。”
他接着解释说:“福州是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我梦中的老地方,三坊七巷等老建筑深深吸引着我,就像老朋友。”为什么不把藏书楼设在北京、上海等地方,而选在福州?施先生认为,“这是对福州一种情结”。
学生:施老师像个中国老先生
去年,袁冰凌博士担任福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03级专业导读课程,随后施舟人接过妻子的教鞭,大刀阔斧地进行教改。
老先生治学认真、严谨,他给学生选择《诗经》做教材,对《诗经》注释著作———《毛诗》观点进行批判,力图还原《诗经》的本来面目。他认为,《诗经》中描述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爱情生活,为什么非要把它们与后妃之德挂钩?施老师喜欢在西观藏书楼为学生授课,他总是笑眯眯,十分休闲地坐在一张古色古香的中国长案后面,案上放着一个圣经架,上面放着厚厚的古籍。
江航同学说:“施老师给我们介绍福州话和闽南语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作用,用古音唱《诗经》里的诗篇,这是在其他课堂上无法接触到的。每当施老师用纯正的汉语读起诗来,特别像是中国古代的老先生。”
黄冰霞同学说:“施老师在我们大一下学期时就要求我们将《诗经》的部分内容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当我们硬着头皮做,施老师也一次一次认真指导后,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发现自己对诗经的理解奇迹般深入了。”
妻子:他知道西方有什么,中国需要什么
从荷兰到中国,再到他们共同倾注心血的事业。谈起丈夫,袁冰凌博士满怀深情,她说:“他受过深厚的西方文化教育熏陶,又研究中国文化长达半个世纪,他知道西方有什么,中国需要什么。”
袁冰凌博士是福州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院长,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1991年,她到莱顿大学当访问学者时与施舟人相识、相知、相恋;2000年两人在巴黎结婚。“回到福建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袁冰凌感慨地说:“2001年9月我和丈夫一起来到福州,4年前恐怕很少人理解我们,当时西观藏书楼是从一间废弃的房屋开始改造的,今天我们已粗具规模,可以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及其他国家的学者,这一切不仅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同时也与福建省和福州大学的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分不开。西观藏书楼能存在证明福建需要它,中国需要他”。去年施先生获得中国颁发的国家友谊奖,法国总统授予的骑士勋位。
学者:他是一位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使者
福建社科联《东南学术》杂志总编辑、研究员、福州大学兼职教授杨健民说,这是一位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学者,他从容地来到中国。面对中国的文化,就像他从容地生长在荷兰,面对西方文化。
但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是他告诉世界,中国的道教文化,有着比西方基督教文化更为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化底蕴中,有着不带火焦气的部分。正是这一部分中,一个“为公平”而来的国际友人带着传播文化的使命,怀着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感恩之心,把大量西方典籍带进中国,架起一座中西文明交流与对话的桥梁;正是在他所构就的这一对话空间里,一个古老中华文明丰韵永存。
杨健民对记者说:“说实在的,我对他并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但我可以说,他向全世界播洒着中华文明的种子,一定会迅速蔓延。作为中国的一名学者,我对他表示敬佩。”
著名汉学家施舟人先生与福州大学缘深情重
新华社福州6月26日电(林文泰 禹志明)6月18日,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法国科学院荣誉厅里,年近九旬的行政院长Leclant先生主持一项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包含著名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Schipper)先生在内的三位院士以法国荣誉骑士勋位(Legion d'Honneur)。
施周人先生,荷兰皇家学院院士、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福大特聘教授,他通晓八种语言,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领域被誉为世界顶级大师。2001年9月,他携同夫人袁冰凌博士,落根福大,成立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并开设"世界文明史"等课程。他集毕生所藏,在福州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座《西观藏书楼》,馆藏西方经典名著、流失在海外的部分中国古珍本一万余册。
1934年出生于瑞典,法国籍的施舟人教授长期以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宗教、哲学进行深入研究,成就卓著。1962年获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1983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驻中国台湾台南)、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曾担任法兰西科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意大利罗马(IsMeo)亚洲学院通讯院士、北京大学文化书院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特聘杰出教授等。目前,施舟人先生担任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暨西观藏书楼主任。
施舟人先生以他对中国宗教文化尤其是道教的研究著称于世,奠定了他作为国际汉学界顶尖级大师的地位。在半个世纪的汉学生涯中,施先生不仅著有《道体论》、《道藏通考》、《中国文化基因库》等十多种著作,近百篇学术论文,多种译著;还培养了三十多位博士、数百名硕士。这些散在世界各地从事中国文化传播与教学的弟子中,有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法国高等研究院教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加拿大McGill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等等。此外,施舟人先生还于1976年在法国巴黎首创了有五百多成员参加的欧洲汉学协会,曾主持欧洲科学基金会最大的研究项目"道藏通考",全欧各重要大学共有三十多位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参加这一项目,前后25年培养了一代汉学新人。
鉴于上述卓越贡献,2004年4月法国总统授予施舟人先生荣誉骑士勋位,授勋仪式于6月18日在巴黎举行。
施舟人先生不仅以其毕生精力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欧美传播弘扬中国文化,并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挚爱,倾一生所有在海外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文典籍与艺术品,并藏有英、法、德、希腊、拉丁等西文书籍一万多册。为了回报他受益良多的中国文化,增进中国人民对世界其它文明的了解,施先生在近两年里将上述收藏全部运到中国,创办了以系统收藏西文文史哲艺术类典籍为宗旨的福州大学西观藏书楼,目标是经过两个五年计划,收藏西文书籍十万种以上,成为国内唯一的西方文献典籍中心。
在荷兰教育部、法国国立科技中心及许多对中国友好的组织与个人的捐助下,西观藏书楼已从海外收集西文书籍近3万册,其中不乏名贵的珍本、善本书。西观藏书楼的网站也在建设中,实现资源共享。如此丰富的西语文献库,为福州大学迅速整合现有的欧美语言文学学科、中国文化学科、社会学科,进而建成中西文明比较研究中心基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结合藏书楼的收藏施舟人教授还为福州大学师生开设了《世界文明史》《世界美术史》等多门课程,并经常组织邀请海内外著名文科学者到福州大学讲学。施先生在福建的所作所为吸引了国内外许多媒体的注意,美、法、荷、英等国大使、总领事和一些知名学者都专程访问过西观藏书楼,表示对这一事业的高度赞赏和支持。
施舟人先生年轻时偶然参观荷兰国立博物馆举办的"远东美术展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从那时起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上。他花费了25年的时间为中国文化基因"测序",把《大明正统道德经》的1483种书籍进行编目、分类、考证,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卷本巨著《道藏通考》,被誉为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界大事。
热爱中国的施舟人先生最终决定提前五年安排了他在法国高等研究院讲座教授的接班人,到中国来生活和工作,如今他偕同夫人袁冰凌博士及活泼可爱的小女儿施心韵,万里赴闽,落户福州大学。(完)
朱维铮谈五经西译与儒经之形成
盛 韵
一听说要谈续修《孔子世家谱》的事儿,朱先生就知道又要得罪人了。从抨击“国学热”,批评于丹“不知道《论语》为何物”,说孔子是“私生子”,到质疑所谓“孔子后裔”的血统问题,这许多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已经得罪了不少“孔教”卫士;他提出的问题,用俗一些的话来说,是要敲掉很多人的饭碗的。然而不论今朝国学怎样热,于丹怎样火,孔子后裔声势怎样壮大,到头来终究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在整个访谈中,朱先生不停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要尊重历史。
最近国家对外汉语办公室在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五经”,据说要翻成八种语言。您参加了研讨会,能不能对此事谈谈看法?
朱维铮:其实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已经翻译过《中国经典》,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加上《论语》、《孟子》,还有《竹书纪年》。理雅各是和中国人王韬合作翻译的。当时王韬因为跟太平天国有联系而被清廷通缉,逃去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就邀请他同译。办法是王韬解释古汉语文本,由理雅各笔译成英文,正好与利玛窦、徐光启以来西书中译的合作模式相反。三年后,理雅各回英国,又邀王韬赴英,继续翻译《周易》。理雅各译本出版后到现在一百多年,不少欧美学者还在使用,可以说影响很大。不过王韬并非经学家,理雅各的汉学修养也可疑,况且“四书五经”文本不可能门门都通。后来也有学者不满他们的译本,要重译,但限于个别经典,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殿爵翻译的《论语》、《孟子》,学界评价很高。然而“五经”整体重译仍未见尝试。
此次重译的组织者是法国汉学家施舟人和袁冰凌两位教授,国家汉办予以全力支持。他们的计划是翻译“十三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还有就是宋以后加进去的《论语》、《尔雅》、《孝经》、《孟子》。这些经典到清中叶都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官方文本,清末民初以来专经的文本研究又有进展,更突显重译的必要。这次国家汉办邀请了二十多位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和国内学者,共同研究重译方案,计划是先把“十三经”译成英文,再参照英文本和中文本翻译成另外八种主要语言。但具体分工我不太清楚。较诸以往理雅各、王韬的合作模式,现在的好处是,参与其事的汉学家均为文史专家,古汉语修养都很好,需要找人帮助也很方便。
您的研究常常提醒我们,经典形成的过程十分复杂,翻译过程中肯定应该考虑到。
朱维铮:所谓的“经”都是汉代的产物,至于每种文本的源和流追溯起来便很难讲。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孔子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论语〉结集脞说》,依据古近种种矛盾的历史陈述,以为今本《论语》,并不是孔子死后几代弟子编辑的本子,甚至不是汉代的三种抄本的某一种,而是孔子死后六百年的东汉末年的郑玄糅合今古文本的改订本。这个文本在魏晋后渐居主流,汉代三种或四种文本也就失传。而且版本问题又牵涉到了文字、句读的问题,举两个有名的例子。
《论语》现在的通行本里面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几句话,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却引《鲁论》,说“易”读为“亦”,也就是孔子办学的鲁国,儒者相传的《论语》文本,这三语的句读应该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处异文就牵涉到了孔子有没有学过《易经》的大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治理民众,可以要他们顺从,但是不可以让他们开启智慧。这是中外前近代权力者通行的愚民政策,基督教《圣经》将信众比作羊群,将教士比作牧羊人,与依据孔子此语将治民称作“牧民”,毫无二致。但是自命孔教的马丁·路德的康有为,却说前人都读错了,这里“子曰”,应该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孔子鼓吹凡事都要征求民意,民众同意了,就可以去做,民众不同意,领袖要说服他们懂得必须这样做的道理,所谓开民智。所以,孔子其实是民主政治的教主。可惜,康有为用如此怪异手法替孔子辩护,连梁启超也不信。
类似例子在经学史上相当多。不仅《论语》存在材料可信度问题,别的儒家经典也都存在结集过程、篇章文字、原典涵义问题,有的更复杂。每种传世文献都有一套文本和诠释的变异史,要厘清很困难。比如所谓“十三经”,自汉至清不少君主都宣称他们所尊的就是孔子的真传本,却只能引发学者的更多质疑,目前争论仍在继续,再过两千年也未必息响。我赞成将它们重译,介绍给全球非汉语世界的读者,但以为要选择目前中外学界一般认可的文本,主要是清中叶以来音训考辨均属上乘的文本,但不能反历史地强调这就是孔孟时代的原典。
翻译过程中也应该参考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吧?
朱维铮:当然应该参考。问题是汉代经书的原型就是当时出现的简牍帛书,多为古文,而用秦汉文字改革之后的“今文”读写,意味着经过筛选才变成传世抄本。如今的出土文献,也许是传世抄本的原型,也许本来是筛选后的弃物。假如将被改编或被否定的某种遗简当作某部经传的原型,可能有孤证不足为据之嫌。比如郭店楚简里有没有思孟学派作品,就值得存疑。郭店楚墓唯一一件与墓主系年相关的器物,铭刻的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学者仍有歧见。如果李零先生所释“东宫之杯”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墓主可能并非楚太子师。这位身份不明的墓主,只觉得这是件宝贝而拿来陪葬。据此推定墓葬年代就难以置信。再说用碳十四测算年代的误差是两百年,而孔孟之间不过一百年,怎么能断定那些残简就是孔孟之间的文本呢?郭店简出土情况还比较清楚,可以作为了解思孟学说的某种参考。然而有些炒得很热的战国遗简,尚不知出土时间地点,也不明流失过程,有学者声称其中内容当属《诗》、《书》原型,恐怕问题就更多了。
我相信“二重证据法”,更相信经过严格科学程序检验的考古文物证据。正因为相信科学,我对于单凭今存经传文字矛盾就大加臆断的“疑古”,以及过度强调来历不明的所谓出土文献价值的“信古”,才都会存疑。出土文献很重要,但是得承认现在的科学手段还没有精确到令人难以置疑的地步。
汪德迈先生在“五经”翻译的会议上说在现代文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多语种翻译中国的“五经”更紧急的事情,言下之意,似乎中国古文明现在成了救世良药。
朱维铮:汪德迈先生是这次参加会议年龄最长的学者,他的弟子程艾蓝教授是“文革”以后第一个来华跟我研习中国经学史的外国高级进修生。他们对中华文明史都深有造诣。
现在的五经翻译,发起者、策划者和参与者,来自中外不同领域,共同目标是用多种语言重译中国传统的“十三经”。因为是翻译,就决定了域外阅读对象是对中国经史感兴趣的读者而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我以为,翻译这些传统经典,可以让域外世界不懂汉语的学者和非学者,能够了解这几百年来中国人所读的经典的面貌,了解近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包括说话、交往的特点的教化由来,从而了解历史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典基础,当然也会注意到这些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形及其历史效应。这是件好事,我很支持,以为有助于增进现代人在全球化氛围中的互相理解。
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一直说历史上有真孔子和假孔子,一直说研究后世的假孔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真孔子。直到“文革”中我堕入“牛”群,“无聊才读书”,重读十三经二十五史,始渐悟周师所述中国经学史,否定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可谓至理名言。还在抗战中期,傅斯年、顾颉刚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宣称“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抹煞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的复合共同体。当时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说法,便彰显了学者敢于坚持历史事实的勇气。我们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历史,现在的汉族有复杂的形成过程。北朝隋唐的皇族都是胡汉混血儿;南朝的权贵也无不是中夏与南蛮结合的产物。从晚唐至清末近千年,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后来都到哪儿去了?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生活以后都渐渐融入汉族了。蒋介石不承认中国有多民族的现状,但不承认是不行的。中国各民族的语言、风尚、传统、信仰都不一样,只有彼此互相尊重,才能增进中华民族的内在向心力。所以我们讲历史,应该反对华夏中心论,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任何非历史的民族特殊论。
最近续修《孔子世家谱》的新闻您看了吗?据说现在孔子后裔的数目已经达到了两百万……
朱维铮:我是研究经学史的,很重视家谱族谱之类史料。以前我常说,如果血亲联系无法证明,那么任何谱系就都难免有伪造的嫌疑。史书上明明白白记载着孔子的嫡系,到他的二十世孙孔融被曹操灭门,就中断了。孔子说过“夷狄之有君也,不如诸夏之无也”。建立金朝的女真权贵痛恨此说,攻打北宋时到曲阜就放火烧了三孔。当时跟随宋高宗南逃的人群里有孔子的族裔,就是迁居浙江衢州的“南孔”。稍后金朝海陵王突然想到要尊孔,就在民间拉出一个人封作衍圣公,于是“北孔”就续起族谱了。这样的历史在蒙元又重演。有历史记载可证。
历史上暴发户认名人当祖宗,屡见不鲜。唐代的三教问题,就是从鲜卑与汉人混血的李唐皇室,认孔子之师老子即李耳当祖宗开始的。认了老子当祖宗以后就有儒教、道教谁先谁后的问题。以后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当皇帝后要掩饰乞丐出身,也想学唐高祖认个名人当祖宗,于是想到了朱熹,可惜当时学者没有现在“体制内学者”聪明,绕来绕去,如吴晗所说,最后就是有一代怎么也连不上。朱元璋火了,便学刘邦干脆自称老子就是淮右布衣出身。最佳近例是蒋介石,这个流氓出身的独裁者,连生父是谁都闹不清,得志后修家谱,却宣称他的祖宗是“周公之胤”。
《左传》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意思是认祖归宗,前提是弄清血统,否则祖先神灵不会享用祭礼,下属民众也拒绝承认贵族所谓的本族祖先。所以要续家谱是可以的,但只应续到自己记得的祖宗为止,不要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来哭,乱烧香可是要引来野鬼的。孔子死后,他的子孙历尽劫难,以致他的八世孙要抱着家族遗物投奔造反派领袖陈胜。不幸陈胜称王,仅半年就被反秦的异己攻杀,孔鲋也跟着牺牲。直到汉初其子孙才再度现身。假如不是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拜孔鲋的侄曾孙孔安国做老师,做了一篇《孔子世家》,后人能够痛说孔子家史吗?现在要重新接续历史记忆固然是好事,但接续的结果多半都是想象吧。
我知道说这话有得罪自称孔子后裔的两百万人的危险。今年已有五十六个“孔子后代”联名写信给我,斥我诬蔑孔子及其子孙,宣称如我不公开认罪,就将诉诸法庭。还有北京某研究院的孔研究员,致函给复旦校领导,要求处分我,说我污蔑孔子。我还是三十年前那句话:欢迎质疑,请提供历史证据。
五经翻译国际研讨会采访有感
屠芫芫
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传播,结束《五经》现代译本缺失的现状,国家汉办启动了《五经》国际研究与翻译项目。7月,《五经》国际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香山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名知名汉学家聚集一堂。我们编辑部采访的这些学者,其中包括: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裴宜理,哈佛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伊维德……处长特别信任地将采访裴宜理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时的我还只是一个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学生。望着采访名单上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这些有分量的字眼,我的手心开始微微冒汗。
没有太多的时间踌躇,上网,查资料,去图书馆搜集她的著作,开始阅读,甚至在回家拥挤的地铁上也没有闲着:《上海罢工》、《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一个陌生的中国一点点随着她的文字映入我的脑海。如果不是此次采访,也许我永远也不会阅读到这些书籍。尽管它们对于我来说有些艰涩难懂,但是对于这第一次采访怎么用功都不为过。
列出采访提纲,为了让提问更加精准,提纲在处长的指导下修改了一遍又一遍,一次次推翻、更新。直到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拨通了她的手机,当我还在猜测着裴宜理会用怎样的英语回答我的问题,没有想到的是,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太好了,我们明天见,国际俱乐部大饭店,到时我会在大厅等你。”
惊讶!她的汉语如此之好!
紧张!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知名的汉学家我该如何提问?又该如何对话呢?
两杯绿茶飘着淡淡的香气,我们如约见面了。
眼前的裴宜理是一位有着褐色头发,穿着浅白色中式印花唐装的学者。随着一问一答,我被她的故事吸引,她的成长轨迹逐渐清晰起来:1931年裴宜理的父母作为传教士来到上海,他们相识相爱,1948年裴宜理在上海出生;60年代末她考入美国威廉史密斯大学攻读政治学,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文化大革命,为了弄明白她出生的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裴宜理开始学习汉语……
“1979年我在南京,那时候的人们都穿着清一色的蓝制服,清晨学校的大喇叭里会播放革命歌曲!你那时候估计还没有出生吧!”裴宜理打趣地说。
交谈继续着,氛围轻松自然,裴宜理用缓缓的语调和我诉说着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此刻的我完全沉浸在她的故事中,忘却了所有的紧张。眼前的裴宜理平和又亲切,像是老师更像朋友和长辈。
作为一个外国人,她竟然能用流利的汉语和我对话,作为一个外国人,她竟能不远万里重返中国,深入工厂和乡村调查研究,作为一个外国人,她竟能如此热爱汉语,热爱中国文化。她的内心里深藏着对中国怎样炽热的情感?采访中,我的脑海里不停闪过一个个疑问,裴宜理一一作答。这一聊一直持续了近2个小时。
走出国际大饭店俱乐部,7月的北京明明酷热难当,我却仿佛置身茂密的森林,深吸着清润的空气。能聆听广袤思想真是人生幸事!裴宜理不仅谈到她和中国的缘分,促成她研究中国问题的原因,还把我带入了那个我出生前还不太了解的文革后的中国社会,从一开始的闭塞到后来逐渐开放……她呼吁应该在国外大学里开设和中国政治思想以及东方哲学相关的课程,要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不仅西方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哲学,东方也有自己的传统……
于是,2周后就有了刊登在《孔子学院》2009年第四期杂志上的那篇专访——《半个故乡在中国——专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
以后的一年多时间,我采访到了哈佛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伊维德,奥运会吉祥物设计师韩美林,著名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前驻法国大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孔子学院》使我很快地完成了角色转换,从一名学生成为编辑。《孔子学院》更是一个特殊而广阔的文化交流平台,在这里,中西文化自由地交流碰撞,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汇聚交锋。这里的每个故事都是新奇,每个人物都让人尊敬,他们有着不同的职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着中国。
《孔子学院》2009年3月创刊,开始只有中英文版,但刚一问世就受到各国朋友的热烈欢迎,认为内容都是他们非常希望了解的,而表现形式又特别符合他们的欣赏习惯。为了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更有针对性地介绍汉语和中国文化,从2010
年7 月起,中西、中法、中俄、中阿、中日、中泰、中韩等另外7个中外文对照版的《孔子学院》院刊相继创刊,它们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又一新窗口。
此刻,远处德胜门城楼前的樱花开得正艳,柳枝由嫩绿变成翠绿,一切都生机勃勃,蓄势待发……时光疏忽,窗前的景致悄无声息地变换着,轮回着。而办公桌前堆积如小山一样的修改文稿似乎在告诉着我:2011年新一期的《孔子学院》又快要和全球朋友们见面了……
法国汉学家:中国是不容易被征服的国家
(法)谢和耐/钱林森 中华读书报
提要:西方人认为世界历史是从他们的历史那开始,并从他们自身来判断别的事物。传教士来中国前自信十足,自认来拯救中国人出地狱。但到中国,他们发现中国不容易被征服,为了适应中国,传教士们不得不去掌握中文及四书五经。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谢和耐
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谢和耐(JacquesGernet)先生于1921年12月诞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青少年时代在阿尔及尔接受正规教育。1942年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投笔从戎,1945年回巴黎,入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学习汉语,1948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EPHE。1949—1950年间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成员,1951年进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在1955—1976年间,曾先后任高等实验学院的研究导师、巴黎大学文学院教授、巴黎七大教授之一,1975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1976年出任享有盛名的汉学刊物《通报》法方主编,1979年以唯一一名汉学家身份选入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教授专事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著述等身,是法国汉学界的头面人物。
1982年值此利马窦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先生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曾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在我国也相继有两种中文译本为读者所知。1999年2月23日和2001年6月11日,我曾两次在巴黎汉学研究所拜访过谢和耐先生,就他这部著作写作背景、成书后的反响,特别是他在这部大作中描述的东西方两种不同形态的文明首次相遇、对话时所碰到的困难,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及由此而提供给我们的教训和启迪,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据我们的交谈整理了若干问题寄给他,谢和耐先生又据我的提问,先后两次逐一笔答,下面的文字就是依据我们两次交谈和谢和耐教授的笔答整理而成的,谢和耐先生两次法文笔答由马利红女士译成中文,在此一并感谢。
钱林森(简称钱):您的大著《中国与基督教》(ChineetChristianisme)从1982年在巴黎出版以来,受到了西方和东方读者的广泛欢迎,引起学界的重视。据我所知,法国老资格的比较文学大家艾田朴先生(R.Etiemble)就把您这部著作视为研究中西文化关系的权威性著作,给予了极高评价,在其两卷集的代表作《中国之欧洲》(L'Europechinoise;1988-1989;Gallimard)多次加以引述。中国先后有两种译本问世,一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译本,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的译本,在中国读书界广泛流传。我首先想问的是,您花了多长时间酝酿、撰写这部著作?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这部书问世后在学术界和宗教界引起怎样的反响,这也是中国广大读者和学者感兴趣的问题。
谢和耐(简称谢):大约从1970年起,我开始对基督教与中国这个主题发生兴趣,那时我正应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洛代尔之邀,准备撰写一部关于中国通史的书——《中国世界》(这本书有一个很好的译本,开始面向中国读者,由黄建华先生和黄迅余女士翻译,《中国社会文化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它也促使我尝试去更好地了解明朝。我的第一篇文章事实上开始写于1972年(《关于17和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接触》),(1972年中文翻译登刊在《国际汉学》,由商务印书馆1995年出版),紧接着1973年写了另一篇文章由《将近1600年前后利马窦的皈依政策和中国精神生活的演变》,(1973中译本刊登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和1976年写了《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的基督教主义和中国哲学》,《尚蒂伊国际汉学讨论会文集》。
当我写这本书时,我的想法是,中国人对传教士行为和传授的反应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由于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问题在西方并没有被研究过。西方人仍旧认为世界的历史打他们的历史那儿开始,并且从他们自身来判断别的事物。认为现代西方人是过去所有时代,对所有文化具有价值典范的想法,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完全消失,西方原则优越性的偏见也没有完全消失。因此,仔细研究17世纪中国人对传教士言行的反应是把这些观念再次提出来加以审视的途径,这也是表明,除非人类有所意识,他们是受其时代、阶层,尤其是在一个不同于欧洲和中国的氛围中,以及所有他们继承的历史传统所制约的。社会组织、政治体系、思想、行为,所有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宗教传统,所有这一切在既定的时代和文化中形成相对凝聚的整体。所有这些方面都得予以考虑。相反,如果人们认为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那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在一段历史中人们是被设想为一个叙述。这个历史可能非常艰深、博学,有时甚至具有教育性或娱乐性,但是在历史和文明过程中它提不出异于其他的根本的思想问题。)
我并不很关心我的书出版后的反响。我相信应该总体反应是好的(除了耶稣会士杂志《学习》中一篇一位耶稣会士写的恶意的文章。文章影射我不懂中文,因此我不能阅读我曾译过的文章)。内容上唯一的批评是基于最后三页,关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一直使我挂虑。我认为人们不能借口剔除所有的思想和哲学,这一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是可以从一种语言译至另一种语言的)。
钱:您的这部书有一个副标题:第一次冲撞(Lapremièreconfrontation)。据此,中国的第一本译书名干脆改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表明本书的主旨在于描述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首次相遇时所存在的差异,所发生的矛盾与碰撞,正像您的导言和再版前言里所强调过的那样。这是您的书有别于同代人和前辈同类作品的地方。我想请您就这部“充满深刻智慧的著作”,就其独特性:构思、选材、论述及主旨诸方面的独特角度,发表您的看法。
谢:您问及我这本书的特色。我上面刚刚说过,我的观点是社会组织、政治体系、思想、行为、传统,尤其是作为这一整体的主要要素的宗教形式,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体,所有这些方面应该予以考虑。相反,如果人们认为面对的只是可互相替代的个体,如果人们假设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变的,而大部分情况则首先他不是赖以生存的世界之产物,(即使他个人是独特的),那么都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
至于工作方法,在我看来应该以文献为基础。在撰写我的著作时,我最重视的就是中国和西方同一时代的文本比照,中西文本、法文和意大利文文本的对照。可以说,这本书就是中西文献的杂集。文献的对照和分析使得我给自己提出问题,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组成这部书的材料。若从先验的观点出发,注定只能讲些平庸的见解,或者从一开始就走上歧途。正如在我看来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王船山所言:“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
钱:就严格意义上的中外文化交流通史而言,在促进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真正意义上交融中,利马窦(MatteoRicci)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近代罗马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真正奠基人,保罗教皇在1982年庆祝利马窦到达中国400周年纪念会上称利氏为“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真正桥梁”。他的重要尝试和贡献在于寻求地球两端独立发展的两个伟大文明首次对话的共同话语,即致力于“合儒”、“补儒”的方针大略,力图将两种不同文化进行“调和”和“会通”,从而构成了中外关系史上永恒而迷人的话题。您作为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对此有何看法?两种不同形态的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能够“会通”和“调和”吗?
谢:似乎可以,实质上不可能,利马窦曾经尝试过,有其历史功绩,但失败了。
要想理解传教士的行为和他们诠释中国人的反应的方式,就必须按照他们的思想来思考:罚入地狱或灵魂永久得救的思想,在人类生活的所有细节,在皈依和圣迹中都有上帝永恒的干预的思想,在头脑中有信仰撒旦的干预和着魔的思想,相信洗礼、圣水、十字架和圣象的效力,善与恶的根本对立。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是深信自己掌握着由上帝亲自默启的真理的。他们深信基督教应该在世界各地获得胜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胜利几乎是完全的,既然他们进驻到美洲、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他们认为正如他们在别的地方所做的一样,他们是来拯救中国人于永恒的地狱,把他们从魔鬼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借助上帝的帮助使人们皈依。他们随时准备必要时去为了证明基督教的真理而献身。中国人的所言所行应该与这些先存的心理模式相协调。
中国不是一个易被征服的国家。最初的两个传教士,罗明和利马窦因此从1583年开始不得不同时被人们当作外国修道士而万分小心地推进。中国人在他们身上首先看到的是一种佛教和尚的新面目。但是中国也不同于被征服的那些国家和日本,因为她是一个由国家高级官员统治的疆域广阔的国家。在中国文化与政治权利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特点也使其有别于印度,葡萄牙人通过武力定居在西海岸的几个城市里)。然而,基督徒他们自身是修道士的同时也是一些学识渊博,颇有修养的人。因为他们想使得皇帝改变信仰——他们相信,这样将会改变整个中国的信仰——最初也是最知名的的基督徒,利马窦认为首先应该赢得统治阶层和文人们的同情。他著名的绥靖政策就是受到这一计划的启发。他在进入广东时的艰难情况逐步令其认识到他以修道士自居的错误以及必须以讲学的西士身份出现的优势,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为了能够深受大学士和高官们的欢迎,为了能够和他们去讨论,他努力去掌握中文知识以及四书五经,并且从1595年起,在他到达肇庆12年后,他改换了服饰,穿着像大学士。这样他就开创了一种几乎为其所有同胞和后继者所使用的方法。他想不仅通过他对古典文学的了解而且通过他惊人的记忆力,他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他的伦理著作,他带来的新奇的玩意儿震撼和感动中国的精英们。从他旅居肇庆开始,他在居住的寺庙中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或称《万国舆图》引起了极大的好奇。从1590-1591年起,他开始教授欧洲数学。
在阅读古典文学的时候,利马窦相信《尚书》和《大雅》中的上帝就是《圣经》中的纯洁的神灵,造物主上帝;他相信中国在基督之前的上古时代经历过一次最初的基督的默启。利马窦和他的一些后继者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所关注的是将基督教的意义赋予古典文学作品和孔子的言录来改造加工这些神灵。但是,这个方法从中国文人方面而言可能与宋朝(基督徒们视之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时代)评论权威们发生冲突;而另一方面,也遇到一些基督教徒和其他嫉妒基督教的宗教阶级(奥古斯丁教派,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修士,在17世纪已自菲律宾进入福建)的强烈反对。这些反对利马窦策略的人拒绝去适应中国传统或者怀疑其效力。他们认为他不用这么谨慎,而应该严格地传授教义。这一敌意自然也延及利马窦及其策略的与会者为赢得中国精英们的赏识所做的事情中(科学和技术的教授,伦理著作或宇宙志)。尤其使那些反对利马窦所创的如此谨慎的方法论著的人震惊的是,构成基督教精髓本身的东西没有被传授,也即基督即上帝的化身,基督教在中国可能会以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简单变种出现。然而,对于中国人耶稣被钉于十字架上是一种侮辱性的酷刑,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图像令他们不寒而栗。利马窦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那场应该激起欧洲高涨情绪的宗教仪式的著名论战正式涉及的只是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上帝和《圣经》中的相似之处以及对已皈依的中国人仍旧继续崇拜孔子的许可。事实上,这触及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想知道是否基督教确实被传授给了中国人。
但是,在谨慎派和坚定派之间,归根究底,只是策略的不同而已。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目的就是改变中国。尽管今天我们很自然会说到这是传教士头脑中的“两个文明的对话”,但这并不是对话的问题,而是知道要使得中国信奉宗教怎样去行事:给中文文本一个新的意义,渗透入文人的思想中去,暂时允许对祖先、孔子、与其所联系的大学士的崇拜,被人当作文人或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其是什么,也即想修道士来中国宣扬福音书?利马窦的尝试在于混淆基督教和中国人的概念的范围里可能允许一些“宗教信仰的改变”,因为改宗一词所隐瞒的事实从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借助古典文学,并想说服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文人阶层,利马窦与他的信徒们走进了一个死胡同。此外,从中国人的观点出发,一方面不能接受其以文人自居的方法混合;另一方面也接受不了耽于那些驱魔法中。
我认为,不应该把这“两个文明冲撞”的结果看得太重要。基督徒的确使得一些西方传统得以传播(尤其是技术和科学),但是应该睁大眼睛,分析一下这些东西带来的后果《几何原本》(《欧几里得数学基础知识》的前六个章节)就是通过利马窦的讲解,由徐光启翻译的。这本书非常不适应中国传统,中国人又以其自己的方法重新诠释过。该书有一些影响,但不是以其最初的形式。从普遍的方法看,许多中国人欣赏那些以“求问和探索”为主的他们称之为西方方法论的东西(诸如质测),要看的不是理论的方面,而是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方面,在那个时代经过东北方面的威胁和16世纪的佛教偏移之后,人们想回到一些具体的事物上(诸如史学)。当人们研究利马窦主要著作《天主实义》时,会看到他在书中铺呈了一系列的抽象论据。这些论据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被中国人认为是人为的(中国人喜欢的是利马窦那有着与中国道义人为的相合之处的道义)。利马窦的论据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理论上的11至16世纪的中世纪经院派论据。这一极其贫乏的经院派理论已经被那个时代正在发展从伽利略到牛顿的古典主义理论的学者所摒弃。这里我并不想花时间谈论这些细节。归根结底,之所以基督徒带来的革新在中国的影响不可能十分深远,是因为思维模式、历史传统、知识基础是大不相同的。大体上,我认为尤其存在着对两根肋骨的鄙夷和错误解释——对于宗教、天、上帝和道义尤为如此。而就传教士本身,为了促成他们所构想的“转变”也有着一些故意的歪曲。
图:身着中国翰林院大学士服的利玛窦(资料图)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