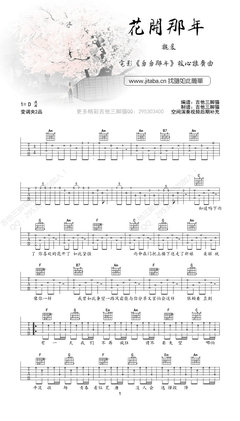那时花开
<?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我家前院的玉兰开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前,我十六岁,外婆去世,我跟着外公抱回这棵小树苗,种在前院。每年春天,外公都带我们在树下数花朵——寄托思念——从最初的五朵到现在的上千朵——二十年的容颜就是这样改变。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穿上了西装,第一次参加追悼会,第一次见到了死亡(外婆是我今生见到的第一个去世的人),第一次被当作大人与六百多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当时舅舅在美国,我站在他的位置送别外婆,第一次觉得自己应该挺起胸膛像个男人了。
那年我还谈了第一次大型恋爱。
二十年后,我还住在这里——外公也已去世,妈妈远在海那边,我自己——离异无子女,热爱音乐、电影和文学——二十年前的征婚启事许多这样写——让人想起那些个纯净的空气里都有甜味的日子。
一个人,也没了数花朵的兴致。
四个现代化好像已经实现了——都是哪四个来着?
我那时的梦想:一辆崭新的,28凤凰自行车;一柄巨大的,只属于我的酱肘子;一卷长发的,懂我的好姑娘——也早已实现了。
我大概是这个城市里为数不多的三十几岁还住在户口本上出生所在地址的人。
清华园,从产房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中间觉得自己长大时曾急切地出逃过,住过不少陌生的房间,最害怕黄昏时醒来——习惯性地望向窗外——窗外没有熟悉的玉兰,再远处没有那根平静的烟囱,空气里没有比我自己的呼吸还熟稔的气味——忽然就觉得什么都没了,彼时会呆坐在床上,百转千迴,天色千万不要暗下来呀,我想家。
今年学校催我搬走,这几栋房子按政策是不卖的,要腾出来给从国外请来的客座教授住(当年外公外婆就是双双在德国得了博士之后毅然带着我妈回国报效的),我想了很久,怎样才能把这棵已经
前天舅舅回国,我对他说要搬家的事,他难过了很久——舅舅和妈妈都在这里长大,虽然现在都在异国,但他们永远会对人说“家在清华”——舅舅说,这里没有了,全家就散了,没有了这个家,故乡的意义就没了。
过两天妈妈也回国,我们想好好求求学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想保住这个家,这里有我们的童年,这里是我们的母校,这里有我们所有的青春年华——
这里有我们的玉兰花。

晓松 天黑了,明早去拍玉兰的照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