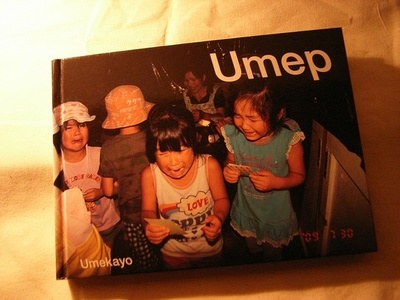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汉文的佛经,绝大部分是唐朝和唐以前翻译的,翻译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今天的陕西一带。古都西安是唐朝的首都,那时西安的官话(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也不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陕西话,而是客家话。
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有大量的梵语是音译而不是意译过来的,也就是说是直接用汉字标注读音的,就好像我们今天直接用汉字“巧克力”来标示chocolate一样。这也是导致今天的人们看不懂佛经的一个原因,很多人据此认为佛教有故弄玄虚的嫌疑,这确实冤枉了佛教。
今天我们在汉文佛经里看到的所有咒语,都是用音译方式标注读音的,而后再对音译的部分加以解释。曾经有网友问过我关于佛教经卷翻译的问题,这里捎带介绍一下。
佛教经典的翻译十分考究,其方法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次由懂汉文的印度学者翻译,然后再由精通汉文而又懂梵文的中国学者译成极好的文言,这个第二次的译稿又重新译成梵文,来与原文对照,加以许多次修正之后,再译成中文,直到最后的译稿文从字顺,且与原文完全吻合而后已。
大部分传至中国的佛教经典都是在南北朝时期和唐朝完成的,唐朝的玄奘法师更是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原则。所谓“五不翻”,指有五种情况需要译音而不能译意。即: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无此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

回到前面的话题。用今天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来念这些唐朝翻译的佛经,音译的部分已经离当时的发音相去甚远。当时汉字标注的读音和梵语十分接近。而今天我们若想听到最接近梵语的诵经读音,只有在藏地和客家人聚集的地区才能听到。
我的上师嘎玛仁波切有很多客家弟子,他发现这些弟子在念佛经,尤其咒语的时候,发音和梵音几乎一样。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语言现象。后来我就开始注意这个语言现象,并且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心经》里有这样一段咒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用今天的普通话来念,就是:jie-di,jie-di,bo-luo-jie-di,bo-luo-seng-jie-di,pu-ti-suo-po-he。而如果用客家话来念,就是ga-di,ga-di,po-ro-ga-di,po-ro-seng-ga-di,pu-ti-sa-po-he。这个读音非常接近梵语,而且与我们用藏文念的读音几乎一样。
还有一个我们常见的英语单词china,很多语言学家认为,china是与秦朝有密切关联的,秦的读音在当时是chin。语言学家认为china就是“秦人”。我个人认为,china这个读音的意思可能要早至上古夏朝时期。“夏”在上古时期的读音是rja(音近嘉),“夏人”就是中国人,用上古时期的读音来念,近于“rjana”。这个音和现在的china就非常接近了。上面我讲到过,客家话把“人”读作na。这个读音和夏时期的读音是一脉相承的,有历史渊源的。
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一个更为有意思的史实,今天的藏族和汉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夏王朝时期是同一个民族。西藏吐蕃王朝的前身是古象雄苏毗女国,根据对藏汉古籍的对比研究发现,古象雄苏毗女国是公元前十世纪以前至前六世纪之间,逐渐从青海省汉藏交界处迁徙到西藏。古象雄是古轩辕国、古支那国、古昆仑;苏毗女国是西王母国。是我国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的遗族和母国。
唐朝时的吐蕃是夏的部族迁徙到今天的藏地的。多识仁波切在他的研究中发现,通过今天依然存在的藏族古姓“嘉(rgya)”,分析大量藏文古籍文献,发现青海玉树村嘉二十五族(rgyasde nyer inga)、外象雄西藏丁青三十九族和川西北嘉绒(rgyalmo-rong),均是象雄和苏毗女国的“嘉(rgya)部落”,是古代夏王朝的同族。也就是说蕃族(今藏族)的祖先和汉族是一样的。
这些历史研究,也得到了医学界的有力证实。医学界曾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做过血液标本研究,在血细胞抗原(HLA)研究中发现,藏民族属于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
话题说得稍微远了一些,不过也可以从中看到,佛教、语言、文化、历史、民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上述仅是个人浅见,本人不是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只是平素喜欢研究这些文化现象,闲聊而已。
话题回到本文最初,南无阿弥陀佛,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顶礼、归命无量光觉,无量寿觉。归命者,众生一心仰赖阿弥陀佛,即众生之信心也。无量寿觉或无量光觉者,佛力助一切众生成就也。众生的信心与阿弥陀佛助众生成就都在这六个字内。因此这六个字是净土法门的至宝。
善导观经疏一曰:“言南无者即是归命,言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斯义故,必得往生。”观无量寿经曰:“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我平素也是常常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也希望大家多念!阿弥陀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