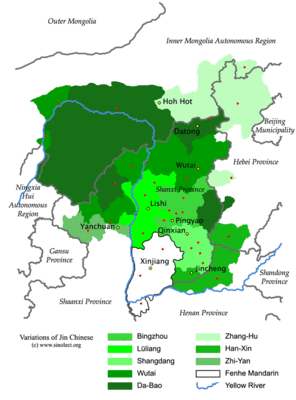![[转载]温玉成将军女儿文章:我想替父亲表达的歉疚](http://img.413yy.cn/images/31101031/31105541t01e09a1676227a0ff5.jpg)
原文地址:温玉成将军女儿文章:我想替父亲表达的歉疚作者:老兵有情
说心里话这些伤心往事在各自的心里一定留下了巴痕,谁也不去提起,相互的不去触碰,都因为我们是亲人,可在我的心里那是一份不说出来就不能了结的心结。
我有一个革命的大家庭,我上一辈的亲人们都是那革命队伍里的战友和同志。他们在战争年代里,是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在和平年代里又结成了错综复杂的儿女亲家。
可在那苛政猛于虎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我亲历了亲人不敢相认,亲情不能维系,眼泪挂在脸上,无情似刀般的割裂血脉。我也亲历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什么是危难时的出手救援,那不是今天所说的用胆量来可以形容,在那黑不见光的日子里,那是赌上了所有的身家性命和前途的出手相救!
一九六八年的冬天,我家从广州搬到了北京,我的父亲如同草鸡般的落在了凤凰枝头。我家的大门口第一回有了许多的战士把守,在门口警卫班的桌子上有一本厚厚的“来客登记簿”。所有来我家的人都要在那本本上写的清清楚楚,开始我还不明白,八、九岁的我也喜欢在那本上涂鸦,可被战士们给严厉的呵斥了。我看见我的外婆来看我们孩子,也要清楚的写明:“关系”、“姓名”、“年龄”、“地址”。再后来,我的外婆不能进我家的门了!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告诉她不要来了,那门口的登记簿是要上缴的,有人在监视着来家的都是些什么人。妈说:那是我的母亲啊!爸说:因为她是右派,会对我们有影响的。
我的外婆也是位老新四军战士,早年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生活的困难。是因为她的哥哥吴仲超为了理想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她是受哥哥的影响参加了革命。为营救陷入苏州监狱的共产党人,她舍得银子还冒着风险的去担保连坐,她也加入了上海的地下党。一九四五年的年初,她的地下党身份暴露了,连夜她带上了自己的四个孩子投奔去了解放区。当时我的妈妈十五岁,大舅十二岁,姨妈十一岁,他们最小的弟弟只有九岁。当然我妈妈他们的革命经历就都是从一九四五年开始算参加革命了,是我的外婆把孩子们都带入了革命的大家庭。
我的父亲也是新四军,战争年代他和吴仲超、王必成、章蕴都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都是队伍里的同志。
1943年吴仲超(中)王必成(右)江渭清合影
解放了,我的父亲在抗美援朝归国后上了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在大家的撮合下,我外婆同意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我父亲,这是段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婚姻。我的姨妈嫁给了章蕴的儿子,我们小辈人都按湖南人的习惯叫章蕴奶奶“娭毑”。章奶奶的爱人更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他叫李耘生,一九三二年牺牲在了南京的雨花台。我在百度里找到了他们的资料:
章蕴(1905年-1995年),原名杜韫章,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妇女活动家。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之妻。
章蕴于1925年在汉口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后又任汉口市乔口特区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1936年起,历任中共中心县委书记,东南分局妇委负责人,苏南区党委委员、妇女部长,苏中区第二地委书记,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等。国共内战期间,任华中分局委员、妇女部长,华东局妇女部长,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第三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校长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华东局妇委书记、上海市委妇委书记。1953年出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并兼任全国妇联秘书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出任中纪委副书记。1982年起任中顾委委员。1995年逝世。
吴仲超1927年秋,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前身)。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乡从事地下工作。
1931年起,先后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南汇、无锡
中心县委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中共苏南特委书记,苏皖区委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政治委员,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西路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6师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京沪路东特委书记,茅山地委书记,苏皖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苏南行署副主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行署主任,苏浙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苏浙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参加1941年苏南反“清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秘书长,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秘书长。期间,为党和人民征集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华东党校副校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助理,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
1984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父亲不准外婆进家来看我们了,可我外婆这老地下党员还是有办法的,她会在我放学时等在校门口,带给我们她亲手做的放在饭盒里的好吃。然后悄悄的告诉我们: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她会从住在鼓楼的舅爷家到北海公园的大门口等我们。父亲曾经警告过我们不能去,可我不听。因为我爱我的外婆,更喜欢她精心为我们做的小吃。每到星期六,我就会自己跑去北海公园的门口找外婆。她会拿出“糖莲藕和八宝饭”“驴打滚和糖卷咕”给我吃,回家时偶尔地会被父亲发现,他会骂我两句,我只当吹耳旁风。现在回想:外婆对我的慈爱是那样的深,那样的厚重。她是第一位遭到我父亲拒绝和伤害的人!
我的姨妈在文革时,也是瞬间变成了“反革命家属”。为什么?因为她的丈夫在两岁时出卖了共产党员!他的父亲。那是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抓住了李耘生,但不能确定他的身份。可国民党在家里也抓住了他唯一的儿子,上演了一场“父子相认”的诡计。两岁的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在见到爸爸时喊了出来。李耘生牺牲了,我的姨夫进了孤儿院。这就成了“文革”时他是反革命的理由,莫须有啊!没有人再说他是烈士的遗孤。
姨妈带着我的表弟来看她的大姐,被堵在了门外。表弟哭了,问妈妈:为什么大姨妈不见我们?我的姨妈无法回答儿子的问题,她也难以理解那和蔼可亲的大姐过去从未如此的冷酷过,他们曾经是那样的喜欢和热爱的大姐变得非常的陌生。这是我父亲第二次的拒绝和伤害了亲人。
在我家的老相册里,有一张我的父母刚结婚时的照片。他们坐在草地上怀里各自搂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这对孩子就是章蕴的弟弟杜平叔叔的儿女。
战友遭难,杜平叔叔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他的女儿杜雅跑到我家想求助我的父亲,小雅姐姐在那寒冷的冬天站在了我家的大门口,我们正在吃晚饭。小的时候在广州,我们就认识了小雅姐姐,我们都非常喜欢她这漂亮的姐姐。听说她在门口时,我们都从桌子旁跳起欢呼。可我的父亲制止了我们的动作,我不死心,顺着墙根沿着夹道溜到了大门口。趴在夹道口偷看,小雅姐姐看见了我,喊出了我的名字。可我不敢再往前走,我知道再走一步是会挨打的。姐姐哭了,伤心的走了。她眼里的温叔叔不再是可以把她搂在怀里的依靠,不再是亲人,也和她的父亲不再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这是我父亲在我眼里留下的第三次拒绝和伤害到了亲人!
世事捉弄人,在那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家庭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革命队伍里”没有人不会遇上冲击和陷害,任谁都躲不过那飞来的子弹,命中率比在战场上的死亡率还要高出许多!没有谁可以当那一世的凤凰。
我的父亲也被关押起来,我们孩子也成了“反革命的子女”。我的母亲没了工作,我们被赶出了部队的房子,搬到了四周都是农田的郊区。
在我们被楚歌四面包围着的时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是我的姨妈不顾一切的冲到了四川!来看望她那受到打击的大姐,看望我们孩子,带给我们温暖的亲情和物质上的关怀。她全然的不记得我的父母是曾经那样的伤害过她,也忘记了她自己还背着的“反革命家属”。对我的母亲来说,那是又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关怀,有了可以也愿意听她说话的亲人,身边有了贴心的人,高度紧张的神经得以放缓,没有崩溃。
在我因为父亲“反革命”的原因失学后,我的精神频于崩溃的边缘。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还是没有放过我这孩子,派来“保卫部”的人要抓我这十三岁的人去下乡,还不告诉我的母亲我是要被送到哪里的乡下。慌乱中,我的母亲还是只想到了她的母亲和妹妹可以救我,连夜把我塞上了火车。是我的外婆和姨妈在我最危机的关头伸手接住了我,我躲到了上海。
最令人可笑的是那想要我们命的“司令”,自己的家后来也被赶出了成都军区。文革结束时,人人都要做“结论”。他的结论叫“上了贼船”,背上了处分,而我父亲的结论里就没有这些个乱七八糟。
我的落难生涯并没因为躲在了上海而结束,中美要建交,那该死的尼克松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要路过上海再滚回美国。我被那“里弄侦缉队”发现了是个没有户口、身份不明的黑鬼,而且住在这房子里的一堆人身份都是很“黑”,“右派”、“反革命家属”、“黑帮的孩子”,我们被告之不准出门,吃喝由街道给送至门口。外婆带着我又开始了躲避,我们潜伏进了北京,我住进了故宫的宿舍。我的舅爷没有因为我父亲的问题而害怕,没有把我拒之门外。这和当年我父亲的做法差距之大!可故宫宿舍也是个难以藏身之地,时间久了人人都在疑问:吴老这是你的孙女吗?舅爷从不含糊地回答:这是我的孙女啊!所以,现在故宫的许多老人和他们的下一代也还都知道:“吴老有一个孙女”。
我在北京的日子就是今天住这家明天住那家,章蕴奶奶也把我收到过自己的身边,我也躲过灯市口的全国妇联宿舍。当他们一家家的收留我时,我的内心就会在一遍遍的反问,当年我父亲为什么就不能象他们一样?伸出你的手?我深深的体会了一个需要救援的人遭到了拒绝会是多么的绝望,一群被你拒绝过的亲人又在不记过往的努力救援你女儿时,你女儿内心所受的煎熬和惭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
最让我痛苦的是:我外婆、舅爷和父母的老战友、老朋友彭炎伯伯和阮波阿姨的一习话!从小我们两家就是来往密切的亲朋,我要是跟着外婆去他们的家,我要喊彭炎伯伯叫彭公公、阮婆婆,跟着我父亲去吃饭就叫彭伯伯、阮波阿姨。我在北京逃难时也躲过他们家,阮波阿姨含着眼泪对我说:“小露露,你知道吗?抓我们去坐牢的逮捕令上盖的是你爸爸的图章啊!”我震惊了,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我的父亲回到了家中。我也从北京赶回了四川去看分别了六年的父亲,我曾哭着问父亲:你为什么会下得去手?去抓你的战友和朋友?父亲茫然了,父亲痛苦的回答我:这些我都完全的不知道啊,因为那“卫戍区司令的图章”不是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我的父亲能在粉碎“四人帮”后马上就被放出来?那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恩来临死前对李先念和陈锡联有交代:你们帮我去找找老温,他在哪里。我是没办法啊,被江青逼得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在那权利相争的年代,你想自保很难!想去保你想保的人更难。如果连他也要倒了,那就更没有人能去找机会救人了。我的父亲明白他的难处,在帮他分担。那“卫戍区司令的图章”也就交给了他,以至于有那么多的在文革中受到了伤害的人,最后把帐都算到了父亲的头上,父亲帮他背了黑锅。可从未有人想过那来救你的人,也是盖章抓你的人。是非总是如此的被颠倒着,黑白永远的难以分辨。因为是那“上帝”打翻了调色板!
我的父亲也是被整的糊涂了,他是真的害怕了一切。他搞不懂为什么他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小心的活着,谨小慎微的工作着,“文革”中没干坏事,可结果是要被千夫所指,后半生灰溜溜的做人。
对文革中的“检讨”来回的说那:“对不起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同志”。我呸!在这件事上,我的父亲没有错!收到检举信逐级的上缴,哪里有错?谁知道那信会流向谁的手中?现在不也还有许多的实名举报信被交到了被举报人的手中吗?你怎能全看清了那蜘蛛是怎么拉的网?你个李必达到现在也没有公开过你写给江青的“检举信”是什么内容,我是否还可理解为你是个想投靠效忠“四人帮”的走狗?抓了你也是活该。
我到认为在文革中,我父亲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亲人间的伤害,他不该因为害怕胆小就将所有的亲人拒之门外,战场走过来的战友情加上亲情变得如此的脆弱。头上的乌纱和屁股底下的板凳,与血肉相连的亲情和生死相交的战友情哪个来得可靠?这才是父亲没有看到和想清楚的错误。
我原谅他!因为他是个老粗,没有文化,做人思维简单。在那个年代,当你的女儿都会指着你的鼻子问:你是哪个“司令部”的时候,你一定也是想回答她:我是那“红色”司令部的一员。可在那黑白颠倒的日子里,哪里可以找到对与错?都是那混君惹得祸,你们都不知道那“兔死狗烹”的故事。
这是我那可爱的小表弟,现在也已经成长的一表人才,他来南京看他的大姨妈,我的妈妈很开心。我的姨妈也为他骄傲,姨妈有个好儿子,他也是我家的第三代将军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