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牧
王彬彬批评汪晖的“学风”的文章,在网上掀起了又一轮讨论学术不端的高潮。毫不讳言,汪晖是我颇为仰慕的一位学者,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却不是为他辩护,而是感到一种悲凉:哪怕对当前学术的圈子化、利益集团化有不少腹议,但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严肃的有思考的人,认真地写着自己既关注内心又关注社会的文章,即使这些文章在发表时因为种种学术弊端而遭遇到了重重困难,但仍然坚信学术乃一项庄重的事业。像汪晖这样在我心目中顶尖的学者也“剽窃”的话,自己仍孜孜以求的学术梦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我于是上网搜索到了王彬彬的那篇正被热议的文章,并对照汪晖那本被批判的《反抗绝望》的书认真阅读起来。应该说,我的阅读是带着疑问的,我不想一下子就将自己推向绝境,不想一下子就因为别人的判断就真的绝望起来。我想看看到底他的问题有多严重。如果真的存在“剽窃”问题,我想我该重新思考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必要了。
真的绝望到来的时候,我想我是没有“反抗绝望”的勇气的。
此外,对于王彬彬,我是有所了解的。他应该是我的师辈,而且看过他的大部分文章。我一向觉得他的文风凌厉,尖锐而有力,而且颇有颇有文采,大江大河,一泻千里。他的文章,大致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骂毛的专制集权,骂革命无所不在的非人道的暴力;二是骂人,骂别人的文章不好。前一类的骂,基本上是跟主流意识形态一个腔调,是1980年代以来将革命污名化的陈词滥调的一部分。其所谓革命就是非人道的,这一类观点不知道多少人说过了,王彬彬不加反思地继续重复,这却是我觉得是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后一类骂人,也许显出了他的个性,甘愿做个学术清道夫,这是颇有勇气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学术,还真的是有问题,多一个骂街的,也不是完全没好处,而且像他这样已经成为学术大腕的人,是有人给他提供骂街的平台的。不像我们这些小字辈,所有的不满,只有腹议的份。
但有一点,骂街的同时,总要先表白一番自己的无辜,自己的清高,似乎也没逃脱这一类骂街文章的叙事成规。任何文体,看似千变万化,但其实都有自己的习得的叙事成规,骂人的文章就是这个成规,首先要将自己撇清,要自己装扮成圣人,之所以要骂,不是处心积虑地要骂,而是因为某种偶然性因素,而之所以这偶然成为必须,是因为出于某种公心,如此等等。比如这次骂汪晖,先说《反抗绝望》是汪晖学术上的“第一桶金”,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而自己却从来不看的——这用来表示自己的不屑,但却也未必是是正常的学术态度,他是搞学术研究的,而且确实写过关于鲁迅的文章,对这么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不看不代表水平高,而是代表不懂得学术规范,因为有一种声音先于你存在了,在理不在理都应该有分辨的义务,不然如何证明自己的研究是否别人的重复呢?
然后,王彬彬说现在看了这本书了,是很偶然的,但却也是出于公心:以正视听,免得谬种流传害人不浅的现象继续下去,因为他的学生不断在写文章的时候要参考这本书。所以说,这非常符合批评文体的叙述惯例,也就是俗套:骂别人的同时给自己戴个高帽子。他这次接受采访时候说,他就纳闷为什么网上的很多评论不冲着小偷却冲着他这个抓贼的人——的确是有些人在对他这个抓贼的人说三道四了,但这有关抓贼的自我定位,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呢?我在对照汪晖的原著读了他的这篇辩难文章后,发现他的确有一种抓贼的心思,但可惜选错了对象,为了抓贼而抓贼,结果在批判别人学风的时候,却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学风的不端。
对此,我想如果逐条罗列的话,是费时费力的,而且写这样的文章,我也明知道不可能发表,换不来学术GDP的增长,反倒有可能得罪人,自毁长城,自断后路,但我却因为要说服自己继续从事这一个行当,却也不能不任着自己的性子说上一两句。所以,我就选择一则王彬彬对汪晖最严重的指控,来谈谈究竟是谁的学风出了问题吧。那么,且看被王彬彬指责汪晖将勒文森著作中有关梁启超的论述直接置换为鲁迅的那段: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反抗绝望》第6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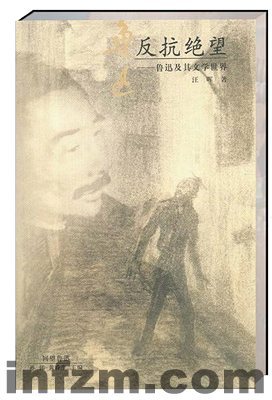
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二章,题为《传统世界的崩溃》。这一章,勒文森这样开头(第46页):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作了这个罗列后,王彬彬就不无得意地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汪晖只把勒文森的‘梁启超’换成‘鲁迅’,其他便‘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抄录勒文森”,而他之所以用了“几乎”,实在不是为了给汪晖留些情面,而是为了下面的文章:
“说汪晖‘几乎’原原本本抄录勒文森,是除了名字的变换外,还有一个标点符号的差异。勒文森的“技术、结构”,在汪晖手里变成了‘技术结构’:‘技术’与‘结构’之间的顿号没有了,这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但‘技术、结构’是两件事;而‘技术结构’则变成了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汪晖的剽袭,总是有意无意地损害原文”。
看了这段,不由得不佩服王彬彬遣词造句的“语文”功夫实在了得,而且排兵布阵处处包藏杀机,他的“几乎”,既强调了“名字的变换”,又追加了一个“剽窃”得“匆忙”乃至在“标点符号”上出现“疏忽”,并且因此而“有意无意地损害了原文”。从王彬彬对“技术”、“结构”及“技术结构”的有板有眼且煞有介事的分析中,他的这篇指责“汪晖的学风”的文章,是写得相当从容的,也就是不可能会有“匆忙间的疏忽”这样的问题的,既如此,那么,他在引述汪晖的文章时,避而不谈相关的注释,并且隐去紧随其后的带有转折性质的表述,则显然是蓄意为之了,但也正因此,让人觉得他挑剔别人“学风”的文章,其实正犯了学风不够端正的毛病。这里,我们不妨将原文粘贴在下面: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人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人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①与梁启超等人不同,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人主要是以否定性的方式进行的,即是以抨击与批判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系统的介绍方式引人。正是经由鲁迅及其同伴的努力,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逐步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历史发展。(《反抗绝望》第68-69页)
这段引文中标注的“①”是个脚注,其内容是“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如果没有王彬彬的指出,一般的读者自然就会以为这是列文森在一本专论梁启超的书中旁及鲁迅的观点,但若细心一点,却不免疑惑,这是一节文章开头的话,此前的行文中并没有提到梁启超,怎么会突兀地出现“与梁启超等人不同”的转折呢?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通常用这样的转折来突出将要论述的核心观念,而前面往往是戴的一个帽子,如果说帽子上写有梁启超的标签的话,这番转折才符合逻辑,不然的话,就会直觉到文气不够顺畅,表达不够清晰。这是低级的错误,但却让人费解,因为这很不符合虽有几分“晦涩”但却特别注重行文起承转折关系的汪晖的文风。感谢王彬彬查阅了“勒文森”(汪晖的文章中用列文森,这种差异应该是同一个英文名字的不同翻译)的原文,原来是论述梁启超的一段话。因为有了前面的疑惑,而又看到这段原文的话,我想我最直接的反应应该是,汪晖或者该书的编辑“可能是匆忙间的疏忽”,而误将“梁启超”写成“鲁迅”了。并且如此订正一下的话,原来突兀的地方,便略微有些顺理成章了。
当然,这样还可能有问题,即是在“与梁启超等人不同”之后,出现了“鲁迅的这种以民族文化改造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引人”的表述,也可能让人觉得汪晖前面的确是说“鲁迅”而不是说“梁启超”。不管怎样,假若认真阅读这段文字的话,最大的疑惑应该来自书写或编辑疏忽,但王彬彬却首先不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而是直接认定汪晖“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将对一头熊的认识用于对一只虎的判断了”。
鲁迅先生论及《红楼梦》的时候曾经说过,“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所以,王彬彬既然以学术清道夫自命,从最有可能的书写或编辑疏忽中看到最严重的学术品德问题,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他为什么在行文中对汪晖对列文森的注释只字不提呢?事实上,他就是根据汪晖的注释才找到列文森的这段被“几乎原原本本地抄录”的话,但因为他的只字不提,不但给人一种汪晖做贼心虚的印象,而且让人以为他是看到汪晖如此论述鲁迅而想起了勒文森曾经这样对梁启超论述过,并进一步翻出勒文森的书,或者是大海捞针,或者是凭借牢固的阅读记忆,将那段话从书中找了出来。如此,汪晖“剽窃”的罪名,在王彬彬预期的阅读效果中,应该是板上钉钉百口莫辩的了。
在此基础上,得出汪晖“很忽视鲁、梁二人的差别”,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正如钟彪以及我们上面的较完整的引文所指出的,汪晖此后的论述重点恰恰就在“鲁、梁二人的差别”上。或者汪晖的论述本身是有问题的,或者他花了大量的功夫,仍然没让我们看出鲁迅和梁启超的差别所在,这是很可诟病甚至批判的,但王彬彬却只在无视汪晖的注解的前提下引述他半句话,并由此而出正义凛然的结论,就不由得不让人怀疑,他这篇指责别人学风的文章,其实本来就是学风不正的。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