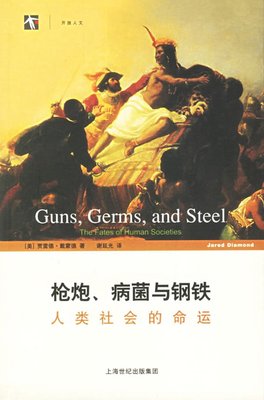北大筒子楼:一代学人的命运变迁
2010-08-0215:48南方都市报
伫立了50余年的北大21楼。
由南门进入北京大学,你会看到蓊郁的树木掩映着一片青灰色的三层高小楼。每三座小楼构成一个“品”字形半围合院子。这是上世纪50年代使用至今的筒子楼。这些以数字命名的小楼如今住着博士生、教工或者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北大校园这些年变化颇大,但这片区域依然保持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面貌。
2007年8月下旬,北大南门27楼拆迁重建的消息曾经引发热议。后来,北大发展规划部发布《北京大学南校门区域功能调整规划开始实施》,宣布南校门一带16至27号筒子楼将规划重建。而今,27楼的原址矗立着教育学院的新办公楼。相同的面积,同样的高度,延续的灰色,但已不是当初的楼。
今年6月,陈平原主编的《筒子楼的故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华诞”的礼物之一,《筒子楼的故事》汇集了北大中文系20余位教师及家属在北大筒子楼工作生活的回忆性文章。陈平原为书作序,题目叫《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我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一历史记忆,不全是‘怀旧’,也不是为了‘励志’,而是相信个人的日常生活,受制于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居住方式本身,又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的知识、情感与趣味。”陈平原对南都记者说。
筒子楼,这带有社会主义风貌特征的建筑,勾连起北大中文系50余年的历史。其所代表的时代的基本居住形态,更是中国50至90年代“单位人”的共同记忆。
1 政治变迁 荒诞的闹剧,信念的绝望
1964年,严绍璗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留校任教。由于成分不好,中文系党委为他的留校问题开了多次的会。后来,中文系党总书记程贤策出来说话,“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一个青年学生,关键在于自己”。
在单身宿舍辗转了几处,三年后,严绍璗搬入了北大三角地东侧的家属宿舍16楼。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筒子楼生活。
那时,与他同期或更早留校的中文系老师多半都住在19楼。当时,19斋(“文革”时“破四旧”不许叫“斋”,改为“楼”,沿用至今)是文科教师的集体宿舍,聚集了中文系、历史系、法律系和经济系的男教员。
比严绍璗早几年留校的洪子诚当时就住19楼,在他印象里,这种集体宿舍一般一个屋住两个人,个别较大的屋子能住三个人。基本配置是,两人共用一张两边都有抽屉的大桌子、一个五层的书架(运气好的话会发到一个七层的书架)。一人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小方凳子“有时候在大饭厅(如今的百年大讲堂)或者东操场(如今的五四运动场)放电影,学生老师人手一个凳子排队去看电影。凳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记得最清楚的是,有的同学会把凳子顶在头上去看电影。”
严格说来,类似于19楼这样的集体宿舍并不能算是“筒子楼”,因为它既不能落家庭户口,也不能开火做饭,楼道里没有洗米洗菜的公用厨房,也鲜少一起过日子的夫妇。大家都吃食堂,偶尔来客人错过食堂饭点则招待“暖瓶煮挂面”———打一壶滚烫开水,将挂面一缕缕放进暖瓶,闷上四五分钟,挑出来加酱油、味精等聊以果腹。
五六十年代中国政治气候波诡云谲,大小运动不断,筒子楼一如北大,不可能置身世外。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北大被中央高层认为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阶级斗争形势复杂。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9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中文系更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镇,正常的教学秩序已无法维持。
“反右”之后紧接着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红专辩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筒子楼位于北大校园中心,离学生重要活动区域很近。筒子楼的居民们眼皮底下就是那个时代风雨飘摇的“大事件”。
1966年5月25日11时,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7人签名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大字报一经贴出,即如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校沸腾。最高领导人亲自下令向全国广播这一大字报,并将北大称为“反动堡垒”。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被打成“黑帮”,更残酷的斗争进一步展开。
严绍璗居住的16楼紧邻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心北大大饭堂,时不时能听到大饭厅传来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或“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他也曾目睹,历史系的教授周一良被当时的红卫兵、激进青年打得嘴角出血。
斗争愈演愈烈,到了6月18日,发展到了最残暴的“高潮”。
严绍璗说,他至今忘不了那一天,“早上在二院学习文件,突然红卫兵扛着一个苇席卷进来,往地上一扔。大家发现苇席里有动静,有人拿墨汁往上浇,苇席里有人喊,发现是原来学生工作组的组长。”
学习进行不下去,严绍璗就走到校园里,一路上都是被戴高帽、浇墨水被批斗人群。中文系的一位副系主任,被拉到二院系办公室的门口,他身后,批斗他的学生拿了一瓶墨汁从他头顶浇下。另一个学生从院内跑出来,将厕所里装满手纸的纸篓扣到了他的头上……
“文革”批斗规格最高的一次,是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批斗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全体北大师生都参加了批斗会,陪斗的是彭真、罗瑞卿、杨尚昆。严绍璗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异常闷热,批斗会结束后一场大暴雨,把人淋得像鬼一样”。
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程贤策被批斗的画面,刻进了很多人的脑海里。在《筒子楼的故事》里,很多人都写出了他们的记忆里的场景。严绍璗向南都记者讲述了在批斗中他接触到的程贤策,“1966年8月底9月初,针对程贤策,中文系组织了两场批判。有一场是在办公楼礼堂,现在的校长办公楼。700人的位置,由中央电影制片厂全场录像。程贤策解放前是地下党,是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女婿,总的来说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批斗结束后,我陪他返回住处,在南阁北阁的门口,程贤策满身大汗,对我说,要休息一下。我就让他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他对我说:‘他们今天讲的很多事和我没关系,我是1948年从武汉大学调任到北大,陆平是1958年从铁道部调到北大,你还年轻,你不知道这些情况。’”
“我想程贤策后来是真的绝望了,信念上的绝望。”严绍璗说。后来,程贤策在香山公园自杀,拿敌敌畏和酒掺在一起喝下去。“他进公园的时候门卫就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浓浓的农药的味道,后来发现这人在里面已经不行了。”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北大清理出一千多人。在全校大会上,进驻学校的军宣队领导说,这只是开始,高潮还在后面。一位老师清楚地记得,针对北大自杀增多的现象,一位姓魏的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就对了,说明运动大大地深入了,真正触及到了灵魂。”
严峻的政治生活同样弥漫筒子楼。19楼成为中文系所有男教员的集中地,即使住在家属宿舍的老师也要集中住到这里,女教职工则住在21楼。家住校外的,星期天晚上才能回家,回来也要报到。当时的中文系教员洪子诚回忆说,“那时大家每天六点钟起床之后要集体出操,白天学习文件,晚上九点钟集体接受军宣队训话,所有教员排得密密麻麻,大家安静地听着。”
这样的集中管理持续了有两个月时间,揪出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的人低头、弯腰挨一番批斗,其他的老师必须一起喊口号,但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谁也不知道。
曹先擢、谢冕、严家炎、唐沅四位教师因为“对江青有意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小集团”,原因是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常常晚上到北大东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有一次说到毛岸青的妻子如何如何坏,大家私下里议论,觉得江青不应该把自己家里的事情拿出来讲。
1967年秋天,北大“文革”转入派系斗争阶段。“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公社”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派仗,卷入全国的大武斗当中。南门外的交通中断,“两派的高音喇叭互相指摘对方,在公路上撒满了黄豆、绿豆什么的,使人寸步难行,真是稀奇诡谲之极。”严绍璗这样描述。
南门一带的筒子楼成了双方争夺的阵地,“井冈山”的红卫兵占领了从30楼起始往北大南墙的一大片楼房,“新北大”则占领了更多的楼房,包围了“井冈山”。于是“井冈山”在28楼挖了地道一直挖到南墙外头,为了躲避对方的武力。
后勤的工人参加两派的斗争,由他们来制造大型“弹弓”,用钢筋焊成一块,自行车车胎做皮筋,砖头做子弹,好几个人才能拉得动。所有窗户都没有了玻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变压器也被炸了。洪子诚的夫人、当时还是中文系学生的么书仪回忆,“记忆中的盛夏,海淀的居民都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摇着蒲扇,听着两派的高音喇叭互相嘲骂讥讽……”
3 思想激荡 畅谈理想、畅谈学问的80年代
筒子楼不只经历政治风云、记录学人生活点滴,更见证学术思想激荡的80年代。
1977年12月,全国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1978年,北大中文系招收了“文革”后首批本科生和研究生。正是这一年,钱理群离开待了18年的贵州安顺,回到北大中文系,攻读王瑶的研究生。这一年,钱理群39岁。
20年前,还是北大大二学生的钱理群,曾在全班同学面前,挥舞着拳头激情澎湃地说:“我同意费孝通教授的意见,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无非是‘一 间 屋 ,一 杯 茶 ,一 本书’,——— 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那是1957年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之后。但很快,费孝通被打成了“大右派”,钱理群也因为力挺右派言论而遭殃。政治落后,再加上出身不好,新闻专业毕业的他不能分配去新闻单位,“发配”到了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在一所卫生学校当老师。再回北大时,用钱理群自己的话说,已是两鬓斑白的“老童生”。
毕业留校后,钱理群在北大的宿舍是21楼,分配到的是一间由浴室改装的潮湿阴冷的小屋,根本不能住人。一次次申诉无果,得到的答复是“北大条件就是如此,要留,就得忍。不想留,悉听尊便。”忍无可忍中,钱理群递上了调离北大的申请书。几番折腾后,钱理群终于从一楼搬到了二楼,换了一间可以住的筒子间。
1983年的深秋,硕士毕业进京联系单位的陈平原被好友黄子平告知:“一定要见见老钱!”也就是在钱理群那十平米的小屋里,日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燕园“三剑客”一聊聊了一个下午。临行前,陈平原将自己刚写完的《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交给钱理群。当晚十点多,读过文章后,钱理群急匆匆跑到勺园,找黄子平商量如何劝陈平原转投北大中文系。此前陈平原已经联系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差不多就定了。
之后,王瑶先生出面,要求北大破例接纳陈平原这位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但最后没有成功。王瑶毅然决定把陈平原收为自己的第一个,也是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陈平原告诉南都记者,“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主要是在老钱那间“筒子楼”的宿舍中完成的,“那时住得很近,就在隔壁楼,端起饭碗就过去,一聊就聊大半天”。
“到1988年的春天,我们三人又聚在一起,分专题从文化角度编选20世纪中国散文。大热天,三人又挤在老钱那间堆满书籍的小屋里‘集体读书’。”像今天住得这么分散,见面聊天要事先打电话约定,再也不可能那样无拘无束了。”陈平原不无遗憾地说,“当然,不全是住宿的问题,还有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
那种侃大山式的“学术聊天”,可能也只属于80年代。
尾声
几十年的筒子楼生活在回忆中删繁就简,渐渐沉潜,但平静中也有反思。
“中国的知识分子价廉物美,誉满全球,但这难道不正是我们的耻辱?!”,钱理群在《我的那间小屋》一文中苦涩地写道。那篇文章写于1988年,那年,钱理群的名字出现在了迁居的名单上。文章收入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文集中,因为批判性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钱理群说,其实,那是对知识分子安贫乐道传统的反思。“费孝通1957年反右运动的时候提的‘一间屋,一杯茶,一本书’,这话实际上是双重意义,一个是物质意义,知识分子要有一个书房,这样一个物质的空间,另一个是精神层面的,这意味着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思考、写作、研究,这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
钱理群认为现在年轻的助教讲师和他们那时候的境遇也差不多,“只不过我们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的做法,看它分不分给你,现在是商品经济的逻辑,你买不买得起。”
1998年,国务院决定要重点解决高校教师的住房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多次开会表示:“决不让筒子楼带入21世纪!”成府路上的蓝旗营小区破土动工,作为解决北大清华教师住房问题的重要举措。
也就是这一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如今,北大清华不少的学者都住在蓝旗营小区,那里一片高耸的塔楼被称为“院士楼”。房子面积一般在一百多平米以上,北大清华的许多老师终于在退休后拥有了自己的书房。而刚留校的年轻教师们,有的则继续在筒子楼里挥洒着青春。只是他们明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终有一天会离开这里。
筒子楼小史
筒子楼诞生于院系合并后的新北大。
上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以及实现工业化的压力下,教育部拉开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的序幕。原来位于“五四”运动策源地———沙滩红楼的北大迁至西郊清华园、圆明园毗邻的燕园,叫做“新北大”。
迁校的准备工作从1952年1月开始。1月8日,以清华大学梁思成、北京大学张龙翔为首的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筑计划委员会成立。全部设计人员和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由清华、北大工学院建筑系的师生组成。这一年的10月4日,新北大第一次开学典礼在东操场(如今的五四运动场)举行,此前,为了按时开学,44046平方米的校舍当年设计、当年开工、并在当年内竣工完成。
“三校建委会”成员、梁思成的学生、建筑师陶宗震当时负责“燕园”中的教室楼建筑群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据他回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方针是“勤俭建国”,原则是适用、坚固、经济,但风格上又要与原燕大的环境协调,“不可能按照‘则例’、‘法式’或美国建筑师莫菲(Murphy)设计的原燕京大学的仿古建筑进行设计,而是参照1951年冬我去福建厦门时,一路所见之新建民间二、三层砖木结构建筑及陈嘉庚新建的厦门大学新教学中心‘中西合璧’的设计方式,结果造价仅80元/平米。”
这些灰色清水砖墙混合结构的楼群,以通向北大南门的干道为新的轴线,形成了新的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
1954年入学的段宝林清楚地记得,1斋到15斋是1952年盖的,“这种二层小楼原来很多,现在都拆光了”。这批设计寿命为10年左右的临时建筑,为北大服务了半个多世纪。而“现在南门一带16至21斋是简易的三层楼,也是1952年盖的,22斋至27斋,是1954年建成的,是大屋顶的三层楼,比较精致。1955年盖了28至31斋,这是平顶的四层楼。1956年拆迁民居,又盖了32至40斋”。这些逐年建成的筒子楼,迎来送往了一届届北大学子,也构成了北大教师多年的栖身之处。
(上图为《筒子楼的故事》封面局部)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