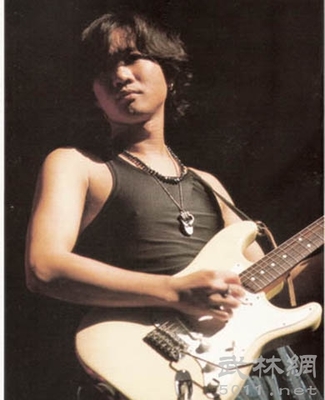这是钢铁业最接近“达达主义”的作品。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位于美洲的钢铁工厂横亘了两座大陆。它的一半在巴西东南部里约热内卢风景秀美的圣克鲁斯湾。人工开凿的运河从这里蜿蜒入海,并连接码头、电站和铁路。这里集合了人类对古老冶金术的所有智慧,数千台摄像机和传感器监控生产,难得一见的昂贵设备在此相互连接,管道和传送带织成一张令人眩晕的网。
网上流动的是淡水河谷(Vale)公司从不远处用火车运来的赤红色的铁矿石,它们被一个个大铲子移走,然后又被扔进许多缓慢运转的机器。这些机器会将铁矿石筛选并划分等级,最后形成两座对称的小山,每座占地周长约一公里,高20米。接着,另外一些如黑色虫子般的机器则负责将煤变成焦炭,它们被用来熔化铁矿石。之后,沸腾的铁水被倒进黑色的盛铁桶,每只大桶装载着 350吨铁水,由强劲的吊车拖至炼钢高炉的所在地。在这里,大桶被举起,翻转,再将铁水倒进一个个比房子还高的转炉。工人们开始往里面掺加一小部分辅料,转炉中的混合物向外飞溅,发出低沉的咕咕声,愤怒的火星闪耀着红色或白色的光,如喷泉般撒向空中。
蒂森克虏伯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田坤(Tilo Quink)告诉《环球企业家》,公司以往的错误来自不透明,“很多事情都是凭关系来做,都是藏起来的。你根本不知道一项投资是怎么来决定的。但当赫辛根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间工厂的另一半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汤比格比河的入海口。这里是美国南部新崛起的工业重镇,来自德国和日韩的汽车制造商均盘踞于此。为了建造巨大而坚固的厂房,超过5万根钢柱被相继打入这片地下。千里之遥的巴西钢厂炼就的又长又厚的钢坯经由海运到达这里。它们经过一台世界上宽度最大的7机架连轧机组,钢坏逐渐受到挤压,变得越来越薄。最后,厚度仅剩数毫米。这个场景看上去很像一台巨型报纸印刷机在不分昼夜地工作。这些钢板十分珍贵,为了防止生锈,工人们会通过高温或电镀的方式在钢板表面镀锌。再将这些薄板打上包装纸卷成筒状,或像铺床单一样铺开,最后才被存入库房。最终,它们将在附近的汽车工厂里华丽变身,成为奔驰C级轿车的车门或者宝马X7的发动机盖。
在这里,美妙之处并不在于蒂森克虏伯能够像制作巧克力曲奇一样轻松熟练地铸造全球最好的钢铁,而是这个极富创造力的构想本身。蒂森克虏伯前任首席执行官埃克哈德·舒尔茨(Ekkehard Schulz)将这两个“配对”的钢厂形容为“实质上一体化的钢厂”,即使它们跨越了两个大陆。这一奇迹工厂诞生的目的在于,蒂森克虏伯试图赚取最低成本的巴西制造和最高利润的美国市场之间的最大价格差。从经济学角度,它们只是拉长了半成品在“厂内”的物流距离,而花在运输高纯度的钢坯上的费用显然远低于运送笨重铁矿石的费用。
在这两座工厂出现之前,全世界的钢铁公司尚未尝试过如此超现实主义的全球化生产,即使这个行业诞生过的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式的巨贾——他也没用尝试过。长久以来,由于运输局限,钢铁业从来都是一个分散且区域性的产业。直到雄心勃勃的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收购了全球最大钢铁制造商安赛乐(Arcelor)并组建安赛乐米塔尔公司(ArcelorMittal)之后,世界上才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钢铁公司。但这位“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卡内基”也未曾尝试如此理想主义的冒险。
但蒂森克虏伯煞费苦心迎来的却是失望。事实上,当这两座钢厂尚未开足马力去拥抱北美市场之时,它便陷入泥沼。最初,巴西钢厂一座炼焦炉迟迟难以安装到位,最终蒂森克虏伯不得不与设备提供商中途解约,这导致开工时间推迟两年至2010年。工厂开工不久,它即遭当地居民起诉,后者称其排放物有害健康。渔民也不断控诉说,工厂的建立影响渔业的收成。里约热内卢州环保机构最终向其开出130万欧元的罚单,并要求它向当地居民提供630万欧元的补偿金。这些罚金仅是九牛一毛,由于建设超支,两个工厂的成本远高于原始的计划投资。
但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梦魇。巴西和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呈现的经济增速的反差,颠覆了蒂森克虏伯的原有计划。这两座工厂成功的基础是,巴西的人力、原料成本一直保持低位,而美国钢材市场则持续繁荣。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这从巴西货币雷亚尔接连升值和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中不难窥见。由于美洲钢铁部门的巨额资产减记,蒂森克虏伯不得不对外宣告2012财年成为公司历史上损失最为严重的一年,亏损额达到50亿欧元,它因此背负巨额债务。
蒂森克虏伯还有别的麻烦。当时它正丑闻缠身。2012年,该公司被指控与竞争对手串谋操纵铁轨价格而遭到1亿欧元罚款,三名高管于12月被开除。最近的一次则发生于2013年初,在一次针对汽车行业钢铁供应的调查中,反垄断监督官员突袭了蒂森克虏伯位于杜伊斯堡的一间办公室。那段时间离,蒂森克虏伯内部还发生了一起工人代表与记者驾车奢侈游玩的丑闻—当时的公司管理几近失控。
蒂森克虏伯三年来首度实现盈利。2013/2014财年,集团实现净利润1.95亿欧元;应付股东净利润达到2.1亿欧元;对应每股收益达0.38欧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这并不奇怪。因为在4年前任命海里希·赫辛根(Heinrich Hiesinger)为蒂森克虏伯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以取代舒尔茨之前,这头大象真正的运转方式并不为外人所知。现年55岁的赫辛根是这家“德国重工业象征”过去200年间首位从外部空降的首席执行官。他曾担任西门子公司(SIEMENS)董事会董事及最为重要的工业部门的首席执行官。因在岌岌可危的西门子重建业务过程中采取强硬立场,赫辛根赢得了改革先锋的声誉。他说话开门见山,但也会坦白心声,他对建立上下级之间的互信关系相当内行,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愿意处理那些棘手的问题。
赫辛根出生在德国一个农场主家庭。年纪很小时,他便被允许独自操作那些非常昂贵的大型机械,即使犯错,他也不会遭到父亲的责骂。这让他变得比同龄人更加勇敢和自信。“如果你在农场长大,你就会知道,获取好的收成所面对的困难到底有多复杂。”赫辛根对《环球企业家》说。
手术
同样的道理,对于治理公司,赫辛根也必须先解决掉那些“必须解决”的问题。他的眼中钉就是位于美洲的那两家工厂。戏剧性的是,最初迫使德国人绞尽脑汁想出这个疯狂点子的人正是狡猾的米塔尔。蒂森克虏伯此前试图通过收购位于多伦多的多法斯科公司(Dofasco)叩开诱人的北美市场,该公司是首屈一指的扁钢生产商,掌握着北美汽车钢铁市场10%的份额。但问题是安赛乐公司已经捷足先登,它先于2005年底向多法斯科公司提出恶意收购。两家欧洲钢铁豪门就此展开争夺多法斯科公司的拉锯战。
这曾是蒂森克虏伯的“尖峰时刻”。经过数轮针锋相对地相互加价,安赛乐公司有“斗士”之称的首席执行官盖伊·多莱(Guy Dollé)最后出现在成功收购多法斯科公司的庆功酒会上。当时的隐情是,多莱已经深切感受到来自米塔尔的威胁,他不惜代价地将多法斯科揽入怀中的根本目的是要为米塔尔吞并安赛乐制造障碍。
事实上,米塔尔在这场竞购的关键时刻曾给舒尔茨打过一个电话,他直接抛出收购安赛乐公司的想法,并向舒尔茨许诺一旦他的计划完成,他会“将多法斯科公司还给蒂森克虏伯”。而在米塔尔对安赛乐发动的那场耗资332亿美元的世纪并购大战中,蒂森克虏伯也曾在危急时刻充当过安赛乐的“白衣骑士”。舒尔茨曾提议蒂森克虏伯与安赛乐合并,以击退米塔尔的计划,他当时称,这种合并将创造出真正的世界第一,“带着老欧洲最棒的工业专有技术勇敢地走向新世界”。但遗憾的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却是米塔尔战胜了盖伊·多莱,成为钢铁业的新霸主,蒂森克虏伯却毫无收获—多法斯科最终并入安赛乐米塔尔公司。
这场挫败令蒂森克虏伯不再追求新的收购对象,而孤注一掷地抛出在美国自建钢厂的计划。2007年,它开出一张公司历史上金额最为庞大的支票,用于投建美洲钢铁项目的金额最终高达120亿欧元,当时用于候选的厂址就多达70个。
巴西项目更是得到巴西本国前所未有的重视。时任巴西总统卢拉(Lula)号召5万名当地工人参与修建该国15年来数额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2010年在巴西工厂的开工仪式上,卢拉、舒尔茨与淡水河谷公司首席执行官罗格阿涅利(Roger Agnelli)一同按响了开工按钮。舒尔茨当时异常兴奋,他在仪式上称,“这些现代设施令我们为之自豪,因为它塑造了我们最宝贵的原则,比如追求技术革新,为高效生产服务。”
之后发生的事实却证明,这是一场误判形势之后的冒进,甚至带有鲁莽的个人英雄主义。对于蒂森克虏伯的美洲业务布局,博斯(Booz)咨询公司副总裁汤姆森·梅尔(Thomas Mayor)曾表示,从成本低的地区进口半制成品运送到美国进行深加工是制造商们通常都会采取的策略,因为制造商不仅需要维持低成本,更需要靠近客户,从而对市场需求和变化作出快速反应。但这一做法尚未在钢铁业流行起来。不过他认为,蒂森克虏伯的经营策略在2007年的时候是可行的。因为当时并没有几个人能够准确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
不过,早在项目投建时,来自钢铁业的质疑声就不绝于耳。美国纽柯(Nucor)公司首席执行官丹·迪米科(Dan DiMicco)就表示,依靠巴西发展美洲的钢铁业务本身就是“坏主意”,他认为两家钢厂不该如此建设。而一位熟悉美国市场的钢铁贸易商批评称:“在此项目中,运费是非常大的缺陷。从巴西运送产品到美国的运费是不可控的,并且占据了项目成本的很大一部分。”他所言不虚——因为即便在美国国内,运输成本在钢铁产品的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也很高。例如从阿拉巴马州运送到密歇根州的钢材产品,有12%至16%的成本是运输费用。
德国《商报》的评论文章则给出另一个视角:“老舒尔茨当时如果激流勇退放弃与米塔尔一决雌雄的念头,他的个人传记会好看很多。”文章指出巴西的商业环境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16位,其市场并不简单,一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很多德国中小企业在巴西投资获得成功,因为他们知道量力而行,逐步积累经验,并扩展关系网。而蒂森克虏伯在多法斯科公司的竞购战中败北,已经从某种层面上宣告了它在钢铁业的谢幕—即使它已经炼了200年的钢。
投资失败的责任最终被归咎于舒尔茨及其他高管,以及蒂森克虏伯监事会主席格哈德·克罗默(Gerhard Cromme)。格哈德·克罗默在过去的24年间代表了德国钢铁业的形象,被认为是一位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人物:他前12年曾担任克虏伯公司的行政总监,后12年担任蒂森克虏伯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他的另一个重要职位是西门子公司监事会主席。

观察者认为,克罗默拥有当时已近百岁高龄、尚未辞世的“幕后主谋”贝托尔德·贝茨(Berthold Beitz)的支持,后者管理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冯·博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是蒂森克虏伯公司最大的股东,因而拥有巨大的话语权。而此前,克罗默被认为将接替贝茨担任该基金会主席—正是贝茨当初选择克罗默监督克虏伯与蒂森公司在1999年的合并。但在2013年1月,一场暴风雨般的股东会议上,克罗默却代表监事会为各种错误与应对迟钝做出道歉,并于不久后宣布辞职。
依照传统,蒂森克虏伯首席执行官将由内部产生。但克罗默却非常希望从公司外部寻找一位接班人,他亲自挑选了赫辛根。由于痛感到蒂森克虏伯在钢铁业的发展太过深入,克罗默开始试图寻求改变公司的发展方向,并致力于推动其向技术型、多元化集团转型。因此,赫辛根被赋予的重要任务是,修订蒂森克虏伯公司的技术业务发展战略,并降低其对钢铁的依赖。
一头银发的赫辛根于2011年1月被任命为蒂森克虏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此前,他曾以蒂森克虏伯董事会副主席的身份在公司工作了超过一年。不过,这位电子工程博士当时并未引起外界更多的关注。而在公司内部,他亦行事低调,只把时间花在拜访工厂和观察同事身上。
“在参观完第50个工厂之后,我已经不再计数了。”赫辛根对《环球企业家》说,这让他有机会去真正了解底层员工的心声,并发现问题所在。尽管初来乍到,赫辛根却已是当时最了解这家公司的人—他在长达6个月不间断的“环球旅行”中收获颇丰。
赫辛根随后发起了一项针对美洲项目的调查。一个以公司最优秀的技术、运营专家构成的团队专门负责研究蒂森克虏伯的问题所在。赫辛根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是技术问题,你们能否找出解决方案”。但赫辛根最终得到的报告却显示美洲项目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它麻烦不断,且亏损日益增大。
随即,赫辛根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出售美洲项目。2011年底,蒂森克虏伯在艾森总部宣布将于2013年9月底之前出售两家钢厂的计划。尽管此前它曾专注钢铁业长达2个世纪之久,也代表公司几乎全部的荣誉,毕竟美洲钢铁项目是全球最为先进的钢铁工厂之一,亦是该公司史上最大的投资计划。“但必须把它和我们的业务脱离开。”赫辛根言辞坚定地说。
出售钢厂并非易事,尤其是在行业低迷的当下。在铁矿石行业中,没有人会在回忆2014年时带有丝毫欢喜。大量新的供给冲击了市场,导致供过于求,铁矿石这种炼钢原料的价格全年下跌50%,成为大宗商品中表现最差的一种。
但毋庸置疑,钢铁业仍十分重要。从摩天大楼到洗衣机,钢铁是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材料。然而,重要却并不意味着高收益。
事实上,钢铁业利润之微薄,以至于较之于航空业,后者亦能成为高收益之典范。这一点在欧洲体现得最为明显,那里的钢铁制造者饱受折磨。中国尽管工业迅猛发展,但如今钢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老生常谈的莫过于产能过剩问题—尽管中国建筑产业需求疲软,中国的钢产量还是不断增长,从而将更多中国产钢材推向国际市场。2014年,中国钢材出口量大幅增加,同比增长50%,增至9380万吨,但炼钢厂销售钢铁的价格平均每吨却下跌了13%。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相信,中国的钢材产量和消耗量可能将在今年见顶。其他人则更加悲观。美奇金投资咨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称,建筑热潮导致中国很多地区住房供应过剩,中国住宅类房地产行业增长放缓,可能导致今年钢铁产量下滑10%。
放眼全球,即使安塞乐米塔尔这样规模效应与成本有效兼得的公司,也不得不忙于削减员工,并关闭钢厂,此类巨头未必会对在美国或巴西新增一个工厂有兴趣。而另一些钢铁公司已经声明他们没有购买上述两家工厂的计划。中国的宝钢和武钢是可能的候选人,他们已经对投资巴西板坯厂表达了兴趣,但究竟能否取得实质进展尚难确定—中国的钢铁业正在经历近十年来最为严酷的寒冬,且他们此前少有海外收购的经验。
归根究底,美洲项目的悲剧性在于它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启动,现在它又被迫在另一个错误的时间以卖出作为结束。
可以预料的是,除非价格足够低,否则没人会出手。在经历漫长的讨价还价后,2014年初,老冤家安赛乐米塔尔和新日铁住金(NSSMC,世界第三大钢铁公司)组成的联合体终于以15.5亿美元获得蒂森克虏伯位于阿拉巴马州的轧钢厂。两者同时达成一项协议,在未来的六年内重新掌管的美国工厂将每年从蒂森克虏伯巴西工厂购买200万吨钢坯。从清除债务和止损的角度,这么做是值得的。但对于终其一生从事钢铁业的蒂森克虏伯员工来说,这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时至今日,巴西钢坯厂至今尚未找到合适的买家,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售价将大大低于当初的投资。
寻找
这注定是赔本的买卖。但当时留给赫辛根的选项并不多,因为钢铁业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眼前这个低谷周期可能会久于大多数人的想象。蒂森克虏伯的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在巴西和美国的两家钢厂绝对不能获得像该公司在电梯及其他业务方面同样的资本回报。“所以这是一个战略的决策,不是运营层面上的问题。”赫辛根如是说。
但奇迹竟然发生了。最新的消息显示,蒂森克虏伯已经在最近的2014财年成功实现巴西钢厂的扭亏。随即就有人质疑卖钢厂的决定,“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还要卖?”赫辛根做出同样回答:“你不要把战略和运营弄混了。”
决定抛售美洲两座钢厂已是赫辛根所推动变革的第二步了。事实上,2011年5月,蒂森克虏伯率先为其欧洲的不锈钢业务以及造船板块的一部分找到了新东家。这些行业同样在产能过剩的烦恼中苦苦挣扎。剥离出去的这部分资产价值百亿欧元,相当于这家公司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场涉及3万5千名工人的业务剥离,源于赫辛根与董事会对现有业务组合的观察与测试。其判断标准是,未来有无发展空间,能否持续;能否取得业内数一数二的业绩。这种测试被赫辛根称为“永远不可能停止的工作”。
赫辛根显然抛弃了德国公司以往惯常采用的渐进式改革,他希望用大刀阔斧的方式带来立竿见影的成效。难以想象的是在其铁腕下,这家此前全球第五大钢铁公司已经将自己的钢铁业务削减一半,压缩至目前只占该集团业务收入的20%,这一成绩实属不易,要知道最高时钢铁业务曾占集团收入超过60%。
同时,他还将原有的8个业务单元缩减至6个,并推出一项名为“挤压(Impact)”的全面降本增效计划,并打算用三年时间,总共削减23.6亿欧元的成本。赫辛根最关心的经济指标是公司的现金流,其次是盈利、净收入、业务增长速度、员工的满意度,以及员工工作的投入度。他解释称:“等公司度过转型期,刚才的排序可能会有一个变化”。
几乎从一开始,赫辛根便在寻找新的起点。最初,他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发现人才上。赫辛根利用刚进公司时那段访问时间,参观了比任何前任都多的工厂。他非常注意察言观色,并经常在参观途中突然造访员工餐厅和公寓,并提出要跟他们坐下来聊聊天,这常常令工厂负责人措手不及。
“蒂森克虏伯有很多拥有才智的聪明人。”赫辛根说。这家公司一直拥有杰出的工程师和几乎无所不能的技术研发团队。过去两个世纪中,蒂森克虏伯人在鲁尔河谷一直从事钢铁生产,这里数代人都靠钢厂谋生。高耸的烟囱随处可见,厂房星罗棋布。当德国在1870年、1914年和 1939年擂响战鼓时,正是他们为普鲁士、后为德意志帝国供应了野战炮、坦克、炮弹和战舰装甲钢板。从某种程度上,自那时起,蒂森克虏伯的工程师便借助自己对金属的理解从事着最为尖端的创造。他们是巨型机器的拥趸,除了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武器之一古斯塔夫巨炮,这家公司还制造过当时全球最大的挖掘机、下潜最深的潜艇、直径最宽的射电望远镜。幸运的是,他们不是一群只会炼铁的平凡工人。
正是在与这些“聪明人”的访谈中,赫辛根才找到了蒂森克虏伯除钢铁以外能够成为未来支柱的产业。它们都在各自细分领域如执牛耳,但此前在集团并不被那么重视。例如电梯业务、风力发电机和汽车行业的机械零部件,还有在材料和化工领域的关键设备等。
以汽车业务为例,目前10辆高端轿车中有9辆配置了来自蒂森克虏伯的零部件。其电梯公司研制的双子电梯(TWIN?)系统掀起了一场电梯界的革命:两个独立的轿厢能够在同一个井道内运行;现有10大风能设备制造商中有9个使用蒂森克虏伯的回转支承;蒂森克虏伯设计和施工建设的上海磁浮列车项目是世界第一条商业运营的磁悬浮专线,其能够在八分钟内穿越上海市区;该公司使用港口建设中常用的钢板桩墙来修复防洪堤,用此技术水城威尼斯得以被拯救。
“In Car”项目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由汽车供应商在不依靠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情况下,独立开发的提高汽车效率的解决方案。蒂森克虏伯的方案能使涉及组件的重量减轻一半,成本降低20%
上任第一年,赫辛根就在研发方面追加了10%的投入。而在最近的三年中,用于研发领域总的投资金额增加了38%
蒂森克虏伯电梯公司研制的双子电梯(TWIN?)系统掀起了一场电梯界的革命:两个独立的轿厢能够在同一个井道内运行蒂森克虏伯最近的一项发明也再次颠覆人类的想象。2014年年底,该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MULTI的电梯。它是世界上第一台由电磁系统驱动,无需钢缆拽引,还能横向移动的电梯。这至少意味着人类的摩天大楼还能建得更高。一位电梯业工程师难掩自己的激动,他在一篇公开的博客上写到:“你还记得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的童话《查理和大玻璃升降机》吗?蒂森克虏伯把它变成了现实。”
但赫辛根发现困扰公司内部这些天才工程师的是“他们并不清楚公司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随后,他正式宣布要将公司变成一家多元化的科技及工程集团。他重点倚靠的业务板块将是机械零部件、电梯、工业解决方案和材料服务,而钢铁位列最后。
为了转型,赫辛根毫不吝惜对未来的业务进行投入,即使钢铁项目每天都在巨额亏损。在上任第一年,他就在研发方面追加了10%的投入。而在最近的三年中,用于研发领域总的投资金额增加了38%。赫辛根还投入45亿欧元用于开设新工厂和扩建那些有竞争力的旧工厂。
这些努力已见成效。赫辛根在位于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全新汽车转向轴工厂里骄傲地告诉《环球企业家》,蒂森克虏伯已经不再依赖钢铁了。他把目光投向眼前布满机器手臂的崭新生产线,紧跟着说:“很庆幸我们那时做了正确的决定。”
过去3年,赫辛根对新兴市场做出的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他格外钟情于中国—每年来中国的次数超过除总部以外的所有国家。自2011年起,蒂森克虏伯仅在中国完成的投资额就已超过4亿欧元,且对该地区的研发投入每年以10%的速度保持增长。它在中国新建了4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并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区总部。至此,蒂森克虏伯在中国的工厂数量已达到20家,大多数用于制造机械零部件,涉及汽车、重型机械和风力发电机。还有一部分是增长迅猛的电梯业务—中国工厂已经完成大规模扩建。
它已在中国雇佣了1.6万名员工,上一财年其在中国的销售额是22亿欧元。赫辛根指着一张用红色圆点标注了其业务布局的中国地图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把电梯的服务机构加上去了,那样整个地图就都是红色了。”
刚刚投入使用的蒂森克虏伯普利斯坦(Bilstein)汽车零部件(上海)工厂正是其开拓疆域的新作。该工厂用于制造汽车转向和减震系统,每年可提供75万支转向轴和180万个减震器。厂址距离其合作伙伴大众汽车(Volkswagen)位于上海的合资工厂仅有60公里,这甚至远比其在欧洲的工厂更加贴近客户。它与现代汽车(Hyundai)、标致雪铁龙(PSA)以及来自中国的长城汽车(Great Wall Motor)保持业务往来,又刚刚赢得了奇瑞(Chery)和吉利(Geely)的芳心。
为了紧贴中国市场,这家工厂覆盖了转向和减震系统的全产业链,并建立了本地的研发中心,有70名工程师专门为当地市场开发产品。而在几年前,还没有类似的公司愿意把研发中心搬到中国。蒂森克虏伯机械零部件技术业务单元管理委员会主席卡斯腾·克劳斯(Karsten Kroos)告诉《环球企业家》:“我们会把大量精力用来关注中端市场,这种规模效应对眼下的蒂森克虏伯非常重要。”
类似汽车避震器和转向系统这种高技术壁垒但却供不应求的产品正是赫辛根极为偏爱的领域。他解释说,如果把这两样东西拼起来,你会发现这就几乎构成了一个汽车底盘。为了迎战这一价值亿万美元的产业,蒂森克虏伯最近推出了一项叫做“In Car”的创新计划。它联合了旗下三大业务板块、投入100名工程师耗时3年研发出40个新的有关汽车行业的零部件产品,涵盖动力系统、车身、底盘和转向系统。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由汽车供应商在不依靠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情况下,独立开发的提高汽车效率的解决方案。蒂森克虏伯的方案能使涉及组件的重量减轻一半,成本降低20%。
值得一提的是,赫辛根并非要简单地放弃钢铁。他认为无论是新兴行业,还是传统行业,机遇都依然存在。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并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优化产业组合是永远不会停息的。”赫辛根说。目前,蒂森克虏伯在欧洲依然拥有1200万吨钢铁产能,但一些用于提升技术的改造已经悄然展开。赫辛根解释称,这绝不是扩大产能,而是加强对高等级、高强度钢的投入,最终驱动公司从普通钢到创新材料的转型。例如该公司正在生产一种“三明治板”—在很薄的两层钢板中间加上一层特殊塑料,这种复合型的材料可以大幅减轻车身的重量。这代表着蒂森克虏伯钢铁业的未来。
内治
最初,当赫辛根成为蒂森克虏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时,几乎没有多少人看好他。当时业界将这一职位形容为“整个欧洲工商界最为烫手的山芋”,并认为蒂森克虏伯可能会像当时的通用汽车(GM)那样等待破产,或者像诺基亚(nokia)那样被瓜分和吞并。批评者认为,美洲项目的投资失败以及各类公司丑闻的根源都是蒂森克虏伯长久以来等级森严的“老人体制”的恶果。因为“在这种管理体制下,盲目忠心似乎比业务的成功更加重要。”
甚至有人将矛头直指当时已99岁高龄的贝托尔德·贝茨,称他为老人政治的标志。贝托尔德·贝茨曾用60年的时间将自己的名字与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画上等号。直到辞世前几天,他仍然每天前往蒂森克虏伯总部的办公室工作,并表示:“只要我的头脑还清醒,就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而受困于此,蒂森克虏伯此前的运转方式亦鲜有人知晓。但伴随着赫辛根的到来,改变急剧发生。此前蒂森克虏伯公司执行委员会一半的成员(3人)被解聘,这显然有利于赫辛根伸展拳脚。
赫辛根并非要简单地放弃钢铁。他认为无论是新兴行业,还是传统行业,机遇都依然存在。但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并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优化产业组合是永远不会停息的。”赫辛根说
不过,当赫辛根初到公司时,他仍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当时的董事会成员极少就公司的基本战略问题去讨论,去贡献智慧,而是每天面对着成堆的文件,签字表示赞同或者反对,如此而已。蒂森克虏伯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田坤(Tilo Quink)告诉《环球企业家》,以往的错误来自不透明,“很多事情都是凭关系来做,都是藏起来的。你根本不知道一项投资是怎么来决定的。”田坤于20年前就加入蒂森克虏伯了,他在不同的分公司担任过大大小小的职务,包括以前的设备制造、原材料、贸易以及钢铁等。“当赫辛根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感慨地说。
在他看来,赫辛根作为一个“空降兵”可以不去顾及原有的公司政治和人际关系,因此可以更加客观地做分析和评判。但更重要的是,赫辛根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大公司,在一个人人担心犯错而犹豫作出决定的时刻,他迅速做了一些极为大胆的决策。而赫辛根之所以敢于放手一搏,是因为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用自己的言行赢得了尊重和信任。
走马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公司所有的领导成员专门召集到一个地方,“我们坐下来,可以说是恳谈”。他希望首先让领导层的管理风格做出改变。他告诫说,作为公司的领导者应该和员工一起就工作内容进行沟通,而且要对此有自己的贡献,不仅仅简单地打一个勾或者打一个叉。事实上,自上年11月被任命到次年5月宣布改革计划,赫辛根只用半年时间就在内部树立了威信。在很多会议上,他鼓励所有人踊跃发言,并且可以激烈地争论,而不是按照以前等级鲜明的方式结束会议。赫辛根想让下属们知道,“勇于在公司里表达自己的见解不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
他时常将最关键的会议地点特意选在一个安静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属于蒂森克虏伯公司,但距离总部有好几公里。这让与会者颇感新鲜。赫辛根说,“既然要从管理的哲学开始改变,那么我从一开始就要发出一个不同的信号。”图书馆会议成为蒂森克虏伯公司内部的一个长效机制。一旦遇到有关公司战略性的问题,董事会成员就会钻进图书馆,在那里持续讨论好几个小时,一开始是集思广益,最后统一意见,做出决策。在取得领导团队的信任后,赫辛根开始用走动式管理争取更多的底层员工。
一只不大的黑色皮质旅行箱是赫辛根过去四年最熟悉的物件。他没有助理,时常坚持独自出差。他经常一人从机场打车到酒店,住的酒店也很普通,从无特殊要求。他把行程安排得很满,总是希望能多拜访一家工厂或一位客户。这让他的每次外出几乎都变成了环球飞行。他不喜欢高高在上,也极少参加追逐名誉的俱乐部活动和颁奖晚会。
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位于美洲的钢铁工厂横亘了两座大陆。它的一半在巴西东南部里约热内卢风景秀美的圣克鲁斯湾。最终,这些钢铁将在附近的汽车工厂里华丽变身成为奔驰C级轿车的车门或者宝马X7的发动机盖等配件
田坤与之曾有过难忘的经历,他第一次在中国接待赫辛根来访时,为其租了一辆奔驰S级轿车。赫辛根却把它让给了其他董事会成员,他自己跳上一辆满载员工的大巴车。他后来告诉田坤,访问非常成功,但下次不要再单独为他租车了,因为“我愿意和我的员工坐在一辆车上”。
在访问工厂的过程中,赫辛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兴奋异常的员工。因为对多数人来说,这是过去十年中首次有董事会成员与其沟通。“你可以想象过去他们心中的恐惧。”赫辛根说。而此前公司等级森严、层级繁冗,如此才导致决策层与一线员工几乎无法沟通。“但当你真诚地与他们交流,你会发现他们都有非常好的点子。”蒂森克虏伯的多元化战略即源于赫辛根与员工的沟通。而这种沟通也让赫辛根做决策时信心倍增,“当我做出一个决定时,我会知道在那个地方一定有人会支持我”。
他总是鼓励下属说真话。在巴西一家工厂访问时,赫辛根在参观设备期间提出想立即听到项目情况的汇报。当时工厂的负责人有些紧张,对方说:“我们明天有一个非常正式的项目汇报会已经准备好了,你是想听明天的会议,还是听我们实际要说的”。赫辛根至今认为那次访问极具价值,因为在了解到最真实的困难和情况后,他立即对那个项目做出了调整,这最终让公司节省了4亿欧元的开支。
为了聆听员工心声,赫辛根建立了CEO电子邮件直通车,还组建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叫做与赫辛根面对面(Direct toHiesinger),员工可以匿名提意见。在赫辛根的力推之下,蒂森克虏伯刚刚完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为详尽的员工调查,分布在71个国家的超过15万名员工每人回答了有关14个主题共计75个问题,如创新、协作和操作流程等。
为了统一行动,公司的每一面墙上都贴着此次员工调查的红色海报,上面四个大字格外显眼——“实话实说!”。办公室的前台墙壁上则用蒂森克虏伯所在71个国家的文字书写的单词“我们”,用来提醒所有员工都是一家人。收获批评亦在所难免,但他异常宽容。“我们拥有16万员工,如果没有批评那将非常可怕。”赫辛根说。
而最令他感到开心的是当四年前发起改革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员工都持怀疑态度,但四年后,每个人都发现,蒂森克虏伯真的变了。它正在接近成功,公司的利润也出现罕见的明显改善。它三年来已首度实现盈利,这是战略转型中的里程碑事件。2013/2014财年,集团实现净利润1.95亿欧元;应付股东净利润达到2.1亿欧元;对应每股收益达0.38欧元。
业绩提升背后的三大驱动力可概况为绩效的提升,工业产品相关业务的强劲增长,亏损的消除以及从资产剥离和重组中获得的收益。“我们已经离开了重症监护病房,正在从麻醉中苏醒。”赫辛根在一次讲话中做出这样的比喻。
巴西项目曾得到巴西本国前所未有的重视。时任巴西总统卢拉(Lula)号召5万名当地工人参与修建该国15年来数额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但不幸的是它令蒂森克虏伯深陷泥潭
蒂森克虏伯的新战略也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股价已是其推行变革之初的两倍,蒂森克虏伯也成为去年德国DAX指数上表现最佳的前三位公司之一。一些曾经批评蒂森克虏伯在金融危机期间表现糟糕的人转而发出不吝辞藻的赞扬,称赫辛根即将完成一场“史诗般的转型”。同时,蒂森克虏伯新任监事会主席乌尔里希·莱纳(Ulrich Lehner)曾希望这位55岁的工程师在2015年合同到期后选择留下,以完成蒂森克虏伯的复兴使命。蒂森克虏伯集团监事会已决定将其任期延长至2020年9月。
棋至中盘,赫辛根仍需特别警惕全球市场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例如中国一些二线城市亦开始商讨出台限制购买汽车的法令,这可能影响到公司的业绩。接下来,他还要在继续优化组合业务和不断降低成本的同时,尽快为巴西钢厂找到合适的买家。如果它再能卖个好价钱,那赫辛根就太走运了。
当被问及他在蒂森克虏伯历史上将留下一个怎样的印记时,赫辛根对《环球企业家》说:“现在还很难描述。因为我们这一页还是空的。”他认为此前4年,自己对负债累累和缺失战略方向的公司理清了发展方向,并将其扭亏为盈,但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其看来,将蒂森克虏伯变为一家很赚钱的公司并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转变全公司员工的工作方式,让其成为一家能够吸引到更好人才的公司。什么样的人才是他想要的?以下是赫辛根的答案。“当我和CFO聊天的时候,我问他我们到底要雇什么样的人?他说是那些既优秀又勇敢的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