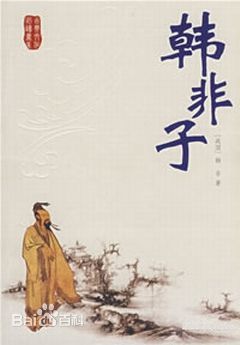“以道佐人主”章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谓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段及下段文字文意相承,似乎可视为一个部分,它们的内容都涉及到了“兵”的问题。
历来的绝大多数注家都将此章中的“兵”解为战事,但是,我的理解与他们俱不相同。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居,楚棘生之。
世传本此句为“以道佐人主者”易引起歧义,而帛书文义显豁。依帛书本,这里显然不是说有一个如范蠡、张良、魏征、刘伯温一样的道家高人在辅佐“人主”,而是说“人主”依靠“道”来治理天下。
兵,基本上所有的注家都将其解为战事。从文字角度而言,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唯一的一种可能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在我看来,还是面临着如下的问题。
首先,它似乎暗示我们不应该靠武力去征伐他国,但它背后隐含着一种大国思维,它需要预设我们已经足够强大到不会受到外来的武力侵袭。注家们多将它看成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乱象的理论上的否定,但这种否定过于理想化,且并不具有实际的解决可能。
其次,这种理解使得《老子》中的论说立场发生了混乱。在他处,老子都将天下作为一个整体,从治理这个作为一个整体的天下的立场而进行的论说。而此处,若作如上解,将兵解为战事,则是将人主置于天下的一个部分的人主的立场而进行的论说。
最后,这种理解,使得本段内容与前后文在意义上都有所隔膜。既不能承前文“取天下”之主旨,又不能启后文“果而不强”之申发。
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我认为,是由于将“兵”理解为对外的战事所造成的。
兵,自然是可以被理解为战事的,这是有它更通用的义项所引申出来的。它更通用的义项是兵卒、军队,如:《左传·襄公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杜预注:“徒步,步兵。”由这个通用的义项向着对外的方向发展,可以理解为战事,而如果由这个通用的义项向着对内的方向发展,则完全可以理解为具有军队暗示的国家的强力工具。我个人,不同于其他注家,倾向于按后者进行理解,其原因在于:一、这可以解决上面所提出的论说立场混乱的问题,这使得《老子》能保持一个相对一致的“取天下”的立场;二、与上章的“去甚”能够构成有效的理论衔接,上章老子通过否定“将欲取天下而为之”提出了“去甚”的原则要求,此章则落实到以“兵”为例举、为代表的“毋以取强焉”的主要规范;三、沈善增先生曾就德经与道经的对应关系做过研究,在他的结论中,此章对应的德经部分为“民之不畏畏”章。我无意以此假设,虽然我认为这一假设具有相当的合理的可能性,作为我的观点的证据,但若以这两章的内容来比较,确实会使得将“兵”理解为对内指向的国家强力工具这一理解显得更加合理,尽管沈先生将这两章的关联理解为“德章论述君主在国内不要事实强权政治,道章进一步申论在国与国关系中。”
“强”可理解为逞强,亦可理解为硬要如何,非如何不可。由于后一种理解更能体现对“人主”主观意识的要求,故取此种解释。
“师之所居,楚棘生之。”我认为是对“其事好还”的补充说明。
世传本中尚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帛书本,景龙、敦煌与道藏龙兴碑本均无此二句。故不采。
此段可通译为:
用“道”来指导君主,不以国家的强力工具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天下,因为这种做法很容易招致还报。(如)军旅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
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
这里的善者,我不认为按照普遍意义取其好义是恰当的。根据语境,承接前文“取天下”及“人主”之论,我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善政。但需要解释的是,这里的善政,侧重于为政所带来的局面,而非为政的具体措施。这样,即能与“果”相协调。
果,有成就、实现义。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这里的果,根据其与后文“毋以取强焉”的对应关系,我认为,应当是指“自然”而非“强”的结果,即:善政的局面是相对于“强”的“自然”的结果。当然,这里的自然的结果不是指完全听凭的不为,而是因循天道而制定的为政原则之为。以此原则,就如在《老子》中多次表述的,侯王、人主,应当将自己摆在弱而非强的位置。所以,此句的“强”,既可承接上句理解为君王以国家的强力工具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天下,亦可淡化上句兵的影响,更加抽象化的理解为君王把自己摆在强者的位置强加自己的意图。
而已,助词,表示仅止于此。犹罢了。如:《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此句可通译为:
善政(为政带来的好的局面),只是自然的结果,不是君王把自己摆在强者的位置强加自己的意图能取得的。
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此三句次序与世传本不同。世传本为矜、伐、骄,逻辑关系较为错乱,帛书所体现的要求体现了一种逻辑上的渐次具体化,义略胜。
此处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果”与“勿如何”的关系。有些注家认为“勿如何”是对于取得了“果”之后所应抱有的态度。这种理解从文字上来看,仅就这部分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整体论说的节奏上则有所跳脱。此处的“勿如何”显然是从具体方法的层面来展开落实上句“毋以取强焉”的大原则。所以,将它们理解为就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次所作的论说显然更加合理。而若是按有些注家理解的,前一个原则层面是就何以能够达到“果”,而后一个方法层面是就达到“果”以后当如何,则显然是造成了问题和层次的错落。因此,我认为此处同样是在讲,是在进一步的从具体方法的层面上讲,何以能够达到“果”。
此处的而,作连词,用在主语、谓语之间以强调主语,含有“竟然”、“却”之意。《诗·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此句可通译为:
(为了得到善政的)结果,不要骄傲,不要自我推崇,不要自我夸耀。
果而毋得,已居,是谓果而不强。
所有注家都认为此句与上句是合在一起用来说“果而不强”的,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显然是因为“果而毋得”与前句的三个“果而毋(勿)”句式相同。但这一结论的得出也仅限于形式上的理由。对内容稍加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此句是呼应“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强焉。”并再次强调且进一步的明确定义“果而不强”。
这里的得,我认为是有所得的意思,指人主不要为了自己的有所得而强行施为。所以,“毋得”是对于上面的具体方法的重新提炼,重新提炼到为政的主观意识层面。
已:有停止义,如:《诗·郑风·风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郑玄 笺:“已,止也。”;还有完毕义,如:《战国策·齐策二》:“左右惡 張儀 ,曰:‘ 儀 事先王不忠。’言未已, 齊 讓又至。”
居:语助词,如:《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所以,我把“已居”意译为:这样放才可以。
此句可通译为:
(为了到善政的)结果,不要以自己的有所得为目的,这样放才可以,这就叫“果而不强”(为了得到善政的结果,不把自己摆在强者的位置强加自己的意图)。
物壮而老,是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句似乎突兀,但如果理解老子的伦说方式则很容易理解。此处又回到形而上道是为了在理论高度论证前述“治道”的正确。从反面,即“物壮而老”的“不道”的角度,来阐说“不强”的重要意义。
“老”与“壮”相对可作为“壮”的反义词,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师直为壮,曲为老”,有“衰落”义。
而:就,在此可理解为前后两个情况时间相距很近,而又带有因果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不道”,我认为,是呼应本文的中心,即上句的“果而不强”。所欲表述的是“道”的“不强”之“弱”,即“弱也者,道之用也。”
此句可通译为:
凡事物刚到壮盛之时就走向衰老,这就表明它们不合于道(之守弱的特性)。不合于道是必早夭。
章节通释:
用“道”来指导君主,不以国家的强力工具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天下,因为这种做法很容易招致还报。(如)军旅驻扎的地方,荆棘丛生。
善政(为政带来的好的局面),只是自然的结果,不是君王把自己摆在强者的位置强加自己的意图能取得的。
(为了得到善政的)结果,不要骄傲,不要自我推崇,不要自我夸耀。
(为了到善政的)结果,不要以自己的有所得为目的,这样放才可以,这就叫“果而不强”(为了得到善政的结果,不把自己摆在强者的位置强加自己的意图)。
凡事物刚到壮盛之时就走向衰老,这就表明它们不合于道(之守弱的特性)。不合于道是必早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