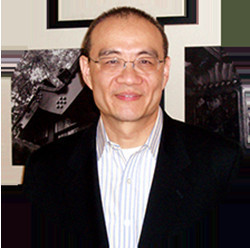最纯最美的风光固然难忘,但草原的美丽和雪山的圣洁并非河南独有。此刻让我最为难忘的还是河南的人。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里的人说起吧,从这群“蒙古族”人说起。
说起蒙古人,我的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弯刀和战马。七百年前,一群成吉思汗的子孙就用书写了一段属于他们的血雨腥风。无情的数字诉说着三千万平方公里欧亚大陆上的一座座尸山、一条条血河;从中原大地到江南水乡,从天山南北到藏北高原,蒙古帝国旗帜迎风猎猎飘扬;西辽、西夏、花剌子模、钦察……一个个曾经的帝国在带血的苏鲁锭长枪下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从朝鲜半岛到两河流域,从东海之滨到多瑙河畔,矮小的蒙古驿马尽情驰骋;马蹄声过后,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已不见踪影,“无所不能”的罗马教皇只能在耶稣像前瑟瑟发抖、恶毒而又无阻地诅咒着这群野蛮的长生天子孙,祈祷着这烈火般的“黄祸”别再熔化掉神圣的圣经。野狼般的利爪将西湖暖风熏染的醇酒美人和勾栏瓦肆里的轻歌曼舞撕得粉碎。
野蛮、凶残和征服是他们的标签,在黄金家族的字典里只有胜利者和战死者的存在。虽然华夏文明和中原歌舞曾用百年的时间将他们腐蚀,但这些被“朱重八”赶回草原的天骄后裔又重新用弯刀和战马捍卫了属于蒙古人的尊严。重要的是,他们从未被遗忘、被征服、被同化。然而,这里却是例外。
六百年前,一支傲视天下的无敌军队奉命来到大元帝国的边疆——青海,他们的任务是为了防止蔵域雪原的入侵,镇压这些野蛮愚昧的藏民。带着征服世界的骄傲,这群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以为此次出征与以往无数次的跨刀上马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再也没有看到熟悉的山峦,胯下的骏马也再没能踏上故乡的草原。他们被留在了这里,或者应该说是被遗忘,被遗忘在了这个如今名叫“河南”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在这片新的草原上生活了超过六百年,与他们曾经的敌人一起,而他们的帝国却早已灰飞烟灭。不只是世人忘记了他们黄金家族的血统,甚至是他们自己也记不起故乡的语言和文字。只有街边宣传牌上的蒙古文字和与小车共同驰骋的骏马诉说着这段逝去的历史。
当然他们的衣着也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化作了典型的藏服。
因为知道蒙古的文字是由吐蕃国师八思巴所创,为藏语蒙音。所以我曾不止一次询问这些说着藏语的当地人是否还识得这祖先的文字,是否还会说成吉思汗的话语,而所有的结果却是无一例外的“摇首否定”。
不止是蒙文,这里的居民们几乎连汉字都无人识得。
当我站在河南县城的大街上(其实所谓的县城不过是一个大型的牧民安置点,两条平直的大街串起了一栋栋新起的安置房)询问出租车是否愿意搭乘时,超过12辆的出租车根本无法听懂我所要去的地名,哪怕那是他们的神洞、圣湖,以及只是找一家能听懂汉语的住地。最后,是在一位正在西宁读书的回家大学生帮助下才找到能搭我前往的车辆。
这是一位朴实的蒙古汉子,曾经的家就在那神圣的“仙女洞”旁,只是因为近几年“退牧还草”的政策,才将家中的草地和牛羊卖掉,在县城里开起了出租车。略懂汉语的他,知道我要去仙女洞和圣湖之后,就将一双尚未读书的儿女也带上了车。
请记住这一双并不干净却充满了稚气的脸庞,请记住他们纯真的笑容。因为他们被人遗忘的姓氏和种族之下,是一颗充满了信仰和虔诚的灵魂。
我们要去的圣湖是坐落在河南大草原上的一个湖泊,晶莹透亮的湖面犹如一颗嵌在绿草之上的翠玉明镜,更因传说此湖可直通圣城拉萨并连接夏河,所以获得了当地牧民们的顶礼膜拜,称其为“圣湖”。
而仙女洞则是草原山谷中的一处天然岩洞,洞内幽深奇特,神秘莫测,因当地人对这些岩石形状和图案的崇拜,故被称为“仙女洞”。
两地相隔不远且距离河南县城也仅有50余公里,但道路及其艰难,一般的夏利出租车都不愿或是不敢走,只有这位师傅因为老家在那才愿前往,饶是如此也走了两个多小时。
其间,强烈的颠簸和剧烈的摇晃让我相信:在这里,走地图上标注的县级公路四个轮子的不如两个轮的,两个轮的不如四个蹄的。然而,这群已经忘记祖先语言的蒙古人却没有失去在草原上生存的本能。当系着安全带的我还在查看车门是否锁好以保证我不会被甩出车外时,司机师傅的一家三口却谈笑风生地吃着烤饼、喝着饮料。我觉得如果让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吃东西,我不是被噎死就是会让吃入鼻子里的东西呛死,真不知是不是蒙古人的血液里天生就有在马背上生存的抗颠簸基因,如若不然,这师傅也不敢大胆到此时还边吃东西边单手开车。
但这样的旅程却是值得的,因为眼前这片几乎未被开放的草原是如此的纯洁和美丽。
这一望无际的绿色中缀满了各色娇艳的野花,无论是整片镶红嵌黄的绿毯,还是一颗颗正沐浴阳光的蓝宝石、红玛瑙,都让人忍不住要在这片草原上奔跑。
跑累了,就放肆地躺下,躺在这上天遗漏的调色板中。闭上眼睛、去大口地呼吸自然界最纯粹的芳香;睁开眼睛,又发现眼前的一切如此迷人,舍不得再闭上双眸,怕身边的野花不见了,也怕蓝天间的白云飘走了。
不只是我,你看,那高原上特有的旱獭(当地人藏语称为哈拉)不也成双结对地观赏着这满地的鲜花吗?
还有这支隐身于这美丽花园中的,不知仅仅露出尖嘴的它是因为调皮而偷跑出来观花的,还是因为害羞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是不是电脑之前的您也与当日的我一样正深深地陶醉于这花的海洋之中?那还是先醒醒吧,因为而仙女洞已经到了。
在山脚下望去,山坡上五颜六色的经幡遮住了那神秘的洞口,只是这洞口破旧的小屋不知是何用途,也许是给朝圣者驻足的驿站吧。一条条写满了崇拜和敬意绸带在纯净的蓝天下,则用自己飘动的身影为我们绘出了如此美丽的图画。
迎着正午的阳光望去,这份灵动的飘逸在一道道美丽的光柱下更闪现出一份圣地应有的神秘。
打起手电走进洞中,便感到一种阴冷的气息笼罩四周,仅有的温暖来自于洞口外些许射入的阳光和这尊挂满了哈达的佛像。
这是一座完全未被开放的山洞,洞内没有一丝光源的存在,偶然可见的洞外阳光也只是将温暖带到卡在悬崖之上的洞口。绝大部分时间,我与一同进洞的司机一家只能依靠我手中那并不强烈的手电光缓缓前行,只是要十分留意潮湿且凹凸不平的地面。
仅仅依靠这微弱的光亮,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行走在湿滑且毫无规则的岩石上,不摔上一身泥似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我们就曾滑到了N次。听着小孩们摔疼后的哭声,我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因为在来此之前,司机师傅曾多次询问我是否带有足够的电筒或蜡烛,而自信走过无数山洞的我却对这份嘱咐不屑一顾,以为手中那支小小的手电就已足够。不想事到临头,不但自己一身脏泥,还连累年幼的孩童浑身疼痛。所以提醒有兴趣前往此洞探险的朋友,一定要带足照明的工具设备。
当然,如果这仅仅是一个布满钟乳石的溶洞,也许许多朋友会感到兴趣索然,因为这样的山洞在喀斯特地貌遍布的西南各省,不说随处可见,也是举不胜举。生在南国,长在壮乡的我当然也不会为这家乡便可见到的景色奔波数千公里。我来此洞的目的是它!
相信许多朋友都没看明白这眼前是什么,那我告诉你们:人的内脏!也许你现在会感到恶心,但请别急着将网页关掉,请看看当地人对这些代表着人体内脏的奇异石块的崇敬吧。
这位蒙古司机正小心翼翼地将附着在石块上的垃圾和泥土清理掉,身后扶着他的双手来自她的女儿。借助闪光灯和三脚架拍摄照片的瞬间,正碰到他儿子不小心滑倒了,一声呼叫引得前方的父女俩回首望去。
在他们看来,这些岩石上自然形成的内脏器官是来自上天的神灵,这个神秘的山洞正是神的内体,每一块山石和每一处凹陷都是神灵曾经降临人世的遗迹。所以几乎每到一处,这位虔诚的父亲都会带着年幼的儿女跪下磕头。
在洞中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双膝有多少次跪倒在冰冷的石面上,他们的前额有多少次亲吻着这一块块代表神圣的山岩。我只记得当我们走出洞中,我身上最脏的部分是摔得生疼的屁股,而他们的面颊则是布满了脏兮兮的泥土。
因认为拍摄这样的照片是对朝拜者和他们崇敬对象的不敬,所以我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直到他们出洞后,出于信仰和禁忌而不能原路返回,只好爬上这陡峭的山崖,我才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
要知道,他们并不是藏人,而是来自遥远漠北草原的蒙古人。虽然在信仰上,蒙古人也信奉藏传佛教,但无论是在呼伦贝尔的茫茫草原之上,还是在阿拉善盟的万里黄沙里,抑或是五当召同样迎风飘扬的经幡下,我都不曾看到如此虔诚的天骄后裔。
洞口的风马还在迎风飘荡,但似乎我的心思已不在静止的影像,那经幡中飘动的灵魂和信仰让我觉得恍如隔世。
出得洞外,我又在这信众们走出的转山道路前沉吟良久:路旁的尼玛堆见证了河南大草原的世事变迁,见证了仙女洞中奇幻神奇,也见证了这群蒙古人的虔诚和迷失。
而我们则是幸运的。无论是经历过多么艰难的岁月,承受过多么巨大的痛苦,我们的民族始终没有抛弃祖先留下的方块字。时至今日,仓颉留下的“横竖撇那”依然在我们的笔尖流淌,“阴阳上去”的四声语调从未在我们的口中消失。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国土曾被入侵,我们的先祖曾被奴役,但我们的文化从未消失,遗忘,征服。
这并非什么“愤青”的自傲,只是因为最近的中日“钓鱼岛”事件实在有些气人而想多说两句。如果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会被视为“愤青”的不满的话,那我毫不介意地做一名“愤青”。我们这历经五千年而不被征服的民族是不会容许这些跳梁小丑任意胡为的,如果他们敢于再起干戈,中华儿女又何惜这一腔热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