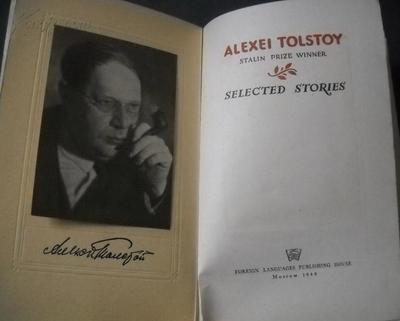再一次阅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对其中关于跳舞会的描写倍感亲切。从舞会的准备到舞会的盛大场面以及各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在大文豪的笔下惟妙惟肖的展现在我们眼前。在忘我的身临其境的阅读中,小说描写的跳舞会里的许多人和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的舞厅里,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本人摘抄的小说章节,出自周扬先生1956年翻译的版本,由于篇幅长度,分两次上传,希望与热爱跳舞又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共同欣赏。
(一)
刚用过饭,吉提就来了。她认得安娜卡列尼娜,但是不十分熟悉,她现在到她姊姊这里来,不免有几分恐惧,不知道这位人人称道的彼得堡社交界的贵妇人会怎样接待她。但是她却博得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欢喜——这一点她立刻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叹赏她的美丽和年青;吉提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感到自己不但受安娜的影响,而且爱慕她,就像一般年青的姑娘往往爱慕年长的已婚妇人一样。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贵妇人,也不像八岁大的小孩的母亲。如果不是她眼睛里有一种使吉提惊异而又倾倒的、严肃的、有时甚至忧愁的神情,凭着她的举动的灵活,精神的饱满,以及她脸上那种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眸里流露出来的蓬勃的生气,她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吉提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其实她却是生活在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世界,那世界是吉提所望尘莫及的。
饭后,当杜丽走到她自己房里去了的时候,安娜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她的哥哥面前去,他正在燃一支雪茄烟。
“斯季瓦,”她对他说,快活地使着眼色,一边替他画十字,一边目示着门边。“去吧,上帝保佑你。”(安娜此行的目的就是让她哥哥嫂子和好,摘抄者注。)
他扔下雪茄,明白了她的意思,就走到门外去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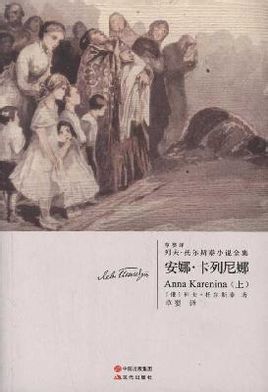
当斯捷潘走了的时候,她又回到沙发那里,她原来坐在那沙发上,被孩子们团团围住的。不知道是孩子们看出来他们的母亲喜欢这位姑母呢,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她身上感到了特殊的魅力,两个大点的孩子,而且像孩子们常有的情形一样,跟在大的后面的小的孩子们,从用餐前就一直缠住他们的新来的姑母,不肯离开她的身边。坐得挨近他们的姑母,抚摸她,握住她的纤细的手,吻她,玩弄她的指环,或者至少摸一摸她的裙襞,这在他们中间成了一种游戏了。
“来,来,像我们刚才那样坐,”安娜说,在她原来的地方坐下。
于是格里沙又把他的小脸伸进她的腋下,偎在她的衣服上,显出骄傲和幸福的神色。
“你们的跳舞会在什么时候开呢?”她问吉提。
“下星期,而且是一个盛大的跳舞会呢。那是一种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跳舞会。”
“哦,有什么时候都使人愉快的跳舞会吗?”安娜含着柔和的讥刺说。
“这是奇怪的,但是的确有。在波布立谢夫家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愉快的,在尼基丁家里也是一样,而在梅兹柯夫家里就总是沉闷的很。您没有注意到吗?”
“不,我的亲爱的,对我说已经没有什么使人愉快的跳舞会了,”安娜说,吉提在她的眼睛里探出了没有向她开放的那神秘世界。“我所觉得的,就是有些跳舞会比较不大沉闷,不大叫人厌倦而已。”
“您怎么会在跳舞会上感到沉闷呢?”
“我怎么不会在跳舞会上感到沉闷呢?”安娜问。
吉提觉察出来安娜知道会得到什么回答。
“因为您什么时候都比旁的人美丽呀。”
安娜是善于红脸的。她微微泛上红晕说:
“第一,从来也没有这种事;第二,即使这样,那对于我又有什么用呢?”
“您来参加这次跳舞会吗?”吉提问。
“我想免不了要去的。拿去吧,”她对达尼亚说,她正在想把那宽松的戒指从她姑母的雪白的、尖细的手指上拉下。
“我真高兴您去呀。我真想在跳舞会上看见您呢。”
“那么,要是我一定得去的话,我想到这会使您快乐,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格里沙,别拉我的头发,它已经够乱了呢,”她说,理了理格里沙正在玩弄着的一束散乱了的头发。
“我想象您赴跳舞会是穿淡紫色的衣裳吧?”
“为什么一定穿淡紫色?”安娜微笑着问。“哦,孩子们,快去,快去。你们听见了没有?古里小姐在叫你们去喝茶哩,”她说,把小孩们从她身边拉开,打发他们到餐室去了。
“不过我知道您为什么想拉我去参加跳舞会。您对于这次的跳舞会抱着很大的期望,您要所有人都在场,所有人都去参与呢。”
“您怎么知道的?是呀。”
“呵!您正在一个多么幸福的年龄,”安娜继续说。“我记得而且知道那像瑞士的山上的雾一般的蔚蓝的烟霭,那烟霭遮蔽了童年刚要终结的那幸福时代的一切,那幸福和欢乐的广大的世界渐渐变成了一条愈来愈窄的道路,而走进这条窄路是又快乐又惊惶的,虽然它好像辉煌灿烂...谁没有经过这个呢?”
吉提微笑着,默不作声。“但是她是怎样经过这个的呢?我真愿意知道她的全部恋爱史呵!”吉提想着,记起了她丈夫阿列克赛的不风雅的容貌。
“我知道一件事。斯季瓦告诉我了,我祝贺您。我非常喜欢他呢,”安娜继续说。“我在火车站遇见了渥伦斯基。”
“呵,他到了那里吗?”吉提问,脸涨红了。“斯季瓦对您说了些什么?”
“斯季瓦全说给我听了。我真高兴...我昨天是和渥伦斯基的母亲同车来的,”她继续说:“他母亲不停地讲着他。他是她的娇子哩。我知道母亲们有多么偏心,但是...”
“她母亲对您说了些什么?”
“呵,多得很呢!我知道他是她的娇子,但还是可以看出他是何等的豪迈呵...比方说,她告诉我他要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让给他哥哥,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做出了惊人的事,他从水里救起了一个女人。总而言之,他简直是一位英雄呢,”安娜说,微笑着,想起他在火车站上所给出的两百卢布。
但是她没有提起那两百卢布。不知怎的,她想起这个来就不愉快。她总觉得那好像和她有点什么关系,那是不应当有的。
“她再三要我去看她,”安娜继续说。“我也很高兴明天去看看这位老夫人呢。斯季瓦在杜丽房里耽了这么久,谢谢上帝安娜加上说,改变了话题,就立起身来,在吉提看来,她心中好像有什么不快似的。
“不,我第一!不,我!”孩子们叫嚷着,他们刚喝完了茶,又跑回他们的安娜姑母这里来了。
“大家一起!”安娜说,于是她笑着跑上去迎接他们,抱起来回旋这一群欢天喜地叫着、闹着的小孩。(摘自小说第二十章)
杜丽在大人们用茶的时候才走出她的房间。斯捷潘没有出来。他一定是从另外的门走出了他妻子的房间。“我怕你住在楼上冷,”杜丽向安娜说,“我要替你搬到楼下来,这样我们就更挨近了。”
“呵,请不要为了我麻烦吧,”安娜回答,凝视着杜丽的面孔,竭力想要探出有没有和解。
“你住在这儿,光线太亮了一点哩,”她的嫂嫂回答。
“我敢对你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睡得像土拨鼠一样呢。”
“在谈什么问题?”斯捷潘从他书房里走出来,向他的妻子这样问。
由他的声调,吉提和安娜两人都听出来已经和解了。
“我要把安娜搬到楼下来,但是我们必须挂起窗帘。谁也不会做,我还得亲自动手,”杜丽向他回答。
“天晓得,他们完全和好了没有呢,”安娜听了那种冷淡和安静的声调,这样想。
“呵,得了,杜丽,总是找麻烦,”她丈夫回答。“哦,要是你愿意的话,一切都由我去做好了...”
“是的,他们一定和好了,”安娜想。
“我知道你是怎样做法的,”杜丽回答。“你吩咐马特维去做那做不到的事,自己倒跑开去了,而他会弄得一团糟,”杜丽这么说的时候,她的嘴角上刻画出了她那种素常的、讥讽的微笑。
“完完全全和解了,完完全全,”安娜想,“谢谢上帝!”于是庆幸着和解是由她一手造成的,她走到杜丽面前去,吻了吻她。
“没有那么回事。你为什么老瞧不起我和马特维呢?”斯捷潘含着轻微的笑意向他妻子说。
那一整晚,杜丽,像平时一样,对她的丈夫说话时声调里总带点讥讽,而斯捷潘是满足和快活的,但也不至于看上去好像他得到饶恕以后就忘掉了他的罪过。
在九点半钟,斯捷潘家里围着茶桌举行的特别欢乐和愉快的家庭谈话,被一桩表面看来很简单、但不知怎的却使大家都觉得奇怪的事情所扰乱了。谈到彼得堡的共同的熟人,安娜急忙地立起身来。
“我的照片簿里有她的照片,”她说;“我也顺便把我的谢廖沙给你们看看呢,”她加上说,露出母性的夸耀的微笑。
近十点钟,她在平时正和她儿子道晚安,并且常在赴跳舞会之前先去亲自招呼他睡了,现在她竟离开他这么远,她感觉得难过;不论他们在谈什么,她的心总飞回到她的卷发的谢廖沙那里。她渴望着看看他的照片,谈谈他。抓住第一个口实,她站起身来,迈着轻快的、稳定的步伐走去拿她的照片簿。通到她房间的楼梯正对着大门的温暖的大楼梯口。
恰巧在她离开客厅的时候,铃声从门廊传来。
“这会是什么人呢?”杜丽说。
“来接我还嫌早,来看旁的人可又太迟了,”吉提说。
“一定是什么人送公文来了,”斯捷潘插嘴说。当安娜走过楼梯顶的时候,一个仆人跑来通报有客人来,而客人自己就站在灯光下。安娜朝下面一望,立刻认出来渥伦斯基,一种快乐和恐怖交并的奇异的感情使她的心微微一动。他站定了,没有脱下他的外衣,从他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来。恰好在她走到楼梯的中途的一霎那,他抬起眼睛,看见了她,他面部的表情罩上了一层困惑和惊慌的神色。她微微点了点头,就走过去,听到斯捷潘在她身后大声叫他进来,以及渥伦斯基用平静的、柔和的、沉着的声调谢绝。
当安娜拿着照片簿转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斯捷潘告诉他们,他是来问他们明天请一位刚到的名人吃法的事的。
“他怎样也不肯进来。他真是一个怪人呢!”斯捷潘加上说。
吉提涨红了脸。她以为只有她才知道他是为什么来这里,又为什么不肯进来的。“他到了我家里,”她想,“没有找到我,猜想我一定在这里,但是他却又不肯进来,因为他觉得太晚了,而且安娜又在。”
大家面面相觑,没有说什么话,开始观看安娜的照片簿。
一个男子在九点半钟去访朋友,询问关于计划中的宴会的细目,没有进来,这原来没有什么特别和稀罕的;但是他们却都觉得奇怪。尤其安娜觉得奇怪和蹊跷。(第二十一章)
当吉提和她的母亲走上那灯火辉煌的,两旁布满了花,站立着穿红上衣、搽了发粉的仆人的大楼梯的时候,舞会刚开始。从舞厅里传来了好像是从蜂房传来的、不绝的、均匀的、那样动作的綷祭声;当她们站在两旁有树的梯顶上,在镜子面前最后整理她们的头发和服装的时候,她们听到了舞厅里乐队开始奏第一支华尔兹舞时四弦提琴的准确的、清晰的音调。一个穿着便服的矮小的老人,在另一面镜子前理了理他的两鬓的白发,发散着香水的气味,在楼梯上碰着她们,让开了路,很显然地是在叹赏他所不认识的吉提。一个没有胡须的青年,一个谢尔巴茨基老公爵所称为“花花公子”的社交青年,穿着敞开的背心,一边走一边理他的雪白领带,向她们鞠躬,在走过去了之后又回转来请求和吉提跳一个卡的里尔舞(一种四人组成二对,包含六个舞式的舞蹈)。因为第一场卡的里尔舞她已经答应了渥伦斯基,所以她答应和这位青年跳第二场。一个军官,扣上他的手套,在门边让开路,一面抚摸着他的胡须,一面在叹赏玫瑰色的吉提。
虽然吉提的服装、法式、和一切赴跳舞会的准备花了她许多劳力和苦心,但是现在她穿了一身套在淡红衫裙上面的罩上纱网的讲究的衣裳,这么轻飘这么随便地走进舞厅,仿佛一切玫瑰花结和花边,她的装饰的一切细节,都没有费过她或者她家庭片刻的注意,仿佛她生来就带着纱网和花边,头梳得高高的,头上有一朵带着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正在走进跳舞厅之前,她的母亲,老公爵夫人,想要替她理好丝带的皱折的时候,吉提稍稍避开去。她觉得她身上的一切都该是生来完美的、很优雅的、无须乎整理。
这是吉提最幸福的一个日子。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她的花边披肩没有殚下一点,她的玫瑰花结也没有被揉皱或是扯掉,她的淡红的高跟鞋并不夹疼她的脚,而只使她愉快。金色的假髻密密层层地覆盖在她小小的头上,宛如是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纽扣通通扣上了,一个都没有松开,那长手套裹住了她的手,却没有改变它的摸样。她的小金匣子的黑天鹅绒带特别柔软地缠绕着她的颈项。那天鹅绒带是美丽的;在家里,对镜子照着她的颈项的时候,吉提感觉得那天鹅绒简直是栩栩如生的。别的有东西也许还有可疑之处,但那天鹅绒却的确是美丽的。在这舞厅里,当吉提又在镜子里看到它的时候,她微笑起来了。她的裸着的肩膊和手臂给予了吉提一种冷澈的大理石的感觉,一种她特别喜欢的感觉。她的眼睛闪耀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当她还没有跨进舞厅,走进那群满身是网纱、丝带、花边和花朵,等待别人来请求伴舞的妇人——吉提从来不属于那群妇人——的时候,就有人来请求和她跳华尔兹舞,而且是一个最好的舞伴,跳舞界的泰斗,一个有名的跳舞指导者,标致魁梧的已婚男子,科尔松斯基。他刚离开巴宁伯爵夫人,他是和她跳了第一场华尔兹舞的,于是,观察着他的王国——就是说,已开始跳舞的几对男女——他看到了刚走进来的吉提,就迈着跳舞指导者所独有的那种特殊的、轻飘的步子飞奔到她面前去,连问都没有问她愿不愿意跳,他就伸出手臂去抱她的纤细的腰。她朝周围望望,想把她的扇子交给什么人,于是他们的女主人向她微笑着,接了扇子。
“您准时来到了,多么好啊,”他对她说,抱住了她的腰,“迟到真是一种坏习气。”
弯起她的左手,她把它搭在他的肩头上,她那双穿着淡红皮鞋的小脚开始敏捷地、轻飘地、有节奏地合着音乐的拍子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移动。
“和您跳华尔兹舞简直是一种休息呢,”他对她说,当他们踏上华尔兹舞的最初的慢步的时候。“妙极了——多么轻快,多么准确。”他向她说他差不多对所有他熟识的舞伴都说过的同样的话。
听了他的称赞她笑了笑,越过他的肩头继续环顾着舞厅。她不像一个仿佛觉得舞厅里的一切面孔溶成了仙境般的幻影的那样初舞的少女;她也不是一个舞得太多以致把舞厅里的一切面孔都看熟了而且腻烦了的少女。而她是在两者之间,她兴奋,同时她也足够沉着地去观察周围的一切。在舞厅的左角她看见社交界的精华聚在一起。那里有胸颈赤裸到不能再赤裸的美人丽姬,科尔松斯基的妻子;有女主人;有克里文的秃头闪耀着,但凡是有上流人的地方总可以找到他的;青年人向那一个方向眺望着,却不敢走近前去;在那里,她的眼睛也看见了斯季瓦,看见了穿着黑天鹅绒长袍的安娜的美丽的身材和头部。他也在那里。吉提自从拒绝列文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用她的远视眼睛,她立刻认出了他,甚至观察到他在看她。(第二十二章待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