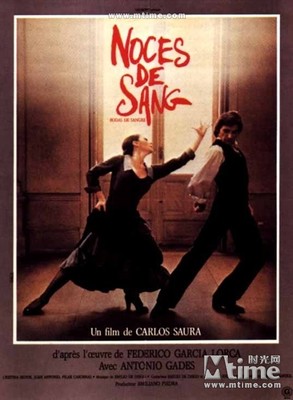《新暗恋桃花源》舞台探索研讨会综述
本刊编辑部
2011年7月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杭州红星文化大厦·红星剧院联合主办,杭州东西文化艺术中心水南半隐艺术文化会所协办的《新暗恋桃花源》舞台探索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隆重举行。来自戏剧界、评论界以及新闻界的20多位专家学者,秉持着“中肯评论、立足学术、坦诚交流”的宗旨,对《新暗恋桃花源》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深入的交流。
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茜,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副巡视员、评论家梁鸿鹰出席了此次会议。到会专家学者有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季国平,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安葵,原《中国戏剧》副主编王育生,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王晓鹰,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宋宝珍,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清华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文化评论家肖鹰,《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徐涟,《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向云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庆梅,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胡薇。同时,来自演出制作方的领导专家有杭州红星文化大厦·红星剧院总经理、杭州东西文化艺术中心主任、杭州文广演艺机构负责人程俊,中国戏曲学院教师、《新暗恋桃花源》越剧编剧颜全毅,杭州东西文化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秘书长李莉,杭州艺术项目负责人白凤荣。另外,《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新浪网、搜狐网等二十余家媒体与会。会议由《艺术评论》副主编唐凌博士主持。
刘茜(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艺术评论》举办这次大型舞台研讨会很有意义,《艺术评论》在追踪热点问题、评论当下艺术现象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新暗恋桃花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模式戏剧,它在同一个舞台上用悲喜两种形式、两个剧种、两种历史背景下的情境,来表现两个意境深邃的完整剧本,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探讨。
梁鸿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副巡视员、评论家):赖声川创作有三个特点:一是现实的锋芒。二是倾向于搞原创,不愿意走跟别人相同的路。三是具有复合性。现在的文艺创作,线性的倾向于一个方向的作品比较多,但赖声川的剧作显然丰富得多。当下,新创作品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思想内涵上,到底能否经得起琢磨,并且让多方面的人都能有多种解读,这应当成为艺术家的一种追求。
季国平(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新暗恋桃花源》一剧很新鲜,也很有趣,比较感人。我有两点感想,第一,《新暗恋桃花源》二十多年常演不衰,里面有很多诸如明星效应的商业因素。同时戏本身很有内涵,戏里面有两岸的情结在。第二,话剧和越剧的嫁接很值得关注。这个剧目本身的结构就有利于这两个剧种来表达。同时,嫁接之前首先考虑了群体,观众定位为年轻人,这都是跟市场相关联的。
王安葵(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新暗恋桃花源》在追求娱乐性的同时,核心的东西是使人感动的。云之凡和江滨柳两个人的生离死别,确实有着非常清晰的政治背景,就是两岸的分离。暗恋同时,拿《桃花源》这个寓言性很强的故事来混搭,用来跟“暗恋”进行对比,“暗恋”很严肃,“桃花源”很滑稽。这是用滑稽跟严肃的、人生的东西做对比。这种滑稽、无奈也是一种很深层的人生感受。
王育生(原《中国戏剧》副主编):现在的泛娱乐化是十分危险的,像《新暗恋桃花源》这样有文化内涵的戏剧是好的戏剧。艺术最大的价值就是探索、创新,没有探索、创新,其他别的因素都不存在。
王晓鹰(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话剧院副院长):《新暗恋桃花源》剧在整个戏剧大环境变化当中体现出的文化意义是,第一,赖声川在做这个戏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做实验戏剧的观念来做这部戏的。他用一种喜剧和悲剧的组合,用严肃和荒唐的组合,执著和无奈的组合,悲情和滑稽的组合,来表达一种现代人生活当中情感的复杂和无奈。第二,在娱乐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主流文化语境的大潮下,让一个有文化价值的作品,不断有生命力,不断随着文化的审美潮流往前发展,势必要引入娱乐的概念。今天我们用一些影视明星出演的时候会更多吸引观众,会有更多剧场效果,会有更多票房收入,有更多现代文化产业的意味,这都是时代必然的推进。第三,越剧本身讲究精致、唯美,促使这部戏的文化气质、文化品位值得关注。当娱乐业发展到今天,有必要提一个“娱乐道德”的观念。要看戏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娱乐经过严肃、严谨、高品质的制作,而不是简单低成本的粗制滥造。最后,赖声川把不同品位、不同品格的东西组合在一起,用一个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这个东西完全是他一贯的艺术追求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
路海波(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这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戏,首先,这部戏风靡了二十多年,屡演屡新,导演不断变化演出方式,这是值得研究的,很多经验是值得借鉴的。第二,它并不是简单的混搭,用越剧跟话剧的混搭,两方都很出色。这个戏表面上是嘻笑怒骂,实际上寓意深远。陶渊明的《桃花源》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寓言,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社会建设成和谐社会,那就是桃花源。所以这部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戏,值得大陆话剧界的同行们认真反思、学习。
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第一,《新暗恋桃花源》剧表明了赖声川和这个戏的主创的主张,戏曲的加入,公开地表明了舞台的假定性,承认戏就是戏,戏可以对生活进行夸张,或者说比生活更高。第二,它摒弃了俗势力,保留了戏曲表演的本质精神。但是,这个戏由于戏曲加入之后,还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比如说两个戏中戏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且从舞台时空上看,话剧方面是固定的,戏曲方面则超脱、流动等等。
宋宝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首先,赖声川的集体即兴式的创作模式,对于这个戏总体风格的形成应该是意义重大的。第二,“暗恋”的文本和“桃花源”的文本有对称性,以片段化、场面化的情节演绎了不同风景下的人生画面。此外,这个戏打破了传统戏剧幻觉效果,把舞台的假定性发挥到了极致。
吴文科(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所所长)说:看完戏后,我感到四“无”,人生无奈、人生无常、人生无解。但是正因为这样才要去探索,用艺术去思考人生;最后,人生无望。但是在无望中又看到了人的可贵、可悲、可爱、可怜。人们执著追求,不放弃、不忘怀,其实人生很可敬。
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美学教授、文化评论家):赖声川整个戏剧的根本,实际上是布莱希特的间离化的结构。观众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带进去,来进行一种思想的探索。赖声川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一个是两个剧组的冲突。另外,用了两个经典的叙事,一个是桃花源,这部戏剧在80年代展开时,实际上它展开了中国文化一个基本的情景,这个情景对大陆来说是改革开放,对台湾来说是何去何从;一个是“暗恋”,“桃花源”是一个经典叙事,是一个乌托邦。这种理想的情感追求,在当代还有没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还有没有可能?此外,越剧版的《新暗恋桃花源》成和败都有。成,因为“桃花源”有很大的表现空间,局限在于,越剧版的《暗恋桃花源》,从戏剧艺术来说还是一个草稿,还是草创、初步尝试,如果要把它经典化打造还有很多空间。
徐涟(《中国文化报》副总编辑):这部戏剧虽然由来于26年前,但它仍然在讲当今现实生活和人的情感普遍遭遇到的困境,这就是这部戏的经典性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对《新暗恋桃花源》来说,混搭的尝试确实非常有意义,也许很多话剧观众正是通过这样一次机会了解了越剧。我有一个大胆的提议,那就是如果这个戏全部做成越剧,是否会给戏曲一些新的启示?这样的一个戏观众会非常欢迎。
向云驹(《中国艺术报》社社长):这个戏是后现代的背景,这是主要的语境,所以它对后现代有一些贡献。后现代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拼接和重组,而这部戏不是简单的拼接和重组,而是碰撞。两个剧组的碰撞、话剧与越剧的碰撞,虚拟与写实的碰撞,历史与现实的碰撞,喜剧与悲剧的碰撞。另外,这部戏有三个空间:暗恋的空间、桃花源的空间,两个剧组在一个排练场的空间。三个空间和后现代的三个语境也是相对的,乌托邦,反乌托邦,异托邦。如果说一点不足就是极致化还不够,该深刻的还要更加深刻,该反深刻的还要更加反深刻,两个剧组在一块的时候是否应该更加冲突,两个剧组之间甚至可以发生一些爱恋,架可以打得更激烈一点。
陶庆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青年戏剧评论家):这个戏看上去是混搭,但在混搭底下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暗恋桃花源》有三个构成它的基本动力:第一是两岸关系。两个戏一个是生离,一个是死别,都在讲分离带来的人生差别,其中有巨大的情感动力在这个戏里。第二,在舞台上,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构成,《暗恋》和《桃花源》同时演出时,这两个戏出现统一的格局,可以发现两个台词是完全接得上的,尽管一个是悲剧,一个是喜剧,如此造成的戏剧效果是最强烈的。第三,对人生痛、悲、留恋,各种各样很复杂的情绪都传达出来。最后,《新暗恋桃花源》本身的气质,赵志刚本人的表演,让《桃花源》在最后关头实现了从喜剧往悲的地方非常好的转达。
胡薇(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副教授、青年评论家):《新暗恋桃花源》的越剧部分特别有光彩。首先,它契合了戏曲刚刚兴起时候的状态。另外,也契合了现代人喜欢追求乐活的心理。传统戏剧的魅力只要找到合理的载体,永远不会过时。另外,每个人心中实际上都有一个桃花源,每个人一生都在寻找新的桃花源。这是《暗恋》和《桃花源》拼接在一起的情感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基础。
最后,出品方代表就《新暗恋桃花源》的创作过程和缘起,与到场专家进行了交流。杭州红星文化大厦·红星剧院总经理程俊认为娱乐是为价值观服务的,这样才称得上文化,不然就是娱乐。红星剧场每年演出180多场。他们做剧场也在选择戏,如果作品不符合主流的价值观,就不让它到剧场来演。去年剧院在西湖边做了万人的演出,在大草坪上席地而坐。一万人散去以后,草坪上没有留一个垃圾,文化最大的意义是教育我们的行为,包括这个戏,有思考就是最大的意义。
《新暗恋桃花源》舞台探索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它深度挖掘了该剧可贵的探索经验和成就,为话剧舞台的实践及时提供了理论总结,也为越剧的进一步继承发展贡献了宝贵的良策。
责任编辑:霍明宇
看话剧越剧版《暗恋桃花源》
季国平
我是第一次看《暗恋桃花源》,看话剧越剧版,看得很开心,很新鲜,很有趣,也被感动了。二十几年常演不衰的话剧,应该说是一个名剧了,由于越剧的介入,话剧与越剧的混搭形式很少见,自然很新鲜,也很好玩,很有趣。戏的最后一场,就是黄磊担纲的角色与当年暗恋的对象重新见面的那一段戏,让我深深地感动了。
二十多年来,大家对该剧成就的分析研究已经很多,在这里,我想结合当下剧目创作的现状和本次版本的特点,说两个方面的感想:一是剧目与市场,二是话剧与越剧。
先说剧目与市场。
两岸三地,《新暗恋桃花源》常演不衰,毫无疑问首先是明星效益的助推,剧目有很多商业因素,同时戏本身也很有内涵。导演自己讲,它不是一般的爱情戏,这里面有两岸的情结。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现在随着两岸之间的交流往来更多以后,这个情结可能会慢慢淡化,但是在二十多年前的八十年代,两岸情结是多么的浓烈!我这次看戏被感动,主要就是最后一场戏。
感动之余,我联想到前两年福建创作的京剧《北风紧》,戏中那种人生遭遇的两难境界,面对知遇之恩和养育之恩艰难抉择的无奈,自然令我联想到两岸之间很多的无奈。这部戏最让我感动的正是这一点。就这一点,也才充分显示出这部戏所独有的价值。形式很新鲜,内容更关键,这是这部戏的魅力所在。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部戏演了二十多年,从主创人员如何创作,到二十多年来的各种有效的市场推广,包括现在出来了越剧和话剧版,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大陆戏剧人关注和研究的话题。当下正进行着艺术院团的文化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创造有利于艺术生产和发展的环境,核心还是要出人、出戏。怎么出人、出戏?恐怕我们不打破现有的各种不利的体制机制,包括我们创作的思维定势和运作模式,就很难改变目前剧目创作往往总是和市场脱节的现状。
戏剧是大众艺术,演出来是要给观众看的,剧目从创作开始要有为观众的意识,创作出来的推广同样很重要。剧目要有内涵和艺术的创新,这是新剧目的生命力所在,同时,戏要走市场,要让观众来看,这个道理很简单,从《暗恋桃花源》应该得到启示。这次话剧越剧版的创作和市场做得就很好。
再说第二点,话剧与越剧。
首先从艺术样式、从艺术的不断创新来讲,导演不断追求的精神就非常令我们敬佩。二十多年了,该剧的演员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却总是常演常新。这个剧目本身的结构,很有利于用话剧与其他不同的剧种样式来表达,话剧本身很擅长当下的“暗恋”,越剧或其他传统戏曲样式更擅演旧日的“桃花源”。
再从地缘的因缘来讲。我跟赖声川不熟,但是我跟杭州很熟,我和杭州越剧院很熟。杭州的文化创意产业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包括邀请赖声川的加盟,赖导创作话剧和越剧版也是在为杭州的文化创意产业做贡献。
第三,让越剧和话剧嫁接有着剧种的优势。越剧的都市化程度在所有地方剧种里是最为突出的,是最能走演艺市场的。越剧是青年观众非常喜欢的剧种,越剧也常说有两个奶妈,一个是昆曲,一个就是话剧,越剧本身与话剧就有着内在的重要的联系,当二者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话剧和越剧两方面青年人的眼球。
话剧与越剧混搭版《暗恋桃花源》是成功的,一方面是话剧与越剧二者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话剧和越剧又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即使全剧是话剧统领着越剧,但越剧的基本风格仍然很完整,甚至越剧的独特魅力和表演上的强势做派,时不时还抢了话剧的风头,越剧表演艺术家抢了话剧明星的戏。
当然,我看戏的那天可能话剧迷要多于越剧迷。以何为证?大家都知道,越剧迷对越剧名家和流派的崇拜可能比话剧迷还要“盲目”,我看戏的那一天,越剧名家赵志刚、谢群英、徐铭表演精彩,流派纷呈,但从他们出场、开腔起,台下的掌声不多的剧场反应看,那天的铁杆越剧迷恐怕不多。相对来说,话剧演员那天剧场的共鸣肯定比越剧要大一些,黄磊粉丝的热情也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即便如此,那天的戏,越剧演员的表演非常抢眼,如果说他们抢了话剧演员的风头的话,更说明了话剧演员要多向深厚的传统戏曲学习。我相信,话剧越剧版《暗恋桃花源》在南方,在江浙一带的剧场效果一定会更好,那里的越剧知音会更多。
季国平:中国剧协驻会副主席、戏剧博士
责任编辑:贾舒颖
人事沧桑:滑稽还是苦痛
王安葵
赖声川话剧《暗恋桃花源》以前的几版没有看过,这次看了话剧与越剧“混搭”的升级版,觉得确实是一出值得回味的戏剧。在特定的年代,戏剧是为艺术还是为人生曾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但在今天,真正的艺术不能不表现人生,想表现人生的作品首先又应该是“艺术”。《暗恋桃花源》艺术地表现了人生中最难抵御的遭遇——人事沧桑,又是通过人生际遇展示的有震撼力的艺术。
《暗恋桃花源》的主体是在两岸分隔的背景下的一段人事沧桑:一对恋人江滨柳和云之凡,在重庆曾是同校的同学,但没有相识;在上海的茫茫的人群中却相识而又相爱了。相识相爱似乎并不久,但已难舍难分,时间、空间对于他们来说,似乎都停止了。然而以为是暂短的分离却成了数十年的音信隔绝。男主人公到了台北,但是在他病倒在医院的病床上时,才知道他的恋人也是在数十年前就到了台北。这时他已成家,但难忘当年的恋人,于是他登报“寻人”……“桃花源”是另一段人事沧桑。古人在这个故事中表现的东西很丰富。有美丽的想象,也可以引发人们对于瞬间与永恒的思辨,逃避了灾难,或者得到了长寿,但却失去了真实的生活。从哲理的层面说,它比“暗恋”更深邃。但赖声川先生把它的哲理意味消解了,使它世俗化、并且滑稽化了。渔人老陶和他的妻子春花在一起应是已生活多年,这比“暗恋”中的男女主人公要实在得多。但他们“俗”,他们没有真情,所以他们的悲欢离合虽然也难免有苦痛,却终究是一种滑稽。老陶没本事,打渔打不着大鱼,性生活可能也无本事,连个酒瓶盖儿都打不开,所以妻子去“偷人”。他想死,他想逃避,去了一趟桃花源,结果发现生活无法改变,因此一切都毫无意义。《暗恋桃花源》是用老陶一家来与“暗恋”的主人公做对比的,当苍老的云之凡来到医院与病床上的江滨柳相见时,当他们再次分别——这可能是终生之别——时,当江滨柳伸出僵硬的手向她招手,当他们的手握在一起,当他们离别后,江滨柳发出凄惨的声音时,我们不能不深深感动!“有些事情不是你说忘就忘得掉的”,这句核心台词,不能不让人反复回味。“不思量,自难忘”,这是苏轼的《江城子》词,如果是真情,那就无论时间长短,都是难忘的。无尽的思念应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亲身经历过这种人生之痛的“导演”在回忆中有无限的美好,他说云之凡是“白色的山茶花”,要男女演员都演出这种感觉。但男女演员说,演不出来。他们没有这种深刻的苦痛,就表现不出这种深刻的爱。
除了主要情节、主要人物之外,剧中还有许多情节和细节表现人们不能互相理解、无法沟通的无奈。做助理的不能理解导演的想法和要求,在画桃花的幕布上想当然地“留白”;那个叫顺子的,想当然地理解老板的意图,把布景拉到“廊坊”;护士不能理解江滨柳,江的太太也不能理解他;老陶到了桃花源会把陌生人看成自己的妻子和她的情人;而当老陶出走,袁老板与春花如愿以偿地住到一起之后,又陷于互不理解之中;那个为相思所苦、找刘子骥的女人不能理解别人也不被别人所理解。两个剧组在同一时间租用了同一场地彩排。这一切都在陈述着人生的无奈和生活的滑稽。
我没有看过全是话剧的演出,现在用越剧来“混搭”,我想赖先生是想更增加“桃花源”的滑稽感。“越剧王子”赵志刚用丑角的风格来演老陶,对一位名演员来说,增加一种戏路,也是有好处的。作为几乎是硕果仅存的越剧男演员,赵志刚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形象,何文秀、浪荡子、沙漠王子,各有特色,近年在《赵氏孤儿》、《藜斋残梦》、《第一次亲密接触》等新编剧目中的表演,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一位追求突破的表演艺术家,他说,不寻求突破,就不是好演员。他认为演《暗恋桃花源》,打开了他自己的喜剧之门。但是如同茅威涛演孔乙己让她的许多粉丝失望一样,在这个戏里,我看不到原来的赵志刚了,如果事先不知道,我不会看出他是赵志刚。不是赵志刚演得不好,是角色在这个戏中的位置决定的。老陶这个形象就是为了与江滨柳对比而存在的,他的作为不是要人感动,而是要表现这种人生的无意义、无价值。我想赖声川先生如果想再玩一把,是否也可做这样的实验:让赵志刚来演江滨柳。当然需要请懂得越剧的编剧和音乐家来帮赖先生一起做,让赵志刚运用越剧的唱腔和表演来演绎这一场人事沧桑,让他发挥越剧的优势来表现江滨柳的苦痛,我想一定会取得不同寻常的戏剧效果,一定会有更强的震撼力。
王安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贾舒颖
碰撞产生的后现代智慧与象征——《新暗恋桃花源》观感
向云驹
(一)
在荒诞开始的地方,正是现实的真实境况。《新暗恋桃花源》就是这样展开叙事的。观剧以后,回望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生,一切的荒诞的产生,难道不都是这样的事实过程吗?《新暗恋桃花源》让观众五味杂陈、悲喜交集,把一切不可能的、不现实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事件、形象、感情、思考杂烩在一起,让人的情感随着剧情大起大落,悲悲喜喜,跳进跳出,断断续续。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剧体验。它让你深刻,也让你滑稽;让你沉思,又让你轻浮,让你憧憬,也让你无奈;让你圣洁,又让你世俗;让你审美,又让你像街头的围观者。它把所有的戏剧冲突都集合起来,推向极致、极端;同时也把观众经历过的所有审美经验和艺术体验都调动与混搭起来,使你无言,使你心绪难平,使你陷入理不清剪还乱的困窘与困境。你必须在悖论和混沌中思考。
当我们身处一个无可回避的后现代时代时,《新暗恋桃花源》的后现代风格,或者说我们把它指认为一出后现代戏剧,就是顺理成章的。
早在1989年,台湾学者就开始译介、研究后现代思潮和理论。早期的译介者对后现代的最基本的理解就是:后现代是一种复制、拼贴的技术、手法极其泛滥泛化;同时,后现代不限于一种复制重组的技术,而且也是一种在后工业信息社会中出现的大规模的信息传递方式,一种整体性对传统思维方式的颠覆方式。后现代主义除了采用复制拼贴以及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将庸俗的世俗文化与严肃的精英文化融合起来,不惜由此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反讽(台北,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湾学生书局)。
诚然,几十年过去了,台湾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在走向新的境界;与此同时,大陆后现代知识几乎与台湾同时被引进和译介,迄今也在深入展开中。这使我们可以在《新暗恋桃花源》中会心而笑,毫无生涩隔阂。
假如说戏剧根本结构在于戏剧冲突,在人物命运、情感、性格、事件、情节的冲突的话,这种冲突通常是戏剧深在的、内蕴的,是震撼人心的命运矛盾;那么,《新暗恋桃花源》却不是这样。它把这些戏剧原则全部表面化、视觉化、外在化、形式化,它以戏谑性的矛盾冲突,放大所有的形式化的矛盾,以后现代的风格和手法,在解构中重新建构,在消解深度中重新组建超越性的思想,仿佛是感观性的快乐取代了剧场内的思考,实际上是把戏剧空间与思想空间由两者统一分解为剧场内外的并置的状态,使戏剧思想穿越剧院空间,在观众的空间里幽灵般徘徊。
(二)
《新暗恋桃花源》具有鲜明的拼贴与重组的后现代戏剧范式,但是我们在这里更愿意用“碰撞”来替代拼贴重组。《新暗恋桃花源》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哭笑不得的“碰撞”,把观众的审美经验逼入绝境,再让观众绝处逢生,找到审美的出路。这一系列“碰撞”包括:
两个剧组的碰撞。两个剧组在同一个场所排练,为了场地,互不相让,最后只好你一段我一段,或者两家同台排练,你一半、我一半。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事件,这种场景来自生活,来自我们身边,就像一地鸡毛一样,琐碎、平庸、习常。也正是这一庸常的现实主义场景,为两个超越现实的戏剧故事奠定了观赏的可能性,同时也为这两出风马牛不相及的戏剧能够同台相会、同台共演提供了真实的舞台。它为观众设置了审美的前在,设置了理解戏剧荒诞呈现的日常关系,设置了观众“穿越”和戏剧“穿越”的心理认同与同构,设置了演员和观众一起跳进跳出的心理动机。
越剧与话剧的碰撞。桃花源以越剧演绎,暗恋以话剧表演,两种戏剧集于一台,不仅开创了戏剧表演的全新形式,而且让观众对两种艺术样式进行交叉审美。在最外在的层面,观众能够欣赏到话剧的美,也能领略越剧的美。同场欣赏两种美,让人浮想联翩;加之两个班底的演员都是技艺高超的优秀人才,他们给人的审美愉悦是前所未有、从未经验和体验的,审美的陌生化效果成为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在深层里,创作者给观众以巨大的审美惊奇和审美意外,使得此剧不同凡俗。
虚拟与写实的碰撞。戏曲长于虚拟,话剧天生写实,这一虚一实同台会面,确实产生了虚实相生、虚实互补、虚实相济的效果。这是一种戏剧节奏,也是绝妙的戏剧叙事策略。虚者,人物虚,表演虚。动作是程式化的,主题是虚无缥缈的,表演是虚拟的想象。实者,实事实演,高度的生活化。主题是深刻的,形象是真实的,场景是写实的。两者对比、交叉、互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命运的荒诞、人生的无常都在不经意间充盈思绪。
大陆文化与台湾生活的碰撞。越剧是大陆本土的经典戏曲样式,桃花源的故事也是中国文化的经典桥段;而暗恋所反映的台湾人生活也是那样地真切、动人。这两者原本是很难汇聚碰头的。但是正所谓,不是怨家不聚头,它们聚首一处、同台呈现时,滑稽的外表和可笑的冲突下,有深度的契合,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意义与效果。
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暗恋桃花源的相遇,也是历史与现实的遭遇。桃花源不仅是一出古装戏曲,也是古老历史的缩影。暗恋则是充分的现实题材,书写了一则有着强烈现实意义并逼真地状写现实生活的动人故事。两个故事都讲述了爱情、婚姻、家庭与生存的意义。但是历史是荒唐的,爱情是可笑的,充满了背叛、欺瞒、虚伪;而现实在残酷中有美,在痛苦中有幸福,在分离中有心灵相通。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为什么相遇和碰撞?这是作者向所有观者提出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它逼迫观众不能不作出思考与回答。
喜剧与悲剧的碰撞。通常我们有悲剧、喜剧,甚至也不乏悲喜剧。但是像《新暗恋桃花源》这样直截了当、生硬拼盘的悲剧与喜剧相加,实属罕见。由于暗恋与桃花源是交叉演进的,所以,观者就不能不反复交叉体验时悲、时喜,时庄、时谐的观剧过程。两个剧种的反差,两种美学风格的对比,两个情节的并行,引发观众的思考和笑声,引发出含泪的笑和复杂的思。
当所有这些不可能的时空碰撞在一起时,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审美爆炸,颠覆了我们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神经,但同时,也催生了我们的全新的想象和对生活的体验。这是一般后现代的拼贴与重组不能指认、比对和抵达的;它的后现代性不仅体现为超越拼贴重组的“碰撞”性上,而且它的全部意义甚至可以止于“碰撞”的瞬间爆炸效果,无须再作深度延展。当然,它依然具有延展性。
《新暗恋桃花源》不仅让观众重建审美经验,重构想象力的边际,重悟生活与存在的本质与真谛,事实上,它的一系列碰撞,也撞击出人类审美疲惫、困顿、麻木后的生机、智慧、火花与闪电。比如,暗恋中的严肃的人生、忠贞的爱情与桃花源里的戏谑人生、搞笑的情爱,谁更真实?谁更理想?暗恋中的爱情是几十年的人生真实,但是它是如此刻骨铭心,如此凄美动人,如此短暂却又如此永恒。而桃花源,它流传了几千年,为什么会这般荒唐、这般无奈?这般令人生疑、令人荒诞不经?又比如,因那历史的巨变、动荡,使江滨柳、云之凡虽天各一方实又近在咫尺,几十年风雨,但情在爱在,是生命的绝唱也是爱的大不朽。两人如此,两岸亦然;生命如此,文化亦然;人事如此,情理亦然。
(三)
《新暗恋桃花源》还有一组意象充满象征意味。这出戏实际上由三个空间组成。一个是两个剧组两出“内”戏,其中分出两个时空,暗恋的剧情空间,桃花源的戏曲空间,这是两个不同的艺术空间,剧中人真实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一个是两个剧组的戏外空间,此时,所有的人物都回到争抢舞台的剧组身份中。在各自的剧目中,他们扮演着演员,纯粹而且艺术;在剧组中,他们个个都很世俗,甚至不乏低俗与卑琐,卸去了艺术的面具,露出了生活的本相,甚至不惜在舞台上互相嘲讽和贬损各自的创作、剧本、排练和演出。这里的喜剧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也见出编导对自己的无情嘲弄。但事实上,这里还有另外的深意,别样的象征。
我以为,这三个空间同时呈现在舞台上,给我们对应的是三个关于乌托邦的想象与象征。一个是乌托邦,一个是恶托邦,一个是异托邦。乌托邦源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有之乡”,它指人类对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的空想和幻想,但乌托邦往往又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是人类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追求和憧憬。《暗恋》的凄美爱情颇类于此,它几乎类于柏拉图的精神之恋,高尚、美好、纯洁。它是动荡年代的精神寄托,也是和平时代的精神信仰。对于今天的观众而言,它像乌托邦一样充满童话色彩。《桃花源》本是一出真正的乌托邦寓言。可是在剧中,这则乌托邦以恶搞的形式变成了反乌托邦即恶托邦。这个恶托邦即反讽了陶渊明的桃花源,也反衬了暗恋的“乌托邦”。桃花源里老陶、春花、袁老板虽都是古代的人事,是戏曲的虚拟,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嘻哈文章,但是他们又分明是现实的、生活的、俗世的。历史太过久远就成了现实的诠释(桃花源),而现实离我们渐行渐远时,它就仿佛一如乌托邦(暗恋)。两者交汇又构成了异托邦的景观(排练场)。在福柯的阐释里,异托邦是一个人为的空间,它间离和阻隔着现实同时又置身于现实。异托邦是一种变质的空间,它现实地强力地遮蔽和掩饰生活,或欺瞒社会和自我,或无情规训生命或身体,或制造一时的虚幻。异托邦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但又非常另类并远未引起人类深思的一种特异空间。监狱、医院、军队、学校、游乐园等都是此类异托邦的所在。剧场是不是也是一个异托邦的所在呢?福柯没有论述过。但是我看赖声川营造的两个剧组跳出情节共处一处争执排练场时,这群人事和他们所在的空间很类于异托邦的空间。它让我们走出剧情回到剧场,回到一个人为营造的空间,并在这个空间里告诉我们,这正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影子和镜像。那个幽灵一样的寻找男友的陌生女人,她时隐时现,最后却一声呐喊收束全剧,意义正在于此。
我们被艺术所规训着,但规训与被规训之间是荒谬不堪的,不分你我的,可以身份转换的。假如包括演员、观众在内的整个剧场都只是一个异托邦式的存在与空间,那么,当我们走出剧场时,我们才身处真实的生活空间并拥有真正的本我与本真。异托邦解构了乌托邦与恶托邦,异托邦本身又被现实的空间所瓦解。《新暗恋桃花园》是在一系列的意义消解中生成出一系列超乎寻常、难以理喻、不可思议的意义。这些颠覆传统的、日常的、世俗的意义的意义,是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荒谬的纠结,是爱情的神圣与家庭的世俗的反讽,是理想、空想、乱想、胡想混沌后的原生态。这些意义,只在感觉直觉中,不可言说,也无以言说。这是后现代的新指向、新价值、新样式。
这也是《新暗恋桃花园》中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三邦碰撞的最具震撼力和深刻性的效果。
向云驹:《中国艺术报》社社长、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学术委员、天津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贾舒颖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