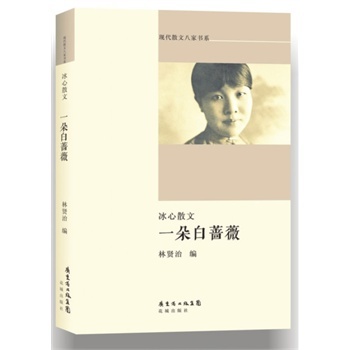俞心樵《狱中日记》(13)
(整理者注:本篇没有注明写作日期)
心中有一盏莫名其妙的灯,忧伤、神秘而又乏力。监狱内的灯始终在下雪,我也不在乎冷不冷。
有句话:冷暖自知。这句话很孤独,却是我需要的。
读高行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全文《文学的理由》,我觉得他不具备一个伟大作家所应有的品质,他对尼采的误解很深,他没有能力处理个人、群体、文学、政治和历史的关系。文学的真实不可能是纯个人的真实,而是,最好是关系中的真实,文学的独立也不应沦为孤立的托词,文学当然不应当等同于愤怒的呐喊,或等同于把愤怒变成控诉,但为什么不能有文学的呐喊或文学的控诉?一味的冷眼静观或冷的文学是否有助长中国人的看客习性之虞?作家,首先应当是作家,但伟大的作家不应当仅仅只是作家,如果同时成为英雄或斗士岂不更能够予人以鼓舞与安慰?但丁如此,拜伦、雨果、鲁迅、聂鲁达,等等莫不如此,他们的英雄或斗士行为,不仅没有损及文学,相反,却是大大地提高、丰富了文学本身,包括丰富、提高了文学形式和诸般文学技巧,他们的作品丝毫未曾被时间损耗,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是积极的,在干涉与互动中决不令人沮丧。
文学的目的不可能完全是为了文学自身,因此文学仍然义不容辞地负有文学之外的责任与义务,过分地强调个体、个人的一切都成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它所导致的可怕局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散沙现象。人性的日益自私、更趋冷漠就是这一现象的特征,民间不再有自我解放的热情,不再有春天的诗意,这无数的孤立无援的所谓个体为暴力的高度组织化清除了一切阻碍,这难道不是极权者最乐于接纳的事实?
中国人盲从的功夫深矣,以往总是结社,总是运动,包括文学的结社和运动,如今在最需要结社,最需要运动的时代,却不见了任何动静,只剩下了那些个前结社劳模,前运动健将针对“结社”与“运动”这两个或名词或动词的冷嘲热讽,他们忘了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建筑的生命在于一动不动;他们难道没有看到,运动仍然存在,而且当前唯一成功,唯一蔚为壮观的运动就是他们的反运动的运动,这反运动的莫名其妙的运动,究其实质,乃是面对危险时的怯懦与慌乱,因此,个体成为逃避、退缩的粉饰或籍口,甚或于置换为使文学成其为文学的理由,那么所谓的文学就更加没有指望,因为这仍然是一场骗局,只是人们更难以察觉而已。受骗上当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大众,还有显赫于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怪不得谁,任何人都难免有上当受骗的时候,只是我们理当保持这样一个警觉:一种不利于人类团结与互助的经由文学(文化或文明)包装的个体迷信正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更加不可收拾,它很有可能使人类全都变成冷血动物。这决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如果不是对未来的预言,至少也算得上一个警告,没有预言和警告能力的文学,有悖于文学中的伟大传统,对真实的浅尝辄止,在政治与功利之间的无聊辩解,无非包含着对政治与功利的屈就,也包含着当今消费市场中有关“适者生存”的恶俗哲学。
诚然,文学不是祭品,作家也应当尽可能避免无谓的牺牲,但是(高潮),当我们(?)置身于特殊的地点、关键的时刻,无论如何也无法欣赏那种“躲起来挑战”和“跪着造反”的作家与文学,只是(低潮),大可悲哀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这两者都倍受纵容,人类已习惯了文学品质的一再沦丧和幸福标准的一再降低。
以上言论不完全针对高行健,它只是我读了《文学的理由》之后所作的一点思考,对高行健其人其文,我已关注了十多年,对其不足之处的批评苛刻些,却无恶意,只愿他做得更好。
去年春天,在北京监狱,我给瑞典国王和皇家科学院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我,这一要求的提出,一是出于自身文学成绩的自信或谦虚的确认,一是出于功利思想,即一个蒙冤入狱的作家想藉此尽早获悉。写出这一封信,极为深重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只是为了自由与生命的保全,我不得不出此下策。不过,无论何时、何地、何种险情,我始终坚持认为,人类正义不低于个体的自由与性命,为正义而牺牲了我的自由与性命,虽然痛苦却无须后悔;而且我还认为,人类之爱是高于任何奖项的。
到了去年冬天,传来了高行健获奖的消息。报道这一消息的自由亚洲电台也报道过我入狱的消息。随后卫民、镂克、晓渡等友人来信谈及此事,或高兴或表示不满。在我看来,这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我已托晓渡、谢冕等人转达了我对高行健的祝贺,同时为本人未能为汉语作家首获诺奖表示遗憾。
作为对以上言论的补充,我有必要指出,高行健获奖事件暴露出了中国文学现状的一大病痛,有那么多从事文学的老朋友(?)或牛B人物跑到国外去凑热闹,去帮闲,却几乎无人过问一下一个蒙冤入狱、危在旦夕、亟待救援的作家,而其中不少人在以往是以能够与我见面、与我交往、与我通信为快事的,如今都远远地避开了,其中某几个明星在我入狱前夕,还在与我约会,与我通信,并且引以为荣,如今却表示“无话可说”了,或者说“我们无此义务”,正如目前正在让他们“引以为荣”的高行健所说:“文学对他人不负有什么义务”一样。当代汉语文学的病痛正在于此。一个说了几句真话的人成了“危险人物”,成了大家惟恐避之不及的瘟神。因此,从总体而言,当代中国(汉语)文学仍然是投机、小商人、小太监、小奴才、小绅士、小市侩诸如此类小小的“我”(个体)花样不断翻新的时装表演而已。更等而下之的是,从这张牙舞爪的众“小”之中还衍生出一种名曰“过度阐释”的小玩艺。如今自囿于小的自恋实在是史无前例,而且为了给这小小的“我”(个体)确立合法性,真实不虚的高山与大海被指控为“膨胀”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切无非是为了享有他们那相传的肮脏的安全。本来问题不在于小,小本身从来就无可厚非,小有小的好处、妙处、可爱处,只要小得其所,那么小人和小文学仍然不失其真实的一面。现在的问题在于小的霸权,并且利用传媒倡导了惟小是理,惟小是尊的风尚。呜呼,六畜能言人失语。
对看不见的,没有把握的,甚至注定要“失败”的事物充满信心,这样的生存状态才能对世俗有所超越,这也是接近“神明”的最佳途径。我由衷地藐视世界的那些个所谓的“成功”,虽然有时我不得不借助世俗的力量来达成通灵的目的。当一个人清除了自己身上多余的东西,那人类之灵自然得以彰显。
身处困厄,有时我难免愚钝和脆弱。我渴望神的降低,人的提高。问题不在于我是否信神,而在于,我知道人的命运被更大的力量所控制。人如何能主宰自身?尤其是面向无限的时候,只在极其有限的范畴内,这回答才是肯定的,就生存的乐趣而言,取决于你是否善于遗忘。
可我偏偏要保持记忆,并且带着不可磨灭的记忆进行抗争。我所有的不幸盖出于此。但,生活也因此得以深入,没有一个所谓的“成功”者能这样深入生活,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失败的地方,我赢得自己需要的优越感。
我关心着这世界,但我爱上了这孤独。
抽象,具体的抽象,我需要。
我愿意和人类一起得病。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重在参予又能怎样呢?是人就要和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哪怕最终所得到的仅仅是羞辱。
疼:眼睛。我希望能被我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越少越好。
又听到了机器声,这真是太糟糕了。如果飞机能加速人类之爱,倒也不是件坏事,我想我会赞同的。
仇恨。没有必要过早取消仇恨,我想看一看丽川的《仇恨》是小说还是戏剧?她的《仇恨》质量如何?人类的喜怒哀乐,一切情绪都是有质量之分的。须知,仇恨不是目的。
小瑜在写些什么?我爱波波,这是不用多说的,我也爱川谨、炎娃、李丫……就这么爱着,也是不用多说的。我不爱男人,哪怕他们是卫民、镂克、志洲、晓渡、许强……等等,我不爱他们,我只是感谢他们,并且为他们祝福,我向他们致敬。如果非得说这也是一种爱,那就爱吧,男人对女人的爱是单纯的、神圣的,而男人对男人的爱则是复杂的、智慧的。我相信爱与恨的相对性与互动性,两者均受制于具体的条件、情境或语境。所谓无缘无故的绝对的爱与恨,或许也有,只是难以理喻了。
我生活中遭遇到许多男人,都可以忽略不计,但遭遇到的不少女性,有的终生难忘,有的时常想起,这是怎么回事呢?要记住或想起很多男人,这需要对我的记忆加以严格的训练,而记住或想起女性,几乎可以不借助记忆,而是更多地出于本能。我赞美这样的本能,我从来不敢亵渎这样的本能。男性女性,通常情形下,历来经谓分明,但就伟大的“人”而言,是兼有男女双重性的,而“人”的伟大,也只能归于思想与灵魂的伟大,因此,对伟大者的记忆,在于我,亦更多地出于本能。
我的记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但我还能记住但丁,记住维吉尔,记住莎士比亚,记住歌德,记住贝多芬、梵高、惠特曼、卡夫卡、普鲁斯特,记住屈原、杜甫、李商隐、曹雪芹、鲁迅、秋瑾,我还能记住老子、孙子、佛陀、基督、穆旱默德、克里希、那穆尔提、奥修,记住苏格拉底、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康德、加缪、萨特、维特根斯坦,记住中国的四大美女,还有病恹恹的不杇的林黛玉,以及外国的数倍于中国的真实存在过的或是完全被创造出来的美女,记住路德甘地、金.曼德拉、切.格瓦拉、哈维尔.拉宾,记住王阳明、李贽、金圣叹、蔡培元、孙中山、徐锡麟、早年毛泽东,记住魏京生、王友才、江棋生、徐文立、李柏光、赵昕、马哲、熊晋仁……如此等等,可谓群星璀璨、令人仰望。我乐意于偷偷地呼喊这些名字,我愿忘了我自己。
在深深的遗忘中,仍保持一部份必须保持的记忆,这几乎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它关乎人类的幸福与尊严。
就本性而言,我是个喜欢拈花弄草的人,我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我喜欢诗歌、音乐、美术、建筑、丝绸、陶瓷、纸笔、竹、傢俱、自行车、雨中的绿邮箱……我喜欢鲜花和美酒,我不愿意成为革命家、政治家或什么领袖之类,如果非得是什么“家”,我也只愿意是个作家或思想家,因为我的内心还有极其严肃的一面,我视正义与自由高于一切之上,甚至高于性命,因此,长年以来,我这个生性风流的绍兴佬,往往是全身心地被某种从天而降的崇高情怀席卷而去。如今身陷囹圄,深知牢狱之灾最大的惩罚乃是对性的惩罚,当我孤独难熬,性欲旺盛之时,是多么悔恨当年错过的云雨之欢,有的与我相恋经年,有的投怀送抱甚至同床共枕,竟然也都错过了。值得庆幸的是,凡被错过的,在我的回忆中都更具丰富的意味,如今我拥有的,不仅是我曾经拥有过的,我也拥有了曾经失去的一切,我得承认,我的内心从未贫乏。
在这漫漫长夜,我将生命中不同程度地爱过的女孩一一提起,一一地再爱一遍。古稀之年的蔡其矫写道:“少女就是俞心樵的宗教。”诚哉斯言,对于少女们,我除了热爱与景仰,岂敢粗暴无礼?
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噪音与污浊,我迷恋于她们的清纯的肉体和芬芳的灵魂。如果现实并非完全如此,我将行使美化的特权,对她们稍作美化,事实上,我与她们或她们中的她之间,有许多更美好的被遗漏了,或是牢牢记住却难以状写。
京,我是个傻瓜,我对不起你。想当年我被崇高所困,我下不了手,我的观念是何其错误。我对你言说着崇高,越说越崇高,再也下不来,我想,我是个崇高的人,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虽然在你之前我干过,在你之后我也干过,但面对你,我为什么只想保持一个崇高的形象?这是多么地错误,多么地荒唐,多么地要不得。我还记得你的话:“一个让人心痛的傻瓜。”
京,今夜我想起你,如果今夜你能飞回北京,如果家里还只是你一个人,如果你呼叫我,召我前去,如果你已在大浴缸里备好了热水,并且已经打开了酒,打开了音乐,如果今夜我不在牢狱,而是在清华园,不,而是已经洗完了澡,穿着你父亲没有带到国外去的睡衣,已经坐在你家客厅的地毯上喝酒,我就再也不会没完没了地说得那么远,那么离谱,我就不可能伤害你,让你我得出“我不爱你”的结论。
京,如此这般错过的,又何止你一个。
春天,花在开,鸟在飞,人在坐牢;春天,我愿大家都有一个好名声;春天,诗歌是一项我值得为之犯傻的事业。

什么是伦理?答:诗歌。
什么是伦理?答:伦理就是一种或多种积极状态下的真实,是不损及到他人的对人性的张扬。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