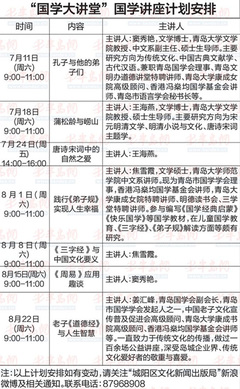善知识 2010-11-14 01:42:54 阅读50 评论5 字号:大中小订阅
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各位同修、尊敬的各位大德,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因缘,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这块宝地。在这里我要和大家说的是,首先我们要感恩十方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感恩龙天护法善神的慈悲护佑,感恩净空老法师慈悲,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殊胜的机缘,使我们大家在一起相聚,共同探讨学佛的快乐。
我今天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师父上人从正月初一到现在,好多次在网上讲关于我的事情,使我成了一个名人。在这里我告诉大家,我很惭愧,我不像师父说的那么好,只不过是我是一个比较老实的念佛人而已。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我告诉你们,就是两个字,老实,你们要把这两个字学到手就可以了。别的地方,我真没有什么值得你们学习的,这不是我谦虚。我现在来到这里,我既没有提纲也没有题目,什么都没有。我就真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是佛菩萨借我的嘴跟大家讲,来让我们一起享受学佛的快乐。
现在我给大家讲第一个题目,题目的名字就叫做[绝症不绝,两死一生]。为什么把这个作为第一个题目讲?可能是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关心我得病以后的情况,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如实地向各位作一汇报。
我是一九九九年得了一种绝症,就是红斑狼疮,这种病的死亡率特别高,能够活下来的很少很少,到现在已经十一个年头了,我现在就坐在你们的面前,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我。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我不单活了十一年,而且活得愈来愈好,愈来愈健康。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我本人,有些居士提出疑义,说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我告诉大家,现在坐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我,不是谁来扮演的。
我要给大家说,绝症不绝,两死一生,是怎么回事呢?一九九九年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当时我们黑龙江省的两个知名的医院基本上都宣布我死刑,因为当时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已经到了很重很重的程度,按照大夫说的,我随时面临死亡。为什么我绝症没绝?我跟大家说,第一个是我的心态比较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得这个病,一个是外貌特别吓人。我跟你们说说我当时的情况,当时我是头发没有几根,几乎都掉光了,头上是厚厚的疤瘌,那个嘎嘣,非常恐怖。两只手伸不直,骨节特别粗,几乎五个手指头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间隙,手指头是弯著的,像鸡爪一样,不能伸直也不能攥拳。腿膝盖肿的就像那个发面的大馒头,蹲不下,起不来。每天都在发烧,没有一天间断过。就是这样,我仍然坚持上班,就到我住院的头一天我还在上班。所以说那个形像,病到那种程度,真是随时都面临著死亡。所以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说你可真是不怕死,你知不知道你病到什么程度了?我说我知道我病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死亡的问题,所以心理上没有负担。当时这个情况,让我们全家人都非常紧张,孩子们也哭,大人也非常痛苦,他们的意思都害怕我离去。
我为什么心态比较好?就是一九九八年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西藏生死书》,这个书是一个喇嘛写的。他的语言和咱们汉族的语言不完全一样,看的时候不是看得非常懂,但是偏偏凑巧我就把那个“死”看明白了。一九九八年看到这本书以后,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了,一九九九年我得了这场重病,所以就没有思想负担,好像知道死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换过程,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也没有什么恐怖的,所以我就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心态。
当时我在医院住了十二天院,我是看了十二本《华严经》,就是宣化上人师父讲的《华严经》,它一共是二十四本,两个包装,我拿到医院去,在床头柜上,我每天都在读《华严经》,所以五十七天一共是读了十二本。就这个举动,让医院的医生、护士都非常震惊,也非常感动,他们都说,老太太得这么重的病,妳为什么心态这么好?我说,有什么不好的?既来之则安之。
所以当时医院里和我一样病的一共有几个,我年龄最大,病情最重。其他几个,有二十四岁的,有十五岁的,最小的四个月,医生说,我们几个,我是最重的,他说,妳可能随时面临死亡。我说没关系。后来有的病友说,医生不应该这么说。我说没关系,说你们,你们可能受不了;说我,我就像听故事一样,我说无所谓,到时候我就该回家,我就回家了。所以我在医院里五十七天,就是对医生也好,还是护士也好,还是病友也好,影响非常好。白天没什么事的时候,打完点滴了,其他病房的佛友、病友,都愿意到我那屋,到我那床上去坐坐,和老太太唠唠嗑。说和老太太一唠唠嗑,我们的心情就好了,好像我们都没有病一样。因为当时我们几个我是最重的,所以她们就想,老太太病这么重,心态能这么好,那我们还有啥心情不好的?所以我们在一起,我就给他们讲笑话,逗他们笑得哈哈哈,这样就使大家放松,别那么紧张。
住了五十七天,我为什么出院了?如果我在医院里,要是打针也行,吃药也行,那我肯定是走这条路了,那就打针吃药治这个病。但是我吃药也不行,打针也不行。打上针以后,十分钟左右就开始发高烧,三十九度以上。所以这样,给我治病的那个教授就说,老太太,妳这病我们研究不明白了,妳说,在医院里,妳既不能吃药,也不能打针,那这病让我们怎么给妳治?我说教授,我不难为你,我说你研究不明白,我自己回家研究去。他说妳自己回家怎么研究?妳为什么要回家去研究?我说,你们不说,这个病全世界没找到成因,就是为什么得这种病,到现在没查出原因来,当然也就没有治疗的办法。你不曾经说过,谁要把这个研究明白了,谁就得诺贝尔奖金。我说你们现在不都没得到?那我回家研究去,我要是研究出来了,我就得诺贝尔奖金了,你们就得不到了。这实际是一个笑话,但是说得大夫们都挺开心。
我记得护士长手里有一本书,是专门讲红斑狼疮的,我跟护士长说,我说护士长,妳能不能把妳那本书借给我看看?我帮著妳研究研究。护士长说,不行,这书怎么能给患者看?没有病都得吓出病来,有病都得吓死。我说不至于那么严重。她说,那不能借妳,主任要批评我的。我说那样,主任下班了,妳就借给我,我今天晚上不睡觉,我把它读完,明天早晨主任上班之前,我一定还给妳,不让妳挨批评。后来让我给护士长磨得,她说,这老太太,那我就借妳看看。就把那本书借给我了。我拿到病房以后,我一宿没睡觉,我把这本书看完了。如果是按这本书里说的,确实是像护士长说的,没病得吓出病来,有病得吓死。因为那本书里所说的这个病,没有一条是活路,各个路都是死路。我给护士长还书的时候,护士长问我,老太太,读完了么?我说读完了。她说什么感想?我说没什么感想,我就像读小说一样,把它读完了。那护士长都用那种眼神看著我,都不知道老太太怎么能这样,看这样的书,还像看小说一样。我说对,我就是像看小说一样。
因为吃药不服,打针不服,我住五十七天院,我就回家了,出院了。出院以后,我姑娘说,妈,我也不能眼看著让妳等死,我还得找地方给妳治这个病。我说姑娘,别费那事了,这个病没有哪个地方能彻底治癒,能够维持就不错了。因为我的两个学生,一个一九七四届毕业的,一个一九七0届毕业的,都是这种病走的。当时他们得这个病以后,就维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相继都走了,所以我知道这种病的严重性。当时我一九九九年得这个病的时候,因为我基本上从来不看病,所以我不知道我得的是这个病。儘管外貌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个体徵也非常明显了,我就是傻到这种份上了,不知道去看病。
后来是我一个老处长的老伴,到我办公室去,我在写材料,坐在椅子上。她站在我的背后,看著我的头上这些厚厚的大嘎嘣,没有几根头发。她就说,哎呀这都什么样了,怎么还不去看看病?因为她的老伴和我对办公桌,她就跟她老伴说,她说你能不能找个大夫给小刘看看病?完了后来她老头就给我找了一个教授,是一个内科教授,到我家去给我看的。看了以后,我感觉到这个老教授人家看明白了,但是没说。就跟我这个老处长说,没事,挺好的,五脏六腑都挺健康。她这个皮肤病我看不明白,我给她推荐个人,明天带去看看吧。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医大医院的皮肤科的教授,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就给我开了个条,第二天早上,我姑娘就带我去了。
去了以后,往大夫跟前一坐,都没化验,人家大夫就说,红斑狼疮,系统性的。一听这个名,那不正好和我那两个学生的病是一样的?我就知道了?这个病那特别严重了。当时我姑娘就哭了,完了我还说,哭啥?回家。完了那个大夫说,都这样妳还想回家,赶快住院。我说,先不住院,我那个工作太忙,我没功夫住院。大夫说了,妳是要命,还是要工作?我说最起码我工作我得交代交代。当时那天我没住院我就回家了。回家了,我姑娘说,不行,妈我还得找地方给妳看。当时听说大庆有个医院,专门看这个病,整个车就给我拉到大庆去了。当时人家说,妳必须得做切片,来确诊是不是这个病,说我这做不了,妳还得回医大医院去做。我就回医大医院了,医大医院大夫说,这个病已经非常明显了,还用做什么切片化验?就是这个病,你就在这住。所以当时就给我按下住院了。这就在住院的头一天,我还是正常上班的。虽然是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很弱了,就从我家走到省政府,按我平时走路的速度,大概也就最多不过十五分钟,这个时候我就十五分钟的路我都走不到了。在省政府和我家之间,我还有一个办公室,我就早晨上班,走到我那个办公室,上午在那办公。中午吃完饭,再到省政府去办公,就两个地方这么倒著,要是一次性从我家走到省政府,我就走不去了。就是这样,我没有耽误一天工作。所以大夫说我太能拼命了,他说,如果妳要是,假如妳要是在工作单位妳就不行了,那怎么办?我说,那该在哪走,就在哪走,那有什么了不得的?所以人家大夫都说,说妳在对待自己这个问题上,妳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我说我还觉得我挺负责任的。
就这个病,后来回来以后,我姑娘还是不甘心么。说那哈尔滨治不了,我得带妳到北京去治。我姑娘就带我到北京去了。当时是在中医院看的,这个病是确定无疑,没有错。但是他只给拿十天的药。要么妳就得十天去一趟北京,要么妳就得在北京常住。我说这样不行,咱们没有这个条件,还是回家吧。
后来有人给我姑娘介绍说,说石家庄有个医院治这个病。我姑娘又带我到石家莊去。当时到石家莊看,这个病那是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这个病了。他那是有中草药有中成药,中草药一个月的药量是四袋子,就是装大米的那个丝织袋子一共是四袋子,是一个月的药量。我和我姑娘俩扛回来的,扛到哈尔滨的。然后还有中成药,这个就是我在北京,是父女俩那看了这个病,拿了一个药,就是带包包的。然后到石家庄又拿了四袋中草药,还有中成药,这一共是两个月的药量。
回到哈尔滨以后,我先吃的包的,越吃越重,一个月下来,药也吃完了,身上的病反应更强烈了。然后第二个月就吃的那个中草药,把这四袋子药也都吃掉了,比第一个月还重。我说,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药一律停,就是这样了。
就这样以后,也可能就这么一个机缘,我的一个老同事就给我送去那个大悲咒,当时我不知道这大悲咒是幹啥的,她说,妳在家没啥事,妳就念。我说这个起什么作用?我那老大姐说,妳就别问起啥作用了,妳就当消磨时间。我就想,我也不能上班了,也不能下楼了,那我就在家念。所以我就每天念一百零八遍大悲咒,大约是得两个半小时左右,我一共念了半年多的时间。
念了这个以后,我觉得起作用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半睡不睡的时候,就觉得有人往脸上给妳抹一种东西,非常清凉。因为当时我脸,就像那个很长很长时间没下过雨的那个地,曬的七裂八瓣的,特别难受。他抹这个东西,我就觉得非常清凉,好像是在润滑似的。但是当妳睁开眼睛,什么都没有,妳再用手摸摸脸,还是那么乾巴巴的难受,就是这样。但过了一段时间,我脸上的那个斑,它就逐渐逐渐地消失了。因为这个斑,妳当时是满脸都是,非常恐怖。给我看病的那个教授都说,他说得很客观,就是意思是,你能生命维持一段时间就不错了,妳脸上这斑肯定是不掉了。我还跟人家开玩笑,我说没关系,这么大岁数了,反正也不找对象了,它不掉就不掉。
我得这个病那年是五十五岁,今年这十一年了么,我今年六十六岁。所以说,本来是绝症,实际这种病,说通俗一点,就是血癌。因为人的血液,听医生讲,是十八秒钟在人体内循环一周。那么我的全身的毒都在血液里,那你说这是不是全身都是毒了?所以这个病严重就严重在这。它这种病,不但是外貌非常恐怖,就是那个痛苦劲,一般人很难忍受。所以得了这种病,为什么有好多人承受不了,甚至有的想自杀,那是因为我经历了,所以我知道这种病的严重和痛苦,和对人的身体上的折磨、心理上的折磨。妳没法见人。因为你说我现在这个形象,你们想,就在我现在这个基础上,再长五十斤,然后满脸满身满头都是那个斑和嘎嘣,你说这个人该是一种什么形象?
所以说这种病得了以后,很多人时间不长就走了。为什么?一是病,二是恐怖,心理负担太重。我好在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我没有心理负担,我没把死当作一回事,所以我的心情一直是比较快乐的。人家大夫都好奇,说这老太太,随时面临死亡,一天还那么乐乐呵呵的,那么高兴,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就研究我,说为什么老太太心态这么好?因为那个护士长她对我非常好,她给我打点滴的时候,她哭了。我以为她挨领导批评了,我说护士长,妳怎么哭了?护士长说,那个我哭妳。我就笑了,我说我老太太还没死,妳咋就开始哭我了?完了她说,我就想,这么好的老太太,怎么得这种病?我说那该得就得。就这么的。所以说,我自己心态好,也影响别人。
你看我的学生。我一九六四年参加工作以后是当老师,小学和中学我都教,所以我的学生比较多。大一点的学生,一九七0届毕业的,大约也就小个五、六岁,六、七岁这样,所以他们上医院去看我,就四张床,认不出来我,你说,我这外貌该变化多么大。我学生去看我,扒门瞅瞅,我听叨叨说,没有老师。我说,老师在这。完了,我学生进屋以后,到我跟前,仔细的瞅,是您吗老师?我说是。这说话声像,这怎么外貌一点都没有那模样了?这个男孩女孩都开始哭。我说哭啥?老师都不哭,你们哭。我说我教你们的时候,我教你们怎么哭了吗?完了,他们都说,老师,妳咋还开玩笑?我说,有啥不开玩笑的?
所以就这么心态特别好吧,所以这个病,它还真好过来了。你说,我又不吃药了,又不打针了,回家就是念大悲咒,就把病逐渐逐渐地,就减轻了,就好过来了。
后来,我是带一个同事的同学,去找给我看过病的教授看病,她得的和我一样的病,她是大庆的,我俩还不认识。我那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刘大姐,我有一个同学得的和妳一样的病,妳带她去看看病。我说,行,来吧。我俩就约个暗号,在医大医院门前碰见的,我就带她找给我看病的那个教授去看病了。那个教授一看我,特别惊讶,惊讶什么?那眼神,那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好长时间没看见妳来了,妳还活著!就是这个眼神。完了,那教授就直直地瞅著我。我说教授,你是不是问我,妳怎么还活著?那教授就笑了,他说,妳真创造奇迹了,妳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看病?他说,我真以为妳不在了。我说,我不但在,而且还活得挺好。然后他说,那妳脸上的斑怎么掉了?因为就这个教授他说过,他说我脸上的斑不能掉。我说它自己就掉了,有人让它掉它就掉了。他说,谁让它掉的?我说,那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相信。就这样,你说是玩笑么?不是玩笑,我没法跟人家大夫说。
完了后来,我跟他熟了以后,有的大夫问我,他说,妳能不能告诉我,妳那个病怎么好的?妳脸上的斑是怎么掉的?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既不能打针,也不能吃药,这你们都是知道的,我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好的。那大夫都很惊讶。说实在的当时他可能不相信,但是现在大家看,我就坐在你对面,是不是?我这个病,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们,我就是念阿弥陀佛念好的。心诚则灵,我真是一片诚心,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就把我这个病念好了。
一九九九年到今年,十一个年头。我自己感觉,一年比一年好,愈来愈好。你看我,我跟大家不是开玩笑,我跟你们说,老法师是腊月二十八那天和我通过一次电话。通了电
话以后,我真是没有想把这件事情告诉谁,宣传宣传这件事,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我不喜欢张扬。我也没把老法师给我打电话这事,就想上多么了不得了不得,我真没有这种想法。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初一那天,老法师在网上讲《华严经》的时候提到我。因为我家里没有网,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一个佛友打电话告诉我的,说老法师在网上讲妳。我说老法师讲我什么?他就把当时老法师讲的那一段话给我学了一遍。我当时非常惊讶,我想,我说这老法师是说我么?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我和我老伴在家,我跟我老伴说,我说真是这么回事么?我老伴说,那我哪知道?这是初一。然后初叁,有佛友就把网上那个老法师讲的内容下载了,下载了以后製成光盘了,製成光盘了以后,就送到我家去了。当时我一看,老法师说了,叁天前和我通电话来著。我一想,这下糟了,那这个我不想告诉大家,那老法师讲了,大家要是看网的,肯定都看到了,然后又製成光碟这么一发,那肯定知道的人就愈来愈多了。所以就这样,我从正月初四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刚才我跟老法师说,我说老法师,你都把我讲成名人了。又像二00三年我第一张光碟《信念》,那张光碟出来以后,我家都热闹到啥程度,电话从早到晚不断,来人从早到晚不断,几乎是吃不上饭。这次又和那次差不多。所以从初四到现在,我在家里基本没有正儿八经吃过一顿饭,有时候一天连一顿饭都吃不著,因为人不断。要么就把我找出去,要么就上我家来,一拨接著一拨的,所以我没有时间吃饭,我这一个月,前天,我量量我这体重,比我春节前降了十斤体重。我跟我老伴开玩笑说,我说这还不错,它自然还减肥了。我老伴说,妳本来也不胖,妳还想减。我说它那减呗,我说我觉得这一个月没吃饭,把粮食都省了,完了人还苗条了,还漂亮了。完了,我这个人就是心比较大喜欢开玩笑。所以你看,明明是一个绝症,我就没有绝。
后面我不说[两死一生]么?我跟你们说,这[两死]是怎么个死法,第一死就是死路一条。人家医生、大夫、教授,人家都说妳这病我们研究不明白了,人家都没办法了;那个书,又一条活路没有,所以我面临的就是死路一条。第二个死就是,死心塌地。那我心就定了,反正不就是死?那就老老实实好好地念佛。所以,死路一条就逼得我死心塌的念这句阿弥陀佛。所以我就两个[死],换来我现在的生,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我的[两死一生]。
所以现在当我面对你们的时候,你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我的时候,你们相不相信?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救了我,使我一直活到现在,而且活得这么健康,这么快乐。
所以我说,[绝症不绝创奇迹,两死一生是真的,医学理论难解释,一句弥陀绵密密]。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个题目,就是[绝症不绝,两死一生]。
我再一次告诉大家,我的病是真真实实是念阿弥陀佛念好的。我为什么这次应老法师的邀请,我来到了香港?我告诉你们,我的性格是内向的,我十一年基本上不怎么出门,我也不跑道场,我就是在家里听经念佛。所以第一次约请我的时候,我记得是尤居士给我打电话,现在说起来都挺好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老法师要给妳发邀请信,想邀请妳到香港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不去,你不了解我,我说我这性格特别内向,我多少年我都不出门,我哪也找不著。我说现在老法师把我讲成名人了,你们就热闹起来了,我还不太适应。你说,我都傻到这个分上,我就这么回答的尤居士。可能尤居士还想,这人咋这么说话?我真是实际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现在因为老法师第二次约请我来香港,我必须得遵师命来香港,我也想和香港的同修们结个法缘,结个善缘,也让你们亲自看到我本人,这样会坚定你们念佛的信念。因为我们都是佛陀弟子,所以我想,我要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给诸位同修们做个好榜样。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讲,顺境和逆境的问题。
人的一生总有顺境,总有逆境,哈尔滨的同修见到我都说,刘居士,妳的条件太好了,妳环境也好,妳人也好,妳各方面都好。我跟他们说,我说,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每个人的逆境,每个人的挫折,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路,每个人都要经历。我说,我经历的可能你们都不一定经历的,我所遭遇到的痛苦,你们未必经历过。
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就说说我的逆境。
第一个例子,我的老伴是精神病患者,我们两个今年结婚四十四年。我的老伴,我俩是怎么结合的?因为我俩曾经是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我老伴高中没念完,他就进工厂参加工作了,在工厂他就得了这个精神病。因为我老伴是独生子,他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得了这个病以后,他是到处跑,还专门往大野地里跑,要是夏天的时候,就得钻高粱地、苞米地。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特务。你要见著人都是特务,家里所有的玻璃镜子,就是外面的窗户镜子,家里照人的镜子,全都得用牛皮纸糊上,为什么?看著镜子里的人都是特务,所以都得糊起来,他就病到那种严重程度。
当时我记得我们同学在一起,我们班同学就说,他说,素云,咱们班妳最善良,年华得这个病,总得有人照顾,妳嫁给他吧,妳照顾他吧。我当时就立马我就答应了,我说行,我嫁给他,我照顾他,我就到他家去了。我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因为他爸爸看了他半年,老爷子就得了高血压病,就是爸爸和妈妈,你说还谁能撵他?谁能跟著他跑?精神病患者他跑特别快,一般人撵不上他。所以我就想,那我就应该照顾他。因为精神病人在街上我也看过好多,实在太可怜,所以我不想看到我的同学落到这种境地,我去跟他爸爸妈妈说,我说我嫁给你儿子,我照顾他,你们二位老人不要担心。当时两个老人都哭了,说孩子,那我们不能眼看著妳跳火坑,他病到这种程度,连人都不认识,那我们不把妳坑了?我说总得有个人照顾他。所以,我和我老伴就是这么结合的。
我们俩结婚的那一天,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我记得那时候在饭店还不时兴包多少桌,好像就一桌,也就那么十几个人,来表示庆贺庆贺。我出去买糖,我回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景象?就是给我们主持婚礼的那个人,塞到桌子底下去了,当时大家都围著这桌子大眼瞪小眼瞅著,谁都没办法。完了我说,怎么的了?他们说年华把他塞桌子底下,不让出来。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是美利坚合众国派来的特务,幹扰婚礼,得把他塞桌子底下去。多亏那天他认识我,如果他那天要是不认识我,我也没办法。完了我就跟他商量,我说你,今天你认不认识我?他说我认识,妳今天是我的新娘。我说你要认识我,你必须把他放出来,没有他给咱主持婚礼,咱俩是非法的,他是重要角色。他说他不是特务吗?我说他不是特务,他问我,那你是不是特务?我说我不是你新娘吗?我怎么是特务呢?他说那你俩都不是特务,那行。就这样,把主持婚礼那人才从桌子里让出来的。就结婚那天就是这样。
就那个时候,他一周大约能认识我一次到两次,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是特务,那就得审问我,妳是哪国派来的?妳执行什么任务?妳的碟报机藏在什么地方了?妳得交代!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就这样的逆境,有多少人经历过?
你比如说我老伴治精神病吃那药,有丸药、有面药、有汤药,所有的药必须得我先吃,我不吃他不吃,他吃他怕药死。所以我俩是面对面坐著,我先把药吃了,他瞅著我,过十分钟左右问我,妳死没死?我说我没死。妳再吃。我再吃。又过十分钟问我,妳死没死?我说,你不看著我?我没死。那妳没死,我吃了。所以,所有他吃的药,我都得先吃。治病的那个大夫,还记得是一个老大夫,姓赵,他跟我说,他说孩子,这药妳不能吃。他说治精神病的药,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我说有什么副作用?他说最起码第一个副作用,妳会发胖的。我说那胖也就胖了吧,那没办法,我不吃他不吃啊。所以后来他的病能好到现在这种程度,我们同学、同事、亲戚朋友,都说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同学在集会的时候,他们都说,素云,妳一片真诚心,妳一片善良的心,感动了天和地。他说年华这个病能好到现在这种程度,太了不起了!
我老伴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正常的,他就是思惟和正常人还略有差别,其他的一切都正常了。所以我说,这个逆境算不算逆境?你过不过?四十四年来,应该这么说,我老伴给我出了无数无数个难题。但是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老伴,妳要是今生成佛,妳第一个要感谢我,是我助妳成佛的,我不给妳出这么多难题,妳能成佛么,妳不说,不磨不成佛?我说对对对。所以我给他写了一首诗,我说[我家大菩萨,名叫刘年华,今生来度我,我要感谢他]。我说老伴,我给你写首诗,你看看。他一看,特高兴,他说,老伴,这首诗我太喜欢了。我说,你喜欢就好,你真是咱家大菩萨。因为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刚烈的人,我在家是老姑娘,爸爸、妈妈、我姐姐,就我们四个人,爸爸妈妈和姐姐都非常宠爱我,所以我在家里没有受到过什么委屈。嫁了这么样一个丈夫以后,一下子生活环境就大改变,我不会幹的活我都学会了。所以他出了那么多难题,他真是把我考成就了。所以我今生如果我成就了,我首先要感谢我老伴,是他助我成佛的,我不能忘了他,他是我的大善知识。
这么一个难关,一般人是很难逾越的,它不是一天两天,不像朋友之间,好了我多来往,不好我少来往。这是丈夫,每天都要面对。后来,给我出的难题,我都觉得有点承受不了,我都跟他谈,我说老伴,你这个题怎么愈来愈难?他说,那妳念小学,我给妳出小学题;妳念中学,我给妳出中学题;妳念大学,我给妳出大学题;妳现在都要读博士了,妳都要上西方极乐世界了,那我不得给妳出考博士那题吗?我说对对对。他说,妳修行在升级,那我考试的题也在升级。我说老伴,真是谢谢你。但是你可知道,你这个题的难度可真是实在有点大。但是现在我可以坦然地告诉大家,我过来了,这关我一个一个都过来了。所以我现在,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学佛的快乐,所以说,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念佛是人生最大快乐,我真是切身体会到了,我非常感恩佛菩萨的慈悲,让我这一生能够走过这么一条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路,最后我能够回家。这是我要给大家说的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你就比如说我这个要命的病,你说好过么,这关?不好过。我也曾经有过失望,有过灰心,不是说一点曲折、一点波折没有。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在话,因为什么?有家庭的问题,是不是,哪一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当我得这场重病以后,我就想,我自己能不能把这个家支撑起来?因为老伴是这种情况,那这个家要靠我支撑。所以我就想,这个压力对我来说实在是有点大,因为当时我行动都很困难,我躺在床上我翻不了身,我要翻身我得坐起来,脸转过来再躺下。要再翻那面,我还得坐起来,再转过去再躺下。就是这样。那比如说做饭什么的这些活,我都照做不误,那个手虽然不太好使,但是反正笨笨磕磕的还得去办,还得去做。就这样,这些年,我经历了这样的逆境,我闯过来了,我就像跳障碍似的,我一个障碍一个障碍的我都跳过来了,我现在我离我的家门愈来愈近了,那个家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真正的故乡,我觉得我离家愈来愈近了,所以我的心非常定,非常坦然。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顺境和逆境。
因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佛友们,我们在一起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佛友就是,顺境,高兴得不得了;逆境,又痛苦地不得了。这两样都不行。顺境,你也不要高兴,都要稳稳当当的;逆境,也不要灰心丧气,也要稳稳当当的,你都把它当作平平常常的事情去对待他。所以你顺境你过去了,逆境你过去了,你这两关都过了,你才能回家。如果你顺境,你过不去,你也回不来家;逆境你过不去,你也回不了家。
再一个问题,我要给大家讲什么问题?就是学佛的人要拓开心量,要心量大。这个是我这十一年有病在家,念佛听经闻法的一个体会。我是这么想的,人不说,心大、量大,法才大。如果你心量很小,你的量必然是小的,你就的那个法也小。所以这个我真实体会到了。原来,我一个是性格比较刚烈,另外我的心量不大,遇到什么事容易想不开。这场重病,我在家听经闻法念佛,我明白了好多道理,我觉得我的心量拓开了。我现在这些年,我把我自己捨掉了,我把我自己交给阿弥陀佛了,我说我剩下的时间不给我自己,我都交给阿弥陀佛了,我就是我这个肉身,就是为众生来办事,为众生来服务。什么时候这个人世间没有我的任务了,阿弥陀佛说,妳该回家了,我就高高兴兴回家了。如果说,这个人世间有些事还需要妳继续办,那好我就留下来,老老实实的继续为众生服务,我就是那么想的。
所以人不自私,不自利,你那个心量就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宽,这个真是我的真实感受。有的佛友说,我家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我孩子如何如何。比如说上我那去,有的佛友就说,刘姐,或者有的管我叫刘姨,说妳能不能念佛给我们家谁谁迴迴向?我就笑了,我说,你怎么就想著你家的谁谁?她说,那妳早晨念佛的时候,妳怎么迴向?我说,我从来没给我家任何一个人单独地迴向,我迴向就是给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我觉得无论是你家人、他家人、谁家人,还是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全都包括在内了,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当你想到这些众生还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想,我应该怎么做,我不应该怎么做。所以现在我觉得,我没有我自己,我馀下的时间全都是交给阿弥陀佛了,全都交给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了,他们需要我办什么,我就办什么。我甚至有一次,那佛友跟我开玩笑说,说刘大姐,如果现在阿弥陀佛站在妳身边,说妳该回家了,妳一点也不打怵?一点也不犹豫?妳都安排好了?我说,这个机缘我绝对不会错过,我说,如果说现在阿弥陀佛说,妳该回家了,我都不会等一秒钟,立马我跟阿弥陀佛回家,我这个决心我是下定了。
现在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叁年一定要成就自己。这个成就,就像我刚才说的,需要我回家,我就回家;不需要我回家,需要我在这个人世间再继续做一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妨碍,我就继续在这个人世间,继续为大家做事。如果说这个心量要不拓开,人你要是以我为圆心,以自己为半径,你画个圈你把自己圈到这个圈里,你很难很难跳出去,你看到的,就像那个井底之蛙一样,你看到的,就是井那么大的一块蓝天,你不知道井外面的天是多么广阔。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跳出自我那个小圈子,画一个虚空法界众生的大圈圈,然后你的心量就会拓得非常大非常大。你们体会体会,当你什么事都为自己著想的时候,这个事你觉得不如意,那个事你也觉得不如意,好像都不顺心,你会生活在烦恼当中,生活在痛苦当中。可是当你跳出自我的小圈子,你的身心全都是为众生服务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件事,自己都会感到非常快乐。所以,你们看我现在为什么能活得这么快乐?我就是把我捨掉了。我想,捨掉小我,你得大我;捨掉了大我,你就得无我;如果你把无我再捨掉了,你得的就是大自在;当你得到大自在的时候,你就品尝到了学佛的享受和念佛的快乐。这是我真真切切的自我感受,我都如实地告诉大家。
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题目,你们看我现在面对你们,我既没有提纲,也没有发言稿,真是这样的,我就是随机说。不是说我有什么本事,我有什么能力,是十方诸佛菩萨加持。这么多场次,我在哈尔滨,他们请我去讲,我全都是没有提纲,没有稿,到哪都是这样的。他们让我準备,说妳拿个提纲,妳準备个稿。我说难为我,我準备不出来。我刚才见了老法师的时候,我还跟老法师说,我说我现在大脑还是空白,我还不知道我今天讲什么。老法师笑了,说到时候就知道讲什么了。所以坐在这,面对镜头,我现在给你们讲的,真的,不是我準备出来的。所以我说,什么叫真学佛,什么叫假学佛,我给你们说几个标準,你衡量衡量。
第一个,你学佛学到现在,你是越学烦恼越少,快乐越多?还是学到现在烦恼还是那么多,没有品尝到学佛的快乐?这是一个很根本的衡量标準。如果说我学佛,我在这念著佛,我磕著头,我读著经,但是我烦恼还照样多多。那你得反省反省,你是不是学佛有点学不对劲了?路没走对,得赶快纠正过来。如果你现在你觉得,我一年比一年轻松,一年比一年快乐,你学佛学对了,你体会到了。我不知道什么叫法味,但是我觉得那种快乐,我现在尝到了。所以咱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同修,你们品尝到这种快乐了么?如果品尝到了,继续努力,这条道是走对了。如果愈学愈烦恼,那赶快反省反省,把那个走偏差的地方给他纠过来。
再一个就是,你的信念是不是愈来愈坚定?还是左右摇摆?老法师讲我讲了那么多次,我没有完完全全都听到,因为我家没有网,有的佛友把製成的光碟一部分拿给我看了,我刚才说了,我说我没有老法师讲的那么好,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惭愧。你说在这个时候,老法师把我推举出来,说我是大家的一个好榜样,我真是不敢当,我没有做到那种程度。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你们学习的,我告诉你们,你们就学我老实就行,我念佛真是老实。这我不是在你们面前自誇和吹牛。那叁个我做到了,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我一点怀疑没有,我也不间断,我也不夹杂,我就是这一句佛号老老实实念下去。我就相信,我今生一定能够成就。所以这个学佛的路上,曲曲折折,但是一定要坚定这个信念。
如果我们学佛是走形式,我说,现在学佛有几个什么误区?
一个误区就是有所求,求什么?第一个,求眼前点切身利益,比如说孩子上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或者是做点小买卖,发点小财,这就求眼前点切身利益。第二个层次,求点人天福报。如果是带著这样的求去学佛,今生不能成就。求什么?就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求生净土。如果说带求字的,我现在就这么一个带求字的,我其他一无所求。
老法师不说[人到无求品自高]?你得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境界是怎么提升法?在你学佛念佛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当你提升自己境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学佛在进步,你会有感应的,这个感应绝对不是神通。我告诉大家,因为我是属于一个傻乎乎的老太太,我非常单纯,我今年六十六岁,按老法师说的,六十六岁,在老法师那还年轻。所以我那两天,我讲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是一个六十六岁的年轻老太太。真是这样,你们看,我已经六十六岁了,但是我的心,我的思惟,可能和儿童差不多,我特别简单。我能简单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上我们哈尔滨极乐寺,我回家的时候可以把车坐反。我坐到那面去了,下车一看,找不著家了,这是哪?这不是我家。我在哈尔滨住了多少年,我一九五四年搬到哈尔滨的,到现在多少年了,我没有几个地方我能找到。我现在我给他们叨咕叨咕,我就知道省政府,因为那是我上班的地方;再有,我现在能找到极乐寺。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第一次领著同学去极乐寺,去给那个极乐寺的师父办一件事,我把车下错了,下车一看,我就跟我同学说我说,糟了,这不是极乐寺,极乐寺怎么搬家了?完了,我同学说,妳头几天,妳不说妳还来过?我说来过。他说,那不至于这么两天,这极乐寺能搬家吧?我都能简单到这种程度。
你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哈尔滨又弄了个笑话,我一个老大姐给我弄了一张坐车的卡,她说,妳拿这个卡,妳上车就不用老準备零钱了,妳拿这卡就可以了。我那天和一个佛友上一个道场去,他们约请我去,我就跟这佛友说,我说小刁,这回我这有卡了,咱俩就不用準备零钱了,你在我后面,我在前面按这个卡。我就拿著这卡就上车了,一按按错地方了,我自己还一个劲说,它咋不响?因为那个卡一按,它不得“嗞”响一下吗?我按错地方了,我按哪去?就是投币的那个东西,我往那上按,那上能响吗?人家那边那个东西是按卡的。就是这样的笑话我是层出不穷。所以我刚才跟怎咱们那尤居士说,我说我很少到道场,我说道场的规矩我可不懂。我说我到你们这来,我需要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做,你们可告诉我,要不我又得闹笑话。真是这样的,我思想特别单纯。
你们看我现在,就今天来香港这一身打扮,都是我来之前,佛友给我打扮的,就是包括衣服、鞋,这里里外外,全都是他们给我现弄的。我说,你别给我整新衣服,新衣服我穿上我出了门,我不带劲。所以他们给我说,尽可能给妳拿旧的。里边这衣服,外边这衣服,都是我佛友今天现给我打扮上的。你说,我简单到什么程度?我从来没想我自己生活我应该怎么安排,我应该穿什么衣服,我应该吃什么饭,我从来没想过。
所以这个学佛,如果你要是太复杂了,想的事太多了,我说,你就没地方装阿弥陀佛了。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说就像一个玻璃容器,它怎么看不都是透明的吗?你要是装的都是阿弥陀佛,你怎么转看它也是阿弥陀佛,非常清凉。我说你要这儿拣点垃圾放里了,那儿拣点垃圾放里了,那你这个透明的容器它就乱了,它也不透明了。就和我们学佛的人心一样的,你要保持你的心是清净的,这样你学佛,才能学透彻、学彻底,你才真正能够达到学佛的那个境界。
我告诉大家,我学佛比较老实,就是这十一年,我没有别的什么高招,我就是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我给你们说说我的日程安排,我没有什么早课、晚课,就是人家一位问我,就说,你早课怎么安排,晚课怎么安排?我都如实告诉大家,我没有什么正规的早课、晚课,那都没有。
我是早晨,每天两点钟起床,我早晨起的比较早,起来我先拜那个叁十二观礼,拜完二十二观礼,读一部《无量寿经》,然后剩下的时间我磕头。我原来是每天早晨磕四个小时的头,一边唱佛号,一边磕头。我现在是在家里磕大约是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上外面去绕佛,因为我家住在开发区,我现在是每天早晨绕著我们住的那开发区绕佛,两步一句阿弥陀佛,大约是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这样早晨绕完佛回来,做饭收拾屋,就我老伴我俩,非常简单,吃的也简单。收拾完了以后,大约也就八点钟左右,我老伴喜欢看电视,他看著电视,我不幹扰他,我进屋里看我的光碟,他也不幹扰我。如果这一天没有什么客人同修来,我就坐那看光碟,可以连著看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七个小时、八个小时,我都可以不动地方,就看进去了。如果是来佛友,那我就把时间让给他们。我为什么早晨起来地比较早?我就是想把白天的时间给佛友留出一部分,因为有很多佛友特别愿意上我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跟我说,说上我家,就搁我家坐著,都觉得浑身舒服。我说你们简直是迷信,怎么能达到这种程度?说和你唠唠嗑,心里那不愉快那个疙瘩都解开了,来的时候是憋憋屈屈来的,走的时候是乐乐呵呵走的。我说我这都成诊所了。反正我的特点就是,对每个人我不分别,我很真诚。所以这些佛友愿意上我家,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理由。
我再给大家说,学佛学到一定的程度,有没有感应?我告诉大家,有感应。这个我刚才说了一句,绝对不是神通,我不懂神通,我也从来没追求过神通。但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可能好多事,你们不知道,我知道。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它不是我想出来的,我不会编瞎话。好多事情,经过验證,都百分之百準确。我那时候都单纯到什么程度?我们办公室是机关单位和公会合署办公,一共四个人,叁个男同志,就我一个女同志。我那个时候,我怎么给你们形容感应?我就用土话说,它就自己冒出来的,我没琢磨。你们想想,我工作量特别大,我可忙可忙了,我的主要工作是写文字材料,那大材料是一个接一个,有时候都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你说,我哪有功夫琢磨那些事?
我就给你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就知道阿拉法特怎么怎么回事,克林顿怎么怎么回事。我当时我就纳闷。这个克林顿的事和阿拉法特的事。和我有啥关系?完了还说国内谁谁谁如何如何,谁谁谁如何如何。这不,四条新闻,两条国际的,两条国内的,具体新闻我就不跟大家报告了,保密。我上我办公室,我报告了,我一进屋,我就说,诸位哥们,我给你们报告国际国内新闻。人家那叁个同事,人家就瞪眼听我报告新闻。我就说,第一个,阿拉法特如何如何;第二条,克林顿如何如何;完了第叁条,第四条,两条国内的报告了。说完了,人家那叁个同事就问我,这哪个广播电台广播的?我们咋没听著?我说[刘素云广播电台]广播的。完了,那个时候完全就当笑话,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以后有好多事,就有人就告诉我,说妳别傻呵的,那天机不能洩漏。我说啥叫天机?他说有些事那就是天机。我说,那也没告诉我,哪条是天机,不让我说;哪条不是天机,让我说。说,那妳就乾脆,妳就别说了。所以后来,他们一问我,说今天有啥新闻报告?我说没有了,天机不可洩露,我不能报告了。我就能单纯到这种程度。
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种感应,就是那个自己往外,就像那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象那个温泉。我曾经上过兴城去疗养,它那地方有温泉,那温泉池子里不有冒泡的地方,咕嘟嘟咕嘟嘟往外冒泡吗?我的这种感觉就和那个差不多,但是不一定非常贴切,它就自己就冒出来了,完了你们不知道的事,我就知道了。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不经过验證,那可能就过去了,它偏偏有的事,一件一件一件的全都验證了,而且一点误差没有。完了,他们就开始研究我,说妳怎么回事?谁告诉妳的?我说我不知道,我也听不著声,我也看不著图,我也没有影,反正我就知道。
你看,我姐就问我,小云,妳听著,谁告诉妳的?我说没有。她说,妳看著什么图了?我说也没有。她说,那妳怎么知道的?我说,那我说不出来,反正我知道。我姐说,那我咋不知道?我说,那妳咋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咋知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的事我就知道,这就是一种感应。后来我听老法师讲法的时候说了一个词,叫[至诚感通],我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至诚感通,反正我心倒是挺诚的。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在我印象当中,我好像我不会说谎话,我不打妄语,我就说真的。
我那天讲的时候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把大家都笑得够呛。我在我们居士林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说我讲真话就讲到什么程度?我调到省政府以后,和我们叁位领导一起出差到齐齐哈尔去,搞调研。我们四个人坐在火车上没啥事,就打撲克消磨时间。一个是祕书长,两个是处长,就我一个小兵,就我们四个人打撲克,我和柳处长打撲克,打升级的,祕书长和方处长对家。第一把不得亮叁吗,我运气好,第一把我就抓个“3”,抓个“3”我就亮了。亮了以后,这个莊就是我的了,然后我把底下那六张也拿起来了,把没用那六张扣下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出牌了,我开始我就出浮。祕书长就问我,说小刘,妳有大王?我没有大王。他说,妳没有大王,妳是莊家,妳怎么不调主?我说,那大王不在柳处长那么?就指我对家。柳处长就急歪了,说我没大王,妳别听她瞎说。完了祕书长说,老柳,你别说让小刘说,她不撒谎。完了,小刘,妳说怎么知道大王在老柳那?我说刚才抓完牌,他拿脚在底下踹我一脚,我理解,他就告诉我,那大王在他那,所以我就不调主,我要调主,不把他大王给调下来了?那我还得出浮。完了,柳处长还不承认,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大王。祕书长说,你别吵吵,咱出到最后,看看那王在谁手上出。那肯定是在柳处长那。最后牌都出完了,那大王不就露出来了,这不就在柳处长那吗?祕书长说,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小刘不撒谎吧?那大王就在你那!后来柳处长说,从今以后,打撲克,我再也不会跟小刘打对家了,说,这也没有说大实话能实到这种程度了。他说了一句什么,说,不是耍钱鬼耍钱鬼么,那这玩撲克,妳还那么较真?我说你耍鬼,你跟别人耍,你别跟我耍,我说我不耍鬼,我打撲克我也是真的。就能真到这种程度。可能在你们在周围大概找我这样实实在在的真诚的人,不怎么太好找吧?我都有点傻气。所以有人说,你看这老太太是不是有点傻冒?你说,她怎么能天真到这种程度?我真是天真到这种程度。
我的学生和我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说,老师,几十年过去了,妳的社会经验没增长一点,妳和教我们的时候一样。我说我教你们的时候,怎么教的你们?给我学学,我都忘了。我学生给我举个例子,说老师,妳接我们班的时候,就在黑板写了一个字。我说,我这老师的水平也真太够呛了,一个教语文的老师,第一堂课就教学生一个字,满黑板写一个字,我说我写的啥?我学生告诉我,说老师,妳就写了一个“人”字。我说,那我教你们做人,是不是?他说对,老师妳就那一堂课就说这一个字,就人,人是怎么回事,这两笔是怎么支撑的,人一生应该怎么样度过,应该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们第一堂课接受您的教诲,就是这个人字。我说,你们都几十年过去,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老师,那印象太深刻了,那个人字就像印在我的脑海里一样。他说,老师,妳那时候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他说,我们当时不太理解。那时候他们还不太大,基本上还是孩子。他说,现在我们逐渐逐渐理解了,当我们走上社会以后,我们就体会到,老师告诉我们的话是对的。但是我们在实践当中行不通,我们按照老师告诉我们的去做,我们就吃亏,占不著便宜。我说这就对了,我教给你们的都是吃亏的那个主意,没有教给你们占便宜的主意。到后来我的孩子都说,在我妈的教导下,一个傻妈妈教出来两个傻孩子。我一个姑娘一个儿子。我就告诉他们,别的,妈不会教你们;我就教你们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吃一百次亏,不要占一次便宜。我告诉他们,我说,老法师说了,你人生能活百八十年顶多了,你就拿一百岁来说,你吃一百年的亏,你最后你做佛去了,老法师说,你占大便宜了!我说,你要占便宜,占这个大便宜,别占那些小便宜;你占那些小便宜,实际上是吃大亏了。孩子们理不理解,那就看实践了,我觉得慢慢他们会理解的,会走上学佛这条道路的。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题目的中心呢,就是至诚感通。不要去求,求是求不来的,你求来的东西是假的,很可能著魔。所以我告诉大家,不要求,你就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如果你们要信我的话,真正地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你会有感应的,佛菩萨会分外地关爱你,垂爱你。我就觉得我现在就像佛菩萨的一个小娇孩似的,好像我周围有无数无数个菩萨在关爱我,我到哪都那么快乐,我到哪都那么有人缘,不是我人好,我觉得真是十方诸佛菩萨在加持我。
我现在每天早晨,我在拜佛的时候,每当我这头一磕下去的时候我的手心这么一亮,手心手指头,全都是放电,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别的佛友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他们说没有。我不知道我这种感觉是一种什么感觉,那种感觉,就是手放电,有时候甚至觉得妳全身都在放电,就是感觉,但是我看不到什么。所以说至诚感通,那就是怎么得来的,是你的真诚心感召来的,你什么样的心感召什么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善心你感召来的一定是善的,你恶心感召来的一定是恶的。
我这个人好就好在我比较善良,我自己怎么苦怎么难都可以,我看不得别人苦、别人难,就因为这个,也曾经弄过不少笑话,有的人甚至批评我,挖苦我。我当时还不太理解,怎么能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一九九一年,团中央发了一个号召,[希望工程],就是救助那些念不起书的孩子们。我没有什么崇高的境界,我当时是从《人民日报》上看著的,它那有一个表,说,如果你要是想救助这个困难学生,你就填这个表给团中央发回去,然后团中央就给你分孩子。我看了以后,我就填了两张表发回去了,我就要两个孩子。因为我得掂量掂量,我那时候的工资是九十一块钱,我没记错的话,好像不是九十就是九十一块钱,那时候是一九九一年。我想,我供两个孩子,大概还可以,所以我把表寄回去以后,团中央就给我分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是湖南的,一个男孩是汉族的,一个女孩是苗族的。所以这两个孩子,当时是让每个学期给寄二十块钱学费。我第一次寄的时候,是给这两个孩子各寄二十块钱学费。第二次,我就觉得不行,二十块钱好幹啥?所以我就给他寄五十块钱。后来我一想,五十块钱也不一定够,我就给他们寄一百块钱。然后,这两个孩子就又增加到五个孩子。怎么增加的?这个男孩的弟弟又上学了,也供不起,我说我供。女孩的两个姐姐考学了,还念不起,我说一定要去念,一个偏远山区的孩子,能够考学考出去,多么不容易,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说一定不要错这个机会,我说妳们姐三个我都供。所以这面就姐三个,那面是姐两个,我就供这五个孩子上学。
这件事,我们单位任何人不知道,我家里也任何人不知道,因为在我的思想当中,我没把它当个事,也没想这个事我应该告诉谁,所以就我自己知道。我就到时候就给这五个孩子寄钱,这是一九九一年开始。五年以后,我们单位发现了这件事情,怎么发现的?我出差没在单位,这孩子给我来的信,因为小孩他写那信就歪歪扭扭的。我的老同事一看,说她家在湖南也没什么亲戚,也没听她说过,这谁给她来的信?拆开看看。完了就把信给我拆开了,拆开以后一看,孩子们说的是这件事,孩子们有的管我叫阿姨,有的乾脆就管我叫妈,就这样的。我说这只是一个代号,你叫啥都行。所以我们单位这个老同事一看,这种情况就给我汇报上去了,汇报了,我们委领导就把我们机关党委书记批评了,就说,机关党委为什么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掌握?机关党委书记说,她自己都没说过,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也真是这么回事,我真是没说过。这机关党委书记就不是那么太高兴,挨批了。完了后来就跟我说,他说,素云,妳说在咱们委,妳穷嗖嗖的,也不是什么富户,有钱的人比妳多著了,幹嘛妳窝窝头翻跟斗,显大眼?妳供啥学生?当时说的那么一瞬间,我心里很不高兴,因为我不是什么窝窝头,我也没想翻跟头,我更没想显大眼。那你说,我五年我都没跟任何人说,那叫你们把信拆开了,你们知道了,那还怨我吗?但是我跟谁说去?后来我一想,算了,人家挨领导批评了,人家给妳发发牢骚,发发牢骚吧。所以我该咋做,我还咋做。我当时出差回来,我一回到我们单位,我就看,他们怎么看我的眼神都不对?看我什么眼神?就那样事瞅我。完了我到我们办公室,我们办公室那个门,手里拿著一遝打字的,就这么举著,[刘姨刘姨,向妳学习]。我说,啥向我学习?我一看那个题目是[向刘素云同志学习]。我就拿过来,我说这幹啥?这时候我还不知道。完了我一看,我说,谁把这事说出去了?完了他们说,看妳信了看著的,就这样事的。就这个事,后来就是暴露出来,就是这么暴露的。这不是我们单位人就知道了么,我家人不知道。后来我们单位的人上我家去,就说起这件事了。我老伴不是有毛病么?一听以后,气的够呛,我老伴说,这么大的事,妳就敢自己做主?也不和我们商量商量,妳都寄几年了。你看,一九九一年开始,五年以后么他才知道。我不会撒谎,我告诉他,寄五年了。他说以后还寄?我说以后寄也得寄,一定要把他们供到毕业。我说,要不他中途他会辍学的,念了一半不念了,多可惜。我说,你看,五个孩子,都是农村的孩子,他们能上学,太不容易了。我说,咱们拿出这一点钱,对咱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孩子来说,也可能就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那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完了,别人也说,说妳有多大能力?妳看人家有能力的人,未必幹这样的事。我说,那别人我不知道,我也没想我要怎么显我自己,或者怎么回事,我也没想要名,我也没想要利,我就想著孩子困难,我能拿出这点钱,我说,我要是有很多很多钱,我就不能供五个了,那我可能供五十个,供五百个,五千个。我没那么大能力,所以我就供这五个。
一直到二00四年,到现在,我和他们不通信了,我有病我没告诉这几个孩子。到现在为止,这五个孩子,我一个都没见过,已经都四个差不多都成家了,最準确的是叁个成家了。所以这个事,我现在跟大家说,就是说有这事,不是说你心里想显示自己,你就觉得这个事应该做我就去做了。做了以后,可能受到了一些非议,我想没关系,是不是?至于说,妳如何如何,妳自己不了解妳自己?妳知道妳自己的心是怎么想的,如果妳要是想显示自己,那妳当时妳就会自己到处去宣传了。
那你看,我一九九一年请了观音菩萨,我可是到处去宣传,我上班以后,我恨不能让我们单位所有人都知道,我家请观音菩萨了。后来我那个范大姐说,妳别傻呵呵到处宣传,妳知不知道妳是幹啥的?这个工作单位、工作环境,妳幹的这工作性质,允许妳这么宣传吗?我说,这么好的事,幹嘛不宣传?我请了观音菩萨以后,我觉得可好可好了,我就想让大家都知道。你说,我就我说这个事我可以宣传。但是我供孩子念书这个事,我根本就没想宣传。
后来一九九七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国家在湖南召开会,正好应该我去参加会,我这回我心里暗暗地高兴,我说这回我有机会,我去看看这几个孩子。完了,我就跟我们主任说,我说湖南这个会,这次是不是决定让我去?我们主任当时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主任说,不行,素云,工作离不开,派别人替妳去开。我说主任,就这个会,我求求你了,你让我自己去开,我说以后我上哪开会,你都可以派别人去替我,我说这个会你别替我,行不行?我们主任说,不行,现在工作这么急,妳要出去开个十天八天会,这个工作谁整?我说,你都给我留著,我回来幹行不行?那也不行。就这个机会我就错过了。所以从一九九一年到现在,这五个孩子,我一个都没见过。那次是柳处长上湖南,去替我开会。他临走的时候,这个事不是已经暴露了吗,就是这柳处长拆的信,我说,你得将功补过,我说这次你上湖南去替我开会,你替我去看看这五个孩子,都怎么个情况。
柳处长去了,去了以后,他和那个湖南团省委联系的,因为这个不是团中央搞的活动吗,他就和湖南的团省委联系了。团省委派人专门找这几个孩子,把那个男孩找到了,这个男孩和这个男孩的老师和他的父亲,一起去看的我们这个柳处长,到柳处长住的这个宾馆。柳处长回来跟我学,哎呀,当时我太难受了。他回来怎么跟我学?他说,小刘,你这五个孩子真是没白供,太困难了。我说怎么的?你跟我学学。他说,这个男孩他爸来的时候,穿的一个就是短袖的,小白布衫,是现管别人借的,穿的那个鞋甚至都要露脚指头了。就这样一件衣服,还是为了来看柳处长现借的。穿的那样一双鞋,柳处长说,进屋就给他跪下了,说谢谢恩人。柳处长说,你谢错了,不是我给你们孩子寄的钱,是我们小刘寄的。完了这个男孩他爸说,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有恩人的照片,但是你来了,你就是恩人,我就得给你磕头。柳处长就跟我这么学的。我说,他家靠什么生活?柳处长说两样,一个是种白菜,一个是烧炭,冬天就是烧炭,夏天就是种白菜,就靠这个维持一家的生活。他家是四口人,爸爸妈妈,两个孩子。他妈妈是病号,没有劳动力,就靠他爸爸自己劳动。所以我就想,咱们对我来说,可能我不属于那富户,但是我要和他比起来,我要比他富的多得多,我生活没有困难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对供这五个孩子,我无怨无悔,儘管我没有见到他们。我也比较惦念他们,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想,如果机缘成熟了,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看著他们的。
为什么二00四年以后我不再给他们通信了,我也不给他们打电话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病比较重,我不想让他们替我担心,我告诉他们,只要你们都生活得好,我就会生活得更好,你们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将来你们长大成人了,不要忘了,一定要用你的学识报效祖国,报效人民,我说,是祖国和人民把你们养大的,要报自己父母之恩,父母这么难供你们上这个学。那个苗族的小姑娘,他家是八口人,爸爸妈妈,六个孩子,五个女儿、一个儿子。你说,这要是供叁个学生,那肯定是供不起的。现在这几个孩子都出来了,有搞医的,当医生;有的是中学教英语的老师。是不是,你说咱们花那点钱支持他一把,值不值得?我觉得值了。儘管我的工资不高,我拿不出去多少钱,但是我觉得我尽力了。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是一种安慰,是一种快乐。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学佛的人,所有有爱心、有善良之心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能伸出你们的双手,帮他们一把,这样帮助孩子们改变他们的命运。
我给大家说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要炫耀我自己,我就说通过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大家,什么事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事我们不应该去做。反正关于享受,怎么为自己打算,我是从来没有打算过,我也没有享受过,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给大家举例子,你们如果听了我二00六年和今年讲的光碟,我不知道在哪我举了这个例子,我说我一点积蓄没有。我现在我还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到现在为止,我一点积蓄没有,这可能在一万个人里大概也找不出来几个。有人说,就说,说妳得弄点过河钱,我说啥叫过河钱?说妳走的时候,那就把妳发送出去,那不还得钱吗?我说,这个我没想过,我真没想过。完了结果就那种感觉,就我说它自己湧出来的那种感觉,我就知道,就告诉我那四句话,就是说,[我有莲花台,何须过河钱?一心为众生,弥陀来安排]。所以我是为众生服务的,我由弥陀来安排。所以我从来不为我,过去没为我自己操过心,想过事;现在我也不为我自己操心想事;今后我也不为我自己操心想事。我把我自己交给阿弥陀佛,交给众生了,我自己的事和众生的事它是一体,因为这个我听经我听明白了,我和众生是一体,所以我的事就归阿弥陀佛来安排了,你说这有多自在。
我说我现在没有积蓄,你们看我那个碟,我举那个例子,这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我就找出来那么一张存摺,是我的名,我自己非常纳闷,我不知道我哪来出来一张存摺?后来我一看,是省政府后面那个储蓄所的,我就想起来,是头几年,我们弄这个存摺攒钱,每个月开支往里边攒钱幹什么呢?买房子买断,我们公家分的那个房子,你需要买断,要交现金,我就那个攒的钱,交这个钱。后来攒够了,把钱交上去了,剩下这个底,我就忘了,现在我从柜里收拾柜,把它看著了,我就非常纳闷,不知道哪来的存摺,还是我的名。最后我又想起来了,就这个就是一共多少钱?我跟我佛友说,我有一张存摺。他们大眼睛瞪著瞅著我,就想听下文,你有多少钱?我不说,我抻著他们。待会抻不住了,问,妳有多少钱,那存摺里?我说,一百多,好像是一百零几块钱,大概一百零四块钱。我六十六岁了,到现在为止,我的积蓄就是这一百多块钱,在存摺上,这就算我的积蓄了。你说,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没啥放不下的。就这个样的例子,我可以给你能给你举出很多很多。
因为我虽然穷,但是我不自私。街上走的人,我看到他困难,我可以把他领家去,有啥困难,我手里有钱我给钱,我有衣服给衣服。你看我衣服都是佛友帮我张罗,我的衣服都送出去,包括佛友给我的衣服。我说,你们别给我弄衣服,你弄我这存不住,我随时随地就送出去了,这都是真的。你看我二00叁年那张光碟,我上极乐寺去,第一次见师父,我没裤子没鞋,真真实实的事情,一点没有虚构,答应人家去了。没有裤子,没有鞋,咋去见师父?我好朋友问我,妳咋整的,衣服呢?裤子呢?鞋呢?我说,送人送没了。就能送到那种程度。结果我好朋友回家给我找了叁条裤子,上秋玲公司买了一双鞋,给我拎到极乐寺的门口,我是在极乐寺门口的台阶上,换的新买的那双鞋去见的师父。你说出不出洋相?就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的,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我。这两天佛友们天天上我那去,琢磨怎么给我包装包装,打扮打扮。说,那去见老法师,得给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说老太太长得已经够漂亮了,不用打扮。我说我去见老法师,让老法师就见到的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我,没必要包装。那没办法,那现在是经过包装,我要不包装,要比这土得多,我穿的衣服可能扔到垃圾堆,大概都不见得有人捡,我就和那个许哲居士差不多,谁的衣服我都能捡,还不能穿新衣服。
我告诉你,我一九八四年调到省政府的,我调到省政府以后,出了一个笑话,过了不长时间,我们处长跟我说,说小刘,听没听到咱们委对妳是议论纷纷。我说议论我啥?我也不出门,我来了就进屋,我就幹我的活,下班我就回家,我说幹吗要议论我?他说,人家都问,说你们计生处,搁哪挖出一个出土文物?为什么说挖出了一个出土文物?我给你们学学我当时的打扮,就这个头型,四十年一贯制,从来没变过,我没烫过头,就四十多年就是这样。我结婚以后,那时候不让梳小辫,让剪短发,我就剪了,就一直到现在,就这个形状,四十年没变过这个头型。穿著我老伴的一个迪卡上衣,我老伴穿破了,把那领子穿破了一圈,我还不会做针线活,我就拿线给他撩上了,那个大针脚可大了,从外面看就清清楚楚,完了,他的衣服我穿著,还肥肥大大、松松大大的,又旧又破,一个蓝布裤子洗得发白,脚上穿的一双鞋是毡底鞋,烫过绒的,带个眼的,系带的。省政府没有这打扮的,所以人家别的处就问,说你们计生处搁哪挖出个出土文物?完了,我们处长说,妳来回上下楼,妳没发现人家别人都瞅妳吗?我说因为我走道目不斜视,我不看别人,所以我不知道别人看我。完了,这不就一直是可能整个省政府办公大楼,大概就我这么一个出土文物。我说那出土文物还不错呢,让你们计生处能挖著,真是挺好。
就这样,这回从正月初一开始老法师在网上讲我,我那天跟佛友开玩笑,我说没想到,当年省政府这个出土文物,让老法师给我挖出来了,我现在就是发光了,我就是,你看出土文物一出来,它不就发光了吗?给那佛友笑的。你说,这真是,大家坐在一起开玩笑,就说这些一件事一件事,都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觉得,我做人这已经快一生了,六十六年了,大半生,因为我定下叁年期限,所以我剩下时间不会太多了,我觉得我活得很真实,很自在,很潇灑,我没有那些个複杂的心思,我不会动脑筋去琢磨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所以我现在我就想,我把我的每一天都当作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昨天的事情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我不再琢磨它,我不想。明天事情还没来,我也不去想它,我不打那个妄想。我今天早晨两点钟一睁眼睛,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又多了一天念阿弥陀佛的时间,我就把今天的这一天阿弥陀佛念好,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今天要做的事就是这个。佛友有事需要我帮忙,需要我去做,我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佛友没有什么事找我,我这一天就是听经,念佛。这就是我一天的安排,所以你说我能不快乐么?我能不高兴么?我没有那些个苦恼事,要是他们跟我说什么什么苦恼,什么什么苦恼,一看我眼睛瞪得圆了,瞅著对方,那就是没听懂,就没明白,咋这么多苦恼?我没有。
所以我就有些时候,可能是不是对别人也不理解,你们看我这十一年,这是一个绝症患者,是个病号,我现在可能了,我现在照顾病号,我经常上医院去照顾病号去。你比如说北京一个人给我来个电话,说我妹妹有病了,搁医大医院住著,血癌,白血病,妳能不能去看看她?我说,你告诉我具体房间。我就去了。从我第一天见著她,到一直送她走,你们猜,我照顾她多长时间?整整九个月。我家老伴和孩子都不太理解了,说妳本身是病号,是需要别人照顾的,现在妳反而上医院去照顾病号,这不本末倒置了吗?我说,你妈现在没病,我说我现在是健康人,我的佛友有病,需要我去照顾,所以我就去照顾。我照顾她九个月,送她走。
那天白天,我给你们学学我俩唠的啥磕。下午三点,我说董婷,让妳回家妳不回家,妳在医院,妳说妳要走了,我怎么找佛友来给妳助念,人家医院也不让。那立马就得给妳穿衣服,往外折腾。完了就说,那大姐,妳想想办法,那怎么办?我是不回家。我说,那这样,妳听我吆喝。她说妳咋吆喝?我说我就吆喝,我说董婷,妳这个神识赶快跳出妳这个臭皮囊,我得给妳换衣服,我说妳听不听吆喝?董婷哈哈笑了,说刘姐,我听妳吆喝,说妳就吆喝吧,妳吆喝我就往外跳。我说好,说话算数。这是我俩那天叁点多钟说的话。她是那天晚上,下半夜叁点十五走的,就这么长时间,她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她姑娘,我俩,她姑娘一个劲地哭。我说妳别哭,帮刘姨给妳妈穿衣服。这孩子也顾不得。我现在我都想,我不知道我怎么一个人我把衣服给她穿上了。我就先,我真吆喝了,我说,董婷,咱俩不约好了,我一吆喝,妳就跳,我说现在就吆喝,妳马上跳。我就把刚才吆喝那一段话吆喝出来了,完了,我就给她穿裤子。我一个人提不上,我说董婷,抬,就这么一提,我就把她裤子给她穿上了,把衣服给她穿上了。
穿鞋的时候可糟了,两只鞋一个鞋底。我头一回面对真正的死人,就我自己面对死人,我头一回。一穿鞋,怎么就一只鞋底?我想这怎么办?你说,这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智慧,我就喊,心里喊,阿弥陀佛,快点送鞋!阿弥陀佛啊快点送鞋!我真是这么喊的。完了,就把衣服都给她先穿上了。就这时候来了一个帮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阿弥陀佛派来的,来了一个男的,我就问他,我说哪有卖鞋的?快点整一双鞋来。他说我妹妹是卖这个鞋的,我给我妹妹打个电话。他就给他妹妹打个电话,十五分钟他妹妹来了,把鞋拿来了,鞋的问题解决了。你说,这不是两只鞋都有底了,把鞋穿上了。她还是受戒,她掛著叫搭衣,因为我受五戒,我不会搭衣,我不会掛那个、别那个。完了,我说,妳会不会这?他说我会。结果把搭衣也给穿上了,我俩就把她整得利利索索的。这时候她弟弟才来,来了以后就整车,就要拉到那个西华园什么送冰柜。我当时我说了一句,我说不能送冰柜,那是刚走一个多小时,送冰柜,那不下寒冰地狱吗?人家他弟弟说,我们不信这个。他弟弟不信这个。所以我说,念了半辈子佛,最后在医院走了,走了一个多小时,就被人家送到寒冰地狱去了。我就跟人家去了,不甘心,我就去了,人家给放那个柜里别插电,别给她送冷,完了,人家那个人说,妳说了算,我说了算?不送冷出毛病妳负责?当时就把电送上了,那你没办法,我就这么大本事了。完了反正从医院一直给她送冰柜里,眼瞅她进冰柜的,你说心里难不难受,都是同修,你这佛念的。如果要在家,何苦这样?如果在家,我肯定,最少我给她念二十四小时。你说我一个人送她,完了说的又不算,最后这个佛友就这么的就走了。那走了以后那上哪去,那不很明显吗?那不会上好地方去,多痛苦!
那有一个佛友,不就是送那里以后,第二天早晨,就是等出殡的时候,十个手指头都从那叫棺材还是啥,抠出来了。他们给我讲的,太阴森恐怖了!就是死了以后,就给他送到冰柜里,可能他神识没有走,所以他特别痛苦,他的手大概就抠,就把棺材那两个帮都抠透了。十个手指头,等出殡的时候,都在外边伸著,你说是不是多么悲惨!就是我说十个手指头在外伸著,这个老居士,特别有钱,有好多好多钱,给儿孙们分的,最后因为钱打仗,人家都不顾她了,钱分了。有的分的多,有的分的少,分的多的不嫌多,分的少的嫌少,所以这儿孙们就开始打官司打仗,就把这老太太撩在旁边不管。完了后来又翻出来十万多块钱的券,说也能换钱,就开始分这券。老太太在旁边躺著,听得清清楚楚,一口气没上来,气死了。气死了正好,痛快地送冰柜去,就这么的把她送冰柜了。送冰柜以后,完了就十个手指头就抠出去了。
所以我说,咱们学佛人,千万要有一个正知正见,我的理念就是积福积德,不积财,积
财是个大祸害,你不但给儿女留不下什么财富,你真是给他们留的是魔难。要不我二00五年病重那次,我那次我真是我可能要回家了,真準备回家了,结果那次没回去,叫那些佛友把我哭回来了,非得让阿弥陀佛别接我走,就这样的我就没走了。我那次就给我孩子们写了遗嘱,我那遗嘱真是就非常简单,我就这么写的,我说,孩子们,妈妈一生清贫,没有给你们留下任何财富,如果说妈妈能给你们留下什么,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如果你们认识了,妈妈给你们留下的是无价之宝;如果你们不认识,妈妈什么也没给你们留。这就是我给我的儿女留的遗嘱,很简单。后来我们一个老大姐看了不就哭了吗?我说大姐,妳怎么哭了?她说素云,没看谁写遗嘱这么写。我说我不知道别人写遗嘱咋写,那我的遗嘱就是这个,我就要这么嘱咐他们。后来我跟佛友说,我说如果说我给儿子留的是阿弥陀佛,我给姑娘留的是南无阿弥陀佛,那还多俩字。我都一样,都四个字,阿弥陀佛,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你们啥也别争。妳说我一无钱,二无东西,我说我死了以后,保证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他们不会因为这个打仗。因为都知道,清清白白,啥没有,没有啥分的,所以不会打仗的,也不会立马就把我送冰柜去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我现在真是劝大家,生活要简单,想的要简单,吃的要简单,住的要简单,为人处事要简单,要把複杂的事情变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变得更加简单。这样我们学佛才会有成效,真的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今天罗罗嗦嗦跟大家说了些什么,真是不知道是谁借我的嘴跟大家说的这一番话,如果说对了,那是十方诸佛菩萨慈悲加持;如果说错了,那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因果自负。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些,阿弥陀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