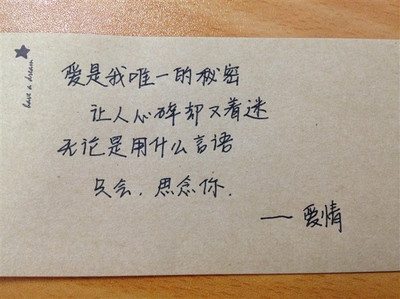看来我是老了,有时会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怀念一起吃一根腊肠,一起在操场上露宿,一起在水库边的草地上吃西红柿的那些旧友。平日里在外工作,或者忙着读书,只有到了过年回家,才有机会给老同学打个电话,或者聚一聚。
吉大的旧友,是我时时会梦见的。但即使没有变得生份,也不见得还有见面的机会了。现在,跟毛毛都聊不起来。即使是离得最近的小符,如今一年到头也没有一条信息了。高中三年的回忆,本来就不那么美妙,同学间自然联系更少。初中的同学,原在2005年聚过,整个年级,百来号人,我嫌闹腾,而且许多是不认识的,因此第二届聚会就没有参加。之后他们也没有再搞,据说是因为成立的同学会,只管搞摊派,人又不团结,所以大家没了兴致。
今年似乎也不例外。不想在年初三早上,带孩子们出去买玩具,在楼下见到春凤,上来我家坐了坐。初四中午,她就约了我和水清、雪琼,到英武家里吃了个饭。春凤从自家农场里带的肥鸡和油菜,好吃得紧。她们大谈怪力乱神,我也只姑妄听之。
这次的聚会,虽然说人不多,但比同学会这种形式要好。过去有句玩话:“没事开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倒不在这里。虽然当年都是同窗,但现在处境早分了高低。或者挖矿,或者养殖,或做装修,或包工程,身家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也不乏其人。其次的,或者到了审计局,或做村官,或在机关,能捞的也捞了不少。就算当教师,总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在家务农的,还有在外打工的、当保安的,语言间不免多了几分优越感。
我曾经也有心思见一中老同学。但是,这几年看下来,有钱的人,总爱和有钱的人聚。即使不为共享资源,单拿爱好来说,就已经大相径庭。比如打麻将,他们上手就是五十一百的,叫只打一二的卫生麻将的人情何以堪?我也不大欣赏他们一见面就赌钱,而另外一些不愿意赌,或者没资本赌的同学就得倒茶倒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本来在各人的生活中已经足够多,够让人讨厌了,又何必扩大到同学当中呢。至于那些把农村改造工程款打进自己账户的人,或者当计生干部,又或者嫁给计生干部的人,我看不见得还有多少共同语言。
穷的同学,或者,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发展中的同学,心里面是不愿意跟这些有钱同学玩的。曾经都在一个校园里,现在有人动不动拿钱来显摆,请吃饭,请唱K,自己吃了别人的请,就有了低人一头的感觉,又何苦来哉。也有一些同学,为了想借钱装修,为了能够调动单位,而对某些人特别热情。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看在我这个原教旨主义者的眼里,就不那么有趣了。
我是老了,我曾经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几个人坐下来,聊聊过去,不要赌钱,也不要攀比。但现在我已经打消这个念想,阶层的分野已经是如此鲜明,如何能够不影响到各人的意识。如果不承认这个现实,倒是我这个唯物主义者的天真了。
曾经的同学,炫耀所谓的国际幼儿园,和豪华的房子。这么说来,打败我的,其实不是天真,而是“无鞋”。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没裤子穿的年代了,也不会有人真的没有鞋子。但是,路边小摊上买来的鞋子,对穿几千块钱的名牌的人来说,跟“无鞋”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我还记得,从小时候起,我就是喜欢跟“无鞋”的同学做朋友的,难道长大之后,反而为“所识穷乏者德我而为之”?我愿意和我爱的小美一道,拥抱彼此的天真,任凭这个时代,是如何的“无鞋”。至于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将过去唤醒,唤醒了也只是僵尸。
又想起我素习的新中国史。起初大家也不过是满脚泥的庄稼汉。后来因为买不起鞋的人太多了,有钱人的鞋子都卖不出去,这种“和鞋”就不复存在了,那些无鞋汉,无套裤汉,就一起拿着两把菜刀,去冲破这种原以为牢不可破的现实了。而现在,虽然又分出了所谓红色贵族和农民工,“无鞋”又变成了一种现实,但是总有一天,要小心鞋卖不出去。昨天有一个同学说,人总是现实的。而我赞同黑格尔:凡是合乎理性的,才是真正现实的。过于天真,容易不顾现实。过于现实了,就一定活得快乐吗?所以,还是取中庸之道的好。
这当然是题外话了。食肉者谋之就好了,我并不想扯进去。省点力气,打我的卫生麻将去。人生只在呼吸间,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累?不如好好地爱自己的爱人,有点钱有点闲,就追寻真理,除此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2013-2-14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