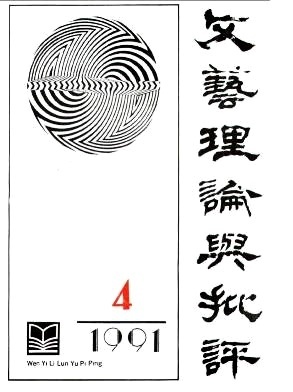(1942-1978) 何休

三、后期第三阶段——“文革”10年(1966-1977)
何其芳的“文革”阶段也是值得研究的,他的思想状态与别人显然不同。在“文革”阶段,何其芳也处于受冲击、受审判的不正常状态,自然不会有什么正规的文学与创作活动;但他的“文革心态”倒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何其芳自信20余年积极宣传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使他在“文革”浪潮中坚信自己的“一贯正确”,绝不承认自己有“反毛泽东思想”的表现;但由于他在一段时间里也发表过引起过批评、争议的文章,如《回答》那种诉说心曲的诗篇,《论阿Q》《论红楼梦》提出超阶级的“典型共名说”,从“文革”极左思潮的高度看来,他只得承认自己“尚有小错”。何其芳在“文革”中的这种自省的乐观心态,使他在下放牛棚时仍然能够以乐观的心态去劳动、工作和学习,还编出了总结养猪经验的《养猪三字诀》,写出了8首新诗和36首旧体诗,成为新中国以来他所没有的高产量,表现了相当的政治热情。
(二)经过“文革”的“洗礼”,何其芳构划着按照“高大全”的理想化创作原则,创作多部头的长篇小说,表现自己一代人“走向革命的历程”。他积极收集素材,进行创作准备,雄心勃勃地就要开始自己“真正做想做的工作”了,并写了出长篇小说的头两章。只是由于他身体实在太差,没有能够完成其宏伟的创作计划,就于1977年就过早地去世了。按照已经写出的头两章来推测:即使这部小说能创作出来,离生活的真实性将是相差甚远的,其审美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正因为如此,何其芳终其一生,都没有从长期“左”的思潮和文艺政策中解放出来,反倒还受着“文革”意识的严重束缚。直到临死之前,他都不会怀疑毛泽东会犯错误,也不会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他是带着过去的“主流意识”,再加上“文革意识”,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有研究家尖锐地指出:何其芳经历“文革”之后,“为不该忏悔的而忏悔,该忏悔的却没有忏悔”⑨ 。这不是醒悟,而是一种倒退。但这不能怨他,他没有捱到醒悟的时间,获得醒悟的机会,像其他的文艺家那样(如周扬)有进行反思的机会。
历史和人生,总是那样令人遗憾。何其芳没有等到1978年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来得及清理自己的思想,把他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想个透彻,也来不及重新构思拟议中的多部头长篇小说,这样就令人遗憾地走了!这是何其芳的人生悲剧,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典型性的重要的文艺家的悲剧。
四、“何其芳现象”的实质与经验教训
何其芳先生已经走远了,我们不会忘记:在20世纪的文学活动中,他曾有过的天才和创造;他一生的勤奋、困惑及其给予我们的正、反两个方面的馈赠。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他,纪念他呢?又怎样认识“何其芳现象”的实质,及其发生的原因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