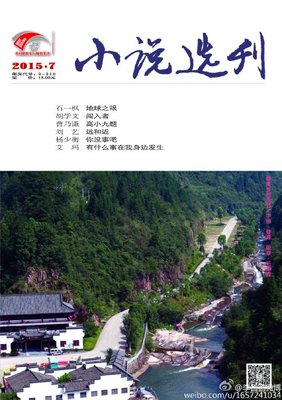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他学贯中西,既接受了扎实的传统古典式教育,又深得西方文学以及哲学的浸染,这自然使得废名早期的乡土抒情小说显现颇具现代因素的实验性特点。废名于1922年开始进行小说的创作,从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到后来的《桃园》,废名的小说似乎越来越具有禅意和田园化的理想色彩,他语言近乎干燥的简洁也使得废名的小说常常被贴上“晦涩”的标签,读者读起来觉得“隔”,所以废名名声很大,但相比较别的乡土作家的作品,却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关注。直到沈从文、萧红之后,废名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才被关注和挖掘。《浣衣母》是废名在1923年的作品,后来被收入到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中,那么就让我们以这篇小说为线索,来浅析废名小说之所以“隔”的原因,即是他小说中鲜明的实验性特点。
一.独特视角中的情节淡化
废名的小说初读时的感觉,我想引用鲁迅先生在《域外小说集·序》中的一句话:“旧派文人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的确,废名的小说包括萧红等人的小说中都没有很跌宕起伏的情节,因而读者常会产生对情节的阅读期望破灭之后的失落,传统小说依赖情节的产生——发展——高潮——结果,穿梭主要人物的言行举止,最终达到一种作家既设情境的再现,使读者产生共鸣从而引起审美快感。如果带着这样的心理去读废名的小说是必然要失望的。以《浣衣母》为例,如果非要整理出一条故事线索来就是:浣衣妇李妈忽然成了众议的焦点,而后就是对李妈生平的描述,丈夫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两个儿子也不成器,身边只有一个驼背的女儿作陪,周围的邻居都跟照顾她,孩子们也乐于来李妈这嬉戏,李妈仿佛成了公共的母亲,驼背姑娘死后有一个汉字来到李妈这里支摊卖茶,在邻人的议论中又最终离去。这个小说有相对完整的情节,但没有剧烈的矛盾冲突,小说的进程始终是舒缓而平静的。“情节”这一要素在这里并未消失,只是被淡化,然而在淡化中,读者却能够在故事文本之外汲取到一种情趣,一种情绪,一种悲与喜的哲理。
再看叙述者对情节的阐述,叙述者并不充当角色,不介入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他的讲述似乎很客观,但往往我们又能在不能言明的瞬间感知到叙述者主观情绪的存在,这是在“物我交融”中才能产生的“客观叙述”。如小说结尾处说道“那汉子不能不走。李妈在这世界上唯一的希望,是她的逃到什么地方的冤家,倘若他没有吃子弹,倘若他的脾气改过来。”这句话的叙述视角是通篇主观流露较为明显的一处。这句话是源自李妈之口,还是叙述者自己略带感伤的叹息呢?这个界限是模糊的。在废名的小说中,读者无法直接面对故事,故事如何开始,人物的活动,情节的进行都受控于这个隐形的叙述者,由他用声音传递给读者,而后再在读者的头脑中生成画面,还原于文本。从这个角度讲,废名的小说是应该被读出来的,这样才能体会到废名小说中颇具实验性的独特叙述视角,在沈从文的《边城》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到相似的叙述视角。
二.背景因素地位的提升
小说除却情节、人物之外,还有一个要素就是背景了,小说的人物之一也是“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废名的早期作品同王鲁彦、台静农等人的作品一起被归入乡土小说的大系中,在广阔的具有地域色彩的故土背景中表达作者的主观情绪,但我认为,相对于其他乡土作家,废名的乡土背景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背景”了,在废名小说的整体构建中,“背景”上升成为一种“意境”,他对背景的刻画营造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禅意的平静,其中蕴含着平凡人的悲恸和生存的伟大,从而彰显不同于其他作家批判、揭露、讽刺的独特立场来。很难说背景和主人公哪个更占据主体地位,比之从前的小说,废名小说已经将背景的地位大大的提升了,背景不再是单纯的主人公活动的环境,它有沙滩有竹林有水,人的行动穿插其中,像山水画里透出的一点寺庙的尖,背景成为人物内心世界的直观反映,如
流水激着桥柱,打破死一般的静寂,在这静寂的喧嚣当中,偶然听见尖锐而微弱的声音,便是驼背姑娘从梦里惊醒喊叫妈妈
“流水”和“夜”,这一动一静既冲突着又奇异地融合着,“静寂的喧嚣”这正是李妈和驼背女儿相依为命的真实写照,对亲人和人事的诸多失望是内心的喧嚣,然后河水的平静也将心灵的波澜尽数消解。“流水”“桥”这些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生活而打上了象征的色彩,有了境外之情,废名小说的禅意正是来自背景地位的拔升。周作人说废名的小说应该在树荫下细读,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吧。
三,悲剧意识的表现形式
废名小说笔下的人物,其生老病死都是平平常常一笔带过,李妈青春的流逝,驼背姑娘的死,李妈两个儿子的一死一逃,都是一笔叙过就不再提及,这甚至会给人一种逃避的感觉:“李妈的哥儿长大了,酒鬼父亲的模型,也渐渐现得没有一点差讹了。李妈诅咒他们死;一个真的于是死了,哪一个逃到什么地方当兵”。这样的叙写平淡而冷静,死亡难道就此不痛了么?然而在驼背姑娘死后,李妈内心的悲恸和孤寂才在下面这段景物描写中透露出来:“除掉远方的行人从桥上行过来,只有杨柳树上的蝉鸣。朝南望去,远远一带山坡,山巅黑簇族,好像正在操演的兵队,然而李妈知道这是松林;还有层层叠叠被青草覆盖着的地方,比河边荒地更是冷静。”草木皆兵,松林,荒地,透过这一系列的景物描写,我们能够感知到李妈心中的悲怆如平静河面下的暗流,虽无痕迹却静默汹涌。废名实验性的悲剧意识的变达正是隐藏在平凡的人事之后的,不依赖情节的冲突,而在细小灵魂的背后表达出来一种宽容和坚韧。以慈悲的心写人世悲苦,在平凡的生活中将这悲苦消融。废名在电光火石类型的悲剧变现方式又实验了一条似乎圆满而实则悲怆的平静悲剧。
另外,废名小说喜用孩子的眼光来观照人生,在成人的意外中点染出悲剧的意味,如
李妈的气愤,统行吐在驼背姑娘头上了。驼背姑娘再也不能够笑,呜呜咽咽的
哭着。她不是怪妈妈,也不是恼哥哥,酒鬼父亲脑里连影子也没有,更说不上怨,
她只是呜呜咽咽的哭着。
她谁都没有埋怨却不知所以的悲从中来,呜咽地哭,李妈不再呵斥她“又把她拉在怀里,理一理她的因为匆忙而散到额上的头发。”废名的孩子气的用笔有一种天真拙朴的内蕴在里面,不动声色的打动人心。
《浣衣母》的结局采取的是开放式结局。老无所依的李妈后来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这种开放式的结局在西方小说中是很常见的,这种结局的采用也使废名的小说呈现出了一种现代性与实验性。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向来是背地里期望着大团圆,亦或是有几分遗憾的小团圆,最起码也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是非归途,《浣衣母》开放式的结局能够带来一种馀味将故事蔓延到现实生活中,人世的琐碎、故事的喜悲加上无结局的结局,这很容易碰撞出一种悲剧意识,发人深思。废名自己也说过,自以为中国人是缺乏一种悲剧意识的,他的这种思想在这篇小说中有较为明确的表现。
四,废名小说语言上的实验性。
废名在小说创作中最直观的实验性特色就是小说语言的运用。以散文化的语言介入小说创作在文学史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但像废名这样以诗话语言来写小说而卓有成就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确是独一无二的。废名推崇晚唐诗,尤其是绝句简约自然的风致,欣赏李商隐的诗歌意境,废名小说不可避免地追求一种诗歌式的意境。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上,他打破了常规的叙述顺序,现代诗歌的一些手法也自然地运用其中,仍以《浣衣母》中的句子为例来具体分析废名诗化小说的语言实验性。
废名小说语言简奥隐约,简练到几乎无一字多余,这显然是受了古诗的熏陶的,让我们来看一段李妈与驼背姑娘的对话,女儿提前烧了早饭,反而被母亲埋怨。
“弄谁饭?——你!”
“·······”
“糟蹋粮食!丫头!”
简短有力,在废名的其他小说如《我的邻舍》、《河上柳》等作品中,人物间的对话都是如此简单直接的,字句之间却不无逻辑性和跳跃感,再看下面一句“只有城门口面店的小家伙,同驴子贪恋河边的青草一样,时时刻刻跑到土坡;然而李妈似乎看不见这爬来爬去的小虫,荷包里虽然有铜子,糖果是不再买的了。”从“孩子”到“虫子”,两个意象之间的联系仅在于他们都在动,这种跳跃性的思维显然受到了现代诗的影响。
诗化小说虽然在语言上必然破坏情节上的某种连贯性,造成意义上的断层,但是诗化的语言又能使读者在情节之外收获到一种韵味与情调,作为某种人生状态和人生况味的具体体现而存在。废名在诗化小说上的实验性对后来的作家,尤其是萧红的影响是很大的,如萧红在短篇小说《牛车上》开头写道“金花菜在三月的末梢就开遍了溪边”,诗的意象,诗的跳跃都可以寻到。
以上四点分别从四个方面浅析了废名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实验性特点,他在小说语言、小说情节构建等方面做的有益探索和实验为随后的小说创作指出了一条新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