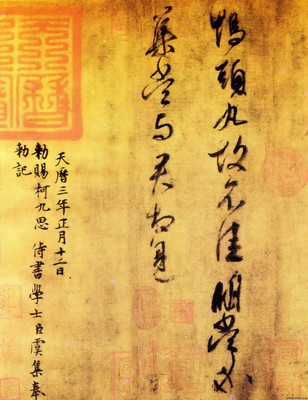尤金·尤涅斯库 著
高行健 译
第一场
[一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内室,几张英国安乐椅。英国之夜。史密斯先生靠在他的安乐椅上,穿着英国拖鞋,抽着他的英国烟斗,在英国壁炉旁边,读着一份英国报纸。他戴一副英国眼镜,一嘴花白的英国小胡子。史密斯夫人是个英国女人,正坐在他身旁的另一张英国安乐椅里,在缝补英国袜子。英国的沉默良久①。英国挂钟敲着英国的十七点钟。
史密斯夫人:哟,九点钟了。我们喝了汤,吃了鱼,猪油煎土豆和英国色拉。孩子们喝了英国酒,今儿晚上吃得真好。要知道我们住在伦敦郊区,我们家又姓史密斯呀。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猪油煎土豆特棒。拌色拉的油原先可没哈喇味。拐角那家杂货铺子的油比对面那家杂货铺子的好,甚至比坡下那家杂货铺卖的还好。但是我不愿意说他们这些铺子卖的油差。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不管怎么说,拐角那家铺子的油比哪家的都好……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玛丽今儿土豆烧得好。上回她可没烧好,土豆要烧得好我才爱吃。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鱼倒是新鲜。我可没馋嘴,就吃了两块,不,三块。吃得我拉肚子。你也吃了三块,可你那第三块比头两块小,我可比你吃的多得多。今晚我比你吃得下。怎么搞的?往常总是你吃得多,你可不是个没胃口的人呀。
[史密斯先生打了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可就是汤多少咸了点,反正比你有味儿,嗳嗳嗳!大葱搁多了,洋葱少了。真后悔没叫玛丽在汤里加点大料,下回我可得自己动手。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我们这小儿子也想喝啤酒,他将来准是个酒鬼,象你。饭桌上你没见他瞅着酒瓶那副样子?可我呀,往他杯子里倒白水。他渴了,照喝。埃莱娜象我,是个好主妇,会管家,会弹琴。她才不要喝英国啤酒呢,就象我们小女儿只喝奶吃粥。才两岁就看得出来。她叫培吉②。芸豆奶油馅饼特棒,吃甜点心的时候最好能喝上一小杯澳大利亚的勃艮第③葡萄酒。可我没让葡萄酒上桌,免得让孩子们学会喝。得教他们生活简朴、有节制才好。
[史密斯先生照样看他的报,打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帕克太太认识一个杂货店老板,是个罗马尼亚人,叫波彼斯库·罗森费尔德,他刚从君士坦丁堡来,是个做酸牛奶的大行家,安德烈堡的酸奶制造商学校毕业的。明天我去找他买一口专做罗马尼亚民间④酸奶用的大铁锅来,在伦敦郊区不常碰上这种货。
[史密斯先生照样读他的报,打个响舌。
史密斯夫人:酸奶酪对胃病、腰子病、盲肠炎和偶像崇拜症都有特效。这是常给我们邻居乔恩家的孩子看病的那个麦根基·金大夫告诉我的。他是个好大夫,信得过的。他自己没用过的药是从来不开的。他替帕克动手术前,先给自己的肝脏开刀,尽管他什么病也没有。
史密斯先生:那为什么他自己动手术没事,帕克倒被他治死了呢?
史密斯夫人:他自己的手术成功了,可帕克的手术没做好呀。
史密斯先生:麦根基总归不是好大夫。他俩的手术要不都成功,要不都该完蛋。
史密斯夫人:为什么?
史密斯先生:一个有良心的医生要是不能同病人共同把病治好就应该同病人一块去死。遇到海浪,船长总是同他的船一起殉职,不自个儿偷生。
史密斯夫人:病人能比做船?
史密斯先生:干吗不能?船也有船的毛病嘛,再说,你那个大夫跟军舰⑤一样健康。所以说,他得和病人同时暴死,象大夫同他的船一起完蛋一样。
史密斯夫人:噢!我原先没想到……或许有道理……那——这得出什么结论呢?
史密斯先生:这就是说,医生没有不是江湖骗子的,而病人也都是一路货色。英国只有海军才是正直的。
史密斯夫人:水手可不。
史密斯先生:那当然。
[间歇。
史密斯先生:(报纸仍然不离手)有件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民事栏里总登去世的人的年龄,却从来不登婴儿的年龄?真荒唐。
史密斯夫人:这我可从来还没有想到过!
[又一阵沉默。钟敲七下。静场。钟敲三下。静场。钟半下也不敲。
史密斯先生:(报纸不离手)咦,这儿登着勃比·华特森死了。
史密斯夫人:我的天,这个可怜人,他什么时候死的?
史密斯先生:你干吗这副吃惊的样子?你明明知道,他死了有两年了。你不记得了?一年半前你还去送过葬的。
史密斯夫人:我当然记得,一想就想起来了。可我不懂,你看到报上这消息为什么也这样吃惊?
史密斯先生:报上没有。是三年前有人讲他死了,我靠联想才想起这事来了。
史密斯夫人:死得真可惜!他还保养得这样好。
史密斯先生:这是英国最出色的尸首!他还不显老。可怜的勃比,死了四年了,还热呼呼的,一具真正的活尸!他当时多快活啊!
史密斯夫人:这可怜的女人勃比。
史密斯先生:这勃比是男的,你怎么说成女的了?
史密斯夫人:不,我想到是他妻子。她同他丈夫勃比一样,也叫勃比·华特森。因为他们俩同名同姓,见到他们俩在一起,你就分不清谁是谁了。直到男的死了,这才真知道谁是谁了。可至今还有人把她同死者弄混的,还吊唁她呢。你认识她?
史密斯先生:我只是在给勃比送葬的时候偶然见过她一次。
史密斯夫人:我从没见过她,她漂亮吗?
史密斯先生:她五官端正,可说不上漂亮。块头太大,太壮实了。她五官不正,倒可以说很漂亮。个子太小又太瘦。她是教唱歌的。
[钟敲五下。间歇多时。
史密斯夫人:这一对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史密斯先生:最迟明年春天吧!
史密斯夫人:那得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史密斯先生:要送份结婚礼物。我在考虑送什么。
史密斯夫人:从我们结婚别人送的那七个银盘中拿一个去送他们不行吗?我们从来没用过。
[短暂的静场。钟敲了两下。
史密斯夫人:她年纪轻轻就守寡,够她伤心的了。
史密斯先生:幸亏他们没孩子。
史密斯夫人:他们就差没孩子!可怜的女人,不然叫她怎么办?
史密斯先生:他还年青,还可以再结婚。男人死了她巴不得。
史密斯夫人:那谁照看孩子呢?他们有一男一女呀。这两个孩子叫什么?
史密斯先生:勃比和勃比,同他们父母的名字一样。勃比·华特森的叔父,那个老勃比·华特森有钱,他喜欢男孩子。勃比的教育他完全可以负担得起。
史密斯夫人:那没说的。勃比·华特森的姑妈老勃比·华特森也可以把小姑娘勃比·华特森的教育担当起来。这样一来,勃比·华特森的娘勃比也可以再结婚了。她有没有对象?
史密斯先生:有呀,勃比·华特森的一位堂兄。
史密斯夫人:谁?勃比·华特森?
史密斯先生:你说的是哪个勃比·华特森?
史密斯夫人:说的就是勃比·华特森呀,死去了的勃比·华特森的另一位叔父老勃比·华特森的儿子。
史密斯先生:不对,不是他,是另一个。是死了的勃比·华特森的姑妈勃比·华特的儿子。
史密斯夫人:你是说勃比·华特森,那个推销员?
史密斯先生:勃比·华特森全家都是推销员。
史密斯夫人:多苦的行当!可赚大钱呀。
史密斯先生:是呀,只要没有竞争。
史密斯夫人:什么时候才没竞争?
史密斯先生:星期二,星期四同星期二。
史密斯夫人:一个礼拜有三天?勃比·华特森在那几天里干吗?
史密斯先生:他休息,睡觉。
史密斯夫人:为什么这三天没竞争他们就不干活呢?
史密斯先生:我哪能都知道。我不能一一回答你这些愚蠢的问题。
史密斯夫人:(有伤自尊心)你说这话侮辱我?
史密斯先生:(满脸微笑)你明知道没这个意思。
史密斯夫人:男人都是一路货!你们呆在那里,不是叼着烟卷,就是抹粉、擦口红,一天五十次,要不就是一个劲没完没了灌黄汤!
史密斯先生:要是你见到男人象女人们一样,整天抽烟、擦粉、抹口红、喝威士忌,你又有何感想呢?
史密斯夫人:我呀,才不在乎呢!你要是讲这些来叫我讨厌,那……你知道我不喜欢这种玩笑!
[史密斯夫人把袜子扔得老远,生气了,站起来。
史密斯先生:(也站起来,向妻子走去,温情地)啊,我的烤小鸡,干吗发火呢?你明知道我是开玩笑的呀!(搂住她的腰,吻她)我们扮演了一对多么可笑的老情人呀!来,我们关灯睡觉去!
——————————
译注
①“英国的沉默良久”和下文的“英国的十七点钟”,都属于文字游戏,剧中大量采用这类词句的反常搭配,以显示作者对常轨的讽刺。
② 培吉原文用的英文,剧中不时用几个英文的词,以便造成奇特的效果。
③勃艮第,法国地名,当地以产葡萄著称。剧中人说成是澳大利亚的地方,正如下文把土耳其的城市君士坦丁堡说成是罗马尼亚的地名一样,为的是引人发笑。
④ 台词中往往故意塞进些不伦不类的词语,如下文的“偶像崇拜症”,以便挖苦剧中人不学无术又好卖弄聪明。
⑤ 以下一些不合逻辑的语句,都讽刺了思维逻辑。
第二场
[前场人物,加上玛丽。
玛丽:(边说边上场)我是女佣人。我下午过得特快活。我跟个男人上电影院,看的是有女人的电影,打电影院出来,我们去喝酒,喝牛奶,随后又读报来着。
史密斯夫人:但愿你过了个快快活活的下午,同个男人上了电影院,还又喝了酒,又喝了牛奶。
史密斯先生:还读了报!
玛丽:你们的客人马丁夫妇在门外。他们早就来了,一直等我,不敢自个儿进来。他们今晚上要和你们一起吃晚饭?
史密斯夫人:啊,对了,我们是等他们来着。后来都饿了,老不见他们来,不等他们就准备吃啦。这一整天我们可什么也没吃呀,你不该出去的!
玛丽:是您准许的呀。
史密斯先生:可不是故意把你支开的啊!
玛丽:(一阵大笑,跟着就哭,转而又笑眯眯地)我替自己买了个尿盆。
史密斯夫人:亲爱的玛丽,请把门打开,让马丁夫妇进来。我们就去换身衣服。
[史密斯夫妇从右边下。玛丽开左边的房门,马丁夫妇上。
第三场
[玛丽和马丁夫妇。
玛丽: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太不礼貌了,应该准时嘛,懂不懂?现在就坐那里,等着吧。(下)
第四场
[前场人物,除去玛丽。
[马丁夫妇面对面坐下,不说话,相互腼腆地微笑。
马丁先生:(下面这段对话要用一种拖长、平淡的声音说,声调有些像唱歌,但不要有任何起伏①)请原谅,夫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
马丁夫人:我也是,先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
马丁先生:夫人,我会不会在曼彻斯特碰巧见到过您?
马丁夫人:这很可能。我就是曼彻斯特人!可我记不很清楚,先生,我不敢说是不是在那里见到您的。
马丁先生:我的天!这太奇怪了!我也是曼彻斯特人,夫人!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
马丁先生:这太奇怪了!不过,我,夫人,我离开曼彻斯特差不多有五个星期了。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多巧啊!我也是,先生,我离开曼彻斯特差不多也五个星期了。
马丁先生:夫人,我乘早上八点半的火车,五点差一刻到伦敦的。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真巧!我乘的也是这趟车!先生!
马丁先生:我的天,这太奇怪了!说不定,夫人,我是在火车上见到您的?
马丁夫人:这很可能,真没准儿,非常可能,总而言之,没法说不!……可是,先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
马丁先生:我坐的是二等车,夫人。英国没二等车,可我还是坐的二等车。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真巧!先生,我坐的也是二等车。
马丁先生:这太奇怪了!我们说不定就是在二等车厢里碰上的,亲爱的夫人!
马丁夫人:这很可能,真没准儿。可我记不太清楚了,亲爱的先生!
马丁先生:我的座位是在八号车厢,六号房间,夫人!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亲爱的先生,我的座位也是在八号车厢六号房间呀!
马丁先生:这太奇怪了,多巧啊!亲爱的夫人,说不定我们就是在六号房间碰见的?
马丁夫人:这很可能,不管怎么说!可我记不起来了,亲爱的先生!
马丁先生:说实在的,夫人,我也记不起来了,可说不定我们就是在那里见到的。如果我记得起来的话,看来这是非常可能的。
马丁夫人:噢!真的,肯定,真的,先生!
马丁先生:这太奇怪了!……就是三号座位,靠窗口,亲爱的夫人。
马丁夫人:噢,我的天,这太奇怪了,这太怪了,我是六号座位,靠窗口,在您对面,亲爱的先生。
马丁先生:噢,我的天,这太奇怪了,多巧啊!亲爱的夫人,我们原来面对面!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这有可能,先生,可我记不起来!
马丁先生:说真的,亲爱的夫人,我也记不起来了。不过,我们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场合见到的。
马丁夫人:真的,可我一丁点也不能肯定,先生。
马丁先生:亲爱的夫人,那位请我替她把行李放到架子上,然后向我道谢,又允许我抽烟太太,难道不是您?
马丁夫人:是,先生,那该是我呀!这太奇怪了,多巧啊!
马丁先生:这太奇怪了,这太怪了,多巧啊!嗯,哦,哦,夫人,我们或许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吧?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真巧!亲爱的先生,这很可能!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记不起来了。
马丁先生:夫人,我也记不起来了。
[静场片刻。钟敲二点又敲一点。
马丁先生:亲爱的夫人,我来伦敦一直住在布隆菲尔特街。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这太怪了!先生,我来伦敦也一直住在布隆菲尔特街。
马丁先生:这太奇怪了,嗯,哦,哦,亲爱的夫人,我们也许就是在布隆菲尔特街遇见的。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这太怪了!无论如何,这很可能!亲爱的先生,可我记不起来了。
马丁先生:亲爱的夫人,我住在十九号。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亲爱的先生,我也是住在十九号。
马丁先生:嗯,哦,哦,哦,哦,哦,亲爱的夫人,我们也许就是在这幢房子里见面的吧?
马丁夫人:这很可能,亲爱的先生,可我记不起来了。
马丁先生:亲爱的夫人,我的套间在六层楼,八号。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我的天,这太怪了!真巧,亲爱的先生,我也住在六层楼,八号房间。
马丁先生:(若有所思)这太奇怪了,这太奇怪了,这太奇怪了。多巧啊!您知道,我卧室里有张床。床上盖着一条绿色的鸭绒被。亲爱的夫人,我这房间,这床呀,绿色的鸭绒被呀,在走廊尽里头,在卫生间和书房中间!
马丁夫人:太巧了,啊,我的天哪!巧极了!我的卧室也有张床,也是盖的一条绿色鸭绒被,也在走廊尽里头,亲爱的先生,也在卫生间和书房中间呀!
马丁先生:这太古怪,太奇怪,太妙了!哦,夫人,我们住在同一间房里,睡在同一张床上,亲爱的夫人。也许就是在那儿我们遇上了?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真巧!很可能我们是在那儿遇上的,说不定就在昨天夜里。亲爱的先生,可我记不起来了。
马丁先生:我有个小女儿,亲爱的夫人,我那小女儿同我住在一起。她两岁,金黄头发。她一只白眼珠,一只红眼珠,她很漂亮,亲爱的夫人,她叫爱丽丝。
马丁夫人:多希奇的巧合啊!我也有个小女儿,两岁,一只白眼珠,一只红眼珠,她很漂亮,也叫爱丽丝。亲爱的先生!
马丁先生:(依然拖腔拖调地、平淡地)这太奇怪了,太巧了,真怪!亲爱的夫人,说不定我们讲的就是同一个女孩啊!
马丁夫人:这太奇怪了,亲爱的先生,这很可能。
[较长时间的静场……钟敲二十九下。
[马丁先生思考多时,缓缓站起,不慌不忙地向马丁夫人走去。马丁先生庄严的神态使她大为吃惊,她也缓缓站了起来。
马丁先生:(还是用那种少有的、平淡、近似唱歌的腔调)我,亲爱的夫人,我看我们肯定已经见过面了,您就是我妻子……伊丽莎白,我又找到您了!
[马丁夫人不急不忙地向马丁先生走去。他们拥抱,毫无表情。钟很响地敲了一下。响得叫观众吓一跳。
[马丁夫妇俩却没有听见。
马丁夫人:道纳尔,是你呀,宝贝儿②!
[他们在同一张安乐椅上坐下,紧紧地抱在一起,睡着了。
[钟又敲了好几下。玛丽踮着脚尖,一只手指贴在嘴唇上,悄悄地上场,转向观众。
——————
译注
① 尼哥拉·巴达依导演这出戏的时候,用一种真诚的悲剧语调和风格来处理这一段对话。——原注。
② 原文这个词用的是英文,下同。
第五场
[前场人物和玛丽。
玛丽:伊丽莎白和道纳尔这会儿美滋滋的那个劲,顾不上听我说话。我可以给你们透个风,伊丽莎白才不是伊丽莎白呢,道纳尔也不是道纳尔。证据就是道纳尔讲的那个孩子不是伊丽莎白的闺女,不是同一个人。不错,道纳尔的那小丫头同伊丽莎白的那小妞儿一样,都是一只白眼珠,一只红眼珠。可道纳尔的孩子白眼珠在右边,红眼珠在左边;伊丽莎白的孩子红眼珠在右边,白眼珠在左边!这一来,道纳尔的那一套论证体系碰到这最后一关就垮掉了,他那一整套理论也就完蛋了。这些希奇古怪的巧合看上去像是证据确凿。其实,道纳尔和伊丽莎白并不是同一个孩子的爹妈,所以,道纳尔也不是道纳尔,伊丽莎白也不是伊丽莎白。男的以为自己是道纳尔,女的以为自己是伊丽莎白,满不是这么回事。男方把女方当作伊丽莎白,女方把男方当作道纳尔,两人自己骗自己,空欢喜一场。究竟谁是真的道纳尔,谁又是真的伊丽莎白?这一错再错,谁捞到好处?我可不知道,也不去刨根问底,由它去好了。(朝门口走了几步,又转身回来,面向观众)我的真名叫福尔摩斯。(下)
第六场
[前场人物,除去玛丽。
[钟随意乱敲。隔了好久,马丁夫妇方始分开,原位坐下。
马丁先生:宝贝儿,忘掉我们之间的往事吧。我们现在既然重逢,千万别再失散了,还是象从前一样生活吧。
马丁夫人:好的,宝贝儿。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