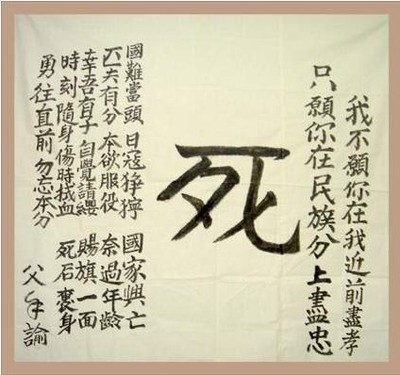葛炎刘琼
杨丽坤包斯尔
《阿诗玛》是上海电影制片厂1964年根据同名民间长诗改编、著名导演刘琼执导、杨丽坤、包斯尔、韩非、崔超明等主演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舞蹈片。
阿诗玛是我国云南撒尼族的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
云南地方有一个撒尼族姑娘名叫阿诗玛,她聪明美丽,与青年阿黑相爱。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支,贪婪阿诗玛的姿色,心存歹念。在传统节日集会中的摔跤场上,阿支不可一世,当他刚摔倒一个小伙子,便要扯下获胜的彩绸。阿支正要解绳,阿黑从远处射来一箭钉住了旗杆上的绳索,阿支吓得缩了回去。接着阿黑跑过来,与阿支展开激烈的较量,最后将阿支摔倒。阿黑获胜赢得全场的喝彩,阿诗玛也亲热地跑过来为他祝贺,阿支见此十分生气。
在一天的晚上,阿支学着阿黑的样子,在阿诗玛家附近吹起了笛子。阿诗玛听到笛声,误以为是阿黑,顺着笛声飞奔出去。当阿诗玛在竹丛中见到阿支,怒气冲冲地转身便走,阿支急忙去拉她,阿诗玛用力将阿支甩开,险些将阿支摔倒。当阿支站稳以后阿诗玛已不见踪影。阿支贼心不死,央求媒人海热带着厚礼,到阿诗玛的家中,求阿诗玛的母亲将女儿嫁给他。海热见笑脸相求不行,便恶狠狠地威胁她母亲。这时,阿诗玛从外边闯了进来,将海热的酒杯打翻在地,并将他轰出门。
于是,阿支趁阿黑去远方牧羊之机,派人将阿诗玛劫走,阿诗玛趁阿支不备,将与阿黑定情的山茶花掷入溪中,溪水立即倒流。阿黑获讯赶回救援。途中被大山所阻,他用神箭射穿大山,开出通道,纵马驰骋,快速前进。阿支用尽种种威胁和利诱手段,都不能使阿诗玛屈服。阿支恼羞成怒,正要举鞭毒打阿诗玛,阿黑及时赶到。阿支提出要和阿黑赛歌,一决胜负。
阿黑与阿支赛歌赛了整三天,阿黑越唱越精神,阿支越唱越没劲。最后,阿黑唱道:“问你谁来造彩云,问你谁来造太阳,谁来造星星,谁来造月亮,高山大海谁来造,快回答!” 阿支听到阿黑所问,瞠目不知所答。
阿支赛输了,但仍不甘心,又企图用暗箭杀害阿黑。阿黑愤怒地用神箭射穿大门和大厅的柱子,箭射在神主牌位上,阿支命众家丁用力拔箭,箭却纹丝不动。阿支被慑服,只得将阿诗玛释放。
阿诗玛和阿黑喜悦地同乘一骑回家。他俩来到溪边,下马小憩。阿支带人偷走阿黑的神箭,放洪水将阿诗玛淹死。
阿黑悲愤地呼唤着她的名字,但阿诗玛已化为一座巍峨的石像,千年万载,长留人间。
1956年,作家公刘长诗《阿诗玛》问世,电影《阿诗玛》就是根据公刘的长诗改编的。
《阿诗玛》比较彻底的摆脱了“讲故事”的传统模式,采用了无场次-板块式结构,以黑、绿、红、灰、金、兰、白等不同色彩的舞段,围绕着阿诗玛、阿黑、阿支的爱情矛盾,着力揭示不同的人物性格。以细腻的笔触,精心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阿诗玛、阿黑、阿支组成了很精彩的双人、三人舞段。同时在不同色彩的板块式舞段中,从容、酣畅地展现着绚丽多彩的彝族各支系的民间舞。
这部舞剧大胆地运用了交响编舞法和某些意识流手段,由于编导有深厚的生活与艺术积累,借鉴中较少斧凿之痕,保持了鲜明的民族性。
《阿诗玛》于1982年获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1994年获文华大奖,并被确认为“20世纪经典”。7
美丽的云南石林,诞生了美丽的传说“阿诗玛”;美丽的阿诗玛也使美丽的石林更加神奇迷人,世世代代吸引着海内外千千万万崇尚正义和善良、追求和谐和美好的男女老少。
电影的主要演员杨丽坤,称为美丽的化身,1942年出生在茶乡普洱县磨黑镇。她的父亲和哥姐都爱好音乐,能弹会唱,从小培养了她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加上有一位叫段师傅的邻居经常教她唱歌跳舞,艺术的甘泉浸透了她童年的心灵。1950年,未满8岁的杨丽坤被大姐带到昆明,送进新村小学读书。1954年,云南省歌舞团看中了她朴实美丽的身姿和对艺术的灵性,选拔入团,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1959年4月1日,《五朵金花》的导演王稼乙到省歌舞团挑演员,一眼就看中了杨丽坤。杨丽坤第一次主演《五朵金花》,便迷倒了亿万观众。《五朵金花》上映当年,先后在46个国家争相放映,受到观众的高度赞誉。她主演的第二部影片《阿诗玛》再次成功地塑造了云南又一个美丽的天使形象。1960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亚非电影节”上,杨丽坤获得了“最佳女演员银鹰奖”,成为世界电影界一个光彩夺目的明星。
“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杨丽坤一夜之间被打成了“黑五类”,身心受尽摧残,夺去了她短暂而又璀璨的艺术生命,后来一直病魔缠身,1974年结婚,于2000年7月21日在上海家中平静病逝,从此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虽然杨丽坤一生只演过《阿诗玛》和《五朵金花》两部电影,却在中国亿万观众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两部电影获奖无数,给她带来莫大的荣誉,但也因为这两部电影,“文革”中杨丽坤被迫害致精神错乱,住进了云南省长坡医院,这一年她28岁。此时的杨丽坤已经拥有巨大的声誉,但是,在以后的三十年,她没能走出那个噩梦,也没能再演电影。
2000年7月21日18时30分杨丽坤去世,她的墓碑,上海一座、昆明一座。她的骨灰,上海一半,昆明一半。
电影《阿诗玛》诞生记
袁成亮
“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每当提起《阿诗玛》,人们耳边便会响起电影《阿诗玛》中那一段段脍炙人口的唱段,想起彝族青年男女阿黑和阿诗玛爱情的不幸和悲惨的命运。作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阿诗玛是如何被搬上银幕的呢?它的背后又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呢?
一
《阿诗玛》是流传于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一部口头传说,它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美丽、坚强、勇敢的青年男女阿黑和阿诗玛爱情的不幸和悲惨的命运。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在撒尼族的传统节日里,阿黑在射箭和摔跤比赛中赢了富家子弟阿支,夺得了彩绸与阿诗玛互订终身。阿支早就看中阿诗玛,趁阿黑不在把她抢走。可是,阿支和哥哥比武都敌不过阿黑,只好将阿诗玛放走。就在阿黑一行高兴而归时,阿支引进的汹涌洪水淹没了他们。待阿黑挣扎起来后,阿诗玛已化为一座山石。
1956年,作家公刘长诗《阿诗玛》改编成电影剧本,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很快决定将其搬上银幕。正当海燕电影制片厂着手投拍事宜时,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原先参与整理长诗《阿诗玛》的黄铁、杨智勇、刘绮、公刘等被打成右派,由公刘改编的电影剧本也遭到被封之命运。尽管如此,海燕电影制片厂却一直对《阿诗玛》情有独钟。1960年该厂又请出老诗人,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李广田来重新对阿诗玛进行修订。准备再次上马,但不久李广田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阿诗玛》的拍摄又一次搁浅。
俗话说好事多磨。几经波折之后,196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终于在《阿诗玛》拍摄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并很快组成了拍摄班子。刘琼出任导演,葛炎、刘琼负责改编剧本,罗宗贤、葛炎负责音乐创作,李广田任文学顾问。杨丽坤由于在《五朵金花》中的出色表演而出演“阿诗玛”。
作为影片的主演,由于此前杨丽坤参加过五朵金花的拍摄,此次在影片中饰演阿诗玛显得很是得心应手。她抓住阿诗玛美丽、善良的本质作为角色创作的“内核”,并发挥了自己善舞的特长,在表演中增加了许多别具特色的舞蹈,并由此形成了清新、质朴的表演风格,将纯情、秀丽、善良、甜美的阿诗玛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受到了剧组的一致好评。
与《五朵金花》一样,杨丽坤主演的阿诗玛声音都是配音师后来配上去的。但是细心的人还是发现了电影《阿诗玛》中有两处阿诗玛的独白与影片中其它独白有些不一样。其中有一处是阿黑临别阿诗玛时投下那朵山茶花在急流中飘动时,随着背景音乐中一句韵白:“水呀!你为什么不往高处流呀!”,那朵山茶花竟然顺流而上。这句独白实际上是阿诗玛念的。说来这还与周总理的嘱托分不开的。那还是1961年,杨丽坤和歌舞团同志一道跟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和演出。在繁忙的访问期间,周总理多次与杨丽坤交谈。当他了解到杨丽坤饰演的金花是由别人配音时,非常亲切又严厉地与杨丽坤讲,当一名演员不仅要善于表演,也要学好普通话。杨丽坤听了,从此下决心学好普通话。经过刻苦努力,她的普通话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距离拍电影要求还相差很大。但能在电影中念一两句台词,她心里也算是对周总理关心有一个交待了。
经过全剧组的共同努力,1963年11月,影片《阿诗玛》完成了四本样片的的制作。刘琼等人立即将样片送到文化部审查。时任文化部部长、主管电影工作的陈荒煤看了样片后很是赞赏,当即表示:“《阿诗玛》质量相当高,杨丽坤形象与表演都很好,色彩和摄影也很不错,音乐曲调基本上是民族的。”陈荒煤有此表态,刘琼等人心里别说有多高兴了,全剧组也都欢欣鼓舞。北京回来之后,大家又加班加点,加紧拍摄,到同年5月整部影片的制作便宣告完成。由于有前次审查作底子,大家对文化部的终审也充满了希望。
1964年6月初,刘琼等人带着已完成的《阿诗玛》再度来京送审,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次陈荒煤却没有了上次看片的那种兴奋。当时正值文革前“阶级斗争”暗流涌动之时,对于这部以爱情为题材的片子是否能够上映,陈荒煤心里很是没底。他看了影片后,心思重重地对刘琼等人说:“还不错。可是你们要注意啊,现在提出了群众路线问题,风声很紧啊!先请夏公看看再说吧!”刘琼听了,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影片随即被送到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那里,夏衍看了对这部影片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囿于当时形势,他认为目前在国内还不宜放映,可先拿到香港“第二地带”放一放,国内稍等一下再说。
然而,事情的发展连身居要职的夏衍和陈荒煤也没有能够把握住。就在电影《阿诗玛》送审不到一个月,7月2日文化部整风开始了。主持电影工作的夏衍和陈荒煤被认为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判。江青在调看了包括《阿诗玛》在内一大批影片后公开宣称:“这些影片的本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把它们放在仓库里,应该拿出来公开批判。摄制一部影片要花几十万元,批判了,可以思想经济双丰收”。康生也斥责《阿诗玛》是“恋爱至上的大毒草”。同年12月,江青又到中宣部召开会议,点名批判了《阿诗玛》等一批影片,气势汹汹地说:“《阿诗玛》无法修改,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影片,不要再浪费人力、物力,原样上映批判。”1965年4月11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些坏影片的通知》,被列入坏影片的共有7部,《阿诗玛》为其中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电影《阿诗玛》被视为“宣传恋爱至上”的“修正主义大毒草”而遭到了批判。疑聚了一批文艺工作者心血的电影《阿诗玛》未及上映便遭禁锢,令许多关爱它的人痛心不已。参与《阿诗玛》的长诗、京剧、舞剧及电影创作的众多文学艺术工作者也遭到牵连。李广田被迫自杀。扮演阿诗玛的杨丽坤也被视为“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美女”而遭到非人的摧残,并因此患上了心因性精神忧郁症,在那非人的年代里,不堪折磨疯掉了!
《阿诗玛》被禁映后,在云南,杨丽坤被当作“黑苗子”遭到批斗。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的杨丽坤经受不住这个打击,造成精神失常。杨丽坤一个人终日在昆明街上流浪,别人给她两块钱就给人家唱一段《阿诗玛》。
杨丽坤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乱走,曾经离开昆明。后来别人终于发现她失踪了,开始大规模地寻找,结果竟在边疆小城———镇沅找到了她。经过治疗,杨丽坤身体慢慢地复原了。
1970年,杨丽坤被作为黑线人物再次被关入地下室牢房,经常挨批斗。她的病又犯了,病情一天天加重。而“群专队”落井下石,抓住病人的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又给她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日夜不停地审讯。更有甚者,一群人经常恶作剧,把她从这头轰打到那头,又从那头推打到这头。
由于杨丽坤总是不停地在申辩,地下室牢房的人觉得她太吵。“群专队”竟在云南省歌舞团舞台下搭了一间小黑屋子,把杨丽坤关了进去。里面没有床,只有两把凳子。每当夜深人静,人们经常听到杨丽坤那凄厉的呼叫声。直到后来确认杨丽坤精神再次失常了,才把她放了出来。
所幸的是,杨丽坤后来遇到了伴她一生的知心爱人唐风楼。晚年的杨丽坤在老伴的照顾下,才得以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杨丽坤夫妇生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晚年生活在幸福之中。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去世。
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随着文艺界“百花争呜、百花齐放”双百方针的恢复,我国的影视事业也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二个春天。文化部及各电影制片厂也着手对一大批在文革中遭禁的影片进行重新审查。上海电影制片厂复审小组对《阿诗玛》也进行了复审。由于长期受到文革的影响,当时参加复审的某些小组成员,听说戏里有神话和恋爱故事,情绪就紧张起来。为了谨慎起见,对《阿诗玛》的审查是在夜间进行的,当时为了防止有人进来,还将外面大门上了锁。但此次审片并没有能挽救《阿诗玛》被禁的命运。电影厂的一位领导甚至放言:“再百花齐放,谈情说爱就是不能放。”由于“左”倾思想的束缚,在文革结束后两年,《阿诗玛》依然锁在深宫无人知。
《阿诗玛》遭禁事件也时时牵动着陈荒煤的心,眼见许多被禁铟的影片一一重见天日,他终于坐不住了。1978年7月,陈荒煤趁到昆明参加“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和外国文学教材协作会议”之时,在与当地的教育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特别提到了电影《阿诗玛》,并希望能看看影片,他的倡议得到与会者的赞同。经当地政府安排,被封存长达14年的电影《阿诗玛》终于在小范围内与学者们见面了。大家看完后对这部影片给予了高度评价。但陈荒煤心里并没有因此而显得轻松,为了使《阿诗玛》重见天日,同时也是为了解救遭到迫害的杨丽坤,陈荒煤写了一篇《阿诗玛,你在哪里?》的长文寄给《人民日报》。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公开为电影《阿诗玛》平反的第一篇文章。实际上陈荒煤的文章虽是讲《阿诗玛》的问题,但它深层的意义还在于怎样对待一批影片和电影工作者的问题,可以说是他为一些被封禁的影片所发出的“解禁”信号。《人民日报》领导收到陈荒煤的信后很是重视,将他的文章作为1978年9月3日头条发表,而且题目还用了陈荒煤的手写体。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荒煤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很多来信,对陈荒煤的文章表示赞赏,还有许多人询问阿诗玛扮演者杨丽坤的下落。为了回应读者们对杨丽坤的关心,上海的《解放日报》特地登载了张曙、汪习麟的文章《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远在上海的杨丽坤夫妇读到陈荒煤的文章后也非常感动,特别通过《人民日报》给陈荒煤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长信。陈荒煤的文章为《阿诗玛》的复出打开了通道。时至1978年10月,人们的思想也开始从“左”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上海电影界有关人士专门组织了一场由杨丽坤参加的《阿诗玛》看片会,在看片会上,看到十多年前由自已主演的影片,想到《阿诗玛》给自已和许多相关的人带来的种种不幸,杨丽坤禁不住泪流满面。这次看片,大家一致给影片下了这样的评语:电影《阿诗玛》描写了健康的爱情,用神话形式反映人民抗暴的思想,在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看片会上,上海方面专门将为《阿诗玛》平反材料呈报文化部。文化部接到材料后,虽然对《阿诗玛》平反一事进行了多次研究,但却迟迟作不了结论。此时,爱情题材虽然已不再是影视文学创作的禁区了,但有人仍担心《阿诗玛》会给青年人带来副作用,如影片中表现男主人公阿黑和阿诗玛相爱时有“一天找你九十九遍”这样的歌词。有人还担心影片将民间传说中阿黑和阿诗玛的兄妹关系改成爱情关系,是否有损于撒尼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否有碍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同志为此专程到阿诗玛的故乡-——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奎山地区,请最有权威的评定者撒尼人鉴定。
就在文化部对影片《阿诗玛》因内部纷争迟迟作不了结论时,1978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举行的电影酒会上,电影《阿诗玛》却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在银幕上,并获得了观众的热烈好评。随后,新华社发布一条激动人心的重要消息:《阿诗玛》等一些影片将在元旦恢复上映。1979年元旦,《阿诗玛》在全国上映,历经坎坷的《阿诗玛》终于回到了观众中间。
1982年,该片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桑坦德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节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
电影《阿诗玛》的解禁风波
忧伤的《阿诗玛》
1978年9月3日,陈荒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公开为电影《阿诗玛》平反的第一篇文章。
杨丽坤,这个出生在云南思茅磨黑的彝家女,曾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没有谁能像她那样,只演过两部电影,却在中国亿万观众的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她的辉煌被永远地定格在电影《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上。
《阿诗玛》是流传于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一部口头传说,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美丽、坚强、勇敢的青年男女阿黑和阿诗玛爱情的不幸和悲惨的命运。1956年,公刘根据这一长诗改编成电影剧本,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投拍,但是1957年“反右”风暴骤起,《阿诗玛》的四个整理者,有三个(黄铁、杨智勇、公刘)被打成了右派。海燕电影制片厂不愿放弃这一优秀的题材,1960年请出了老诗人、当时的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来重新“修订”。可是,不久李广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影片的拍摄再次搁浅。
196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继续拍摄。由葛炎、刘琼联合改编;音乐部分,由罗宗贤、葛炎一起创作,导演即由剧本作者之一的刘琼担任,李广田任文学顾问。杨丽坤由于在《五朵金花》中的不凡演技,被选中扮演“阿诗玛”。
但是,伴随着影片的开拍,厄运也开始了。“当时'两个批示’发出,康生枪毙了一批影片,文化部正在进行整风。”其后,《阿诗玛》的创作人员,也如政治狂风中的浮萍,一个个“夭折”;直至“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犯下了“迫害杨丽坤、李广田的罪行”。他们的悲惨遭遇,也如同忧伤的阿诗玛的命运一样,令人不忍回首。
1963年11月,《阿诗玛》摄制组将拍摄完成的四本样片送审时,陈荒煤正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11月11日,陈荒煤观看了样片后明确表态:“《阿诗玛》出四本,质量相当高,杨丽坤形象与表演均好,色彩和摄影均好,音乐曲调基本上是民族的。”他对张瑞芳说:“《阿诗玛》拍得好,百花奖我投一票!”有了陈荒煤的表态,上海电影制片厂快马加鞭,在1964年6月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制作,送到文化部审查。
此时,对于这部以爱情为题材的影片,是否能够上映,陈荒煤又颇踌躇了。6月8日,他看了影片后,心思重重地说:“还不错。可是你们要注意啊,现在提出了群众路线问题,风声很紧啊!先请夏公看看!”夏衍看了《阿诗玛》后也予以肯定。不过,囿于当时的形势,他认为目前在国内还不宜放映,提议先可拿到香港“第二地带”去,国内稍等一下再说。
7月2日,文化部开始整风。主持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首当其冲,被认为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而遭到批判。江青在调看了一大批影片之后,公开宣称:“这些影片的本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把它们放在仓库里,应该拿出来公开批判。摄制一部影片要花几十万元,批判了,可以思想经济双丰收。”这其中就包括《阿诗玛》。康生也起而呼应,斥责《阿诗玛》是“恋爱至上的大毒草”。这年12月,江青又到中宣部召开会议,点名批判了《阿诗玛》等一批影片,气势汹汹地说:“《阿诗玛》无法修改,是一部典型的资产阶级影片,不要再浪费人力、物力,原样上映批判。”1965年4月11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些坏影片的通知》,共列7部,《阿诗玛》为其中之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电影《阿诗玛》成为“大毒草”,并迅速波及参与了《阿诗玛》的长诗、京剧、舞剧的众多文学艺术工作者。李广田被迫自杀。他的众多“罪状”中就有参与了“宣传恋爱至上”的“修正主义大毒草”《阿诗玛》的修订和担任影片的文学顾问。杨丽坤的罪名更加严重,什么“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美女”等等,一起扣在她身上。这位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的优秀演员遭到了非人的摧残。虽然历经“文革”磨难,她活了下来,但这位才华出众的优秀演员的艺术生命被扼杀了。
陈荒煤的文章
粉碎“四人帮”后,一大批被打入冷宫的影片陆续与观众见面。但是,杨丽坤主演的《阿诗玛》却迟迟没有得到上映的消息。当人们重新观看了她主演的《五朵金花》后,自然想到了《阿诗玛》。关心电影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探问:杨丽坤在哪里?《阿诗玛》何时能放映?
陈荒煤也在关注着《阿诗玛》,关注着杨丽坤。
1978年7月,陈荒煤到昆明参加“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和外国文学教材协作会议”。他在应邀与当地的教育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提到了电影《阿诗玛》,并希望能看看影片。他的倡议得到很多人的赞同。经当地政府安排,与会者才得以观看那部还没有公开放映就被封存长达14年之久的影片。
其后,当地政府邀请与会代表游石林,并参加撒尼人的火把节。陈荒煤看到了耸立于石林中酷似阿诗玛的石像,并与那位万年来一直在等待着阿黑哥归来的“阿诗玛”合影。当人们按照民间传说,对着形似阿诗玛的石头大声叫着:“阿诗玛,阿诗玛!”并且听着那从山谷间传回来的声音时,这位老作家感伤地哭了。尤其是当他了解到杨丽坤被“四人帮”迫害的情况时,心情更不能平静。
在这个辗转难眠之夜,想来陈荒煤想到的不仅是应该为《阿诗玛》的解禁呼吁,为杨丽坤重现银幕而呐喊,更想到了一大批尚在冷宫中的影片和那些依然背负着各种罪名的电影工作者。带着这种激愤哀伤的心绪,回到北京后,他写出了他复出后的第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
文中陈荒煤特别提到杨丽坤在“文革”时的悲惨遭遇:“她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苗子’,终于神经失常。”
当然,陈荒煤文章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失误,这就是他在后来给周扬的信中所说的,他不记得他曾经两次看过这部影片,因而文中说自己是在昆明第一次看到的。这本是个记忆上的小问题,后来却因此招致了责难。
陈荒煤的一声呼唤,唤起了人们对杨丽坤、对《阿诗玛》的关切之情。很多读者为杨丽坤的不幸而激愤,为至今没有解禁《阿诗玛》感到不解。
陈荒煤的呼唤发出后,新闻界也有了强烈的回应。上海的《解放日报》登载了张曙、汪习麟的文章《阿诗玛就在我们身边》。平反杨丽坤的冤案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年10月,文化部部长黄镇作出了给杨丽坤平反落实有关政策的批示。
1979年春天,陈荒煤借在上海参加当代文学研讨会的机会,看望了因病魔折磨而与以前判若两人的杨丽坤。陪同他到杨家的刘士杰回忆说:
荒煤见到杨丽坤,竟许久没有说话,直到杨丽坤又叫了一声“老局长”,他才梦醒似地回到了现实。他望着杨丽坤,眼里充满着怜爱、同情。我想象着他内心一定燃烧着仇恨的怒火:万恶的“四人帮”把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演员摧残成什么样子!……从杨丽坤家出来,荒煤默默地走着,长久没有说话,脸上现出惆怅、若有所失的表情。他是不是又听见“阿诗玛,你在哪里?”的呼唤声?为什么明明找到了,又好像失去了?
此后,失去了艺术生命的杨丽坤定居上海,在亲人、丈夫和上海人民的关心下养病、生活,直到2000年8月去世。
给《人民日报》的信
陈荒煤的呼唤,虽然促使杨丽坤的冤案获得平反,但电影《阿诗玛》的解禁,还要费一番周折。
到1978年10月,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阴影依然存在,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摆脱极左路线的束缚,处在被党史学家所描述的“两年徘徊时期”。文坛回春的气象,也因为这种“徘徊”不时被“倒春寒”所侵袭。当时主持文化部工作的个别领导,无论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历史潮流,认识不那么深刻,步子迈得不大,滞后于群众的要求。陈荒煤写作、袁鹰主持发表《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其意义正是希望文化部重视群众的呼声。但是,文化部的个别领导却没有把这篇文章看成是对自己工作的推动,反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上提出指责。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副院长周扬是支持陈荒煤的。胡乔木在与陈荒煤的谈话中说,他读了《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后,曾与文化部的一位领导谈及,说《阿诗玛》应该放映。可是,这位领导对乔木的意见不表态,却说当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对这部影片也有意见,是康生(那时,康生的反动政治面目还未被揭露)提出要批判的。谈话中,这位领导对陈荒煤的文章也表示了不满,说陈荒煤在文章中说他第一次在云南才看到此片,不确;在“文革”以前他就两次看过这部影片———言外之意是,当年封存这部影片,你陈荒煤也是有责任的。这位领导人还希望乔木转告荒煤,让他写个信给文化部,事情就过去了。
这位领导说到的周恩来和陈毅对影片的态度,关于陈毅对这部片子的看法,因没有查到材料,无法考证,但是,说周恩来对这部片子不满,则有材料可以证明,是不对的。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杨丽坤的成长。她主演的《五朵金花》,周恩来就很赞赏,杨丽坤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两次随周总理出国访问。在一次出国途中,周恩来知道《五朵金花》是别人配的音,就勉励她严格要求自己,学好普通话。《阿诗玛》开拍后,周恩来又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杨丽坤的普通话是否讲好了。显然,周恩来对《阿诗玛》所打的电话,当然不是对这部影片的否定,而是对杨丽坤提出的严格要求。
与胡乔木谈话后,陈荒煤开始认为,文化部并未正式向他提出意见,而自己也的确没有什么好检讨的———难道十年后不记得自己看过这部影片也需要检讨?他认为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后来,陈荒煤考虑再三,从照顾团结和尊重胡乔木意见的愿望出发,给社科院党组写了一个情况汇报,委托社科院党组转交文化部。周扬认为陈荒煤的做法是对的,予以支持。
但是,从当时陈荒煤给周扬的一封信来看,文化部对陈荒煤的情况汇报是不满意的,并进而提出要陈“写封信给《人民日报》”进行更正。陈荒煤无奈,“为了照顾关系,尊重党组意见”,只好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并将此信转给周扬审阅。
陈荒煤对这种指责是不满的,他甚至涌起了为此事给“邓(小平)副主席写个信”的想法。他也曾愤愤不平地对周扬说,对电影工作不再发言了,并将原定于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而写总结建国以来电影文学创作的文章的计划取消,还从中国电影出版社取回自己将要出版的《电影论文集》一书。周扬则肯定他的文章没有错误,即使是有些记忆不准确,也不是什么大错,要他冷静一些。
文化部看到陈荒煤草拟的给《人民日报》的信后,倒没有考虑令自己“被动”的问题,反而同意这封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7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以《关于<阿诗玛>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了陈荒煤的这封信。信中陈荒煤说:“在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承文化部电影局同志查告,我对影片拍成后的一些主要经过说得不对”,“我在文中说该片制成时我已离开电影界,今年在昆明才第一次看到”,“确实是我不应有的疏忽”。
这封信发表后,由《阿诗玛,你在哪里?》一文所引起的小小波澜,也归于平息。不过,《阿诗玛》这部影片依然没有被解禁。
《阿诗玛》回来了
在给周扬的信中,陈荒煤说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根本不能提到'广大群众’希望看到影片”的要求,以免造成给文化部“施加压力”的印象,但是,正如陈荒煤在信中所说的,却“不能不让读者要求放映这部影片”。但是,文化部却迟迟不动。文化部迟迟不动的症结在何处?大约可以从粉碎“四人帮”在电影界流行的一个真实的笑话找到根据。这个真实的笑话说:某单位放映外国影片,演到中途,银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大黑影,原来是放映员的手掌。大伙正纳闷,扩音器响了:“注意,领导有话,这里要挡一挡。”半分钟后,黑影消失,刚才被遮挡的是几个男女主角谈情的镜头。在那个年月,视表现爱情题材的电影为禁区,虽然不是很普遍,但确不乏一些人持这样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复审小组曾审阅过《阿诗玛》。当时,参加复审的某些小组成员,听说戏里有神话和恋爱故事,情绪就紧张起来,因而出现了这样的现今无法理解的滑稽场面:审看《阿诗玛》是在夜间。大门上锁,闲人莫入。说也怪,久不闻哥呀妹的唱词,乍听觉得不大入耳。电影厂的一个领导说:“再百花齐放,谈情说爱就是不能放。”
到了1978年的10月,人们的思想开始从禁锢中挣脱出来。上海电影界有关人士陪同杨丽坤再看《阿诗玛》时,看法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给《阿诗玛》的评语是:影片描写了健康的爱情,用神话形式反映人民抗暴的思想,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上海方面为此专门写出为《阿诗玛》平反的材料呈报到各有关部门。但是,文化部还在犹豫。原因是有人仍担心《阿诗玛》会给青年人带来副作用。比方男主人公阿黑和阿诗玛相爱时,有“一天找你九十九遍”这样的歌词。
有人还担心影片将民间传说中阿黑和阿诗玛的兄妹关系改成爱情关系,是否有损于撒尼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是否有碍于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同志为此专程到阿诗玛的故乡——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奎山地区,请最有权威的评定者撒尼人鉴定。
不管文化部内部如何争论,广大读者感兴趣的是,《阿诗玛》要“走出仓库”了。十天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说,《阿诗玛》等一些影片将在元旦“恢复上映”。在此之前的12月27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庆祝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举行的电影酒会上,《阿诗玛》已正式“亮相”。到1979年元旦,《阿诗玛》终于回到了观众中间。(《都市文化报》2005年12月1日)
《阿诗玛》剧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