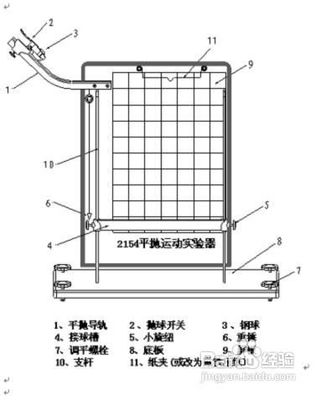兀然而立的双子峰 ——牟森与孟京辉的“实验戏剧”
文/ 辰风
八十年代中期戏剧滑向低谷,这块曾在“文革”结束后的岁月里繁盛一时的艺术领域渐渐退化为一片贫瘠而荒漠的地带,虽有耕者勤勉不辍,或偶有奇花突绽,但草木凋零的生态劣势始终难以彻底改观。可幸的是,在大的晦暗与艰困中,这里也依然上演了令人感怀的传奇,也出现过“拼命硬干的人”——由“探索戏剧”的立帜至“实验戏剧”的呐喊,一些改革先驱以失败的悲楚和成功的煊赫,以青春的血与痛,使曾经血脉瘀阻的戏剧肌体内悄然发生着变异、更新、再生……
寻望中国戏剧近一二十年蜿蜒而来的路径,迷朦中似乎还难以辨识所有的峰回路转、交错起伏,毕竟间隔尚短,犹在此山之中。但掉头望去,在那一段继往开来的特定时空中,最清晰耀目的是牟森与孟京辉这对“实验戏剧”双子峰——它在沉郁空阔的戏剧大地上兀然而立,交相辉映,不期然间已将自己的身影长长地投射于四野,隐隐地伸展向远方。
牟森、孟京辉皆非戏剧科班出身,而同为京城师范中文系的果实。他们是喧噪、亢进、虔诚、多思的80年代的典型产儿,与当时众多敏感叛逆、志怀高远的知识青年的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莫名地独钟戏剧,并日益为之痴狂疯魔。读书期间,牟森排演了外国名剧《课堂作文》、《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孟京辉编创了《西厢狂想曲》,戏剧白日梦初起之时两个人便得缘相识。牟森毕业后远赴西藏寻梦,梦碎后“流浪北京”,1986年,他成立了当代首个独立民间戏剧团体“蛙实验剧团”,孟京辉即是成员之一。1987年至1989年间,“蛙实验剧团”排演了尤涅斯库的《犀牛》、瑞士音乐戏剧《士兵的故事》、奥尼尔的《大神布朗》,孟京辉在前两部戏中分别扮演“让”与“说书人”。虽然资金窘迫,舞台粗陋,但演出被浓郁的理想主义氛围所包裹,被热切的创造梦想所照亮。牟森在《大神布朗》节目单上留下了一篇《蛙实验剧团致观众》,其中刻录着“实验戏剧”先行者的精神“原型”,呈现出“实验戏剧”源起时期真挚、纯粹、深广的精神基点——“亲爱的观众,请记住1989年1月28日这个普通的夜晚。在这个晚上,当您在这里观看我们的《大神布朗》首演的时候,在首都的另外一个舞台上,北京人艺的老艺术家们正在最后一次演出老舍先生的经典名剧《茶馆》。一代老艺术家创造过一个辉煌的戏剧时代,但是,生命总是处于轮回和更替之中,就像《茶馆》埋葬了一个旧时代,《大神布朗》孕育着一个伟大的梦想一样,更替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巧合,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狂妄而谦卑的艺术朝圣者们的“宣言”,当时看似自命不凡而脆弱动人的梦呓,谁知它却准确地预告了一种反叛传统、鲜活新异的戏剧形态不久之后的跃然而出。
198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硕士研究生——编者注)的孟京辉,逐渐开始走上一条与牟森所追求的彻底职业化、边缘化迥然有别的道路,但他携带着“蛙实验剧团”时期潜隐下来的那种对戏剧虔敬、苦恋、骚动的气质,搅动了一个时期的戏剧学院。他在那里是令前辈权威烦心皱眉的不安定分子,又是同学们勃勃雄心的有力煽动者,他排演了《送菜升降机》、《深夜动物园》、《秃头歌女》、《等待戈多》,还完成了广受欢迎的早期代表作《思凡·双下山》——这些受困于环境与财力的校园戏剧实验,才情烂漫,品质珍异,已全然展示出个性化的风格魅力与审美取向,其动人之处尤在于:艺术表现上毫不显青涩稚嫩,情绪上却溢满时代与青春的迷惘。
截止到新世纪来临前,孟京辉将实验的触角探向四面八方,接续完成了《阳台》、《我爱×××》、《放下你的鞭子·沃依采克》、《爱情蚂蚁》、《第十二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坏话一条街》、《恋爱的犀牛》、《盗版浮士德》等,每部作品均各有所得,各具风骚。他的作品皆具灵动写意、谐谑机趣、绮丽妩媚的面貌,其奔突喷涌的生命激情,自由驰骋的创造活力,张狂不羁的挑战姿态,深深撩动着那个流转多变时期的人心——这样一种既悦目怡情又悖于“常规”的戏剧,大多中国观众见所未见,舆论界既兴奋惊诧,又茫然失语。
1993年,牟森以“戏剧车间”的名义赫然再现。《彼岸·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对格洛托夫斯基、铃木忠志的戏剧观念首度成功引介,以高纯度的“贫困”与“形体”完成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戏剧表达;其后他创作了小剧场《零档案》、《与艾滋有关》、《红腓鱼》等,这些“脍炙人口”实验作品虽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巡演,反响甚烈,使牟森成为了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先锋戏剧的标志性人物,却从未在国内卖票商演,只是广泛流传于有限观者的口头与文字记载中。《零档案》被置于一个工厂车间的环境中,四周充斥着切割机,电焊机,鼓风机,钢条,噪声,火花,《与艾滋有关》则被一个建筑施工现场环绕,舞台是烟熏火燎的厨房内景,扮演自己的诗人于坚、舞蹈家金星、导演吴文光等从始至终忙着拌馅,擀皮,捏包子,炸丸子,两台戏中人物的“行动”就是完全旁若无人漫无边际的闲话、碎语……但这其中却超前地涉及到了一些日后显要的社会文化议题:成长,分裂,身份焦虑,语言歧义,艾滋病,农民工,同性恋……牟森将“反戏剧”的戏剧品质推到了极致,所有演出皆无传统性的文本故事,规定情境,人物塑造,刻意避开专业演员,模糊艺术与生活的分界,以即时即兴的方式尽力维护情绪的自然流程。
牟森的戏剧实验看似前卫激进、玄妙怪异,实则不过是一种返朴归真,极简为零——他试图以此去除所有的人为遮蔽,人性积垢,破除所有戏剧教条,表演积习,用彻底本真的裸露撕破观众的文明铠甲与固有观念,从而重获对人性的认知,重归戏剧的本原。作为卓有所成的戏剧革新者,牟森也同样具有将自己复归为“零”的勇气与坚执。1997年,牟森以《倾述》进行了一次不很成功的商业尝试后,舞台生涯再次戛然而止。其后他曾涉足一些新兴的职业领域——网络公司CEO,影视策划,也做过一些演出和活动的“剧目总监”、“文学顾问”等,期冀借此引入先进的戏剧管理理念和运行方式——与其说牟森的一些选择具有务实色彩,不如说始终未脱“探险”性质,他似乎总在以身试法地探寻着新的社会关系中艺术家的真实身份、真实价值,他仍是一个当代的“流浪艺人”,一个心神难安的漂泊者。
排演于1998年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可以视作孟京辉积微成著,最终赢得广泛社会认可的分界线,“实验戏剧”由此跃出地平线,从圈内小众扩散到知识大众,从逼仄的半地下空间登堂入室进驻庙宇正殿,从话语真空转为文化宠儿;1999年小剧场《恋爱的犀牛》在演出市场上大获成功,遂成孟京辉戏剧突击全面告捷的另一重要标志,时尚趣味、新潮元素的加入,使他的作品开始赢得年轻一代新型观众的广泛关注与钟爱。新世纪孟京辉推出了《臭虫》、《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琥珀》、《水月镜花》、《艳遇》、《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儿童剧《迷宫》、《魔山》等多类作品,他始终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更加注重形式美感的经营与技术手段的完善,作品格调更趋精巧沉静,情绪表现上火气渐褪。
作为实验戏剧的开拓者,牟森、孟京辉曾并蒂绽放,随着各自的成熟又花开两枝,但他们仍有着重要的同代互补关系。牟森的戏剧风格具有一种内在的仪式感和反省气质,质地开阔、严肃、坚硬,同时又隐藏着东突西撞的野性与哀恸——这样的戏剧气质其实与中国戏剧的传统精神与欣赏习性格格不入,一时又与新时代涌来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难以接轨,但它却前端性地预设了一项无可回避的“实验戏剧”标尺;孟京辉的戏剧风格尖利而柔软,强韧而融通,他能在戏内将唯美、伤感、暴力、讽刺、诗情、科技等纷杂丰富的元素凝合于一,也能在戏外将官方/民间,体制内/外,先锋/市场等颇为矛盾、甚或对峙的事物转化为和谐既济——这种罕见的能力使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创造了当代的现世戏剧奇迹,他以自己作品非凡的亲和力,一步步感召、征服、改变、创造着广大的戏剧观众,让原本保守单一的戏剧模式自然而然趋于崩解,使已呈萎缩之态的戏剧生存天地与传播空间大为拓展。与此同时,他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套作品包装、推广营销方式也日益成熟,成为一种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可资借鉴与探讨的有效操作范例。
“实验戏剧”不是对80年代探索戏剧的同构延续,它与一代艺术青年的生命历程血肉相连,与时代脉动息息相关,因此它不仅仅是一次戏剧观念、艺术修辞的革新,它也为一个时代留存了一份真实的精神记录,为那个时代抹下了一道耐人寻味的文化印痕。
中国“实验戏剧”的著名人物 牟森(右1993年)
1997年排练《爱情蚂蚁时》,孟京辉(右)与音乐人张广天讨论音乐创作问题
(转自《新剧本》2009年第4期编辑/工人李普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