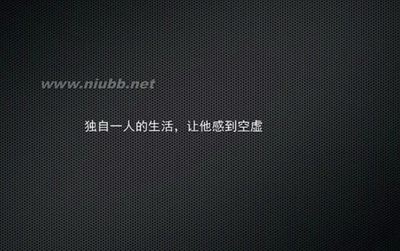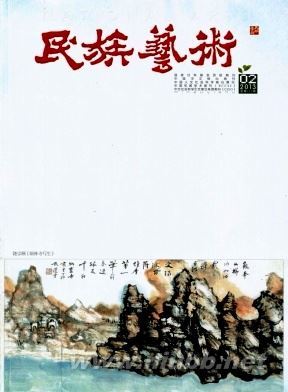第三节旁见侧出的“谤书”《史记》
李陵被俘,使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受到宫刑。刺激之下,司马迁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之说而提出“发愤著书”一说。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其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他若不因直言而获罪,亲朋好友无人假以援手,《史记》绝对不会写成今天这样。他太痛苦了,受宫刑之后,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借著史以抒一腔悲愤,于是《史记》成了最具个人魅力的正史,而《史记》也表现了司马迁的绝代史才及其旷世奇思。
用史实行褒贬的最大优势,就是用事实说话,无可辩驳,此其一。借史流传,千年不废,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翻案不易,此其二。史迁既敢直书,又擅婉笔,更创旁见侧出之法以塑造人物,快意褒贬。
史迁敢于直书其事,莫过《高祖本纪》。刘邦早年游手好闲,饮酒赖帐;起兵败逃之际,抛儿弃女;进入秦宫而欲住着不走;楚汉定约而又背盟……纯一流氓无赖。身为汉人而敢如此书写高祖,胆气不凡。便是现任皇帝汉武帝,他亦有所讥讽。
《史记》口诛笔伐的手段端的是厉害。
一、让人自我表白,现身说法
如《李斯列传》:(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栗,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又如《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到主父偃为了功名大事陷害,“大臣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他解释道:“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能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穷,故倒行暴施之。”这种人的下场是: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二、选取典型画面,突出人物
如写叔孙通的“爬”。陈胜起义,诸生主张发兵,秦二世向来不爱听什么情况危急之语,闻之不悦。叔孙通见此便说:“诸生言此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秦二世闻之大悦,立拜他为博士,赐帛二十匹。事后诸儒生责备他:“先生何言之谀也?”他说:“公不知也,我几脱于虎口。”此后,他不断换主,最后投靠刘邦。当时天下未定,他专门向刘邦推荐善斗之人,他的学生不满,问他:“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他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刘邦当了皇帝,诸将在皇宫里饮酒争功,行为粗鲁,场面混乱,不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叔孙通制成朝仪使刘邦“知为皇帝之贵”,于是被拜为太常,并赐金五百斤。这时他向刘邦推荐弟子,皆得为郎。他们个个喜出望外,称赞起老师叔孙通“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又如写万石君的“慎”。石奋,景帝之时,列为九卿,与四子皆官至二千石,号为万石君。
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孝景帝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仆䜣䜣如也,唯谨。上时赐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於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六匹马也要一一数之,恭谨如此,能不当官吗?
三、借助他人之口,一语道破
如借韩信之口评价项羽不过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
又如借汲黯之口讽刺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奉禄甚多,然而布被,此诈也。”
四、偶尔一笔带过,发人深省
如记石奋起家原因时写道:“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石奋的姐姐成了刘邦的女人,石奋随之入朝为官了。
又如介绍霍去病时,加上“大将军(卫青)姊子”五字,可见一代名将要想登上历史舞台也要靠裙带关系呀!
五、灵活运用虚词,以示其伪
司马迁在《封禅书》中有“若”、“盖”、“云”、“焉”、“矣”等虚词来讽刺汉武帝好鬼神之事是头脑发昏。如“若望见光云”,“(天子)获一角兽,若麟然”。
《史记》的“旁见侧出法”,又名“互见法”。此种写法既能突出人物的典型,又能避免述史的繁复。当然,也可用于口诛笔伐。《孝武本纪》中的汉武大帝近于昏君,而其雄才大略则散落于他人传纪当中。看来,司马迁对汉武帝颇有不满。《史记》又以世家记陈胜,以本纪记项羽,专为酷吏立传,专为游侠立传,史迁之意,还不明显吗?《史记》又以“太史公曰”直陈己见,此法后世多有采用。不过清人毕沅所言也有道理:“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斯为赘也。”
董卓伏诛,蔡邕在司徒王允侧,闻之惊叹。王允怒其悲董卓,乃下廷尉,欲杀之。邕自狱中上书曰,欲“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允不从,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遂诛蔡邕。(事见《后汉书•蔡邕传》)
《史记》用心褒贬,却是依事而成,岂可视为谤书――你敢干还怕别人写吗?道遇一屎,指而言之:“屎。”不料其勃然作色曰:“诽谤!”东汉班固认为《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恐是同行相忌之故。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赞:《汉书》体例,用于评论,类似于“太史公曰”)中说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但也承认《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至于《汉书》,行文谨严有法,更有史味,但读之不如《史记》动人,却也偶有富于情趣之处。王莽建新,而《汉书》未为立纪,而只立传,视其为乱臣贼子。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批评道:班固,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事事剽窃……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话说得重了。
东汉崇尚气节,南朝刘宋范晔编著《后汉书》时首创《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种列传。东汉党锢大兴,朝臣与宦官互相攻杀,其中张俭、范滂、李膺等人可谓高风亮节,对后世影响很大。《列女传》记“才行高秀者”,后世史书却改成了《烈女传》。
后世篡权夺位之事史不胜书,故而史传多用曲笔,自《三国志》开始,名为主动,实为被迫的“禅让”表演就多了起来。当然,被称为“秽史”的《魏书》不也传下来许多史料吗?虽然魏收放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种种手段用多了就已成了常规,一眼便可看破。如《隋书•文帝纪》中说文帝代周,沿历代国史旧例,叙九锡文,禅位诏,然后文帝三让才受。至于文帝被杨广杀掉,在此书中毫无痕迹。
一部“二十五史”,除了《史记》,多有曲笔。不过,字里行间还能看出许多眼泪和鲜血来。如《旧五代史》中的《梁书•太祖本纪》载朱温为了阻止李克用军,决滑城黄河堤,“为害滋甚”。又《梁书•王师范传》载朱温以旧怨,“遣人族师范于洛阳,先掘坑于第侧,乃告之。其弟师诲,兄师悦及儿侄二百口,咸尽戮焉。时使者宣诏讫,师范盛启宴席,令昆仲子弟列座,谓使者曰:‘死者人所不能免,况有罪乎!然予惧坑尸于下,少长失序,恐有愧于先人。’行酒之次,令少长依次于坑所受戮,人士痛之。”
如《宋史》立“奸臣传”,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民族败类、卖国奸臣皆在其中。
私人著史,也可助人了解真相。谈迁编撰《国榷》,记载明朝史实,毫不隐讳。明太祖晚年屠杀功臣,实录只写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事极简,无经过。而《国榷》却如实记载。如记朱元璋诛功臣傅友德事:
(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自杀。……自九江降,骁勇绝人,累立大功。以蓝玉诛,内惧。定远侯王弼谓:“上春秋高,行且旦夕尽我辈,宜自图。”上闻之,会冬宴,彻馔未尽,友德起。上责友德不敬,且曰:“召尔二子来!”友德出,卫士传语以首入。顷之,友德提二首至,上惊曰:“何忍也!”友德出匕首袖中,曰:“不过欲吾父子头耳!”遂自刎。上怒。分徙其家属于辽东、云南。
肉食者何其非人也,岂有一丝人性,难怪明朝末年叛臣峰起。这位怒摔《孟子》的狠人,不把臣子当人,打下这样的底,报应全落在崇祯身上了。
史册虽不能生诛其身,却可永标其名。夏贵,南宋大将,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宋元战争最为激烈的前线上,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投降元军,造成南宋全线溃败,接着临安陷落。夏贵以自己的无耻换得参知政事一职,按理《宋史》应有其传,可是元修《宋史》,以其是降官而未为立传。至明修《元史》,又以他投降元朝之后三年就死了而无事可记,亦未为立传。柯劭忞著《新元史》立《夏贵传》,让后人得知这个民族败类的所作所为。
著有《史通》的刘知几认为“史有三才:才(表达能力)、学(历史知识)、识(鉴别判断)”,除此之外,还要有“仗气直书,不避强御”的勇气。他在《曲笔》中说:“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对于“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之举,刘知几斥之为“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他自己就将《春秋》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义例,斥之为“爱憎由己”,“厚诬来世”。
奈何,秉笔直书又谈何容易?以前历史教科书大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卖国。后来,总算承认国民党也打日本鬼子了,不过还是“片面抗战”。目前,进步到了统称“中国军队”的地步了。--真可怜那些抗战老兵--想起一部电影名字:《老无所依》。
 爱华网
爱华网